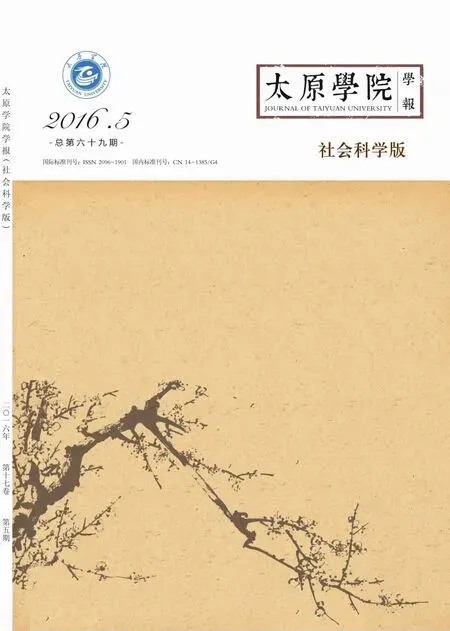元杂剧中母亲形象丰富性的成因探析
2016-02-10马兰
马 兰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系,安徽 淮北 235000)
元杂剧中母亲形象丰富性的成因探析
马 兰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管理系,安徽 淮北 235000)
元杂剧母亲形象塑造在宏观群体和微观个体上都具有丰富性,这缘于元杂剧演绎世俗生活的文体特点、元代社会中女性地位的提高与剧作家希望理想化的母亲积极承担起维持家庭伦理和社会政治伦理秩序责任的主观追求。
元杂剧;母亲形象;丰富性
翻开元之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会发现母亲形象零星散存于一些文学作品中,数量较少且人物形象不够丰满。元杂剧中出现了较大规模描写母亲形象的作品,有些人物形象也刻画得较为生动、丰满、传神。为什么会在元杂剧中大量出现如此丰富的母亲形象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文章主要从元杂剧的体制、元代较为开放的女性观念和剧作家的创作追求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母亲形象塑造的丰富性
(一)母亲形象宏观群体的丰富性
元杂剧中纷繁的母亲形象,可以说是构成了母亲形象画廊的“百母图”。以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戏曲》为例,作品中共出现了近百位不同角色的母亲形象。身份各异、性格迥异、不同命运的众多母亲形象交相辉映,充分显示了其丰富性的特点。从人物的身份来看,既有身份高贵的母亲,像《赵氏孤儿》中的晋国公主;又有身份低微的母亲,像《五侯宴》中的王大嫂。就人物的性格而言,既有刚烈的母亲,如《介子推》中的介子推母亲;又有温柔的母亲,如《王粲登楼》中的王母。从人物的品质来看,既有隐忍牺牲的母亲,像《灰阑记》中的张海棠;又有冷酷绝情的母亲,像《还牢末》中的萧娥。就人物的命运而言,既有被朝廷褒奖的母亲,如《剪发待宾》中的陶母;又有被凌迟处死的母亲,如《灰阑记》中的马大娘子。剧作中纷繁的母亲群像犹如一幅多彩的画廊,母亲形象宏观群体的丰富性不言而喻。
(二)母亲形象微观个体的丰富性
剧作者在塑造元杂剧中的单个母亲形象时,也不就其单一性格来刻画人物形象,而从多方面展开。剧中的一些母亲形象具有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即“大丰富”中的“小丰富”。如《五侯宴》中的王大嫂就是一位性格丰满的母亲。王大嫂为了埋殡夫婿,将自己典身于赵太公家做乳母。凶狠的赵太公暗地里将典身三年的文书偷换为卖身文书,企图终身使唤王大嫂。狠毒的赵太公嫌弃王大嫂的儿子王阿三与自己儿子争食,强说王大嫂将乳食都喂了王阿三,企图摔死他。王大嫂面对儿子的性命不保,她“哭啼啼扳住臂膊,泪慢慢的扯住衣服”[1]卷一,327,苦苦哀求赵太公饶儿子一命。最终,赵太公答应不摔死王阿三,但必须将他“抱将出去,随你丢了也得,与了人也得,我则眼里不要见他”[1]卷二,328。大雪天气,可怜的王大嫂抱着幼小的儿子慌慌张张地离开赵家。在路上,王大嫂抱着“仪容儿清秀,模样儿英杰”的儿子,内心百般不舍。
虽然爱子情深,但她又必须舍弃儿子。来到荒郊野外,她还是牵肠挂肚不忍心把孩儿舍弃,只能跌脚搥胸来表达内心的不舍。无人处,再一次给孩儿喂些乳食,准备将儿子放到官道旁边,用草遮盖住,唯恐大雪天气冻坏孩子。她一会将孩子放在地上,哭了一会离去,一会刚行数十步可又回来,抱起那孩子来又啼哭,在不忍离去又不得不离去的艰难抉择中,王大嫂的舐犊之情尽情地展示出来。十八年后,她在井边和儿子不期而遇的交谈中,虽已猜测到眼前的翩翩公子就是自己日夜思念的儿子,但也没有与他相认。她虽是出于自己身份低微的顾虑,但更多的是怕儿子为难、怕影响儿子的身份和前程。在王大嫂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宁肯自己牺牲也要成全儿子的忍辱负重、自我牺牲的贤良母亲形象。
又如《西厢记》中的崔夫人,也是一位性格丰满的母亲。护送丈夫灵柩回乡途中,暂居普救寺时,崔夫人察觉到莺莺“闲愁万种”,立即叮嘱红娘陪女儿到佛殿散心,可见对女儿呵护疼爱至极。被围之时,她为女儿的生命安全起见,果断地采纳联姻的灵活策略,拳拳爱女之心不言自明。大难之后,崔夫人又为女儿的长远幸福担忧,因为张生此时既无功名,也无门第,又无钱财。为了女儿,她不顾失信于人的名声,一再赖婚。后来,她发觉女儿与张生难舍难分之时,明智而变通地督促张生上京考取功名。此举既维护了崔家的士族地位,又保证了女儿的长远幸福。所以说,崔夫人不是一位固执的封建家长,而是一位疼爱女儿又精明变通的母亲。
二、元杂剧中母亲形象丰富性的成因
(一)元杂剧自身的因素
元杂剧盛行之前,诗词和散文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从篇幅看,诗词较为简短,不利于人物形象塑造;从内容上看,诗词主要用来抒发个人的情感,叙事写人不多;从观念上看,“诗言志”[2]1的观念一直影响和制约着诗人的文学创作,他们在内心深处也不屑于塑造人物形象。即使在他们笔下出现的人物形象,大多也是能够代表他们心声的人物形象,如:才气奇高的文人士子、激情高昂的军卒、行侠仗义的侠士、令人黯然销魂的美女弃妇之类。对于母亲这个形象,他们在作品中则罕有书写。
在“文以载道”的观念影响下的散文,偏重于文学的教化目的,更加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被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158的散文成为传播儒家之“道”的手段和工具。在“载道”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散文也较少涉及到家庭生活,因此局限于家庭生活的母亲,很难进入文人的视野。即使有,也是零星地提及,宣扬她们的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作为教化世人的道德典范。
历史发展到元代,社会和文学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这一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作为社会的重要阶层迅速地发展壮大,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有别于传统雅文学的通俗文学样式来表达思想和话语,迎合他们的审美需求。在对宋金文学继承、发展的基础上,元杂剧作为一种通俗文学迎合了市民阶层的审美需要。
在内容上,元杂剧多表现人们所熟悉的世俗生活。家庭生活是市民所熟悉的重要生活场景之一,也是市民阶层比较关心的话题。在以演绎世俗生活家长里短故事为主的元杂剧中,母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而也就很容易进入了杂剧和观众的关注视野。在一定意义上,母亲的存在是家庭生活的真正开始,是家庭生活的主轴。因而,杂剧中的母亲形象大量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形式上,元杂剧特殊的体制提供了人物活动的空间。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体制相比传统诗词,篇幅较长、空间较大。在相对宽松的篇幅和空间内,杂剧可以表现家庭生活中较多的人物形象,作家也可以挥洒笔墨、铺陈情节、刻画人物性格。这也为更多母亲角色进入杂剧、充分展现鲜明而生动的人物形象提供了舞台。元杂剧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为作家表现母亲形象提供了可能性。
(二)元代较为开放的女性观念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封建王朝中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这个崛起于北方山林草原之间、崇尚武力的游牧民族,其社会风气特别是女性观迥异于中原农耕文明。
在蒙古族的家庭中,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关系崇尚自由平等,女性在家务劳动和牧业生产中起到很大作用。她们不仅承担着日常的家务劳作、抚养教育下一代、照料服侍老人,而且还担负放牧驾车等牧业生产的重担。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蒙古女性同样可以骑马征战,从事与男性一样的劳动,“其俗,出师不以贵贱,多带妻孥而行,自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钱物之类,其妇女专管设立营帐、收卸鞍马、辎重、车驮等物事。”[3]169相对于受各种礼教约束而无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自身价值、处于依附地位的中原女性而言,蒙古女性在家庭中具有颇高的地位。成吉思汗时确立了后妃与大汗一样有固定的座序,蒙古皇后可以同朝接受朝见。在元朝历史上还出现过参与并把持朝政的皇后,像《元史·后妃列传》中记载了元世祖之后弘吉刺氏“性明敏,达于事机,国家初政,左右匡正,当时与有力焉”[4]2871。甚至在最雅的国家庙堂乐队中,元朝也允许女性参与,女性成员在庙堂乐队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入主中原后,这些原有的习俗使得元王朝的统治者对女性的态度显得比较开放,中原地区男尊女卑的观念得以松懈。忽必烈在位期间,得知火州城里生女孩多被撇在水里淹死的民情,便命令掌管畏兀儿事务的亦都护:“今已后女孩儿根底水里撇的人每,一半家财没官与军每者。”[5]211后来又在国家律例上禁止此类事情的发生,“诸生女溺死者,没其家财之半以劳军。守者为奴,即以为良。有司失举者,罪之”[6]2542在元朝的国家法律中,对于社会中买卖女子的陋习,也曾颁布有关法律大力禁止:“诸以女子典雇于人,既典雇人子女者,并禁止之。”[6]2542
粗犷而豪放的蒙古民族以武力统治中原后,中原地区原有的儒学思想伦理体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破坏。加之蒙古人松散的礼法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出于解构、重整的状态,这就有利于解放一直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所以相对于理学盛行的宋王朝时的女性,这一时期的女性地位有所上升。根据《元史》记载,元代有许多侍奉、孝敬母亲的孝子。即使是继子,也有许多诚恳笃实善待后母的先例,这也反映了女性在元代社会地位的提升。
在这些社会思想文化因素、固有的风俗观念和蒙古统治者律法规定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下,元代社会的女性观较前代社会有所进步。在此影响下,元汉文人对男尊女卑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进行了新的思考,对女性的态度也显得较为宽容,这在通俗文学的元杂剧中有了明显的反映。元杂剧中出现了大量女性的篇章,像渴盼真挚爱情婚姻的大家闺秀,沦落风尘、渴求从良的风尘女子,聪慧体贴的婢女,贤惠持家的妻子,无私忘我的母亲,都出现在元杂剧的舞台上。于是,作为女性角色之一,母亲形象受到关注,成为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剧作家主观创作的追求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元曲,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剧作家的创作动机完全是自然而然的。”[7]87母亲形象多出自元代知识分子之手,这些落魄的儒生在创作母亲形象时,难避将自身特殊的人生况味隐于其中,使得这一形象从潜在心理层面上体现出一种文人情感。因此,探究母亲形象丰富性的原因,很有必要从作家的创作动机方面考察这一形象在元杂剧批量出现的心理根源。
“学而优则仕”[8]202,一直是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到了“以弓马之力取天下”的元王朝,士阶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仕途理想骤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元朝自太宗九年(1237年)到延佑二年(1315年),取消科举考试长达近八十年,阻断了儒生习以为常仕进之途。他们失去了“四民之首”的崇高地位,“门第卑微,职位不振”[9]2,沦为社会下层并成为众人鄙弃的对象。
风月剧中的鸨母们对白衣书生多表现出嗤之以鼻的态度。《玉壶春》中李玉壶志得意满道:“寒窗下曾受十载苦功,他日必夺皇家富贵。”[1]卷五,455而在鸨母李氏眼中他这等“穷秀才”怎么也不如富有的商人甚舍。《曲江池》中李氏在女儿李亚仙面前骂郑元和“这个一千年一万世不能够发迹的穷乞丐”[1]卷三,518。《金线池》中李氏认为韩辅臣只是一个“一千年不长进”[1]卷一,115的穷书生,百般阻挠他和杜蕊娘的交往。《百花亭》中贺怜怜中意于“通晓诸子百家,博览古今典故”[1]卷六,506的风流书生王焕,却被鸨母贺妈妈赶走,将两人活活拆散。《对玉梳》中的荆楚臣,自认为“唾手功名自不难”[1]卷五,444,却被鸨母骂作“穷丑生”。鸨母眼中的白衣秀才可以说是当时文人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这些“一千年不得发迹的”书生们,在杂剧中赢得了才貌双全的上厅行首们的钟爱,并金榜题名。现实中他们所受的屈辱和无法诉说的悲苦,在剧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泄和补偿,鲜活到令人生厌的鸨母们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杂剧舞台。
元代文人对现实社会陷入礼崩乐坏的状态的不满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创作大量母亲形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自从宋室偏安东南一隅后,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已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到后来游牧于漠北草原的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进一步削弱了汉族在千百年中形成的伦理纲常,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规范失去了原有的效力。《元史》记载:“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而侈观听耳。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6]1663混乱的社会秩序使得维系人心的风化人伦,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动摇和破坏。家庭剧中恶母的现实存在和繁盛,或多或少也受到当时世风道德的影响,且加剧了本已混乱不堪的社会现状。在元杂剧中,贪婪自私(《老生儿》《合同文字》《薛苞认母》等)、杀父谋财(《灰阑记》《还牢末》《货郎旦》等)、虐待子女(《酷寒亭》《争报恩》)等种种丑恶的母亲们比比皆是。这些恶母的种种恶行可以说是元代社会人伦混乱、家庭秩序失衡的真实再现,她们的存在加速儒家传统道德的解体。虽然这些罪恶的母亲逃不过最终的惩罚,但这些惩罚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他人来完成的。她们的结局表现了作家在自我心理弱化后对恢复社会伦理纲常的强烈而曲折的愿望,实际也是身陷于现实卑微地位的作家虚幻的理想追求。
当前途一片漆黑,现实又不能给书生们提供坚强的后盾时,他们需要有胆识的人为他们指引道路。在受到世人鄙视时,他们希望有赏识千里马的伯乐来发现和宣扬自身的价值。面对社会伦理纲常受到严重冲击的社会现实,元代文人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作品中通过心仪的剧中人物予以反映、表现和重整。于是,剧作家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促成男性成就功名、实现理想、倡导儒家文化的母亲形象。
这些理想化的母亲积极承担起维持家庭伦理和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责任,成为剧中男性主人翁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儒家道德理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守寡多年的杨母(《救孝子》)独自养育两个孩子,同时身兼父职,教育儿子“忠于君能教化,孝于亲善治家,尊于师守礼法”[1]卷三,8。陶母(《剪发待宾》)靠“与人家缝联补绽,洗衣刮裳,觅来钱物”[1]卷五,60来支持儿子读书,盼望儿子“学成了诗云子曰,久以后忠孝双全”[1]卷五,62。陈母(《陈母教子》)宛如一个宣扬儒家文化的循循善诱的儒士,教导儿子们禀“仁义礼智”,习“恭俭温良”。苏母(《衣锦还乡》)在苏秦落魄回家之际,劝说丈夫留下孩儿,给处于人生低谷的苏秦以无尽的温暖。元杂剧中还有一些母亲为了维护捍卫国家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佘太君、长国姑(《谢金吾》)和介母(《介子推》)正是为了正义的政治目标而不遗余力乃至献出生命的英雄母亲。这些母亲承载着多重压力,她们以自身勤劳、坚韧、智慧、无私的优秀品质深深影响了儿子们,给予了儿子们无尽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她们自身所实践的人性向善的精神无疑也是救治社会的一剂良药。作家借助这些美好母亲形象重塑社会之人伦,希望这些母亲形象成为社会的道德模范和精神坐标,可见作家用心之良苦。
母亲形象在元杂剧中大量出现,除了有其客观因素外,主要是因为处于现实困境中的作家需要她们作为一种思想载体来曲折反映儒家文化的削弱、自身价值跌落所带来的心灵痛苦,也显示了他们因社会地位的巨变而引起的心理弱化,以及希望社会秩序得到恢复、理想得以实现的求助心态。
[1]王季思.全元戏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
[4]宋濂.元史·后妃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6.
[5]黄时鉴.通制条格:卷四[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6]宋濂.元史·邢法志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6:2542.
[7]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8]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钟嗣成.录鬼簿·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
[责任编辑:岳林海]
Cause Analysis of Richness of Mother Images in Yuan Drama
MA Lan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 Huaibe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uaibei 235000, China)
The mother images creation in Yuan Dynasty dramas has the feature of richness both in macro-masses and in micro-personality, which is because of the literary style for Yuan dramas to perform secular life, because of the raise of female position in Yuan Dynasty society, and because of the drama writers’ subjective pursuit that they hoped the ideal mothers to carry up the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the family ethics and the social political ethics.
Yuan drama;mother images;richness
2016-06-14
马兰(1981-),女,安徽濉溪人,淮北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及高职教育。
2096-1901(2016)05-0049-04
I207.3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