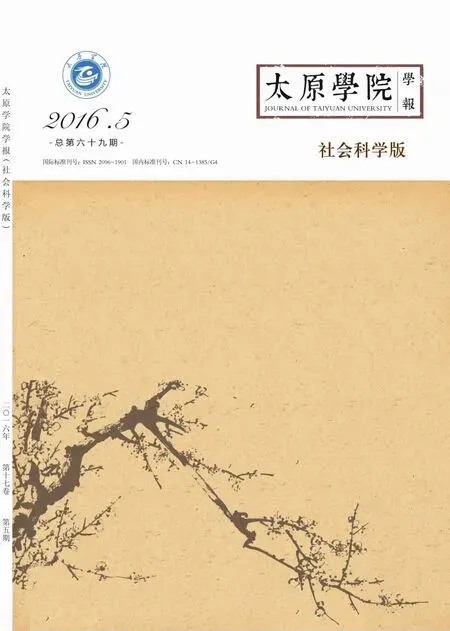试论唐宋诗转型的情感因素
2016-02-10任聪颖
任 聪 颖
(太原学院 中文系,山西 太原 030032)
试论唐宋诗转型的情感因素
任 聪 颖
(太原学院 中文系,山西 太原 030032)
南宋严羽标举宗唐抑宋的诗学理论,近人陈衍则在唐宋兼美的前提下强调宋诗的创新意义,二者观点相对立,但都未揭示出唐宋诗嬗变的原因。影响唐诗向宋诗转变的因素很多,唐宋人性情的差异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唐人的情感自然而浪漫,未经雕琢;宋人的情感冷静而深刻,经过理性的澄汰。唐人把自身作为情感的主体,喜怒都是为我;宋人于自我的关怀之外,更有对国家与民族的忠爱。唐人多无法排遣悲哀与绝望的情愫;宋人因情感中融合着理性,更容易发现超脱之径。唐宋诗风之转移与此不无关系。钱锺书更为强调诗人的性情气质,指出此乃诗歌风格的决定性因素,朝代之别的影响尚在其次。
唐诗;宋诗;性情;风格
严羽在南宋季世揭橥诗宗盛唐的旗帜,他在《沧浪诗话·诗辩四》中写道:“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又:“悟有深浅,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1]11,12此是看到了江西诗派和江湖诗派的流弊,而对其进行矫正与反拨之举。从另一个意义上说,他只有在认识到唐宋诗的不同之后,才能分辨其优劣,进而标举一方,批驳一方,以达到裨补时弊的目的。客观地讲,宋诗是宋代诗人力破唐诗余地的产物,有其长处,并不输于唐诗。在研阅《沧浪诗话》时,我们若能跳出孰优孰略的窠臼,公允地看待两代之诗,正可以窥测以严羽为代表的南宋后期诗人对唐宋诗转型的认识程度。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写道: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着到何在。其末流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
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1]25-26
此段文字要义有二,一是大体勾勒了宋代诗学发展的脉络,一是比照了唐宋诗艺术特征的某些不同之处。就发展过程来看,宋诗经历了规模中晚唐——自出己意——复效晚唐诗风这三个阶段。“自出己意以为诗”实际上就是宋诗力争摆脱唐诗之笼罩,建立自身独特品格的努力与尝试,而这种试验取得了成功。相比唐诗的“吟咏情性”“惟在兴趣”及含蓄蕴藉等艺术特点,宋诗更讲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重使事用典,诗境直白显豁。严羽对此甚为不满,称:“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1]25并主张“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1]26来扭转诗风,走上了文学复古的道路。但他只是从艺术形式上对唐宋两代的诗歌做了比较,其认知并不全面,而且并未就唐宋诗递变的原因作出诠释。时代与文化的因素在严羽的论诗体系中是缺失的。这虽是严羽之唐宋诗学理论的不足之处,但也为后来者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留下了甚为广阔的余地。
唐宋诗确实有着很多相异之处,但两者的区别并非判若冰炭,宋诗对唐诗存在明显的继承关系。陈衍就反对唐诗与宋诗的截然对立,提出“三元”*三元: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29);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1094)说以期沟通唐宋:
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君(沈曾植)谓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余言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宋人皆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庐陵、宛陵、东坡、临川、山谷、后山、放翁、诚斋,岑、高、李、杜、韩、孟、刘、白之变化也;简斋、止斋、沧浪、“四灵”,王、孟、韦、柳、贾岛、姚合之变化也。故开元、 元和者, 世所分唐、 宋人之枢斡也。若墨守旧说, 唐以后之诗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2]7
所谓“诗莫盛于三元”,乃唐宋诗都很兴盛,并驾齐驱之意。而三元皆“觅新世界”“开埠头”的本领,则说明唐宋诗都具有开辟创新的意义,宋诗价值不输于唐诗。在此情形下强分唐诗、宋诗的优劣,显然是难以落实的。陈衍并不讳言宋人对唐人诗法的继承,把宋诗的源头追溯到唐代开元、元和间,认为宋代诗人有取法盛唐者,有规模中晚唐者,然而他更强调宋诗在师古基础上的开新。“推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即是此意。推原陈衍之本心,正是要在唐宋并尊的前提下肯定宋诗,确认宋诗是唐诗的嗣响,标举宋诗突破唐诗,有所创新的成就,进而改变宋不如唐的偏见,缩小唐宋诗的差距,把宋诗提高到与唐诗同样的地位。陈衍的“三元”说比严羽宗唐抑宋的观点远为公允,但对宋诗如何继承唐诗并走向创新的问题未作详细的阐释,也未曾突显宋诗的特出之处。
宋人开一代诗风,从形式上看,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与唐诗重兴趣,重含蓄的气象大异。从风格上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3]36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唐诗成就卓著,宛如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耸立在宋人面前,盛极难继。宋诗欲有所创获,不得不另辟蹊径。就诗歌发展的规律来说,唐诗转型为宋诗必然如此,亦是自然如此。然而,从诗歌抒发情性的本质来看,唐宋诗发生嬗变,更是因为宋人的情感较唐人更为深刻,更为细腻,更为成熟之故。
首先,唐人的感情是自然生发的,真纯如赤子,是浪漫的激情;宋人的感情则受过人文精神的陶钧,冷静而深邃,充溢着智慧。宋代社会流行理学,主张压抑人的欲望,弘扬理性精神,这种环境不利于外向性情感的生成。强烈的感情都要经过思想的提炼与沉淀,成为一种融合着理性的思绪。李白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月歌》)诗中有人,以月为情媒,传递诗人对友人的深忱的思念之情。音韵流畅,语短情长。而杨万里笔下的明月更富理趣,诗人的情感隐而不彰:“才近中秋月已清,鸦青幕挂一团冰。忽然觉得今宵月,元不粘天独自行。”(《八月十二日夜诚斋望月》)有洒脱自然的心灵才可发现一无依傍的明月之美,而这种透脱的情怀需要理性的陶钧。徐复观先生说:“(宋人)把感情加上了理性,甚至是把感情加以理性化。但这种理性化乃是对感情的冷却澄汰,冷却由感情而来的冲动,澄汰去实际上是不相干的成分,以透视出所感的内容乃至所感的本质,并将其表现出来。此即所谓宋诗主意。‘意’是经过理性的澄汰而成为更凝敛坚实的感情。”[4]401然而不管是自然纯粹的情,还是凝练坚实的意,直接表达都是有难度的,需要借助意象来彰显。唐人的感情浩浩荡荡,浑无涯际,充斥着生命力,这种感情是难以用文字来表达的,故诗人习用自然意象来寄托此感情,其实是由于自然万物与充溢着生命力的情感相通。宋人的情感含蓄渊渟,整饬条畅,直抒而出则显枯涩板滞,故诗人常以人文意象、典故来深化情感,寄托人文情怀。邓小军教授指出:“宋诗的特质,是借助自然意象,发挥人文优势,以表现富于人文修养的思想感情。”[5]66此言道出了宋诗主意的真谛。宋诗多发议论,往往理趣盎然,而“议论也发自人文修养,是抒情的延伸与深化。”而这些思辨之诗多是关照现实人生的,其中“精彩的议论,可喜的理趣都是发自热爱生活的襟抱,闪耀着人生智慧的光彩。”[5]67关注现实人生的诗篇反映出凝敛情感之热烈的一面。
其次,唐代诗人多把自身作为情感的主体,喜怒歌哭,多是为己而发。宋朝诗人则在自我之外,重新发现了国家与民族的苦难,其胸怀更为广阔博大。唐诗抒发的情感主要是来自诗人对自身的关注。边塞从军之豪迈与哀怨,山水隐逸之适意与寂寥,随侍君王之自得与惶恐,诗酒联欢之忘忧与纵恣,羁旅远行之超脱和依恋,日徂月迈之绝望与无奈,这些都是唐人发之于心,系之于己而难以摆脱的情愫。只有杜甫这样才性健全的诗人对国家、对大众发生了人溺己溺的关切与同情,而有唐一代同调甚少,直至宋代才蔚为大观,这与宋朝人文教化之盛不无关系。唐人主体意识过于强烈,如李白的《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反映的是诗人目睹冶炼场景时新奇和兴奋的感觉,歌颂的是力之美,而没有涉及冶炼工人劳作的辛苦。宋代诗人则较能为平民代言,立意较深:“陶尽门前土,顶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梅尧臣《陶者》),“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张俞《蚕妇》)唐宋诗发生这一转型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徐复观先生认为:“宋承五代浩劫,在文化中发生了广大的理性反省,希望把漂浮沦没的人生价值重新树立起来,以再建人自身的地位。……宋代文人较唐代文人是更为理性的,在生活上是较为严肃的。”[4]401正因为如此,宋人比唐人多一份担当,多一份社会责任感,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也更为真挚。在北宋的和平时代,这种情怀表现为“正直刚强的品节与宽裕从容的涵养”[5]68,在南宋外敌入侵的危急关头,这种情怀又表现为可歌可泣的民族气节。另外,宋代士大夫与国家的关系比唐代士人更为紧密。唐代的门阀贵族仍有相当的势力,在唐人的心目中门第观念依然很盛。很多诗人出身于世家大族,对家族的情感甚于对国家的忠爱。而门阀势力在宋代早已消失殆尽,“宋代士人多出身平民,也以平民身份自甘。”是朝廷的科举制度给予他们参与政权的机会,长于闾巷的人生经历又使得他们对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有所了解。他们将这种对国家的忠爱、对民众的关怀写入诗中,就形成了与唐诗甚为不同的情感基调。
第三,在面对悲哀、绝望等负面情感的问题时,唐代诗人往往无法排遣,甚至难以直接面对,而宋代诗人则可以较为自如地将其化解,可见他们情感的成熟与健全。缪钺谓:“宋代国势之盛,远不及唐,外患频仍,仅谋自保,而因重用文人故,国内清晏,鲜悍将骄兵跋扈之祸,是以诗人之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3]50就此看来,宋人的生存环境并不乐观,忧患意识在其情感体系中理应占有很大比重。为何他们可以走出伤感的阴霾而唐人却不能?吉川幸次郎认为,汉魏六朝以来,“把人生视为绝望的,充满悲哀的存在的看法成了诗的基调。绝望,首先是由于视人为渺小的存在,并认为人处于超越其努力的命运的支配之下而产生的。进而把绝望或悲哀看作人所承受的最主要的命运。”[6]22唐代诗人继承了这种宿命论,所以在纵情声色,流连山水之余仍摆脱不了绝望与悲哀。宋朝诗人虽身处国家忧患的环境,但由于受到宋代哲学的影响,从两个方面超越了一己的哀感。一是与其关注人的生命,不如关注人的使命;二是与其关注个人之哀乐,不如为人类全体祝愿幸福。这种观念是“不视人为渺小存在的哲学”[6]25,一方面承认人生在世当有所为,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另一方面从个体生命有涯,而群体生命无限的角度破除了生命的虚无感。苏子所谓“抚古今于一瞬”“渺沧海之一粟”就是此意。而这种哲理正需重思尚意的宋人来发明,也只有感情受过理性澄汰者才能体会到。谪居崖州的李德裕诗中充塞着去国之感、失意之悲,沉重得无以复加:“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登崖州城作》)这百匝千遭的青山直是诗人心中重重叠叠的愁城的象征。苏轼也被放逐儋耳,但他在面对苦难时,心胸就开阔得多:“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是何等的从容洒脱!可见宋人在修养、气度方面超过唐人。从现实的角度看,科举制度的推广、文官制度的确立及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也是宋人比唐人更易乐观的原因。宋代参加科举考试而获荣升之阶的人数远胜于唐,宋朝又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士人的地位比唐代时要高,他们不仅俸禄优厚,而且可以顺利地参与国是。相比之下,唐朝士人或为谋仕进而汲汲奔走,或为生计而屈入武人幕府,志意蜷缩,襟抱不展,处境远不及宋人。另外,宋朝虽有因言获罪者,但绝未因言论与当政者相左而发生流血事件,可见当时政治之开明。宋朝的士大夫无生计之忧,有言论之便,更能以沉静之心灵感悟生命的真谛,此种情感反映到诗中,自然不是悲哀绝望的灰暗色调,而是一片乐观开朗的光风霁月。
以情感的不同来探究唐宋诗的差异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笼统地说,唐诗的感情近于天真浪漫,宋诗的感情近于老成凝重。诗歌可以以时代为分野、以唐宋来命名,天真浪漫、成熟凝重或他种情感却不具有时代性,是因人而异,非随时而迁的。钱锺书先生有言: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至殊。……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
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搀合古今者。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
诗分唐宋,本乎气质之殊,非仅出于时代之判,故旷世而可同调。[7]2-5
由此可见,“诗分唐宋”不是以朝代为绝对标准的划分,而是以个人气质性情以及诗歌风格不同为标准的。唐宋诗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两大范式,并未随着朝代的终结而成为历史名词。二者的风格亦多出于后世诗人之笔底,可知后人的性情气质多有暗合于唐宋前辈之处。而诗主性情之论也就有了历久弥新的意义。
[1]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陈衍.石遗室诗话[M].郑朝宗,石文英,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缪钺.论宋诗[C]//缪钺.诗词散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徐复观.宋诗特征试论[C]//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5]霍松林,邓小军.论宋诗[J].文史哲,1989 (2):66-71.
[6]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M].李庆,等,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7]钱锺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1.
[责任编辑:岳林海]
On Emotional Cause of Poetic Change from Tang Dynasty to Song Dynasty
REN Cong-y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Taiyuan University, Taiyuan 030032, China)
Yan Yu in South Song Dynasty insisted his poetic theory of valuing Tang poems and Looking down upon Song poems; while Chen Yan in recent years emphasizes the creative significance of Song poems in the premise that both are beautiful. But both the two opposite views did not reveal the cause of the change from Tang poems to Song poems. There are many factors influencing this change, but the temper difference betwee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s certainly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e temper of Tang people is natural and romantic without any carving; while Song people’s temper is calm and profound, experiencing rational processing. Tang people usually take themselves as the emotional main body; while Song people hold the loyal love to their country and nation beside the care for themselves. Tang people can not remove their sorrowful and hopeless emotion; while Song people can easily find the way to keep aloof since they merge some rationality in their emotion. All this is related with the poetic style change from Tang to Song. Qian Zhong-shu greatly stresses the emotional quality of a poet and thinks that it is the decisive factor of his poem styl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Dynasty difference is in the second place.
Tang poems; Song poems; emotion; style
2016-08-01
任聪颖(1985-),男,山西文水人,太原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2096-1901(2016)05-0041-04
I207.22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