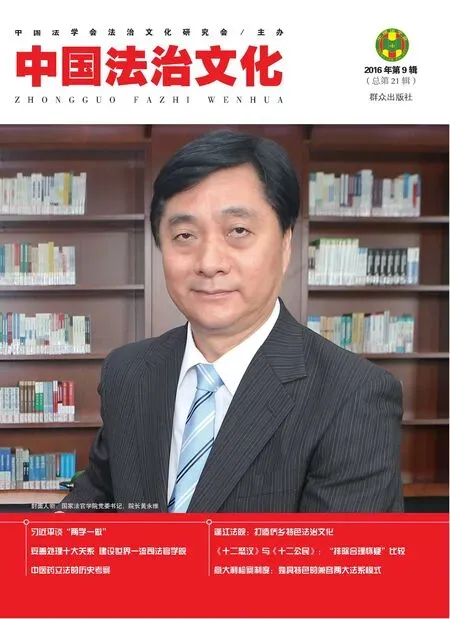《十二怒汉》与《十二公民》:“排除合理怀疑”比较
2016-02-10杨洁
文/杨洁
《十二怒汉》与《十二公民》:“排除合理怀疑”比较
文/杨洁
一、问题的提出
电影《十二怒汉》于1957年在美国上映,讲述了一个在贫民窟中长大的男孩被指控谋杀生父,十二位由各行各业人士组成的陪审团通过紧张激烈的辩论,最终达成男孩无罪的一致意见的故事。这部黑白电影没有精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对白,全部剧情均在一个密闭的房间中展开,但却以其揭示的人生百态、宣扬的法律程序和法律原则、体现的对生命的尊重成为法律电影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笔。2015年,这部经典的法律电影被中国青年导演徐昂进行了成功的本土化改编,以《十二公民》的新名称搬上中国的大屏幕,获得一片好评。由于中国并没有陪审团制度,徐昂将故事安置到政法大学的模拟法庭中,植入了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的因素,如将被审判的对象由“贫民窟少年”换成了“富二代”,将扭转局面的8号陪审员的职业由工程师改为检察官。此外,中国版还用字幕的形式交代了最终真正的杀人者被捉拿归案,达成了一个更完满的结局。
两版影片引人入胜的原因,在于十二位陪审员激烈的辩论过程。起初,根据已知的证据,即犯罪嫌疑人随身携带的刀具和两位目击证人的证词,这个案件几乎可以定案,只有8号陪审员认为证据不足,并最终说服了另外十一名陪审员,得出无罪结论。辩论和说服的过程体现了刑事案件中证据应用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排除合理怀疑”原则。这一原则是陪审团最终得出无罪结论的关键环节,也是这部电影能够展开的基础。“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本是英美法系的刑事审判原则,大陆法系在判案过程中也开始借鉴这一原则,尽管这一原则在不同法系里有着相似的要求,但在具体的适用过程中,由于适用这一原则的法官或陪审员来自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呈现出不同的内涵,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这种不同在两部电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十二怒汉》与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原则
(一)“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美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最早产生于英国,但随着美国司法过程的进步,美国逐渐成为应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典型。《十二怒汉》早在1957年就被搬上荧屏并颇受好评,足见“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美国刑事审判中的历史。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期开始,“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就得到了美国多数州以及整个联邦系统法院的认可,发展到今天,美国已将“排除合理怀疑”上升为“宪法原则”,要求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都予以遵守,在英美法系中具有“标杆”作用,对大陆法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美国的司法制度中存在四个基本标准,即优势证据,清晰且有力标准,清晰、不含糊且有力标准以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其中,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被认为是可以防止冤假错案发生的有效方式,是无罪推定的重要环节,体现了法律对人权、对生命的尊重。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布莱克斯通的名言更为流行:“与其让一个无罪的人受到惩罚,不如让十个有罪的人逃避惩罚。”①这也体现了“无罪推定”和“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美国刑法观念中的独特地位,而正是有了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十二怒汉》的剧情才能在美国的陪审团中展开,才能得到电影观众的认可。
(二)《十二怒汉》与美国“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思维逻辑
尽管美国已将“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纳为“宪法原则”,但对于这一原则的具体内涵以及适用方法,各州享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进行不同的解释。通过分析《十二怒汉》中的具体情节和辩论过程,我们可以总结出美国在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过程中存在下列思维逻辑:
1.道德确信
自1850年开始,“道德确信”成为解释“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标准,这一标准主导了美国一个世纪之久。“道德确信”与伦理道德无关,不是以价值判断取代客观事实,更不是靠法官或陪审团的个人好恶定案,而是类似于精确的数学计算结果的一种确信状态。从休谟开始,哲学家们认识到现实世界中的人类事务不同于精确的数学和逻辑计算,没有任何可以达到绝对确定状态的事情,刑事判决也一样。后来的洛克和威尔金斯等人认为,“道德确信”是最接近绝对确定状态的方式:“我想我可以断言,道德学是一般人类的固有的科学和职务。”②这种哲学思维明显影响了法学领域,所以有学者指出:“合理怀疑是基于理性和常理的怀疑。这种怀疑会使一个理性的人在作出决定时犹豫不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必须是具有这样的确信,即一个理性的人基于确信在处理他自己最重要的事务时不会犹豫不决。”③
随着法律实务的开展,“道德确信”原则受到了来自各方的质疑。“道德”和“理性”毕竟都是主观的判断,也很难保证法官和陪审团在作判决时是否保持了绝对的理性,这样,法律事实和客观真实之间就有了更大的鸿沟。但即便如此,道德确信依然是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第一步。在《十二怒汉》中,8号陪审员并非确定来自贫民窟的男孩不是杀人凶手,他之所以坚持让大家坐下来讨论,只是出于一个理性人的“道德确认”,认为“我们该给他一个机会”,所以起初他才不断质问“假设我们错了呢?”而急着赶时间的陪审员、毫无见地的富家子、歧视贫民的新贵族、性情暴躁的老警察,都没有达到一个理性人的标准。可见,只有内心存在“道德确信”,一个理性人才有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意识。
2.坚定信念
美国加州法院认为,合理怀疑是指“案件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对案件的所有证据进行全面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不能说他们对指控的事实已经坚定相信”。④俄亥俄州法院也有基本相同的规定。在《十二怒汉》中,只有8号陪审员没有根据已有证据形成被告有罪的坚定信念,所以才会出现大段类似的对白:“你真的觉得他是无辜的?”“我不知道。”“我想问你,你真的相信他的说辞?”“我不知道,或许我不相信。”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没有形成坚定信念的8号陪审员促成了男孩的无罪判决,而起初坚决认为男孩有罪的另外十一名陪审员却差点酿成大错。这说明,信念的牢固性与信念是否理性并不能等同,更危险的是,信念的坚定完全可能来自某种不理性的信仰和偏见,这样的坚定信念并不能达成真正的“排除合理怀疑”,这种危险在儿子离家出走的3号陪审员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对儿子的恨投射到了被告身上,产生了一种来自于“移情”的偏见。所以,有学者指出:“信念本身对于认定犯罪而言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它是建立在证据之上并通过有理有据、经得起质疑的推理而形成的。”⑤
3.给出理由的怀疑
在1972年的杰克逊案件中,美国初审法院指出排除合理怀疑必须是“一种建立在一定理由基础上的怀疑”,美国学者杰西卡·N.科恩也认为“合理怀疑不是一种幻想的怀疑,不能是一种仅仅可能的怀疑,不能是一种怪诞的怀疑,不能是一种推测。”⑥“给出理由的怀疑”成为“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一种极为普遍的解释方法,要求法官和陪审团在决定应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时必须有证据、程序等方面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十二怒汉》中,8号陪审员先后说服其他陪审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利用证据方面的瑕疵逐步使其他陪审员产生有理由的怀疑的过程。在证明了并不是只有男孩才有类似的作案工具,且以男孩与被害人的身高差看来,刀口的方向不对,以及老人和女人的证词并不可靠之后,陪审员们才越来越产生了合理的怀疑,最终认为判决男孩为杀人凶手证据不足。
但是,用“给出理由的怀疑”界定“排除合理怀疑”也有不恰当之处。首先,这样的解释其实是一种同语反复,相当于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其次,要求陪审员一定要为自己的怀疑给出理由,可能会使陪审员产生不适当的压力,甚至产生恐惧感而不将自己的怀疑说出来。例如,在《十二怒汉》中,8号陪审员起初并不确定男孩无罪,他的怀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这个十八岁生命的尊重和同情,所以他才说:“我不知道,或许那是没有原因的,这孩子老是被踢来踢去。他在贫民窟出生,九岁时母亲就过世了,他在孤儿院待过一年半,当时他父亲因为伪造文书罪入狱,他是先天不良,他是个充满愤怒的野孩子,为什么?因为每天都有人打他,他过了悲惨的十八年,我觉得我们该给他一个机会。”可见,“给出理由的怀疑”这一标准未免过于严苛,甚至违背了“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初衷。
4.其他进路
除此之外,美国还有学者用“拟制第三人”标准、社会共同意识标准乃至“无须解释”来回应“排除合理怀疑”原则,这些标准在《十二怒汉》中也有所体现,如8号陪审员一直强调“我一直让自己站在那孩子的角度来想……”这是“拟制第三人”标准的体现,即站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思考;而各位陪审员通过重现作为证人的跛脚老人听到声音下楼观察案发现场等的场景,发现了老人证词的不真实性,这其实是通过场景重现使各位陪审员达到一种共同意识,即老人不可能在十五秒内下床走到门口看到案发现场的景象。可见,对于什么是“排除合理怀疑”,不同的法院在不同的案件中,存在多种解释进路和思维方式,或许正因为此,美国才有多个州的上诉法院坚持要求法官不得向陪审团解释何为“排除合理怀疑”。
三、《十二公民》与“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中国路线图
(一)“排除合理怀疑”原则与中国的证据证明标准
如前所述,传统的中国刑法实行的是“有罪推定”原则,并不存在“排除合理怀疑”的观念,因而导致了不少冤假错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遵循大陆法系的程序和原则,并未正式将“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引入法律实务中,直到2011年8月31日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这也标志着“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中国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实务中的转机,被视为未来刑事证明标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但是,我国对“排除合理怀疑”原则显然比美国更为审慎,从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来看,我国只是将这一原则看作是达成“证据确实、充分”标准的一个环节和依据,并未将其上升到单独的证据证明标准,更未将其上升到宪法原则的高度。目前,我国的刑事证据法依然主要是从六个方面强化证明标准的客观性,即“每一案件事实都有证据证明”、“单个证据具备证明力和证据能力”、“证据相互印证”、“全案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直接证据得到其他证据的补强”、“结论的唯一性和排他性”。⑦所以,在中国的司法实务中,“排除合理怀疑”更多的是以一种隐性标准存在,“一是进入地方证据规定的文本之中,上升为‘地方性规则’;二是作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潜规则,发挥了实际证明标准的作用。”⑧《十二公民》的导演徐昂将电影展开的场景从真实的法庭搬到政法大学中的模拟法庭,除了我国没有陪审团制度之外,也可以解释为在我国的法庭中,已有证据可能已经足以使法官作出有罪判决,“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可能并无用武之地。
(二)《十二公民》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十二公民》的辩论过程几乎遵循了与《十二怒汉》一致的套路,都是8号陪审员逐个说服其他陪审员,作案工具、女人和老人的证词被推翻的过程。因此,对道德确信、坚定信念等排除合理怀疑的“美式原则”也有所体现。除了让观众更形象地了解到陪审团制度的运行程序,体会到“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内涵之外,作为法理学研究的典型,我们应当在更深入的层面理解“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1.“排除合理怀疑”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则的关系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排除合理怀疑”并非独立的刑事证明原则,而是作为质疑意见的根据,应用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则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字面意思应当是法官对待证明事实的认定达到了百分之百的确信,但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总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原则是以理想目标代替了可操作性的证明标准,更多的是一种指导性原则,是一种司法实践需要达到但又达不到的目标,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种证明标准“更具有证明目标的属性,而难以发挥‘证明标准’的功能,因此,那些将这一证明标准予以具体化的立法努力,才具有了一种天然的局限性”。⑨从《十二公民》呈现的效果来看,“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局限性。8号陪审员会对富二代杀人的结论产生怀疑,说明这一结论并没有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而后来的一系列被推翻的证据,也说明这种合理怀疑产生了积极的后果。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之下纳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而不把“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单独的原则,既吸收了英美法系的优势,又避免了单一的“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2.警惕“排除合理怀疑”中的偏见思维
《十二公民》将被告的身份由贫民窟男孩改为富二代,可以说是一种贴近中国社会现实的改编。不同于美国存在的种族歧视、出身歧视等,当前的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仇富心理,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富二代是一群无所事事、狂妄自大的纨绔子弟,因而在与富二代有关的案件中,中国人会不自觉地偏向于富二代的对立一方,药家鑫案和李天一案就是很好的说明。这是中美不同的偏见思维,而这种偏见会极大地影响甚至左右刑事案件的审判。如果把《十二公民》中的被告换成来自贫困地区的少年,8号陪审员说服其他人的难度可能会减小很多,因为中国人对来自贫困地区的孩子总是多一份同情与谅解,十二位陪审员就更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为这样的被告争取机会,更容易排除“合理怀疑”,如此一来,他们的辩论可能就不会太激烈,而少了辩论带来的戏剧冲突,这部电影就少了太多色彩。
3.“排除合理怀疑”与正义的冲突
法律中的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符合性。“排除合理怀疑”对刑事案件的证据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定罪的难度,这就容易帮助凶手逍遥法外,产生法律与正义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在“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和法律程序观念影响深远的英美法系会得到舆论的支持与理解,辛普森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这种程序与正义的冲突在爱憎更为分明的中国人眼中却常常是难以理解的,可能会引来舆论的质疑。这大概也是导演徐昂在《十二公民》的最后,说明了最终真凶被捉拿归案的结果的原因,这更符合中国市场的主旋律,也更符合中国观众的口味。
四、《十二怒汉》与《十二公民》的启示
从两部电影的分析看来,美国刑事证明标准中的“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在内涵、效果等方面存在着争议和缺陷,但总体来说,这一原则的引入利大于弊。首先,将“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性要素注入到“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化要求中,确立了主客观相结合的证明标准模式,比原有的证明规则更为科学合理,更有实用性;其次,当前中国的刑事案件存在着证据不合理、不合程序使用,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等问题,“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引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启发办案人员注重程序、重视生命和人权等;最后,“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确实在界定和应用上存在一些争议,但“对于‘合理怀疑’的内涵和形式,人们只要诉诸于经验、理性和良心,就不难达成共识”⑩。具体来说,在两部电影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法官和陪审员应具备的素质
在两部电影中,冷静、理性的8号陪审员是扭转局面的关键,而其他陪审员则差点将一个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这说明法官或陪审员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素质将是十分危险的。具体来说,一个合格的陪审员或法官应当处理好理性与感性的关系,杜绝偏见,不放过任何证据的任何一个细节,而且有敢于将自己的合理怀疑明确表示出来的勇气,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判案过程中的主观性问题,利用现有证据得出相对正义的结论。
2.识别“排除合理怀疑”中的影响因素
从对《十二公民》和《十二怒汉》的对比与分析中,不难看出,“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适用有多种影响因素。如中美不同文化特质中生成的不同的偏见思维、不同意见的陪审员形成的多数人的暴力、个人的不同生活经历等,这些因素都会阻碍陪审员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这就要求法官和陪审员能理性地识别这些影响因素,并最大限度地避免这些因素的影响。
3.实现“排除合理怀疑”从主观到客观的转变
《十二公民》和《十二怒汉》实际上展现了“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两个过程。起初,8号陪审员的怀疑可以说是完全主观的,他只是认为既然组成了陪审团,就应当行使陪审团的职责,而他为被告争取机会,也是来自于对生命的尊重和同情。此时,他的怀疑可以说是消极的,这种怀疑的根据来自于人的良心。但是,随着刀具、女人和老人的证词被否决,陪审团的怀疑逐渐客观化,成为积极的怀疑,这样的怀疑有了证据、一般性知识、常识等方面的可靠来源。这启示我们,“排除合理怀疑”不是一个完全主观的、毫无根据的瞬间决定,而是一个既有主观又有客观依据的过程,我们应当注重这种从主观到客观的转变,这样的怀疑才是“合理怀疑”。
(本文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法学理论专业法治文化方向研究生)
① 转引自赖早兴:《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② 洛克:《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43页。
③ 转引自赖早兴:《美国刑事诉讼中的“排除合理怀疑”》,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④ 陈永生:《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
⑤ 李昌盛:《反思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3年春季卷)》2013年4月。
⑥ 陈永生:《排除合理怀疑及其在西方面临的挑战》,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
⑦ 陈瑞华:《刑事证明标准中主客观要素的关系》,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
⑧ 李训虎:《“排除合理怀疑”的中国叙事》,载《法学家》2012年第5期。
⑨ 陈瑞华:《刑事证明标准中主客观要素的关系》,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
⑩ 陈瑞华:《刑事证明标准中主客观要素的关系》,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