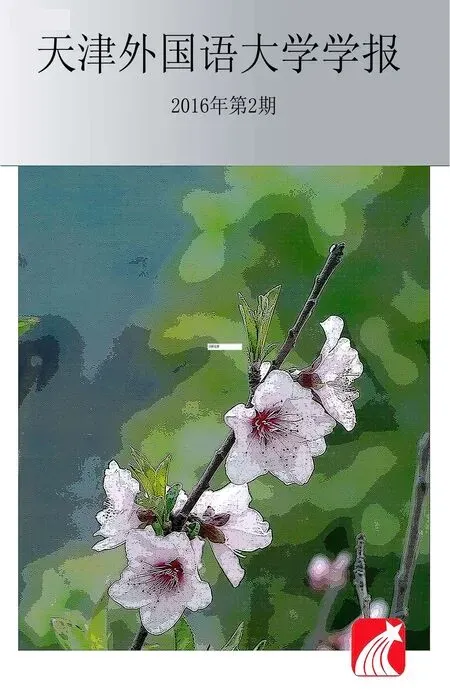论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的梦境描写
2016-02-10张能泉
张能泉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永州 425199)
论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的梦境描写
张能泉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永州 425199)
“一带一路”沿线语言文化研究
编者按: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沿线国家分布在亚洲、中东欧、独联体和非洲,涉及语言包括英语、日语、俄语、朝鲜语(韩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斯瓦希里语、印度尼西亚语、缅甸语、马来语,等等。“‘一带一路’沿线语言文化研究”栏目将为研究这些国家的语言及其文学文化提供一个发表成果的平台,助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世界和平发展。欢迎赐稿。
谷崎润一郎在其短篇小说中运用梦境描写来揭示作品主题与状写人物心理。其梦境描写的审美价值在于打破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在细腻真实与奇异神秘中展开人物心理,揭示人物潜在意识和心理历程,表现作品的深层主题,使作品在展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方面获得一种形象、逼真的艺术效果。梦境描写成为谷崎深化作品的思想内涵与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艺术手段。
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梦境描写;艺术功能
一、引言
众所周知,梦是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由于它与人类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人类认知自我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人类自古以来就表现出对梦的浓厚兴趣,并促使他们运用语言文字来描述各种离奇、怪诞的梦境。由此可见,梦与文学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关系。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反映,梦往往是作家在其文学创作过程中揭示人物心理活动,展现人物心路历程的一种重要途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就曾对文学创作与梦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研究。他认为作家从事文学创作就如同白日梦一样,都是为了满足创作主体那种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因而,“某个目光犀利又富有创造力的作家,对其转变过程具有分析的深刻认识,可以从相反的方向,将其富有想象的作品回溯到一个梦境”(Freud,2008:515)。事实上,许多作家都善于在其文学创作中描写梦境。虽然这其中的缘由非常复杂,但是由于梦境具有非现实的艺术效果,它可以拉近读者与人物心理距离,使读者走进人物的梦境中感知它的内心世界,为揭示人物的潜在心理和展示人物的心路历程开辟了新的艺术领域。近年来,谷崎润一郎(Junichirou Tanizaki,1886-1965)研究逐渐成为国内日本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评论家们或从主题学的角度阐述其文学的耽美主题,如赵仲明的《唯美主义:谷崎润一郎的文学世界》认为谷崎对美的执着追求和完美表现不仅延续了日本传统文学中的真实观,而且还以艺术的方式呈现了人的本能欲望,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或从比较文学角度分析其文学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如曾真的《茅盾与谷崎文学的女性审美意识比较》通过比较矛盾和谷崎在其文学创作中对女性身体的书写异同,指出各自不同的创作原则让他们指向两种不同的创作方向。或从译介学角度解读述其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介绍情况。如张能泉的《谷崎润一郎国内译介与研究评述》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谷崎文学在中国文坛的译介情况。毋庸置疑,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国内谷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却很少涉及谷崎短篇小说的梦境描写。即使有也仅是蜻蜓点水式的一笔带过,缺乏相对深入的研究。虽说运用梦境来揭示作品主题,呈现人物心理并不是谷崎的独创之举,但是其短篇小说创作却表现出大量的梦境描写。因而,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谷崎的短篇小说,研究其作品的梦境描写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谷崎短篇小说梦境描写的解读,阐述其梦境描写的审美价值在于打破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在细腻真实与奇异神秘中展开人物心理,揭示作品的深层主题,以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谷崎及其短篇小说。
二、揭示作品的深层主题
作为人类潜在心理的一种反映,梦不仅是人类认知自我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作家展现作品深层主题的重要途径。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2001:33)对此认为:“梦是我们心灵的最低级和最不理性的表达,也是它的最富有和最有价值的功能表达。”因此,梦不是一种空穴来风、毫无意义的精神现象,而是展示人类心理活动,表达人类真情实感的有效方式。当作家们将这种独特的心理现象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的时候,梦境描写便成为作家们揭示作品深层主题的重要手段,因为文学作品中的梦境描写既有益于袒露人物的性情与意念,又有益于展现人物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为读者深刻理解作品的人物形象,把握作品的深层主题提供有利的条件。其中,日本耽美派代表作家谷崎就善于在其短篇小说创作中运用梦境描写来隐含与影射人物丰富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作品的深层主题。《异端者的悲哀》(異端の悲しみ)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小说一开篇就向读者详细地描述了主人公章三郎午睡时的梦境。在这里,章三郎梦见了一只白色的鸟儿正在用翅膀扑打他的脸颊。虽然一开始他因羽翼贴近他的鼻尖,使他感觉呼吸不畅,但很快他发现这只美丽的白鸟可以使他“在灵魂里回味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愉悦”。随后,睡梦中浮现的鸟儿变成一个妖艳的女子。鸟儿的形状逐渐演绎成从黑暗深处喷涌出来如同肥皂泡一样的美妙气泡。最大的气泡表面“不知何时清晰地映现出一个极其奇异的躶体美女”。这位妙龄少女“一边如随风袅娜的轻烟般翩翩起舞,一边展示着各种各样的媚态”(異端の悲しみ:380)。正当章三郎沉浸在喜悦之中时,美梦随即就消失了。当章三郎睁开睡眼惺忪的双眼,一种无名的惆怅和伤感在其内心油然而生。他试图再次闭上眼睛,重现这稍纵即逝的美丽幻影,却深感无能无力。最后,章三郎为此发出了一声感叹,“睡梦中景象是如此美丽,为何自己所处的这个人世却是如此的肮脏不堪!”(異端の悲しみ:380)
谷崎在此利用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梦境描写揭示了作品深层的主题。具体来说,谷崎笔下的梦境描写表面上给读者一种离奇、诡异的感觉,但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人物内心深处的潜在思想,揭示了作品的深层主题。章三郎梦中出现的白鸟虽然因其羽翼黏覆在他的鼻子上,让其感觉呼吸有些不畅,但很快这种白色的鸟儿幻化为无数美丽的汽泡,并且在最大的气泡表面出现了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影姿,其展现的姿态赋予了女子一种无与伦比的魅力。这种源于女性官能之美的魅力如磁铁般强烈地吸引着章三郎,使他为之迷恋和倾倒。然而,梦幻中白鸟变成了美妙多姿的女性,在成为章三郎的审美对象之后,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即使章三郎试图多次努力重回梦境,仍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之下,他接连发出了人生无常,命运弄人的感叹。那么,梦境描写中的白鸟有何寓意?它对揭示作品深层主题又有何作用?为较好地解答上述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认清小说在谷崎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根据谷崎在散文《〈异端者的悲哀〉前言》(異端の悲しみはしがき)中记载,这篇短篇小说不仅是他唯一的一篇自传体小说,也是为纪念刚刚离世的母亲而创作的短篇小说。“就如今作为美好的纪念,我把这篇小说公之于众。对于将儿子培养成艺术家的母亲来说,作为母亲生前的回忆形式,我把这篇故事奉献出来。”因而,该小说“将我当时心中真实的情绪,尽一切可能地、没有任何滞碍地、毫无遮掩和坦诚直率地描绘了出来。就此意味而言,只有这一篇才是我唯一的告白书”(谷崎潤一郎,1975:23-24)。由此可见,谷崎创作小说的初衷在于表达对母亲的追忆之情。作品中的章三郎是一位典型的神经质患者,他既敏感又多疑,既自负又好强。在一场因唱机而引起的家庭风波中,为了向家人证明自己有能力处理母亲从表姐阿叶处借来的唱机,他不惜怒目相向,冒犯父亲,欺负妹妹,与他们发生激烈的争吵。章三郎这种背德性行为让深爱他的母亲伤心不已,悲叹不绝。面对母亲种种痛心的表情,章三郎对自己卑鄙无耻的行为产生了厌恶之情。虽然作品中的章三郎至始至终都没有真正悔改,但他对母亲的态度与对父亲和妹妹有着明显的差别。如果说对父亲与妹妹的冒犯是一种叛逆,那么对母亲的行为则是一种顺从。母亲就如同梦中的白鸟,纯洁而又善良,是一种令其倾心之美的象征。这只白色的鸟儿围绕在他的身旁,时而轻抚着他的面颊,时而爱抚着他的鼻梁。变成少女之后,她身上散发出来美与媚让他痴迷和神往。因此,梦境中出现的白色的鸟儿形象地呈现了章三郎潜在的恋母心理,艺术性地揭示了作品恋母这个深层主题。梦境虽然具有浓郁的非理性色彩,但是梦境中出现的意象却具有丰富的意义,尤其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梦境意象无不体现和灌注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情感和审美理想。因而,作为一种感性的审美表现形式,梦意象所呈现的内涵不仅是作家精心构思的结果,也是作家主观情感流露的重要渠道。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梦境主要以意象进行思维。”(Freud,2008:46)梦境中的意象具有形象性,它能将丰富的思想寄寓其中。章三郎梦中出现的白鸟就如荣格所言的阿尼马一样将其心中最美的女性特点展现出来,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
这种在梦境中表露人物恋母心理,揭示作品恋母主题的短篇小说除《异端者的悲哀》之外,《恋母记》(母を恋ふる記)也是这方面的代表性小说。该作是谷崎为悼念去世两年的母亲而创作的优秀短篇小说。小说全篇采用梦境描写的形式书写“我”对母亲的深深眷念和真切思慕。整个作品宛如一首抒情小诗,情感真挚,感人肺腑,可谓是谷崎恋母小说的标志性作品。
小说从头到尾都向读者讲述寻梦者“我”在寻母过程中的种种遭遇。作品中的“我”是 一位年仅七岁的少年。有一次,“我”在朦胧的月夜下独自走在街道上去寻找自己的母亲。在历经几番挫折与失望之后,“我”忽然听到从远处传来的一种好像是三味线的奇妙声音。听闻此音,“我”心头涌动,思绪万千,儿时与母亲美好的回忆瞬间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寻音而去,只见一位头戴草笠的年轻女子,手拿三味线走在“我”的前面。这位沐浴在月色下的年轻女子风韵楚楚,格外动人。尤其是她的脸型、肤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突然,女子不知为何驻足不前,只是把低着的头抬起来仰望空中的明月。她那白色的脸颊好像发出了银光,同海面上的潮水一样,只见她娇嫩的脸颊上一闪一闪地滚落下来的东西好像荷叶滑落的露珠似的。原来这位落泪的女子正是“我”苦苦寻找的母亲,她紧紧地将“我”抱入怀中,甜美的乳香将“我”包围着。“我突然醒来。枕头被泪水浸湿了,可见我真的在梦中哭了。我今年三十四岁,而在前年的夏天,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当这一想法涌上心际时,新的眼泪又落到了枕头上。”(母を恋ふる記:219)
小说以“我”寻母的精神历程入手,在梦境描写中将“我”对母亲的思念之情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弗洛伊德认为梦境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心理活动,相反它是一种充满含义的心理行为,它由“显在的形式”与“潜在的内容”两部分构成。梦境的根本源泉在于人们某一愿望的满足与实现。因而,“梦的内容在于愿望的达成,其动机在于某种愿望,梦始终是一种渴望满足的欲望。”(Freud,2008:46)虽然谷崎在此采用的是梦境的显在形式,既身处梦境中的“我”能够意识到梦境的存在,但是这种显在的梦境形式却能形象地传达人物的潜在意识。为了传达人物浓郁的恋母情感,谷崎摒弃了传统小说对人物故事情节的表层式描写,而是采用梦境描写的形式,状写人物的内心活动,在梦幻中传递人物的思想与情感。小说中的“我”既是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又是叙述者。“我”的所作所为不仅体现了人物的意志,也表现了叙述者的意愿。对母亲的思念主导了“我”的一切言行,家道中落让“我”想起了为家操劳的母亲;见到生火做饭的老妪误认为是自己的母亲;偶遇弹奏三味线的母亲却又错认为是莫不相识的阿姨。梦境叙述记载了“我”对母亲的深深眷念之情,引导读者跟随“我”梦母的历程走进人物深邃的内心世界,感受和体验人物内心深处浓郁的恋母心理。梦境中具体的细节和场景描写将“我”思母的渴望刻画得逼真传神。因此,梦境描写在此将人物潜在的意识演绎为可视可感的形象,让人物的情感、意愿与欲望以其生动、具体的艺术方式在梦境中得到最佳的展现,使作品的恋母主题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效果和艺术感染力。
由此可见,梦境描写不仅是读者进入谷崎文学世界的重要媒介,也是理解其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契机。谷崎笔下的梦境描写不仅揭示和深化了作品的深层主题,而且也艺术性地传达了作者的真情实感。其独特的人生阅历与生命体验使谷崎钟情于在作品中借助梦境描写来表达其浓郁的恋母意识。1917年5月14日,年仅54岁的母亲因病离世后,谷崎便经常在梦境中浮现出母亲的形象。“自己心中一直描绘的只是母亲的幻影。自己幼小心中的母亲形象不是上了年纪的女人,而是永恒美的女性。”(谷崎潤一郎,1974:31)“我时常浮现出已故母亲的脸,那不是她临终时的脸,是何时我也说不清了,大概是我七八岁孩提时代吧。年轻美丽的母亲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我母亲可是一个美人啊!这时的我感到了一种最为崇高的美。”(谷崎潤一郎,1975:124)因此,无论是《异端者的悲哀》,还是《恋母记》都以梦境描写的形式来寄托和书写谷崎浓郁的恋母情结,进而孕育其作品浓厚的女性崇拜思想。
三、展示人物的心路历程
梦境描写在谷崎短篇小说中不仅可以揭示作品的深层主题,还可以展示人物的心路历程,描绘人物的精神状态。《飓风》(飓風)中的直彦就是通过梦境的形式呈现其浓郁的官能意识。1911年,谷崎应《三田文学》主将永井荷风的约稿,创作了一篇描写青年画家直彦因沉溺于女性官能生活而猝死在青楼女子怀里的短篇小说,这便是日后被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飓风》。小说刊载于明治四十四年《三田文学》十月号上,由于该小说涉及浓郁的病态性官能描写,致使小说一经杂志发表就遭致明治政府以“伤风败俗”为由,禁止发行。事后,永井荷风撰写《废文》一文对此事进行了评论。他认为这篇小说虽然描写了青年人的性欲问题,但是并不是谷崎随意的行为,而是经过作者严密的研究,当局以伤风败俗为由对此禁止发行,这是一种典型的文以载道行为。(叶渭渠,2005:37)永井荷风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批评了明治政府过激的行径。小说采用梦境的方式来表现直彦赤裸的官能意识,不仅反映了明治末期社会青年的个性觉醒和自我解放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而且以梦境的形式表现人物情感发展的细微过程,向读者展示人物的心路历程。
小学毕业后,直彦来到京城,师从名家学习绘画。23岁时,直彦已经是日本少壮画家中的俊才,受到世人的赞誉。然而,知道他的人与其说是赞美他的艺术,倒不如说是羡慕他的美貌。由于他经常出入烟花柳巷,致使纵欲染疾。悲叹之余,他深感自己已经失去了生命的价值。于是,他决心前往白雪皑皑的北国写生六个月,以求恢复身心健康。然而,离开吉原的直彦即便坐在列车上也依然梦见自己焦思苦想的女子。
“他仍然独自一人陷入在思恋女子的梦幻中,无论如何努力想见到心中孕育的恋慕之情。他坐在快速行驶的车厢一角,眼神呆滞,各种奇怪的想象与情欲的感觉骤然涌上心头,其强烈反应未曾所见。”(飓風:216)
直彦离开吉原的初衷是为了摆脱艺伎的束缚,以求身心的康复。然而,事与愿违,坐在列车上的直彦却因对艺伎的强烈思慕而使自己陷入到梦幻之中。虽然谷崎在这里并没有以大量的文字去描述梦境的具体内容,但是精炼的语言概括却能让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使其在想象中感受直彦真挚而又浓郁的思女情怀。众所周知,语言一经作家艺术化处理后,往往具有模糊性。然而,正是这种模糊性给人以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使文学语言具有韵味无穷的特质。正如王国维(1982:193)在评论宋祁的《玉楼春·春景》所言:“‘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一个“闹”字之所以能够让诗歌富有意境美,关键在于“闹”字的能指与所指不一致,最大限度地表现出语言的模糊性。也就是说,诗人在表现春天百花争艳的美景时并没有采用具体的事物描写,而是巧妙地借助“闹”字来诱发读者的想象,从中感受诗歌的魅力。就小说而言,谷崎也没有运用精确性的语言去描写直彦的梦境情况,而是以“各种奇怪的想象”(いろいろと奇怪な想像)等具有模糊性的语句来修饰。如此模糊性的语言描述不仅使人物梦境的内容具有丰富性,而且还可以增强文本的可读性,留给读者审美再创作的广阔空间,使其在想象中感受和理解人物浓郁而又微妙的心路历程。
为了疗养,直彦首先在会津的东山温泉停留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他除了每天给新闻社送去一两张写生画外,就是泡温泉。一天,直彦因思慕东京的艺伎再次陷入了梦幻之中。然而,这次直彦做的却是恶梦。
“恶梦袭来,他从蒲团上临空跃起,一边感到强烈的心悸,一边飞奔到枕边的的镜子前面,脸上惊恐充血,带有异常的红味。夜间魑魅魍魉织出奇妙的幻觉,煽起不可相逢的感觉,意识到在梦中相见的东京恋人”(飓風:217)。
此处的梦境描述与之前的存在明显的区别。在这里,作者以传神之笔,对人物梦境情形展开了生动而又形象地描摹,使之梦境呈现出浓郁的官能色彩。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学说中将人的本能欲望视为是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举止的内在动力和根本源泉。然而,在人类诸多本能欲望中性本能却是最为基本的欲望,它对于人的心理与行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只不过这种本能欲望由于受到社会秩序与伦理道德的约束,往往以会梦幻的方式显示其存在。因此,作家如果能在其文学创作中形象而又准确地把握和描述人物的性心理,不仅有利于刻画和塑造人物形象,而且还可以从中展现和揭示人物的心路历程,为读者理解人物和把握作品的主旨提供有效的艺术途径。直彦梦见自己从蒲团上临空飞起,浑身心悸不安,脸上还带有异常的红味。这其实是谷崎对人物性欲本能的一种隐性书写。梦中出现的镜子更是这种隐性书写的最形体现,因为它能形象地将人物内心的本能欲望呈现出现。按照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婴儿便是通过镜中的形象来确认自我的存在,即使婴儿的这种自我认同是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但是这一认同的过程却充满了喜悦和欢快。因此,镜中出现的影像是人物自我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梦中出现的镜像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直彦此时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在呈现,谷崎通过镜像中的直彦形象艺术性地呈现出直彦浓郁而又真挚的思女情怀。虽然镜像是人物自我想象的结果,但是镜中之像不仅是人物内心真情实感的外在投射,也是人物窥见自我心路历程,寻求自我认同的有效途径。具体来说,谷崎在此抓住直彦出现中镜子的神情,以脸上的表象为基点,勾画人物的性心理,还原其本相。直彦满脸充血而出现的绯红不仅是直彦生理反映的真实写照,更是其性爱意识的外在表征。谷崎以镜子来刻画直彦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客观写实,因为镜子作为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物象往往富有丰富的隐喻意义,它不仅能够形象地反映客观事物,更能生动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镜中的直彦形象其实是直彦内心欲求的对象,是想象中的自我形象。谷崎正是借助这个形象将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其外在表情有机结合起来,在揭示人物性心理的同时,展现人物的内心图像。
除《飓风》之外,《西湖之月》(西湖の月)、《天鹅绒的梦》(天鵞絨の夢)也是以梦境的形式来揭示人物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位与中国有着密切关联的日本现代作家,谷崎不仅曾先后两度游历中国,而且还发表了一系列诸如《西湖之月》、《天鹅绒的梦》、《秦淮河之夜》(秦淮の夜)、《鹤唳》(鶴唳)、《鱼的李太白》(魚の李太白)等以中国为题材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往往与“空想”、“梦境”、“幻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西湖之月》中,谷崎把月下的西湖描写得宛如仙境,当“我”泛舟西湖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具少女的浮尸。在皎洁的月光下,女尸显得特别的美丽。目睹眼前华美的景象,“我”陷入了梦境之中。“尽管她向上的面容被比玻璃还要薄的浅浅的水流轻轻地拍打着,但是月光透射,反而比在空气中更清晰地在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尸体的容颜上形成亮点。”(西湖の月:532)谷崎在此以月光来衬托女尸的美丽,具有浓郁的虚构色彩。梦境中的女尸宛如皎洁的明月,洁净、靓丽,虽是一具死尸,却洋溢着青春的生命气息。因此,死亡在谷崎眼中不是毫无意义的存在,而是凝聚永恒之美和无限活力的生命呈现方式。西湖之上的明月、湖水和未知姓名的女尸所组成的安静而又纯美的世界才是人类心灵的诗意之所,才是身处梦境之下“我”所憧憬和梦幻的理想国度。如此以来,中国作为谷崎笔下的形象也就具有浓厚的虚幻色彩,它是一个远离现实世界的梦幻国家,是谷崎心驰神往的梦想之地。如果说《西湖之月》是借梦境中的女尸来抒发谷崎的中国情趣,那么,《天鹅绒的梦》可以看成是谷崎则是以大富翁温秀卿与其妾泛舟西湖的梦幻情景来表达他的中国趣味。“满月之夜,湖上宛如打磨的银盆发出皎皎之光,令人心旷神怡。”(天鵞絨の夢:532)作品中的西湖景色被描绘成一个梦幻般的美丽景色,显然是“我”进入梦境之后幻想的结果。因此,谷崎笔下的中国景致不是实景描绘,而是人物处于梦境中幻景的呈现。这种梦幻中景致描写不仅具有鲜明的轮廓和鲜艳的色彩,而且还真实地流露出人物的心路历程,传递其浓郁的中国情趣。总而言之,谷崎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过程的时候,注重以梦境的形式表现人物细腻的情感过程,在如诗如画的梦幻中展示人物心路历程。
四、结语
谷崎在其短篇小说中善于以梦境的形式来描绘人物心灵深处的意识活动,通过梦境描写来展现人物的潜在意识和心理历程,揭示作品的深层主题。谷崎笔下的梦境描写作为作家形象化的艺术表现方式有利于读者走进其人物的内心世界,理解其真实的创作意图。因而,对谷崎来说,其梦境描写的审美价值在于打破现实与幻想的界限,在细腻真实与奇异神秘中展开人物心理,揭示人物的潜在意识,呈现梦者所寻求的心灵归属过程。这样既有效地拓展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广度与深度,增强了人物性格的真实性,又把作者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思考融入到梦境之中,成为其深化作品思想主题的重要手段。总之,谷崎短篇小说的梦境描写巧妙地突破了传统写实小说的局限性,在细腻中状写人物复杂的心理世界,表现作品深刻的思想主题,使其小说既具有浓厚的梦幻色彩,又赋有深远的思想内涵。
[1] 弗洛伊德. 2008. 释梦[M].孙名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 弗罗姆. 2001. 被遗忘的语言——梦、童话和神话分析导论[M].郭乙瑶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3] 谷崎潤一郎. 1974. 谷崎潤一郎全集(第四卷)[M].東京:中央公論社.
[4] 谷崎潤一郎. 1975. 谷崎潤一郎全集(第二十三卷)[M].東京:中央公論社.
[5] 谷崎潤一郎. 1974. 谷崎潤一郎全集[M](第六卷)[M].東京:中央公論社.
[6] 谷崎潤一郎. 1974. 谷崎潤一郎全集(第十三卷)[M].東京:中央公論社.
[7] 谷崎潤一郎. 1975. 谷崎潤一郎全集(第二十二卷)[M].東京:中央公論社.
[8] 谷崎潤一郎. 1973. 谷崎潤一郎全集(第一卷)[M].東京:中央公論社.
[9] 王国维. 1982. 人间词话(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0] 叶渭渠. 2005. 谷崎润一郎传[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红周)
I106.4
A
1008-665X(2016)2-0051-05
2015-12-16;
2016-01-27
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谷崎润一郎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关系研究”(13CWW008);2014年湖南省社科基金项项目“谷崎润一郎短篇小说研究”(14YBA178)
张能泉,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