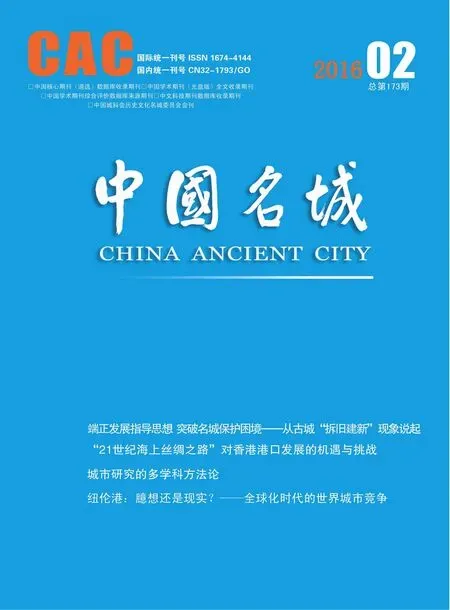论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主体及功能定位*
2016-02-05张巍张勇
张 巍 张 勇
论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主体及功能定位*
张 巍 张 勇
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选择是理论建构和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基于我国国情和社区建设实践,中国未来城市社区建设的未来理想图景是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对社区建设模式主体的确定及功能的定位,是理论构建社区建设模式的基础,未来的内生型社区建设模式下,存在着党、政府、社会、市场和居民五大主体,各主体的角色功能应定位为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行动、市场辅助和居民参与。
社区;城市社区;社区建设模式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被打上深深的外生型城市社区模式的属性与特征①,在外生型的社区建设模式下,所形成的刚性社区管理体制部分的消解了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目标的实现,因居民的参与不足引发社区治理困难,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也往往不足且失衡,在深层次上出现因社区精神培育不足使社区部分本质流失[1]。面对如此困境,未来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目标何在,路在何方?
1 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选择与内涵
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选择是主观和客观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体现着社区建设主体对未来社区的主观性的判断与理想诉求;一方面这种选择又必须奠基于现实基础——包括理论现实基础与社区建设实践基础之上。城市社区建设的已有实践和成果是我们选择未来理想社区建设模式的实践基础,已有学者对建设实践进行的理论归纳与总结为我们选择理想社区建设模式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理论资源。在实践中已出现了较为成熟的青岛模式、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百步亭模式、盐田模式等。有学者从本质特征对其进行归纳和分类认为可以大致分为四大模式:一是组织构建模式;二是行政推进模式;三是提升功能模式;四是自我革命模式[2],有学者根据社区建设主体及其在社区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把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模式概括为三种模式或三个阶段:一是行政型社区——政府主导型模式;二是合作型社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结合型模式;三是自治型社区——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型模式。[3]
每一种社区建设模式的归纳与设想,既奠基在对社区建设客观现实的考量之上,也承载者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和理想诉求。每一种归纳与构想都加深了我们对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认识,我们可以从模式的多样性透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诸模式的阶段性,从模式的个性透视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共性,从模式的共性透视城市社区建设的规律性[4]。笔者认为,对未来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模式的选择,至少要符合以下标准:①客观性。即选择的社区建设模式奠基于客观现实基础之上。这种客观现实主要包括两点:一是我国的具体国情,即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其制度环境;二是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现有模式和水平,因为每一种制度的变迁都受制于已有制度。②社会性与人民性。即理想的社区建设模式既需要满足社会整体的需求,也能满足居民个体的需求。③规律性。即选择的社区建设模式符合社会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本质性规律要求。④前瞻性。即社区建设模式不仅能满足当前现实和需要,还要能在一定程度上预见和顺应未来社会发展和社区建设趋势和需要。
根据上述选择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四个标准,我国未来城市社区建设的理想模式可定位为内生型社区建设模式,该模式及其实践路径不仅具有现实性,与我国国情和社区建设基础相适应,而且具有理想性,符合社会和居民的理想需求,更为重要的是符合社区发展的本身规律性要求。所谓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是相对于外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而言的,概括说来,内生型社区建设的建设在力量来源上,主要依靠社区内部的社会力量;在社区建设的目标上,将生活共同体作为主要目标来实现社区本质的回归;在社区建设动力来源上,社区居民需求是社区建设决策的主要依据;在社区建设主体上,各主体在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功能的回归与合作;在社区建设内容上,更注重社区精神的培育;在社区建设路径上,经过国家主导下的社会行动发展阶段,最终达到社区自治的理想状态。内生型社区建设最为突出的特征在于其动力和力量来源的内部性和社会性,以及建设主体间关系的多元性与合作性,当然,内生型社区建设的结果是社区内涵式的发展,是对社区本质的靠近与回归。
2 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主体界定
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选择与理论构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社区建设各主体的确立及职责功能的定位。社区建设主体在理论上是一个意义包含很广的概念,在实践中也包含很多主体。柯亨、阿拉托提出了“市民社会一经济一国家”三分法,[5]当然,对于比较典型的三分法除此以外,还有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一经济一国家”三分框架[6],莱斯特·W·萨拉蒙提出的“政府部门一营利部门一非营利部门”三分框架。[7]由于在诸多场合,“政府”常常取代国家,“市场”也常常取代“经济”,于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分的局面开始形成,[8]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国家-市场-社区”[9]或“政府-市场-社区”[10]的三元结构分析框架,据此,在宏观上,社区建设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行为主体。同时,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虽然其行为基本上都融入到政治、经济或社会的三大系统中,但因传统理论认为“社会”主体中的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而居民个体,因此,在此将居民个人作为社区建设的单独主体来看待。而且,将居民个人作为社区建设的单独主体来考察也存在着一定的客观必要性和意义:一则居民个人的行为并非总是与组织行为保持一致,或者说个人对其利益的理性判断及其行为并非一直符合组织的利益与行为需要;二则,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居民个人不仅存在参与到组织中去的组织化行为,也存在着个体性的行为,个体性的行为依然发挥着一定的功能,实现着一定的目标。因而,总体上看,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主体包括:国家、市场、社会和居民个人。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认为我国的政治体系其实包括基于宪法的宪政体系和基于党章的政党结构体系,而这两大体系中,具有主导性意义即真正具有决策功能的是执政党结构体系[11],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作为社区建设主体的国家,在实践中存在政府和执政党两种主体形式,尽管二者在根本利益与目的上存在一致性,都属于国家力量的范畴,但在社区建设中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分工,其行为方式与逻辑并不相同,其功能也存在一定差异,所以在下文论述中将二者分别论述。
3 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主体功能定位
在“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法视域中,包含着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领域,三大领域依次对应的是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三大系统每个系统内具有自身属性的主体,各种主体都主要围绕系统内的主要运作平台发挥自身各自不同的功能、作用和影响。政治领域的活动主体主要是国家(政府),经济领域的活动主体主要是企业,而社会领域的活动主体主要是社会组织。社区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社会发展经由社区发展,社区建设推动社会发展,在社区的舞台上,呈现的依然是三大系统及其相应的主体在社区建设实践中的功能与作用。“社区的行动领域是社会性事务,国家的行动领域是行政性事务,市场的行动领域是经济性事务”。[12]在每一领域,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原则,“国家遵循权威或等级化控制原则,市场遵循交换或通过交易而实现的协调原则,而社区则遵循团结或规范性整合原则”。[13]根据三大领域及其主体的在社区建设中的特点及目标,社区建设主体的功能定位如下:
3.1 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社区建设的政治保证,也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加强和改善党对城市社区建设的领导,从本质上来说源于以下几方面的需要:一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需要,使城市社区成为我们党组织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社会,从而实现有效领导和执政的重要工作平台;[14]二是社区建设内在需求,党不仅是社区建设的领导和推动力量,而且社区党建本身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三是执政党所建立的从中央到地方最为完备的组织体系与机构,利用此强大而丰富的组织资源不仅有助于国家建构,而且更具社会渗透力。[15]
党组织对社区建设的领导从本质上来讲,依然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但对于未来的内生型社区建设模式下的党的领导,其领导行为需要更高的领导艺术,其领导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决策,参与制定社区建设的重大决策;二是模范激励,通过党员在社区中的模范效应影响和带动居民行为;三是协调,协调社区建设相关主体间关系。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城市社区出现的新情况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要求社区党组织在社区各项工作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扩大党在城市社区工作的覆盖面,充分发挥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优势来做好群众工作。[16]
总体看来,党在内生型社区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及其实现可以概括为:“地位要加强,行为要科学,方式要艺术”:首先,不论在何种状态下,党的领导作为政治保证不能有丝毫放松,毕竟社区建设在客观现实上承载着基层政权建设的重任,他不是西方国家单纯的社区发展;其次,执政党的领导行为要具有科学性,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遵循社区建设的本质与规律要求,满足社区本质规律需要;最后,社区作为最基层的社会单元,每一社区的社区禀赋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党对社区建设的领导一方面要有创新性,开拓新的领域,寻找新的载体;一方面要具有高度灵活性,与社区实际具体情况相适应。
3.2 政府主导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了政府的基本职能为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确定为政府的基本职能。在2004年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勾勒的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政府在社会管理的角色定位为“政府负责”。在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社区自主性和自治性尚不可能自然生成的特殊国情下,政府作为培育社区、发展社区的核心主体,具有无可争议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城市社区生成的路径和突破口从根本上取决于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结构发育这两大基本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动状况。[17]
政府作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是由我国具体国情、社区建设现实需要和我国政府特质所决定的。第一,社区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到方方面面,需要最具权威性的机构从整体出发制定科学的建设规划和政策措施,并付诸实施。美国学者诺斯认为:政府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并具有实施规则的强制力。[18]政府也肩负管理组织经济社会生活,制定政策的法定职责,因而政府具备社区建设所需要的权力要素;第二,政府作为公共财政和公共资源的支配主体,理应成为社区建设的主要供给者;第三,社区建设内容与城区政府的工作任务具有高度一致性,政府的工作目标实际上也是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第四,政府能够进行社区资源整合与动员。在未来的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那种自治程度很高、关系稳定、运转灵活的社区在中国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扮演重要角色”。[19]因为我国社区建设既不是单纯的政府行为,又不是单纯的民间行为,而是政府实施社会管理,推动社会发展和基层群众自治相结合的产物,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化”行为,注定政府在社区建设中居于主导性地位。
在未来的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中,政府的主导作用应该体现在那些方面?笔者认为,对于内生型社区建设的政府行为,一是要注意区分政府行为的具体性,在社区建设的不同具体领域,其作用发挥的程度及方式存在不同;二是要注意政府行为在社区建设过程中的阶段性,社区建设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力量对比环境下,政府扮演着不同角色;三是政府在社区建设过程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四是政府的主导作用的宏观定位在倡导、动员、一定的经济和政策支持、监督、评价和经验推广,是用政策去促进社区建设资源的聚集和社区的持续发展。
3.3 社会行动
按照萨拉蒙的三大部门划分理论,社会部门(系统)的主体是社会组织。广义来说,“作为名词的社会组织,是指人们为着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以某种方式结合而成的集体”。[20]从狭义的角度来看,社会组织指除政府与企业外,面向社会自主提供某个领域公共服务的法人实体,可以分为准行政组织、事业组织、公益组织和中介组织四种基本类型。[21]从功能上看,社会组织是以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稳定的方式把人类的活动或他们所生产的物品协调在一起的手段。[22]“社会组织是社会部门和社会发展领域的主体,社会发展更多体现为社会行动(社会组织在行动)”。[23]
在未来的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下,社会力量是社区建设的主体力量,社会组织行动是社区建设的主要行动,因为在社区建设领域,政府和社会组织是天然的同盟军,是最佳伙伴。[23]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会救济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一剂药方。”[24]泰勒说:“不论你为社区做了多少事情,除非而且直到能够自主发展的群体被培养起来,社区是不会得到发展的”。[25]社会组织因具有民间性、公益性、自治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在社区建设的舞台上,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其他主体不可比拟的优势:①推进居民民主自治。社区社会组织本身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自治的组织方式和参与公共决策、参与社区发展的渠道。②满足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多元、多层次需要。社区居民利益的分化,必然带来多元的利益需求和多层次的需求,对这样多元、多层次的需求靠政府是难以无法满足的,而社会组织的服务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恰好能满足居民需要。③充当政府与社区居民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社会组织能够凝结社区居民的意愿和利益;一方面社会组织能够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来有序的表达诉求。④监督和规范政府行为,促使政府职能转变。组织化的力量能够对政府起到个体无法起到的制约性作用,而且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中去,本身就促使政府职能的转变。⑤协调居民利益,化解社会矛盾,维持社区秩序。社会组织发挥着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的作用,同时增强居民对社会的容忍度。⑥整合社区资源,将社区社会力量整合到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行动中来。⑦增强社区凝聚力。社会组织是社会交融的“粘合剂”,对社区认同和社区共同感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未来内生型城市社区建设,社会行动是关键,要形成社会行动,一则社区要具备社会行动的力量和主体,二则国家要留有社会行动的空间与途径,前者是对行动主体的要求,后者是对行动环境的要求。因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会环境制约等多方面影响,我国社会组织发育缓慢,而且参与社区建设的行动力量弱小,难以胜任未来内生型社区建设对其需求。为了激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社会行动力量,一要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提高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和水平;二要规范和提高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的科学化水平,推动社会组织自主发展的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和引导;三要营造良好的公益环境和慈善氛围;四要完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制度空间,积极搭建社会组织参入社区建设制度平台。总之,就是要保证社会行动“行动有力量,行动有保障,行动有空间,行动有效果”。
3.4 市场辅助
市场是城市社区建设的主体,市场力量是社区建设的重要辅助性力量。这种辅助性力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力量可以弥补政府和社会力量不足,满足城市居民需要和社区需要。特别是在社区服务的供给方面,市场凭借其自身的优势能够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另外,市场也可能为社区建设直接提供经济支持或经济资源;二是市场机制可以运用到社区建设的某些领域中来,发挥其效率优势。市场机制本身就内含着效率机制,而这一机制完全可以被社区建设所借鉴和利用;三是政府、社会和市场可以在社区建设领域合作,在共赢的局面中推进社区建设。政府或社会的职责可以通过“合同”或“委托”的方式交由市场完成,市场在分担政府或社会的任务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利益需要。
但市场毕竟属于经济活动的领域,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是其首要目标,而社区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建设的范畴,而社会领域的基本价值在于公平与公正,这种目标价值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利用市场力量的有限性和对待市场力量的谨慎态度,或者说市场只能充当社区建设的辅助性力量。一方面要积极发挥市场力量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特别是利用市场机制和资源解决社区建设的资源紧缺和效率不高问题,同时要创新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作机制,拓宽合作领域;一方面要对市场参与社区建设进行规范性引导,消除其负面影响,同时激发市场主体(企业)的社会责任。而这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要建立完善的市场参与社区建设的制度化的激励机制与引导机制,一方面对公益性的市场行为进行激励,不排除采取利益激励方式;一方面引导市场力量投入到社区需要的领域中去。同时,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以强制性的、具有约束力的方式规定市场主体企业的社会责任及承担方式。
3.5 居民参与
社区居民既是社区建设的受益者,更是社区建设的主体,是最为重要、必不可少的参与力量。参与,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对一定领域内的事务的治理过程,包括问题认定、决策分析、实施过程、结果反馈和追踪决策等环节,它在分解的基础上予以整合,在整合的指引下予以分解。[26]“社区居民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影响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行为和过程,其目的在于推动社区发展,从而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7]社区居民参与是社区居民生活方式的一种,在“社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只有居民的直接参与,才能培育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现代社区意识,才能有效地整合和发挥社区自身的各种资源。居民社区参与是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离开了居民的社区参与,就没有真正的或完整意义上的社区发展”,“一部社区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培育居民社区意识、提高参与能力、扩大参与领域、提升参与质量的历史”。[28]
社区居民参与在社区建设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首先,推进居民自治。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是社区居民自治的根本前提,通过居民参与,可以培养居民的社区意识、社区共同体观念和社区责任意识,同时扩大了基层民主,使社区居民直接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决策、监督,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为居民自治提供基本保证。其次,提高公民素质,培育社区精神。一方面居民参与的过程,也是居民经受训练与熏陶的过程,是公民素养和参与技巧提升的过程;一方面在居民参与过程中,可以增加社区成员间的理解,宽容程度,有利于化解社区矛盾,培育社区共同体精神。其三,解决社区建设资源不足及配置效率问题。社区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有赖于每一个社区居民的参与,特别是对社区服务而言,居民参与符合现代社会福利基本理念和发展方向,社区社会化服务网络的建立在根本上依赖于居民参与情况。
总体上,我国社区居民参与普遍存在着参与意识薄弱,参与率低下,参与程度不高等问题。[27]特别是在社区建设过程中,“被动员式”执行参与是居民参与的主要形式,所谓被动员式执行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在政府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动员下被动的参与执行或落实社区管理机构业已形成决定的事项,这种参与在取得一定的效果的同时,却极大的降低了社区居民参与的意义与价值,失去了“参与”的本来意义。按照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观点,任何一种制度的实施,是在特殊背景下相关行动者为了自身利益而相互作用的结果。[29]居民是否参与社区建设中去,往往也会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激发居民参与热情的前提是要使参与的行动与居民利益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或者说居民的参与行动应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就意味着要促使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一方面,要在社区利益整合的基础上,使社区参与行动与社区利益,特别是和其居民成员利益建立起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培育并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和归属感,使他们主动融入到社区参与中来。研究表明,“个人对群体的认同感愈强烈,便愈可能涉入组织和参与政治。”[30]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社区参与的体制创新,为推进社区参与的广泛化、制度化合规范化提供制度保证。只有这样居民才能从“被参与”的臼巢中走入到“要参与”的理想状态。
注释:
①关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所具有的外生型属性及特征的论述,可参见系列论文:《论我国外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的实践逻辑》,《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我国六十年城市社区建设历程、脉络与启示》,《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张勇.外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现实基础与实践困境[J].社会主义研究,2012,(4).
[2]胡宗山.全国社区建设模式评析[J].中国民政,2000,(6).
[3]魏娜.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4]王青山,刘继同.中国社区建设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童世骏.“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市民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4).
[6][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7]康晓光.权力的转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8]白瑞,邹静,沈卫,张雪峰.论城市社区自治的缘起与发展及对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建议[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5,(4).
[9]刘继同.从依附到相对自主:国家、市场与社区关系模式的战略转变[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3).
[10]曹绪飞.社区制基本问题再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2007.
[11]胡伟.政府过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2]Zhang Jing,Neighborhood-Level Governance: The Growing Social Foundation of Public Sphere,in Jude Howell ed.,Governance in China[M].Maryland Co: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4.
[13][意大利]阿尔伯特•马蒂尼利.市场、政府、共同体与全球管理[J].社会学研究,2003,(3).
[14]林尚立.社区:中国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2).
[15]彭勃.路径依赖与治理选择: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变革.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16]唐忠新.构建和谐社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17]陈小兵.深化社区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社区建设研讨会”综述[J].社会,2001,(2).
[18][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19]许放明.简论政府在社区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
[20]童星.社会管理学概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1]张尚仁.“社会组织”的含义、功能与类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22][英]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齐心,王兵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3]陈伟东,卢爱国,孔娜娜,谢正富.中国和谐社区:江汉模式[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24]张俊芳.中国城市社区的组织与管理[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
[25]Charles Taylor,“Cross-Purposes: 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Debate”,in Nancy L. Rosenblum(ed), Liberalism and the Moral Life[M].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6]潘小娟.城市基层权力重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27]潘小娟.中国基层社会重构——社区治理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28]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
[29]胡荣.理性选择与制度实施: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选举的个案研究[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30][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M].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王凌宇
Urba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mode select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building and realistic practice,based on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practice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the ideal picture of the future Chinese urban communities construction mode is endogenous urban community construction mode.Determining the main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main’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is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del in theory building community-construction mode.Under the endogenous community construction mode in the future,there are five main body, including party, government, society, market and residents, the main’s role and function should be positioned as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government-led, social action, marketassisted, community residents participating.
community;urban community;community construction mode
C912
A
1674-4144(2016)-02-43(6)
张巍,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讲师。
张勇,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2012年岭南师范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相对落后地区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战略研究——以粤西地区为例》(W1204)的阶段性成果;广东省宣传文化人才专项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