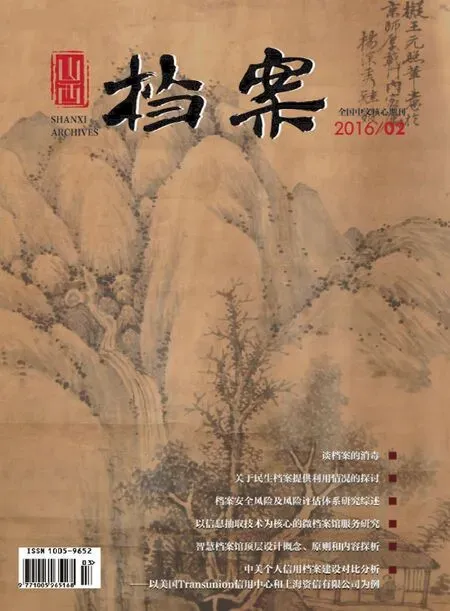从序跋论《颜氏家训》的接受与传播
2016-02-03程时用
文/程时用
从序跋论《颜氏家训》的接受与传播
文/程时用
研究《颜氏家训》的序跋,不但可以清晰了解到世人对作者及作品的评价,也可以折射出颜氏家族家学门风及中国家训发展概貌,而且还可以了解历代社会主要文学思潮。序跋不仅从多方面指导着世人对作品的阅读和理解,还有力地推动了作品的传播与接受。
《颜氏家训》;颜氏家族;序跋
颜之推是南北朝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用敏锐的目光审视人间,饱含心血,撰写了誉称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此作自问世以来,世世刊行天下。在反复刊刻中,留下了序跋。本文对序跋梳理和探讨,勾勒出《颜氏家训》在历史长河中传播与接受情况。
一、《颜氏家训》序跋的基本特征
《颜氏家训》自隋代成书,现存唐代序1篇,宋代序、跋各1篇,明代序4篇、跋3篇,清代序7篇、跋2篇。虽然数量不多,但可以了解我国家训序跋这一文体的发展脉络,并可以大致勾勒《颜氏家训》的传播与接受特征。
(一)作者体现出官方化和学者化特征
宋本序跋由时任礼部侍郎的沈揆所作,明代有国史官张璧、翰林国史修撰张一桂、翰林字修撰颜慎行、前睢宁学谕翁广烈、东海佐储公署颜志邦作了序或跋,清代有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朱轼、朝廷大臣黄叔琳、提督湖南学政卢文弨作了序或跋。作者的官方化、刻本的官府化,提升了作品的权威,加速了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同时,清代大学者赵曦明、钱大昕、古文献学家余嘉锡、大藏书家鲍廷博,还有颜氏子孙兼学者颜如瑰、颜星、颜邦城都曾作序或跋。这些官员、学者作序或跋,以旌表的方式赋予重刊家训的崇高地位,强化了家训的传播与接受。
(二)写作围绕政治和文化中心
宋本沈跋:“惟谢氏所校颇精善,自题以五代宫傅和凝本参定,而侧注旁出,类非取一家书。”[1](p580)颜之推任太子太傅,当时生活在长安,作品的传播主要在都城长安。宋代流传的主要是沈本,此本由沈跋依据家藏闽本,参考知政事谢公家旧蜀本和五代宫傅和凝本而成,由乡贡士州学正林宪等八人同校和监刊。刻本质量高、权威性强,成为后世历代底本。在宋代,蜀本、闽本、浙本为著名的坊刻本,《颜氏家训》流传下来的三种版本俱存,表明此书在当时极受世人关注和青睐。
“宋明以来,具有特权等级的士族没有了,家训所针对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主要由有文化背景的士大夫官僚之门,转向普通老百姓之家。”[2](p136)明代以京城南京为中心,有浙江副使傅太平刻本、颜嗣慎刻本、程荣汉魏丛书本、建宁府同知绩溪程伯祥刻本、苏州颜如瑰刻本。清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印刷术的提高、颜氏子孙分布地域广,在京城、江西、湖南、江苏、浙江、广东都有不同的刻本,传播更为广泛。
二、《颜氏家训》序跋的主要内容
序跋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史料。通过序跋,可以了解重刊作品的动机、作品的成书,可以了解作者的生平、爱好,可以考察文人学者对作品的认识、评价,也可以鉴定作品版本等多方面内容。
(一)评价作者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他的创作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3](p75)这也是我国古代“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4](p726)“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传统,要求读者既要了解作者人生经历、为人处事和精神世界,又要了解社会生活、政治环境对作者造成的影响。《颜氏家训》唐人序载“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学优才赡,山高海深”[1](p577),宋本跋称“颜黄门学殊精博”[1](p579),明傅太平称“北齐颜黄门家训”[1](p581),明刻本后序称“侍郎博雅闳达,为六朝人望”[1](p583),这些序跋对作者人品大加赞誉,对其学问进行了高度赞扬。这种评价恰如其分,今人范文澜也认为颜之推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5](p277)文如其人,对作者的评价直接影响到世人对作品的接受。
(二)梳理版本源流
人们写作序跋,习惯介绍作品版本的源流以及各个时期的出版发行状况。根据宋本沈序,唐五代时期《颜氏家训》在宫廷传播有五代宫传和凝本,此版本成为宋本的主要依据,经过沈揆等人的努力,刊刻成七卷本,宋代乃至元明清其他本子多以之为祖。这是官方版本的源流情况。另外,颜氏家族内部流传版本也有记载,安史之乱中,颜氏后裔遭到迫害和排挤,被迫离开长安。宋末又奉旨南移,颜氏家族漂泊流离,家藏的《颜氏家训》失传,只余一残本。明朝后期,颜如环秉其父颜四会遗志,历经多年遍访各州郡学者及颜氏宗亲,由山西到苏州,始求得两种版本,与家藏残本互相参校,使《颜氏家训》得以复全,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冬重刻刊行,兴盛于世。明程荣汉魏丛书本序:“余,楚产也。家训,楚未有刻也。”[1](p587)这记载了作品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流传发端。
(三)分析作品内容
《颜氏家训》历代受人青睐,主要是内容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对家庭教育发挥着重大作用。沈跋认为“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处朋友乡党之闲,其归要不悖六经,而旁贯百氏。至辩析援证,咸有根据。”[1](p579)傅太平认为“盖序致至终篇,罔不折衷今古,会理道焉,是可范矣。”[1](p581)颜嗣慎认为“夫其言阃以内,原本忠义,章叙内则,是敦伦之矩也;……其撮南北风土,俊俗具陈,是考世之资也。”[1](p583)在儒学为主导思潮的社会中,作品经世致用的处世之法符合世人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视野,自然会被广泛传播与接受。
(四)分析作品艺术
家训序跋是研究古代家训理论的最有力的原始材料。宋本序记载着唐人评语“镜贤烛愚,出世说之左”[1](p579),高度评价了作品的写人艺术。沈跋认为此作“虽辞质义直”[1](p577),张璧称为“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1](p581),张一桂称“其称名小而其指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心危,故其防患深;其虑详,故繁而不容自已”[1](p583),清代颜星评为“盖祖宗切切婆心,谆谆诰诫,迄今千余年,只如当面说话,订顽起懦,最为便捷”[1](p591)。这一系列评价,赞扬了颜之推平易而务实的写作风格。范文澜先生也认为“《颜氏家训》的佳处在于立论平实。平而不流于凡庸,实而多异于世俗,在南方浮华北方粗野的气氛中,《颜氏家训》保持平实的作风,自成一家言,所以被看作处世的良轨,广泛地流传在士人群中。”[5(p277)今天,《颜氏家训》流传的版本多达150余种,可见此作影响之深远。
辽宁轨道交通职业学院采用奥威亚高清录播系统,投资30余万元,录播教室总面积为50余平方米,学生座位近30个,位于学院图书馆位置相对封闭的房间,授课教师可以在不受外部影响的情况下开展教学活动。
三、《颜氏家训》序跋的文化意蕴
(一)广为传播与接受的原因
《颜氏家训》广为传播与接受的原因,其一,颜氏子孙世世宝之,历代子孙念念不忘对作品理念的践行与传承,通过多种形式对作品收集、刊印,强调家训可以保族延嗣,维护着颜氏家族的繁荣昌盛。序跋用大量笔墨介绍颜氏家族的源流及延绵不断的兴旺传承,这对世人接受及效仿《颜氏家训》有很大的启示。其二,从社会发展来看,“有余力则学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社会上的每一个家庭要延绵发展、香火不息,自然会重视家庭教育。人们需要借鉴像《颜氏家训》这样成功的家训勉励后代,教化后人。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在家国同构的古代社会,“家是国的缩微,国是家的放大”[6](p116),家教而家齐,家齐而国治,国治则天下平,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教化的作用,通过家训实现教化,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清代康熙皇帝作《庭训格言》并颁行天下,推广家训文化。
(二)折射了颜氏家族家学门风
在颜氏子孙撰写序跋时,撰者常常有着浓厚的远代世系情结,将颜氏始祖追溯至素以德行著称的颜回。西晋期间,颜氏南渡,形成了忠义的家风门风,“颜氏忠义之家风,与家训俱存而不泯”[1](p587),“侍郎子若孙,则思鲁、师古,并以文雅著名;其后真卿、杲卿兄弟,大节皎皎如日星,至今在人耳,斯又圣贤之泽也。”[1](p586)正因为颜氏家族传承着良好的家学门风,从魏晋到唐代中期,颜氏家庭中史籍可考者34人,其中官至五品以上有17人,而官居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侍中、秘书监等高位有8人,还有7人因德行或家风严整被封爵。[7]
(三)揭示出颜氏家族的兴衰过程
《颜氏家训》广为传播,“由于颜氏后裔的多次翻刻,于是泛滥书林,充斥人寰。”[1](p1)实际上,每到太平盛世,颜氏后裔中的有识之士就想方设法重刻或重刊此书。此书在唐代已广为接受,但未见颜氏子弟重刊,因为“逆胡所害者八人”[1](p588),颜氏忠义之名人惨遭迫害,甚至满门抄斩。颜氏子弟只得隐居峄山,天下平静后才回归曲阜、长安、南京等故地。北宋末年,金兵入侵,颜子后裔奉诏伴驾,再次南迁闽浙。元明清三代颜氏子孙大多遵循“位居中庸”的原则,处世低调,位居高官人数较唐代少,因此在历史的变迁中,影响比较小。明末清初,曲阜颜氏一支兴旺发达,颜光敏与时俱进,应势而为,秉承颜氏家庭教育主旨,作《颜氏家诫》以训子孙,这是继《靖候颜规》、《庭诰》、《颜氏家训》思想基础上,颜氏家族的应时之作,后人评价:“《家诫》四卷与北齐颜黄门《家训》一书,均有光于复圣,可并传也……言愈浅近,义亦愈确实。”[8]这些重刊不是简单的表明教子态度,而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家庭或家族教育实践活动。
(四)反映中国古代家训发展轨迹
在现存的《颜氏家训》19篇序跋中,明清序跋有16篇,这一数量正好反映了我国古代家训发展轨迹。“春秋所以重世家,六朝所以重门第,唐宋以来重家学,家训,不仅教其读书,实教其为人,此洒扫应对进退之外,而教以六艺之遗意也。”[9](p2)据《中国丛书综录》所列书目记载,中国古代家训一类著作共117种:南北朝1部、唐朝2部、宋朝16部、元朝5部、明朝28部、清朝61部、民国初年4部。
不同时代的文人学者对同一部作品的评价与接受,折射出不同时期的文化特色,显示出不同时期的文化心理、审美趣味、价值判断等。宋朝的文学创作在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宋本沈跋“虽辞质义直”一句表现出对文风的遗憾。明代在求真务实思潮引导下,创作文风大变,张璧称为“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到了清代,文学向通俗化转变,“只如当面说话”[1](p590),语言口语化、平易化。在清王朝高压文化政策下, 人们谨言慎行的做法也得到体现,如朱轼评点:“及览养生、归心等篇,又怪二氏树吾道敌,方攻之不暇,而附会之,侍郎实忝厥祖。”就连颜氏子孙也毫不讳言“或因其稍崇极释典,不能无疑。”[1](p593)
四、序跋对《颜代家训》传播与接受的意义
(一)引导世人选择家训蓝本
“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1](p7),是我国古代家庭共同的主题,随着家训的快速发展,大部分家庭无需“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1](p1)而重新写作家训。特别是对于缺少文化知识积累的普遍家庭而言,借鉴或模仿一套广为世人接受的成功家训,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做法。影响极为深远的宋本沈跋认为《颜氏家训》“当启悟来世,不但可训思鲁、愍楚辈而已”[1](p579),明傅太平刻本序:“乃若书之传,以禔身,以范俗,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则不独颜氏一家之训乎尔!兹太平刻书之意也。”[1](p581)清黄叔琳刻颜氏家训节钞本序:“然历观古人诏其后嗣之语,往往未满人意……余观颜氏家训廿篇,可谓度越数贤者矣。”“以古人之训其家者,各训乃家,不更事逸而功倍乎?”[1](p594)这一系列高度评价,指导着读者的选择,有力推动作品的社会化,于是“由近及远,争相矜式”。
(二)指导世人的阅读与接受
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序跋作者首先是作品的接受者,但又不是一般的接受者,与普通读者的区别在于他们是批评性阅读。他们在阅读时,除获得审美享受外,会更专注于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探讨其家庭教育的规律,力图为世人家庭教育提供优质指导。序跋作者常常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乃至生命体验都融入到家训之中,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使家训具有独立的文本和欣赏价值,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指导读者对作品的阅读。晁公武读书志云:“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1](p604)明颜嗣慎刻本对记载的佛学内容作了合理解释,并希望读者抓住作品主流思想,选择合适的教育内容,“或因其稍崇极释典,不能无疑。盖公尝北面萧氏,饫其余风;且义主讽劝,无嫌曲证,读者当得其作训大旨,兹固可略云。”[1](p583)
总之,在作品的流传过程中,序跋作者的官方化和学者化,官府的重刻或重刊,朝廷对颜氏家族的表彰,各朝代有名书坊的承刻或承印,都大大提升了作品的宣传力和影响力。颜氏家族历晋、宋、隋、唐千余年,名人硕士,垂声实载籍者,不可胜数,为古代家庭教育提供了成功的蓝本,这些合力必然会促进作品的传播与接受。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项目“网络环境下高职人文教育构建研究与实践”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1JXN023)
(责任编辑:杨秋梅)
[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2]张国刚.中国社会历史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
[3][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译.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清)焦循著,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05.
[7]封海清.琅琊颜氏研究—兼论文化在世族仕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J].昆明师专学报,1989,(3).
[8]周洪才.乾隆《曲阜县志.著述门》研究[J].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6).
[9]刘禺生.世载堂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0.
The Spread and Acceptance of Yan Instructions Seen from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Cheng Shi-yong
G40
A
1005-9652(2016)02-0168-04
程时用(1976—),男,湖北黄石人,广东轻工职业学院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