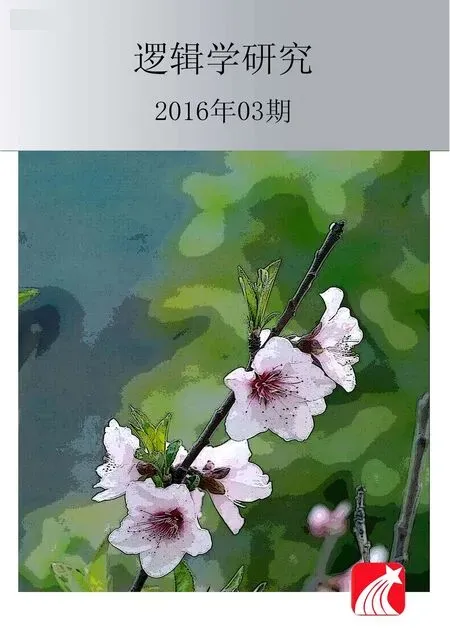佩雷尔曼的理性观*,†
2016-02-02蔡广超
蔡广超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ljxcgc@126.com
佩雷尔曼的理性观*,†
蔡广超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
ljxcgc@126.com
在对价值判断理性基础的探寻过程中,佩雷尔曼意识到传统理性概念的局限,进而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理性”: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佩雷尔曼对传统理性概念的批判,不仅限制了在很长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唯理性的适用范围,也为合情理性的可能性与合法性提供了辩护。在法律论证中,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之间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唯理性所依据的逻辑一致性与不合情理的结论之间存在冲突,另一方面,唯理性与合情理性彼此相互支持。在本文看来,以合情理性为基础的佩氏理性观不仅构成新修辞学论证理论的哲学基础,而且对于将包括非形式逻辑在内的论证理论置于更为健全的哲学基础之上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佩雷尔曼;理性;唯理性/唯理性的;合情理性/合情理的
在西方哲学史上,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理性观是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主导,笛卡尔的唯理性主义立场代表着一种独断式的理性观。在《新修辞学》中,为探寻价值判断正当性的理性基础,佩雷尔曼逐渐意识到笛卡尔唯理性主义的局限,主张应限制这种流行的理性观,倡导包含多元价值观和多样合理性的合情理性观。([21])为更好地理解佩雷尔曼所提出的新理性观,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厘清“理性”一词的两种含义——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二是阐明笛卡尔的唯理性是以数学知识为典型的神圣理性,这种理性的必然性、普遍性和自明性的特征彰显其自身适用领域仅限于形式领域;三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佩雷尔曼通过限制流行的理性观,倡导包含多元价值观和多样合理性的合情理性观;四是揭示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辩证关系,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在法律中得以充分体现。
1 “理性”的两种含义
在《新修辞学》开篇,佩雷尔曼指出:
“出版这本有关论证(argumentation)的论著,以及其主题与希腊修辞学和论辩术的古老传统之间的联系,构成了跟那种可归于笛卡尔的理性和推理概念(a concept of reason and reasoning)的决裂,后者在过去三个世纪的西方哲学中已深深地烙下了自己的印记。”([21],第1页)
“尽管没有人否认商议(deliberation)和论证的力量是一个合情理的个体(a reasonable being)的显著标志,但是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逻辑学家和认识论学者却完全忽视了对用来确保遵从的证明方法(the methods of proof used to secure adherence)的研究。……笛卡尔把自明(the self-evident)作为理性的标志,认为只有那些演证(demonstrations)才是唯理性的(rational),它们从清楚明白的观念出发,通过不容置疑的证明,把公理的自明性传递到推导出来的定理。”([21],第1页)
就本文的主旨而言,上述两段引文中有如下三个语词值得注意:“reason”、“rational”和“reasonable”。1笔者认为,“reason”、“rational”和“reasonable”术语的翻译应基于使用者的语境,也应兼顾汉语言表达习惯。在《新修辞学》中,佩雷尔曼在泛指意义上使用“reason”一词,本文译为“理性”。“rational”和“reasonable”是源于“reason”的两个形容词,其中“the rational”的主要含义指与数学理性一致,是神圣理性的反映,本文译为“唯理性的”;相应地,“rationality”译作“唯理性”。“the reasonable”的含义强调与人的行动和实践领域有关,与常识和共同感有密切联系,是普遍的且内在于具体情景之中,本文译为“合情理的”;相应地,“reasonableness”译作“合情理性”。在大多数英语词典中,后两个语词可以相互替换。在它们成为佩雷尔曼的关键性术语后,它们被赋予的意义未必是标准英语词典给出的意义,也未必是学者论述或日常用法中具有的意义。2在1977年渥太华会议与听众互动时,佩雷尔曼承认自己的这种区分未必与这些语词的实际用法相一致,但他认为自己既不是一个语言学家,也不是一个语法学家,对这种语言区分没有兴趣。在其看来,语词仅是语言使用者赋予其意义的符号。参见[7]。佩雷尔曼认为,尽管“唯理性的”与“合情理的”源于同一个名词,两者的意义都是合乎理性,但是它们不能相互替换。我们可以说符合逻辑规则的表达式是唯理性的演绎,但不可以说它是合情理的演绎;相反,我们可以说合情理的妥协,却不可以说唯理性的妥协。([17],第117页),在佩雷尔曼的观念中,语言仅仅是一个工具,语言的使用既要着眼于它的暗示(suggestive),也需要知道如何应用语言以使其满足哲学、法律和其他需求。([18],第213-214页)
“理性”所具有的这两种含义,在佩雷尔曼看来,表明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具有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两种表现方式或具体形态。自现代理性主义兴起以来,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不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区分的侧重点不同。斯坦利·劳克林(Stanley K.Laughlin)和丹尼尔·休斯(Daniel T.Hughes)认为,“唯理性”与形式逻辑相一致,“合情理性”与常识、传统观念或公平与公正的直觉意义相一致。([24],第187-205页)在《正义》中,卢卡斯也指出,唯理性严格以自我为中心,合情理性内涵道德意蕴,意指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他人想法。([9],第37页)菲什(W.R.Fisher)则更为简明地阐释了佩雷尔曼对两者的区分:“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不同反映了演证与论证的不同,唯理性与理论领域的演证相关,涉及人类行为的可计算性、非情绪性的行动;合情理性与论证相关,理性不仅在于证实、演证,更需权衡、批判和证成,提供支持或反对意见的理由。”([4],第93页)爱默伦和荷罗顿道斯特认为,“‘唯理性的’与‘合情理的’这两个语词的主要区别是‘运用推理的能力’以及‘合理(sound)使用推理的能力’,据此,我们把‘唯理性的’一词用作使用推理的能力,把‘合情理的’一词用作合理使用推理的能力”。([2],第124页)
从理论渊源来看,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不同与亚里士多德“灵魂的认知与推算部分”相类似。在分析灵魂唯理性部分的结构时,他假定这部分又包含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考察那些具有不变本原的存在物,另一部分是考察那些具有可变本原的存在物。……我们把一部分称为认知的,把另一部分称为推算的。”([1],第1139a5-12行,[32],第121页)其中,灵魂认知部分处理一成不变的事情,它的目标是必然和普遍的真理,倾向于演证的方法,偏爱精确性,对应用实践不感兴趣;灵魂推算部分处理可变的事情,把人类的行动作为对象,它与不确定的事物有关,倾向于真理的大致框架,使用权衡的方法,偏爱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调解,强调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晋荣东认为,灵魂认知和推算部分彼此青睐认知价值的不同,在彰显彼此差异时,也使人们很容易认识到唯理性和合情理性与灵魂的认知和推算方面相类似,据此,他指出佩雷尔曼对人类思维过程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区分,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灵魂唯理性部分的结构分析。([7],第1-15页)
综上所述,“理性”的两种含义中,唯理性以数学知识作为典型,它与形式逻辑相一致,使用演证方法,其特点包括必然性、自明性和普遍性,它构成《新修辞学》之前理性的全部内容,以笛卡尔的唯理性主义为代表;合情理性以人文科学领域知识为典型,它与常识、传统观念或公平与公正的直觉意义相一致,使用论证方法,其特点包括或然性、不确定性和特殊性,这种理性倡导包含多元价值观和多样合理性的合情理性,它拓展了人们对理性的狭隘理解,其集中体现是佩雷尔曼的合情理性观。
2 笛卡尔的唯理性
笛卡尔是现代理性主义的开拓者,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其为“现代哲学之父”。作为一个数学家和哲学家,他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传统,以数学作为哲学的楷模,坚持人类知识的统一性,致力于科学体系的构造。([30],第59页)在形而上学部分,笛卡尔使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树立了理性的权威,确立了理性的独立地位,这种理性为上文所谓的“唯理性”。在《新修辞学》导论中,佩雷尔曼援引笛卡尔的观点来阐述这种理性,即“为了展示理性的自明性品质,只有那些从清楚、明确观念出发的演证才是唯理性的,并通过不容置疑的证明把公理的自明性推广到所有定理。”([21],第1页)以笔者之见,这段引文不仅说明理性(即唯理性,笔者注)具有自明性和普遍性的特点,也内在彰显实现唯理性必须满足的条件——从清楚、明确的观念出发,使用演证的方法。接下来,我们从两个方面分别予以论述:
首先,唯理性具有自明性。自明性是一种力量,每一个正常的心智都必须向它屈服,由于它是自明的,可以作为绝对真理的标志。同时,自明性能够将心理学和逻辑学领域连接起来,允许相互之间在这两个层次的通融。在认识论中,自明性命题就是通过理解其意义就知道该命题为真,而不需要证明。帕斯卡则直接运用笛卡儿的自明性理论,指出所有证明都可以归于自明性,所有自明性的事物都无需证明。([11],第443页)在笛卡尔那里,自明性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自明性是唯理性的,它对所有唯理性的心智都是有效的,与时间和个体无关;二是自明性是一种心理特征,笛卡尔把它作为对每一个唯理性存在者有效的标准;三自明性的标准依赖直觉,思想和存在连接的自明性似乎对其具有强制性。([15],第132页)
其次,唯理性具有普遍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唯理性的出发点是清楚和明确的观念,二是唯理性使用演证3有关“演证”的详细论述参见[27]。的方法。在演证的现代形式中,演证是依据先前确立的规则进行的演算,其研究对象是纯数学领域。证明(演证)的目的是以为“真”的前提,而导出事物之自明性,证明(演证)导出的事物自明性乃具有强制力,听者必须接受之,不予接受则是非理性。([31],第309页)为此,演证必须使用完全无歧义的人工语言,运用演绎推理模式,并把公理作为演证的出发点。在数学演证中,公理并非争议的话题,数学家把公理作为真理、自明的或简单的假设,在使用公理时,不需要考虑听众是否接受它们。([19],第9页)在笛卡尔看来,只有以数学为基础的演证方法可以运用到一切知识之中,这种精确的推理方法反映了人类理性的真正本质:
“哲学这个名词的意思是研究智慧,所谓智慧指的并不只是处事审慎,而是精通人能知道的一切事情,以处理生活、保持健康和发明各种技艺;这种知识要能够做到这样,必须是一些根本原因推出来的。所以,要研究怎么取得这种知识,一个真正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应当首先研究这些根本原因,也就是本原,而这些本原应当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非常清楚、非常明显,人心一注意到它们就不能怀疑它们的真理性;另一个是要依靠它们才认识其他事物,……从这些本原推演出各种依靠它们的事物的知识,做到推演系列中没有一个环节不十分明显。”([28],第61-62页)
正是有见于唯理性所具有的自明与普遍的品格,笛卡尔向渴望建立具有科学尊严思想体系的哲学家推荐趋向几何学(more geometrico)的推理模式。在其看来,“凡只具备看似合理的事物,几乎都是虚假的”。([22],第8页)而一门唯理性的科学不能包含是非不明的观念,必须详细阐述适用于所有唯理性群体的必然的命题系统,对它们只能一致同意,而异议仅代表错误。([21],第2页)不管何时,只要两个人对同一事物做出相反的判断,两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是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掌握真理。因为只要其中一个人持有明确、清晰的理由,他就能以令对手信服的方式向后者讲解这一观点。([23],第11页)图尔敏则对笛卡尔的唯理性作了简要概述:“伴随着精密科学的兴起,随之而来的是唯理性的三个梦想:普遍方法、精确语言以及一元的自然体系,这些梦想也表达了新科学家对‘唯理性’的渴望。”([26],第67页)
笛卡尔以唯理性为核心的理性观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唯理性与数学理性一致,它是神圣理性的反映,旨在把握必然的联系,认识先验的、确定的、自明的和永恒的真理;二是在同一时刻它既是个体的又是普遍的,因为它在一个独特的心灵中展现出来,却又把自己的主题强加给所有理性存在者,且毫不逊色于经验和对话。它既不依赖于教育,也不依赖于环境或时代文化;三是唯理性与自明性真理以及令人信服的推理有关,其有效性仅限于理论领域,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唯理性”的行为符合原则和系统精神,行为的终止依据原因的知识,使用最有效的方法,并使人们的行为与思考、构思的结果相一致,不允许任何情感或情绪的介入;四是在基于唯理性构造出来的“人”形象中,人的理性往往与其他人类能力相分离,人是像机械装置那样运转的存在者,被剥夺了人性以及对环境的敏感性,与合情理的人相对立。([17],第117-118)
笛卡尔之后,他的唯理性思想为后来学者继承和发展。斯宾诺莎把这种思想完全几何化4斯宾诺莎在早期受笛卡尔哲学的影响,但其思想的两个特性与笛卡尔不同:一是宗教在斯宾诺莎与笛卡尔思想中扮演的角色不同,由于不受宗教教条的限制,他能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思想;二是斯宾诺莎受到某些犹太思想家的影响,后者比圣奥古斯丁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更进一步。参见([15],第139页)。,莱布尼茨使唯理性的演绎法与前者极端化了的几何学方法相混合,帕斯卡则直接利用笛卡尔的自明性理论。在人类思维过程中,笛卡尔唯理性思想的影响也极为深远,佩雷尔曼早期的学术思想就受到笛卡尔唯理性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1940年,佩雷尔曼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科学与哲学推理的相似性“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包括从某些原则以及从定义出发的演绎……一系列结果,并把这些结果与事实进行比较。”([12],第39-50页)在分析正义概念时,佩雷尔曼把形式正义规则作为所有唯理性活动的基础。([16])而从传统观点来看,哲学话语也是理性的论述,这种理性是神圣理性或模仿神圣理性阐明的一种永恒不变的能力,它为所有唯理性的个体共同具有,并构成人类的特殊性质。([17],第47页)事实上,佩雷尔曼的早期观念与其他哲学家一样,都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追求普遍与抽象的真理,这是因为它们对所有拥有唯理性能力的人来说易于理解,基于此,早期哲学家试图把自己的系统建立在必然性或自明性论题之上。
综上所述,自明性和普遍性是唯理性的重要特征,唯理性在处理人文科学领域问题彰显的不足,促使佩雷尔曼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声——欲使理性来指导我们自己的行动以及影响他人行动,使论证理论有立足之地,我们就必须挑战作为唯理性特征的自明性观念。([21],第3页)为此,我们应限制流行理性观的适用范围,倡导包含多样价值观和多样合理性的合情理性,以处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行为或价值判断相关问题。
3 佩雷尔曼的合情理性
在笛卡尔唯理性思想的影响下,由于其他方法无法彰显必然性的特性,逻辑学家只有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分析证明时才感到安心。在上个世纪,这种倾向得到有力加强。依佩雷尔曼之见,在数理逻辑学家的影响下,逻辑已经被局限于形式逻辑,即对数理科学中的证明方法的研究,其结果便是与纯粹形式领域无关的推理完全为逻辑甚至理性所排斥。([21],第1-2页)他在其他地方还指出,人们不仅试图把逻辑等同于形式逻辑,而且主张由于非形式推理不能被形式化,它们不再属于逻辑。这种看法导致了逻辑的真正贫困和一种狭隘的理性观。这就是说,一旦演证不可得,理性的统治将无法维系。“合情理的”观念甚至变得对逻辑来说很陌生,诸如“合情理的决定”、“合情理的选择”、“合情理的假设”的表达将因毫无意义而被弃之一旁。([17],第vii页)在这里,“理性”一词等同于“唯理性”。根据哲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各种不同形式,形式逻辑是演证和证实的唯一工具。如果唯理性的定义过于狭窄,那么包括政治和道德在内的整个行动领域都是非唯理性的(irrational)。([10],第18页)
在研究正义问题时,佩雷尔曼意识到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中间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由于每一个规范系统是武断的,逻辑上具有不确定性,人们不能从“是”推出“应该”。但是,通过调查我们在权衡、决策和选择时使用的推理方式,佩雷尔曼发现我们的行为不是武断的,而且我们能给出做出选择和决策更为可取的理由,由于行动哲学必不可少,因此我们需要价值判断逻辑。([20],第189页)在行为和决策中,由于两者不可能为真,它们被描述为正确的、适当的、合理的、公正的、沉思的、符合道德规范或者法律规定,对它们来说真值问题毫无意义。在哲学上,尽管传统形而上学试图揭开内在、永恒的原则,但佩雷尔曼相信哲学应该阐明合情理的存在、思想和行为的原则。([14],第5-19页)在其看来,“哲学的目标在于影响心智、赢得一致性,而不是进行命题的纯粹形式转换”。([15],第101页)
在以上论述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唯理性不能为人文科学领域提供决策的理性基础,二是人文科学领域也不是依据形式化的方式行事。如果使用唯理性来处理人文科学领域问题,就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的不对等,其原因在于人们对“逻辑”概念的狭隘理解,而形式逻辑又过度限制了理性概念的内涵,缩小了理性的适用范围。在其他地方,佩雷尔曼曾经表达了把逻辑归约为对形式推理研究的失望,他认为狭隘的逻辑领域对于人类科学、法律和所有哲学分支的方法论具有灾难性影响。([13],第245页)在探寻人类在不同领域做出决策的理性基础时,佩雷尔曼发现,笛卡尔的唯理性主义理论、形式逻辑的标准以及现代数学的程序都被证明毫无用处。([6],第13-14页)对于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唯理性局限性的认识,英国哲学家图尔敏(Stephen Toulmin)也表达了相同看法——形式逻辑学家使用“几何学”方法对待合情理性——“当且仅当我们对某事物有理由充足的信念时,我们对它才有所‘认识’(在这个术语充分而严格意义上讲);当且仅当我们能够提出充分的理由支持信念时,我们的信念才是理由充足的;当且仅当我们提出‘令人信服’或形式有效的论证,把信念引回到无法挑战(最好是无法挑战)的出发点时,我们的理由才真正‘充分’(依据最严格的哲学标准)”。([25],第89页)
基于对唯理性局限认识,佩雷尔曼主张应限制流行理性观的适用范围,倡导扩展的理性概念。在新修辞学中,他为人文学科提供了一个新的“合情理性”视角,它与古典理性主义相对立,证成哲学和政治的多元主义,这种理性“不是分析哲学家要求的纯粹形式,而是非形式的推理模式以及修辞学家使用了几个世纪的演讲方式。”([5],第1页)。有学者称这种合情理性为“弱的唯理性概念”或“修辞理性概念(the notion of rhetorical reason)”,它源自于对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重新解释。在《作为行为科学逻辑的修辞学》一文中,麦克斯罗·雷沃对修辞理性概念作了阐述,认为“修辞理性概念的研究与非规约性、含蓄和不明确的话语有关,它试图通过对其说明以获得在不确定性的边缘话语中被含蓄使用的推理系统的结构。这些不确定性话语会影响修辞理性概念,当话语的意义自身需要通过新的事实或情况予以辩护时,情况更是如此”。([8],第457-458页)佩雷尔曼希望合情理性能为法律、伦理学、哲学、政治争论和其他在严格逻辑意义上被认为不相干的领域提供理性基础,他相信真正的实践逻辑必定能应用到这些领域。([6],第28页)
一般说来,合情理性反对接受不加批判确立的现实,它促进多元变化,具有稳定性。([10],第20页)一个合情理的人,其判断和行为会受到常识的影响,他关注的是在所处情景之中以及情景之外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所有人都应当接受的。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位置,一个合情理的人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例外情况,而是力求遵守每个人都接受的行动原则,在其看来一条不能被普遍化的行动原则不合情理。即使他人认为可接受、合情理的行动原则,也不能随意地支持某些人或某些情况,也就是说,什么是合情理的必须成为先例以启发类似情况中的每个人,由此而言,一般化或普遍化的价值是合情理的特征。但是,一条行动原则在某一时刻或在某一情况下被定义为合情理的或是自明的,在另一时刻或不同情况下可能是武断的或荒谬的。在一个时代合情理的事情,在另一个时代并非如此;在今天合情理的事情,在昨天并非如此,依佩雷尔曼之见,合情理性像常识一样不断发生变化,它通常致力于一个更加一致、清晰和系统的观点,这也是变化的基础。([17],第118-119页)概而言之,合情理性(原文使用“合情合理”一词)更多地与人的行动和实践领域有关,它与常识、共通感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普遍的,但这种普遍性本身又内在于具体的情景之中。([29],第1-6页)
在新修辞学之后,佩雷尔曼有一个更加广泛、宏大的目标,他希望建立人类决策制定的理性基础。虽然他自己的知识经历较为完整,摆脱了早期事业的实证主义假设,但是由于笛卡尔唯理性主义理论者和现代数理逻辑学家两个群体对其所属哲学团体仍有重要影响,他认为这两个群体对依然流行的理性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6],第27页)通过对比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佩雷尔曼不仅指出人类思维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也表明人们理解理性的两个不同视角。在传统哲学中,唯理性彰显普遍性、必然性和自明性的真理,偏爱演证的方法,后者主要是现代形式逻辑研究的对象;合情理性表达对情境性、变化性以及可接受性的偏爱,使用论证的方法。([7],第1-15页)
4 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辩证关系
以上论述可知,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的不同在于评判某一行为、言论或其他相关对象时,唯理性服从某种绝对法则,合情理性则依据修辞学的要求,以听众遵从为导向。但有时候,唯理性依据的逻辑一致性与不合情理的结论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反映出唯理性与合情理既对立又统一,构成了思想进步的基础。([17],第120页)在《唯理性与合情理性》一文中,佩雷尔曼详细阐述了唯理性与合请理性的辩证关系在法律中如何得以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唯理性与合情理性用途不同。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把唯理性等同于自然法(natural law),后者规则由上帝自己制定,并通过“理性之光(the light of reason)”来教导人们,这些法律往往陈述永恒的正义,但无论是成为法还是不成文法,没有任何人的权柄可以废除或改变它们。在大陆法系中,作为服从上帝理性的人类理性思想已沦落为立法者的唯理性思想,这是解释法律文本的先决条件。为了保持法律体系的一致性,立法者应知道自己使用的语言以及新的法律被嵌入的体系,而且立法者使用的方法应与其追求的目标相适应。在法律中,唯理性相当于遵从一个永恒不变的神圣标准,或遵从法律体系的精神、逻辑性和一致性、依照判例和目的性。([17],第120-121页)
在法律中,合情理性表征判决自身,描述民意认为可以接受或不可以接受的事实,后果对社会是有益或是有害的,它是公正的或是有偏见的。([17],第121页)合情理性的要素具有不同作用,首先,合情理性用以确立法律体系运行之内的外部界限,它假定法定权力将会得到合理地行使,一个“不合情理的”法案和判决在法律中不可接受。其次,法律合情理的方面决定了具体判决的语境,对社会的影响及其社会的可接受性是客观公正的。佩雷尔曼指出,在法律体系中,不同机构或部门强调唯理性或合情理性取决于它们的具体职能。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倾向于维护在宪法中、法院判决和意见的先例中确立的法律原则,法律体系的逻辑一致性是最高法院关心的主要问题,这类法院强调“唯理性”。地方法院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具体判决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以及解决问题方法的合情理性,这类法院强调“合情理性”。因此,在不同级别的法院运作中存在冲突或张力的内在联系,这种张力也是一个法律体系必要驱动力(necessary dynamics)的组成部分。([24],第189-190页)
其次,唯理性与合情理相互支持。
在斯坦利·劳克林和丹尼尔·休斯看来,佩雷尔曼理论的中心主题为唯理性和合情理性分别代表两种法律的本质和动态互补性,它们对一个健康的法律体系来说必不可少。“唯理性”要素使得人际交往更具一致性、更为有序和更容易预测,它使我们能够建立和维护社会组织必要的人际互动。如果法律的唯理性不受合情理性的影响和限制,那将会非常可怕,只有法律合情理的方面才能使其更加人性化,使社会组织更具容忍性。([24],第190页)当唯理性与合情理性彼此相互支持,当依据法则的推理以令人满意的决定结束时,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当忠诚于法律体系精神却导致一个不可接受、有偏见或社会不接受的结论时,或结论是一个不合情理的决定时,有必要对法律体系进行重新思考。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教义学(doctrine)与法理学(jurisprudence)通过部分修改法律体系的方法来寻求冲突的解决方法。但有时候,证成起初看似公平、合情理的判决通常需要诉诸于虚构(fiction),而虚构可能是描述与实在或明显动机相悖的事实。([17],第121-122页)
在法律缺少严格裁决规则时,合情理的思想相当于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但是,佩雷尔曼指出诉诸合情理性仅仅是给出一个暂时解决方法,它需要等待对新的、令人满意法律解释(legal construction)的详细阐述。而合情理性是引导其走向系统化、走向唯理性系统的解决方法。([17],第123页)
5 结语
基于对价值判断理性基础的探寻,佩雷尔曼意识到传统理性概念的定义过窄,理性等同于唯理性;理性的适应范围过于宽泛,不仅包括形式领域,也包括人文科学领域。通过对传统理性概念的批判,既限制了流行唯理性的适用范围,也为合情理性的可能性与合法性提供了辩护。而合情理性的提出丰富了传统理性概念的内涵,以其为基础的佩氏理性观不仅构成新修辞学论证理论的哲学基础,而且对于将包括非形式逻辑在内的论证理论置于更为健全的哲学基础之上也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佩雷尔曼所倡导的合情理性在终结独断式的唯理性观的同时,也开启了人们对合情理性相对性的反思。爱默伦认为论证的可靠性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论证试图影响的人,这就意味着论证的可靠性总是和听众相关,而可靠性标准的后果是流行的理性规范与武断的人群相关。佩雷尔曼提供了一种完全相对的理性标准。([3],第115-116页)欲使合情理性成为人类决策的理性基础,应避免对合情理性的不同理解而出现的对立状况,为合情理性提供清晰、可行的标准是规避其走向相对性的可能途径。
[1]Aristotle,1991,TheCompleteWorksofAristotl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F.H.van Eemeren and R.Grootendorst,2004,A Systematic Theory of Argumentation:The Pragma-Dialectical Approac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F.H.van Eemeren,R.Grootendorst and F.S.Henkemans,1996,Fundamentals of Argumentation Theory,Mahwah(N.J.):Erlbaum.
[4]W.R.Fisher,1986,“Judging the quality of audience and narrative rationality”,PracticalReasoninginHumanAffairs.StudiesinHonorofChaimPerelman,Dordrecht/Boston/Lancaster/Tokyo: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5]J.T.Gage,2011,“Introduction”,in J.T.Gage(ed.),The Promise of Reason:Studies in The New Rhetoric,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6]A.G.Gross and R.D.Dearin,2003,Chaim Perelma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7]R.Jin,2011,“Rationality,reasonableness and informal logic:A case study of Chaim Perelman”,in F.Zenker(ed.),Argumentation:Cognition and Community:Proceeding of the 9th Biennial Conference of OSSA,University of Windsor,Canada,pp.1-15.
[8]M.Loreau,1965,“Rhetoric as the logic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51(4):455-463.
[9]J.R.Lucas,1980,On Justi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0]M.Maneli,1994,Perelman's New Rhetoric as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for the Next Century,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1]B.Pascal,1952,On Geometrical Demonstration,Section II:Concerning the Art of Persuasion,Chicago:Brittanica.
[12]C.Perelman,1940,“Une conception de la philosophie”,Revue de l'Institut de Sociologie,20:39-50.
[13]C.Perelman,1955,“Reply to Henry W.Johnstone”,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16(2):245-247.
[14]C.Perelman,1964,“On self-evidence in metaphysics”,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4:5-19.
[15]C.Perelman,1965,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Thinking,New York:Random House.
[16]C.Perelman,1967,Justice,New York:Random House.
[17]C.Perelman,1979,The New Rhetoric and the Humanities:Essays on Rhetoric and Its Applications,Dordrecht/Boston/London: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8]C.Perelman,1979,“Therationalandthereasonable”,inT.F.Geraets(ed.),Rationality today,Ottawa: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19]C.Perelman,1982,The Realm of Rhetoric,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C.Perelman,1984,“The new rhetoric and the rhetoricians:Remembrance and comments”,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70:188-196.
[21]C.Perelman and L.Olbrechts-Tyteca,1969,The New Rhetoric:A Treatise on Argumentation,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2]R.Descartes,translatedbyE.S.HaldaneandG.R.T.Ross,2003,DiscourseonMethod and Meditations,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23]R.Descartes,translated by J.Cottingham,R.Stoothoff and D.Murdoch,1984,The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Descart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4]K.L.Stanley and T.H.Daniel,1986,“The rational and the reasonable:Dialectic or parallel systems?”,Practical Reasoning in Human Affairs:Studies in Honor of Chaim Perelman,Dordrecht/Boston/Lancaster/Tokyo: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25]S.Toulmin,1976,Knowing and Acting:An Introduction to Reasoning,New York:Macm-illanp.
[26]S.Toulmin,2001,Return to Reas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7]蔡广超,“佩雷尔曼的‘准逻辑论证’及其结构重建”,逻辑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95-117页。
[28]笛卡尔(著),王太庆(译),谈谈方法(第三部分),200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29]晋荣东,“现代逻辑的理性观及其知识论根源”,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6页。
[30]李超杰,近代西方哲学的精神,2011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31]廖义铭,佩雷尔曼之新修辞学,1997年,台湾:唐山出版社。
[32]亚里士多德(著),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1992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任天鸿)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the rational basis of value judgments,Perelman realized the limit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reason,and distinguished two kinds of“reason”:rationalityandreasonableness.Perelman'scriticismtotraditionalconceptofreason not only limited the scope of the application of rationality which occupied dominant position for a long time,but also offered a defense for the poss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 reasonableness.In legal argumentation,there is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antinomy and identity between the two concrete forms of reason.On the one hand,there are conflicts between the rational basis of logical consistency and the unreasonable conclusion;on the other hand,rationality and reasonableness support each oth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uthor,on the basis of the reasonableness,Perelman's reason view not only constitute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argumentation theory of new rhetoric,but also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which the theory of argumentation including informal logic is put on a more sound philosophical basis.
Perelman's Views of Reason
Guangchao Ca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Yan'an University
ljxcgc@126.com
B81
A
2015-12-28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批判性思维的理论基础与培养策略研究(13CZX063)、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佩雷尔曼论证理论的哲学基础研究(16JK1837)和延安大学校级科研计划项目(YDQ2014-24)资助。
†致谢:感谢我的导师晋荣东教授、延安大学武宏志教授对本文初稿出的意见和建议,感谢本文匿名评审专家、责任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使我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