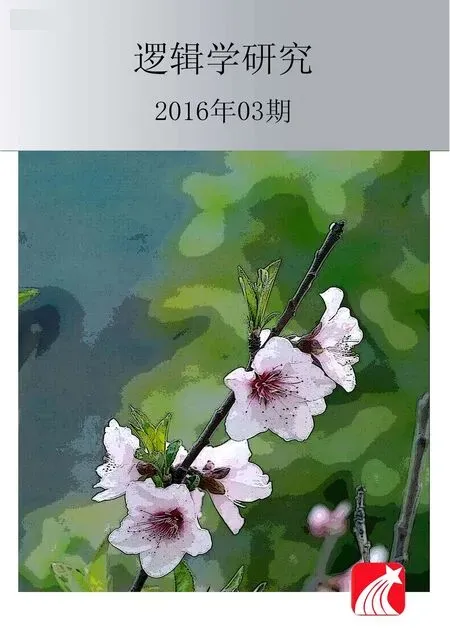批判性思维的灵魂——理性标准*
2016-02-02武宏志
武宏志
延安大学21世纪新逻辑研究院
yaydwhz@126.com
批判性思维的灵魂——理性标准*
武宏志
延安大学21世纪新逻辑研究院
yaydwhz@126.com
批判性思维从怀疑出发,激发思考问题的多元视角,但它更重要的任务是依据理性标准对相互竞争的观点及其论证的相对价值做出判断。理性标准是批判性思维与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分水岭;批判性思维的本质以及大多数权威的批判性思维定义都内蕴了理性标准;每一项批判性思维技能都与相应的理性标准相匹配;不同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法也或隐或显地认可一系列理性标准。理性标准是让学生从绝对主义的二元论思维升华到评估主义的批判性思维的关键。中国的“明辨”虽然与西方的批判性思维有相似之处,但明显的差距在于缺少精细的理性标准。培育公民思维文化,营造健康的论证文化,都离不开理性标准这个根基。
批判性思维;理性标准;批判性思维技能;批判性思维教学法
批判性思维的研究与教学在我国方兴未艾。但是,人们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存在表面化和片面化的倾向。比如,不少老师所从事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活动,仅仅限于鼓励学生提出怀疑、反对或不同看法,根本没有触及到批判性思维内核——根据理性标准对不同主张的相对价值做出判断。这种批判性思维教学容易蜕变为相对主义,让学生误以为各视角、观点和论证都是“半斤八两”,混淆了“人人有表达自己看法的权利”与“每个人的看法同样有理”,没有理解批判性思维是基于所确认的一套标准来评估断言之相对价值的工具。批判性思维教学应注重明示和阐述一系列理性标准,促使学生从认知的多元论者水平发展到评估论者水平,成为真正的批判性思维者。
1 理性标准是批判性思维与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分水岭
质疑,问“为什么”,从不同视角提出不同看法,继而在多元可能选择中根据理性标准确定最佳答案,这是批判性思维的主线。这条主线包含三个环节:质疑、提问或怀疑——多元意见(替代选择)——最佳选择(判断)。理性判断预设了理性标准。Critical Thinking词组中的critical一词源自两个希腊词kritikos(辨别,判断)和kriterion(标准),因而批判性思维意味着“基于标准的辨别性判断”的发展。([16],第4页)
虽然批判性思维从怀疑发动,但怀疑尚不足以构成完整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也倡导多元视角、多元意见,否认某种看法的先天优越性,但止步于多元性和相对性,同样不是健全的批判性思维。把批判性思维与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区别开来的恰恰是基于理性标准的论证和判断。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也珍视怀疑、否定和多元意见。比如,巴门尼德、芝诺、麦里梭、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这些思想家都觉得,我们用感官发现的原始观念可能都是不可靠的,都需要不断被检验。([20],第66-67、79、128-129页)智者对传统的文化采取怀疑、否定的态度。“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哲学概括,也是相对主义的,最终导致怀疑主义。([33],第303、308、312页)
为什么这些表达怀疑论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没有被尊为批判性思维的始祖?因为他们未曾注重理性原则和标准。相反,苏格拉底有一个关于“真正的知识应当是什么样的”可靠的严格的标准,并且知道人们要达到这个标准还差多么远。([30],第27页)公元前5世纪中叶,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怀疑论,对认识自然的可能性抱有怀疑。如果根据表面印象说苏格拉底也不过是一个怀疑论者,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苏格拉底关心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共同原则。([30],第34、82、91页)亚里士多德指出,苏格拉底的认识论和科学方法是归纳和普遍定义。该方法假定:真理是个一致的系统,与一个真原则相冲突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为真。([30],第96、99-100页)归纳法旨在得到一种逻辑上真实的准则,主要目标是确定概念即确立定义。那个时代的理智主义特征——努力做到用鲜明概括的概念和清晰的理解来代替不清楚的观念和模糊的猜测,在苏格拉底身上达到顶峰。他肯定批判的权利,即用由经验和推理查明适合于推进人类福利的单一标准来批判所有权威和所有传统,批判所有制度、法令和戒律的衡量标准。按此方法,每个机构、戒律、行动规则都被看作是实现清楚理解的手段,并检验它迄今为止的妥适性。([30],第135-136、146、149-150页)可见,苏格拉底成为批判性思维的始祖不只是因为他怀疑,提出不同看法,更因为他的探究性质疑(probing questioning)方法,这种方法所依据的一个核心标准就是一致性。
现代批判性思维的先驱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提倡的“反省性思维”本质上是假说的系统检验,有时也称为“科学方法”。假说检验的标准可能包括:可检验性(testability)——是否能被检验;丰富性(fruitfulness)——是否成功地预见新现象;广泛性(scope)——所解释的多种现象的数量;简单性(simplicity)——所做出的假定的数量;保守性(conservatism)——与已确立信念相符合的程度等。([32],第180-189页)质疑,问为什么,考虑问题的多种可能答案并根据理性标准进行估量和权衡,获取一个基于当下证据的最佳答案,这才是批判性思维的完整过程。关键是,最佳答案是从可能解决方案中筛选出来的,而这种筛选必定以某种理性标准为依据。
与怀疑主义者、绝对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不同,批判性思维者是评估主义者。他承认不同意见存在的合理性,也承认基于证据的估量和平衡可以在这些意见之中区分出理由充分的意见和无充分理由的意见。正是基于理性标准的评估,批判性思维者与绝对主义者和相对主义者可以被区别开来。人的认识论理解起源于孩提时代。孩童持有这样一种认识论:所有信念都直接来自外部世界,而不是由认识者建构的。因此,人人都理解同一个外部实在或客观现实,不存在事件的不正确呈现,也没有冲突意见的任何可能性。那些认为来自外部来源的知识是确定的,断言是外部实在之拷贝的人,他们没有批判性思维的需求。可是,一旦认识到断言是心灵做出的,不一定符合实在,断言之间现在就变得有所区别了。此时,出现了科学思维的可能性。但是,认识的产品暂时依然附属于认识对象而不是认识者。在这种“绝对主义者”水平上,知识被看作是某些事实的累加集。断言是实在的表征,是正确或不正确的事实。知识来自外部来源,是确定的,但不是直接可获得的,可能生成虚假信念。所以,批判性思维是比较断言与实在,决定断言之真假的工具。绝对主义的认识论信念在童年期占主导。八、九岁的儿童认识到,个体心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实在,但绝对真理依然存在,只要相关信息披露出来,就可以知道这个绝对真理。一个人是对的,其他人是错的。不过,过渡到“多元主义者”或“相对主义者”水平构成进一步发展的特征。青春初期出现了向多元主义转变的可能性。理性人甚至专家也有意见分歧。从多元主义视角看,知识并不是由事实构成,而是由意见构成,是其拥有者自由选择的个人财产。断言是被其拥有者自由选择的意见,人人有权提出自己的意见。知识现在被看作是出自认识者,而非被认识的对象。这种在认识论理解上的进步,以协调认识的主观与客观元素为特征。但是,这种协调却付出了重大代价:竞争的知识主张之间没有任何可区别性,承认多元意见至少暂时遮蔽了对可以充当评估冲突主张之基础的任何客观标准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批判性思维毫不相干。然而,在青春晚期,许多青少年将会恢复认识的客观维度,达到这样的理解:虽然人人都有权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对信念的证明不只是个人喜好。从得到论证和证据的更好支持的意义上来说,某些意见比别的意见更恰当。在认识论理解的“评估主义者”水平上,认识被看作是由判断构成的,它需要用一种替代选择、证据和论证的架构来支持,可以按照论证和证据的标准进行评估和比较。知识是人的心智生成的,不确定,但对评估敏感。此时,特别需要批判性思维,因为它是基于确认的一套标准来评估断言相对价值的工具。([12],第28-30页)
说到“怀疑”,需要注意当今的几种不同含义。1.一般性的怀疑,多数人在某段时间都经历过。比如,我们可能普遍对推销员等抱有怀疑。在这里,评价和决策可能受到乐观或悲观、恐惧、无知、先入之见、宣传、偏见或偏执的影响,有时根本没有批判性思维。2.特定的怀疑,代表一种对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具体情况尤其是伪科学和超自然理念的态度。伪科学对世界如何运行持一种与既定的、公认的理解相矛盾的主张,可能使用未经证明的(甚或已被否证的)方法论和世界观。超自然理念的持有者着眼于直接否认广泛接受的科学证据,肯定超自然力、透视眼、不明飞行物、占星术、反常生物、算命、麦田圈和神创说等。这种怀疑论所采取的观点并不是说这些事物不真或不可能真,而是认为它们未被证明。在某些情况下,某个论题支持证据的可能性接近于零。3.批判的怀疑,用来描述更为正式的怀疑论运动。有许多城市、州、地区和国家的大大小小的怀疑论者团体,它们独立活动但通过共享一种态度和方法而联系起来。有不少出版的通讯或杂志、网站、博客和播客,使用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以及其他社交媒体相互联系,有定期的社会集结(常在酒吧和咖啡馆)。批判性思维是怀疑方法的基本信条。这是一种巩固全部活动和发现,利用科学方法(研究、分析和同行评审)给我们的观点提供证据的方法。这些怀疑论者很可能比别人耗费更多的时间践行自己内化了的批判性思维,也分析他们自己的动机和行动。批判性思维导致好决策,对别人也有帮助。而别的替代可能带来更多的恐惧、疑心甚至对他人的怨恨,常常鼓励无知。有些伪科学和超常现象理念的提供者常常竭力阻止提问和审议。([19])可见,后两种怀疑论者由于注重根据理性标准的分析和评价,因而实际上也是批判性思维者。
2 批判性思维内蕴理性标准
当代重要的批判性思维专家都强调理性标准在批判性思维中的核心地位,批判性思维的权威定义都反映了理性标准的关键性。研究批判性思维定义40余年的恩尼斯(Robert H.Ennis)在说明自己批判性思维定义的特点和优势时,总是突出“做出判断的标准”,“合理性(reasonableness)”和“帮助我们评估结果的标准”。恩尼斯的论著常常出现这样一簇词:rationality、rational、reasonableness、reasonable等。大致说来,前两个所指的“合理性”、“合理的”往往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相联系,甚至“合理性”就是形式逻辑的“逻辑性”(logicality),即与某种形式算法相联系的合理性。在图尔敏(S.E.Toulmin)等人对这个合理性概念的批判之后,人们开始区分合理性的实质概念与合理性的形式(逻辑)概念。有时用reasonableness来表示实质合理性,相应也就有了rational和reasonable这两个有所区别的形容词。恩尼斯批判性思维定义中所用的“reasonable”是实质合理性意义上的,它与评估标准相联系。在日常用法中,当人们说某人某事是“合理的”时,泛指它与普遍的原则、规律或公认的目标相一致,而且具有好思维的某些品质,比如一致性、融贯性、清晰、理由充分等等。([7])可见,恩尼斯定义中的reasonable一词强调批判性思维的标准或规范维度,而reflective一词突出怀疑、审慎判断和元认知。恩尼斯最近描述自己定义的10个特征时把“强调精细的标准”列在首位。([9],第9-12页)在他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清单里,澄清、判断来源、观察、假说、定义等均有相应的具体标准。在最新论述中,恩尼斯继续提醒读者注意“做出关于信什么或做什么之决定的标准和原则”。([8],第45页)
批判性思维教育的一种著名形式——儿童哲学的创始人李普曼(Matthew Lipman)的批判性思维定义也突出理性标准:“批判性思维是促成好判断的娴熟的、合理的(负责任的)思维。因为它依赖于规范,它是自我校正的,对语境敏感的。”([15],第28、212页)任何给定的准则或判据(criterion)既指示要比较或测量的实质内容,也指示代表实际比较或测量的程序方面。概括地说,一个准则(比如拼写的准确性)由现象或行为组成(如拼写),它可以被测量,从而允许基于比较基础做出判断。标准(standard)指示基于素材的测量方式,即所讨论的哪个行为将达到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水平或评价。在传统教育中,教育者负责建立标准,学生负责达成它们。人们构建的批判性思维架构一般都以规则、原则、准则和标准为重点。([13],第3页)李普曼还认为,批判性思维的结果是判断,判断涉及一般标准和“标准的标准”——准则。批判性思维是既使用准则也被这些准则加以评估的那种思维。准则的意思是“做出判断时所利用的规则或原则”,它是一类特别可靠的理由。每当我们提出一个主张或表达一个看法时,如果不能用理由支持它们的话,就容易受到攻击。批判性思维依赖经过长时间检验的准则,比如有效性、基于证据的担保(warrant)和一致性。以逻辑为手段,我们能够有效地扩展自己的思维;以准则这样的理由为手段,我们可以辩护和保卫我们的思维。好理由必须对所讨论的看法是相干的,比所讨论的看法更强有力——更易于被接受或假定是如此。有一些用来挑选准则的准则——元准则。把相干的、有力的理由当作是好理由,意味着可靠性、有力和相干性是重要的元准则。从日常思维到好思维的改善极为依赖学生为自己的看法发现和引用好理由。([14],第150-151页)
西格尔(Harvey Siegel)主张一种认识论视角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将批判性思维等同于合理性。批判性思维的关键能力是“恰当地评估理由的能力”,而支配理由评估的原则有两种类型:“学科专属”的原则和“学科中立”的原则,后者即是形式的和非形式的逻辑原则。恰当的理由是由逻辑分析的原则和规范决定的。如果一个主张排除了“武断、不一致、偏爱”,那么它就有恰当的理由或被证明是正当合理的,这假定了对普遍、客观标准的约束力量的承认。([26],第23、30-34)当我们谈论思维者的思维技能或能力时,我们不是在谈论任何暧昧的私下心理实体或过程,也不是不假思索的习惯行为或无须动脑筋的惯例,而是谈论思维的质量。思维的熟练程度即是满足控制质量的相关准则和相关标准的程度。西格尔坚持强调按照质量标准来理解成熟的思维:使用所要满足的相关标准对思维做出了肯定性的规范评估。西格尔和论辩对手约翰逊(Stephen Johnson)都批评对思维技能的不当理解和许多教学法瑕疵,同时也赞成重视思维的基本规范。“思维的纯熟恰恰是就一定质量而言的,即对相关标准的满足达到了适当程度。”([27],第60、83页)伯林(Sharon Bailin)和巴特斯比(Mark Battersby)倡导一种教授批判性思维的探询方法(inquiry approach),指出探询要求聚焦于议题或争点(issue),因为探询是由某个需要解决的挑战、争议或意见分歧发动的。探询包括对证据、论证和观点的批判性审查,它不只是信息收集,关键是按照相关准则或判据(criterion)进行批判性评估。探询的目标是获得理由充分的判断,不只是一个有理由的判断,而是有好理由的判断,满足相关标准(standards)的判断。而且,做出理由充分的判断不可能仅凭评估个体论证,而是要求对竞争论证和看法进行比较性评估。([1],第126页)
梅可派克(John E.McPeck)认为,至少就其表面来看,也许批判性思维最为突出的特性是:它包含一种对某一给定陈述、既定的做事规范或模式的怀疑论或暂停同意。([17],第6、8-9页)批判性思维可“非形式地”定义为:以反省的怀疑论从事一种活动的倾向和技能。“反省的”指的是熟思的质量或水平,因而批判性思维者看来能够提供一个似真的替代选择;批判性思维也蕴含着一种由经验所调和的怀疑论的明智运用,这种明智的怀疑论的标准来自所讨论的特殊主题领域。([18],第78页)
美国哲学学会“德尔菲项目”(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批判性思维定义)主持人费西万(Peter A.Facione)根据该项目得到的批判性思维专家共识定义,提出最新表述:批判性思维是反省性判断的过程,它体现在为了决定信什么或做什么而对证据、语境、方法、标准和概念化的理性思考(reasoned consideration)之中。([10],第10页)非形式逻辑学家约翰逊(Ralph H.Johnson)认为,批判性思维是基于适当的标准或规范,判断一个智力产品,包括信念、理论、假说、新报道和论证。([11],第49页)
保罗(Richard Paul,1937-2015)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和整个体系由思想8元素和一般理智标准(intellectual standards)构成。“批判性思维是以改善思维为目的的分析和评价思维的过程。它预设思维最基本结构(思想的元素)和最基本的理智标准(普遍理智标准)的知识。批判性思维之创造性方面(思维的实际改善)的关键在于把思维重建为对其分析和有效评价的结果。”([3],第38页)批判性思维以超越主题内容的普遍理智价值即理性标准为基础,思想8元素中的每一个元素都要经受这些标准的检验。保罗和埃尔德(Linda Elder)指出,标准把我们导向始终如一的卓越思维,藉此我们可以保持思维走在正道上,帮助我们将现实中发生的事物反映到我们的思想里,揭示情境的真相,使我们能够决定如何最佳地过好我们的人生。当我们认真对待这些理智标准时,这种明确性将导向对这些标准及其对人类生活之重要性的更高水平的认识。它将使学生和教师能够在每一领域或科目中更有成效地思考,更好地思考这些领域或科目本身。理智标准的概念化以下述7个假设为基础:
1.理智标准的术语扎根于日常语言,被每一科目、学科和人类思想领域所预设;
2.为了规训人们的思维,我们可以从自然语言现有理智标准的丰富表现形式中提炼普遍理智标准;
3.理智标准形成相互关联的意义群集,可以将它们放在如清晰性、正确性、精确性、相干性、重要性和公正性这样一些范畴标题之下;
4.自然语言中的很多概念(如正直、同理心、公平心)尽管本身不是理智标准,但预设理智标准;
5.要使人们在高技能水平上运用理智标准,系统化的培养是必需的;
6.在科目和学科的整个推理过程中,为了恰当地监控,应该将希望人们坚持的理智标准明确表述出来;
7.始终如一地、明确地满足理智标准对于控制人们的生活质量是重要的,更一般地说,对于塑造由衷重视批判性思维的社会是重要的。
理智标准是在规训人类心智在思维上的可能优势与弱点的过程中形成的概念,它们体现为语境中的理智标准词汇的合适使用。所谓的“理智标准”,更准确地说是“理智标准词汇”。所有现代语言都给其使用者提供了广泛的理智标准词汇,恰当使用的自然语言可以担当评价推理的合理指南。([5],第34-35页)保罗和埃尔德假定,至少有9个基本理智标准对日常生活中的纯熟推理是重要的:清晰性、正确性、精确性、相干性、深度、广度、逻辑性、重要性和公正性。任何正确的推理不可能违反这些标准。从这9个理智标准出发,将帮助我们为说明更广泛的理智标准和认识理智标准在人类推理中的基本角色打好基础。([24])标准对于做出正确判断、良好推理,形成知识,生成理性的、合乎逻辑的思维,都是必需的。使用理智标准意味着更好的判断标准和理性理解的标准。它们对于人们持续关注和评价自身思维和他人思维的优势与不足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大多数人似乎难得仔细考虑他们在决定接受什么、拒斥什么时所使用的标准。人的心智并不是自然而然地执行理智标准,而是倾向于使用有缺陷的标准——往往是非常自我中心和群体中心的那些标准。相反,有公平心的批判性思维者认识到满足理智标准在实现个人抱负的理性生活过程中的基本作用,因而满足这些标准成为他们的常规工作。他们能识别出自己和他人何时没有满足这些标准。([6],第33页)当然,还有一些可以在某些语境中应用的其他标准,如完全性、有效性、合理性、充分性、必然性、可行性、相容性、真实性、实效性、效能等。人们还可以确认与自己的情境相关的其他标准。保罗和埃尔德认为,普遍理智标准组成概念群集(conceptual constellations)或概念网络,每个标准都有可辨识的核心意义,但最好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之中来理解,最终作为一种相互关联和集成的概念系统,即理智标准词汇形成相互关联的意义系统。理智标准以各种方式相互关联,有时交叠,常常表现为很长的连续体(服务于一系列目标)的概念网络。同时,在英语或任何其他自然语言中,有至少几百个语词有资格成为特殊语境中的理智标准术语,因而理智标准术语构成一个个群组,其中一般理智标准术语作为位于中心的范式概念或核心概念,围绕它的是若干近似术语(同义词或近义词)。当然,在每一群组之内,会发现其对立面。例如,一般理智标准相干性(Relevant)作为一个标准群组的核心术语,围绕它的有逻辑上的精确的相干性(Pertinent)、紧密相关(Germane)、贴切(Apposite)、适切(Apropos)等,而其对立面是不相干(Irrelevant)等。要对任何特定理智标准形成准确的理解,需要知道标准可能在多种语境中被违反的方式,研究理智标准与其对立面的关系。理智标准与自然认知过程相联系,人们常常错误地构想分析、综合、比较和对照这些暗中坚持理智标准的认知过程,可能使得理智标准更容易违反。保罗和埃尔德呼吁,应该将理智标准置于教和学的中心。可惜,全世界的大学离这个现实还很远。([25],第35页)
保罗和埃尔德还系统总结和阐述了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标准”(competency standards)。要让学生学会批判性思维,老师就要明确地教授批判性思维,而标准对这样的教学必不可少。只有大多数教师在他们所教的科目中培育批判性思维标准,才能希望学生获得这些能力。这些标准包括鉴别学生把批判性思维用作学习基本工具的程度。那些内化这些能力标准的学生将看到,批判性思维导致有效交流和问题解决技能以及克服一个人的自我中心和群体中心的天然倾向。([3],第38页)思维8元素中的每一元素都对应一个能力集,每一能力集都匹配标准、指导原则、执行指标和学习成果。([22])这样,能力就用这4个成分来定义:
1.该标准勾勒出特殊能力集所瞄准的首要的批判性思维倾向;
2.指导原则提供标准背后的假设;
3.执行指标描绘包括批判性思维倾向在内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4.学习成果是教师可以直接评价的可测量的学生活动或行为。
据此,教师可以判定学生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能力的具体部分。仅当学生合意地取得了某一能力之内的全部成果,才算达到了能力标准。([21],第36页)同样,公正心、理智的谦逊、理智的勇气和理智的同理心(intellectual empathy)这四个基本理智德性能力也属于最重要能力之列,它们对于培养有公正心的批判性思维者和营造公正的批判性社会,都不可或缺。它们也有相应的标准、原则、执行指标和学习成果。([4])此外,他们还讨论了具体学科,如精读艺术、实质性写作(substantive writing)艺术和伦理推理艺术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标准。([23])
3 批判性思维技能及其教学以理性标准为核心
批判性思维技能通过满足匹配的理性标准显现出来。一种可教、可测、可比较的批判性思维技能系统,必定伴随理性标准的适用。任何一种可以在教学中落实的批判性思维定义,必定匹配成套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和相应理性标准的清单。例如,我们可以先判断某一主张来源的可靠性,继而决定对该断言的态度。完成这种判断就是要依据标准展开一系列检验。判断来源可信性的标准是:1.专家意见;2.没有利益冲突;3.与其他来源一致;4.声誉;5.常规程序的使用;6.知道冒声誉的风险;7.给出理由的能力;8.仔细的习惯。对基于观察与观察报告的断言,要根据以下标准进行评估:1.包括最低限度的推论;2.观察和报告之间时间间隔较短;3.由观察者而非其他人报告;4.提供记录;5.证实;6.证实的可能性;7.良好的观察机会;8.在适用的情况下恰当使用技术;9.观察者或报告者满足可信性标准。([9],第16页)而且,在评估中,我们一方面需要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也需要预见、考虑和反驳不同的尤其是对立的观点及其论证,这便是约翰逊所看重的论证的“辩证充分性”(dialectical sufficiency)。不过,这种考虑替代选择的“平衡”有不同的水平,也就是满足标准的程度不同。在水平0,有良好的单边论证,即有支持自己观点的有效而清晰阐述的论证;在水平1,清晰阐述了支持自己观点的论证,也提到相反论证,但没有予以反驳;在水平2,虽然清晰阐述了支持自己观点的论证,也准确说明了相反论证,但并没有较好地发展反驳;在水平3,不仅清晰阐述了支持自己观点的论证,也充分使用合理反驳对相反论证予以合理评估,提供了平衡的结论。([2],第75页)话语清晰性的一般标准至少包括:用自己的话清晰而准确地表述概念和断言;用不同方式清晰而准确地重新表达概念和断言;了解概念和断言的含义与涉及的范围;能举出属于和不属于某个概念的实例;能辨别和处理概念和断言的多义性;能识别和处理概念和断言的含混性;能对概念的定义做出初步分析。
批判性思维的理性标准是批判性思维技能和方法的基础。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技能——论证技能牵涉不同层次的标准。比如,保罗9个一般理智标准中的“逻辑性”标准就可以展开为一个多层级的标准系统。在这个最一般标准之下,有“论证标准”,论证标准可以更具体化为非形式逻辑学家的“RAS”(相干性、可接受性和充分性)标准,进一步体现为采用不同推理形式的各种论证的标准,比如演绎有效性等;而落实到合情论证(plausible argument)时,更细化为匹配某一论证型式(argument scheme)的批判性问题所代表的标准。可见,从标准角度看,批判性思维的学习和教学并不那么轻松,要掌握一个小小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或方法,恐怕也要牵涉到一系列概念和理论。例如,分析“人身攻击”谬误,不能如人们常常那样大而化之,而要考虑提出这种论证的意图,使用这种论证的语境,品格与议题的相干性,对待结论的态度等等。这就显示出评价该论证之标准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由此,我们想到伍兹(John Woods)从谬误研究引出的关于论证评价标准的“革命性”思想。论证的传统评价标准是“错误标准”,“传统逻辑学家极度沉溺于有效性和归纳强标准,使推理的出错率人为地变高,达到了完全拒斥第三方式推理的地步。”演绎有效性和归纳强的标准在一些语境中是要强制实行的标准。数学证明要求有效性标准,样本到总体的理论探索,统计―实验科学的其他形式,要求归纳强的标准。然而,大多数人类推理发生在不同的语境中。像我们这样的存在物所处的认知生态就不太一样:我们的认知议程适应我们的兴趣和环境,我们的推理与我们获得成功结果所需的条件是成比例的,大多数推理是第三方式推理,对它而言,有效性和归纳强都不是合适的正确性标准。([29],第518页)
任何批判性思维教学法都与理性标准有关,区别仅在于是否在教学过程中明确阐述这些理性标准。目前,批判性思维教学法有三条主要路径:一般方法、学科方法和混合方法。一般方法承认普遍标准,当然也假设存在一般思维技能。大学里设置的批判性思维独立课程是一般方法的典型形式,它以教授批判性思维技能及其标准为目标。学科方法包括浸没法(Immersion)和注入法(Infusion),以教授学科内容为目标,但采用的是批判性思维方法或渗透着批判性思维技能。浸没法是在学科课程中潜移默化具体学科的批判性思维,如历史课的“像历史家一样思维”,科学课程的“像科学家一样思维”,法律课程的“像法律人一样思维”。浸没法从来不明示具体学科的批判性思维原则或标准,这些标准完全“浸没”在学科内容教学之中。反之,注入法教学在科目内容教学中明确阐述批判性思维的一般的或学科的原则和标准。那些假设存在批判性思维一般技能的人,在教学中会明示批判性思维的一般原则或标准,而那些不默许这个假设的老师则可能明示学科批判性思维的原则和标准。例如,采用注入法教授历史课程,可能涉及到历史上的重大决策(如杜鲁门总统决定给日本投原子弹以结束二战),这时老师可能明确阐述决策的一般程序(标准),而且还要把这个一般决策程序迁移到其他情况(如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或别的语境(如现时的民生工程决策)。混合法(mixed approach)是著名批判性思维专家恩尼斯、珀金斯(David Perkins)、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等知名学者倡导的,这是一种组合一般方法与注入法或浸没法而形成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法。采用该方法时,有一个独立主线(如中小学的“写作艺术”)或独立课程,旨在教授批判性思维的一般原则,同时学生也参与到特殊学科的批判性思维教学中。可见,除了浸没法之外,所有批判性思维教学法都明示理性标准(一般理性标准或学科理性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注入法和混合法越来越受到重视,有人认为它是把思维教学引入学科课堂的“最自然、最正宗的方式”。注入法教学研究专家斯沃茨(Robert J.Swartz)曾提出注入法基本原理的三个主要原则:越是明确的批判性思维原则教学,对学生的影响越大;课堂教学越是包含一种关怀气氛,就越有利于使学生重视好思维;思维教学越是与内容教学相结合,学生就对所学东西思考得越多。([28],第2页)注入式教学结构的四环节都以批判性思维技能及其标准为核心。在第一个环节“课程介绍”中,除了介绍要学习的科目内容而外,还要向学生介绍相应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或过程,尤其是理性标准。在“思维活动”环节,老师利用言语提示(常常是提问)和图表引导思维活动,这些提示和图表是与某种批判性思维技能相应的理性标准的具体化、视觉化。在“对思维的思考”或元认知环节,老师提出一些反省性问题,比如,你在进行何种思维?你是如何完成的?你的做法是进行这类思维的一种有效方式吗?这些问题的要害就是让学生用与批判性思维技能匹配的理性标准来检查、对照自己在思维活动阶段的表现,以发现缺陷,加以改善。在最后的“应用思维”环节,老师帮助学生把课堂上所教的思维技能和标准应用到其他情境。无论是“近迁移”还是“远迁移”,都提供应用技能和标准的重要实践机会。所以,注入法的力量就在于它能提供很多重要语境中的学习标准、好思维的原则和恰当的心智习性。([31],第206-207页)
“混合法”有时以“跨学科的批判性思维”的面目出现,比如大学里的“跨学科写作”计划。贝克大学(Baker University)通识教育方案中有50学时以上的“批判性思维与写作”课程。该课程包括所有学生必修的三个特别设计的课程:两个学期的新生序列(LA101:“批判性思维与有效写作”和LA102:“想法与阐述”)与一个大四顶峰体验(senior capstone)——(LA401):“科学、技术与人文价值”。前两个课程属于形式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技能方面的教学,旨在教会学生将这种知识成功应用于书面说明文(论说文)。最后一个课程要求大四学生从当前科学或技术的发展中选择一个公共政策议题,然后研究、准备、提出和辩护一个立场论文(15到25页),对有关该议题的一个具体公共政策做出论证。议题可能有克隆、水使用政策、能源政策、生育问题、各种医学问题和国防政策等。文章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批判性分析与对不同政策或所建议政策之反对的回应,学生必须考虑每一个备选方案的伦理后果。([31],第208-209页)恩尼斯所假想的“智慧大学”的批判性思维教学也采用混合方法,称作“跨课程批判性思维计划”(CTAC)。它的基础课是给新生开设两学期批判性思维原理必修课,包括一般批判性思维倾向和能力(恩尼斯批判性思维技能和理性标准清单),每学期上14周(共28周),每周三学时。课程进度安排是,前21周的内容是批判性思维的一般概念、原则和标准;接下来的6周,主要是把一般的或领域专属的批判性思维原则应用于具体学科领域,一周涉及一个领域——人文,社会科学,物理学,生物学,职业领域(商业、农学、教育)和计算(概率、数学、统计、计算机)。在此期间,学科教员代表负责作业、内容、讨论和小作业等活动。课程的最后一周用于两学期课程的复习和最终评价。同时,智慧大学也期望每一学科领域都开发自己课程的计划和方法,既促进每一专业学生的一般批判性思维,也促进学科专属的批判性思维。每个学生都要做一个专业或学科内的高年级项目,其最终报告包括项目的描述,研究程序,说明和辩护其主要论题或论点,也要包括学生在做这个项目时所使用的一般的和学科专属的批判性思维倾向、能力、原则和标准的例示清单。恩尼斯在教学“基本策略”和“战术”中建议,“让学生把注意力放在批判性思维原则和标准如何运用在迁移情境中”;“确保批判性思维原则和标准被明确展现出来(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陈述出来的)”;“提供一套论文、报告、信函、建议或表达立场之陈述的评判标准,该标准应该反映批判性思维原则,而且老师已告知学生这些原则是重要的”;“让学生互相阅读彼此写出的立场论文,运用这些标准并提出建议”。恩尼斯要求对这些课程进行开发并明确加以标识。无论实施哪个课程,都应发布和澄清任何一般批判性思维课程或模板要教的批判性思维倾向和能力,让所有老师和学生都知道每一课程或模板要促进的是批判性思维的哪些方面,学生要从课程或模板学会怎样的东西。要促进学习向新领域的迁移,明智的做法是规划批判性思维原则和标准的反复应用,最好也向学生指明各种课程中的相似应用。([31],第228-233页)
批判性思维由怀疑发动,它比较和权衡相互竞争的主张和论证,以获得理由充分的判断为依归,理性标准构成其灵魂。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就不能从多元意见中进行比较和筛选,也难以表明一个判断是“理由充分的”或合理的。批判性思维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表现,但完全意义上的批判性思维不仅包含质疑、多元意见和判断这三个环节,更把理性标准作为估量和平衡的规准。就此而言,虽然中国的“明辨”有一些批判性思维的元素,但明显差距恰恰在于缺乏精细的理性标准,或者设置了不当的标准,比如把天子之言或圣人之言作为永恒标准。今天,营造公民思维文化或论证文化的关键就是要让理性标准深入人心。
[1]S.Bailin and M.Battersby,2015,“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 as inquiry”,in M.R~.Barnett(ed.),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Higher Education,pp.123-137,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N.-M.Chan,I.T.Ho and K.Y.Ku,2011,“Epistemic beliefs and critical thinking of chinese students”,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1(1):67-77.
[3]L.Elder and R.Paul,2010,“Critical thinking:Competency standards essential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tellectual skills,Part 1”,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ducation,34(2):38-39.
[4]L.Elder and R.Paul,2012,“Critical thinking:Competency standards essential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tellectual skills,Part 4”,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ducation,35(3):30-31.
[5]L.Elder and R.Paul,2013,“Critical thinking:Intellectual standards essential to reasoning well within every domain of thought”,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ducation,36(3):34-35.
[6]L.ElderandR.Paul,2013,“Criticalthinking:Intellectualstandardsessentialtoreasoningwellwithineverydomainofthought,Part3”,JournalofDevelopmentalEducation,37(2):32-33.
[7]R.H.Ennis,1991,“Critical thinking:A streamlined conception”,Teaching Philosophy,14(1):5-25.
[8]R.H.Ennis,2015,“Critical thinking:A streamlined conception”,in M.Davies and R.Barnett(eds.),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Higher Education,pp.31-47,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9]R.H.Ennis,2011,“Critical thinking:Reflection and perspective,Part I”,Inquiry: Critical Thinking Across the Disciplines,26(1):4-18.
[10]P.A.Facione and N.C.Facione,2013,“Critical thinking for life:Valuing,measuring,and training critical thinking in all its forms”,Inquiry:Critical Thinking Across the Disciplines,28:1-25.
[11]R.H.Johnson,1992,“Theproblemofdefiningcriticalthinking”,inS.Norris(ed.),The Generalizability of Critical Thinking,pp.38-53,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
[12]D.Kuhn,Y.Wang and H.Li,2010,“Why argue?Developing understanding of the purposes and values of argumentive discourse”,Discourse Processes,48(1):26-49.
[13]M.Lipman,1992,“Criteria and judgment in critical thinking”,Thinking Across the Disciplines,9(4):3-4.
[14]M.Lipman,2004,“Critical thinking——What can it be?”,in A.C.Ornstein,L.S. Behar-HorensteinandE.F.Pajak(eds.),ContemporaryIssuesinCurriculum,pp.149-156,New York:Person Education.
[15]M.Lipman,2003,Thinking in Educ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6]M.Mayfield,2014,ThinkingforYourself:DevelopingCriticalThinkingSkillsThrough Reading and Writing,Boston,MA:Wadsworth.
[17]J.E.McPeck,1981,Critical Thinking and Education,New York:St.Martin's Press.
[18]J.E.McPeck,1990,Teaching Critical Thinking:Dialogue and dialectic,New York:Routledge.
[19]T.Mendham,2011,“Skepticism and critical thinking”,Issues,95:4-7.
[20]C.Osborne,2004,Presocratic Philosoph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R.Paul and L.Elder,2011,“Critical thinking:Competency standards essential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tellectual skills,Part 2”,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ducation,35(1):36-37.
[22]R.Paul and L.Elder,2011,“Critical thinking:Competency standards essential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tellectual skills,Part 3”,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ducation,35(2):34-35.
[23]R.Paul and L.Elder,2012,“Critical thinking:Competency standards essential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tellectual skills,Part 5”,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ducation,36(1):30-31.
[24]R.PaulandL.Elder,2013,“Criticalthinking:Intellectualstandardsessentialtoreasoningwellwithineverydomainofthought,Part2”,JournalofDevelopmentalEducation,37(1):32-33.
[25]R.PaulandL.Elder,2014,“Criticalthinking:Intellectualstandardsessentialtoreasoningwellwithineverydomainofthought,Part4”,JournalofDevelopmentalEducation,37(3):34-35.
[26]H.Siegel,1988,EducatingReason:Retionality,CriticalThinkingandEducation,New York:Routledge.
[27]H.Siegel,2010,“On thinking skills”,in S.Johnson,H.Siegel and C.Winch(eds.),Teaching Thinking Skills,pp.51-84,London:Continuum.
[28]R.J.Swartz,S.D.Fischer and S.Parks,1998,Infusing the Teaching of Critical ThinkingandCreativeThinkingintoSecondaryScience:ALessonDesignHandbook,Pacific Grove,CA:Critical Thinking Books&Software.
[29]J.Woods,2013,Errors of Reasoning:Naturalizing the Logic of Inference,London:College Publications.
[30]泰勒,龚珀茨(著),赵继铨,李真(译),苏格拉底传,199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
[31]武宏志,张志敏,武晓蓓,批判性思维初探,201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2]席克,沃恩(著),张志敏,武晓蓓(译),怪诞现象学,2013年,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33]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199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琳琦)
Critical thinking starts from doubting and inspires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but more importantly,it concerns with making a judgments from competing views and arguments according to Reasonable Standards,the dividing lines of which seperates from skepticism and relativism.The nature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most authoritative definitions of critical thinking all imply Reasonable Standards.Every critical thinking skill matches with a corresponding rational standard.The various critical thinking teaching methods also acknowledge a series of Reasonable Standards implicitly or explicitly. Reasonable Standards are the key to promote students from absolutism to evaluativism. Chinese“discretion”has something in common with critical thinking,yet the distinctive difference lies in lack of fine Reasonable Standards.To foster the thinking culture of citizens,to create the sound argumentative culture,all thes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basis of the Reasonable Standards.
Reasonable Standards——the Soul of Critical Thinking
Hongzhi Wu
21st Century New Logic Research Institute,Yan'an University
yaydwhz@126.com
B81
A
2016-05-16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法律论证逻辑研究——面向‘法治中国’建设的整合性和应用性研究”(15AZX019)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