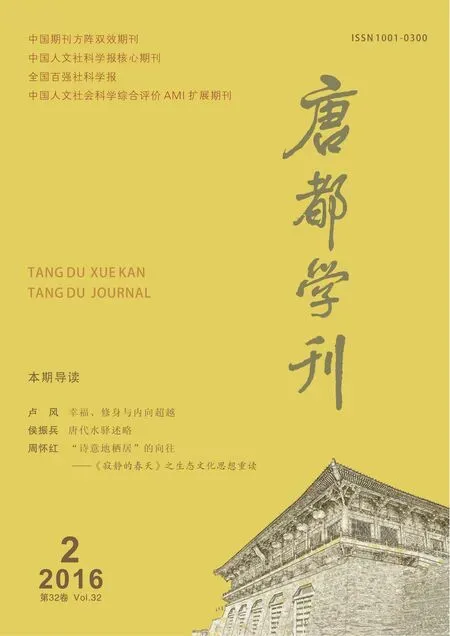幸福、修身与内向超越
2016-02-02卢风
卢 风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084)
【伦理学研究】
幸福、修身与内向超越
卢风
(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100084)
经济学家发现,虽然一个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但人们的幸福感并不会提高,这一现象被他们称作“伊斯特林悖论”。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悖论,人生永远都是苦乐相伴的。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都不可能增加人类的幸福,而只能改变人们感受苦乐的具体形式。幸福生活必定包含很多快乐时光,但也必然伴随一些痛苦和烦恼。内向超越和外向超越是两种基本的追求幸福的途径。内向超越即改善自我、提升自我;外向超越即改造世界、征服自然。中国古代文明激励人们以内向超越为本,而现代工业文明一味激励人们外向超越。儒家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内向超越。激励内向超越的中国古代文明较好地约束了人们物质贪欲的膨胀和征服性技术的发展,从而没有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因而是可持续的。一味激励人们贪得无厌地追求身外之物的现代工业文明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现代人若想走出现代工业文明的深重危机,必须学会内向超越,且优先重视内向超越。
幸福;修身;内向超越;外向超越
一、快乐与幸福
近些年来,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越来越热衷于谈论幸福。有西方研究者说:“30年之前,没有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会在自己的学术论文中使用‘幸福’这个词,然而,到了2007年,在经济学的杂志中,使用‘幸福’这个词作为论文题目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过了1 000篇。”[1]英国经济学家莱亚德(Richard Layard)则用现代科学(特别是脑科学和心理学)去说明幸福是客观的[2]20,并进而宣称,幸福之所以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就是我们整体的动力装置”[2]24。说幸福是人类整体的动力装置并没有表达什么新见解。边沁早就说过:“大自然已将人类置于两位至高无上的主人的统治之下:这两位主人就是痛苦与快乐。只有他们俩能指示我们应该做什么,并决定我们将会做什么。他们把正当与错误的标准和原因与结果的链条都紧系在自己的宝座上。他们决定着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我们所能做的每一个摆脱其束缚的努力最终都只能证明和巩固他们的统治。”[3]
但我们有必要把作为生活目标的幸福与快乐区分开来。莱亚德所说的可以科学、客观地测定的幸福就是边沁所说的快乐。当我们说幸福是最高的善或人类生活的共同目标[4]时,“幸福”就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不同于快乐。在这种抽象的语境中,“幸福生活”与“好生活”同义。人人都希望过幸福生活或好生活,说汉语的人们都用“幸福生活”或“好生活”这两个词去说自己的生活目标,但信仰不同的人们对什么是“幸福生活”或“好生活”则有不同的理解。
幸福生活肯定包含快乐时光,但肯定也包含痛苦、烦恼、无聊等等。分分秒秒都快乐的人生和分分秒秒都痛苦的人生都是不可想象的。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嫦娥》中所言:“凡哀者属阴,乐者属阳;阳极阴生,此循环之定数。”当一个人说自己的生活是幸福之时,只表明他对自己一直以来的生活是满意的,并非指他从来就没有痛苦和烦恼。
人所享受的快乐也绝不能归结为科学仪器所能测量的脑电波一类的东西。人超越于非人动物之上,就因为人创造了文化。人是悬挂于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文化动物。人所能感受的快乐和痛苦已超越了非人动物的本能的快乐和痛苦,已打上了文化的烙印。人在通常情况下是趋乐避苦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任何快乐都可以追求、享受,也绝不意味着任何痛苦都可以逃避。非人动物能享受的快乐和能逃避的痛苦受自然条件的严格限制。人所能享受的快乐和能逃避的痛苦除了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外,还深受文化的制约。
二、追求幸福的两种途径
对一个人来讲,有两种追求幸福的途径:一是向外用力,一是向内用力。
向外用力就是去赚更多的钱以便拥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如买空调、冰箱、洗衣机、汽车、豪宅、珠宝等,旅游坐头等舱、住五星级宾馆等。在中国,你也可以力争做更大的官,因为你做的官越大,就越能改善你的生活条件。说到底,向外用力即努力追求身外之物,这里的“物”不仅指豪宅、豪车、珠宝等有形物,也指权力、荣誉(如劳动模范、长江学者一类的称号)一类的无形物。
向内用力就是改变自我,调节自己的心态,培养自己的德行,提高自己的境界和智慧,使自己不仅能安享各种幸福,还能从容镇定地面对各种艰难困苦。一个有抑郁症的人必然不幸福,他必须首先治好自己的抑郁症才可能幸福起来。一个心胸狭窄、嫉妒心过强的人,即便腰缠万贯、身居高位也不会幸福,因为总有人比他更有钱、更有权。他必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提高自己的境界才会幸福。
对一个社会或国家来讲,改善民生的途径也不外这样两种:一是激励人们向外用力,一是激励人们向内用力。向外用力包括我们在毛泽东时代常讲的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可概括为改造客观世界;向内用力则有毛泽东时代人们常说的改造主观世界的意思,但那时说的改造主观世界特指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去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自我(或主观世界)的思想体系很多,中国的儒释道三家都能帮助我们改善自我。
如果我们称改变现状、追求幸福(好生活)的努力为超越*这里的“超越”不同于西方哲学所说的“超越”。,那么向内用力就是内向超越,而向外用力就是外向超越。一个明智的人必定能在内向超越与外向超越之间保持平衡,一味内向超越或一味外向超越都不可能幸福。你作为一个社会成员,必须参与社会协作与竞争,你必须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和交际能力,这样你才能有一个正当职业,从而有一份合法收入。简言之,你在社会上、职场中必须有足够强的竞争力,这是你必需的外向超越的能力。你又是一个有个性和独特性的个体,你的内心总有他人所不可触及、不可理解的东西。你还是一个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你永远有欲求,但不可能要什么有什么,他人和社会也永远不可能完全按你所希望的那样“公平”地对待你,你随时都可能受挫甚至受委屈。正因为如此,你必须学会调适自己的心态,才能生活得比较幸福。换言之,你必须学会内向超越。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引导人们在外向超越与内向超越之间保持平衡。在物质匮乏或遭遇严重灾害时,必须激励很多人去从事物质生产,去抵御灾害。这时,改造环境、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就是迫切的任务,国家或社会就应激励人们外向超越。当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像东汉末年和民国年间那样战乱频仍,就必须有志士仁人出来改造社会,或者改朝换代,或者根本改变社会制度。但一个国家若只激励人们外向超越而不激励人们内向超越,那就十分危险。在社会矛盾激化的年代,必然是真正注重内向超越的人太少。人们唯利是图,争权夺利,富人不仁,穷人不义,社会矛盾必然日益激化。反之,如果很多人有平和的心态,则容易保持社会和谐。
其实,测定一个人快乐时的脑电波改变只对做研究的科学家有所谓的客观意义。对每个人来讲,快乐也好,幸福感也好,归根结底是他自己的感受或体验。一个人幸福不幸福,只有他自己的判断或体验才最真切,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可见,一个人的幸福感主要取决于他自己的身心状态——是否有抑郁症,嫉妒心强不强,心胸宽广不宽广,境界高不高。一个自强不息的人不难谋个衣食无忧的职业或地位,他幸福不幸福就更多、更直接地依赖于他的身心状况。有一项研究表明,连疾病对人的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也是可调适的,“病患会短期降低人的幸福感,但是只要一个人并非病情不断恶化或出现持续的、让人体力衰竭的疼痛,则病患不会造成长期的痛苦”[5]332。这便表明,一个人幸福不幸福主要取决于他的精神境界。由此可见,内向超越才是追求幸福的最直接、最可靠的路径。
三、修身是内向超越的基本方法
内向超越的基本方法就是儒家所极为重视的修身,也就是佛学所说的修行。《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此一言道出了传统中华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根本区别:传统中华文明要求人们以内向超越为主,而现代工业文明激励人们以外向超越为主。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写道:“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6]中国古代社会的科举制度决定了只有读书人才可能跻身于统治阶级,科考的主要科目是儒家经典,在通常境况下,入仕者都是学术精英或思想精英。中国古代的思想精英根本不同于今日的科技精英。中国古代思想精英,如董仲舒、韩愈、王安石、司马光、王阳明、张居正等,看重和精通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相当于今天讲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和大智慧,而今日科技精英看重和精通的是分析性、技术性、计算性的知识。中国古代社会是由思想精英领导的,而现代社会是由科技精英和商业精英领导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激励人们修身,即激励人们重视内向超越,而现代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激励人们积极从事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广告创新,即激励人们重视外向超越。
中国古代思想精英的终极关怀是成圣。孔子在《论语·里仁》中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闻道是孔子的终极关怀。但儒家所说的道不是外在于人的“逻各斯”或抽象的最高原则,而是与人不可须臾分离的生活方式。《中庸》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就体现为事君、事亲、交友、做事的具体方式,道不离人伦日用,其要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闻道就是成圣,成圣就是成为一个德行圆满、境界极高且极有智慧的人。如果把成圣看成一个人生目标,则这个目标在人格之内,即是人生的内在目标,或说是人生之内的目标,既不同于财富、权力、荣誉一类世俗的外在目标,也不同于“天国”一类的外在的神圣目标。
蒂利希(Paul Tillich)说:“信仰是终极关怀状态,信仰的动力就是人之终极关怀的动力。”[7]1蒂利希讲的信仰以基督教为典范,而许多基督徒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中国人有信仰,中国人的信仰是“天人合一”的信仰。蒂利希说:“‘终极关怀’一词把信仰行动的主体方面(信仰者)和客体方面(被信仰者)统一起来了。前者是表示终极关怀人格之核心行动的经典术语,而后者是表示信仰行动之指向的经典术语,指终极实在本身,即神的象征。”[7]10-11蒂利希讲的终极关怀是基督教的终极关怀,是主客二分的终极关怀,也是外向超越的终极关怀。神在人之外,人绝不可能达到神的全智全能和尽善尽美,人只能祈求神的拯救。基督徒的终极关怀便体现为对全智全能、尽善尽美的神的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对神的外在拯救的盼望。中国人内在超越的终极关怀迥异于此。在“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里,没有清晰的主客二分。“天”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作用类似于“神”在基督教体系中的作用,但儒家对天人关系的诠释根本不同于基督教神学对神人关系的诠释。天人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彼此内在的关系,而神人关系是彼此外在的关系。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人性就源自天命,天命就内在于人性之中。成圣的内在超越就体现为《易经》所言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终身学习和实践,这种学习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修身。成圣的要诀在于修身。周敦颐《通书·圣学》有言:“‘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8]31成圣的要诀是无欲。此处“无欲”非指完全没有欲望,而指摒除一切不合天理的欲望。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没有西方现代性中的道德律与自然律的截然二分,故儒家讲的天理是自然规律与道德规范(礼)的统一。一个人若能克尽人欲之私,则自然能存天理之正,从而能成圣贤。“克尽人欲之私”说说容易,真正做到是无比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下日新又日新的修身工夫。
重视内向超越的人,不会怨天尤人。正如《中庸》有言:“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处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一个人若有此境界,则自然幸福。马一浮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乃为君子之道。”[9]行君子之道,就免了怨天尤人的负面情绪,从而永葆精神健康。
四、现代性一味激励外向超越
现代性基本上不激励人们内向超越,它主要激励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广告创新等,它也特别激励各种竞争。简言之,它一味激励人们外向超越,激励人们永不知足地追求身外之物。
现代性的承诺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增长、机器的增多、机器的改进和社会的改善,人们将生活得越来越幸福。简言之,现代化的发展会使人们生活得越来越幸福。发展的根本标志就是财富增长和科技进步。这似乎是个直观的道理:古代农民或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或者“面朝黄土背朝天”,如今不必那么辛苦了,有各种机器和除草剂了,脏活、累活都由机器或除草剂代劳了,于是现代农民比古代农民幸福。真是这样吗?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至今天,世界经济总的来讲呈快速增长趋势,科技更呈现加速进步趋势。那么,人类的幸福感也在增长吗?当代经济学家用问卷和统计的方法研究了很多国家的人们的幸福感,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各种证据表明人们的平均幸福感还不如50年前[2]3。经济学家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所谓的悖论:“当一些国家在物质上变得更加富裕,也变得更加健康时,其平均的幸福感水平并不会提高。”这个悖论后来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1]18。在哲学家看来,这并不是什么悖论。人与所有的非人高等动物的个体都注定要终生不断地感受快乐与痛苦(抑或烦恼、郁闷、无聊等负面情绪)的交替(如前所述)。或如赫拉利(Yuval N.Harari)所言,一个人的幸福只会维持在相对恒定的水平[5]387。经济学家喜欢定量化表述,让我们向他们学习。如果我们以时间为横轴,以痛苦-快乐为纵轴,纵轴原点以下表示痛苦,原点以上表示快乐,则一个人的心情曲线永远都沿着横轴上下波动,而不可能不断上扬。可见不需要插秧、除草的农民肯定不会分分秒秒都快乐,没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痛苦,又会产生其他痛苦(烦恼抑或无聊)。
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会不断改变我们的具体生活内容,但永远也不可能增加我们的幸福感。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能消除特定的痛苦,但它消除了甲种痛苦之后,我们又会产生乙种、丙种、丁种痛苦,如空调消除了我们盛夏时难耐的炎热的痛苦,但在有空调的地方我们势必会产生其他种种痛苦(烦恼抑或无聊)。换言之,以外向超越的方式追求幸福是徒劳的、愚蠢的。
可见,一部人类文明演化史绝不可能是人类快乐不断增长的历史。人类感受苦乐的谱系(具体形式)在不断演变,但苦乐相伴、苦乐相随的本性不会改变。古人有古人的苦乐,今人有今人的苦乐。例如,古代穷人常受饥寒之苦,而今日中产阶级则难免营养过剩和过分肥胖之苦;古人能享受琴棋书画之乐,而今人能享受电子游戏之乐;如此等等。各种不同的快乐或痛苦在科学家的测试中会被归结为客观的、同样的脑电波,但文化上的差异却是巨大的,而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值得研究。
人是追求意义的文化动物。一个人的信仰决定着他以何为乐,决定着他甘愿承受何种痛苦。周敦颐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8]32-33颜子能见其大而忘其小,从而做到“贫而乐”,就因为他“信道笃”(马一浮语)。西方传教士不畏艰辛来中国传教,也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仰。而现代人认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能使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幸福,也因为他们信仰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
人生总是有苦有乐,古人如此,今人如此,未来的人也只能如此。对每个人来讲,真正重要的是能否觉得自己所做的事乃至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只要你觉得自己所做的事乃至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你就会有精神充实感,就能安享自己的快乐,且从容应对自己必须承受的痛苦。“心泰则无不足”就是这个意思。反之,一个人若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且无法改变这样一种无意义感,他便极有可能自杀。就此而言,蒂利希所说的植根于坚定信仰的终极关怀才是幸福生活的根本。
现代性提供的信仰便是独断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10]。信仰现代性的人们也能具有精神充实感。今日世界各行各业的精英不乏坚信现代性者。正是他们在推动着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广告创新。现代性激励贪婪和竞争。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多蒂说:“‘贪婪’一词如此声名狼藉可谓不幸。但是,若没有贪欲,我们又怎么可能拥有室内的水管装置、带钟的收录机,甚至南加州的淡水呢?”[11]简言之,若没有贪婪,哪来现代社会的物质繁荣?现代社会的物质繁荣也离不开竞争。在自由主义者看来,“竞争只意味着……无压迫”[12]287,“竞争就是自由,破坏了行动的自由,也就是破坏了选择、判断、比较的可能性和能力;也就扼杀了智慧、思想和人”[12]288。“个人利益是不可战胜的个人主义力量,它促使我们,激励我们去寻求和发现进步并设法垄断之。竞争同样是一种不可战胜的人道主义力量。随着进步的完成,竞争从个人手中夺取进步,使其成为人类大家庭的共同财富。上述两种力量,孤立地看待它们时是可以指责的,但合在一起,从总体上说,它们构成了社会协调。”[12]291竞争是一种“刺激剂”,“它促使我们离开不毛之地,走向那肥沃的乐园”,“竞争的自身运动是越来越达到平等,同时提高社会水平”[12]303。现代社会的外向超越就集中体现为贪婪和竞争。这种贪婪和竞争的外向超越,推动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但这种快速发展非但未使人们生活得越来越幸福,反而使人类文明深陷于危机之中。现代工业文明的危机正是极度外向超越所导致的自作孽的危机:人们以为生产、消费的物质财富越多就越幸福,但实际情况是人们没有生活得越来越幸福,但地球生态系统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人们以为机器越来越先进,人类就越来越幸福,但有科学家认为,将来机器人可能消灭人类[13]。
如果说人生总是有苦有乐,那么说修身或内向超越可以增加人类的快乐也是说不通的。我们可以说修身或内向超越能确保一个人生活幸福,但不能说修身或内向超越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快乐(注意快乐与作为人生目标的幸福的区别)。修身或内向超越可以提升自我境界,增强自我智慧,从而拥有一种极高明的生活状态。儒家“致中和”的思想就代表着对这种极高明的生活状态的追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未发之中就是一种极高明的生命状态,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未发,并不意味着他处于无情感的状态,仅指他处于一种宁静虚灵的精神状态,保持这种状态,他就总能对外界事物做出正确判断和适当回应。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当喜则喜当怒则怒,喜怒哀乐合于天理,则不碍赞天地之化育。
注重修身而有境界的人与不注重修身而没有境界的人所感受的具体苦乐是不同的。一个名利心和嫉妒心极重的人,一次晋升受挫就会痛不欲生,而一个有境界的人就不会。对于儒家的君子来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可见,他仍有其烦恼和忧愁,但他的忧愁和烦恼又是那些没有境界的人所没有的。密尔倾向于把人所能享受到的快乐做质量上的区分,进而断言:“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14]。用儒家的语言说,即宁肯做一个不满足的君子,也不做一个满足的小人。修身可使我们的心情曲线随时间的波动很平缓,这可与吸毒者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吸毒者总是处于兴奋与抑制的剧烈波动之中,而一个有境界的人常处于“未发之中”,故其心情是十分宁静的,即便有波动,也很平缓。
从全球文明发展趋势看,激励外向超越的文明与激励内向超越的文明的差别较大。中华古代文明激励人们以内向超越为主,这便有效约束了人们的物质贪欲和征服性技术的发展,从而一直远离“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具有较好的可持续性。一直以外向超越为主的西方文明发展为现代工业文明,一味激励外向超越,且现代人的外向超越已不再体现为对上帝的虔信和对天国的向往,而体现为征服自然、创造财富的努力。它又强有力地同化着地球上的一切文明,迫使全人类都永不知足地追求身外之物。最新科学(如量子物理学、生态学、耗散结构理论、复杂性理论等)和全球性生态危机这样的事实都证明这种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大自然允许人类永不知足地追求境界或精神价值,但不允许几十亿人永不知足地追求物质财富。现代工业文明在展示其巨大的征服自然的力量的同时,也暴露了它空前的危机。现代人必须重新学会优先重视内向超越,才能既生活得幸福,又走出危机。
[1]卡萝尔·格雷厄姆.这个世界幸福吗[M].施俊琦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2]Richard Layard.Happiness: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M].Penguin Books,2005.
[3]Jeremy Bentham.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M].Batoche Books,Kitchener,2000:14.
[4]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OGER CRISPPP[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0-11.
[5]Yuval N.Harari.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M].McClelland & Stewart,2014.
[6]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2:21.
[7]Paul Tillich.DYNAMICS OF FAITH,HARPER TORCHBOOKS/The Cloister Library[M].HARPER &BROTHERS,NEW YORK,1957.
[8]周敦颐.周敦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马一浮.马一浮全集:第一册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46.
[10]卢风.论环境哲学本土化[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1-10.
[11]詹姆斯·L·多蒂,等.市场经济——大师们的思考[M].林季红,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3.
[12]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谐经济论[M].许明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3]雨果·德·加里斯.智能简史[M].胡静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08.
[14]约翰·密尔.功利主义[M].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
[责任编辑王银娥]
Happiness, Self-cultivation and Inward Transcendence
LU Fe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Economists argue that people’s happiness wouldn’t improve necessarily although the national economy is on the steady growth, this phenomenon is known as the Easterlin Paradox.Actually, this is not a paradox, life is full of joy and sorrow.Neither the economic growth nor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wouldn’t improve mankind’s happiness but can change the people’s ways of feeling happy and sad.Happy life is filled with many happy moments, yet accompanied by sufferings and worries.Inward transcendence and outward transcendence are two ways of pursuing happiness.Inward transcendence refers to self-cultivation and self-improvement while outward transcendence refers to changing the world and conquering the nature.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encourages people to be focused on inward transcendence whereas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blindly encourages people to be oriented towards outward transcendence.Confucianists stress that all the people from emperors to the common people should be oriented to self-cultivation.Self-cultivation is inward transcendence.Accordingly, Chinese ancient civilization restrains people’s expansion of the material lus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me conquering technologies, which prevents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hazards, so it is sustainable, on the contrary,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brings about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cological destruction and climate changes, so it is not sustainable.Modern people should attach greater importance to inward transcendence if they want to get out of the deep crisis from the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happiness; self-cultivation; inward transcendence; outward transcendence
B825
A
1001-0300(2016)02-0005-06
2015-12-28
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伦理问题研究”(14AZX021)
卢风,男,安徽六安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应用伦理学、科技哲学、现代性和生态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