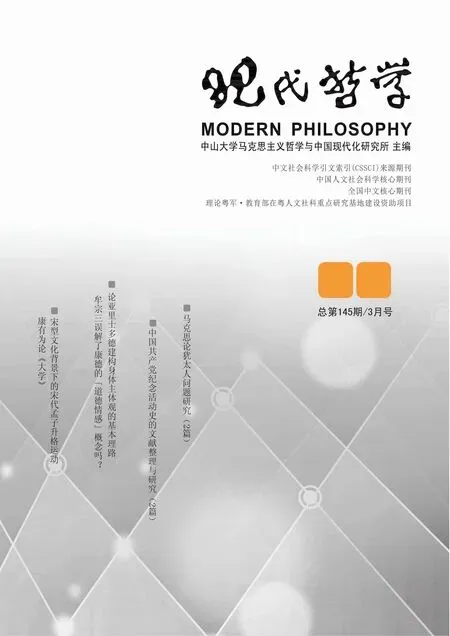牟宗三误解了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吗?──与方旭东教授商榷
2016-02-01李明辉
李明辉
牟宗三误解了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吗?──与方旭东教授商榷
李明辉*
【摘要】方旭东在其论文《道德情感是能力吗?──论牟宗三对康德“道德情感”概念的误读》中批评牟宗三对康德“道德情感”概念的误读。经我仔细检查方旭东的论点,发现牟宗三受限于英文译本或疏忽,的确有若干误译康德文本之处,但情节并不严重,基本上无碍于他对康德思想的正确把握。反倒是方旭东,由于他自己对康德哲学的隔阂,严重误读了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
【关键词】牟宗三;康德;道德情感;意志;意念
一
今年(2015)六月底笔者到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出席该院成立五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会中遇到方旭东教授。承蒙他的好意,获赠他刚出版的新著《原性命之理》。笔者立刻翻阅该书,发现书中有一篇论文《道德情感是能力吗?──论牟宗三对康德“道德情感”概念的误读》特别引起笔者的注意。因为在牟先生对儒学的重建中,他藉由重新诠释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来分判孔、孟与康德的心性论观点之异同,并主张“道德情感”可以“上下其讲”,以解决康德的“道德情感”理论之困境*参阅拙作:《再论牟宗三先生对孟子心性论的诠释》,收入拙著:《孟子重探》,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第111—131页。。笔者当年也由于受到牟先生对“道德情感”的诠释之启发,决定到德国深入研究康德的“道德情感”理论,并完成了博士论文《康德伦理学发展中的道德情感问题》*Ming-huei Lee, Das Problem des moralischen Gefühls in der Entwicklung der Kantischen Ethik,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年。。如果牟先生真如方教授所言,“误读”了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则牟先生对儒家心性论的诠释也会受到根本的质疑,此事实非同小可。故笔者迫不及待地拜读方教授此文。拜读之后,笔者松了一口气,因为笔者发现:方教授所谓牟先生的“误读”其实是基于他自己对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之“误读”。以下让我们来检讨方教授对牟先生的质疑。
众所周知,牟先生系透过康德著作的英译本来研究康德哲学。不可讳言,这对于理解康德哲学难免会隔了一层,而且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当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康德著作英译本尚未问世,牟先生所依据的几种英译本未必完全理想,有可能造成他的误读。方教授就是藉由检讨牟先生对相关文本的翻译,指出牟先生的“误读”。他说:“除了一些明显的技术错误之外,牟译的问题主要来自他对康德哲学的了解不够。”*方旭东:《原性命之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2—73页。以下引用此文时,直接将页码标注于引文之后,而不另加脚注。方教授显然学过德文,因为他在文中也引用了德文版的康德著作。但是笔者无法判定方教授的德文理解能力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须知康德使用的是十八世纪的德文,仅了解现代德文而对康德哲学欠缺深入了解的一般读者未必能准确地理解康德的德文文本。
方教授的检讨有点烦琐,所幸他在文末将牟先生的所谓“误读”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在康德那里,道德情感属于一种先天的心灵禀赋,牟宗三不了解这一点,将道德情感归为“能力”一类范畴,失却康德原意。其次,在康德那里,与道德情感相对的是道德认识(moralischer Sinn),前者主观,后者客观,牟宗三不了解这一点,将后者译为“道德感取”,认为那仍是一种感性作用,从而未能真正认识道德情感的特性。再次,在康德那里,道德情感作为一种感受,其对象是自由意志的由理性法则推动的运动,牟宗三不了解这一点,错误地以为道德情感是对自由意志受法则推动这件事的感受。(页73)
方教授在其论文的第一至三节提出这三点批评。以下笔者将逐项讨论方教授对牟先生的翻译与诠释之批评。
二
首先,方教授质疑牟先生将康德所说的“道德情感”理解为一种“能力”,这点质疑甚至见诸其论文的标题:“道德情感是能力吗?”方教授引述康德在《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kderSitten)中谈到“道德情感、良心、对邻人的爱与对自己的尊敬(自重)”时的一段文字:
(1) Sie sind insgesammt ästhetisch und vorhergehene, aber natürliche Gemüthsanlagen (praedispositio) durch Pflichtsbegriffe afficirt zu werden [...]*I. Kant, 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 (以下简称MS), in: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Akademieausgabe, 以下简称 KGS), Bd. 6, S.399. 以下引用此书时,直接将页码标注于引文之后,而不另加脚注。为了便于讨论,笔者将康德的引文均加上编号。
笔者译:它们均是感性的与预存的、但却自然的心灵禀赋,即为义务概念所触动的心灵禀赋。*此书有笔者的中译本:《道德底形上学》,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5年。由于此一中译本在边页附有德文原版的页码,读者不难找到相对应的文字,故本文不另外注明中译本的页码。
对于这段文字,方教授指摘牟先生将Gemüthsanlagen误译为“能力”,而且略去括号中的拉丁文对应词praedispositio。他认为这种做法“关系重大”(页61),因为“如果道德情感相当于禀赋,是可以将其归为道德品质范畴的。不然,如果将道德情感理解为能力,再认为它属于道德品质,那就说不通了”(页62)。牟先生根据的应当是爱尔兰康德专家阿保特(Thomas Kingsmill Abbott)的英译本Kant’sCritiqueofPracticalReasonandOtherWorksontheTheoryofEthics。此书的第一版于1873年出版,以后一再重印或再版。牟先生使用的究竟是哪个版本,如今已不得而知。在英译本中,阿保特将Gemüthsanlagen译为capacities of mind (praedispositio),并未略去拉丁文的对应词。牟先生将此词译为“能力”,显然是采取capacities之义*牟宗三:《康德的道德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第15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第501页。以下引用此书时,直接将页码标注于引文之后。。
当然,就翻译而言,将Gemüthsanlagen译为“心灵禀赋”,更能贴合原文,较诸简化为“能力”,显然更为恰当。但牟先生将此词译为“能力”,是否会造成严重的“误读”呢?恐怕未必。因为当我们说人具有某种“禀赋”时,这显然包含“他具有某种能力”之义。例如,当我们说人具有判断道德是非的“禀赋”(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时,这显然包含“他有能力判断道德是非”之义。因此,说道德情感是一种“心灵禀赋”,与说道德情感是一种“能力”,两者之间并无矛盾。事实上,康德也曾明白地将道德情感视为一种“能力”。例如,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谈到“道德的兴趣”时,就将“道德情感”界定为“对法则感到这样一种兴趣的能力(Fähigkeit)”*I.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KGS, Bd. 5, S. 80.。因此,牟先生将Gemüthsanlagen译为“能力”,虽未完全贴合原文,但基本上也未违背康德的意思,更没有“说不通”之处。
方教授接着说明上述的引文(1)之涵义:
natürlich(自然的)是说道德情感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后天的习惯;vorhergehend(先在的)是说道德情感先行于道德义务;而ästhetisch(感性的)则是强调道德情感与theoretisch(抽象的)相对。将道德情感简单地翻译为能力,就很难理解道德情感所具有的这些丰富特质。(页62-63)
方教授将ästhetisch译为“感性的”,并指出英译本将此词译为sensitive,而认为牟先生据此将它译为“敏感的”,是不对的。平情而论,在这一点上,方教授是对的。但方教授在这段说明中犯了几个错误。首先,方教授说:“道德情感是自然而然的,不是后天的习惯。”而在文末又说:“在康德那里,道德情感属于一种先天的心灵禀赋。”(页73)换言之,他将“自然的”等同于“先天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方教授所说的“先天的”是指a priori,因为它是相对于“后天的”(a posteriori)而言。若是如此,他的误解可就严重了。因为如果道德情感是感性的(ästhetisch),它便是后天的,而不可能是“先天的”。方教授可能是混淆了a priori与angeboren二词。后者可译为“天生的”,它依然属于经验的领域,因而是后天的。至少对后期的康德而言,先天的情感,即使是道德情感,都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日后的现象学伦理学家谢勒(Max Scheler, 1874-1928)质疑康德之处*参阅拙著:《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60—64页;简体字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48页。,也正是牟先生之所以主张“道德情感”可以“上下其讲”之故。
其次,方教授将vorhergehend译为“先在的”,认为这意谓“道德情感先行于道德义务”。就翻译而言,将此词译为“先在的”,不能算错,但他的解释却可能引起严重的误解。因为“道德情感先行于道德义务”之说很容易让人以为道德情感是道德义务的基础,或是道德情感产生道德义务,但这两点都是康德所反对的。因此,笔者将vorhergehend译为“预存的”,以表示道德情感是我们对于道德义务的意识之主观条件,或者说,我们若无道德情感,便不会意识到我们的义务。但这决不等于说:道德情感是道德义务的基础,或是道德情感产生道德义务。最后,方教授将theoretisch译为“抽象的”,并强调“道德情感与theoretisch(抽象的)相对”,也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这是方教授在其论文的第二节讨论的重点,故笔者在下一节一并讨论。
三
方教授对牟先生的第二点批评涉及《道德底形上学》中的一段具关键性的文字:
(2)Dieses Gefühl einen moralischen Sinn zu nennen ist nicht schicklich; denn unter dem Wort Sinn wird gemeiniglich ein theoretisches, auf einen Gegenstand bezogenes Wahrnehmungsvermögen verstanden: dahingegen das moralische Gefühl (wie Lust und Unlust überhaupt) etwas blos Subjectives ist, was kein Erkenntniβ abgiebt. — Ohne alles moralische Gefühl ist kein Mensch; denn bei völliger Unempfänglichkeit für diese Empfindung wäre er sittlich todt, und wenn (um in der Sprache derrzte zu reden) die sittliche Lebenskraft keinen Reiz mehr auf dieses Gefühl bewirken könnte, so würde sich die Menschheit (gleichsam nach chemischen Gesetzen) in die bloβe Thierheit auflösen und mit der Masse anderer Naturwesen unwiederbringlich vermischt werden.(S. 400)
笔者译:将这种情感称为一种道德的感觉(Sinn),并不恰当。因为“感觉”一词通常意指一种理论性的、牵涉到一个对象的知觉能力;反之,道德情感(如同一般而言的愉快或不快)却是纯然主观之物,它并不提供任何知识。没有人完全不具有道德情感;因为一个人若对这种感觉完全无动于中,他在道德上便等于死了;而且如果(以医生底用语来说)道德的生命力不再能对这种情感产生刺激,则“人”(彷佛按照化学定律)将化为纯然的动物性,而与其他自然物底群类泯然无分了。
方教授指出牟先生在这段文字的中译文中有两个小错误。一是牟先生将rzte误译为“物理学家”,显然是将阿保特英译文中的physicians误解为“物理学家”。二是将Naturwesen误译为“物理存有”,显然是根据阿保特的英译physical beings而译的。方教授的这两点批评是有道理的。如上所示,笔者将Naturwesen译为“自然物”。不过,方教授也承认:“就整体文意而言,这两处误译并无大碍,但如果从德文本直译或者后用德文本覆校,这类错误应当是可以避免的。”(页69)
在这段文字中出现theoretisch一词,如上一节末尾所说,方教授将此词译为“抽象的”。基于这种理解,他又将moralischer Sinn译为“道德认识”。他的理由是:
道德情感是一个有关苦乐之情的概念。认识到这一点对理解康德的想法非常重要。因为,正是这一点决定了道德情感是主观性的(Subjektiv)概念,从而不同于通常总是与一个对象(Gegenstand)相关的道德认识。依康德,后者提供知识(Erkenntnis),而前者则否;前者是主观性的(Subjektiv),而后者则与理论抽象有关(theoretisch)。因此之故,康德反对将道德情感与道德认识混为一谈。这个区别在英译中多少还能看出,前者被译作moral feeling,后者被译作moral sense。可是一旦被中译为“道德情感”与“道德感觉”,它们的差别就不是那么明显了。(页64-65)
这里提到的moralischer Sinn一词是苏格兰哲学家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 1694-1747)的核心概念moral sense之德文翻译。康德早年在1760年代曾深受哈奇森的道德哲学之影响。将moral sense译为moralischer Sinn并无问题,中文可译为“道德感”。但无论是英文的sense,还是德文的Sinn,都有歧义。依哈奇森,moral sense是一种情感,它是道德之“证成理由”(justifying reason)。但是sense一词也有“感觉”之义,例如视觉的英文说法是the sense of sight。这种感觉涉及一个对象,因而具有知识意义。由于这种歧义,康德担心moralischer Sinn一词可能使人误解它是一种具有知识意义的“感觉”。
方教授将theoretisch译为“抽象的”,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在德文里,与“抽象的”一词相对应的是abstrakt。theoretisch通常译为“理论(性)的”,牟先生有时亦译为“知解的”或“观解的”。它是相对于“实践的”(praktisch)而言的,是具有知识意涵的。所以康德说:“‘感觉’一词通常意指一种理论性的、牵涉到一个对象的知觉能力。”在这句话中,“牵涉到一个对象”是对“理论性的”一词之进一步说明。由于感觉为我们的经验知识提供材料,所以“感觉”一词具有知识意涵。方教授将theoretisch译为“抽象的”,可是康德明明说“感觉”是一种“知觉能力”,“知觉能力”怎么是“抽象的”或“与理论抽象有关”呢?由于不了解这一点,方教授才会坚持将此词译为“道德认识”。在德文里,与“认识”相对应的是Erkenntnis,而不是Sinn。
牟先生别出心裁,以“感取”来翻译Sinn,而将moralischer Sinn译为“道德感取”,并且解释说:它是“道德方面的感性作用,一般笼统地说为道德感觉,更简单地说为道德感”(页502)。对此,方教授质疑道:
除非牟宗三所说的“感性作用”也能提供知识,否则“感取”这样的译名终究还是不能契合康德对Sinn (sense) 的设定:指向某个对象(bezoge auf einen Gegenstand)、提供知识。(页66)
感觉就是感觉,它和抽象有什么关系?同样,作为“感性作用”的感取又怎么会是一种知解性的知觉之力量?难道“感性作用”里还包括了“知解”的成分在其中?(页67)
牟先生将Sinn译为“感取”,将theoretisch译为“知解的”或“观解的”,是否恰当,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他说“感取”是一种“感性作用”,并无问题;而说这种“感性作用”会“牵涉到一个对象”,而提供知识,也没有问题。我们只要阅读《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都可以确定这一点。艾斯勒在《康德辞典》中解释道:“‘理论性的知识’是这样一种知识:‘藉由它,我认识现存之物’。”(“Die ‘theoretische Erkenntnis’ ist eine solche, ‘wodurch ich erkenne, was da ist’”)*Rudolf Eisler, Kant-Lexikon (Hildesheim: Georg Olms, 1977), S. 534.可见它不限于抽象的知识,也包括关于感性对象的知识。方教授质疑道:“感觉就是感觉,它和抽象有什么关系?”这显然是由于他自己误解了theoretisch一词的涵义。至于他质疑说:“作为‘感性作用’的感取又怎么会是一种知解性的知觉之力量?”则是误解加上望文生义的结果。
方教授还有一个翻译上的错误。他将pa-thologisches Gefühl译为“生理性的情感”(页64)。关于pathologisch一词,邓晓芒与李秋零一贯都译为“病理学的”。这些都是误译。让我们看看艾斯勒对pathologisch一词的解释:“以一种承受、忍受为基础的,以感性为条件的。”(“auf einem Leiden, Erleiden beruhend, sinnlich bedingt”)*同上,第409页。因此,笔者将此词译为“感受的”。日文的《カソト事典》(东京:弘文堂,1997年)也用汉字将此词译为“感受的”(页49)。
四
方教授对牟先生的第二点批评涉及《道德底形上学》中的另一段文字,这段文字系紧接着引文(2)而出现:
(3) Wir haben aber für das (Sittlich-) Gute und Böse eben so wenig einen besonderen Sinn, als wir einen solchen für die Wahrheit haben, ob man sich gleich oft so ausdrückt, sondern Empfänglichkeit der freien Willkür für die Bewegung derselben durch praktische reine Vernunft (und ihr Gesetz), und das ist es, was wir das moralische Gefühl nennen.(S. 400)
笔者译:但是我们对于(道德上的)“善”与“恶”并不具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正如我们对于真理并不具有这样一种感觉(尽管我们经常如此表达),而是我们具有自由意念对于“它自己为实践的纯粹理性(及其法则)所引动”的感受性,而这便是我们所谓的道德情感。
在这段文字当中,方教授批评的焦点集中于“Empfänglichkeit der freien Willkür für die Bewegung derselben durch praktische reine Vernunft (und ihr Gesetz)”一语的翻译与诠释。方教授先引述阿保特的英译:“we have a susceptibility of the free elective will for being moved by pure practical reason and its law.”方教授评论道:“可是句意却并没有因此而显豁,反而因为主词we的出现而使句子成分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for being moved’中的for究竟何解?”(页70)其实,阿保特在此补上we have,只是顺着前文补上省略的主词,根本没有增加什么内容,何至于“变得更加复杂”?至于for being moved,也是贴近原文的翻译,其涵义下文再讨论。
接着,方教授引述牟先生的翻译:“但是我们关于自由选择的意志对其为‘纯粹实践理性以及纯粹实践理性之法则’所推动这一点,却有一种感受。”(页503)对此,方教授评论道:
虽然从英译而来,但牟甩开了英译所补的主词we(我们),而将意志作为真正的主词,从而摆脱了语义缭绕,使整个句子结构明朗起来。经过这样疏通,康德的意思变成:自由选择的意志对于它受实践的纯粹理性(praktische reine Vernunft)(及其法则)推动这一点自有一种感受,而这种感受就是道德情感。(页71)
为了佐证他的解读,他又引述牟先生自己的说明:“它〔道德情感〕只是‘自由选择的意志’当为理性法则所推动时,所有的一种感受。”(页503)但方教授随即强调:
这种理解及由此而来的翻译并不符合康德的本意。康德本意是说,我们感受到自由意志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受理性法则推动的。众所周知,自由意志是康德道德学说的根基,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而这个理由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我们感受到自由意志的运动。这种感受是道德义务的根基所在。所以,感受的对象是自由意志的由理性法则推动的运动,不是自由意志受法则推动这件事。(页72)
基于这种理解,方教授建议将这段文字翻译为:“(我们拥有)……一种对于自由选择意志的感受性,即一种对于由实践的纯粹理性及其法则推动的自由选择意志的运动的感受性。”(页72)
方教授认为牟先生的翻译与理解方式违背康德的原意,因为:
按照康德,当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之决定是从义务之法则而来时,主体的感受就是一种纯净的快乐之感。反之,当自由选择的意志与纯粹实践理性及其法则相违,那么主体就有一种不快乐的感受。
如果像牟宗三理解的那样,道德情感是自由选择的意志为理性法则推动时的一种感受,读者从中就很难了解康德想要表达的“道德情感是与义务法则相关的苦乐之情”那样的意思。(页72)
以上笔者已尽可能忠实地重述了方教授对牟先生的批评,现在让我们检视方教授的批评是否有道理。
首先,方教授说:“这种感受是道德义务的根基所在。”这等于是说:“道德情感是道德义务的根基所在。”这完全违背康德的基本观点,因为这是哈奇森的观点,而为康德所反对。其次要指出的是方教授误读了牟先生的翻译。在牟先生所说的“我们关于自由选择的意志……”一语中,主词仍是“我们”,“关于自由选择的意志”必须连读,“自由选择的意志”是the free elective will的翻译,而后者又译自德文的freie Willkür。用英文来表达,方教授将牟先生的翻译误读为our will to free selection。因此,牟先生根本没改变阿保特英译的句子结构。
但是真正造成方教授的困惑的,并非这个句子的结构,而是他对德文Willkür一词的严重误解。在《道德底形上学》中,康德对Wille与Willkür明确地加以区别。笔者分别以“意志”与“意念”来翻译这两个词汇*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6卷,北京:中国人民学出版社,2007年。收入张荣所译的《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按照字典上的意义,将Willkür译为“任性”,这是非常不恰当的。因为在康德的著作中,Willkür一词是个专门术语,而非日常语言。张荣将freie Willkür译为“自由任性”,实在令人觉得不知所云。。方教授忽而将freie Willkür译为“自由选择的意志”,忽而将它译为“自由意志”,可见他根本不知道康德对Wille与Willkür所作的区别。阿保特将Willkür译为the free elective will,牟先生将它译为“自由选择的意志”,虽嫌累赘,但并非没有根据。其根据便在康德自己的说明。
在《道德底形上学》中,康德先后有两次说明Wille与Willkür的区别,其文如下:
(4) Das Begehrungsvermögen nach Begriffen, sofern der Bestimmungsgrund desselben zur Handlung in ihm selbst, nicht in dem Objecte angetroffen wird, heiβt ein Vermögen nach Belieben zu thun oder zu lassen. Sofern es mit dem Bewuβtsein des Vermögens seiner Handlung zur Hervorbringung des Objects verbunden ist, heiβt es Willkür […] Das Begehrungsvermögen, dessen innerer Bestimmungsgrund, folglich selbst das Belieben in der Vernunft des Subjects angetroffen wird, heiβt der Wille. Der Wille ist also das Begehrungsvermögen, nicht sowohl (wie die Willkür) in Beziehung auf die Handlung, als vielmehr auf den Bestimmungsgrund der Willkür zur Handlung betrachtet, und hat selber vor sich eigentlich keinen Bestimmungsgrund, sondern ist, sofern sie die Willkür bestimmen kann, die praktische Vernunft selbst.(S. 213)
笔者译:依乎概念的欲求能力,就其行动之决定根据见诸它自身之中,而非在对象中而言,称为任意作为或不为的能力。就它与其产生对象的行为能力之意识相结合而言,它称为意念(Willkür)〔……〕。如果欲求能力之内在的决定根据、因而甚至意愿都见诸主体底理性之中,它便称为意志(Wille)。因此,意志之为欲求能力,并非(像意念一样)着眼于它与行为相关联,而毋宁着眼于它与意念底行动之决定根据相关联;而且它本身根本没有任何决定根据,而是就它能决定意念而言,它就是实践理性本身。
(5) Von dem Willen gehen die Gesetze aus; von der Willkür die Maximen. Die letztere ist im Menschen eine freie Willkür; der Wille, der auf nichts Anderes, als bloβ auf Gesetz geht, kann weder frei noch unfrei genannt werden, weil er nicht auf Handlungen, sondern unmittelbar auf die Gesetzgebung für die Maxime der Handlungen (also die praktische Vernunft selbst) geht, daher auch schlechterdings nothwendig und selbst keiner Nöthi-gung fähig ist. Nur die Willkür also kann frei genannt werden. (S. 226)
笔者译:法则出自意志;格律出自意念。在人之中,后者是一种自由的意念;意志所涉及的无非只是法则,既无法被称为自由的,亦无法被称为不自由的。因为意志不涉及行为,而是直接涉及对于行为底格律的立法(因而涉及实践理性本身),所以也是绝对必然的,而且甚至没办法受到强制。因此,唯有意念才能被称为自由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枝蔓,并便于接下来的讨论,我们可以将这两段文字的要点归纳如下:
1)由意志产生法则(客观原则),由意念仅产生格律(主观原则)。
2)意志不直接涉及行为,意念才能直接涉及行为。
3)意志为立法能力,故无所谓自由或不自由;意念为抉择能力,始有自由可言。
4)意志本身无任何决定根据,但可决定意念,并透过意念来决定行为;就此而言,意志就是实践理性本身。
阿保特将Willkür译为the free elective will,牟先生将它译为“自由选择的意志”,就是根据第三点。
此外,在其《道德底形上学》一书的初稿中,康德对“意志”与“意念”之区别有进一步的说明。他以“理体”(Noumenon)与“事相”(Phänomenon)的关系来解释“意志”与“意念”的关系。他写道:
(6) Die Freyheit der Willkühr in Ansehung der Handlungen des Menschen als Phänomenon besteht allerdings in dem Vermögen unter zwey entgegengesetzten (der gesetzmäβigen und gesetzwiedrigen) zu wählen und nach dieser betrachtet sich der Mensch selbst als Phänomen.-Der Mensch als Noumen ist sich selbst so wohl theoretisch als praktisch gesetzgebend für die Objecte der Willkühr und so fern frey aber ohne Wahl.*Vorarbeiten zu Die Metaphysik der Sitten. Erster Teil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KGS, Bd. 23, S. 248.
笔者译:的确,就作为事相的人底行为而言,意念底自由在于就两个相反的行为(合乎法则与违反法则的行为)作抉择的能力,而且人根据这种自由将自己视为事相。──作为理体的人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实践方面,均是为意念底对象自我立法者,且就此而言,有自由而无抉择。 在康德的用法中,“理体”与“事相”之区分约略相当于“物自身”(Ding an sich)与“现象”(Erscheinung)之区分*参阅拙作:《牟宗三哲学中的“物自身”概念》,收入拙著:《当代儒学之自我转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年。第28—30页;简体字版:《当代儒学的自我转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5—26页。关于“意志”与“意念”之区别,参阅拙作:《孟子的四端之心与康德的道德情感》,收入拙著:《儒家与康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第114—116页。。
“意志”与“意念”之区别对于我们理解引文(3)中那个有争议的句子极具关键性。在“Empfänglichkeit der freien Willkür für die Bewegung derselben durch praktische reine Vernunft (und ihr Gesetz)”这个句式当中,derselben是指freie Willkür(自由意念),durch表示被动之意。因此,“die Bewegung derselben durch praktische reine Vernunft (und ihr Gesetz) ”意谓“自由意念为实践的纯粹理性(及其法则)所引动”一事,自由意念所感受的即是此事。笔者为了便于中文读者的理解,稍稍改变句法,将此句译为:“我们具有自由意念对于‘它自己为实践的纯粹理性(及其法则)所引动’的感受性。”而牟先生将此句译为:“它〔道德情感〕只是‘自由选择的意志’当为理性法则所推动时,所有的一种感受。”意思也大体无误。
方教授之所以不接受牟先生的翻译与诠释,主要是由于他自己将“自由意念”误解为“自由意志”。既然对康德而言,意志是立法能力,因而是决定者,方教授便将die Bewegung derselben durch praktische reine Vernunft (und ihr Gesetz)简化译为“自由意志的由理性法则推动的运动”。按照这样的翻译,die Bewegung derselben便意谓“自由意志的运动”,运动是由自由意志所产生的,而全句则意谓:自由意志藉由实践的纯粹理性(及其法则)所产生之运动。这样的翻译在文法上固然说得通,但在义理上却说不通。因为derselben不是指“自由意志”,而是指“自由意念”,而根据康德自己的说明,意念属于直接涉及行为的“事相”,是被道德法则或感性对象所决定的。因此,当我们的自由意念为理性法则(道德法则)所引动时,自由意念对此事便会感受到一种愉快,这便是道德情感。反之,当我们的自由意念为感性对象所引动时,自由意念对此事便会感受到一种不快,这是一种负面的道德情感。根据这样的诠释,我们并不会如方教授所担心的,“很难了解康德想要表达的‘道德情感是与义务法则相关的苦乐之情’那样的意思”。反之,如果依方教授的诠释,这种感受性便是“自由意志的感受性”;但依康德的说明,自由意志属于不直接涉及行为(包括“运动”)的“理体”,如何会有感受性呢?可见他对于freie Willkür的误解导致“一着错,全盘皆错”的严重后果。
方教授在其论文的末段评论道:“作为有自己观点的哲学家,牟宗三与康德的看法容有不同,只是,他在译注康德时受自身观点的干扰未能准确地传达对方意旨。”(页73)然而,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固然发现牟先生受限于英文译本或疏忽,他的确有若干误译之处,但情节并不严重,基本上无碍于他对康德思想的把握。故大体而言,牟先生并未误解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反之,方教授虽然在语文条件上优于牟先生,但由于他自己对康德思想的隔阂,反而严重误解康德的“道德情感”概念。方教授在文末又说道:“反省前人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无论如何,用中文消化康德学,道路既阻且长。”(页73)看来这句话更适于用在他自己身上。
(责任编辑任之)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2-0081-07
*作者简介:李明辉,台湾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合聘教授、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合聘教授,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