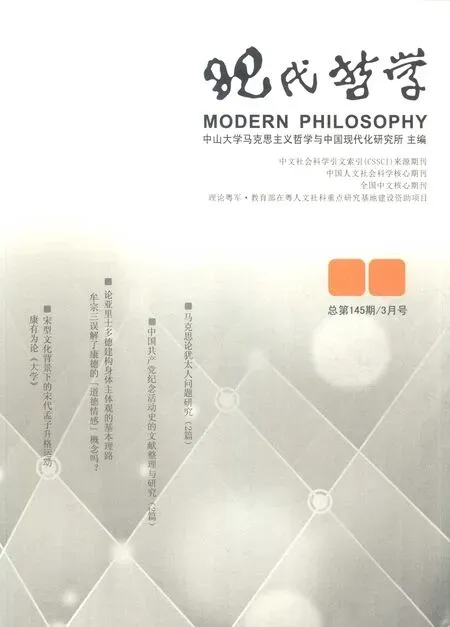两个关于“世界史”的哲学论述
——京都学派与柄谷行人之间*
2016-02-01廖钦彬
廖钦彬
两个关于“世界史”的哲学论述
——京都学派与柄谷行人之间*
廖钦彬**
【摘要】当日本进入太平洋战争与欧美诸帝国进行一场世纪大战时,以西田几多郎与田边元为首,底下包括务台理作、西谷启治、高坂正显、铃木成高、高山岩男及大岛康正等人在内的京都学派因应现实,在哲学理论的建构上提出“近代超克”论。结果带来的是“世界史的建构如何可能?”的历史哲学问题。事隔七十余年的现在,柄谷行人以《世界史的结构》(2010)一书,思考人类如何克服“国族(nation)、国家(state)、资本”在当代所产生的问题,借以建构新的世界史图像。
柄谷在该书中透过贯穿“漂泊者、氏族社会/国家/资本/世界共和国(A/B/C/D)”的“交换模式”理论,来取代马克思的商品交换模式,并援用以康德“永久和平”理念为基础的“世界共和国”概念,来提出现今人类所应朝往的理想境地。此种“世界史”结构的论述,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问题意识上,与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理论截然不同。
柄谷借用弗洛伊德的“被压抑之物的回归”说法,探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可能性,后者以大乘佛教的空或无的思想为基础,探讨超越固执于自我同一性存在的可能性,也因此为国族、国家、资本保留了存续的可能性。虽说如此,两者在建构世界史图像时有个共同点,那便是透过哲学的想象力主张“过去不再只是过去,它会透过现在而在未来中被改变”、“未来的形成是透过现在改变过去才可能”。
【关键词】京都学派;世界史;近代超克;交换模式;世界共和国;想象力
一、前言
在今日,我们需要何种史观,已经不是一人、一国、一个区域或任何一个权力机构所能提供与掌控的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有众多史观可供我们参考。譬如宗教上的有末世论史观、正像末史观,哲学、政经或生物上的有观念论史观、唯物论史观、进化论史观、性史观、循环论史观、殖民史观等等。这些冠上某某概念或名称的史观都在告诉我们,历史有无限的解释可能性,同时也意味着任何可能性只能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而不是一个绝对的必然。今日人们无论在客观认知上了解了多少史观,每个人必拥有一个与自身生命、信念贴近的史观或价值观,姑且不论它是否会随时间而有所改变。而这种立场正传达出一种讯息,即生命、信念(甚至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史观。这种“生命即是历史”、“历史即是生命”的表现和用实证的方式搜集、专研史料并拼凑出历史的具科学及客观的精神恰恰相反。两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是否有自身生命的跃动。
笔者在本文透过对京都学派与柄谷行人(KarataniKōjin, 1941-)的“世界史”论述之探讨,所欲思考的正是“生命即是历史”与我们自身有何种关连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京都学派还是柄谷行人,都是以自身对人类或世界的关怀,来勾勒“世界史”的蓝图并对它赋予当代性的意义。
二、昔日的“世界史”图像
当日本进入太平洋战争与欧美诸帝国在意识形态上进行一场理念性(一种随处既是中心亦不是中心的理念)的世界大战时,以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ō, 1870-1945)与田边元(Tanabe Hajime, 1885-1962)为首,包括务台理作(MudaiRisaku, 1890-1974)、西谷启治(NishitaniKeiji, 1900-1990)、高坂正显(Kōsaka Masaaki, 1900-1969)、铃木成高(Suzuki Sigetaka, 1907-1988)、高山岩男(KōyamaIwao, 1905-1993)及大岛康正(ōshimaYasumasa, 1917-1989)等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因应现实状况,在哲学理论的建构上提出“近代超克”论,结果带来的是“世界史的建构如何可能”的历史哲学问题。事隔七十余年后,柄谷行人以《世界史的结构》*[日]柄谷行人:《世界史的结构》,东京:岩波书店,2010年。一书,思考人类如何克服“国族(nation)、国家(state)、资本”在当代所产生的问题,借以建构新的世界史图像。前后者的“世界史”论述虽都以自身面临的现实状况出发,但因时代背景的不同,所以本文将在此章与第三章先阐明“世界史”图像的昔与今,之后再探讨两种图像之关连。*关于京都学派与柄谷行人的“世界史”论述,在根本上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但笔者认为两者在建构世界史图像时有个共同点,那便是透过哲学的想象力主张“过去不再只是过去,它会透过现在而在未来中被改变”、“未来的形成是透过现在改变过去才可能”。关于其异同,笔者将于以下的探讨中突显出来。
(一)铃木成高的世界史学
关于京都学派“世界史”概念的成立,首先必须检视铃木成高的世界史学。铃木世界史学的形成来自于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世界史学。铃木在其第一本着作《兰克与世界史学》*[日]铃木成高:《兰克与世界史学》,京都:弘文堂,1939年。中对兰克史学的出发点、形成过程、基本概念、结构等做了详细的分析,并认为在其史学中有一个精神在贯穿着整体。此精神即是透过历史来掌握个别的事实(个别史),并将这些个别史连接到一个“普遍的关连”的世界史精神。*同上,第16页。兰克史学的成立奠基在以史料客观地考察历史(纯粹的历史认识),并显示出内在于各个历史中的原理,藉此接近神。*同上,第23—26页。也就是说,他的史学既是个别的也是普遍的学问。而这种“个别即普遍”或“多即一”的兰克史观,造就了他自身的世界史学。*同上,第49页。
然而,兰克的世界史学绝不是像历史哲学那样,以抽象概念或理论来建构学问,也不是基督教末世论下的产物。对兰克而言,各个历史是不被任何概念与理论所包摄的绝对性存在,绝不会被神所包摄。然而,各个历史事实越是清楚就越和神有关连。而且各个历史并非是分裂的状态,而是透过客观、实证的彻底历史主义,拥有各自的绝对性价値,同时亦被神的摄理所连结。很明显的,兰克的史学里潜伏着个别与普遍这两个基本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兰克想以哲学理念或理论来建构历史,应该说那是意味着因他那虔诚的神信仰,而自发性地表现出来的历史。铃木将兰克的史观和十八世纪以降的启蒙主义或理性主义史观以及基督教末世论史观做了明显的区分,认为那是尊重个别历史事实的世界史观。
兰克所谓的世界为何?它是指讲义录“近代史的诸时代”(überdieEpochenderneuerenGeschichte, 1854)中说的西罗马帝国瓦解后(中世以降)所形成的西欧世界。*参见[德]兰克:《世界史概观:近世史的诸时代》,[日]铃木成高-相原信作译,东京:岩波书店,1941年。兰克在此讲义录所意图的是,将东罗马帝国从西罗马帝国排除的西欧世界(西方欧洲)之形成史。铃木指出此形成史正是兰克所谓的世界史,并认为此世界史以欧洲世界为界线而没有能超越它,是因为世界史不是并列的历史,而是“建构的历史”。*[日]铃木成高《兰克与世界史学》,第126页。兰克的世界史并非来自史料的数量积蓄或诸多历史事实的罗列,而是来自他自身的“个别即普遍”或“多即一”的史学立场及民族的“道德生命力(moralische Energie)”*同上,第48页。。
昭和18、19年(1943-1944)铃木撰写《欧洲的形成》*《欧洲的形成》收录于[日]铃木成高:《欧洲的成立——工业革命》,京都:灯影舍,2000年。时,便是批判式地继承上述的兰克史观,并重新解释“欧洲的世界史”即是“世界史中的欧洲”。因为世界史已经无法停留在兰克所说的西欧世界史。新的世界史之建构,既是为了世界史,也是为了欧洲本身,这是一个来自新世界的要求。*[日]铃木成高:《欧洲的成立——工业革命》,第6页。此时的铃木世界史学之出发点,便是兰克的世界史学。然而,两者对古代罗马史的掌握却不同。铃木并没有接受兰克将古代罗马视为世界史以前的历史(即世界史的前史)的立场。如前述,兰克的世界史是指中世、近代的西欧世界史。而此世界史形成的原因来自兰克将东罗马帝国排除在西罗马帝国之外。也就是说,兰克的世界史决定于如何掌握该前史,即古代罗马史这一态度上。相对于此,铃木并没有将从古代到中世的转换视为罗马-日耳曼式世界(西欧世界)的成立过程,而是从新的世界史视野,来阐明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Orient与Occident(即东洋*此处的东洋和近现代所言的东洋不同,是指西洋史学上的“古代东方”。这里指邻接地中海的西亚地区,特別是指东罗马帝国的领域。([日]铃木成高:《欧洲的成立——工业革命》,第92—101。)与西洋)的分裂过程。*[日]铃木成高:《欧洲的成立——工业革命》,第43页。
铃木指出,若说从古代到中世的转换即是兰克西欧世界史的成立根据的话,那么他早已将原本在古代罗马史中的欧洲与亚洲(西洋与东洋)之复合体排除。无疑的,这是一种狭隘的世界史观。*[日]铃木成高:《兰克与世界史学》,第142—153页。因为这表示西欧世界切断了包含东罗马帝国的东洋世界文明,而形成了一个独自闭锁的文明。铃木指出兰克史学特征后,特别注意古代罗马史中的西洋与东洋的关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自身的欧洲图像。因为他认为西洋和东洋的关联,在欧洲图像形成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功能。*[日]铃木成高:《欧洲的成立——工业革命》,第109页。据此可知,铃木的古代罗马史观一直包含着东洋与西洋。
若兰克与铃木的欧洲图像之差异,是在于上述古代罗马史观的不同,那么针对两者所追求的世界史图像,我们可做以下的理解:兰克的世界史是排除东洋的西欧世界史,而铃木的世界史则是包含东西洋的世界史。原本应包含东西洋的世界史,经由兰克的主观选择,被转换成欧洲(即西欧)的世界史。而此种史观支配、影响着十九、二十世纪欧洲人的世界史观。欧洲人自此以其史观为中心,来看欧洲以外的世界及其历史。铃木认为,此种到世界任何地方都只是欧洲的延伸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正是兰克所造就出来的欧洲中心史观。藉此可知,铃木世界史学的核心就在于克服此种兰克所造就出来的欧洲中心史观,并重新将欧洲的世界史建构成世界史中的欧洲。
(二)西谷启治的“世界史的哲学”
和上述铃木的世界史学不同,西谷关注的是世界史哲学的成立可能性及其课题。西谷认为世界这一概念,是近世欧洲各国将其势力扩张到世界各地后,才开始被世人所意识。而在此意识下,世界本身才能得以自存。在那之前,世界的意识并不存在。因此欧洲的近世,已经是属于世界史的近世。然而,这种世界的概念,却只是欧洲人的世界。也就是说,欧洲即是世界的意思。但这种观念,随着日本的崛起,而有所改变。世界也因此才开始以其原本的、真正的面貌出现。*[日]森哲郎编:《世界史的理论:京都学派的历史哲学论考》,京都:灯影舍,2000年,第17—18页。这道出因日本的出现,欧洲中心主义下的世界观,显然已开始产生变化。
如铃木所指出,兰克的历史研究是经由客观的史料分析所产生,因此是一种纯粹的历史认知。其做法是透过历史掌握个别的事实(个别史),同时将它连接到一个“普遍的关连”。而西谷指出,这种具有实证性及客观性的世界史立场在欧洲成立,也是在倪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1)与兰克之后的事。然而,这只是欧洲人的世界史立场而已。日本人在世界史的认知上,亦是以其立场出发,因此带有浓厚的欧洲世界史观色彩。但此情况,因日本在世界地位的改变,显然已面临一个精神上的转换。世界史不再是某个特定主体或民族的所有物。西谷认为,世界史观虽根源自既有的世界意识(过去的观念),但它必须因应现实的历史世界(现在的局势)而有所改变。此可说是世界史哲学的立场。*同上,第20—21页。也就是说,世界史哲学的立场意味着日本在现实世界的地位,显然面临担负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的责任。世界史经由日本的参与,更能达到彻底排除具有主体性的世界史的意思。*同上,第25页。在这层意义上,世界史的哲学可说是把被主体遮蔽的真理呈现出来的思考活动。
另一方面,西谷却又指出真正的世界史建构,也不完全是无主体性的历史,它还必须透过回归古代与中世恢复主体的立场,来克服近世的部分客观立场。如此一来,西谷的世界史所欲呈现的即是将近世的客观立场推到极致的主体实践史观。而统一这种客观与主观、观看与创造的矛盾对立,成了西谷世界史哲学的最重要课题。*同上,第26—27页。
西谷认为自己的世界史立场,并不是由经验科学,也不是由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 1880-1936)所说的文化形态学,更不会是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所说的,由观念或理念所形成。“总之,世界史的时代是具有新结构的世界在旧世界开始发生的同时所酝酿出来的。该世界随着破坏旧世界结构的同时,又作为新时代而出发。”*同上,第29页。西谷断言道,每个时代的历史只是世界的自我实现过程而已。
西谷指出近世欧洲的世界史哲学完成于黑格尔。黑格尔所谓的世界史的哲学,事实上是启蒙主义以来的哲学式世界史观发展之完成。完成的理由是,超越历史的理性再次以具体形式内在化于历史性的世界史当中。而兰克的史学立场排除了像黑格尔那样以理性这种客观的角度来观看历史的立场,他认为应该以没有任何角度与动机的立场,来观看历史本身*同上,第37、39页。。很明显的,这里透露出近世欧洲的世界史经历了黑格尔的哲学化(世界史的哲学)与兰克的历史化(世界史的史学)过程。然而,西谷并不满意这两种立场。前者因黑格尔主张世界史的发展是精神的开展、是自由意识发挥的具体表现,而缺乏主体对现实世界的实际创造。相同的,后者也因兰克的实证性及客观性立场,而缺乏主体的实践。
兰克的世界史就西谷来看,只是以国家史、民族史为出发的欧洲中心史。相对于其静态的观照史观,西谷主张动态的实践史观,并认为历史世界应该是西田几多郎所谓“我和汝”*关于“我与汝”,西田如此说道:“我与汝是绝对的他者,包摄我与汝的并不是任何一般者。然而,我透过承认汝,才是我。汝透过承认我,才是汝。我的内部有汝,汝的内部有我,我透过我的内部向汝结合,汝透过汝的内部向我结合。正因为是绝对的他者,才能于内部结合。”([日]西田几多郎:《西田几多郎全集》第6巻,东京:岩波书店,1979年,第381页)。我与汝在此是一种辩证法的存在形态,即绝对二物的统一态。关系下的世界,是多民族作为主体相互交涉下的世界。唯有在这种我和汝的相互关系下,才会有真正的主体性。而真正的历史世界正是此种交互主体关系的场所。因为“一即多、多即一”才是世界的原本形态。兰克虽然脱离了黑格尔的观念论史观,但其实证史观下的世界史,却只停留在欧洲里。*[日]森哲郎编:《世界史的理论:京都学派的历史哲学论考》,第50页。西谷认为日本正处于突破兰克世界史观(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观)的处境。世界史不仅要有客观的分析还要有主体的实践,也就是说,理念与实践必须互为根据。*同上,第54页。世界史必须是世界的世界史。显然的,西谷援用西田几多郎“我和汝”、“一即多、多即一”的世界观,来辩证黑格尔与兰克的世界史立场,企图建构一个有日本参与的世界史图像。
(三)高坂正显的“世界史观的类型”
高坂就像呼应“世界史必须是世界的世界史”一样,因当时的历史现实及日本在世界的主导地位,认为世界史的问题不仅是现代的也是日本的问题,并指出世界史意识的形成来自两个情况。一是一个历史世界和其他异质的历史世界接触的情况(不同地区及文化的接触),另一是一个世界史的时代转移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史的情况(不同时代及价值观的转变)。也就是说,这是空间与时间所带出来的世界史意识。而日本当时所处的状况,在空间上是东洋诸世界的抬头,在时间上则是近代的即将被超克。也就是说,当时是一个世界旧秩序转换到世界新秩序的时代,而日本史的原理,因其地位,也必须是世界史的原理。高坂主张世界史的哲学须奠定理论基础(Grundlegung)与实际方向(Orientierung)。除了上述两种世界史的发展类型外,高坂还强调不可忘记主体性世界史的存在*同上,第59—62页。。高坂提出空间、时间与主体性这三种世界史类型,是为了藉由思考这些类型的意义与局限,来建构日本的世界史原理。
关于空间型的世界史观,高坂将焦点放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世界史的地理性基础”(die geographische Grundlage der Weltgeschichte)上。黑格尔将世界史的三大阶段与地理条件分别列举如下:一、拥有巨大草原及干旱高地的蒙古、阿拉伯等游牧民族的场所,这些属于文明未开的状态,因此是矿物阶段;二、拥有河流平原,大地丰饶,有人定居,有法、财、文化的中国与印度等地方,这些属于文明半开化的状态,因此是植物阶段;三、靠海,沿海有土地,海洋让人勇于冒险、创造财富的欧洲地中海诸国等,这些属于文明开化的状态,因此已达到开放、具体的普遍者阶段。然而,高坂指出黑格尔的世界史包含时间与空间,相对于时间叙述下的抽象世界史呈现出比较具体的面向有其意义存在,但它毕竟还是以精神、理性的发展来谈论历史,因此空间只是次要的因素而已。*同上,第64—68页。
关于时间型的世界史观,高坂举出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上帝之城》中的基督教史观。奥古斯丁认为世界历史是神救赎人类的历史。历史只有一次,是神创造的,开始于神也结束于神。他将人类一生的自然经过分成六个时期,即婴儿、少年、青年、壮年、高年、老成,并将这些阶段比拟于基督教从亚当堕落到末世审判之间的六个时期:一、亚当到罪恶洪水的时期;二、接着到亚伯拉罕的期间;三、从亚伯拉罕到戴维的时期;四、接着到巴比伦囚虏的时期;五、接着到耶稣基督的时期;六、最后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时期。然而,此六时期只是神国的一小部分。最后,由神所创造的人类历史会再次回归到神,因此人类的历史只有一次,不会重来或循环。另外,高坂还简略说明了孔德(IsidoreAuguste Marie François Xavier Comte, 1798-1857)的人类历史三阶段说:第一、神学的阶段,这是魔法、禁忌、咒术的世界,是一个从多神教发展到一神教(如基督教、天主教)的时代;第二、哲学的阶段,这是从宗教改革、怀疑主义的批判到启蒙、无政府主义的时代;第三、科学的阶段,这是从法国革命到实证、社会主义的时代。未来则属于第三阶段。孔德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成上述三阶段的世界史,其特征在于对人类理知(理性、科学至上)与社会生活对应关系的阐明。显然,这是以实证主义精神朝向将来乌托邦世界的直线上升之人类史及世界史。*同上,第79—81页。
关于时间型的世界史观,高坂归纳出以下几点共通的特征及缺点。一、世界史无论是摄理(神意)、悟性或理念,都被认为是某种合理性的东西,在那里并没有偶然性或非合理性,只有历史的乐观主义。而此种史观只不过是观念的史观。空间型与时间型的世界史观,分别具有特殊性与普遍性,但两者却都缺乏真正的主体性,也就是个别性。二、人类虽然拥有各种区域和时代的差别,但由一贯的普遍性所贯穿,所以能看到连续性的进步或发展。其缺点是历史的哲学化或合理化。历史既不是理念的产物,也不是体系性的东西。历史不能只属于合理性,因为历史的主体是非合理性的世界史之诸民族。若将世界史视为先验的世界计划之显现的话,那是对历史诸时代的抹杀。在这种视点下,不会有历史多样性的产生,三、在空间型的世界史观里,世界被否定而分散在各地区,缺乏一个统一性,相对于此,时间型的世界史观因自身的普遍性格而拥有一个统一性。然而,问题是人类的理念并无法由自由或知性的原理来道尽。*同上,第83—85页。
至于主体型的世界史观之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的史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对欧洲一切价值进行颠覆。他在批判基督教的同时,主张回归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生命奔放、狂欢的世界。这意味着对理性、神性、信仰的反抗。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崇尚的是取代基督教理想的“超人”(übermensch)。而这个具有个性的主体——英雄或“超人”,正是高坂所说的主体型世界史观的主角。历史的意义对尼采而言,不在于神、理性、民族、国家,而在于英雄或“超人”。尼采在《道德的系谱学》中说明贵族(君主)的道德(Herrenmoral)以强力、高贵为重,以弱小、卑微为误,奴隶(众愚)的道德(Herdenmoral)强调世俗的善与恶。而后者对前者的怨恨(Ressentiment),正如同禁欲的僧侣对自由的超人之怨恨。尼采基本上认为,历史的流动可从这两种道德的斗争中看到。高坂虽评价尼采上述非合理性的思维及主体性的实践,但却认为他只不过是世界史的心理学家。因为在尼采的史观里既没有宗教,也没有国家、社会、民族,只有高贵的超人而已。*同上,第87—90页。
然而,高坂宣称日本面对世界史的问题,已无法再利用以上的任何一种类型,主张必须要有新的类型来对应当代,此即为世界史的第四种类型,也就是“绝对无”的世界史。因为空间、时间、主体这三类型,如上所述,各有其长短处。空间型史观虽强调土地、区域的重要性及自然主义与多元性,但缺乏普遍与个别性。时间型史观虽具有连续性、发展性、普遍性、一元性及理性主义色彩,却缺乏特殊与个别性。主体型史观虽具有实践性,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但缺乏特殊与普遍性。而第四种类型则虽包含这三种特性,却不为三者所束缚,因为它只是“绝对无的象征”而已。高坂说道:“世界历史是绝对者的发现、象征。原本绝对者就是绝对无,在对象上是无。世界历史只是象征性地显现它而已。只要人类的理念和此种绝对者能够有所连系,人类的理念就应该能在世界史中被象征性地显示出来。世界史毕竟是象征人类命运的象征式人类的历史。”*同上,第94页。对高坂而言,“世界史是绝对无的象征的历史”*同上,第96页。。
(四)务台理作的“世界史的系谱学”
务台主张时代的区分不仅是世界史哲学,也是现代日本自身的历史实存课题,并认为每个时代必有其系谱,也就是时代自身的来源、出自与形成,因为时代是一种历史情境的“非连续之连续”。而追求世界史的系谱学(Genealogie)的成立可能性,可说是务台世界史哲学的最大课题。
关于时代区分法,务台提出凯勒(Christoph Keller, 1638-1707)的时代三分法,即“古代→中世→近代”。凯勒认为此三分法,是来自“古典→非古典→恢复、再生古典”的区分方式。他之所以会如此解读,是因为毎个时代虽有异于其他时代的特质,但绝不是完全不相关、完全被裁断的历史。而此种三分法的区分方式在世界史,已成为一种难以被推倒的公式。*同上,第191—192页。
然而,务台认为日本所处的世界史情况,已无法再用凯勒时代三分法来加以解释。它应该是如此的区分方式,即“古代→中世→近代→现代”。因为人类的历史已经来到一个转换的时期。务台所勾勒的模式是“世界史的系谱=时代的系谱=切断、停止历史的连续、延伸、圆环”。对务台而言,“古代→中世→近代→现代”的时代转换是一种世界观的转换、价值的颠倒。而日本所要超越、克服的正是源自西方且蔓延到世界各地的机械文明、近代国家及无宗教信仰等。但此种对近代的超克,并不是意味着历史(事实)的变更,而是历史世界观的变更。他强调造形美术、雕刻、建筑等样式的变迁,亦和近代超克的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同上,第195—196页。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世界史的形成是来自于人类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上述的世界史四分法,目的是在于确立否定近代的现代,也就是恢复、再造中世。务台认为恢复中世的宗教性,是现代的课题之一。然而,这并不意味现代是一种既进歩又倒退、既非宗教性(理性)又宗教性(反理性)的背理时代。因为务台所谓的系谱是指从现在追溯到过去,藉此形成自身的意思。对务台而言,世界史的系谱的主体是时代本身,而对现在的掌握、定位则是各个时代的系谱之原型。因此日本人作为具有历史性的民族,也应该要完成自身使命、成就自身,接受时代的挑战,自主性地解决该时代的课题。此课题即是对现在的确认,也就是对西洋近代的超克。如务台所说的,“向过去追寻现在系谱的意志,事实上和把现在设立在未来的意志是一样的”*同上,第206页。,正意味着务台的世界史的系谱学是属于朝向未来的学问*务台在这里谈的世界史的系谱学,实是一种时代区分学。至于如何区分的问题,在战后为大岛康正《时代区分的成立根据》(京都:灯影舍,2001年)所继承。。
三、柄谷行人的“世界史”想象
京都学派哲学家的世界史论述让我们感受到,人在面对自身生命的困顿及在困境下该如何生存或行动的问题时,自然会对自身所处世界的价值观(无论是被给予或自身持有的价值观)进行一种改造或转变。而京都学派哲学家的世界史建构,便是属于其中一种自然反应。
那么活在当代的我们,难道对生命自身及所处世界都没有任何不满、失望或绝望吗?在面对无国界的跨国企业之自由资本主义行动,人们只能束手无策,任由其宰割,国家社会在自身的存亡上,已疲于奔命,对内不仅得安抚人民的不满情绪,对外还得应付国际间的尔虞我诈,甚至是无形的资本猛兽。在这种“人、国家社会、资本”三者纠缠难解的情况下,柄谷行人感到人类自身有必要重新认识世界的结构及它所应该朝往的理想形态。
柄谷的世界史与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目的有所不同,前者企图超越国家、民族、资本,后者则保留了这三个要素。然而笔者认为两者的哲学行动或态度,却没有太大的差异。因为当两者在面临过去(历史)与现在(现实)的压迫与束缚时,自然会对未来产生一种想象,渴望在朝往充满希望的未来之途中,能改变过去与现在所带来的窘境。柄谷说明自己会在当代提出世界史,完全来自对现实的关怀,并认为要对世界史有一个当代性的创造,必须倚靠人类自身勾勒过去与未来的“抽象力”及“想象力”。*[日]柄谷行人:《世界史的结构》,第48、322—326页。
(一)世界史的结构与交换模式理论
柄谷在《世界史的结构》的序文开头处便告知读者,自己并不是要撰写世界的历史,而是企图从交换模式重新检视社会构成体的历史,藉此提出一条能超越现代的“国族(nation)=国家(state)=资本”*超越、克服这三者对人类的宰制是柄谷在《世界共和国へ―资本=ネーション=国家を超えて》(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的主要思想工作。中译本参见[日]柄谷行人:《迈向世界共和国:超越资本=国族=国家》,墨科译,台北:台湾印书馆,2007年。三者结合之道路。在这过程中,他试图透过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来重读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并透过康德来重解马克思,当然在其中不可缺漏的就是对黑格尔的批判。因此,这本长达504页的大著作,可说是他对古典哲学的再诠释。当然,此著作还包括对近现代哲学家、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包括地政学家)、社会学家等学说的继承与批判,在此无法一一列举。柄谷谈到社会构成体的历史时,举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哲学进行转换的过程。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人类历史的进程视为自由能够普遍被实现的过程(其发展过程是从非洲、亚洲、希腊-罗马到日耳曼社会及近代欧洲的过程)是对历史的一种观念论式掌握,并指出历史必须以生产模式,即谁拥有生产手段这种观点来加以掌握。人类的历史透过马克思的解释,变成以下的结构:“无国家→氏族社会”、“亚洲型国家→王与一般的隶属人民(农业共同体)”、“古典古代国家→市民与奴隶”、“封建国家→领主与农奴”、“近代国家→资本与无产—劳动阶级”。*[日]柄谷行人:《世界史的结构》,第33页。柄谷认为此种模式的史观虽有可取之处,却必须加以改造与再诠释。
柄谷首先将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归结出来的生产模式及商品交换(狭义的交换模式)观点,转换成广义的交换模式观点,并将交换模式分别以A、B、C、D来表示。此四种交换模式被归纳成“互惠、赠与与还礼关系”、“掠取与再分配、支配与保护关系”、“商品交换、货币与商品关系”以及“X(指透过B、C的扬弃恢复A的交换模式)”,分别代表着以下四种社会构成体,即“氏族、部族”、“国家(亚洲、古典古代、封建型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共和国”。*同上,第15、39页。
显然,马克思从生产模式或商品交换来解释世界史,已经不合时宜*京都学派左倾哲学家三木清(Miki Kiyoshi, 1897-1945)在《人学的马克思形态》(1927)便表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ie)。该史观必须与具有人的基础经验与反省经验的人学(Anthropologie)以及无产阶级者的基础经验处于一种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否则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史观([日]三木清:《三木清全集》第3卷,东京:岩波书店,1984年,第5—41页)。三木的主张不能说是直接影响了柄谷将马克思的商品交换转换成广义的交换模式,但当时与现今的无产阶级者之意涵,有极大的不同。那便是现代的无产阶级者同时也意味着消费者,也就是说基础经验已经改变。因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要套用在现今的世界史观,显然已不合适。。当然这是就柄谷的世界史观点来评判的。而之所以不合时宜,全然是来自柄谷对世界史建构所发挥出来的“抽象力”与“想象力”。因为他在氏族社会以前设置了漂泊者(band)的存在,并在资本主义之后提出“世界共和国”的理念。*当然漂泊者与世界共和国并非柄谷的独创。前者早已由莫斯(Marcel Mauss,1872-1950)、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泰斯塔(Alain Testart,1945-)所提及,而后者则由康德提出。这两种被构想出来的社会构成体,可说是柄谷世界史理论的关键。*柄谷在《世界共和国へ》中大抵勾勒出《世界史的结构》的內容,但从他在后著增加第一部“迷你世界系統”(“ミニ世界システム”),以及在各处增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交换模式理论的关系,可见其重要性。此外,作为“迷你世界系统”的延伸,柄谷在《游动论:柳田国男与山人》(东京:文艺春秋,2014年)一书中,为柳田国男进行辩护的同时,提出山人的理论,藉以说明漂泊者(band)在日本的存在。其交换模式的时态分别是过去与未来。就笔者来看,此种对历史的构想,完全是来自柄谷自身对未来的憧憬与期待,这与京都学派历史哲学的基本立场没有太大的不同。譬如田边元提出“人类因现在如何行动,甚至在未来朝向何种目标,来改变过去”的说法便是明证。*参见拙论:《战后京都学派的历史哲学与“近代超克”:以田边元与大岛康正为中心》,《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8卷第1期,2011年6月,第275—300页。
漂泊者是由柄谷配合交换模式A所想象出来的存在。漂泊者为一个极为松动、没有固定居所的3-50人的采集狩猎之小集团。在此集团中的互惠行为里,并不存在上下权力或约束关系。然因地球天气变迁,开始定居在海边,才形成氏族集团或部落。自此交换模式A开始有些许转变,但还尚未进入交换模式B,也就是国家权力下的行动模式。柄谷指出,无论是漂泊者或他们定居后所产生的氏族集团、部落或共同体,都与集权国家有一线之隔。前者因“互惠、赠与与还礼”模式保持和平与平等状态,拒绝成为后者。*[日]柄谷行人:《世界史的结构》,第62—72页。
柄谷在《迷你世界系统》的最后篇幅,提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图腾与禁忌》的精神分析概念“杀父”,来说明氏族社会不会变成集权国家的理由。兄弟杀父亲代表着氏族社会拒绝变成集权国家,亦即兄弟永远不想变成残暴、威权的父亲。而柄谷采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立场,认为氏族社会不会变成集权国家,是来自“被压抑之物的回归”,也就是说那是被压抑、忘却的东西(无拘束、自由、平等的状态)又回来的意思。其理由是人类无论处在“氏族”、“国家”、“资本”或交换模式A、B、C任何一个比较强势的状况下,都会面临“被压抑、忘却的东西又回来的”情况。这是柄谷在勾勒世界共和国时所必备的条件,因为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超越、克服当代社会的形态——国家或资本社会形态(交换模式B或C)所带来的人类危机。而其最好的解释自然会落在人有回归到被压抑、忘却之前的状态之本能。以此为基础,柄谷称世界共和国D即是超越、克服“世界=帝国”与“世界=经济”(即国家B与资本C),并在更高的次元恢复“迷你世界系统”(漂泊者或氏族社会A)的理念。*同上,第461页。
在此因文章篇幅关系,不深入讨论柄谷对国家(如亚洲、古典古代、封建型国家)的区分及资本主义之各种形态的分析。总之,他最后归结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无法摆脱彼此,单独成为纯粹的国家B或资本C模式,两者在当代社会仍然以连手的方式压迫、拘束着人类。
对柄谷而言,世界共和国(交换模式D)并不存在于人类的现实世界里。当他在重新解读康德《论永久和平》时,将世界共和国解释成“诸国家联邦”之形态,也就是一个各国不断往世界公民共同体迈进的未来形态。这里存在的只有对现实国家的扬弃运动,而能使这项运动不断前进的是“赠与的力量”。此力量代表的不是分配的正义(柄谷的罗尔斯批判),而是交换的正义(具有来自超越、普遍的命令、义务),也就是交换模式A的高层次恢复。*同上,第446—451、458—462页。此外,柄谷还提出消费者联合运动模式,来解决现代劳资关系下所产生的危机(资本对人的控制与压榨)。总之,柄谷试图分别从如何超越国家B或资本C模式的思考进路,来勾勒交换模式D的形象。
(二)对古典哲学的再诠释——康德、黑格尔、马克思
如果我们想从《世界史的结构》来检讨柄谷的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哲学诠释,就必须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即该诠释绝不会是一般所认为的那种样貌,因为那里充满着解构与重构的思维活动。如前所述,柄谷想透过马克思来重读康德,并透过康德来重解马克思。当然在其中还包含对黑格尔的批判。此节将探究柄谷如何利用自己的世界史想象,来重新诠释康德、黑格尔及马克思的哲学。在此必须说明的是,柄谷透过往来于自身哲学理论与西洋古典哲学之间的运动,来达到对彼此的解构与再创造,因此我们应该把这种运动视为一种过程。
首先让我们来追寻柄谷透过上述的世界史结构如何重读康德哲学。当柄谷试图透过“想象力”来描绘世界共和国时,不仅是后者有迹可寻,就连前者亦是康德哲学脉络下的概念。柄谷指出“想象力”在哲学史上地位很低,处于知性以下的知觉再现能力及肆意的空想能力。康德虽然在《纯粹理性批判》或《判断力批判》都没有很积极阐明“想象力”,然而柄谷却特别强调康德将“想象力”的地位提高,视它为感性与知性的媒介与综合体,并说明它具有先于知性的创造能力。柄谷会如此解读康德的“想象力”,只不过是要拉拢康德哲学来为自己对世界史建构的“想象力”加持而已。*同上,第323、328—330页。
柄谷还认为自身所想象的世界共和国图像,非常接近康德《道德形上学的基础》中谈到的“目的的王国”,因为康德认为“不仅要将他人作为手段,同时还须作为目的”这个准则即是普遍的道德法则。柄谷表示康德的普遍道德法则,正意味着自由的相互性(互惠性),也就是交换模式D。因为在这里,无论是自己还是他者,都是具有尊严而不会被替代的单独个体。此外,康德在《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肯定宗教能开示出道德法则,但却主张道德法则存在于人的理性当中。柄谷指出康德的道德法则并非是内在的,而是外在的东西,而且是外在的交换模式D,并分析康德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商人资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刚开始的时代,其关怀的是劳方若被资方当成一种制造或赚钱手段的话,人必会失去尊严及自由。因此康德的道德法则必然会和社会有所关连,也就是说,道德法则包含了扬弃雇用劳动与资本制的生产关系等。*同上,第345—347页。我们在此显然可以发现,柄谷透过马克思观点来重读康德的踪迹,但更应该说,这是柄谷对康德的主观解读。
至于黑格尔,柄谷评价他在《法哲学纲要》中将“国族(nation)=国家(state)=资本”三者视为一个复合的社会构成体,有其创见,并指出马克思将资本视为下层结构,将国族与国家视为上层结构,反而无法正视三者皆是由交换模式B、C所形成的社会构成体之事实。柄谷批判黑格尔的其中一个重点他只重视事物的结果。也就是说,看事物的任何发展,都是一种事后论或结果论,并不是采事前或未来态势。这关系到需不需要有理念的问题。柄谷认为康德提出目的王国或世界共和国,都意味着在未来必有一个人人可以追求的理念。因为理念正是理性所需要的一种“超越论的假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康德一样,亦是采取未来态势。
根据柄谷说法,马克思本身虽然拒绝谈论未来,但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道:“共产主义对我们而言,既不应该是一个被实现的某种状态,也不是一个现实朝往那里而被形成的某种理想。我们把扬弃现状的现实运动称为共产主义。而此运动便是从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显示了马克思拒绝在前方设置历史的目的(终结),他不仅否定黑格尔,也排拒康德。*同上,序文。总之,柄谷认为没有必要否认马克思的事前立场(未来态势)。
如前述,柄谷指出黑格尔虽在《法哲学纲要》中提出“国族=国家=资本”三者的不可分性,但却没有想要扬弃、超越此复合的社会构成体,因为黑格尔只不过是结构性地、概念式地来掌握这三者而已,并没有想到这三者的结合是由想象力所形成。*同上,第336页。黑格尔对“国族=国家=资本”三者的掌握,竟然在当代美国(unilateralism)与欧洲(multilateralism)之间的世界竞争当中,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柄谷认为,这象征着美国与欧洲(黑格尔与康德之意识形态)的对立,前者不放弃帝国与资本主义式的想法,后者为与之抗衡,采取代表世界共和国的“诸国家联邦”之态势。*同上,第451—458页。简言之,要不要扬弃“国族=国家=资本”这种复合的社会构成体,也成了康德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认知这种模拟方式,全然来自柄谷建构世界史的当代性需求*柄谷于2013年2月4日出席台湾心灵工坊出版社为《世界史的结构》这本翻译书所举办的发表会。他在演讲的一开始便提到触发他想要超越“国族(nation)=国家(state)=资本”这种复合的社会构成体的是,当代日裔美籍的政治思想家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的“历史终结”论。因为柄谷认为人类不会只停留在“国族-国家-资本”这个历史漩涡里,必定会朝往世界共和国迈进。。
至于柄谷如何重解马克思?柄谷企图透过康德的普遍道德法则、目的王国或世界共和国(其实这些也带有浓厚的柄谷色彩)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分别创造出自己的漂泊者、氏族社会与世界共和国图像,并借以提出广义的交换模式(A、B、C、D)取代马克思的生产或商品交换模式。其目的在于,为世界史建构提供一个更基础的、也更具有想象力与伦理性的行动理论。柄谷深切感到,现代的社会问题并无法按照马克思的想法解决。也就是说,只要破坏劳资对立的生产模式就能解决国族或国家的权力问题,已经不合时宜。因为国家与资本既处于彼此不离的关系,又是分别的二物。柄谷认为同时扬弃两者,才是人类世界史所应该前往的方向。总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必须以柄谷提供的方向进行,才有当代的生命力可言。
关于上述的马克思思想再诠释,最明显的是出现在“世界同时革命”的观点上。马克思认为,要打破现行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关系,必须一时掌握国家权力,当前者消失时后者自然也会跟着消失。此立场与蒲鲁东派同调。但当蒲鲁东派要参与巴黎公社时,马克思却反对。理由是与其夺取国家权力,更应该专心在巴黎与法国的重建,因为巴黎公社很快会被普鲁士军歼灭。事实也是如此。柄谷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指出马克思反对的理由是:一国之内的革命起不了作用,必须透过各国的同时革命,也就是说“世界同时革命”才可能。而后人记得的,只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赞美,并没有注意到其反对的理由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是“世界同时革命”。*[日]柄谷行人:《世界史的结构》,第378—382页。柄谷的马克思再诠释,透露出现代人若要推翻控制人类的国家与资本,非得透过“世界同时革命”不可的讯息。这在柄谷解读“世界同时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很明显可以看到。*同上,第441—446页。而这“世界同时革命”的观点,被柄谷连接到康德在《何谓启蒙》中所提到的市民革命。因为他认为康德应该是要主张市民革命追求的是政治的自由与经济的平等,而要实现此理想,就不能只停留在一国之内。而此正呼应能实现世界共和国的“诸国家联邦”之构想。*同上,第446—451页。显然,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革命,已被柄谷从康德观点,置换成“诸国家联邦”的构想。
(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关于柄谷的世界史建构,笔者最后要探讨的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当柄谷检讨漂泊者、氏族或部落与交换模式A(互惠、赠与与还礼)之间的关连时,弗洛伊德的“杀父”概念,在他对氏族社会与国家社会的区分上,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在压抑者与被压抑者之间所产生的对失去东西的恢复之本能、欲望,正是推动人类无论在任何处境或行动模式下,都会对当下体制具有反抗能力,并追寻一个类似但并非失去物本身的东西,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迂回到过去的未来理念。吊诡的是,此并非是对自我同一性的恢复,相反的,是对恢复自我同一性的抗拒。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对自身的自我同一性,应该是采取不断想象、追寻与建构的态度,因为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理念会存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而回归到原始社会绝非是柄谷的本意。
上述的立场我们也可从柄谷对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之解读得到一些讯息。柄谷注意到弗洛伊德对摩西的想象根源自“被压抑之物的回归”。弗洛伊德认为摩西是埃及王族的成员,企图要恢复阿肯那顿(Akhenaten)创始之后被废除的一神教。摩西向俘虏、囚犯的犹太人说,若他们相信一神教,就帮助他们脱离埃及。这是所谓的神人契约,但这并非双方面的契约(因为双方面契约代表权力国家的意思),而是神单方面对犹太人的契约。弗洛伊德还假设犹太人脱离埃及进入绿洲迦南之地前,就将摩西杀害了。因为摩西命令他们要停留在沙漠(这不仅代表游牧民时代的生活方式,即独立与平等,也是否定国家社会的象征)。但被杀害后的摩西,最后以摩西之神的姿态回到专制国家迦南。柄谷认为这正是杀父的反复。因为摩西及其神被杀害后作为“被压抑之物的回归”,又以强迫的姿态出现。*同上,第207—211页。
透过柄谷的弗洛伊德解读,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杀父概念及“被压抑之物的回归”,正是引领人类透过迂回到漂泊者或氏族社会(过去),进而朝往世界共和国(未来)的动力。若交换模式D是交换模式A的高层次之发展的话,就不可能是交换模式A本身。因此停留在沙漠或摩西之神的回归,都是象征性的说法。这意味着人对自身的自我同一性,应该采取不断想象、追寻与建构之姿态的意思。
四、结论
历史不仅是过去不变的事实,它会因人类在面对当下的闭塞状况所产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过去不再只是过去,它会透过现在而在未来中被改变。相反的,未来的形成亦是透过现在改变过去才可能。因此我们可以说,过去发生的事亦是未来发生的事,反之亦然。京都学派哲学家的世界史图像,因日本当时所面临的状况,将近世欧洲的世界史图像转变成是世界(包含日本)的世界史图像。就如他们一再强调的,一个世界必然是由无数的人事物所形构而成,相反的,无数的人事物也必然是由一个世界所形成。这是承继西田几多郎在《日本文化的问题》中的说法。“一到哪都是多的一,多到哪都是一的多。多和一的矛盾且自我同一,则是所谓的现实世界。”*[日]西田几多郎:《西田几多郎全集》第12巻,东京:岩波书店,1979年,第292页。“一即多、多即一”的世界观,其实背后潜伏的是绝对无。当然在绝对无的背书下,柄谷欲超越的“民族-国家-资本”(法兰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还能以否定媒介的方式运转下去。
反观柄谷行人的世界史图像,在某个程度上,和京都学派有相通之处。两者其实都不是在研究或撰写世界的历史,而是用一种哲学想象,将世界史该如何建构视为问题来思考。当然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对人与世界(包含自然)的关怀。他们的做法都是先从想象未来开始,在未来设置一个形上的理念(京都学派是绝对无,柄谷是世界共和国),继而回到过去并改变它(过去)。如此一来,人类的历史该如何发展或会如何发展,就非常清楚了。
京都学派与柄谷的世界史理念显然是透过现在的行动来连接过去与未来。对柄谷而言,现在的行动即是“世界同时革命”。关于这点,不可否认的,是京都学派哲学家所缺乏的。不仅如此,就如柄谷所指出的,无论是现代世界史的建构或人类该朝往何处去的问题,都不能漠视“国族-国家-资本”的关系。柄谷在这点上与京都学派完全不同,他不认为人类在“国族-国家-资本”内能够幸福美满,唯有超越这个循环才能摆脱这个循环的宰制。这意味着人类必须彻底脱离京都学派所提倡的让任何东西都能得以存续的“绝对无的场所”。
当然我们透过比较日本世界史图像的昔与今,除了了解当代问题(柄谷的问题意识)对我们的重要性之外,也不应该忽视昔对今的参考价值。我们必须试问的是,“世界同时革命”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实践的成立根据是什么?田边元于战后,以“存在即罪恶”的姿态,提出绝对他力的忏悔行(自我否定行)。这意味着人类所有行动的成立根据,不再是理性主体,而是一种与他力慈悲的救济行一同进行的“为救他人而牺牲自我”的爱。当然柄谷在谈到普遍宗教中的不求任何回报的赠与力量(交换模式意义下的),亦提出类似的观点。但笔者并无法辨识出那是出自于宗教的慈悲力,还是哲学(或文学)的想象力。*关于想像力在柄谷思想当中的重要性,并非笔者的肆意想像,柄谷在2014年11月14日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举办的座谈会中,以“移动与批判:跨越性批判”为题进行演讲时,便特別强调想像力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参见《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讯》第9卷第4期,2014年,第41—48页。)若是后者的话,相信这会是有待日后研究的新课题。
(责任编辑林中)
*本文系“西学东渐与广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中山大学“三大建设”专项资助。
**作者简介:廖钦彬,(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B3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6)03-0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