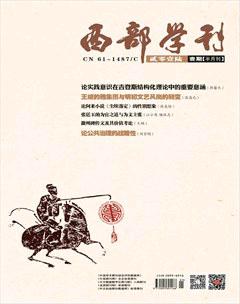论实践意识在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的重要意涵
2016-02-01郭馨天
摘要: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旨在化解社会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个体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实践意识,即“记忆痕迹”。社会结构并不外在于行动者,而是以实践意识的形式内涵于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之中,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实践。实践意识与社会实践关联密切,从分析实践意识入手,可以更好地领会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精要所在。
关键词:实践意识;结构化;社会实践;时空伸延
中图分类号:C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力图消解社会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个体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间的二元对立而作出的一种综合性尝试。吉登斯认为,社会行动和社会结构并不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既定现象系列,即某种二元论,而是体现着一种二重性。结构二重性是理解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关键,“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和使动性。”[1]89由此可见,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社会结构作为实体是不存在的,它是以“记忆痕迹”的形式内在于社会行动之中的,对社会行动不单单具有制约性还具有使动性。这里所说的“记忆痕迹”也即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实践意识,吉登斯十分巧妙地将以往宏观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结构以实践意识的形式融入到以往微观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行动之内,并由此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实践,以此来区别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行动。“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1]61吉登斯所说的时空向度上的有序安排体现着社会实践的层次性,不同层次的社会实践都与实践意识紧密相联,因而从分析实践意识入手,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领会到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精要所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首先是从社会实践的微观层次实践活动入手,中间经由社会实践时空伸延机制,最后上升到社会实践的宏观层次社会制度。下面,笔者也是从实践意识与实践活动、实践意识与社会实践的时空伸延机制以及实践意识与社会制度这三个方面来考察实践意识在整个结构化理论中的重要意涵。
一、实践意识与实践活动
吉登斯认为行动者的主观方面是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的,即话语意识(discursive consciousness)、实践意识(practical consciousness)和无意识(unconsciousness)。话语意识体现着行动者的理性化,即对所行之事以话语形式作出理论性解释,这也是他作为一名行动者资格能力的主要标志,它体现出行动者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无意识是和动机激发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动机是激发这一行动的某种需要,在很多时候人们对自己的动机是很难说清楚的,往往是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产生的。动机激发过程并不与行动的连续性联系在一起,只有当行动偏离惯例的情况下,动机才会作用于行动,而对日常行为来说,则是很少有动机参与其中的。[1]66在日常行为中,实践意识起着决定作用。“所谓实践意识,指的是行动者在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需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意识。对于这些意识,行动者并不能给出直接的话语表达。”[1]64实践意识是“非意识的”(non-conscious),而不是“无意识的”(unconscious)。[2]39实践意识根植于在社会生活日常接触中存在着大量的“知识库存”(stocks of knowledge)或者我们说存在着共同知识(mutual knowledge)。[1]64这样的知识大多是实践性的,行动者往往很难以话语的形式明确地表达出来,这即是实践意识,它类似于我们平时所言的风俗、习惯等文化背景或文化传统。[3]350话语意识和实践意识都是行动者认知能力的体现,代表着行动者的意图性,二者没有什么固定的区分,而是相互渗透。它们之间无本质的区别,只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即什么是可以被言说的,什么是只管去做而无须言说的。而在话语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则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无意识包括某些类型的认知和冲动,它们要么完全被抑制在意识之外,要么只是以被歪曲的形式显现在意识中。”[1]64可见,无意识和话语意识以及和实践意识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都体现着行动者对自身行动的反思性监控(reflexitive monitoring of action),也即行动者始终监控着自身的行动,并希望他人也如此监控着自身。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对自身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主要是靠实践意识,即无需明言就知道如何去做的那些意识。行动者对自身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使得实践活动呈现出一种绵延有序的行动流,这就体现出实践活动的连续性。而以往的解释学唯意志论虽然将社会行动看作是行动者有目的、有意图而为的,但他们将这些行动看作是由一系列单个分离的意图、理由、动机所组成,而忽略了其与具体时空情境的关联,也即忽略了行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实践意识与实践活动的连续性是紧密关联的,而实践活动的连续性就为社会实践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伸延提供了可能性。
二、实践意识与社会实践的时空伸延机制
吉登斯将时空视为社会实践的内在组成部分,认为每一具体的实践都发生在一定的时空情境中,没有脱离时空情境而存在的抽象的社会实践。同时,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机制使得社会实践从微观的行动层面上升到宏观的制度层面。时空伸延机制包括时间上的例行化和空间上的区域化,前者使得实践活动超出了互动情境的时间限制,后者使得实践活动超出了互动情境的空间限制。无论是时间上的例行化还是空间上的区域化,可以看出实践意识都与之密切相关。下面,从实践意识与时间上的例行化和实践意识与空间上的区域化这两个维度来探讨实践意识与时空伸延机制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实践意识与时间上的例行化
“结构化理论关注的是人的社会关系中超越具体时空的‘秩序,而要阐明这种超越过程,例行化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因素。”[1]165时间上的例行化(routinization)体现出时间是双向的、可逆的,而非单向的、不可逆的。例行化的常规使得日常生活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进而对于维持行动者的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来说十分重要。日常生活的例行化特征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行动者在实践意识的支配下,对共同在场情境下的行动进行反思性监控来引发的。可见,实践意识与时间上的例行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在吉登斯看来,社会互动即是断断续续但却是例行发生的日常接触。[1]164日常接触是时间上例行化的最一般的表现形式,其重复性正是例行化的体现。日常接触在很多时候并不是直接受动机激发的,而是由实践意识来维持。日常接触是在社会定位的基础上发生的,行动者在由社会实践所构成的社会系统中有自己的定位,这表明行动者不是独立的,而是处于关系之中。社会定位从静态上讲,表明一个人在社会关系网中的身份类型;吉登斯更强调从动态角度来考察社会定位,他将社会定位理解为“某种社会身份,它同时蕴含一系列特定的(无论其范围多么宽泛)特权与责任,被赋予该身份的行动者(或该位置的‘在任者)会充分利用或执行这些东西:它们构成了与此位置相连的角色规定(role-prescription)。”[1]162行动者在共同在场情况下的定位过程包括身体在日常例行常规各区域间的移动,还有身体运动和手势。日常接触之所以在时空领域内体现出常规性或例行性,或者说日常接触之所以体现出重复性,主要是因为行动者在日常接触中遵循着由社会定位所带来的某种规则,规则使得日常接触框架化(framing),使他们归于某一特定种类,受到一定约束。“社会定位的有关规则一般是具体规定了具有某一特定社会身份或从属于某一特定社会范畴的人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1]168这些规则往往是不成文的、深层次的,行动者对它的把握也主要是靠实践意识,具体表现为行动者对自身行动及所处的时空情境进行反思性监控,然后采取与情境相对应的适当的行为举止,以此来维护行动者的本体性安全。
(二)实践意识与空间上的区域化
社会实践同时是发生在一定的区域之中的,不同的区域之间相互交织体现为空间上的区域化。空间上的区域化也是与行动者在实践意识的支配下对自身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联系在一起的。
赫格斯特兰德的时间地理学对制约人类活动的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出以下五种:(1)肉体存在对人类行动者的限制(2)时间的有限性(3)能力的限制(4)时空限制(5)时空容纳能力的有限性。这几种制约决定了一个人在一天之中所支配的时空量是一个棱状区域,这一棱状区域限制了他的活动,其规模大小受到行动者在沟通和转换方面所能实现的时空交汇程度的影响。[1]197这些制约因素勾勒出区域的边界,场所就是由这种制约因素所构成的区域。“场所是指利用空间来为互动提供各种场景,反过来,互动的场景又是限定互动的情境性的重要因素。”[1]205场所可以看作是发生互动的空间环境,“场所可以是屋子里的一个房间、一个街角、工厂的一个车间、集镇和城市,乃至由各个民族-国家所占据的具有严格疆域边界的区域。但场所的典型特征是它们一般在内部实行区域化,而对于互动情境的构成来说,在场所之内的这些区域又是至关重要的方面。”[1]206吉登斯认为有四种对场所进行区域化的方式。其一是空间的物理形式,也即区分不同区域的物理标志或符号标志,如隔开房间的墙壁使得一些住宅被分成不同的区域;其二是持续的时间,也即以时间段作为划分不同区域的标志如昼夜,这一时间上的划分被用来作为最基本的区域分界标志;其三是时空的跨越幅度,即那些在时间跨度或空间范围上千差万别的分区。其四是区域化的特性,也即场所的时空组织以何种方式被安排在更加广泛的社会系统中。[1]209在吉登斯看来,其中的第四种划分标准即区域化的特性是最为重要的。区域化的特性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场所的特定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在场可得性的程度。“在场可得性”(presence availability)即维持一种共同在场的情境,它体现着行动者对自身及周围环境的反思性监控。行动者根据自身的情况将周围的环境归结为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两类,前后台区域的相对分离对于维护行动者自身的本体性安全有着重要意义。“区域化提供了一个时空闭合的区域,产生某种封闭性,以保证‘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之间可以维持一种相互分离的关系。行动者就是利用了这种分离关系,组织行动的情境性,维持他的本体性安全。”[1]213在前台区域,行动者的表现往往是带有表演性质的,是在扮演某种角色;在后台区域,行动者的表现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在这里行动者身心得以放松,并拥有各种形式的自主性。行动者在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的表现存在着差异,其目的是为了维持其本体性安全,实现的途径是行动者在实践意识的支配下对自身行动的反思性监控。前台区域和后台区域的划分是行动者在实践意识的支配下所采取的策略性行为,并无固定的划分标准,这些不同的区域之间相互交织,体现出空间上的区域化,进而使得实践活动在空间上延展开去。
三、实践意识与社会制度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首先是从微观层面上实践活动入手,中间经由时空伸延机制,最终上升到宏观层面上的社会制度分析,旨在回答现代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经典问题。吉登斯认为,制度(institutions)是时空伸延程度最大化的实践活动,也即在那些在时空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实践活动。[1]80这类实践活动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因而制度也就成为达成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在社会的不同领域内有着相对应的制度秩序,这些不同领域内的制度秩序“聚合”起来,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层面上的秩序。吉登斯对社会制度的分析,也是从内涵于社会实践的结构入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实践意识与社会制度二者之间紧密关联。
结构简单地说是由规则和资源构成的,它们内涵于实践活动之中,并通过社会实践而得以再现。但在结构的两个构成要素中,规则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规则是一种有别于具体规定的程序。“我们不妨将社会生活中的规则看作是在社会实践的实施及再生产活动中运用的技术或可加以一般化的程序。所以说,那些以法律条令、科层规章、游戏规则等言辞表述形式出现的形式化规则并不是规则本身,而只是对规则的法则化解释。”[1]85规则和对规则的法则化解释被吉登斯区分为具有深层特性的规则和具有浅层特性的规则。“所谓具有深层特性的规则,我指的是那些日常活动过程中不断被运用的公式,是那些介入日常生活大部分构架的结构化过程的公式。”[1]86这种具有深层特性的规则是和实践意识联系在一起的,行动者对此的把握是以默契的方式进行的;而行动者对那些具有浅层特性规则的把握,也即对法则化规则的把握,则靠的是话语意识。“行动者只是以默契的方式来把握社会实践的生产与再生产中包含的绝大多数规则,他们知道怎样去‘进行。在话语层次上对一项规则进行形式化概括,这就已经是对该规则的解释了。”[1]86具有深层特性的规则才是吉登斯这里所特指的规则,外在表现为行动者的实践意识。“对社会规则的自觉意识(它首先体现为实践意识)恰恰是‘认知能力的核心”,[1]85这就体现出行动者在从事实践活动时的意图性。
吉登斯认为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内在于各种实践活动之中。[1]89这里的“记忆痕迹”其实也即是实践意识,简言之,结构以实践意识的形式体现在各种实践活动之中。吉登斯将规则分为表意性规则、支配性规则和合法化规则三类,分别代表着结构的三个维度,这三种不同的结构维度并不是彼此独立,而是相互关联形成一个结构丛。表意性规则具体表现为解释图示,所对应的实践活动为沟通,形成的理论为符码理论,最终形成的制度秩序为符号秩序。合法化规则具体表现为规范,所对应的实践活动为约束,形成的理论为规范调控理论,最终形成的制度秩序为法律制度。支配性规则具体表现为行动者可凭借的手段,所对应的实践活动为实施权力。资源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资源可以分为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两类。权威性资源是指对人或行动者产生控制的各种转换能力;配置性资源是指对物体、商品或物质现象产生控制的能力,即各种形式的转换能力。[1]98根据实施权力时所凭借的两类不同的资源,支配性规则所形成的理论分别是资源权威化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最终形成的制度秩序分别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上论述可用下图①加以展示:
结构(规则): 表意 支配 合法化
模态: 解释图示 便利手段 规范
实践活动: 沟通 实施权力 约束
理论领域: 符码理论 资源权威化理论/资源配置理论 规范调控理论
制度秩序: 符号秩序(话语型态) 政治制度/经济制度 法律制度
上面的四种制度秩序所对应的是社会生活中不同领域内的秩序,局部领域内的秩序又是如何达成社会整体层面上的秩序呢?吉登斯认为,社会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是因为存在着“制度聚合”(clustering of institutions)。这些制度聚合将局部领域内的秩序加以协调上升为整体层面上的秩序。制度聚合主要是由结构性原则加以实现的,吉登斯将结构性原则理解为某种组织过程的原则,“该过程以社会方面一定的整合机制为基础,产生相当持久的时空伸延形式。”[1]285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由于结构性原则组织方式的不同,因而整体层面上社会秩序的达成路径也不尽相同。在部落社会即从事狩猎与采集活动的人类群体或社区,各个制度领域尚未分化,整体层面上的社会秩序主要是由共同在场情况下的互动加以完成,传统的道德、风俗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即在这一时期符号秩序起着主要作用。在阶级分化社会即封建社会、古代帝国和城邦国家,城乡开始分离,四大制度领域开始出现分化。在乡村符号秩序依然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途径;在城市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是由国家所代表的政治制度来实现,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从属于政治制度。在阶级社会也即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广大的农村也被纳入到国家的科层制管理模式之下,政治制度在整体层面上的社会秩序的维持上发挥着中轴作用,具体表现为国家监控能力的不断提升,最终导致民族-国家的产生。吉登斯认为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即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是一个权力集装器,它的领土边界与行政范围相适应。[4]213在以上社会秩序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政治制度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吉登斯所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出现是与国家监控能力的提升相伴随而来的。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必须看到,吉登斯对结构(规则)、实践活动、所对应的理论领域乃至制度秩序的划分都只是为了分析方便的起见而作出的理想类型,而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横向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并非截然地分开。[1]98但从微观的结构(规则)到宏观的制度秩序的纵向分析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实践意识作为“虚化”的结构内涵于实践活动之中,并且是贯穿整个结构化理论的一条主线。
四、简要评价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将以往客观层面上的社会结构“虚化”为主观层面上的实践意识,这样从一开始社会结构就以实践意识的形式存在于行动者的头脑之内并内涵于实践活动之中,从而为化解社会学理论中关注社会行动的微观研究与关注社会结构的宏观研究之间的二元对立铺平了道路。我们从中看到了实践意识在整个结构化理论中的重要意涵,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首先,尽管吉登斯将以往宏观社会学所关注的结构以实践意识的形式内化于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之中,但他并不否认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着微观取向和宏观取向的二元。我们看到吉登斯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在这其中就已经包含了微观取向和宏观取向的分野。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实践活动是社会实践微观取向的一元,社会制度是社会实践宏观取向的一元。要强调的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微观取向和宏观取向的二元划分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二者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ity),都统一于社会实践,时空伸延的程度是决定微观取向和宏观取向的关键性变量。吉登斯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统一界定为社会实践,认为“社会学关注的不是一个‘预先给定的(pre-given)客体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造或创造的世界”,[5]277并从实践出发建构其整个理论大厦,这也反映出当今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实践论转向。
其次,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不仅仅指出结构对行动者的制约作用,更为强调结构对行动者的使动作用。吉登斯认为,实践意识作为社会结构的虚拟化形式存在于行动者的头脑中,表现为行动者在从事实践活动时所遵循的共同知识,正是对这些共同知识的认可与遵循使得不同时空跨度内的社会实践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类同性”(the same)。[1]62但吉登斯并没有像帕森斯那样,过于强调价值规范对行动者的制约作用,将行动者看作是“文化的傀儡”。[6]53吉登斯在看到结构对行动者的制约性使得实践活动带有“类同性”的同时,更为强调结构对行动者的使动性的一面,也即是对权力的强调。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吉登斯在结构的三个维度中最为看重的是支配性规则,在行动层面上更为重视权力的实施,在宏观的制度分析上更为看重政治制度在社会变迁和社会秩序达成上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吉登斯日后的学术兴趣从社会学到政治学的转移中得到清晰的印证。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看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始终没有摆脱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吉登斯所说的四种制度秩序(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号秩序)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AGIL是完全相吻合的,所不同的是在社会秩序达成的路径上,帕森斯强调的是价值规范而吉登斯强调的是政治制度。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也是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批判式地继承与发展。
最后,吉登斯通过对实践意识在行动者实践活动中的重要性的强调,再次标明了自己是现代主义阵营里的坚守者。吉登斯和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学理论家布迪厄都将社会实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二者的立场和研究思路有着本质的区别。布迪厄是一位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认为行动者的实践活动所遵循的不是逻辑,而是一种感觉,也即布迪厄所言的实践感。这种实践感带有很强的模糊性色彩,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也就处在动态的、不确定状态之中,因而现代主义者所宣扬的各种理论理性是无法对之作出合理的解释。[7]164吉登斯承认有意图的实践活动往往会带来意外的后果,但这些意外后果并不能否认行动者的实践活动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只能说明行动者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也即行动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吉登斯认为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在很多时候是在实践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之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二者都体现着行动者的理性。并且实践意识所体现的共同知识又会使得人们的实践活动趋同,这就表明了吉登斯对普遍主义价值规范的认可,[8]249从而也体现出他作为一名现代主义社会学思想家的理论品质。
注释:
①此图是笔者综合了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一书中94页和96页两个图表之后而
成的,对其中的有些地方稍作修改,为了是更为清晰地展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
的全貌。
参考文献:
[1](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2](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3]刘少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英)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5](英)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M].田佑中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6]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法)布迪厄等.实践与反思[M].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8](英)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M].陶传进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作者简介:郭馨天(1979-),男,社会学博士,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从事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发展与现代化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