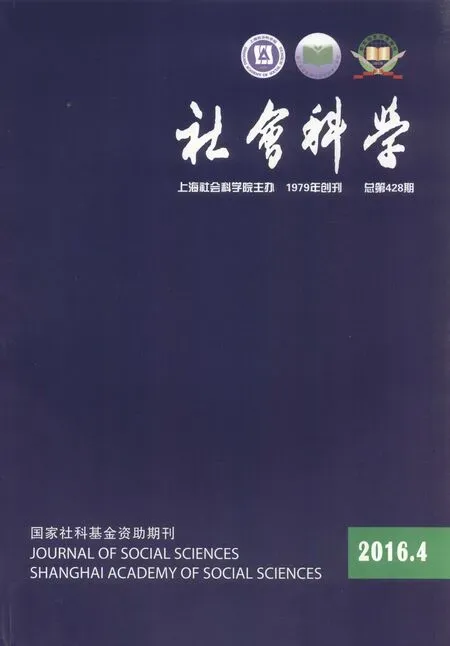实用主义硬核及其中国回映*
2016-01-31陈亚军
陈亚军
·实用主义研究专题·
实用主义硬核及其中国回映*
陈亚军
国人对实用主义的诠释曾有过三个比较醒目的版本,它们分别是:科学方法论、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观、实证主义意义理论,然而实用主义的本体论即它的彻底经验主义学说才是它真正的“硬核”。彻底经验主义是一种与西方传统哲学大相径庭的哲学世界观,它从生存论的角度将人与世界的交缠互动置于哲学的首要位置,否定二元式的哲学思维,否定大写的形而上学,倡导实践优先。所有这些都为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实用主义可以在中国哲学那里觅见自己的回映。
实用主义;儒家;本体论;实践;伦理学
一、关于实用主义的三种诠释
对于国人来说,在整个西学中,除“马克思主义”之外,“实用主义”大概是最耳熟能详的了。迄今为止,实用主义传入中国近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间,国人对实用主义的接受或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历史环境相异,对实用主义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初杜威访华前后。1919年,杜威应邀到中国讲学,原打算只逗留几个月的时间,后来竟一拖再拖,待了二年零二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杜威走访了大半个中国,发表了一系列演讲。这些演讲集合成书,在杜威离开中国之前,就已经一版再版达十次之多,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杜威受欢迎的程度。他甚至被有些人称作“孔子第二”。用胡适的话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载《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借杜威访华之东风,实用主义大规模传入中国,介绍实用主义的文章出现在很多报刊杂志上。不过这些介绍还处于初始阶段,凌乱而肤浅,对pragmatism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译名。*胡适和蒋梦麟当时都用“实验主义”(胡适:《实验主义》,《新青年》第6卷第4、5期,1919年4月15日;蒋梦麟:《实验主义理想主义与物质主义》,《星期评论》1919年10月10日),最早用“实用主义”这个概念的,就笔者所见,是徐彦之(《实用主义方法论》,《晨报副刊》1919年3月22—25日)、周兆沅(《实用主义之要旨》,《晨报副刊》1919年5月19—21日)和朱谦之(《实用主义评论》,《新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7月15日)。这一译法加重了理解的混乱。当时对实用主义的介绍比较多的,是杜威的教育思想,而在哲学方面,关注的主要是他的方法论,实用主义基本上被当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
当时中国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作为杜威的学生,胡适对实用主义情有独钟。但他认为,实用主义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方法。胡适看重的是实用主义方法以及如何将这种方法运用在他的国学研究上。他曾总结道:“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作。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胡适:《胡适文集》(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胡适回国时,杜威最重要的有关本体论的哲学著作尚未问世。后来以胡适的背景和兴趣,也不可能对杜威此后问世的著作下很大的功夫。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胡适解读实用主义的方式,当时就有人表示了不满,认为将实用主义简化为方法论是过于偏颇了。*参见张东荪《唯用论在现代哲学上的真正地位》,《东方杂志》1923年第20卷第15/16期。
实用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登场,持续的时间并不长,随着杜威的离去,实用主义很快便偃旗息鼓了。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和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离得太远。当时的中国,比较盛行的西方思想除实用主义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在近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急于找到一条道路,能够帮助中国人从贫穷落后、积弱分裂中摆脱出来。和马克思主义相比,实用主义这副药太弱,它讲究点滴进步,重视改良而不是革命,它怀疑变革社会的一揽子计划,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过于缓慢了。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形势下,实用主义被马克思主义逐出历史舞台,是一种不难理解的结局。
国人关注实用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主要是1954年到1955年间。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对美国的敌视,被当作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受到清算,而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更是批判的焦点。学术界掀起了批判实用主义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实用主义被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商人市侩哲学,它的方方面面都受到鞭挞,尤其以它的真理学说为甚。实用主义被归结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论。“有用就是真理”,成了对实用主义形象的漫画式的描绘。如果说,近四十年前,中国学术界对于实用主义的理解虽然零散、肤浅、急功近利,但却还保持了几分学术严肃性的话,那么这场关于实用主义的批判则基本上是一种和学术无关的政治运动,其中可以留下来的具有学术价值的东西,十分鲜见。唯一可以称道的是,后来为了供批判所用,陆续翻译了一批实用主义代表作。*古典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的主要代表作,如詹姆斯的《彻底的经验主义》(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杜威的《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等,都在稍后被译成中文。这场实用主义批判的直接后果,就是彻底丑化了实用主义。在多数人眼里,即便实用主义不是一种美国商人哲学,至少也是一种平庸浅薄的无聊哲学。
第三个阶段由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直到今天。在此阶段,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学界重新开始从学术的角度看待、研究西方哲学。恢复实用主义名誉,认真研究实用主义内涵和它的当代发展,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皮尔士研究中心”、“杜威中心”相继成立,《杜威全集》38卷中文本相继问世。当代实用主义代表人物,如罗蒂、普特南、布兰顿、伯恩施坦等,陆续应邀访华,其中罗蒂甚至不止一次来华参加关于他的哲学研讨会。和前两个阶段相比,这个阶段真正开始了对于实用主义的学术探讨。
这一阶段的实用主义研究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重新评价实用主义学说,洗刷实用主义蒙受的耻辱。*复旦大学刘放桐教授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最早提出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口号。1987年刘放桐所发表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现代外国哲学》第十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文,开启了新时期实用主义研究的序幕。二是从不同角度,发掘实用主义内涵,重新定位实用主义。三是引进新实用主义,关注实用主义的当代演变。四是实用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开始进入学术界的视野。*然而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美国哲学家在中国推动的,如安乐哲(R. Ames)和郝大维(D. Hall),他们不仅发表了一些有关实用主义与儒学的比较著作,还在香港等地组织了实用主义与儒学对话的工作论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关于实用主义的解读有一些新的声音出现,如将实用主义当作实证主义的一种,*华东师范大学的杨国荣教授在他的书中提出了这种观点(参见杨国荣《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第三章)。或者认为,实用主义就是一种意义学说,*武汉大学朱志方教授在他的《什么是实用主义?》(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会(2004)会议论文)一文中详细阐释了这一点。实用主义被看作科学主义思潮的分支。随着中国学术界对分析哲学关注的增加,这种实用主义解说,在中国学术界影响颇大。*笔者自己原先也持这样一种看法。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撰写“实用主义”一章时,笔者把实用主义置于科学主义思潮之下,认为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有种亲缘关系。
从方法论、真理观和意义学说的角度诠释实用主义,当然并不错,但在笔者看来,却未能把握实用主义硬核,失去了实用主义最为关键也最有价值的东西。至少在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认为实用主义至多是一种浅薄的美国哲学,和上述实用主义诠释是分不开的。且不说以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观来解读实用主义是如何的荒谬,即便是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学说,也早就不是什么新东西了。就哲学的深刻性而言,如此诠释下的实用主义显然缺少了一种厚度,一种可以和欧洲哲学相媲美的理论魅力。
那么,实用主义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笔者的答案是,实用主义的本体论,即彻底的经验主义学说。没有这种本体论,它的真理观和意义学说是无根的,甚至实用主义本身在今天的存在和复活都是没有理由的。正是这种独特的本体论,使实用主义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也正是这种独特的本体论,使得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之间的比较有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当实用主义被理解为一种科学方法论或意义证实理论乃至一种主观主义真理论时,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二、彻底的经验主义:一种新的世界观
说实用主义本体论昭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意思是它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世界观。我们知道,传统西方哲学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现象与实在的区分。这个区分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真正对这种哲学传统构成挑战的,是实用主义。
在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家看来,我们的日常经验世界是不够真实的,只是一种现象。我们经验到的生死、往复、盛衰等,是变化和偶然的,而真实的世界是永恒的、不变的、完满的。这是一个躲在经验世界背后的大写实在,是只能经由理性才能把握的实在,而只有对实在的理性把握,才有资格被称作知识。柏拉图式的哲学家把日常经验世界看作实在影子,但这个影子毕竟是对实在的一种晦暗的模仿,理性毕竟还可以超越经验达到对实在的认识。到了中世纪的基督教那里,实在和经验世界被彻底分隔开来,大写的实在是上帝,经验世界完全不真实。生活在经验世界的人,完全没有办法通过知识的途径去认识上帝。信仰取代了理性。
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康德结束的启蒙时代,西方哲学将理性重新置于哲学的殿堂。伴随着对理性的恢复,人的主体性也受到极大的弘扬。理性是人的理性,是主体的特性。主体与客体乃至经验与自然被分隔成两个不同的领域。经验发生在主体,实在是与之相对的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经验成了一块幕帘,将我们的认识和世界隔开。笛卡尔的这种二元世界观必然会导致怀疑论,康德虽然以他独特的方式对怀疑论做出了解答,但物自体仍然是我们的知识可望不可及的领域。
总之,在传统西方哲学家的眼里,我们日常从不怀疑的这个经验世界,要么被当作实在的影子,要么被当作虚幻的世界,要么被当作感觉观念,和实在世界永远有一道鸿沟。实用主义对于这种传统的二元式的世界观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詹姆斯、杜威不仅从人道主义、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角度,对它进行了批判,*关于这一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詹姆斯的《实用主义》第一章,杜威的《哲学的改造》、《确定性的寻求》。而且为替代它,提出了一套崭新的世界观,即彻底的经验主义学说。*杜威称它为“自然主义经验论”。在笔者看来,杜威的“自然主义经验论”比詹姆斯的经验论更加彻底,所以我还是倾向于用“彻底的经验主义”来称呼他们的新哲学世界观。这一新学说固然受到英国经验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影响,*布兰顿把这种影响提前到康德(R. Brandom, Perspectives of Pragmat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9, p.14)。但就詹姆斯和杜威(或许皮尔士除外)的直接思想来源而言,康德并不在名单之列。但仍因其独特的、其他哲学流派无法取代的性质而超越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利用商业保险分担农业风险,发挥市场对灾后可持续经营的补偿作用;对于安全要求和生产水平高的农业经济作物,应让市场多多参与,加快经济作物的农业保险商业化进程;减少政府干预,分清公共资源与私人物品的界限,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3]。
和传统哲学不同,彻底的经验主义是一种“描述的形而上学”*这里借用了斯特劳森的用语,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建构的形而上学”,而他所阐释的是一种“描述的形而上学”。,它反对把反思的结果当作本体论的前提,反对把哲学家们关于应该如何的学说当作真实世界的实际如何。用詹姆斯的话说,彻底经验主义的基本前提是,不要把直接经验中的东西拿走,也不要把不是经验中的东西加进来。*詹姆斯:《詹姆斯文选》,万俊人、陈亚军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而杜威则要求我们,不应将旁观者的理论态度而应将直接经验即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作为哲学的出发点。*杜威:《杜威文选》,涂纪亮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145页。
当我们以旁观者的姿态,面对变化的经验世界时,我们总是试图对它提出一种解释,一种理论说明。这原本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在于,哲学家们常常把这种解释当作了事情的本然,把一种基于自己趣好、习惯、训练的理论思考的产物当作了世界的真正存在。于是出现了二元世界的划分,有了哲学家们的用武之地。实用主义者要求我们还世界的本来面目,回到实事本身,不是以旁观者而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开始我们的哲学思考。不是把自己放在世界之外的位置上,充当“上帝之目”,而是充分认识到,我们首先是在世界之中的,“总是和这个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的”*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我们和世界的关系首先不是一种理论认知关系,而是一种生存实践关系。在这种实践生存关系中直接向我们显现的东西就是本体之所是。
这种直接显示下的本体是一种纯粹经验,一种变动的、前后相续的有机整体。和传统哲学不同,在实用主义者看来,直接的、真实的存在,不是某种时间之外的大写实在、真理、上帝,而是时间中的经验之流。詹姆斯从他的心理学背景出发,对这种纯粹经验之流做了意识的分析;而杜威则更加彻底地把它等同于人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在詹姆斯和杜威看来,这是一种理论反思前的直接当下的存在,它是一种流变,但不是杂乱无章、没有方向的流变,它在时间中演变,具有过去、现在、将来。过去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积淀在现在之中、影响着现在,现在受到未来的牵引并同时决定了未来。我们总是倚靠着过去面向未来的。这是一种富有内容的演变,具有真正的时间性。过去的哲学家认为变化表明了一种不完满,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实用主义者不再害怕变化,原来当作更加真实的“形式”或“种”,恰恰是在变化中实现自身的,并且也一直处于进化之中。变化与不变相比,是更加真正的存在。*参见杜威《达尔文主义对于哲学的影响》,《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四卷),陈亚军、姬志闯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变化着的纯粹经验包含着一种意向性结构。詹姆斯指出,意识的特征正在于它的指向对象的意向性,意识在自己的活动中同时将对象建立起来,只有通过它的对象,才能把握意识的活动。*关于这一点,艾迪(J.M.Edie)在他的William James and Phenomenolog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一书中有很好的论述,参见该书第二章。杜威不再像詹姆斯那样,关注意识分析,经验在他那里不是一种纯粹意识而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既是人与环境的交互活动,同时也是赋予对象意义从而造就对象的活动,“对象是通过经验获得的。”*杜威:《杜威文选》,涂纪亮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人的经验活动有语言、观念融入其中,它们既是长期实践的积累又是当下活动的要素,杜威有时把它们称作活动的工具。和对于工具的普通理解不同,杜威意义上的工具,本身就是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工具的活动决定了对象的呈现。有什么样的使用工具的活动,就有什么样的对象显现。在这个意义上,杜威告诉我们,经验是敞开自然的方式,不是阻碍我们了解自然的屏障。“经验既处于自然之内,又是关于自然的。”*杜威:《杜威文选》,涂纪亮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8页。我们和世界不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意向关系。经验——我们和世界之间的交互作用或意向活动——使世界得以敞开,然后才有认识和世界的符合与否的问题。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不清楚,真理问题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和世界之间没有一道表象分界面。经验世界渗透了概念、判断,这些概念、判断并没有把我们和世界隔开,形成一种隔阂,从而导致所谓的怀疑论问题。概念、判断是世界本身具有的,经验总是概念化的经验,世界总是概念化的世界,总是渗透着概念、判断的整体。普特南在谈到詹姆斯的世界观时曾经说,实用主义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它的整体论思想,这种整体论思想与直接实在论的主张密不可分。*H. Putnam, Pragmat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3-22.他的这一判断是中肯的、可信的。
在这种新的世界观下,主观/客观、事实/价值、理性/情感等传统的二元对立,都化成了一种功能性的区别。以主观/客观为例,在詹姆斯那里,这种本体论层面的对立成了经验结构的区别,同一段纯粹经验,在一种经验结构中被当作主观,而在另一种经验结构中,则被当作了客观。比如,眼前这个桌子,当我们把原先用本体论术语对它的解释都暂时悬置起来之后,它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它就是在那里;如果它和劈成木头、燃烧为火焰的经验联系在一起,我们用一个范畴,把它置于“客观”之下,如果它和闭上眼睛看到、睁开眼睛又消失的经验连在一起,我们就用“主观”这个范畴来给它划类。它本身既不是主观也不是客观,全看它和什么样的其他经验相关联。杜威的视角和詹姆斯有所不同,主观在这里基本被消解了,心灵不是什么神秘的内在实体,而是一种外在的能力系统,是个体对共同体在长期的实践生活中所形成的意义系统的一种把握,这是一种能力,它决定了个体在面对当下环境时所能产生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个体对环境打交道所倚仗的工具,它在操作的结果中“变成了规定感觉对象的东西”*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8页。。换句话说,它在对象化的活动中实现了自己。
三、儒家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回映
如果说在西方哲学诸多流派中,还能找出与中国哲学旨趣相近的学派的话,那么它必定是实用主义无疑。海德格尔的思想与中国哲学的近似,被一些人津津乐道,但在笔者看来,与海德格尔相比,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更有一种“海内存知己”的味道。
和实用主义一样,传统儒家哲学是一种以伦理学而不是认识论为出发点的哲学形态。它的核心关怀是“如何生活得更好(善)”而不是“如何认识真理”。它的基本思想和杜威所说的哲学应该关心人的生活而不是抽象原则的主张不谋而合。*汉代刘歆在谈到儒家出处时有段话,很好地表明了儒家的终极关怀在于仁:“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汉书·艺文志》,班固撰,中华书局2012年版。)传统西方哲学认为,只有把握了形而上的原则,把握了真理,才知道什么是“好(善)的生活”。与此相悖,儒家哲学从来没有从人的生活情境之上的普遍原则出发来决定好(善)的生活是什么。它所谓的好(善)生活的标准,不是来自于一种永恒的普遍理性原则,而是来自于历史中积淀下来的与实践语境相关的伦理准则,这是一种从道德实践和道德经验出发的对于伦理原则的把握。孔子心目中的道德理想国不在天上,而在人间。
中国哲学家特别是儒家对所谓永恒不变的大写实体或大写理念从来没有特别的兴趣,在他们眼里,最真实的东西不是不变的,而是变化、持续、转换。在中国哲学的概念中,与西方哲学的大写实体或大写理念可做一比的大概就是“道”了,人们或许会把中国哲学的“道”看成类似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因为“道”具有一种道理、原则的涵义,它是万事万物的根据。但细究之下,我们会发现,中国的“道”和西方的“逻各斯”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概念,不可混为一谈。“道”的词源学涵义很有意思,它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首”,一是“走”,“首”的意思是领导、向前、首要,与“走”合在一起,就是“向前走”或“引导向前”的意思。在西方哲学背景下,只有理性所达到的不变的普遍原则才能引领我们向前走,才是真正的“道”。而在儒家哲学这里,道和人是分不开的,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载《论语疏解》,黄克剑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1页。朱熹对此注道:“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论语集注》(卫灵公第十五)收于《私塾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道”是历史中形成的文化积淀,本身应该在动词的意义上理解。道的涵义是:人类历史形成的遗产,和当下经验融合在一起,指引着朝前演化的方向与路径。
由于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旁观者的视角出发,由于从实践出发而不是从实在和现象的二分出发,中国哲学从来没有将主观/客观做截然的对立,划为本体论的两个领域。中国传统哲学和实用主义一样,不在世界与心灵之间,设立一种表象的屏障。世界是变动的自然,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成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实用主义反对主客分裂,而中国传统哲学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中国哲学讲的是“天人合一”,从表面上看,它与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同属一类范畴:一个强调合,一个强调分,话题似乎是同一个。如果这一论点可以成立,则至少在中国哲学那里,同样有着西方传统哲学所特有的认识论焦虑。然而,这毕竟只是表面上的相似,从实质上说,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哲学意境。“天人合一”的“天”不是客体,不是世界,而“人”也不是主体,不是心灵。主客关系是一种外在关系,通过向外的努力,主体对应于客体;而天人关系是一种内在关系,二者皆以仁为本性。天人合一指的是人与自己道德本性的合二为一,天在这里意味着人之为人的道德根据。它和客体、世界没有任何关系。天人合一讲的是如何通过人自身的道德践履达到与自己道德本性一致的问题。说到底,这是一种伦理学的关怀,它和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关怀,可谓南辕北辙。
认识论的前提是内在心灵实体的独立存在。杜威继承并改造了黑格尔,心灵在他那里被理解为一种历史积淀下来的意义系统,个体通过教化将这套意义系统内化在自己的生命之中,从而有了一种与环境打交道的能力。杜威的“心灵”和笛卡尔的“心灵”,在内涵上已经完全不同,前者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后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那么中国哲学呢?我们发现,在中国哲学中,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概念与笛卡尔的mind(心灵)对应,我们没有这种内在实体概念。反过来,西方哲学家也同样感到困惑:在中国哲学的“心”那里,mind 和 heart竟然没有分离。中国人用“心”这个概念指很多东西的结合,除生理器官之外,还有灵魂、思想和情感等,同时,心还是一种意义承载。当中国哲学家说“心外无物”时,这句话的要点不应该落在认识论的层面上,也就是说,不应该被理解为在笛卡尔式的心灵之外,或我的意识之外,再没有其他事物存在了;而是说,事物的意义和我的意义系统是一致的,不能分开的。这个意义系统不只是认知的,它同时甚至首先是情感的、富有道德意味的。“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王阳明:《传习录》,卷中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实用主义认为,此心出自历史的传承,通过长期的教化,被逐渐内化到“我”的生命之中,是“我”敞开世界的方式。而在王阳明这类心学派看来,此心人人皆有,可谓良知,无须外求,只要自我向内用功即可达到。可以看出,实用主义和儒学对心灵的理解趣味相近,但对于实现它的路径的解释却大相径庭。但尽管有这样的不同,儒家还是和实用主义一样,从来不把认识论当作哲学的辐辏点;中国哲学家既没有建立认识论的动机,也缺乏建立认识论的前提。
和实用主义一样,中国哲学看重的不是从侧面打量世界的知,而是在世界中、与世界交融一体的行。它首先是一种实践哲学,实践理性才是中国哲学的精髓。依照中国哲学的传统,知行从来不能割裂。中国哲学对知的涵义的理解与实用主义相近而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同。按照西方哲学传统的定义,知是一种得到证明的真信念,因此它必须是可以用命题表达的,具有命题内容的。而在实用主义和中国哲学传统看来,非命题性的、在生活实践中为人们所掌握的一种技艺性的能力也是一种知识,甚至是更加基础性的知识。它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知道“单簧管如何发声”,即中国人所说的“庖丁解牛”之类的知识。这种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实践的技能,知和行在此根本无法分开:“我们说‘现在我知道了’——类似于说‘现在我能做这件事了!’”*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8节。儒家哲学强调践履,这是一种实践功夫,当一个人说他有某种知识时,对于中国哲学家来说,那首先意味着他能在实践生活中有不同的表现。这种默会的知识是最为重要的,并且它构成了命题性知识的基础。杜威对此有过详细的论述,他的结论是,甚至在近代西方认识论那里起到基础作用的感觉,也和行动不可分离,是行动整体的一个环节。*参见杜威《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载《杜威全集》(早期著作第五卷),杨小微、罗德红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75页。因此,中国哲学和实用主义的结论是一致的:从本源上说,知行无法分割,知行合一。行是第一位的,脱离行的知识在传统中国哲学那里是没有地位的。从知识的来源说,和行相关的体知是中国哲学家所特别看重的;从知识的学习过程来看,履践是至关重要的;而从知识目的说,行是第一位的。因而,才有孔子结论式的断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载《论语疏解》,黄克剑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5页。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载《论语疏解》,黄克剑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0页。如果知识与行无关,则这样的知识是中国哲学所鄙夷的。正因为这样,形而上的沉思,在中国哲学那里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杜威曾经指出,西方哲学传统因为追求确定性,而将知凌驾于行之上。这在中国,则从来没有发生过。
结 语
实用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如果仅从方法论、真理观或意义理论的角度看它,那么它恐怕最多只具有一种思想史的研究价值,但如果从本体论的角度,即从它的彻底经验主义的角度看它,那么显然,实用主义显示出一种现代哲学的气质,仍具有蓬勃的学术生命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体现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既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终结,同时也是现代哲学的开启。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独特的、整体的、动态的,以生存论为轴心的彻底经验主义也在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那里,寻得了自己的知音。中国传统哲学似乎早已守候在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处。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在元哲学层面上走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路径,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形态转变为伦理学为中心的哲学形态。由于这一转变,实用主义和儒家哲学在一系列重大哲学论点上具有明显的重叠性,比如本文所提到的:不以认识论而以伦理学作为哲学的出发点,拒斥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否定以永恒不变的本质来解释变化着的生活,强调实践、知行合一等等。
然而,哲学旨趣上的相近并不意味着哲学风格乃至某些具体细节上的相同。比较的目的是相互映照、取长补短。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与实用主义当然也有不小的差异,这些差异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讨论,笔者在这里特别想提示两点:
第一,中国哲学家对待语言的态度和实用主义者尤其是新实用主义者极为不同。传统中国哲学,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对语言采取了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大道无言,勉强言说,也只是一种无奈的手段,所以他们从来没有像实用主义者那样关注语言。他们宁愿采用一种诗意的方式,用隐喻、比喻、联想等,有时还强调不言之教、得意忘言。实用主义者如詹姆斯、杜威也认识到言而无行的缺陷,因而强调知行合一,反对空谈。但他们毕竟由西方哲学传统孕育而生,逻各斯的言说之意对于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理性是实用主义者的基本气质。新老实用主义者们都十分注重语言的作用,皮尔士首先将语言提升到哲学的中心位置,倡导“语言转向”,詹姆斯是运用语言的大师,杜威则强调“语言是意义之母”。分析哲学之后的新实用主义更是走上了语言的道路,用“语言”取代了近代哲学的“观念”,将语言置于哲学的核心,以至于在风格上更是与中国哲学相去甚远了。
第二,虽然中国哲学与实用主义在许多观点上相互重叠,但细究之下,某些观点的具体内涵是不尽相同的。就拿对两者都很重要的“实践”概念来说吧,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与西方传统哲学大相径庭,实用主义和中国哲学都主张实践优先,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它们所说的实践概念的具体内涵是有重大区别的。中国哲学家所说的实践主要指的是一种道德践履的功夫,一种自我修炼、自我成全的功夫,一种无待于他物、无待于他人的功夫。“一日三省吾身”是这种实践的最佳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终日静坐书斋的圣人同样可以是一个终日实践不辍的人,这一实践的主要指向是内在自我。而实用主义者所说的实践,指的是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是一种在对待性活动过程中的维持生命、滋养生命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是一种充满意义的目的性的活动过程。这一实践的指向更多地是外在环境,是他物和他人。无论是改造社会还是改造世界,无论是生产劳动还是科学实验,无论是社会集体行为还是个人生活行为,都属于实用主义“实践”的内涵,但一个终日追求“一日三省吾身”的人,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仍然属于智识传统下的人,很难说他是一个实践着的人。
这是两种风格不同、路径迥异的哲学,它们之间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互补,彼此可以从对方那里汲取一些自己所缺乏的养分。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限于篇幅,只能留待另文探讨了。
(责任编辑:周小玲)
On Pragmatism’s Core Concern and Its Echo in Chinese Philosophy
Chen Yajun
We Chinese once have three versions of interpretation about what pragmatism is, which are respectively as follows: a scientific methodology, a subjective theory of truth and a positivist theory of meaning. However, the essence of pragmatism should be nothing but its ontology, namely, its doctrine of radical empiricism. It is a philosophic worldview which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From the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it tak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world as the first premise of philosophy, refutes the thinking way of dualism, repudiates metaphysics in capitals, and advocates the primacy of practice. All of these provides a good platform for the dialogue between pragmatism and Chinese philosophy, especially Confucianism. Pragmatism can find its echo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agmatism; Confucianism; Radical ;Empiricism; Practice; Ethics
2016-01-19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实用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4ZDB022)的阶段性成果。
B087
A
0257-5833(2016)04-0108-08
陈亚军,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杜威中心”主任 (上海 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