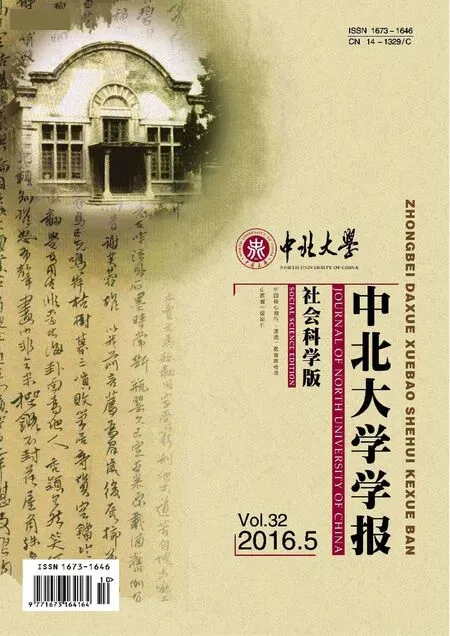清末山西鸦片问题
——以“文交惨案”为中心的考察
2016-01-24岳靖芝
孙 雪,岳靖芝
(1.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2.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清末山西鸦片问题
——以“文交惨案”为中心的考察
孙 雪1,岳靖芝2
(1.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2.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文交惨案”是清末山西禁烟中的一次重要事件。该事件经过民众、官方、士绅激烈博弈,又通过舆论发酵和革命党人运作,由一件单纯的禁烟事件发展成为一个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社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鸦片问题所关涉的利益体系,其既是鸦片问题,而又超出了鸦片本身。“文交惨案”及其生成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结果,清晰地呈现了晚清鸦片政策的历史面相及由此导致的政局演变线路。
清末; 山西 ; 鸦片问题; 文交惨案
0 引 言
鸦片泛滥成灾是近代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鸦片战争前鸦片疯狂走私导致大量白银外流到清政府“寓禁于征”政策推行,全国鸦片进口量不断激增,土产鸦片产量急速上升。作为北方主要鸦片产区之一,山西鸦片问题一直受到世人关注。该省自咸丰年间开始大量种植后,到光绪初年鸦片种植面积已占当时山西总耕地面积的 11.32%。[1]此后几十年间,鸦片在山西一直是农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围绕鸦片所产生的利益博弈和政治关切愈发尖锐,“文交惨案”即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典型事件之一。文水、交城两地在山西鸦片种植与售卖上首屈一指,出产的“交土”因品质好、药劲大著称,因而晚清以降这一地区鸦片问题牵涉了愈益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在区域社会中产生了愈益广泛的影响。所以,笔者选取清末“文交惨案”为切入点,具体分析文水、交城地区围绕鸦片产生的一系列区域社会问题,依据翔实的史料,关注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探讨在当时环境下禁烟活动是如何展开的、利益群体间又是如何博弈的,进而分析其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希望以此加深对晚清山西社会的认识和理解。*早期探讨鸦片问题的论著多将视角集中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等方面,一方面是鸦片进口所带来的白银外流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是因吸食鸦片带来的社会问题。近30年来关于中国近代烟毒史的研究出现从整体性研究向区域微观研究发展的趋势。如于恩德的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华书局,1934年)对中国自禁烟以来各种法令进行了初步概括和总结; 王镜铭的《毒品蔓延于农村社会》(《大公报》1930 年10月15-18 日)通过对河北磁县农村鸦片泛滥的调查,分析了鸦片带来的农村经济衰退; 王宏斌的《禁毒史鉴》(岳麓书社,1997 年)认为鸦片弛禁结果是从前种植农作物的土地改种罂粟; 王金香的《中国禁毒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对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根据地进行的禁烟禁毒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除上述专著外,许多学者发表了与之相关的学术论文,如李三谋的《晚清山西种植罂粟的严重后果》(《古今农业》2000 年第 3 期)认为罂粟广泛种植严重妨碍了粮食生产,破坏了山西农业经济; 林满红的《晚清的鸦片税1858-1906》(《思与言》1979 年 1 月,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8 年)则提出关于鸦片税额征收负担流向的新观点,认为征自烟农的土地税不会转嫁给消费者,但其他税种如营业税、消费税则均为间接税,最终会转嫁给鸦片消费者。
1 晚清山西文交地区的鸦片种植
1.1日益蔓延的鸦片种植
从雍正帝首度关注鸦片问题到嘉庆四年(1799年),清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来禁绝鸦片贸易,历代清帝皆以禁烟为施政基本方针。鸦片战争前,道光帝推动鸦片查禁,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售卖与种植。山西地处内陆,鸦片吸食和罂粟种植传入时间相对较晚,但发展较快。道光十年(1830年),道光帝下旨令时任山西巡抚的阿勒清阿禀告禁烟事宜。*奏报遵旨查明晋省并无种作鸦片及严禁贩卖服食情形事[Z]. 道光十年(1830)十二月初八日,03-4005-0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但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山西巡抚申启贤连上四折,均为鸦片烟查禁事宜。*奏报晋省查拿鸦片收缴烟具情形事[Z]. 道光十八年(1838)十月二十二日,03-4007-046; 呈报山西省阳曲等县拿获兴贩吸食鸦片烟各起及首缴烟土烟膏烟具清单[Z]. 道光十八年(1838)十月二十二日,03-4007-047; 奏为晋省查拿鸦片情形并请奖励霍州知州周云凤等贩获烟较多各员事[Z]. 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二十八日,03-4008-030; 奏报续获鸦片土膏烟具数目并请鼓励绛州直隶州知州吕士淳等人事[Z]. 道光十八年(1838)十二月二十八日,03-6490-0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可见,此时山西鸦片种植已有泛滥之势。据载,19世纪30年代印度鸦片大量进口时,“即有山西商人到广东从事鸦片贸易,从广东引入罂粟种植”[2]23。鸦片战争后,国内禁烟形势急转直下,渐趋有名无实。咸丰帝登基后,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巨额军费支出使清廷脆弱的财政状况顿显困绌。咸丰八年(1858年)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将鸦片列入海关合法贸易品行列,鸦片贸易合法化使罂粟被大量引入山西,开始被大规模种植。[3]309
到19世纪70年代,山西罂粟种植面积达60万亩,占当时山西耕地总面积(530万亩)的 11.32%。[1]除因丁戊奇荒(1877年~1878年)导致的罂粟种植面积骤减外,罂粟种植处于上升趋势。到光绪六年(1880年),山西各府中“每县之田,种罂粟不下十之三四,全省土地计之,应占十五万顷”[4]57。1882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奏报:“晋民好种莺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5]107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调离山西,加之弛禁论调再兴,山西便公开征收土药税,实际承认了民间罂粟种植的合法性,罂粟种植更为顺利。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和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两次增加土药税三成,鸦片税厘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大宗。山西作为清末土药生产最著名的省区之一,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太原县农民种有罂粟苗4 530多亩,榆次县3 000多亩,交城县3 570多亩,文水县4 300多亩,代州5 100多亩,归化厅4 800多亩。[6]463光绪三十年(1904年),全省土药税收已达23万两白银。[7]作为山西境内的著名产烟区,仅仅几县种烟总和便达25 000多亩。“其时,每每有民间大户种数十亩、上百亩,小户种两三亩、十来亩者,多寡不一,无区不有。一到夏日,原野弥望,皆罂粟之花,或嫣红夺目,或犹云朵降落,白色茫茫。”[3]460以1905年~1906年为例,山西罂粟种植面积达96万亩,占全国总量的5%; 年产30 000担,占全国总产量的 6%。[8]16每逢割烟季节,商贩云集,谓之赶大烟场,一时呈现出畸形繁荣。
面对愈演愈烈的鸦片泛滥形势,1906年9月,清廷颁布上谕指出:“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其应如何分别严禁吸食,并禁种罂粟之处,著政务处妥议章程具奏。”[9]5570此后,清廷相继颁布禁烟章程、禁烟稽核章程、严定禁烟考成议叙议处、续拟禁烟办法、续拟严定禁烟查验章程等政策法令,不断加强对鸦片种植的稽查力度和对有关责任人的监督。1910年1月,宪政编查馆奏拟禁烟条例,最终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了各种措施,使禁烟运动有法可依。
1.2突如其来的“文交惨案”
随着禁烟运动开展,山西省内开始禁烟。山西鸦片种植,尤以交城、文水地区突出。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对交城县种植大烟情况曾做过详细介绍:“查该县为全省种烟最盛的地区,平下、截坌、中西各路罂粟均悉在。平下三十五村,除二十三村不种,四村铲除外,其最多之八村。截坌各村,多至三千余亩。”[5]4438由此可见,交城地区几乎已到无村不种地步。1903年,文水一百七十五村共种土药4 302.5亩; 交城一百四十五村共种土药3 573.8亩。*至于惨案当年的具体种植面积,笔者并未找到详细而确凿的数据,但该地区的耕地面积有限,几年间种植面积不应有太大变化。面对这种形势,地方当局主要在禁种、禁吸、禁运三个方面做出努力,但由于鸦片与烟民经济利益直接挂钩,“民间收获利厚,种植愈多,又可榨油,杆可成薪,叶可饲猪”[10],所以,禁种措施的推行陷入困境。加上基层官员与烟户存在利益关系,很多官绅差役自己就是烟民,执法者成了违法者。即便是在禁烟举措日趋严厉的情况下,仍然是“官民吸食如故”,更有官员“不顾物议,日遣人在市趸购烟土,以供合署眷属之用,以致厅属役书多在属前广开烟寮,公然牟利”[11]。种种乱象都使得禁吸难以落到实处; 而邻近陕西及河南的禁种力度又远远落后于山西,导致“外来烟土不绝”[12],使得鸦片难以禁绝。
如前所述,山西鸦片种植已愈演愈烈。农民恃种烟为生,早成习惯。1909年,由于“秋收告歉,麦种失时”[13]8,文交两县农民为弥补损失栽种烟苗。而随着清政府六年禁绝种烟的命令颁布,山西巡抚丁宝铨为邀功谎报山西种烟禁绝,文水知县刘彤光为让农民按时完粮纳税谎称“当为转恳上宪,仍准,次年种烟云云,众遂信以为真”[14]。山西省谘议局派遣倡导禁烟和天足的太谷绅士孟步云前往文水、交城两县宣传禁烟,刘彤光又谎称禁烟之事已经办妥,决无一人私种。但“民政部以各省禁烟,仅据奏报未审虚实。拟派员实行查勘并优给薪资”[15]。
清政府派人到山西查烟,巡抚丁宝铨为掩盖实情遂强行命令文水、交城两县知县督查农民拔除烟苗。禁烟令下,农民顿时失业,而地方官复暴敛横征,与农民惯行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发生了龃龉; 加上“文水县令刘彤光性极贪暴,自从奉文禁烟,该令愎视为利,数派遣丁役下乡勒索。凡无力纳贿者,辄拘案严惩,施以种种非剖”[16]; 事态急转直下,百姓派出代表与官方商量,请求暂缓铲烟,遭到拒绝。两县人民在开栅镇集会,并立执照合同,约定各村齐心协力同请暂缓铲烟。不料这一集会竟谣传成两县烟农聚众造反,丁宝铨急调官兵两营荷枪实弹到交城、文水两县武力铲烟。[18]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三日(1910年3月13日),夏学津率兵开进开栅镇,会同刘彤光,强令农民铲除烟苗。官兵与烟农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击毙群众40余人、伤60余人,酿成“文交惨案”。
2 经济利益与道德压力: 禁烟与种烟的复杂纠葛
2.1农民的困境与欲求
“交文惨案”虽然是当时的一起突发事件,但其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升级,不能不说是晚清山西社会围绕鸦片而产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矛盾激化的产物。而要理清这些问题就不能不看案件的当事人,即鸦片的种植主力——农民的处境和利益诉求。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罂粟种植成为农民为生计奔波的无奈选择。罂粟是温带副热带植物,性喜干冷,适宜生长在沙质疏松或碱分较重的土壤。而文交两地自然地理条件适宜罂粟的种植。《交城县志》记载:“环交皆山也,延袤蜿蜒数百里而遥,沃壤少而瘠土多,俗俭民贫穷。”[18]51复杂闭塞的地理环境为种烟提供了方便。“交城产烟最盛的葫芦峪,地如其名,山路尤为险峻,地势尤为深邃,又皆平遥客民租地偷种,据为利薮,恃其山深径僻,违禁犯科,不但稽查难周,且非寻常劝惩所能禁绝。”[5]4438《文水县志》记载:“谷口秋风落叶,此处独迟,晚田不霜。”[19]75此即文峪河平原气候特点。此外,文峪河可以为农田提供便利的灌溉水源,独特的自然地理为文交两县种植罂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农民选择种烟最大的驱动力源于种植罂粟的巨大经济利益,“种一亩粮食,夏秋两季,收获一千斤,变钱三吊之谱,而种一亩洋烟,每亩一季收获六七十两,就可变钱四五两”[20]96。面对沉重赋税,完纳钱粮再保持温饱已不易,当地文人温洗马写的歌谣中就有“一亩花(罂粟花)二十千(指两万文钱),农夫重利爱金钱”[3]472之语。的确,面对巨大生存困境和经济压力,农民无疑会为利益而在有限土地上种植最具经济效益的作物。另一方面,鸦片贩子、烟馆老板为获得廉价、稳定的货源,对农民进行虚假宣传,称鸦片为“福寿膏”,是奇世灵药,包治百病,可以延年益寿。百姓受其蒙蔽,且种且吸不在少数。加上一些奸民村匪迷惑百姓,强迫农户订立种烟合同,部分烟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亦乐于加入立约合同共同种植。值得注意的是,乡村宗族势力和政府的基层组织往往即是种烟的积极组织者,又是趁机课以重税谋取私利的机构,因而成为罂粟利益链条上极为重要的一环。当朝廷下令让族长、甲长负责拔出烟苗改种五谷的时候,地方官却与他们勾结,消极禁烟,积极征税。“民间日用以致输赋纳厘,半皆取给于此。”[21]他们在包庇种烟者的同时征收超过正赋十几倍的烟田税。更有县官派出小吏巧以明目暗征重税,使得农村种植罂粟更加肆无忌惮,农村烟毒也更为泛滥。
随着自吸自种农民越来越多,鸦片成为当地乡村社会普遍的待客之物,男女老少茶余饭后都要抽上一杆。“晋省吸烟之癖,官吏士民,弁兵胥役,以及妇人女子,虽皆沾染,大率乡僻居其十之六,城市居其十之八。”[22]更有甚者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或卖儿卖女、或以偷盗为生,全为鸦片所累。正是自家产烟为他们提供了廉价的大烟,一旦政府强力禁烟,农民不但生计犯愁,连自己吸食鸦片的廉价来源也会被斩断。所以,烟农不可能积极响应禁烟,禁烟动力也很难来源于民众。
然而,企图靠种植罂粟来过活的农户们并没有过上富足生活,却被鸦片拖累得更加艰难。伴随着土烟迅速普及,种与吸成为多数农户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简言之,“罂粟种植严重影响了地方农业正常发展,地方社会抗灾能力下降; 吸食鸦片人数激增降低了地方社会人口素质,不利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恶化社会风气,破坏社会稳定,对地方乡村社会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冲击; 影响了地方社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使之呈现出“畸形繁荣”的病态景象。”[10]可见,对于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农民而言,他们既从鸦片种植中获取了谋生资本,同时深受其苦。他们在生存困境下的欲求颇值得关注和探讨。毕竟,求生的法则往往会压倒道德和法律上的规训。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山西当局一纸禁烟政令为何会在农民中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
2.2官绅的角色与诉求
官员与士绅是案件中同样引人瞩目的群体。在鸦片问题上,官绅群体内部一直存在多种声音,显示了其复杂的构成和利益纠葛。
士绅中不乏众多的鸦片吸食者,禁烟势必给这些瘾君子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在社会舆论要求禁烟压力下,士绅作为乡村社会中的中上层人物,更在乎在地方中的声誉,因而士绅在禁烟活动中往往还背负道德上的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查禁烟馆、吸食鸦片之人要被发给执照去指定地方购买,这些又都会给瘾君子带来抵触情绪。另外,不吸食鸦片的士绅会通过自己掌控的话语权或与官家联系维持其所在社会的安定,以谋求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在乡村社会所占有的特权与利益。其初衷或行为并不一定是要阻碍禁烟,但事实上对禁烟造成负面影响。在文交惨案发生前夕,面对聚众集会的普通百姓,“村绅告急之书一日数至。凡在籍绅士亦言,非捕拿首要不能解散胁从”[23]。文交两地会见进驻官兵的诱因就是在当地乡绅以一封又一封的告急信中描述民众如何聚集商议要攻打县城、扬言在井中下毒、烧屋毁房、挟迫士绅,正是在这种不实的描述中,刘彤光同各员绅带领眼线约同兵队前往开栅,立将匪首武树福并抗拒匪党多名拿获。可以说这些告急的士绅正是谣传开栅镇烟农花户聚众造反的源头,在新军进村之际他们又变成了兵士的眼线,表面看来他们推动了文交地区烟苗拔除,但正是他们使得文交地区武力冲突火上浇油,惨案发生对于长远解决鸦片问题并无益处,短暂的武力禁烟之后就是罂粟种植的死灰复燃。
当然,开明的官员和士绅对鸦片的危害有着深刻认识,他们自小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具有鲜明的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的思想。1908年秋,山西绅学商界在太原开会讨论禁种鸦片,决议在一年内戒断。随后他们将这项决议转达山西巡抚宝棻。“宝棻即委派了一百多位官绅,在冬烟即将下种之际,分别到各州县演说,劝人民放弃鸦片,改种五谷。”[24]第二年,他又在春烟播种前,遴选了七十多位官员,并由谘议局转邀各地士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逐乡逐村地演说。[25]
除此之外,一些士绅依托谘议局积极发声(主要是有功名的旧式文人和家境较好的受过新式教育之人),为农民寻找出路,寻求罂粟的替代作物。在“文交惨案”发生前夕,就有咨议局组织士绅到农村讲习鸦片危害,劝告农民拔掉烟苗,改种五谷:“孟绅履青,左绅丽齐,于初四日早,由省动身赴文劝导; 张君实生,曾君子常。由初五日早,下交劝导。四君分劝文交各村,初六七日至各村劝导,而各村社首已被村民威胁,不敢出门。”[26]“文交惨案”后,当地士绅更是行动起来,为农民谋生路。当地士绅高叙宾以开栅村北的娘娘庙为农董会的事务所,并租得公地二十亩,以备试种蓝靛、棉花、旱稻、烟叶、桑树各种农作物,委托太原农会编译员杨增容前往保府购买桑秧六千余株,拟徧植西山前面平坡一带,备养各种家蚕野蚕。[27]文水县令徐昭俭到任后,也“会同太原府调查员高叙宾附设本县农务分会,于自治所内拟定章程,选举本邑绅士安鉴为总理,苏堂栋、韩业芳、陈义和、武宗康、成华、韩学琪等协理其事”[28]。可以说,在基层官绅中,不乏吸食成性的瘾君子,亦有浑水摸鱼的好事者,还有在经济利益之外担当起道德责任的地方领袖。官绅的多元面相与多重诉求,与农民的诉求交织在一起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而晚清社会勃然而兴的新闻媒体则又为案件进程增添了更多不确定因素。
3 舆论纷纭与政治斗争:舆论压力下的“文交惨案”与“拔丁”政潮
惨案引起社会舆论普遍关注。面对聚讼纷纭的舆情,山西当局虚弱的舆情处置能力充分暴露。丁宝铨在宣统元年(1909年)由山西冀宁道道台升任巡抚,当时就已成为山西同盟会员主要打击对象。革命党人甚至还专门成立“拔丁”小组,制造“拔丁”舆论。*主要指夏学津艳妾与丁宝铨暧昧关系后被曝光:“别有夏学津者,该抚之私人也,初娶一娼妇为妾,每出必挟以俱行。其妾未脱籍时,与夏学津之妾同时在勾栏中,以姊妹相呼甚昵,夏学津因是往来抚署,如亲串然,该抚大宠任之。”处在风口浪尖的丁宝铨在这场复杂的利益博弈和纷扰的舆论纠缠中左支右绌、进退失据,导致舆论纷纭最终成为各方政治斗争的工具,一起因鸦片而发的群体性事件最终升级为影响其本人政治前途和山西政治走向的事件。
“文交惨案”发生之初,舆论尚未对丁宝铨当局形成口诛笔伐的态势,甚至还有为丁氏当局辩护的声音。《大公报》在报道文交禁烟时称地方“一律安谧”,当局并未惊扰当地百姓,该报还报道了丁氏当局派官绅到开栅镇调查,确保民众没有受到军队骚扰、抢掠。*甚至对于冲突中的开枪行为,该报也为丁氏当局作了辩护,强调军队是在人数悬殊、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迫开枪,目的是为了防止出现“在场官绅咸被戕害,或受拘执,军士军械全行丧失”的情况。(《交文两县土匪煽乱之确情》,《大公报》1910年3月24日第2张第2、3版)但丁氏显然没有注意利用这种尚对自己有利的舆论环境。若丁氏能够因势利导,迅速采取措施整肃军纪、安抚民众,借机消弭官民之间业已存在的巨大对立,树立亲民、护民的政府形象,局面未必不可扭转。然而,丁宝铨不仅不知抚慰民意、解除对立,反而单方面采信谘议局的调查结论*如文中所述,惨案发生后,丁宝铨随即派谘议局议员前往案发地进行调查。当地民众向谘议局申明“开栅一带死伤人数曁官军抢掠实□,谓人民受此奇惨,若但罪文水令彤光一人了事,未免不足昭雪”。然而,谘议局议员却不敢将这一情况告知丁宝铨,反而“一味粉饰,归咎于民”。而久历官场的丁因深知“地方官禀报不足深信”,遂草率地听信了谘议局的结论,将责任完全推给了民众。(《梁议长因被责会议辞职》,《申报》1910年4月29日 第1张后幅第2版),上奏朝廷诬指农民为匪,并保举夏学津升任第八十六标标统。丁氏当局此举无疑是强烈刺激了处在愤怒和忍耐中的民众和舆情,进而激起了全省民众更大愤怒,事态渐趋扩大、舆情急转直下。早已对丁不满的同盟会员阎锡山和南桂馨闻讯后,令晋阳公报总编辑王用宾等撰文予以揭露,并密派张树帜、蒋虎臣到当地调查事实真相,分别刊登于《晋阳公报》和北京《国风日报》上,一时舆论哗然,愤怒的媒体在此影响下开始连篇累牍地声讨丁氏当局触动军队镇压民众的行径,令丁氏难以招架。
1910年4月13日,《申报》以官兵奸抢百姓之残忍为题对交文惨案作了报道:“山西交城文水一带百姓,因筹议种烟被官兵惨剿刻已敉平,兹闻该统带夏学津驻扎交城时,纵令兵丁奸淫民女,抢夺民财,种种悖乱,实堪发指……以搜捕匪党为名,纵兵淫掠,百姓死者不计其数,居民房产焚毁殆尽,直杀至二更以后,该统带始下令封刀,而众兵杀得眼红,一夜惨呼之声至天明尚未息云。”[29]21日,《厦门日报》的《晋省新军之武功》报道称:“曾妄杀无辜百余名,纵兵淫掠各情,已见本报。兹查悉夏兵到镇之后,良民妇女受害者不下数十家。”[30]29日,《申报》又发报称:“陆军部寿尚书前因交文一案官军有杀伤姦抢情形,曾电请晋府惩办为首兵,并撤换管带具奏纠参,兹闻兵备处以此次酿祸,马步各队均犯军纪,良有统兵者举动粗暴漫无约束所致,一标一营管带李逢春,实部队军官亦难自逃法外,拟先撤其差,委以为惩儆之地。”[31]可见,以《晋阳公报》为起点,加之国内多家颇具影响的媒体的炒作造势,丁宝铨和山西当局的舆论压力日益加大。
与此同时,在京的同盟会员狄楼海请御史胡思敬上奏朝廷弹劾丁宝铨、夏学津,胡御史严参文交案[32]又见诸报端,汉口《中西日报》和上海《申报》及各报刊多予刊载。丁宝铨见事已传向全国,难于掩盖,为了转移社会视听,于是变本加厉将刘锦训穿折奏参,又拟逮捕王用宾等人,将对此案敢于说真话的咨议局议员张士秀(同盟会员)以“挟妓逞凶”为名判刑2年并解回原籍临晋县监狱执行,勒令《晋阳公报》发布公电逐走主笔,称“晋阳公报主笔王用宾、荆致中,假公济私,捏造报稿,暗投各报破坏本省禁烟大局,污损公报名誉,被蒋景汾供出,激动绅商学界暨股东公愤,驱逐出馆,停版五期。俟聘定主笔即行出版”[33]。王用宾在逃到石家庄后撰写了正告山西谘议局一文,声讨丁的一系列举动。1910年5月11日,《晋阳公报》第三页将该文发表,旋遭到停刊。丁氏对舆论的粗暴态度充分反映了山西当局难以适应现代信息传播机制的窘困,暴露了其社会治理和风险管控能力的严重不足,其种种失当举措无异于抱薪救火。
就在此时,谘议局议长梁善济带领谘议局全体议员辞职。[34]必须指出,以梁善济为首的山西谘议局对文交惨案持续发酵负有重要责任,其辞职是事之必然。*应当说,当时的梁善济和谘议局因前文所说的在调查中“一味粉饰”,已经处在一种被动的境地。一方面,社会舆论认为其“助官虐民,不称议长之任”; 另一方面,丁氏对谘议局亦心怀不满,丁氏指责谘议局隐瞒实情,“而事实又大不相同,致使余受欺君之罪”,遂“严加申斥”。在这种情形下,梁善济“自知此位难久,乃于是日招各议员决其去”。(《梁议长因被责会议辞职》,《申报》1910年3月20日第1张后幅第2版)但作为被当时社会赋予很多期待和想象的民主宪政的象征,谘议局辞职行为又引发了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反而无形中加剧了对丁的不满情绪。*如《顺天时报》刊文称:“梁君之辞职,系为注重名誉起见,自谓以不名誉之人,领袖舆论之代表,信用一失,近则贻误一省,远则贻羞全国,其视名誉诚重矣……其清节可风也。” (《书山西谘议局梁议长辞职事》,《顺天时报》1910年5月17日,第2版)山西绅商学界维持会专门致电北京同乡官商学界,要求他们“协议设法挽留,以维持宪政”[35]。又有所谓山西全省绅商学界通告书,为谘议局辩诬,更有议员拍案而起,强调如果代表舆论则当“为民请命,不当为官场辩护,应将各兵奸抢实据呈明抚署,然后全局议员一律解散云云”[34]。至此,一场因禁烟与种烟纷争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最终上升为引起社会舆论普遍关注和山西各界强烈反弹的政治纷争,而山西当局在整个事件中的粗暴、颟顸、无能加剧和催化了事态的升级和扩大。
在省内外一片反对声中,清政府给丁宝铨以降职留任处分,文水县知县刘彤光被革职,永不叙用,交城县知县刘星明亦被革职,陆军教练处帮办夏学津撤差褫革。而梁善济则于7月22日回省,俨然成为“倒丁”领袖,“各界诸君相率赴北门外欢迎,道旁车马络绎不绝,俱以手加额,大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意,谈少顷偕至谘议局开会”*1910年8月7日《晋阳公报》复刊,未延用原来排序,改为第1号,第4页登载《维持会欢迎梁议长纪盛》。。此后,丁宝铨从降职罚俸到因病开缺,虽然又经历近一年时间,但其仕途失意的下场业已注定。自1910年9月,多家媒体开始刊载有关丁“患疾” “乞休”的消息。1911年6月18日,《顺天时报》刊发报道:“上谕:‘丁宝铨奏假期又将届满,病仍未痊,籲恳开缺一折。山西巡抚丁宝铨著准其开缺。钦此。’”在两度休假期满而病症不愈的情况下,丁宝铨终于求得一句“准其开缺”*丁中丞患病之原因. 顺天时报[N]. 1911-05-05(7); 山西丁中丞之病状[N]. 顺天时报,1911-05-16(7); 晋抚又蒙赏病假[N]. 顺天时报,1911-05-28(7); 上谕[N]. 顺天时报,1911-06-18(2).。一场因鸦片而引发的“拔丁”行动最终以丁黯然下台而告结束。
4 鸦片何以“拔丁”:鸦片与晚清山西社会的多重面相
“拔丁”是近代山西社会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其影响不仅限于当时,也及于日后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拔丁”取得的显著效果,增强了同盟会的社会影响力,为其进一步掌握军权奠定了基础。此后,黄国梁接任第八十五标标统,阎锡山接任第八十六标标统[36]97,这为日后太原起义做了舆论和军事上的准备。可以说,由鸦片引起的禁种之争在多方力量有意无意的推动下最终在波澜不惊的山西社会中激起层层涟漪,甚至演化成罢黜封疆大吏、推动政权垮台的惊涛骇浪。其背后的复杂情势值得深长思之。
应当看到,“丁中丞自光绪乙巳任冀宁道,历任臬司,藩司,遂升晋抚,于晋省情形极为熟悉”[37]。从朝廷两度准假而不允回籍的表现看,作为久历官场的官僚丁宝铨还是得到了清政府的信任和倚重。面对舆论压力,丁几次乞休则显示了舆论力量的强大和鸦片问题的复杂。可以说,鸦片种植售卖作为道德污点一直贯穿近代山西社会,但它却又是民利来源并与普通大众切身利益关系密切。因此,如何恰当处理鸦片问题就成了考量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表征。面对山西复杂的鸦片问题,丁宝铨的武力禁烟的确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时间烟苗基本被拔除干净,但极为短暂,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鸦片问题。吸食者依旧能获得鸦片,外省尤其陕西、河南等地土产鸦片大量进入山西市场,更有鸦片经简单加工摇身一变成为“戒烟丸”公开售卖,新型毒品如“金丹”“料面”等趁机进入山西市场。此则无疑抬高了鸦片价格,种植罂粟的获利空间较之其它农作物更是有增无减,面对鸦片带来的厚利,农民置国家法令于不顾,偷种罂粟事件时有发生,烟贩为寻求低廉原料不仅组织烟农种烟,甚至去租地种烟,而作为禁烟执行者的官员却与商贩勾结走私鸦片,山西经办禁烟的官员收赃私放烟贩的情况时有发生。更有甚者作为地方长官公然在官署聚众开灯吸食鸦片。虽有清廷详细制定禁烟章程,但在社会变革的动荡阶段,政府对于基层乡村的控制力明显减弱,政府禁烟政策约束不力及执行中对于政策的扭曲,都明显减弱了政府禁烟效果,加剧了鸦片在农村市场的泛滥。
在当时条件下,禁烟激化了烟农、烟贩、烟鬼与禁烟者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拿掉烟农赖以为生的东西时,并未提供新的谋生途径或思路。如此,在生存线上挣扎的普通农民自然不会站在国家、社会的宏大立场上考虑问题,反倒要奋起维护他们被牺牲的利益。同时,烟贩失去了谋生的工具,烟鬼没有了满足生理需求的来源,他们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自然会对政策表示不满,冲突因而不可避免。文交两县甚至山西一省仅靠一两任地方官员的努力和简单粗暴的武力禁烟显然无济于事,又缺乏相应补偿和替代措施,未能考虑到交城、文水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种植传统和民风民情,一味依靠行政命令和高压,势必难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禁烟积极性。而国家与地方政令不一、执行不准,加之社会动荡、舆情汹汹,朝廷、地方官员、士绅及普通民众中很难形成禁绝鸦片的共识。
在禁烟过程中发生的“文交惨案”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在这种复杂情形下清政府对于乡村社会实际控制的弱化和各种新社会力量的增长和成熟。在潜移默化之中,革命党人借机发展了大量积极分子,逐步掌握了地方兵权,谘议局中亦有位置被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把持,如解荣铬、刘绵训、张士秀均为同盟会会员。但同盟会在山西的上述活动中并未解决也未想解决山西鸦片问题,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通过舆论的发酵和革命党人的运作,“文交惨案”被严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这对于惨案的善后、山西鸦片问题的解决难以起到作用,只是单纯放大了惨案影响,为自己的政治军事活动创造机会。而山西地方政府在解决鸦片种植贩卖问题上的无力,协调各方利益关切上的无方,应对突发事件的无序,回应舆论压力的无能,充分暴露了其自身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与日益走向近代的社会要求的巨大差距,这是鸦片之所以能够“拔丁”的重要原因。它表明,在政府威信下降、治理手段落后和社会利益诉求多元的情况下,即便是对国家、民族真正有益的事做起来亦会困难重重。脆弱的社会生态、缺乏信任与共识的官、绅、民、商、媒体之间反而会因一个事件的风吹草动而走向对立和缠斗。
5 结 语
总之,晚清山西鸦片屡禁不止及“文交惨案”发生,表明以鸦片为中心形成的涉及农民、士绅、官僚、商贾的复杂利益格局,他们多元的诉求与关切给问题解决带来了巨大难度和风险。“文交惨案”由一个单纯的禁烟事件演变成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鸦片问题牵动山西社会神经,牵动敏感的利益博弈体系。而地方官员和政府基层控制的薄弱、治理手段的单一、处理危机的笨拙、社会公信力的脆弱又在革命党人和媒体等新兴社会力量挤压下得到充分暴露,给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文交惨案”的生成、发展与扩大早已超越鸦片事件本身,给人们观察转型中的地方社会提供了一个颇具意味的注脚。
[1]王金香. 近代山西烟祸[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3): 38-43.
[2]清实录·宣宗实录(卷184道光十一年)[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3]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山西通史(卷6)[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
[4]广灵县志办公室. 广灵县补志(卷6政令)[M]. 太原: 三晋出版社,1989.
[5]苑书义. 张之洞全集(卷156)[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6]李文治.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M]. 上海: 三联书店,1957.
[7]邵雍. 清末烟苗禁种与反禁种的历史考察[J]. 史林,2007(6): 52-59.
[8]朱庆葆. 鸦片与近代中国[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9]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第5卷)[M]. 北京: 中华书局,1958.
[10]苏泽龙,郭云夏. 鸦片与近代开栅兼论黑色经济背后的乡村社会[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5,17(1): 18-20.
[11]山西种种之怪现象[N]. 大公报,1910-05-27(2-2、3).
[12]时评其一[N]. 大公报,1911-10-16(2-3).
[13]尚德. 山西交文惨案始末述[G]∥山西文史资料(第3辑).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
[14]交文两县民变详记[N]. 申报,1910-04-04(1-2).
[15]禁烟人员选定[N]. 申报,1910-06-02(1-5).
[16]交文两县民变详记[N]. 申报,1910-04-04(1-2).
[17]交文聚众滋事谣传之原因[N]. 大公报,1910-04-25(2-2).
[18]夏肇庸. 交城县志[M]. 清光绪八年刻本,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
[19]王炜. 文水县志[M]. 清光绪八年刻本,太原: 三晋出版社,1994.
[20]师以文. 清末交城文水禁烟事件始末(第8辑)[G]∥交城文史资料. 交城: 政协交城县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1989.
[21]晋抚宝棻奏陈禁烟办法[N]. 申报,1908-11-04(2-2、3).
[22]刚毅,安颐. 晋政辑要(卷20) [M]. 礼制·风俗. 清光绪十四年刻本. 太原: 三晋出版社,2015.
[23]交文聚众滋事谣传之原因[N]. 大公报,1910-04-25(2-2).
[24]杨积广. 清末新政禁烟运动的民众参与[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2007.
[25]晋抚奏禁种土药一律肃清等折[N]. 顺天时报,1909-09-17(2).
[26]山西绅士为文交禁烟事北京同乡官商各界函[N]. 申报,1910-05-04(1-5).
[27]交文农事实验场之布置[N]. 申报,1910-04-27(1-4).
[28]文水令禁烟善后办法[N]. 大公报,1910-05-27(2-2、3).
[29]官兵奸抢百姓之残忍[N]. 申报,1910-03-04(1-4).
[30]晋省新军之武功[N]. 厦门日报,1910-04-21(1-2).
[31]军界: 交文管带将次撤差[N]. 申报,1910-03-20(1-2).
[32]胡思敬: 胡御史严参交文案原奏[N]. 申报,1910-04-18(1-5).
[33]公电[N]. 申报,1910-04-09(1-4).
[34]梁议长因被责会议辞职[N]. 申报,1910-04-29(1-2).
[35]山西绅商学界维持会致北京同乡官商学界公电[N]. 申报,1910-05-24(1-2)
[36]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 山西通志·大事记[M]. 北京: 中华书局,1999.
[37]上谕[N]. 顺天时报,1911-06-18(2).
The Opium Problems in Shanxi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A Study of the Massacre in “Wenshui and Jiaocheng”
SUN Xue1, YUE Jingzhi2
(1.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2.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The Massacre in Wenshui and Jiaocheng was a significant event in the ban on opium-smoking and opium trade in Shanxi provi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 fierce battle among the populace, the bureaucrats and the gentry, the ferment of public opinions and the operation by the revolutionaries, the event gradually evolved from a small conflict into a social problem with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To some degree, it reflected that the ban on opium affected the whole society, especially for the special interests in Shanxi province. The policy actually shook the whole society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The influence of the Massacre in Wenshui and Jiaocheng clearly mirrore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opium policy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ate Qing Dynasty; Shanxi; Opium trade; Massacre in Wenshui and Jiaocheng
1673-1646(2016)05-0038-08
2016-04-14
山西大学第13期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 清末山西鸦片问题及其现代启示——基于交城地区普通民众与鸦片问题之研究(2015013078)
孙 雪(1994-),男,从事专业: 中国近代史。
K252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6.05.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