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花月夜
2015-12-27朱山坡
朱山坡
春江花月夜
朱山坡
春天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和唐教授穿过大半个城市去远在西郊的瓮城大学赴宴。路上有烦人的拥堵,有无尽的喧嚣和漫天的尘埃,唐教授脸上始终堆放着明媚的笑意,没有抱怨半句,因为请客的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朋友。唐教授的到来给晚宴增添了厚重感和庄严感,毫无异议地被安排到了重要的位置。对号入座,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各尽其兴,这样的饭局,我们不知道经历过多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能跟唐教授坐在一起吃饭的从来都是斯文人,本来不会出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这次出现了一些不愉快。席间,三个我叫不上名字的年轻副教授(似乎其中还有一个是讲师)抓住“知识分子与道德重建”的话题大呼小叫,高谈阔论,慷慨激昂。令人厌恶的是满口泊来术语,貌似颇有学识,实属生吞活剥、一知半解。那个德高望重的朋友介绍过了,他们是分别从北京、上海、成都过来的,参加了瓮城大学举办的一个什么论坛,刚刚在论坛上发表了高论。看样子他们余兴尚在,锋芒还来不及收敛。他们各坐一方,我和唐教授分别被他们隔离着,坐在唐教授对面的那个争辩起来张牙舞爪,恨不得跳到桌面上去。他们的导师,唐教授和我都熟知,甚至关系不错。开始嘛,不看僧面看佛面,就不介意他们,但他们的表达欲望太强了,口若悬河,根本停不下来。唐教授张开嘴巴,本想说话,却只能吃菜喝酒,因为每次要说话的时候总被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打断,或被他们有意无意奚落,暗讽唐教授观念老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那个德高望重的朋友已经数次暗示他们注意场合,不要打断长辈的话。但他们装糊涂,隔着饭桌对我们手舞足蹈,口沫横飞。这三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我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心里便分别以无知、无礼、无视称之。十几个人的饭局竟成了他们三个人的独角戏。因而,整个饭局,唐教授自始至终没能完整地说上一句话。尼采说,他心里的火都燃烧起来了,旁人只是看到冒烟。但唐教授毕竟是唐教授,始终正襟危坐,忍而不发,甚至连烟也没有冒,给足了那个德高望重的朋友的面子。回来的路上,我们等了好长时间也打不到的士,只好乘公交车,却被几个叽叽喳喳的女学生挤压到了吐满污物的垃圾桶边。唐教授终于忍不住扼腕长叹:“礼崩乐坏,满目疮痍呀!”我知道唐教授肚子里的瓦斯快要爆炸了,赶紧拉着他中途下了车。
“我们走走,透透气。”我说。
我和唐教授走在笔直的康乐大道上。树木茂盛,街灯昏暗,凉风习习,行人车辆稀稀拉拉。这样的环境适合泄愤。果然,唐教授开始骂娘了。
连概念都没有弄懂,不学无术却信口雌黄,唐教授愤怒地说,讲得好我可以原谅他们,但是,你听听,他们张嘴闭口就康德、福柯、荷尔德林,不知所云!你看看,现在的学术界就是这样,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一片狼藉,满目疮痍!
我无条件赞同唐教授的看法,附和着他疯狂地抨击饭局上的那三个年少轻狂的副教授,将他们贬得一无是处,甚至连他们的导师也一起骂了,教导无方,管教不严,该骂。一直骂到朝阳路口,唐教授才算解气,才恢复他作为一个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的儒雅、豁达、宽容的气度。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唐教授都是一个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惹人喜爱。平时他不是睚眦必报的人,尤其是对后辈他总是以难得的包容待之,因而他在圈子里威望甚高。况且,他人品出奇的好,从没有人说过他的不是。如果个头不是那么短小,肚皮没有那么滚圆,我愿意用完美无缺来形容他。他长我十六岁,所有的人都称他为“唐教授”,唯我敢以兄称之。
“唐兄,今后要多提携提携。”我搂着唐教授的肩头调侃他。
“好说,好说!”唐教授踌躇满志,肚子腆得更高了。
我们转入朝阳路才发现,这个城市变化之大出乎我们的意料。面貌焕然一新,我们居住瓮城二十几年,竟几乎不认得妇孺皆知的朝阳路了。唐教授口干舌燥,进一间便利店要了两瓶水,递了一瓶给我。我张嘴仰面就喝。他不断地拽我的衣角,提示我往左边的巷子里看。
我扭头往巷子里张望。巷子很破旧,像民国遗物,昏暗的灯光里,在每一个门口外都站着三两个花枝招展、搔首弄姿的女人。我明白这是干什么。
“朝阳路原来好好的,什么时候多了这样的一条巷子?”唐教授啧啧称奇,又痛心疾首。
我小声说,是烟花巷,听说唐山路也有。
朝阳路堕落了,像知识分子一样,道德沦丧,满目疮痍。唐教授叹息道,这个时代连知道分子都堕落了,还有什么不能堕落的?
别整得那么严重,不就一条烟花巷吗?何必指桑骂槐、上纲上线呢?我又喝了口水,要往前走。唐教授拉了我一把,有几分暧昧地说,时候还早,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我暗吃一惊,耸耸肩,笑了笑,怀疑他的诚意:不去吧,藏污纳垢之地,黑白是非之所,会影响你的光辉形象,还是远离为好。
唐教授歪着脑袋看我,眼里带有怂恿和轻蔑之意。
我补充说,万一遇上熟人、记者暗访、警察突查、流氓敲诈、摄像留影……
唐教授说,你多虑了,熙熙攘攘,茫茫人海,谁认得我们——你又把自己当名人了是不是?
我支吾其词。在学术界,我的名字虽然不像唐教授如雷贯耳,却也日益为人所知,到了爱惜羽毛、小心翼翼的时候了。
唐教授诚恳地说,你的顾虑也并非没有道理,我也不会愚蠢到贪图一时之快致使一世英名毁于一旦,我们只是去看看,决不做龌龊苟且之事,大大方方地进去,清清白白地出来,保证你全身而退。
处是非之地,焉能全身而退?我还要推托,唐教授佯怒道:还装?差不多就成了,我们都是男人,不必装了。
我还要犹豫,唐教授却已经进去了。我只好紧跟其后。
我们刚进巷子便引起了那些站街女的注意。她们用挑逗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引诱我们。唐教授挨着我对那些面目模糊的女人作一一点评:这个太老了,那个太胖了;这个像一颗地瓜,那个像头母驴;这个脸上脂粉成堆,那个乳房断崖式下垂……残花败柳,满目疮痍!
唐教授不愧为著名批评家,看人看问题总能一针见血,精准无比,虽然不免有些刻薄。巷子里出入的男人很少,因而显得冷清而安静。
“我们只是来看看而已。”唐教授说,“尽管只是看看,但逛烟花巷要比参加今晚这种无聊饭局美妙得多!”
唐教授似乎已经从晚宴的不快中解脱出来,显得兴致勃勃,颇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态,与平时的老成持重截然不同。在一间挂着按摩店牌子的店铺门口,我们被两个香水味很重的女人堵住了,其中的高个子女人还拉住了唐教授的手,将娇媚的脸贴过去,说,唐先生好久不见啦。
唐教授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我姓唐?
高个子女人嗔怪道,我还记得你,你却忘记我了,我们见过的……
唐教授挣脱她的手,争辩道:我什么时候来过?我一辈子从没光顾烟花之地,从不,绝不。他转脸看我,是想告诉我事实,还是要让我证明他的清白?我被另一个女人纠缠着,要拉我进屋。我坚决不进去。里面是龙潭虎穴,藏污纳垢。
唐教授甩掉了高个子女人的手,正色告诉她:“我是第一次路过这里,我只是看一下,我跟你素昧平生,前世也没见过。”
高个子女人说,我知道你们不会来这种地方的,你们跟其他戴眼镜的男人不同,你们是正人君子,道德模范。
少来这一套!唐教授习惯性地扶了扶眼镜,不依不饶地追问,你到底怎么知道我姓唐?
高个子女人惊喜道,你果真姓唐?我是乱猜的。
唐教授说,你真的只是乱猜?
高个子女人很有成就感,自豪地说,是的,有时候真能猜中,这次又猜中了,我中彩了。
唐教授还不放心,你真没有见过我?我们只是萍水相逢?
高个子女人说,现在不是见面了吗?缘分嘛,进来享受一下吧……
唐教授对我说,我们走,我们怎么会来这种地方消费呢!我们只是瞧瞧。
高个子女人有些不悦,你们怎么只看不消费?有什么好看的,没见过世面?
唐教授想反驳,但想了想算了,拉着我往巷子深处走去。侧目而视,我发现唐教授像一匹识途的老马走在回家的路上,脸上兴奋之色仿若桃花。
“刚才那个婊子是信口雌黄,一派胡言。对天发誓,我真没嫖过娼。”唐教授说。
她没说你嫖过娼呀,我说,我绝对相信唐兄从没有光顾过烟花巷,更没有嫖过娼。
唐教授嘿嘿笑了笑说,话也不能说得这样绝对,我,我还是光顾过烟花巷的,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差一票没评上教授那天晚上,和洪爽、莫大、张爱国(此三人曾经都是我们的同事)光顾了烟花巷,但我没有嫖娼——他们都进屋子了,我有贼心没贼胆,一个人守在外头,紧张得浑身颤抖,汗流浃背,他们出来时,看到我脚下一地烟头,满目疮痍,嘲笑我白走了一趟烟花巷,但他们不知道我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默念了二十一遍。唐教授觉得我怀疑他根本不记得《春江花月夜》,竟背了起来: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我及时打断唐教授说,在这里背诗不协调……你守身如玉,终没有失去底线。
唐教授说,有人说这是我人生一大遗憾……
我说,不遗憾,如果那次你同流合污了,说不定你从此就堕落了。
唐教授说,你要更新观念,嫖娼并不能说明人品问题,古代不少文人墨客是以青楼为家的——你说说嫖娼和剽窃,谁更罪大恶极?本校就有人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爬上了高位,他从没嫖娼,但能证明他比嫖客更高尚?那天他还公开批评某人品行不端,我不知道他哪来的道德优越感!简直是厚颜无耻、满目疮痍!
我知道唐教授又在指桑骂槐,指责我们的校长。
又有烟花女向我们招手。唐教授悄悄地凑近我的耳边说,右边那个烟花女不错,像化学系的小宋。
我走近一看,果然像小宋。小宋是我们化学系的年轻海归副教授,长得像日本女人,唐教授喜欢得不得了,可谓动了真情。唐教授中年离婚,孤家寡人,曾信誓旦旦说永不再娶,但见到小宋后,断然否认说过类似的话。然而小宋并不搭理他,看得出来,她从心底里蔑视唐教授。我们都知道,理工科瞧不起说文科,即使你名满天下。唐教授经常为此郁郁寡欢,多次约我喝酒倾诉衷肠。我不少劝慰他,小宋都已经结婚了,老公是物理系最年轻的教授,千人计划引回来的,国家重点培养对象,又帅得一塌糊涂,你干吗偏偏选这样的一个对手?唐教授捶胸顿足悲叹道,此身为何早生三十年?你看看现在的我,与年轻时相比,简直是秋风黄叶,满目疮痍。
关于岁月蹉跎,我没话可说。不到四十岁,我已经谢顶,看上去不比唐教授年轻多少。我若叹息人生苦短,唐教授随时会拍案响应,在这一点上,我们达成共识要比学术容易得多。
此女只是五观有几分像小宋,娇小玲珑,特别是嘴巴和下巴,但气质和涵养哪及小宋万分之一呀?
唐教授果敢走上前去热情地说,小宋你在呀?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宋?”烟花女先是怔了一下,然后开怀而笑,笑得天真无邪。
你真是小宋?唐教授摘下眼镜,嘴巴都快凑到“小宋”的脸上了。
是呀,我是小宋,你还记得我呀?“小宋”说。
记得,怎么会不记得呢?美女犹如好诗篇过目难忘嘛。此时的唐教授和蔼可亲,甚至有些慈祥。
先生,往里面请。“小宋”故作惊喜,与唐教授一见如故,把他的一条胳膊牢牢地抱在胸前,放在乳沟中间,往屋里去。
唐教授并不推辞,甚至没有犹豫,转身对我说,你在这里待着,我跟小宋进去瞧瞧,只是瞧瞧。
“小宋”回头对我说,你也可能进来呀,里面有我的几个姐妹。
我摆摆手婉拒了。我觉得我适合在外头待着。
唐教授进去后,屋子的门关上了。我走到对面的墙头下站着,左右张望。一会过来一个烟花女问我要不要快活。我说,不需要。那你站在黑暗里干什么?我说等人。等谁?我故作高深地说你别问了,我们是同行。你跟我哪可能是同行?我说,你卖肉,我卖灵魂。你说什么?你卖什么?烟花女的质疑和审问竟让我语无伦次,只好说我现在很快活。莫名其妙!那女人轻蔑地丢下一句话,走了。
其实我心里很紧张。我担心唐教授的安危。我害怕警察突然袭击,把唐教授抓走,明天他的名字出现在各大媒体的娱乐新闻上。又担心从哪里冒出一帮小混混,进去将唐教授恶揍一顿,然后勒索万金,我还得替他跑一趟银行……我怕被连累,怕自己才刚刚起来的名声就此被夭折,怕我家被妻子委以了重任的女儿。我不断抽烟。但抽烟也不能有效缓解我的紧张情绪,我的牙齿禁不住打架,汗出如浆。我深吸一口气,开始默读《春江花月夜》,一遍,两遍,三遍……开始是默读,后来是轻声地,到最后是放声诵读。有烟花女甚为好奇,走过来不好气地问,你在干什么?
我说我在等人。
你在这里诵读诗歌,把整条巷子都糟蹋了!这个凶悍的烟花女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用鄙视的语气威胁我,你只看不消费也就罢了,还在这里捣乱,小心有人揍你。
受此轻蔑,我无地自容,说,我们很快就走了。我不断地跺脚,试图给唐教授传递信息。
走之前你把烟头清理掉,你弄脏了我们的巷子。凶悍的烟花女斥责道。
我点头称是。她不再理会我,转身走了。
唐教授进去很久了还不见出来,会不会出现意外?如果出现意外,我应该如何处置?我的脑子里飞快地考虑应急预案。
我拨打唐教授的手机。关机了。屋子里灯光暗淡,看不到人影晃动。又等了一会,实在憋不住了,刚要去敲门,门却开了,唐教授大大方方地走了出来。我赶紧拉着他往外逃。
什么情况?唐教授说,我这不是清清白白地出来了吗?
我有预感,警察要来了。我说。
唐教授胸有成竹地说,哪会有警察?再说了,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呀,我只是瞧瞧……
你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了……
不,只是四十五分钟,刚好是一节课的时间。我跟小宋聊天,谈论知识分子与道德重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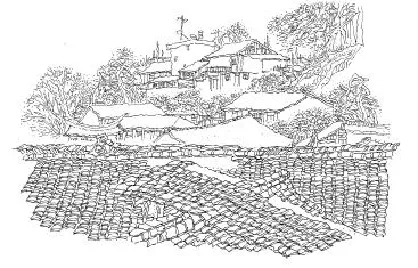
你怎么会跟一个烟花女谈这个话题?
我本来要在今晚的饭桌上谈的,可是他们不给我机会——
唐教授神秘地告诉我,他们就在里面,里面有很多房间,我在小宋的房间,他们在隔壁的房间,我听出来是他们三个人,还有白教授。他们一边享受按摩之乐,一边继续谈论知识分子与道德重建,虽然他们压着声音,鬼鬼祟祟、遮遮掩掩的,但我听得出来就是他们。我跟小宋说,他们说的都是皮毛,都是狗屁,拾人牙慧,满目……
当然,唐教授说的“他们”并不包括白教授。白教授就是那个请我们吃饭的德高望重的朋友,比唐教授年纪还大,比唐教授更稳重,他怎么会来烟花巷,我们不得而知,可能是被那三个小子蒙骗了。但我还是对唐教授的听觉保持一定的怀疑。
我是故意说给他们听的,我给他们讲得条理分明、清清楚楚,免费给他们上了一节课。唐教授信心满满地说,听了我的一节课,我相信“小宋”的学术水平已经超过那三个小子了——你相信吗?
我说相信。唐教授对我的回答很满意。
我拖着唐教授走到朝阳路,站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中间才如释重负。朝阳路才是光明大道、人间正道。
我们往前走,往热闹喧嚣的地方去。
唐教授一直跟我解释说,我真的没做龌龊之事,只是跟“小宋”谈学术,深入浅出,循循善诱,像辅导一个本科生一样。
“但是,我付了她两百元钱。”唐教授最后说。
我不解。为什么呀?
“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唐教授问。
没有。我说。真没有。
那为什么你用不屑和轻蔑的眼光看我?唐教授脸上有愠色。
我说,没有!
唐教授说,从今往后,我们都不要去烟花巷那种地方了,坚决不去了,要去就由他们去吧。
我说,为什么呀?
唐教授挣脱我的手,停下来,环顾四周,茫茫然,扼腕长叹:藏污纳垢,满目疮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