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安的“腰封”
2015-12-25王国平
王国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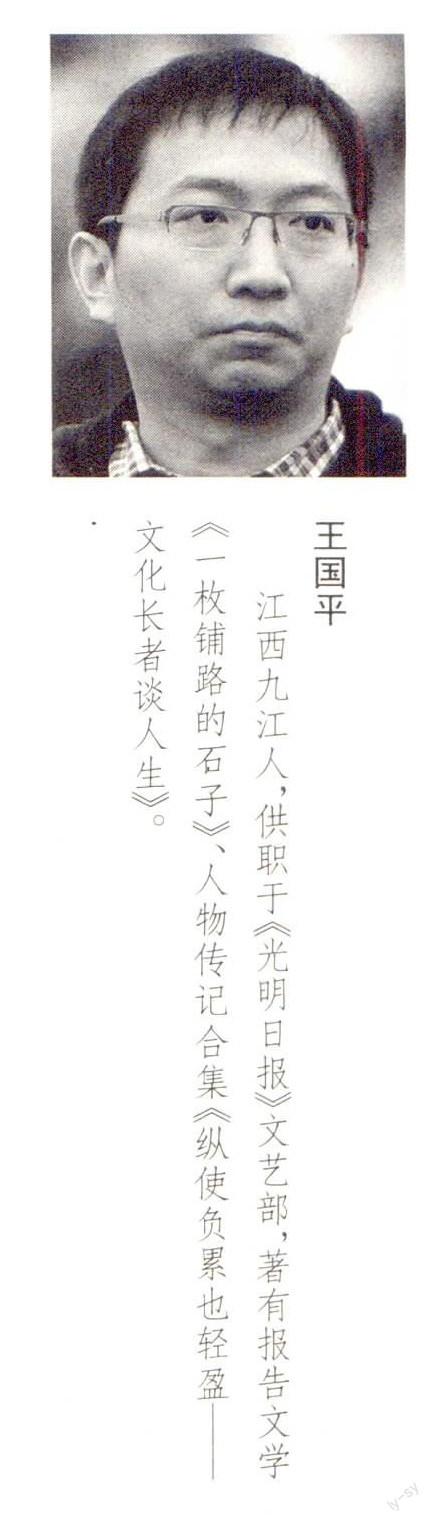
一
在西安行走,步履缀满了一种怯。
还是准备不充分。那么浓的历史场景,那么庞杂的方位信息,形成威压,拾不起来。
徜徉、漫步、闲适,这类的词,好像与西安不太搭调。余光中笔下的李白,“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李白就这样再度被定格了,西安也有了自己固态的姿势。
总是有一些“框架”在人的意识里悬置着,它们在静静等待,狡猾的猎手一样,伺机以动,归类、综合、定型。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斯图尔特·霍尔说这是将人或物简化成“少量的、简单的、基本的特征”,成为“封闭和排它的实践”。说白了,就是带着惬意,自如地敲上一个戳印,心里说:就这么着吧!于是,戳印成了烙印,成了保守势力,顽冥不化。
西安就这般被蛮横地确立下来。是的,西安就是这个样子。是的,西安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是的,西安只能是这个样子。是的,西安还能是一个什么样子。
西安的再生长,不过是长高了一点,长粗了一点。再绵长的滔滔不绝、意气风发,不过是把这个“框架”扶得更周正,更稳妥。
只是,细节的饱满度短了,肌理的丰富性缺了。
奥尔罕·帕慕克在《纯真博物馆》中借主人公凯末尔的口说:“被丢弃在一边的东西会让我很伤心。中国人相信所有东西都是有灵魂的。”
不知夜深人静时,西安有没有力量在集结,忧愤地抗争?那齐整端正、飒爽超拔的兵马俑们,有没有呼应好莱坞电影《博物馆奇妙之夜》,闹一个底朝天?
挪用叶延滨的一句诗,“我努力把一个个干瘪的文字/排成队”,向西安驰援。
二
“一块砖上说华年,听取赞声一片。”
西安有一方砖,稳稳地躺在柜子里,供人观瞻。
它来自大明宫遗址,这就已经够厚的了,让迷恋盛唐华章的人士喝上一壶。它更是狂狷,上边镌刻有“官匠杨志”的字样。
实名制。就像现今下馆子,有些饭店在餐盘上标注厨师的名姓:“×号厨师××为您服务。”
都是为了溯源。
“只见那汉子头戴一顶范阳毡笠,上撒着一托红缨;穿一领白缎子征衫,系一条纵线绦,下面青白间道行缠,抓着裤子口,獐皮袜,带毛牛膀靴;挎口腰刀,提条朴刀;生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腮边微露些少赤须;把毡笠子掀在脊梁上,袒开胸脯,带着抓角儿软头巾,挺手中朴刀……”《水浒传》第十二回刚开张,林冲细细打量的这条汉子也叫杨志,青面兽。
一个唐朝现实人物,一个明朝作家塑造的宋时人物,是否有一些隐秘的关联?
唐时的杨志,衣着、行头应该与宋时有所区分。但身为工匠,你会不会也是个粗人,有着同等的豪迈与洒脱?酷热难耐,砖型设计方案卡壳了,会不会也“袒开胸脯”,发一通盛气牢骚?
然,你是“官匠”,在体制内,是有身份的人。这么说来,言行是不是有一套严密的规范与框定?
目下,“大国工匠”是个热词。“劳动的手”亦可缔造神话,人所敬仰。
真正的匠人相信,物件是有灵魂的,是有痛感的,有瑕疵在身会暗自啜泣。所以,他们在将自己精心打磨的物什脱手的一刹那,愿意饱含爱怜地将之端详,耳朵大张,倾下身来,聆听是否有悲伤泪流。
官匠杨志,你有没有像善待自己的孩子一般,摩挲过这方砖?
哈雷戴维森工厂的装配工总是欢喜地对孩子们说:“街上那些漂亮的摩托车上都有我的签名。”说话间,豪气堆满脸庞。
你是否也手向大明宫,跟自己的孩子说,“彼有吾之名。汝当勉力,承吾衣钵,至要。切切”?
似乎有些莽撞,这方砖参与了你的人生,留下一串串谜,供后来人释读。
三
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有一部纪录片《大明宫》滚动播出。历经一番视听轰炸,人多少有些发怔:话说这是纪录片,怎么还有演员,还有连串的矛盾纠葛?
让故事片有纪录片风格,让纪录片有故事片味道,似乎成了一股劲风。
前者贴近生活,把“舞台腔”甩一边,职业演员非职业化演出,或者干脆请一群不知道什么叫演戏的人粉墨登场,演他们自己,原生态。
后者追求戏剧性,故事扣人心弦,情节跌宕起伏,在故事叙述的间隙完成对事实的忠实刻录。
这难免让人疑心:这还算纪录片么?
比如说,你要从家里外出,正准备扣上门,摄像机却蹲在房间里,记录下你关门的那一瞬间。也就是说,你出门了,都关门了,人家摄像大哥还在你家客厅里耗着,你就放心?这算哪门子事?
《大明宫》不在这样的细部“打转转”,而是跑出一丈远:请来演员出演曾经生活在大明宫里的各色人等,让他们有言有行有表情,见人见事见精神。
这些演员的履历表上有这么一笔:“2009年,出演纪录片《大明宫》。”
不是客观记录的“立此存照”,是主观记录的“想象之真”。
唐德刚的《梅兰芳传稿》就主张“想象之真”。甫一问世就引来哗声一片。他的好友胡菊人打抱不平:“在纪实探源之余,若无文学笔法的艺术加工,梅兰芳亦不过是出土的金缕玉衣,不如读他的墓碑志,翻查他的族谱啦!”
其实,建筑本身就是个活物,是会自己开口言说的,而且说得熨帖、绵密、舒展。
“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艺,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是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合,神志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
“无论哪一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及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地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彩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与兴衰的感慨;偶尔更发现一片,只要一片,极精致的雕纹,一位不知名匠师的手笔,请问那时锐感,即不叫他做‘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他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是不?”
两段论述,出自梁思成、林徽因合著的《平郊建筑杂录》,1932年出版。这对神仙眷侣的弟子吴良镛在《城市特色美的认知》中还毫不客气多引用了两段,理由是“文字很美,不忍割断”。
大明宫了无印痕,那般决绝,没有留下多少灵动可人的“建筑意”。
500个足球场大小,北京故宫的3.5倍、凡尔赛宫的3倍、克里姆林宫的12倍、罗浮宫的13倍……
后人可悲,只能在这样并不严谨的类比中,盲人摸象般感知大明宫的何其大。
《大明宫》握有电脑特技手段,“搭建”出的大明宫富丽堂皇、壮丽无边。创作者言,每座宫殿的规制、方位、周边环境等,均可稽查。
煞费苦心,可佩。
可惜,横竖都还是隔了一层。
观瞻历史还是期待无限地逼近“真”,最好“素颜”登场,实在要化妆吧,切望略施粉黛,就那么轻轻一点缀。
四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海子的诗。西咸新区空港新城想的是给每一条路取一个响亮的名字。
世界那么大,每个字又都是平等的,但有的字往往那么不受待见。比如,一些地名屡次被折腾、被蹂躏。
有的地名“老”了,铲土机轰鸣,不容商量地将其“葬送”,从历史的角落里抹去;有的地名“旧”了,往往视为“不吉利”,于是大张旗鼓地被迫“下岗”,粉墨登场的是一些不相干的时髦字眼;有的地名刚刚“诞生”就“一鸣惊人”,重演着“狐假虎威”的故事……地名,越来越伤痕累累。城市化的步子迈得太仓促,以至于忘了自己姓甚名谁。
空港新城可供炫耀的资本就是“新”。一张白纸上描图画,是创作,要艺术灵感的奔袭。
空港新城借用“外脑”才智。各路专家被邀入驻,给道路以庄严的名号——
渭城大道、自贸大道、周公大道、田园大道、民航大道、天翼大道、临空大道,主打地域风情;
承光路、永和路、顺义路、章义路、明义路、通义路、崇义路、立政路、昭庆路、崇仁路、崇文路、崇礼路、安化路、安仁路、安远路、开远路,清一色的秦、汉、唐三朝城门,恰好航空城乃当今城市门户;
长兴大街、丰乐大街、保宁大街、通善大街、永昌大街,源自唐城坊名,寄望辉煌历史在现实重张;
志千路、泽勇路、管德路、国定路、基达路、凤山路、石屏路、罗阳路、大观路,一律借用近代航空翘楚的英名,既是纪念缅怀,又是自我的表征……
黄志千、尹泽勇、管德、潘国定、屠基达、马凤山、石屏、罗阳、吴大观,这些名字要么被淡忘,要么被遮蔽。西安人向他们发出邀约,奉为座上宾。
有些名字,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字里行间有杯水风波,有时代风雷,有命运跌宕,有情感温度,有精神涟漪。
它们盘活了历史,唤醒已然枯萎的玫瑰,吮吸今时的雨露,让惨淡凋零的遗存有了点血色和脉动。
它们凝结了文明,延展臂膀,对抗永不回头的时间之河。
它们手牵着手,同构起一个圆,旋转出一段优雅的舞。
它们有了灵性,成了“他们”与“她们”。
西安人那么有心,呵护一个个孱弱的地点之名。西安人更当竭力,捍卫一座城之名。
五
“……下班了,想到外面买点吃的,到街面上一看,就连城里的北大街商店都关着门。后来我就改成中午下班时间去买,到了商店,也没有什么东西,只有带壳的核桃——这是陕西的特产,一家家食品店除了核桃还是核桃。这个跟北京就有很大的差距了。”
“当然也还有很好的印象:西安的城市绿化特别好。人行道上行道树、绿篱绿绿的。在市中心的钟楼那儿还有一家花店,里面有大盆大盆的金橘,一盆盆缀满金橘。当时我就想,等我生完孩子、有了自己的家,一定要买几盆金橘摆上。我觉得西安的绿化比北京的好——那时候北京的绿化比现在差多了!”
1966年,张锦秋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来到西安。刚刚落脚,她厌倦了霸占商店柜台的核桃,金橘牵引住了她的目光。那时,她恐怕没有思想准备,将在这片土地上放置自己余生的心血与才情。她反客为主,秉持“新唐风”,书写“石头史书”,牵引住别人的目光。
西安是一部书,张锦秋在书写、贾平凹在书写、赵季平在书写,历史在书写、现实在书写、未来在书写。
西安太厚了。
“……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杜牧笔下的阿房宫,单单一个气候温差,就叫人捉摸不定。
走笔至此,发现上述这些以“驰援”名义排成队的文字,不过是读了西安的一个“腰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