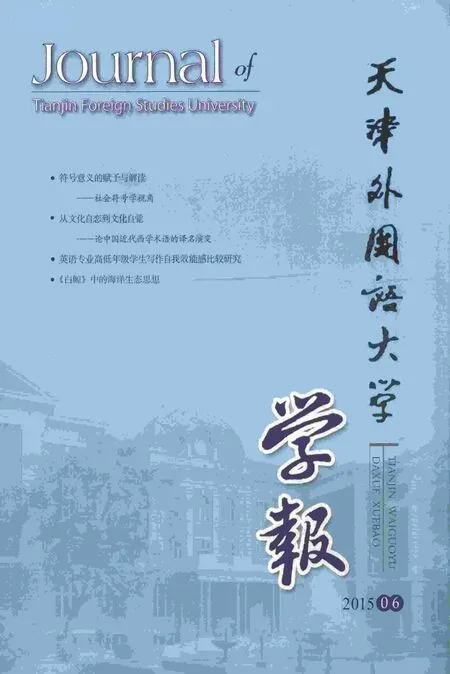高考英语改革背景下中国网民的英语语言态度
2015-12-25罗正鹏
罗正鹏
(香港大学 英文学院,香港 999077)
一、引言
2013年10月,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2014-2016年高考高招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提议从2016年起降低高考英语分值、增加语文比重,突出语文作为母语学科的重要地位、使英语回归到学科应有的位置上,英语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考①。2014年5月18日,《钱江晚报》发文报道:从2017年起英语将不再参加统一高考,改为社会化考试②。新闻发布后,关于英语改革的讨论在互联网上迅速扩散。截至5月19日,已有300万网民参与讨论,发表评论数已超25万条③。不过,该报道并未得到官方证实。2014年9月3日,《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规定:“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④至此,高考英语改革尘埃落定。本文以此次改革为契机,采用评价理论为话语分析方法,探索并呈现中国网民在参与英语改革相关讨论的过程中建构的英语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是社会心理的反映,人们对某种语言的态度反映了该语言的社会地位和价值(高一虹、苏新春、周雷,1998)。本文中,网民的英语语言态度既包括对英语本身价值的认识,也包括对英语学习的评价。关于国人的英语语言态度,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学者们认为英语与中国的政治、经济需求紧密相连(Adamson,2002;Lam,2002;Wen & Hu,2007)。在回顾不同历史时期英语教育在中国的地位、主流文化对英语教育态度的基础上,高一虹(2015)总结出国人对英语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我们将英语视为中国成为国际强国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英语却被看作侵蚀汉语母语和母语文化认同的杀手;长期以来,国人多强调英语的工具性价值,忽略其文化内涵;英语的工具与文化价值成二元对立关系。
对英语工具性价值的强调是国人英语语言态度的一个重要特征(Pan & Block,2011)。有学者对比分析了1981年和2006年的人教版英语课本,指出在课本中英语仅被视为一种了解世界的工具(Orton,2009a)。一项对中国大学英语教师的问卷调查揭示了矛盾的英语语言态度:部分教师认为英语学习浪费时间、占用过多社会资源、并非每个人都需要学习英语、英语学习导致母语文化认同丧失;另一方面,教师亦强调英语的价值,如开阔学生视野、利于求职、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增强经济合作等(Orton,2009b)。张娟(2011)对大学生英语语言态度的问卷调查发现,多数大学生肯定英语在中国的地位及社会价值、表现出英语语言的工具性态度。对英语威胁母语文化认同的担忧是国人英语语言态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有研究表明,我国大学教师和学生遭受“中国文化失语症”的困扰,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丧失了母语文化能力,无法用英语有效表达中国文化概念(肖龙福、肖迪、李岚、宋伊雯,2010)。亦有学者指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缺失,呼吁在大纲制定、教材编纂、课堂教学等方面结合英语教学与中国文化(张为民、朱红梅,2002)。另一些学者则表现出较低程度的文化认同焦虑,以开放多元的态度强调英语在开启学生心智、培养跨文化思维能力、开阔国际视野等方面的人文价值(程晓堂,2014;刘道义,2014;李莉文、李养龙,2013)。从社会建构视角审视中国英语教育的学者摒弃仅将英语视为一种工具的观点,对英语学习与母语文化认同相排斥的立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已成为一门国际“交流共同语”(Jenkins,2007),学习者的动机不再局限于融入狭义的英美目的语文化,还包括成为想像的全球共同体成员(Ryan,2006),获得想象的国际身份认同(Norton,2013)。“母语和外语、民族文化认同的维护与国际身份的获得可以超越二元对立,以‘1 + 1 > 2’的‘生产性’态度来实现”(高一虹,2015:7)。中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并不会因为英语学习而丧失,反而会在全球交流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多元。
语言态度的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直接法、间接法、社会态度分析法(societal treatment approach)(Garret,2007)。 在 直接法中,研究者多以问卷或访谈的形式直接询问人们对语言变体的态度;间接法主要指“配对变语法”,采用多语者的不同变体录音为刺激语料,请研究对象对录音人作出评价,以引发语言态度的投射;社会态度分析法主要通过分析公众领域中的各种话语类型(如语言政策文件、大众传媒素材、网络评论等),透析语言态度背后的社会文化情境,揭示更深层次的语言态度。目前,语言态度的研究多采用前两种方法,研究设计多为定量,社会态度研究法未得到足够重视(Garret,2010)。鉴于直接法存在效度局限、间接法使用的材料真实性受到质疑,学者呼吁采用社会态度研究法,通过话语分析、民族志考查等质性手段深入研究语言态度(Garret,2007)。
高考英语改革是中国英语教育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可作为探究国人英语语言态度的切入点。鉴于目前的语言态度研究对话语分析关注不足,本文选取腾讯网民对高考英语改革的评论为语料,通过话语分析探索并呈现网民评论中建构的英语语言态度。由于网民评论中富含对英语的各类评价,本文选取评价理论为话语分析方法,以揭示网民如何用评价资源建构对英语的态度。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语言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Cameron& Panović ,2014)。人们通过语言使用参与实践、表达对事物的观念及看法、建构社会现实、生产各种各样的话语(田海龙,2009)。通过分析社会中的话语形式,研究者可以呈现语言如何建构和维系人们的观念和看法(Jones,2012)。网络平台开放、互动的特点使网民能够积极参与话语实践,通过语言资源的使用建构英语语言态度。
评价系统(Martin & White,2005)是语篇语义学层面表达人际意义的三个系统之一,关注“语篇中可以协商的各种态度”(李战子,2004:1)。“评价理论是关于评估的—语篇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所涉及到的感情强度,以及表明价值来源、与读者结盟的各种方式”(Martin & Rose,2007:25)。评价系统分为三个子系统:态度、介入和级差。态度系统进一步分为情感、判断和鉴赏;情感涉及人们正反面的感情,判断涉及对人和行为的态度,鉴赏是对事物价值的评估。介入系统涉及语篇中态度的来源、作者呈现价值立场的方式、以及对语篇中不同意见的期待和回应。级差系统关注等级性,是对态度资源和介入资源强度的调节,分为语势(强度或数量)和聚焦(典型性或确切性)两大类。图1为本文使用的评价理论框架(英文字母缩写代表文中出现的评价资源标记;↑和↓分别表示级差的增强和减弱;+和-代表正面和负面态度)(Martin &White,2005)。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1)网民评论中建构了哪些英语语言态度?(2)网民如何使用评价资源建构英语语言态度?研究语料收集自腾讯新闻网报道“中国教育协会会长:全国2017年执行高考新方案”的评论页面⑤。新闻原载于2014年5月18日的《钱江晚报》,发布当天被各大新闻网站转载,引发了激烈的网络讨论⑥。笔者收集了5月18日至6月6日该页面上的所有评论,共计1023条。此阶段是网络讨论的活跃期。收集到的语料进行了匿名处理,以数字编号代替用户网名,保护个人隐私。

图1 评价理论框架
语料分析步骤如下:(1)以用户ID为单位,将相同网民发表的评论汇总,统计参与评论的网民数量;(2)借助质性标注软件Atlas.ti对语料进行穷尽内容分析,归类网民评论中表达的英语语言态度;(3)以评价理论为话语分析方法,呈现网民评论中建构的英语语言态度。
三、研究结果
分析结果显示,共有804位网民发表评论,其中333位表达了英语语言态度。笔者将网民的英语语言态度分为正面和负面两大类,并对各类态度进一步分类。表1概括了网民的英语语言态度以及持各类态度的网民数量。最上层的英语语言态度(正面或负面)互相排斥,但第二层的语言态度并非互斥关系(同一位网民可能表达多种语言态度)。
1 网民对英语的负面态度
大部分网民(75.4%)表达了对英语的负面态度。他们指出英语与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相冲突,表达英语无用、英语障碍、英语学习费时低效等论调。
1.1 谴责英语与中国人文化认同相冲突
29.4%的网民强调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批判国人崇洋媚外、谴责英语文化入侵。

表1 网民评论中的英语语言态度
(1) 还是老话说得好:我是(BA)中国人,何必学外文(CR);不懂ABC(-JG),照做(CT)接班人! (304)
例(1)的网民先用单声资源“我是中国人”强调自己的民族认同。随后的反问句“何必学外文”表达了“中国人无需学外文”是一种不争的事实。“不懂ABC”是对个人能力的负面判断,引发读者对说话人缺乏能力的预期;随后的“照做”驳斥了读者的预期,加强了该网民认为不学英语照样可以立足社会的观点。
(2) 崇洋媚外的(-JG)为西方培养奴才(-JG),外语作为高考就是其中之一,导致精英以加入西方背叛中国(-JG)为荣,这是大方向错了(-AP)。(219)
例(2)的网民认为中国人学英语是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为西方培养奴才”这两例负面判断是对国人英语学习的贬低。“背叛中国”是对精英学习外语后加入西方这一行为的负面判断,也是对外语高考的负面鉴赏。最后网民将中国的外语学习负面鉴赏为“大方向错了”,表现出对外语学习的高度否定。
(3) 英语作为西方国家文化入侵(-AP)的一部分早就该(ET↑)遏制(-AP)了。 (145)
此例中,网民先用负面鉴赏资源表明英语是“文化入侵”,随后用强化接纳资源“早就该”提议尽早“遏制”英语传播,突出提议的紧迫性。同时,“遏制”也是对英语文化入侵这一事实的负面鉴赏和批判。
1.2 英语是一种障碍
34.5%的网民认为英语限制了个人发展,包括剥夺上大学机会、阻碍个人职业发展。
(4)英语害我一生呀(-JG↑),想当年就是因为英语太差(-JG↑),使我失去了对学习的信心,最后没能考上大学!!! (-AP↑)(329)
例(4)中网民认为英语是害自己不能上大学的罪魁祸首。该网民将英语拟人化,谴责它“害我一生呀”,通过语气词加强了对英语的负面判断。接着,网民用“英语太差”负面判断自我能力、用“没能考上大学”负面鉴赏英语对自己的坑害。三个连用的感叹号加强了对英语的控诉,突出英语对网民个人发展的限制。
(5) 老子是高级工程师(+JG),但(CT)通过英语考试后,我从来没有(DN↑)用过英语(-AP),也就是这个英语,害得我(-JG)迟了三年(↓)才获得高工资格,不是(DN)我业务水平不行,而是(CT)我们这些七O后的农村考上大学的人,英语基础太差(-JG↑)中国早就应当(ET↑)改革这个害人的制度(-AP)。(340)
例(5)的网民首先用判断资源“高级工程师”正面评价自己的专业素养,引发读者对自己英语水平高、工作中常用英语的预期。紧随其后的收缩性反对资源“但”反驳了读者的期待。强化后的负面鉴赏资源“从来没有用过英语”体现了该网民对英语价值的高度否定。通过时间上的强化,“害得我迟了三年“突出英语对个人职业发展的拖累和限制。接下来,网民用”不是……而是……”说明自己业务水平并不差,提醒读者关注自己没有按时获得高工资格的真正原因,即英语基础太差。最后网民通过接纳资源“早就该”提议中国改革“害人的制度”,负面鉴赏将英语作为门槛的社会评价体系。
1.3 英语无用
18.9%的网民表达了英语无用的立场,表明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用不到英语。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劳动人民(-JG),从小学到中专,包括后来的自学考,英语也算学了十几年(-AP↑),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AP↑),特别是自考期间,但(CT)我在工作的十几年就没有过使用英语的机会,我在合资企业也工作过,可也是(CT)国人管理的,所以说对社会上占90%以上的(↑)普通大众(-JG)感觉取消英语课是无所谓的(-AP)。(432)
通过负面判断,该网民表明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劳动人民”。通过“学了十几年”和“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两例强化后的负面鉴赏,网民告知读者自己对英语学习投入巨大。接下来的反对资源“但”驳斥了读者对有投资就有回报的期待。虽然网民对英语学习投资巨大,但从来没有过使用英语的机会。评论后半部分,该网民提及自己的合资企业工作经历。一般认为合资企业英语使用比较普遍,然而网民通过反对资源“可也是”否定了这种预期。“90%以上”和“无所谓”则强调了英语对多数普通中国人没用的立场。
1.4 英语学习费时低效
6%的网民批评英语学习的投入和成效不成正比。
(7) 这些年国家、社会、家庭、特别是学生在学英语上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AP↑),它的花费超过了任何学科(-AP↑),但是(CT)在每年毕业的千万(↑)学生中英语发挥作用又是很少很少(-AP↑),应该(ET)是所有学科中发挥作用最小的(-AP↑),而且有很多以前英语学得好的人(+JG↑),由于英语用不到(-AP)而忘得一干二净(-AP↑)了。(698)
该网民先用两例增强后的鉴赏资源“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花费超过了任何学科”评价英语学习,引发读者对英语学习丰厚回报的期待。随后该网民用“但是”反驳了这种期待。“千万”和“很少”突出英语对众多学生的有限作用。接纳资源“应该”承认了对英语的不同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与持不同意见者结盟,使网民对英语的贬低变得更加易于接受。最后,网民指出英语学得好的人也会因为“用不到”而把它忘得“一干二净”,进一步贬低了英语的价值。评论中凸显的是英语学习投资巨大、收效甚微的困境,体现出网民对英语学习费时低效的评价。
2 网民对英语的正面态度
对英语持正面态度的网民仅占24.6%。他们指出英语有利于个人发展、突出它作为信息媒介、国际化渠道、跨文化意识载体的重要价值。
2.1 英语有利于个人发展
8.1%的网民指出英语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素质”(10)和“必备技能”(112),强调英语对个人发展的积极作用。
(8)大家都傻么?(CR)高考不考,企业收人还是(CT)要会英语(+AP)。英语明显(↑)是最实用的科目(+AP↑),可以拓展多少道路(+AP↑)自己知道。(453)
该网民先用反问句(介入资源同意)“大家都傻么?”唤起读者意识,使他们做好理性认识英语重要性的准备(因为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傻)。接下来,网民先承认读者的预期:高考不考英语意味着英语不重要了;这种预期随即被反对资源“还是”所否定,它与正面鉴赏资源“企业收人还是要会英语”相配合,进一步突出英语的重要性。最后,网民用级差资源“明显”,以及强化后的正面鉴赏资源“最实用的科目”、“拓展多少道路”表达了对英语价值的高度肯定。
2.2 英语是一种信息媒介
6.6%的网民认为英语是获取前沿信息的重要媒介,指出“很多有价值的、先进的资料都是英文的”(107),“先进的论文、扎实的教材都来自国外”(577)。
(9) 英语对个人今后的发展,尤其是高精尖人才的发展很有用(+AP↑),特别是(↑)涉及到跨国合作和科研领域(+AP↑),无法想象未来大学生连一篇英文文献都无法大致阅读(-JG↓)会是多么糟糕的一件事情(-AP↑)。(730)
该网民先用强化后的正面鉴赏强调英语对“高精尖人才”发展的价值;“跨国合作和科研”这类高端社会实践体现出网民对英语价值的高度赞赏。负面鉴赏资源“多么糟糕的一件事”表现出该网民对未来大学生英文水平的担忧,担心他们无法用英文阅读文献,从另一个侧面突出了英语的重要性。
2.3 英语是国际化渠道
12%的网民强调英语作为国际化渠道的价值,担忧取消英语可能带来负面后果。
(10)英语很重要(+AP↑),它已经迈向了国际(+AP),取消英语等于闭关锁国(-JG),迷失自我(-JG),整体放弃对外探索(-JG),只会(CT)加大与国际的距离(-JG),疏远国际关系(-JG),等于自取灭亡(-JG)。一门语言不是(DN)固定不变的,它是需要不断改革与探索的,只有(CT)打通国外对话的大门,科技才会进步,经济才会发展,文化才会多元(+AP),如果中国达到了一定高度,汉语也会遍布全天下,所以,请各位三思! (608)
该网民先用两例正面鉴赏突出英语“很重要”、“迈向了国际”。网民接着对取消英语的行为作出一连串负面判断,认为取消英语是“闭关锁国”、“迷失自我”、“自取灭亡”等。接下来网民用反对资源“只有”指出中国的发展必须与世界交流对话,而不是闭关锁国。最后的正面鉴赏资源“科技才会进步……文化才会多元”展望了学习英语、与世界对话的美好未来。在这里,英语被视为参与全球实践的渠道,而非融入英语母语文化群体的工具。
2.4 英语学习促进跨文化意识发展
只有3位网民(0.9%)提出英语学习促进跨文化意识的发展的文化价值。
(11) 学英语是(BA)有用的(+AP),英语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AP)也是一种思维方式(+AP)。(253)
该网民首先用单纯性断言“学英语是有用的”表达自己对英语学习价值的高度肯定,认为这是客观事实。随后,网民用“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正面鉴赏英语价值,体现出其对英语学习促进跨文化意识发展的理解。
3 讨论
高考英语改革背景下的网民评论蕴含着对英语的各种语言态度。总体而言大多数网民的英语语言态度比较消极,评论中蕴含着一定程度的功利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英语被视为一种障碍,限制着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移动潜力”(Blommaert,2010:12);英语和英语学习被视为与母语和母语文化认同相冲突。另一方面,网民评论中也不乏对英语价值的肯定。英语促进个人发展、实现国际化等正面评价反映出网民对作为一种“文化资本”(Bourdieu,1986)的英语的价值强调。网民对英语工具性价值的强调与过往学者的研究相呼应(如Pan,2011;Orton,2009),这种态度或已成为中国英语学习文化的一部分。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当代中国,对英语学习与母语文化认同相冲突的担忧仍是一个突出的主题,这也印证了高一虹 (Gao,2009)的观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外语教育理念已成一种文化惯习,促使国人不断地生产、重复对英语和英语学习的矛盾态度。
然而,网民评论中有迹象表明,英语之“工具”价值和“文化”威胁二元对立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已经去领土化,成为一种国际交流共同语。对于部分网民来说,英语的价值不再局限于工具,它不再刻板地与传统意义上的英美目的语文化紧密相连,而已成为联结中国人与全球实践共同体文化的纽带。这种共同体文化不同于狭义的英美文化,是由参与实践的全球共同体成员在互动中建构起来的。例如:
(12)当今最前沿的科学都是用英文表达书写,而不是中文。英语早已不是英国的专用语言,而已经成为世界先进科学文化交流的通用语言了。不会英语,英语不好,就必然被世界抛弃。[784]
就这位网民而言,英语不再局限于英国的专用语言,它已成为全球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的交际共同语;英语既有工具性价值,其角色亦不再局限于英美文化的象征,而是一座文明间对话的桥梁,促成着更广泛的全球实践活动。
四、结语
本文以2014年高考英语改革为背景,通过基于评价理论的话语分析探索并呈现了中国网民的英语语言态度。文章是对语言态度研究中话语分析方法的尝试,从话语层面揭示了中国草根网民的英语语言态度。研究表明,大多数网民的语言态度比较消极;对英语工具性价值的推崇、对英语学习威胁母语文化认同的担忧仍是国人英语语言态度的重要特征。不过,有迹象表明,英语的全球化对网民的英语语言态度产生着微妙、积极的影响。他们不再功利地看待英语,仅关注它的工具性价值,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参与全球实践共同体的文化纽带,这种态度转变是积极的。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英语在中国的定位。与其不断重复和固化英语工具论、文化冲突论等旧有话语,我们或许可以建构新的英语学习话语,突出英语促进个体参与全球实践共同体的重要价值。话语层面的态度转变或将促进我国英语教育的长足发展。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网民评论的匿名性,笔者无法获取网民的人口学信息(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若能获取这些社会变量,本文或能更深入地揭示网民的英语语言态度。今后研究可结合话语分析和民族志的方法,对公众领域的英语语言态度进行话语研究,充分挖掘话语背后的社会信息,更加深入地解读国人的英语语言态度。
注释:
① 见 http://www.bjedu.gov.cn/publish/portal27/tab1654/info34769.htm,最后访问于 2015年10月19日,17:15。
② 见 http://qjwb.zjol.com.cn/html/2014-05/18/content_2662116.htm?div=-1,最后访问于 2015年10月19日,17:15。
③ 见 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4/0520/c209043-25039117.html,最后访问于 2015 年10月19日,17:15。
④ 见 http://www.moe.edu.cn/public files/business/html files/moe/moe_1778/201409/174543.html,最后访问于 2015年10月19日,17:15。
⑤ 见 http://news.qq.com/a/20140518/003317.htm,最后访问于2015年10月19日,17:15。
⑥ 见http://yuqing.people.com.cn/n/2014/0520/c209043-25039117.html,最后访问于2015年10月19日,17:15。中括号内数字表示评论来源(该评论来自编号为304的网民)。
[1] Adamson, B. 2002. Barbarian as a Foreign Language: English in China’s schools[J]. World Englishes, (2): 231-243.
[2] Blommaert, J. 2010.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 of Capital [A]. In J. Richardson(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C].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4] Cameron, D. & I. Panović. 2014. Working with Written Discours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5] Gao, Y. H. 2009. Sociocultural Contexts and English in China: Retaining and Reforming the Cultural Habitus[A]. In Lo J.Bianco, J. Orton,& Y. H. Gao(eds.) China and English: Globalisation and the Dilemmas of Identity[C].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6] Garrett, P. 2007. Language Attitudes[A]. In C. Llamas, L.Mullany& P. Stockwell(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ociolinguistics[C].London: Routledge.
[7] Garrett, P. 2010. Attitudes to Languag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Jenkins, J. 2007.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ttitudes and Identit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Jones, R. 2012. Discourse Analysis: A Resource Book for Student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0] Lam, A. 2002. English in Education in China: Policy Changes and Learners’ Experiences[J]. World Englishes, (2): 245-256.
[11] Martin, J. & D. Rose. 2007. Working with Discourse: Meaning beyond the Clause[M]. London: Continuum.
[12] Martin, J. & P. White. 2005. The Language of Evaluation: Appraisal in English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3] Norton, B. 2013. Identity and Language Learning: Extending the Conversation[M].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14] Orton, J. 2009a. Just a Tool: The Role of English in the Curriculum[A]. In Lo J.Bianco, J. Orton & Y. H. Gao(eds.) China and English: Globalisation and the Dilemmas of Identity[C].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15] Orton, J. 2009b. East Goes West[A]. In J. Lo Bianco, J. Orton & Y. H.Gao(eds.) China and English: Globalisation and the Dilemmas of Identity[C]. Bristol: Multilingual Matters.
[16] Ryan, S. 2006.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sation: An L2 Self within an Imagined Global Community[J]. Critical Inquiry in Language Studies, (1): 23-45.
[17] Pan, L. & D. Block. 2011.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in China: An Investigation into Learners’ and Teachers’ Language Beliefs[J]. System, (3): 391-402.
[18] Wen, Q. F. & W. Z. Hu. 2007. History and Policy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A]. In Y. H. Choi & B. Spolsky(eds.)English Education in Asia, History and Policies[C]. Seoul: AsiaTEFL.
[19] 程晓堂. 2014.关于当前英语教育政策调整的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 (5): 58-64.
[20] 高一虹. 2015.投射之 “屏幕”与反观之“镜子”——对中国英语教育三十年冷热情绪的思考[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1): 1-7.
[21] 高一虹,苏新春,周雷. 1998.回归前香港、北京、广州的语言态度[J].外语教学与研究, (2): 21-28.
[22] 李莉文,李养龙. 2013.高考英语写作试题研究及其改革路径探索——基于布卢姆—安德森认知能力模型的探析[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1): 55-62.
[23] 李战子. 2004.评价理论:在话语分析中的运用和问题[J].外语研究, (5): 1-6.
[24] 刘道义. 2014.外语教育的作用与高考改革[J].外国语, (6): 8-10.
[25] 田海龙. 2009.语篇研究:范畴、视角、方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6] 肖龙福等. 2010.我国高校英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状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1): 39-46.
[27] 张娟. 2011.大学生英语语言态度研究[D]中南民族大学.
[28] 张为民,朱红梅. 2002.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 3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