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之日
2015-12-23吴文君
⊙ 文/吴文君
立秋之日
⊙ 文/吴文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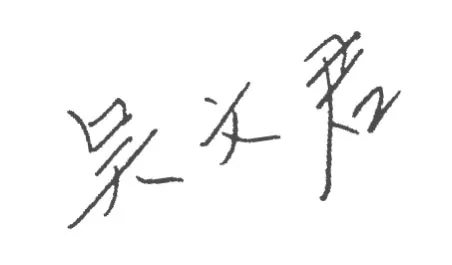
吴文君:一九七一年出生,浙江海宁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收获》等刊,部分被《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刊转载。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红马》。曾就读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
太阳晒着干硬的黄土地,扬起的灰一阵阵吹进车窗。车内的人像被这风封住了口,只有一个被母亲抱着的孩子,朝着窗外啵啵地吐口水。孩子的脸蛋脏兮兮的,带着狡黠的神气,吐到了人,更是高兴,把个身体扭得麻花一样。
李生是非常不喜欢那孩子,仿佛只看这几口口水就能见到那孩子将来的品性,但只要睁着眼睛,那孩子就总在视线里,索性闭起眼睛打盹。
今天立秋,他要去东郊的桐君山给父亲做忌日。
父亲葬在桐君山上。是他带领母亲和妹妹们上的山,并没有什么分量的骨灰也是他安放的。时间一晃,过去了十七年。那一年李生刚过三十,上面想派他去驻京办事处,他想了两天,认为需要服从的条条框框太多,说声算了,便放弃了。时间一年年过去,他像棵树似的,再也没有挪动过。自从科室连人带车间卖给私人老板,名义上上着班,等于闲下来就等退休了,心境也随之大变,从前不敬鬼神,如今一年两次上山给父亲的坟茔培土除草,再放上一瓶酒、两个粽子。
汽车吱地停下,鱼贯上来四个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个瘦高个,戴眼镜,走起来慢慢的,很像厂里原来的工会主席。拿不定主意似的朝车厢里看了好几眼,才走到李生边上坐下了。他后面的是个大个子,穿着松垮垮的汗衫牛仔裤,一副不屑与任何人为伍的神情,上来就往车厢后面走。最后那两个人大概马上就要下,朝车里略微一瞟,在车门口站定了。
每个人看过一遍,李生有几分惊奇。是不是一家人,看眼睛就知道,这四个人中的两个是两兄弟却做出不认识的样子,李生就有些犹疑。这犹疑不过是直觉,年轻时在煤矿上班常要下井,不知名的危险靠近,心就跳得让人不舒服。
车子又朝前开了。
这只是个小站,连站牌也没有,一间盖着灰瓦的小小的杂货店孤零零立在路边。店后一棵高大的榆树,在风中翻卷着叶子。很快,这样的店也没有了。汽车依然一个劲儿在扬起的热乎乎的灰中前行。
这回孩子被母亲按在腿上,给了一块糖,答应下了车买汉堡吃,老实了。
这里的汉堡粗糙得根本不像汉堡。可这与他何干呢?坐第一排的一个女人耐不住寂寞,跟另一个女人大声说话,仿佛一车人都在说话,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让李生烦躁。又有人谈起退休,谈起几天前一个铜矿老板嫁女儿的豪华婚礼。这些人之常情的事,不知何以一样让李生烦躁。
忽然瘦子朝他笑一笑,掏出一根烟,递给他。
李生接过,看这瘦子的脸,有点面熟,依然不认得,笑一笑,掏火柴点上。
瘦子自己也点了一根,吸一口,叹道:“这天可真热得邪乎。”
李生仍一笑:“三月不下一滴雨,还不邪乎?”
瘦子说:“再不下,颗粒无收了……”
这几天电视新闻尽是播些裂了口的地、蹲在地边一脸苦相的瓜农菜农。李生想起这些,却没有话。前年他被人举报有经济问题,被保卫科关了好几个月。开铜矿的老友劝他走,给他留了位置,他去了,也尽心帮这老友赚钱,只是住的离城区越发远,话也越发少了。
瘦子也没话,一根烟快抽尽,又说:“都立秋了吧?还这么热。”
李生看他是热,腋下洇出两大团汗,说:“今天就立秋呀,快了,快凉快了。”
立秋总让他不那么好受。秋天有杀气,“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梧桐能知岁,一叶落知秋,一个节气,连接的却是父亲的离去,对自己从前的放弃也多少有些后悔。真去了北京,总比现在这样子强吧。抽完手里这一根,也掏出烟,回敬瘦子。
瘦子接过,问他:“经常坐这一路车?”
李生说:“也不经常。”现在他不常出差了,过去哪个月也有二十来天跑在外面。
“我知道你以前管供应。”瘦子又说。
“今天遇着熟人了。”李生笑,“你认识我?”
“嘿。”瘦子也笑,“我还知道你是南方人。”
“是啊,南方,吴江,江苏的大县。”
被人认出是南方人,李生总是高兴的。看看瘦子,“我看你也不是这县的。”
“说对一半。”瘦子又笑,“我在这儿出生没错,父亲是东北人,五三年来的,那会这儿连西红柿都还没有,没人知道怎么吃。”说着,又递给他一支烟。
这回李生没有接,从另一个口袋摸出半包烟,说刚才瘦子给他烟,是好意,非抽不可,要说他爱抽的还是这一块八毛的老烟叶,有劲。瘦子说会抽烟的都爱老烟叶。李生说没办法,从前做技术工作经常要熬夜,又没有钱买好烟,反正他也不在乎别人瞧不起,不过凭良心做人。瘦子笑,说现在有几个人凭良心,人人只为自己罢了。
李生说人人为自己没错,小时候学校里先生说:万物各为其私,但各为私于无形中即是为公,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的调和。
瘦子说,可不是,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有道理的。
瘦子话里的冷嘲让李生沉默了下来。瘦子也不再说,只有汽车颠簸着他们的身体,让他们始终处于晃动的状态。但是刚才的融洽还是如烟云一样消失了。他并不怕没人说话的寂寞,大可这么坐到桐君山。他甚至闭上了眼睛,就像方才瘦子没有上来,他看着那孩子朝路人吐口水的时候。可是心里还是活动着什么东西,使他不能真正平静下来。他还想说服说服这个人,看了瘦子一眼,再次开口说,你知道有些事很奇怪。
哦?瘦子看看他,表现得很有兴趣。
李生说他待过的第一家厂里,有个高工,也是南方人。这高工很厉害,不管机器出什么故障,他一到,马上解决。这高工也没什么架子,对谁都挺好,一次来他们办公室,正散着几十块一包的好烟,一个搬运工走进来,高工二话没说也给了搬运工一支。后来高工有两根木头想运回南方老家,车站的人不运,正没办法,搬运工忽然冒了出来,不仅把木头搬上车,还叫人到站后替高工搬下去。
不等瘦子说什么,李生又说了个搬凳子的故事。那时他刚从技术学校毕业,分在一家化工厂,大约上了半年班之后,厂长安排他和几个同事去省里一所学校再去上一年学。这天中午吃了饭,他们几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兴奋地谈着去上学的事,一个穿着破棉袄的人推门走进来,那棉袄也真破,连扣子也没有,用一根绳子拴着。一个人问他干什么,那个人说他来找XX、XX、XXX。XXX一听,出言不逊地说你找我们?找我们什么事?我们有什么事要你找?出去出去!李生看不过,搬了个凳子,说再怎么也得让人家坐一坐。XXX一把抢过凳子,连推带拉把那个人赶了出去。过了几天,他们去学校报到,才知道那个人竟是分管在职人员培训的副书记,他那天倒没穿破棉袄,一见他们就说,你们这样的学生我可不敢要。硬是不肯接收他们。单给他开了介绍信,让他去另一所学校培训了半年,算是感谢他搬凳子让坐。
瘦子听了,大笑几声,说:“有意思有意思。你那时不过二十来岁吧?这么多年倒还记得。”
“说实话,直到这两年才又想起来,想想还是很有意思。”
“你以为忘了,其实这事一直影响着你,你说是不是?”瘦子说着,拍拍李生的肩。
李生就像被拍醒似的心里一惊,难道自己真的一直受着这两件事影响?交错着影响他到现在?只是从没往这方面想过。
他想跟瘦子再说说,瘦子站了起来。
李生朝他摆摆手,很遗憾这瘦子要下车了。看瘦子走了两步,站在车厢中部,再看车门边那两个人不知什么时候换了位置,一左一右成对角站着。李生又是一惊,这太像四面包抄了。一回头,后面穿汗衫牛仔裤的男人也站了起来,四个人齐声说着不要动,手里都亮出了刀子。
除了呼呼灌进来的风,一时车内静寂无声。
李生难以形容自己的错愕,像掉进时间的沟隙,什么都来不及想,就被拽了出来。默然看着眼前这一幕,怀疑这几个人是不是录像看多了。这不是太像警匪片了?一个人简明扼要叫他们别耍花招,老老实实把东西交出来,什么事也没有,不然别怪刀不长眼睛。
很快,第一排的女人爆发出哭声:“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哇!叫我拿什么给你!老天呀,你不来救我。”
那孩子又啵啵地吐口水,朝着瘦子,被他母亲按住头和屁股,只在那儿乱蹬。
有人喊司机,那“汗衫牛仔裤”大喝一声,不准叫!却是冲着那女人的,手一晃,刀已经搁到她颈上。
女人立刻噤声,由着那人翻走皮夹,摘掉腕上的表。摘她手上的戒指时,她痛苦地呜咽着哀求别把这结婚戒指也拿走了,回去怎么跟丈夫交代呢?那人把她蜷紧的手拉直,说少装样子!剥下戒指连手表一块掷入旅行包。
车内的人谁也不敢动,不敢轻率地跟那几把刀作对,由着两个人一排一排洗剥下来,乖乖地把手机钱物交了出来,那孩子手上带铃的银镯也捋去了。
李生眼见此景,心里一阵乱。早听人说过这条路线有抢劫,先想到手上的表,这表是父亲早年入川,在军校任文书时置下的,旧是旧了,倒是只好表。这么多年他一直收着,不能给他们拿了去。
瘦子忽然在他腿上轻轻一按。李生一时不明白什么意思,眼看那两个人逼近过来,不料没看他就走了过去。后排响起一阵窸窣声,一个声音说:“没有了,真没有了,全给你了。”
前排的人被声音引得回过头,李生也回头,见那人一张白净的长脸,白条纹衬衫,黑裤子,只是裤子已被剥至膝盖,露出松松的一圈白肚皮。一人翻了翻,喝令他脱下鞋子。他万般不情愿地脱下一只,告饶说:“你们看,你们看,没有嘛,真没有嘛。”一人喝道:“少啰唆,快脱!”他涨红了脸脱下,一人拿起鞋子一倒,又伸手一挖,掉出一沓钱。四人互相看看笑起来:“别是瞒着老婆找小姐的啵!”
人丛里响起几声低低的笑声。这洗劫进行到最后,便是在这零落的笑声中结束了。
瘦子喊声停车,司机靠到路边停下,四人鱼贯而下,转眼消失在干热的灰尘中。
汽车抖动着重新上了路。开过一个空空的无人候车的小站,司机喊一声有人下啵?没得到应答,闷头朝前开去。
这回那孩子也呆呆地没有动,把一个脏兮兮的脸蛋对着李生。
李生看着他,心仍在未定的惊慌中,忘记方才对他的憎厌。这孩子大了,果真又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自私自利害他的人,还见得少吗?离东郊还有一半路程,他今天不知道要以什么样的心情站到父亲坟前了。
寂静中一只拳头重重敲在他肩上,一个嘹亮的声音瞬间在耳边炸开:“这个人跟他们是一伙的!”
所有的眼睛一时全盯住了他。
“这,”李生申辩,“我都不认识他们,怎么一伙……”
“别狡辩了!”那张白净的长脸此刻通红通红地悬在他头顶上,大张着嘴,“凭什么单单放过你?还给你烟抽!你也给他抽了。我亲眼看见他们给他烟抽!你们听我的,我是税务局的,我叫许国治,这是朱向前,是工商局的。”
“算了,人都跑了。”朱向前劝许国治。他有些踌躇,但被人拿刀逼着抢掉钱的不快还是占了上风,何况他的同伴刚给人当众剥了裤子,正恼怒难当。劝李生:“你说给大家听嘛,那人干吗给你烟抽,你也给他烟了,是不是?什么事都有个理由的,都有个因果的。”
李生只有说:“我自己也在糊涂,有人给我烟,我总要接吧?我抽了人家的烟,总要回给人家一根吧?”
“你少废话!”许国治俯视他的裤袋,“这什么?偷的啵?拿出来给我们看!”
“对!对!拿出来!拿出来!给我们看!”
前后的人都围拢过来。第一排的女人也过来了,站在一步之外愤恨地看着他。
李生挡住乱伸过来的几只手,连说:“我自己拿,你们让我自己拿行不行?”
看清他手中的两样物事,一人讥笑道:“不要是你做贼时吃的干粮啵!”
目睹手中被弄得歪斜的粽子,李生觉得很羞愧。他不想告诉他们这是给父亲带的,父亲还在东郊的桐君山上等他。这能说吗?说了,他们也会说他狡辩。是啊,凭什么单单放过他?凭什么?他真是不认识他们。
空气中充满异样的气息。一车的人都在憎恨他。第一排的妇人观望了这一会儿,跳上来,抓着他的脸尖叫:“还我手表戒指!还我手表戒指!不得好死的!不得好死的!”尽管李生擎住了那两只手,脸已经被她抓出血,丝丝作痛。
他并没有使出十分力,这一擎,女人差点扑倒在地,没了动弹的气力,一张嘴仍绵绵不休骂着。
李生望着她绯红的印着点点雀斑的脸,真想打一拳上去,他这么想着手却松了,妇人往后一仰,站住了,也不再骂,怔了片刻,切齿说:“捉他进去,这样的人就该蹲到派出所里去,死到派出所里去。”
司机呢?许国治想到了司机,走过去冲着司机说:“你死人啊?你这是往哪儿开?开回去!开回去!开派出所去。”
话一出来,马上有人责问现在开派出所还有什么用?刚才不开过去,把那四个贼一股脑儿送进去,这回还说什么?
“司机,你管你开,不要听他。”
一时间满车的人都说起话来,乱声中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
人头晃动中,一个胖大的,刮得赤青的下巴闪了两下,是司机,两只铜铃大眼也不知道在瞪谁。
终于也没有谁上去把司机从驾驶座上拉下来。有人代他说,他天天要在这线上开车,哪敢跟他们结仇,换作你,你敢吗?
汽车在尘土中又往前慢慢腾腾开了一段路,到了站,开了车门,放下不愿意回去的人,调头往回。
抱孩子的母亲不相信拿走的钱会回来,也下去了,嘟嘟囔囔心疼小孩手上被捋去的银镯,又庆幸还有几个钱藏得好,没被拿走。银镯是祖传的,不花钱,钱却是她天天一早起来卖葱卖大蒜攒的,朝一排矮旧的房子逶迤去了。那孩子依稀嚷着汉堡汉堡,头上挨了一掌,一只脏脸蛋一直朝着汽车。
李生看着他,心里宛然若失。
下去十几个人,车内顿然空出许多,阳光投在车窗上,闪动着,如淙淙流水。车内的人,复又像被封住了口,连那喋喋不休的妇人也不说话了。
到了派出所会如何,李生并不十分担心。他没有说谎。他是真不认识他们。没有说谎,他就不怕,况且表保住了,他刚才还为之高兴呢。可是回去这一路,他还是宛然若失。是因为来不及再赶去东郊了吗?他今天无论如何上不了桐君山了。桐君山上的父亲等不到他的酒和粽子了。父亲真的在乎这一瓶酒和这一只粽子吗?给父亲带去这一瓶酒一只粽子,就弥补了他去世自己都不在身边的遗憾了?他尽量眯起眼睛,迎着吹进来的热风,那一刹那涌上来的眼泪,没有流出,吹干隐去了。
汽车吱地停在派出所门口,好几个人一同喊:“下去!下去!”司机扭过他赤青的下巴:“你就下去一下吧。”
李生下了车。
这里他并不陌生,老友带他来过,所长、副所长都认识。老友就是嫁女儿开了一百五十桌酒席的人,他的老板。再过几年,干足五年,老友答应给他一笔钱,让他走,他有了钱,爱到哪里到哪里。
中午时分,值班的一个小个子一个小胡子都不认识,录了笔录,把他带进里间,拿出一只手铐,把他的大拇指往窗栏上一铐,关上了门。
跟进来的人在外面喧嚷着散去,那女人的声音尤其尖利,他无心听她说什么,也无心恨她,他从来没恨过谁,恨就像一个癌细胞,一旦有了,自己也是幸免不了的。他只有一种奇怪之感,他是去桐君山的,怎么又陷入了牢狱。
这房间也没有椅子,空空荡荡,没一样东西。窗栏上过白漆,好几段剥落了,露出底下的铁锈。远远的地方,却有琅琅读书声传来。他凝神听着,想起这附近是有所小学校,是小学校里的学生在念书吧。他在这读书声里听到自己饥肠鸣动的声音。
他站了一会儿,恍然想到这还不是囚室。他们还不算把他关起来。挨饿,站几个小时,这对他都没有什么,只要憋得住屎尿。一旦屎尿遍身,再没有人的尊严可说。
屋内恍惚暗了一层,水泥地的颜色深了一层,那念书的声音早没有了,偶尔有一阵有歌声传进来,又过了一会儿,那歌声也同样没有了。屋内恍惚又暗了一层。难道都快晚上了?那小个子把他的手高高地吊在最上面一层窗栏上,只好踮起一只脚。一直这么踮着,他已经站得麻木了。就是这时,他听到外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脚步声很快朝这边过来了。门哗啦打开,李生眼见进来的人,正是所长,还没有开口,所长先吃惊地咦了一声:“李生?怎么是你!”
李生苦笑:“还不是你的手下铐的。”
所长叫小个子过来,说:“这是李生李工程师啊!”
李生上了厕所,所长泡好茶,招呼他坐,递了一根烟给他。
小个子送上笔录,队长扫了一眼,放到一边,说:“没办法,一地有一地的难,你多担待啊。”
李生执着烟,深吸一口,仍一笑:“你再不回来,我就真惨了。”把经过说了说,吁叹几声,摁掉烟头,站起来。所长说:“这么急干吗,吃了饭走吧?”李生说:“不用了,出了这一身臭汗,我要回去洗澡换衣服,再打电话叫一个会开车的朋友来接我。”
等车的时候,所长又跟他扯了会儿闲话,问他老板最近在不在家。李生说不在,他刚嫁了女儿,和老婆一起陪女儿女婿去澳大利亚了。他在那边也开了公司,以后准备让女婿管去。
说着话,车到了,所长站起来说:“老板回来替我问声好。”
“一定一定。”李生说。
朋友把车开到他家附近停下。他下了车,看着朋友把车开走,恍然不认识东南西北。
天还没有黑透,还是青蓝色的。一颗星星已经挂了上去。直到此时,他才有一点后怕,看刚才在车上的情形,他们揪住他痛打一顿也说不定,不知怎么他们就放过了他。
几个女人在一个小广场上正在跳舞。李生看其中一个眼熟,差点以为又碰到车上的女人,也是满头亮晶晶的发卡,也是闪闪发亮的衣服裙子。再一看就知道不是。只是相像而已。
音乐响起,李生已经走出几十米。想起她切齿的声音,“死到派出所里去”——背上心里都是冷冷的。
立秋这一天李生遇到的事,就这么有惊无险地过去了。跟相熟的人说起,不过惊讶的惊讶,感慨的感慨,瘦子何以给他烟,何以放过他,却是始终想不透彻。
他虽想着再找一天去桐君山,忙忙碌碌,一拖就拖了月余。白露秋分都过了,再不去,都要寒露了。寒露菊花开,说的是隐士,李生的日子却是在俗世中一日日过去的。这一天上午,他又去了车站,等车的时候,忽而眼前晃过那四个人的身影,心里一惊,凝神再看,果真是那几个,绝不会错,都是三十来岁,天冷,都穿上了体体面面的外套。
李生看着他们登上一辆车。那戴细金边眼镜的瘦子清清晰晰也在其中,在一窗边坐下,悠然吸着烟。
李生只觉一个念头呼之欲出,盯着他看着,看着,恍然想起几个月前他在市内坐公交车,前面一个人掏钱带落一把钥匙,用一根红线拴着。虽然“当”地响了一下,这个人并没有听见。李生捡起来还给了他。
他放过他,就因为这枚钥匙?
汽车开动了,拐过一个弯,载着瘦子和他的同伴离开了车站。
李生也上车了,找到座位坐好,若有所思地看着窗外。
汽车开动了,拐过那个弯,载着他离开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