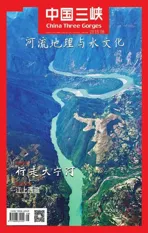学者吴锐说
2015-12-20
学者吴锐说
人类早期的神秘主义潮流产生了巫文化。宗教迷信也是维系社会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锐。 摄影/谭勇
发动汽车的那一瞬间,想到自己是要开着一辆属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汽车去探讨发端于上古的巫文化,感觉有一点穿越,还有一点喜感。汽车行驶在北二环拥挤的车流里,从车窗看出去,能看见雍和宫的屋顶。以藏传佛教兴盛的雍和宫,其香火一向旺盛,尤其是每年农历正月初一那天,雍和宫附近都要进行交通管制,还要出动大量的警力以保障如潮的香客们的安全。看来,无论人类的物质世界怎样发达,都替代不了精神世界的需求。车内后视镜上的平安符随着汽车的一停一动轻轻晃动,我似乎瞬间找到了今天出行的正当性,对窗外的拥堵也有了几分包容。
在建国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东门见到出来接我的吴锐研究员,他一如既往地穿着朴素,微笑里深藏了一个学者的智慧与谦和。吴锐研究员师承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在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如果不是因为要了解巫文化的来龙去脉,我大概没有勇气跟这样的学者对坐探讨深奥的上古史。
什么是巫文化?东汉许慎《说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褎,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凡巫之属皆从巫。”可见巫是人与鬼神的媒介,而巫往往以歌舞的形式娱神,所以巫也多半通晓歌舞。
吴锐研究员以他史学家一贯的学术思维首先从人类和宗教的起源开始了对巫文化的探讨。
最早的文明在沼泽地产生
人从古猿进化而来,经过了五个阶段,即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等阶段。沼泽的进退与人类文明的产生关系重大。
吴锐研究员说,人类是起源于非洲一个地方还是多个地方,学术界有争论,非洲中心论更胜一筹。非洲早期人类经东南亚进入中国的孔道必然是西南。中国西南部在创造早期文明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三苗、巴、楚等古老民族就诞生在这里。杰出的建筑学家、华中科技大学张良皋教授关于沼泽的进退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的探讨值得我们注意。

大山小河是世代大宁河人的生存背景。此为巫溪县北部鸡心岭山下一景 摄影/谭勇
张先生认为,经历海水侵蚀之后,最早的文明在沼泽地产生。灵长类动物的生长需要十分苛刻的气候条件:温暖湿润、植物丰富、天然食物多,难以在北纬30度以北生存。鄂湘川黔交界地区即古代巴域,在北纬30度线左右,从云南的元谋猿人到重庆巫山猿人、湖北建始猿人,都在这一条线上。从西面的大巴山,经荆山、桐柏山、大别山到黄山,形成一条文化热线。古人有“崇东”意识,即不断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追逐迁徙。当元谋猿人和巫山猿人东迁到达湖广盆地西岸,只好止步,因为在远古这是约20万平方公里的大水体,为了适应沼泽水位涨落的变化,他们发明水上巢居干栏。因此湖广盆地西岸正是中国文明曙光升起之处。这一文化沉积带,自河南方城县城东北部的方城垭口至广西灵渠,直线距离900公里,是一条漫长的古代淡水海岸线。湖广盆地西岸有无数的小河谷形成盆地,其中开发最早的应当数江汉之间、神农架以北的堵河和南河盆地,孕育了古代的庸国,在产盐、制陶、铸金、筑城、宗教、文字、文学等多方面,都优于周边。这里有最优越的条件,出现中国第一位“神农”。大宁河、神农溪和香溪盐源尤其重要。巴域就是四川盆地东岸至湖广盆地西岸之间由于长江穿过而时开时合的一道巨大“陆梁”。西北是汉中盆地,东北是南阳盆地,西南是四川盆地,东南是湖广盆地。人类最早的宗教文化——巫文化在这一文化带极为兴盛,并开始影响到更广的地域。
在吴锐研究员看来,人类早期的神秘主义潮流产生了巫文化,巫文化从一开始就扮演了人类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角色。“没有人否认,人类历史曾经走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宗教时期,人们在巫师的引导下,对神战战兢兢,步履维艰,但是宗教迷信毕竟属于一种思想,是动物所不具备的,它标志着人类进化的台阶又上了新的一步。有趣的是,宗教迷信还是维系社会的力量。卓越的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不可忽视迷信的作用,他甘愿充当魔鬼的律师,为迷信辩护。”(《古史考》第八卷《从神守社稷守的分化看黄帝开创五千年文明史说》)吴锐研究员的这一观点对我思考巫文化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很长时期以来,我跟许多人一样把巫文化简单归为迷信一类,这样的想法从一开始就蒙蔽了巫文化的许多有价值的内容。
巫师曾集王权神权于一身
高贵的祭司(巫师)常常不仅名义上而且实际上都是国王,既掌握君权,又掌握神权。
在吴锐研究员的上古史学术体系中,中国历史上国家的发展经历了神权向王权的转化,他称之为“神守”和“社稷守”。在神守时期,巫师以及巫文化在人类社会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在巫术盛行时期,巫师作为最早的专业集团,作用和地位逐渐加强,一个特殊的巫师阶层日渐形成,他们中的佼佼者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首领。“高贵的祭司常常不仅名义上而且实际上都是国王,既掌握君权,又掌握神权。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有‘神’、‘天君’、‘鬼主’等称呼,充分说明了他们集王权与神权于一身。”(《中国古典学第一卷·中国西部文明研究》之《文化传统生生不息:从仰韶文化的神秘主义到土家族的端公》)

青山碧水总是能给大宁河人心灵以无尽的滋养。此为大宁河支流马渡河小小三峡。 摄影/丁坤虎
吴锐研究员给我展示了几幅仰韶文化的鱼纹图,其中有一幅是人面跟鱼相组合的,如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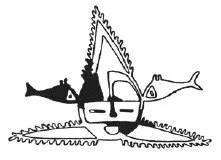
我首先想到了在大宁河见到的“端公”的帽子的造型,同时有种要急于知道面具下到底有怎样一幅面孔的渴求。吴锐研究员将这一图像解读为“神鱼”或者“天鱼”,是带着面具的人与鱼的组合。这种带有某种神秘意义的纹饰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样富有神秘色彩的巫文化,或者这一图像直接指向的就是当时巫师的形象。我在采访巫山巫文化传承人刘柏芝时,他就在端公的“职业服装”上很考究。看来,就算到了科学十分发达的今天,巫文化仍然需要或者更加需要某种外在的神秘来完成人神沟通的使命。据考证,大宁河流域所属的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仰韶文化的影响可以深入到大溪文化的中心。大溪文化遗址中发现大量鱼骨,这一点与仰韶文化中的鱼图腾崇拜也似乎有着某种关联。

巫神占卦。以治病、消灾、驱邪、除鬼为目的地巫术活动。 摄影/丁坤虎
记载大宁河流域巫文化的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山海经》。在中国浩瀚的古代典籍中,《山海经》当排在奇书之首。这部书记载了中国古代的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等,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盆、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向巫山当地的学者向承彦先生请教有关巫文化的问题时,他给我展示了他搜集的十幅以巫山为题材摄影作品,分别命名为“十巫”,也算是对巫文化的另外一种读解。《说文解字》:“灵,巫也,以玉事神。”在古文字中“灵”和“巫”原本是一个字,有学者就直接把“灵山”解作“巫山”。如此,可以看出巫山巫文化之盛,当然这里的“巫山”的概念与现在巫山县的地理概念应有较大差距,但大致范围应该包含了如今的大宁河流域。
十巫之中,巫咸排在第一位,其地位应当最高。著名学者张良皋先生在《巴史别观》中这样描述巫咸:“巫咸是一位盐神。巫的职掌是沟通天人。术业精湛的制盐技师很容易受人尊敬,取得神性。”这样的描述与大宁河流域丰富的盐业资源是相符的。可以想见,在远古时代,盐业资源的丰富与否直接决定了一个部落或者国家的“国际地位”,而掌握制盐技术的巫咸由普通的巫师进而成为人人敬仰的盐神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古代,大宁河流域还生产丹砂。《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这里的“帝药”就是丹砂,被认为是神仙不死之药。丹砂即硫化汞,人们对它的认识早在旧石器时代便有,当时用它来作颜料和涂料,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它的医疗作用被发现了。内服可镇心养神,益气明目,通血脉,止烦闷,杀精魅邪思,除中恶、腹痛、毒气、疥、瘘诸疮,亦可用于外治。因此《神农本草经》称丹砂为药之上品。远古先民认为它是可以使人长生不死,甚至起死回生的仙药。正因为古代巫山盛产丹砂,故又称为“丹山”。
大宁河流域拥有了宝贵的盐和丹砂,使得这一地区的部落、氏族物质财富上极为丰富,人们有更多的空间去追求精神财富,巫文化得以充分发展,大宁河流域的部落、氏族首领也就成为“法力”最为强大的巫师。
巫文化是人类文化之源在中国直接催生了道教
巫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英国人类学家J.G.弗雷泽说,巫术是人类文明的“胎盘”。巫术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科学、宗教和艺术。
大宁河流域自古就盛行巫文化,以至于有学者将大宁河流域认定为巫文化的发源地。巫文化作为人类早期的思想,是在人类认识自然、应对自然的能力还不够强大而产生的神秘主义思潮背景下诞生的,应该是在有人类足迹的地方就会自然产生巫文化,而不见得是发源于某一个地域。
在人类发展的早期,人类面临两大困境,一是生存,二是恐惧。巫师是最早学会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发现各种规律、总结解决问题方法的一群人,其实就是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在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人类的早期是在恐惧中度过的,恐惧来源于自然灾害、凶猛动物,更来源于死亡。生之艰危犹能忍受,死之绝望却让人们常常深陷恐惧的深渊,巫师便成为最早的“心理医生”。
一切人类文化均来源于早期巫文化。在巫文化的基础上,后来分化出科学与宗教两大文化形态。易中天先生说,“科学是巫文化的‘嫡长子’”,“宗教是巫文化的‘次子’”。
巫文化与科学的紧密关系在中国文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农耕文化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跟中国数千年来重视农业、依赖农业有直接的关系。早期的巫文化中,有大量针对农事、生活等的占卜、禁忌等内容,某些内容在现在看来仍然有效,而且能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给予合理解释。研究发现,巫文化中大量关于占卜、禁忌的内容,比如夜观天象、选择吉日、选择吉地等,跟现代天文学、气候学、河流地理都有紧密联系。
巫文化对宗教的影响在中国集中体现在巫文化与道教的关系上。学术界认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主要来源就是巫文化,吴锐研究员在《神守传统与道教起源》一书中这样描述道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一进秦汉,专制皇权扼杀自由思想,百家争鸣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低层次的思想泛起,整个社会跌入神秘主义的深渊。”加之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层大力提倡“黄老之学”、神仙方术信仰大行其道,于是便有了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在跟巫山端公刘柏芝的交谈中,他认为自己的“师承”应该主要归为道教,为此,他还专程到武当山、青城山等道家的重要道场去游学,也算是一个注重学养的巫师了。
巫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发展之源还体现在它对艺术的影响。关于艺术起源的观点很多,其中最为有影响的就是艺术起源于巫术。“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许慎《说文解字》)舞蹈一开始就是巫文化的重要内容,巫师一方面借助舞蹈“娱神”,另一方面也借此“娱人”。在大宁河流域考察期间,我所了解到的巫音的主要价值便是在舞蹈和音乐方面。
巫术与绘画艺术也联系紧密,“古代的美术作品能够流传下来并且广为人知的主要有装饰画、岩画和雕塑三大类别,无论从作品本身形象与线条还是据有所考证的象征意义,这三种形式的美术作品都和巫术有着密切联系。”(李越《人类学巫术观的评析——以文化功能看待中国巫术》)易中天先生说:“巫术还有一个女儿,这就是艺术。”(《易中天中华史·国家》)
吴锐研究员认为,很难说人类文化起源于某一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巫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英国人类学家J.G.弗雷泽(1854~1941)在《金枝》里说,巫术是人类文明的“胎盘”。

下葬前的法事——为亡人开路,祈愿亡人上山路途顺畅。 摄影/郑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