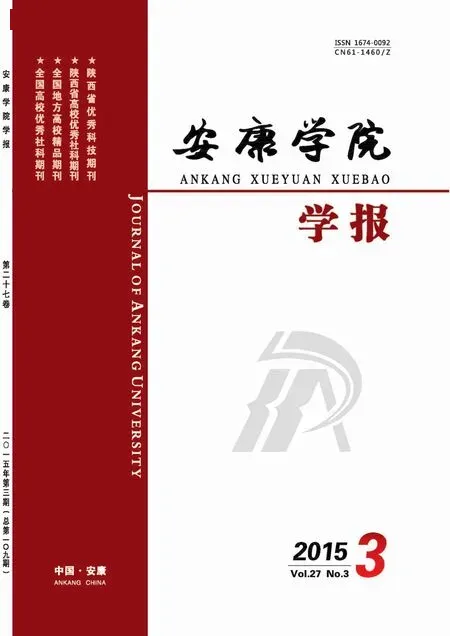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成因考论——基于印度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的分析
2015-12-19和建伟
和建伟
(安徽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安徽 凤阳 233100)
马克思曾对艺术发生学作过精辟论述,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即以希腊史诗为例阐述艺术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1]马克思此论断依据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在马克思看来,文艺属于一定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它产生并服务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社会存在。只有现实的社会生活(指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约束下形成,包括自然环境与历史文明等一切关系的现实生活),才是产生特定的文学艺术的源泉。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产生过程正是这一原理的生动体现。
一
史诗通常以神话传说和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摩诃婆罗多》书名的意思就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虽然史诗穿插许多寓言、插话、哲理、法典,但其故事内核是古代俱卢族与般度族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一场大战。这场战争在长期的流传、加工中逐渐形成了以《摩诃婆罗多》为代表的文学经典。我们注意到,从发生学原理来看,该史诗的产生首先与印度的自然条件关系密切。
印度东临孟加拉湾,南接印度洋,西濒阿拉伯海,北靠喜马拉雅山,雄踞南亚而地处东西方海陆交通要冲。其北部是难以逾越的自然天险昆仑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东北方也是崇山峻岭,交通极为不便,西北经巴勒斯坦可通向中亚和阿富汗,但路途遥远且沿途有荒凉沙漠。东、西、南三面临海,但缺乏良港,且印度洋风暴较多,不便航行。这使得印度成为基本与外界隔绝的独立单元。印度内地地貌多样,有盆地、丘陵、高原、湖泊,这给交通造成诸多困难,加上道路不畅,运输工具落后。印度长年的雨季更加剧了交通的困难,使得印度本身分割成许多小的“独立王国”。印度境内温度不一,气候多样,既有喜马拉雅山的干燥寒冷,又有科罗德海岸的潮湿酷热,兼具寒带、温带、热带气候。印度一年一般划分六季,足见其气候的多样化。总体而论,印度大部分地区属热带季风气候。除高山地区外,各地年均气温在24~27℃之间,动植物种类繁多。印度河流经平原地区以及半岛沿海平原地区水量充足,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特别适于农业生产。兼以热带蔬果丰盛,独立王国的居民容易存活,中央政权长期以来也无力统一全国,遂使得印度长年处于隔离与争战状态,形成许多彼此隔离乃至与世隔绝的村社,即使在莫卧尔王朝与英国人统治时期,印度境内也存在数百个大小不等的王国。马克思在《不列颠对印度的统治》中指出,印度村社长年自治管理,不关心国家状况与君主的更替,村社制度形成了印度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他进而指出,长年的隔绝状态使得印度注定成为侵略者的目标。因为这些不开化的村社居民“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整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2]。印度历史上长期为外来民族入侵,先后为雅利安人、古希腊人、突厥人乃至近代英国殖民者所强占。这种地理上的隔绝状态正是史诗主要故事存在的前提,《摩诃婆罗多》的主干部分即为般度五子与俱卢百子争夺王位,由于印度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才能形成俱卢族与般度族以及其他小邦的多年割据状态。此外,史诗主要围绕恒河与大森林展开,史诗由歌人之子厉声向修道人讲述故事开始,而讲述地就在森林中①本文所据史诗版本为[印]毗耶娑著,金克木等译《摩诃婆罗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相关故事引用不再一一标明页码。。而气候湿热,多有物产的森林也使得般度五子被流放其间多年仍能坚持存活,他及其部族也是在大森林中得到长年苦修的仙人的指点与帮助,从而东山再起。例如《森林篇》中,阿周那就得到毁灭大神湿婆的法宝,从而功力大增。我们更要注意的是,史诗的主神,战争胜负的决定者毗湿奴就是在印度的汪洋大海中开始创造的。在史诗的结尾部分,般度族战胜俱卢族后,老国王持国归隐森林,最终死于森林大火。可见,在《摩诃婆罗多》中,地理因素不仅作为史诗许多故事发生的背景,多方面点缀了史诗的场景,并增添许多美感②例如《森林篇》与《林居篇》有对作为史诗主人公生活与流浪场所的广袤森林的精美描写。,而且在许多情况下直接影响了故事情节的推进过程。
印度多姿多彩的自然地理环境培养了印度人民的想象力和形象思维,为他们的美妙幻想提供了一个可以海阔天空、随心所欲驰骋的空间。在封闭的地理环境和无法驾驭的自然力量面前,印度先民很早就感到宇宙的广袤和个人的渺小,感到寻求一种足以安身立命的依托的需要。于是幻想着用祈祷、祭献或巫术来影响主宰自然界的神灵以获得庇佑,同时赋予这些神灵以神秘的超自然的性质,由此产生了印度最初的宗教。印度宏伟的崇山峻岭、奔腾的河流、繁花茂林、奇禽异兽这些美好的景物就成为文学艺术的题材,如著名诗人迦梨陀娑的名诗《云使》和《鸠摩罗出世》就是以雪山(喜马拉雅山)为背景,《时令之环》更是以鲜艳色彩直接描绘印度各季节的景物。印度的宗教神话也常常反映出地理环境的作用,印度气候酷热,旱涝交替,水的问题至关重要,印度司风雨的神就有很多,如因陀罗、楼陀罗等,《火神往世书》中还试图了解自然现象的变化与人事的关系。也正是在这片土地上,热带气候使得植物生长更替很快,释迦牟尼才可能从中体悟到人的生老病死之内涵,从而创立以“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四法印”为核心的佛教。而《摩诃婆罗多》中多处涉及到神话传说与神话人物(如太阳神苏尔耶、风神伐由、暴风雨神摩录多等),正是印度先民对其自然地理之合理想像。在万物有灵的思维模式之下,除了对以上非生命元素的想像,先民们还设想动植物与人发生关系,它们或在仙人的帮助下,或借助自然的机缘巧合,与相关核心人物结合生子,直接参与到史诗的故事中。史诗多次提到动物与人交合产生后代,例如一头雌鹿吃进了无瓶修道士遗下的元阳,生下了鹿角仙人;一条大鱼吞下空行国王遗下的元阳,生下一男一女。这些带有浓厚的自然崇拜因素的情节在许多时候对史诗的进程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在史诗的插话部分,印度独特的动植物种群也有多种展示。在《宝沙篇》《布罗曼篇》《阿斯谛迦篇》中,反映了人类与蛇族的恩怨情仇,由于仙人之子阿斯谛迦的干预,蛇族最终免于灭绝。而且,在双方交战过程中,象群作为主要战争工具也多次出场。总之,印度丰富多样的花鸟虫鱼、珍禽异兽或作为氏族图腾,或作为史诗人物得力助手,或作为精灵神仙,不断参与到史诗的文本之中,营造出一种亦真亦幻的奇妙情景。
综上,印度的地理环境及其间衍生的动植物对史诗的生成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但我们也绝不能因此而忽略古代印度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对史诗生成所做的贡献。
二
《摩诃婆罗多》离不开印度社会的现实土壤,史诗的故事于史有据:“俱卢王室内的一起家庭纠纷导致了一场流血战争,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毁灭性战争。在战争中,古老的俱卢族,甚至整个婆罗多家族险些毁灭殆尽……描述这次大战的诗歌在民间传颂着,一位姓名早已埋没的伟大诗人把这些诗歌编成了一部英雄颂歌,歌咏俱卢之野的伟大战争”[3]313。在反映这场大战的同时,《摩诃婆罗多》还较全面地反映了印度社会的思想文化特征,古印度各派教规和法典、古代哲学思想流派等内容在史诗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
季羡林先生曾以《罗摩衍那》为例,指出印度文学呈现出“深刻而糊涂”的特征,例如该史诗思想深刻,内容宏大,但情节简单,笔墨多花在人物、战场、风景等细节的精细刻画上,可谓思想深刻,逻辑不清[4]。我们认为,季先生的评价对于《摩诃婆罗多》也完全适用。《摩诃婆罗多》的思想十分深刻,这主要体现在“大史诗真正的核心”[3]246——《薄伽梵歌》中。《薄伽梵歌》是黑天大神在这次俱卢王室之战中对般度族将军阿周那所做的教诲,主要内容是印度早期的数论哲学和瑜伽学说。数论哲学“散见大博罗他纪事诗诸书中”[5],认为原因与结果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区别仅在于原因是隐性的存在,结果是显性的存在。现实的世界万物作为显性结果必定有一个最初的或终极的原因,这就是“自性”。数论哲学从原始的直线性的因果论来看待宇宙生成与变异、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形成“因中有果论”。至于瑜伽学说,则并非哲学观点,而是传自远古的人生实践方式或修炼方式,核心是通过苦行或修炼使人获得超自然力量。它将各种对立物视作本质上的同一,认为物质世界是幻象、错觉的成双与对立,如苦乐、成败、祝福、得失、男女等等。这些表面的现象虽然对立,但都由宇宙之神创立,因此本质同一。瑜伽学派让人超越这种幻象对立,达到对本真的认识,而超越之法即通过瑜伽方式修炼,以求得精神解脱。
《摩诃婆罗多》还宣扬了正法观、战争观、妇女观与民主意识等,其中最重要的正法观念,可解释为天道、大道、天理等[6]135,史诗形象地表明正法观念在人世间的推行。用史诗中黑天大神的话来说,人间的正法受到破坏时,他就下凡来重建正法,以使人间能够恢复正常的理想的社会秩序,让所有生灵能够成长、发展。需要注意的是,正法并不等同于我们的“正义”思想,史诗提到,般度族与俱卢族争战时,许多天神要选择支持的一方,黑天意欲支持般度族,却又将自己的军队与自己各作一分,让双方来选,以示“公平”。既然俱卢族代表邪恶,黑天为何要多此一举呢?而且,黑天在随后的战争中又多次采取不正当的手法打击对方。这表明史诗宣扬的是某种善恶同源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善恶都统属于正法的范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然善恶同源,那么战争也无法清晰地区分正义与非正义属性。史诗中的战争因王位继承问题引起,但史诗提到,老国王持国天生目盲,不宜当王,于是王位由般度继承,可是般度不能生育,必须借种生子(这是当时的习俗,也为后来的法典所承认)。如此一来,持国既然让位,其后代不能继承大统,但般度五子为借种所生,没有王族血统,继位也遭非议。战争因此不可避免地爆发。如果说战争起因已难辩是非,那么因之而起的争战就更是复杂难解。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在开战之前,签订了一个关于战争规则的协议,为进行战争规定了某些准则,以约束战争的某些残忍和疯狂,这寄予了史诗作者的美好愿望,可惜史诗并未提及如何防范单方的毁约。为战争订立文明条约,尝试用文明与理性来约束非理性的战争,这也表明了善恶交织思想的某种深刻性。
《摩诃婆罗多》“糊涂”的方面也比比皆是,这首先表现在内容的驳杂上。《摩诃婆罗多》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共分十八篇,长达数百万字,但其核心只是般度五子与俱卢百子争夺王位的故事,也即《毗湿摩篇》《德罗纳篇》《迦尔纳篇》《沙利耶篇》这四篇,这个情节我们用几千字即可叙述清楚,那么,印度人如何处理这数百万字的篇幅呢?原来史诗采取了话中套话、故事中套故事的框架式叙事结构,整部史诗如同一段漫长的对话,一切故事都被吸纳进来,而且大故事中又穿插进中故事,中故事中又插入小故事。这使得史诗充斥了大量传说,古代“法典”,以及颂神诗歌和神学、哲学等著作。不少插话的内容也十分驳杂,以《教诫篇》为例,这段插话是毗湿摩对坚战王的长篇教诲,它包括对刹帝利与婆罗门教义的尊崇,以及祭祖、斋戒、婚姻法、继承法、业报和轮回等内容,其中有些内容还与史诗其他部分矛盾。例如婚姻法中提到刹帝利娶妻数目是两个,婆罗门可娶三个妻子,但是在史诗中提到,阿周那有四个妻子,黑天娶妻则不计其数,而婆罗门倒常常只有一个妻子。这些插话思想内容复杂,甚至互相矛盾,致使今天的读者经常陷于其中而难以把握史诗的基本内容。而且,众多插话的存在,也在某种意义上混淆甚至淹没了史诗的主干,造成了《摩诃婆罗多》“糊涂”的另一面:史诗主题的含混不明。史诗最初可能由婆罗多民族所作,用于表达对民族英雄的追慕,对民族图腾及神灵的赞颂,以及对敌对势力的诅咒等。但由于印度半岛争战频仍,占领者不断变换,胜利者都喜欢在史诗中为本民族增添光辉,因此史诗中的神祉与传说越来越多,说教与道理越来越复杂,终于使得史诗原本的主题被冲淡,从而呈现出多样化主题阐释的可能,例如正义必胜说,正法观念说,四季循环说,瑜伽修炼说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摩诃婆罗多》“深刻而糊涂”的特点,正是印度人思维模式的某种体现。印度人想象力丰富,善于思考,在远古时期就“创造了不少的既有栩栩如生的幻想又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神话、寓言和童话”[7],其中包含大量关于自然、人生、宇宙的深刻学说。但印度人在一些所谓的细节方面又十分“糊涂”。例如他们习惯以神话传说代替历史事实,直到公元10世纪才有较可靠的史书。直到今天,印度仍有学者按照神话传说来判定史诗成书于公元前3100年①有印度学者依据《摩诃婆罗多》中“在迦利时代和二分时代之间,普五地区发生俱卢般度之战”来推断史诗成书年代。按照印度神话传说,迦利时代开始于公元前3102年,黑天死于迦利时代的第一天。又按照史诗的故事,般度族五兄弟在黑天死后升天,而毗耶娑在般度五兄弟死后开始创作史诗,用了三年时间,这样,成书年代便在公元前3100年。用史诗内容推测史诗成书年代本就陷入循环论证,且《摩诃婆罗多》充满神话传说,并不可信,但印度学者安然接受。今天看来,大史诗应是反映雅利安人所创造的印度教社会的,而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是在公元前二千多年。由于印度历史本身能够提供的可靠资料太少,今天只能大致推断史诗或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之间,其间相差800年之久。。印度人对史诗的作者也不关心,史诗署名广博仙人,但他同时又是印度最古老的4部吠陀的编纂者,这4部书与《摩诃婆罗多》根本不在同一时代。但是不少印度学者认为广博仙人是史诗真正的作者,因为他本来就是修道人,而且其本人在史诗中也具有非凡能力,其长寿并非不可能。印度学者用神话传说作为论证依据,显然不符合现代科学精神,而其用作品来解释作品,则有循环论证之嫌,这也显示了印度人“糊涂”的一面[6]21-22。
《摩诃婆罗多》的生成与印度的地理环境关系密切,后者在多方面构成了史诗的发生背景;印度独特的动植物也在史诗中有不同程度的展现,它们在某些时候影响了情节的发展。史诗对印度自然风光的描写呈现出壮美绚丽的特色,给人以独特的审美感受。史诗的生成更得益于印度的历史文化,作为故事内核的王位争夺战直接源自印度历史,由众多插话与故事主干构成的史诗呈现出“深刻而糊涂”的特点,而这正是印度民族思维方式的重要表现。《摩诃婆罗多》成因的社会学意蕴鲜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基本原理。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760-76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47-149.
[3]季羡林,刘安武.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4]季羡林.季羡林论印度文化[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275-277.
[5]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8:70.
[6]刘安武.印度两大史诗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季羡林.五卷书·译本序[M]//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