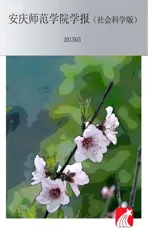论《新青年》派“戏剧改良”运动
2015-12-17范天阁
网络出版时间:2015-06-25 13:03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625.1612.016.html
论《新青年》派“戏剧改良”运动
范 天 阁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摘要:五四运动爆发前不久,《新青年》上演了一场 “戏剧改良”运动,对中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新青年》为材料,再现《新青年》“戏剧改良”现场,从几则广告入手,分析这场运动的前期准备情况;再从几封信为切入点探索《新青年》派戏剧改良背后深层的原因,或许能够在近距离考察的基础上深入对《新青年》派“戏剧改良”的认识。
关键词:《新青年》;《新青年》派;戏剧改良
收稿日期:2014-01-09
作者简介:范天阁,男,河南西华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7.3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3.019
中国现代戏剧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了改造社会、启蒙民众的教化作用。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戏曲改良运动大倡戏剧的社会价值;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要“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1]。中国现代戏剧的“酝酿”与社会、政治的浮沉相上下。文明新戏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发展到极盛,辛亥革命后政治形势急遽恶化,各种封建势力再次抬头,新剧到1914年出现了所谓的“甲寅中兴”,随后,文明新戏渐渐走向衰落。正在此时,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从二卷一号起更名为《新青年》,为表述方便,在此皆作《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胡适、傅斯年等以其为阵地,展开 “戏剧改良”,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新青年》派戏剧改良运动发生的原因进行探寻,研究者往往钟情于社会性考察,在宏大的时代背景和先驱们的大声疾呼中探求其发生的必然性,然而,笔者在繁多的文献中,却发现了其中存在宏观视角难以觉察到的偶然性,试以《新青年》为材料予以阐释。
一、 “戏剧改良”运动的“现场”
《新青年》(五卷四号)上刊载了六篇与戏剧有关的文章,主要可分为二类,一类是以《新青年》派为主的改良派,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胡适)、《戏剧改良各面观》(傅斯年),附文《予之戏剧改良观》(欧阳予倩)及《再论戏剧改良》(傅斯年);一类是以张厚载为主的守旧派,如《我的中国旧剧观》(张厚载),另外一篇是《近世名戏百种目》(宋春舫)。《新青年》派戏剧改良文章的集体亮相,使得此号成了名副其实的“戏剧改良专号”[2]。
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提出的“文学进化观”与《易卜生主义》(《新青年》四卷六号)中提出的“写实主义”,是《新青年》派戏剧改良的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指导思想。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以“门外汉”身份,分别讨论改良旧剧和创造新剧、如何改良与如何创造,他在另一篇文章《再论戏剧改良》的后半部分对剧本的建设发表了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而作为“门内汉”的欧阳予倩则对戏剧改良的办法说得更清楚,在文字方面从剧本、剧评、剧论三方面着手,在培养剧才方面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方案。
由以上几篇文章可以看出,这次“戏剧改良”的主题,已不再是对旧戏的攻击,而是志在旧剧的改良和新剧的创造。
《新青年》(五卷四号)上的论战主要在张厚载与傅斯年之间发生,确切地说,是张厚载的自辩与傅斯年对张厚载的批判。张厚载在《我的中国旧戏观》中主要论述的旧戏的好处有“中国旧戏是假象的”、“有一定规律”、“音乐上的感触和唱工上的感情”[3]等,尤其是第三点,具有针对性地对旧剧作了详细辩护,文章最后说道:“中国旧戏,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社会急进派必定要如何如何的改良,多是不可能。”[3]傅斯年在《再论戏剧改良》一文的前半部分对张厚载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批评。首先是对“假象”与“抽象”的辨析。傅斯年认为张厚载在文中混用了“假象”与“抽象”,使文意不明。傅斯年对这两个词的辨析很有道理,但张厚载的论述未必就混沌不可识,张厚载首句便说:“中国旧戏第一样的好处就是把一切事情和物件都用抽象的方法表现出来。”[3]他引证了六书中的“会意”——“指而可实”,加以说明,此后又引了许多具体的例子,如《四郎探母》、“背躬”等。而傅斯年对两个词的辨析虽然很准确,并且从词的概念出发去理解张厚载的观点,但张厚载的着力点并不在傅斯年所认定的抽象的含义上,结论就差之千里了。傅斯年认为,“上马是一种具体的象,一拿马鞭子,一跨腿,又是一种具体的象”[4],那些动作与物件固然是具体的,但其所指示的内涵并非这些具体的象所能代表的,傅斯年用“代替法”来复述张厚载的“抽象”,但二者在涵义上并不是对等的关系。在这个回合中,傅斯年的理解出现了偏差。第二回合是关于“旧剧有一定规律”是否是优点的辩论。这本是两可的问题,二人各执一端,自各有各的道理。第三回合是关于“唱工”的争议。“废曲用白”是“戏剧改良”运动的主要措施,而张厚载则将“唱工”作为旧剧的一大优点。实际上,这场争论看似针锋相对,最终却成了没有对上话的“对话”。
其实,戏剧的改革很早就进入了《新青年》派的视野。《新青年》的创刊者陈独秀早在1904年即以“三爱”的笔名发表《论戏曲》,阐释戏曲的教化作用。《新青年》先驱者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里,有直言戏曲的,也有未明言戏曲而仅言文学或小说的,但皆包含了对待戏曲的态度。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主张“提高戏曲对于文学上之位置”,“种种恶腔死套,均当一扫而空,另以合于情理、富于美感之事物代之”[5]。最为激进的要属钱玄同,他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道:“至于戏剧一道,南北曲及昆腔,虽鲜高尚之思想,而词句尚斐然可观,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固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有文学上之价值也。”[6]他甚至提出要像废“八股”一样废掉“二簧西皮”[7]。当然其中也不乏中肯意见的,如周作人的《论中国旧剧之应废》。正因为这些文学先驱们从未忽视过戏曲,随着探讨的日渐深入,《新青年》上出现“戏剧改良”的激烈争论和集体呈现也就水到渠成。
二、从几则广告看“戏剧改良”运动前的“热身”
“戏剧改良”运动不仅经历了上述的理论探索积累,而且曾经过一场精心策划的广告宣传。《新青年》(四卷四号)上有一则《本社特别启事》,全文如下:
易卜生(H.Ibsen)为欧洲近代第一文豪,其著作久已风行世界,独吾国尚无译本。本社现拟以六月份之《新青年》为“易卜生号”,其中材料,专以易卜生(Ibsen)为主体。除拟登载易卜生所著名剧《娜拉》(A Doll’s House)全本,及《易卜生传》之外,尚拟征集关于易卜生之著作,以为介绍易卜生入中国之纪念。海内外学者如有此项著述,望于五月十日以前,寄至北京东安门内,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本杂志编辑部,为祷。
这则广告是《新青年》编辑部将《新青年》(四卷六号)作为“易卜生专号”的预告。文中所指出的原因仅有一个,即作为“欧洲近代文豪”的易卜生,“已风行世界,独吾国尚无译本”,将“以为介绍易卜生入中国之纪念”。《新青年》并不是易卜生在中国的首倡者。鲁迅在《文化偏至论》[8]和《摩罗诗力说》[9]中就有所称述;陆镜若《伊蒲生之剧》系统地绍介了易卜生的十一部剧作];宋春舫在北京大学开设“欧洲戏剧”课程,在《世界新剧谭》中推易卜生为“欧洲近世剧家”之“鼻祖”[11]。而应该说明的是,当时鲁迅正留学日本,陆镜若文章只限于介绍,宋春舫的受众大多在学堂,由此先前易卜生在中国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见,《新青年》引介易卜生是在一定的接受基础之上的,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
如果说《新青年》(四卷四号)上的这则广告算是“普通”的预告的话,那么在《新青年》(四卷五号)上的“本志特别通告”就相当“别致”了:
本报现以第四卷第六号为易卜生号,为“易卜生号”以为介绍欧洲近世第一文豪易卜生(Ibsen)入中国之纪念。内有易卜生之名剧《娜拉》、《国民公敌》、《小爱友夫》三种之译本,及胡适之君之《易卜生主义》长论一篇,附以《易卜生传》与其他关于易卜生之论著。读者不但可由此得知易卜生之文学思想,且可于一册之内得三种世界名剧。此为中国文学界杂志界一大创举。想亦为海内外有心文学改良思想改良者所欢迎也。定六月十五日出版,特此预告。
这则广告在目的上与前一则相同,都是为“易卜生号”作推广,在紧邻的两期上刊登,自然会起到叠加和强化的广告效应。而与前一则广告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文字排版”方面的新颖醒目:长短不等行列的顺时针环绕,大小不同的字体字号的间隔错落,很是与众不同,由此也可见倡导者的慎重态度和良苦用心;其次在内容介绍方面,除了介绍得更为具体之外,还对《新青年》开设“易卜生号”这一举动作了高度评价,即“此为中国文学界杂志界一大创举”,而且应当指出的是,这实在是一种自我评价、自我推销。可见当时倡导者们是以何等的热情和豪气来进行引介的。不过此时还并没有提出“戏剧改良”的确切目标,而只是将引入易卜生戏剧作为促进“文学改良、思想改良”的一种途径。
在“易卜生专号”(《新青年》四卷六号)的目录之前,也有一则与《新青年》(四卷四号)类似的《本社特别启事(一)》,拟将“十二月份之《新青年》为‘萧伯讷号’”。另一则《本社特别启事(二)》是暑假后印行《易卜生剧丛》的预告。《娜拉》(《新青年》四卷六号)剧前介绍亦有通告。
可见此时倡导者们有意将引介、翻译戏剧作为长远之计,这种热情和壮志此时正高涨着,正如胡适在《易卜生主义》的引言中所说的那样——“大吹大擂”[12]。
以上都是在“戏剧改良”专号之前所做的广告鼓吹。为了说明“戏剧改良”运动在时间上的完整性,有必要引出另外一则广告,而这则广告正从某个侧面显示了这场运动的“不完整性”。在《新青年》(四卷四号)所预告的“十二月份之《新青年》”(即五卷六号)上的《本志启事一》,其文曰:“本期原定为萧伯讷号。现以译稿未全,拟缓期出版。有负阅者,伏乞鉴原。”在戏剧改良运动高潮中所作的承诺半年后并没有兑现。如果将第一则广告看作此次戏剧运动的“前奏”,那么这则“启事”则可看作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尾声”。至于胡适所允诺的《易卜生剧丛》更是不知所终。从这里可以知道,“戏剧改良运动”虽然是在策划中形成的,但并不是一次周密行动,其间包含着很多偶然性因素,从这一层面来讲,可以说这是一次在总的指导思想(思想启蒙)之下由热情驱动的有始无终的行动。
三、 从几封信看“戏剧改良”运动发生的原因
“戏剧改良”运动在一番“大吹大擂”之后,“剑拔弩张”地发生了。当戏剧经历了一百年的发展之后,拨去历史的尘埃,出现了一个看似非常浅显的问题:作为文化启蒙的《新青年》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戏剧改良”运动?
《新青年》(四卷四号)载文《日本人之文学兴趣》,是一封日本留学生寄给胡适的信,落款为“T.F.C.生”。在这封信里,“T.F.C.生”向胡适介绍了当时日本戏剧的改革情形。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知道几个信息:一、小说戏曲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相当位置,而中国依旧贱视之;二、观剧作评在世界上也已是平常之事,而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到位;三、小说戏曲“有益于世道人心”,对青年有一定的吸引力,可以借以教训和引导青年;四、日本善于借鉴、引介外国戏曲,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对于中国来说,可以作为一个成功之例来借鉴;五、输入新文学、去除旧文学,乃造就新青年、挽救人心之途径。在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体察到写信者的忧国忧时之心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以及与《新青年》同仁同样强烈的改革壮志。《新青年》刊载这封书信,或可说正是“以为然”也。这封信与“易卜生专号”的第一则预告启事同期刊载,置于本号的篇末,两者首尾呼应,无形之中为将要推行的“戏剧改良”运动作了说明和辩护。
T.F.C.生的启蒙想法正与《新青年》派的启蒙意图相合。从《新青年》(四卷五号)上的“特别通知”即可看出戏剧改良作为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的初衷。而“戏剧”并不是文学的全部,为什么在“文学革命”之中会单单出现“戏剧改良”运动呢?《新青年》为什么几乎再也没有出现像“易卜生专号”、“戏剧改良专号”这样目标集中、行动一致的倡导了呢?“文学革命”的口号要比“戏剧改良”的口号要响亮得多。如果将“文学革命”比作一场战役,那么可以说“戏剧改良”只是一次目标比较集中的攻坚战。“文学革命”以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二卷五号)为标志,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二卷六号)紧随其后,又有《我之文学改良观》(刘半农,《新青年》三卷三号)、《历史的文学改变观念》(胡适,《新青年》三卷三号)、《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新青年》四卷四号)等助阵。此外,胡适还写有《论短篇小说》(《新青年》四卷五号),只是并没有后继者或再深入探讨小说改革之类的话题。其实原因倒也简单,早在十多年前,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而此时已有周氏兄弟——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新青年》四卷五号)、周作人在译介方面——大有所为;同样,在诗界经历了“诗界革命”的新诗,不再“旧瓶装新酒”,而是白手起家,胡适本人也已尝试着白话诗的创作。当然,“小说界革命”中的“小说”,“文学革命”中的“文学”自然当包括“戏剧”,只是这些探讨已成为“持久性”的战役,并不像“戏剧改良”那样来得集中、来得猛烈。至于戏剧改革,自晚清戏曲改良运动至文明新戏趋于末路,戏剧的发展此时又走向迷茫,《新青年》派即以一贯倡导西学的作风,揭竿而起。
值得一提的是,一年后《新青年》又刊载了“T.F.C.生”写给胡适的另一封信,题作《论译戏剧》,胡适亦有回信,二者均刊载于六卷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五号)上。此信作于“十二月四日”(当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四日,此信的写作时间与预告取消“萧伯讷号”的时间相近,T.F.C.生的两封信分别刊载在戏剧改良运动的“前奏”和“尾声”,其中意味实在值得揣摩)。信里表达了“对于译剧”的“有些怀疑”,即译剧难以压倒“旧剧”,并且建议“译剧”之后要“演剧”——其实,这正指出了《新青年派》“戏剧改良”运动所缺乏的重要环节。《新青年》译剧令人怀疑之处,或尚不止此。《新青年》上对戏剧的引介,并不是从“易卜生专号”才开始的,《新青年》(一卷二号)即开始连载《意中人》(An Ideal Husband,Oscar Wilde,英国王尔德作,薛琪瑛女士译。分别刊在第二、三、四、六号,二卷二号上,未完)。《新青年》(四卷二号)上有《天明》(Dawn,P.L.Wilde. 刘半农译)。在“易卜生专号”上,刊载了易卜生《娜拉》(A Doll's House,三幕,第一、二幕罗家伦译,第三幕胡适译)、《国民之敌》(An Enemy of the People,陶履恭译,部分,后连载至五卷四号)、《小爱友夫》(Little Eyoff,吴弱男译,部分,后连载于五卷三号,未完)。又载有《老夫妻》(五卷四号,陈衡哲著)、《遗扇记》(五卷六号,英王尔德著,沈性仁译。后载于六卷三号,完)、《终身大事》(胡适)。以上剧作从整体来看,在戏剧内容方面,从翻译引进外国戏剧到自行创作戏剧,《新青年》派对“家庭问题”剧的偏爱是一贯的;思想上的共通性也是胡适《易卜生主义》中所指出的“写实主义”,这对以后中国戏剧的发展影响深远。单从借鉴与创作方面来讲,从“翻译”到“创作”,虽然在“演剧”上留有缺憾,但也可以说,《新青年》派大体上完成了这次“戏剧改良”的基本动作。
开始得轰轰烈烈的《新青年》派的戏剧改良运动,并没有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这次改良运动的实验性和未完成性,必将一直激励着后学。然而对于“百忙中人”及其在运动中所表现的偏激与疏漏之处,我们当持包容的态度,加之考虑到时代原因,“此时不配排演《娜拉》一类的新剧”[13],更不敢因此苛求于先行者们。作为五四运动爆发前夕的一场“启蒙运动”,其思想和历史价值更值得肯定。
参考文献:
[1]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J].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1).
[2]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J].新青年,1918,(5)4.
[3]张厚载.我的中国旧戏观[J].新青年,1918,(5)4.
[4]傅斯年.再论戏剧改良[J].新青年,1918,5(4).
[5]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J].新青年,1917,3(3).
[6]钱玄同.通信[J].新青年,1917,3(1).
[7]钱玄同.随感录(十八)[J].新青年,1918,5(1).
[8]鲁迅.文化偏至论[C]//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52.
[9]鲁迅.摩罗诗力说[C]//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79.
[10]陆镜若.伊蒲生之剧见[J].俳优杂志,1914(1).
[11]宋春舫.世界新剧谭[C]//宋春舫论剧,北京:中华书局,1930:253.
[12]胡适.易卜生主义[J].新青年,1918,5(4).
[13]胡适.论译戏剧[J].新青年,1919,6(3).
责任编校:林奕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