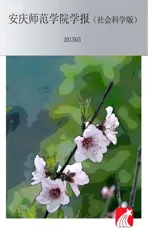《爱妻》的多元叙事策略
2015-12-17刘坤
网络出版时间:2015-06-25 13:03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0625.1612.010.html
《爱妻》的多元叙事策略
刘 坤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小说《爱妻》在叙事手法上大胆革新,通过对话叙事、嵌套叙事以及狂欢叙事等多重叙事手段,呈现了意义多元的文本世界,并表现了美国社会多种族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小说的对话叙事艺术是对拒斥同一性和唯一真理的后现代美学思想的一种呼应,而“未完成”的嵌套叙事带来的开放式结尾和狂欢叙事,折射出任碧莲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东方想象共同体的颠覆。
关键词:任碧莲;《爱妻》;叙事策略
收稿日期:2014-05-10
作者简介:刘坤,女,安徽合肥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712.074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3.013
任碧莲(Gish Jen)是继汤婷婷、谭恩美之后风头最劲的美国华裔女作家。她于2004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爱妻》 (The Love Wife),讲述了一个建立在混血和领养基础上的美国现代家庭故事。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文学界和评论界的关注,被《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评为年度十佳小说之一。美国知名评论家、普利策奖获得者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撰文称“《爱妻》是任碧莲迄今为止最有野心,情感最为丰富的作品”[1]。《爱妻》延续了任碧莲前期作品中关于“何为真正的美国人”问题的探讨。不同的是,此次任碧莲以一种“后多元主义文化”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美国家庭”[2]243。也有学者认为任碧莲旨在通过作品“质疑家庭和民族应当建立在同源基础之上的观念”[3]211。理论界对这部小说的关注,大多集中在移民在文化适应过程中遭遇的文化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和自我认知的焦虑。这固然是解读该作的重要维度,然而,《爱妻》在创作形式,尤其是叙事策略上的革新同样值得关注。
一、对话叙事
《爱妻》是任碧莲沉寂六年之后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作品采用多角度叙述视角,融入莎士比亚戏剧独白的元素,标志着作者的创作生涯进入了全新阶段。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是第一人称叙述者,他们悉数登场,讲述各自的故事。这些叙述声音“时而插入别人的叙述声音中,时而详尽地叙述,时而相互对抗,时而打断对方”,“在各种声音的反复循环中抓住前一次叙述的线索,继而完成他们的故事”[4]8,彰显出复杂多样的对话关系。《爱妻》中对话性叙事技巧首先表现在多重叙述声音之间的“大型对话”(great dialogue)。“大型对话”的概念最初由苏联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巴赫金(M. M. Bakhtin)提出,用来描述文学作品中多重叙述声音彼此难以融合,继而“构成多重看似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意识形态世界”[5]25。巴赫金指出,“大型对话”普遍存在于复调小说中,作家“把整个小说当做一个‘大型对话’来结构”[6]58,其中包括人物和结构的对话,而前者主要表现为人物之间的对话、人物内心的对话以及人物和作者间的对话。《爱妻》的作者完全隐退到小说之外,而作品中人物之间和人物内心的对话则贯穿小说始终。例如第十四章《商》,兰成为有钱人商的情妇之后,不论在性格还是外貌方面都跟之前判若两人。小说通过卡内基、布朗迪、温迪以及利兹的多重叙述视角来表现这一变化。缺少任何一方的叙述,读者都无法看到兰变化的全貌。如果这些变化全部出自一位叙述者之口,不仅难以让人信服,也不会激起读者的好奇。
这一章标题虽为“商”,但是读者对这个人物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卡内基和兰自我独白式的叙述。一般认为,叙述者自言自语式的内心独白不具有元语言学所定义的一问一答式的对话关系。可是这几段独白内部却有明显的对话关系。在兰的独白中,商带她去豪华的餐馆用餐,教她跳舞,教她经商之道,是一个翩翩君子。而卡内基了解的商性格暴戾、劣行斑斑——“曾经杀过一匹马……用大理石质地的飞盘奖杯将电脑屏幕砸毁并将其扔出窗外”[7]294-295。兰认为“商和妻子在一起并不快乐……他很孤单”[7]299,因此甘愿做他的情妇;兰不介意商对她拳脚相对,因为她相信“没人能像她那样让商镇定下来”[7]305。而这一切在卡内基的叙述中则变成,商试图利用兰开拓中国市场,兰与商的关系就像二流电影里的桥段。通过兰和卡内基的轮番叙述,兰建构了一个美丽浪漫的灰姑娘般的故事,而卡内基则将美丽浪漫解构成残暴恶俗。兰继而不断为自己申辩,卡内基则不断提出质疑并加以否定。两种立场、两种价值观的对立和一问一答式的辩论构建了两个叙述声音间的对话。
在小说的单个叙述声音中,最能体现小说艺术张力的是一种隐藏并渗透在小说语言内部的“微型对话”(micro dialogue)。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F. M.Dostoyevsky)的小说时提出“双声语”(double-voicedness)的概念,认为小说语言如果“既针对言语的内容而发(这一点同一般的语言是一致的),又针对另一个语言(即他人的话语)而发”[8]255,则具备“双声语”的特点。在这样的小说中,两种相互争论的声音会进行一场“微型对话”,并以此揭示更深层次的意义。小说中的二女儿温迪的叙述语言便有这种特点。温迪是一个特殊的角色,既没有姐姐利兹的叛逆,也没有弟弟贝利的“亲生子”身份。这个看似无足轻重的人物却是除布朗迪和卡内基以外最重要的叙述者,对推动小说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小说中甚至专门有一章名为“温迪”。
温迪的叙述视角随着小说的发展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小说刚开始时,温迪是王家内向、害羞的二女儿。被领养的身份让温迪感到一种无以言说的自卑。她无法融入同龄人的群体,因为同学们嘲讽她是中国人。但同时她又对自己的“根”——中国,一无所知。身份的困惑导致她自我认同的失败,并强化了她的自卑感。因此,温迪前期的叙述基本是对别人的话语或事件的复述,丝毫没有“我”的痕迹。随着兰的到来,温迪的内心世界发生了转变,尤其表现在其叙述语言上自我意识的增长。小说中有一处,兰向温迪、利兹讲述鸦片战争的故事。当兰反复强调英国对中国的羞辱时,温迪想着:“当她说他们羞辱了我们时,我并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能感觉到‘我们’不是指她和我和利兹。我们指的是她和她的中国同胞,这一点让我很伤心。虽然她说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不同,但当她说他们时,我仍然能听到你们。声音很轻,就像你长时间盯着红色的东西看,猛然抬头看到绿色一样。你们羞辱了我们。”[7]221
这段语言体现了一种“暗辩体”的“双声语”,即叙述者既考虑他人的语言,又将其留在叙述者语言之外;由他人的语言而发,“旁敲侧击,话里有话”[6]64。在这段独白中,温迪的自我意识是以思考兰口中的“他们”和“我们”为背景展开的,听起来像是温迪的自我意识同兰的暗中辩论。小说对兰的话语采用了斜体字处理,似乎在暗示你一言我一语的辩论过程。兰刚来时,温迪将她视为“救命稻草”,企图通过她了解中国,寻找自己的“根”,并以此获得身份认同。这种将文化等同于身份的认识是片面的。了解中国文化、学习中文、取中文名字和中国人的身份之间仍然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眼中的我’总是以‘别人眼中的我’为背景”[8]276,兰无意说出的话让温迪认识到她从内心无法认同温迪的中国身份,也打碎了温迪在文化中寻求身份归宿的梦想。这段独白标志着温迪对身份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巴赫金认为,意义不是“在与环境隔离的思想和纯涵义的世界里”[9]50凭空产生,而是在展现自我和他人意识的有效对话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因此,对话是“生命的最低条件”[8]344。对话也是小说《爱妻》生存的最低条件。在“作者已死”、“文学枯竭”的后现代创作语境下,任碧莲用对话的模式取代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文本的意义不再是作者或某个权威叙述声音赋予的,而是在“众多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8]29的对话中产生。这些声音时而互补,形成更为完整的意义;时而相互对抗,形成引发读者思考的矛盾意义。各个叙述者的自我意识也在对话过程中不断发展,彰显出意义在对话中流动、变化的过程。不论这些叙述声音呈现怎样的对话关系,小说中始终没有统摄一切的声音来赋予这一切秩序或意义,也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意义的终结,使得文本不断衍生出新的意义。
二、嵌套叙事
小说《爱妻》讲述了卡内基夫妇为了获取家书,被迫遵循母亲的遗嘱,将素不相识的中国女人兰接至家中生活,并由此产生的种种遭遇。故事的主线围绕兰来到美国之后展开,其中穿插了几位主人公关于往事的追忆,几乎每个章节都不同程度地被嵌入了关于过去的叙述。过去和现在两条叙述线索的糅合和重叠制造了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但这种“混乱”的背后却是作者巧妙建构的深层嵌套叙事结构。
叙事学中普遍认可小说是“以单一的话语框架包容众多的故事、声音和叙事层次”[10]133,但对于以何种标准来划分叙事层次却说法不一。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一个叙事所讲述的任何事件,在叙述层次上都高于产生这个叙事行为所处的层次”[11]228。因此,作者的叙述是处于第一层次的“外叙事层”,例如《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中马洛直接面向读者,讲述自己非洲之行经历的行为;在第一层次里面讲述的事件,是“内叙事层”,例如《西游记》中每次唐僧被妖怪抓走后,总会出现一位神仙向孙悟空讲述妖怪的故事;比内叙事层更内一层的,热奈特称之为“元叙事层”。当内一层的叙事不断被嵌入相对外层的叙事时,多层叙事便在结构上呈现一种“中国套盒”式的关系。《爱妻》所呈现的正是这种嵌套式叙事结构。
《爱妻》中的故事围绕过去和现在两条线索,形成三层叙事结构:外叙事层是卡内基、布朗迪和兰共同生活后发生的故事;内叙事层是这三位叙述者对往事的追忆,即王妈妈去世前的事以及兰在中国的经历;王妈妈的故事则是元叙事层。这三层叙事皆由王妈妈过世后留下的一本神秘家书联系在一起。为了得到家书,卡内基必须先执行王妈妈的遗愿——接兰到家中生活,这才有了后面的故事。从小说第一章的标题可以看出,“兰来了”表示故事的开始,也是外层叙事的开始。在这层叙事中,卡内基一家的叙事声音是受到限制的。尽管他们叙述着兰在美国的生活,但除了“王妈妈的中国亲戚”的身份,他们和读者一样,对兰的背景一无所知。表面上看,兰在王家做着保姆的工作,但她和女主人的相互“敌视”、和男主人的暧昧关系都超越了一般意义上保姆的范畴。
通常故事层的疑问不会在故事中直接被解答,而是被搁置和刻意回避,直到次故事层来“回答诸如‘是什么事件导致了现在的局面’之类的问题”[12]166。通过分散、多次的嵌入叙事,兰向读者和卡内基一家诉说了她的故事。兰本是苏州大户人家的小姐,却因为“文化大革命”失去一切。她目睹父亲死于红卫兵之手,之后被发配到黑龙江一个偏僻的农村,在那儿受尽折磨。兰的叙述似乎正解释了她在美国的种种行为。为了弥补父亲的缺失带给她的伤痛,兰试图在美国找到一个能像父亲一样保护她,让她重新过上体面、舒适生活的男人。所以,兰先和男主人建立一种暧昧的关系,甚至尝试勾引他。而当一个比卡内基更有希望让她“过好日子”的商出现时,兰便甘愿做商的情人,甚至忍受他的暴力行径。当这段关系破灭后,兰只好下嫁给商的司机苏先生。而在丈夫意外地葬身火海后,怀有身孕的兰为求一份安全感,不惜破坏别人的家庭也要留在卡内基身边。
与兰的叙事同时嵌入外层叙事的还有布朗迪和卡内基的内层叙事。在这一层叙事中,布朗迪讲述了她和王妈妈间紧张的婆媳关系。布朗迪的疏忽导致了王妈妈的意外死亡。这一事件带给布朗迪的愧疚和不安,让她“合理”地把兰建构成她和卡内基婚姻关系中的假想敌,即兰是代替王妈妈来惩罚和报复她的工具。当看到兰与丈夫、女儿们相处得十分融洽时,布朗迪越发确认自己的设想,认为兰终究会代替她的位置。布朗迪的嵌入叙事和她在外叙事层主动为兰介绍男友,主动放弃工作来照顾家庭,当丧父又有身孕的兰“无辜”地投靠卡内基时以离婚来威胁卡内基等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元故事的事件和故事的事件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11]232。同样,卡内基在内叙事层“书写”了他和母亲之间深厚的感情。母亲的突然离世对卡内基而言无疑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创伤。对于王妈妈在遗愿中坚持将兰接至家中生活之举,卡内基同妻子一样,将其理解为兰就是王妈妈的替身,是母亲生命的延续。由此,内叙事层解释了卡内基和兰之间“越界”的情感关系不单单是移民“身份流动和易变的象征”[13]74,更是卡内基安度创伤、寻求内心慰藉的方式。
内叙事层尽管解释了兰和卡内基、布朗迪之间复杂的三角关系,但王妈妈让兰来到王家的真正原因依然困惑着几位叙述者和读者。正是这样才有了叙事继续发展的需要。虽然卡内基在内层叙事中已经交代过王妈妈的美国奋斗史,但那仅仅是通过卡内基的有限视角看到的故事。小说元叙事层中出现的家书揭开了卡内基的身世之谜——兰才是王妈妈的亲生女儿,卡内基则是被领养的。家书的内容通过香港亲戚的一封信和卡内基的叙述间接地呈现给读者和其他叙述者。“有些次故事层的叙述,不论(或几乎不论)其内容如何,单靠叙述行为本身就能维持或推进第一叙述故事中的行为”[12]165。小说中的元叙事层虽然仅有一段文字,却立刻对外层叙事产生了“行动”效应——卡内基当场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抢救。但不同于内叙述层全面实现的“阐释”作用,元叙事层并未完成其“行动”功能。换句话说,家书虽将卡内基“送进”医院,对布朗迪或兰却未产生任何效应。随着身世之谜的揭晓,他和两位“爱妻”——布朗迪和兰之间的矛盾理应得到某种和解,可小说就在此刻戛然而止。未完成“行动”功能的元叙事层使得读者无法从叙事中得到小说的正解。因此,小说中层层相扣的嵌套叙事最终指向一种结构的开放——反映在故事层面就是小说开放式的结局。
三、狂欢化叙事
《爱妻》中的王家,不同于任碧莲前期作品中典型的移民家庭。王家有亚裔也有欧裔,是一个融合了领养、混血、移民多重元素的现代美国家庭,代表着“美国的新面孔”。因此,王家成员的对话不仅仅是小说中人物的对话,也象征着美国社会中代表着不同种族身份的群体间的对话。小说中的对话既有和谐互补式的协奏曲,也有对抗式的争辩,象征着美国社会多个种族、多重文化间时而和谐共存时而对立冲突的相处模式。因此小说中的对话叙事或嵌套叙事结构表现出的多元意义不单局限在文本层面上,更是对美国社会的复杂现实的一种隐喻。小说中几处狂欢化的叙事不仅进一步强化了文本意义的多元,也加深了现实的复杂性。
狂欢是一种狄奥尼索斯式的酒神精神。在狂欢生活中,“原来的生活形态,道德基础和信仰全变成了腐烂的绳索,人的两重性,人的思想的两重性,此前一直隐蔽着,这时全暴露出来,不仅人和人的行为,就连思想也从自己那些等级分明的封闭的巢穴里挣脱出来,在绝对性的对话(即不受任何拘束的对话)的亲昵氛围里相互交往起来”[8]222。通过狂欢仪式,不平等的规矩或秩序被颠覆,对话被“脱冕”,狂欢的文化本质才能实现。卡内基和布朗迪的婚礼便是一场典型的狂欢仪式。在仪式进行时,向来反对异族通婚的王妈妈暂时将种族偏见至于一边,表现出超越种族身份的“宽容”。婚礼上的宾客也都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诚地对待王妈妈。双方的互动和调侃宛如一家人般的默契。王妈妈在狂欢氛围中的“异常”表现让读者看到即便是最有种族偏见的人也有推动种族大融合的一面。小说结尾处颇具狂欢色彩的一幕也意味深刻。在获知卡内基得救的消息后,布朗迪和兰激动地搂在一起,“兰紧握着妈妈的手,妈妈也握着她的手”[7]379。此刻的她们不是“情敌”,也没有文化、种族身份上的对立,发自肺腑地为卡内基的“新生”狂欢着。
虽然人物在狂欢叙事中经历了瞬间的变形,营造出“世界大同”的美丽图景,但任碧莲并没有通过狂欢仪式清除王家的矛盾,统一他们的思想,取消他们的独立。故事的最后也没有一个唯一、终极的观念来整合这部小说。狂欢结束后,王妈妈依然不接受布朗迪做她的儿媳,布朗迪和兰依然貌合神离,正如布朗迪的祖母常说的,“这个世界一会儿一个样儿”[7]379。人物在狂欢仪式中表现的其实是人性所共有的情感体验。通过狂欢叙事,任碧莲似乎在提醒读者,小说中的人物不仅仅只有主流意识形态赋予他们的种族、文化等附加身份。他们最根本、最重要的身份还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具有共通的人性。
《爱妻》是任碧莲在创作技巧上的一次重要革新。在多重叙述声音间的“大型对话”和叙述声音内部的“微型对话”中,“世界的独白型单一主体性被克服了……每个主人公都成了永不完结的对话中的一种声音和立场”[8]347。表面上看,小说似乎从对话中开始,又在对话中结束。但开放式的结局意味着对话并没有结束,甚至可能成为下一轮对话的开始。通过对话叙事,小说展现了一个“多元的世界……这里不只有一个,而是有许多个观点……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复杂的多声的统一体中”[8]347。多重主体间的对话使得《爱妻》的“首要构成成分是对立而又相互修正的社会声音组成的多重性,不可能分解为明确的独白的真实性”[14]129,是对强调异质性、拒斥同一性,强调无调性、拒绝唯一真理的后现代美学思想的一种呼应。“未完成”的嵌套叙事和狂欢叙事导致的文本意义的不确定和多元则是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东方想象共同体的颠覆。
任碧莲刻意让文本的意义复杂化、多元化,其目的就是要呈现美国社会中多个种族间微妙、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远不是反抗-压迫的二元对立关系可以简单概括的。没有结局是小说最好的结局。读者期待卡内基在“爱妻”和“爱妾”之间做出抉择,正折射出被贴上族裔作家标签的任碧莲陷入窘境。如果卡内基最后被推出病房,做出非你即我式的选择,则表明任碧莲接受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鼓吹的单一性和中心化的价值体系,也就陷入了东方想象共同体的话语范围。如此一来,小说可能会沦为另一个为少数族裔“言说”的政治文本,其艺术性也会因此受到影响,而这正是致力于和族裔身份保持距离的任碧莲不想看到的。诚如任碧莲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为自己“申辩”:“这像是人们的一种应激反应:‘你是族裔作家,那么你一定要写人们如何保护(本族文化)传统’。我倒不是说我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和去保留或去承担什么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只是觉得我的作品里还有些其他东西”[15]114。
参考文献:
[1]Kakutani, Michiko. World and Town—A Novel[N]. The New York Times, 2004-09-07 (6).
[2]Partridge, Jeffrey F.L. “Review Essays, Adoption, Interracial Marriage, and Mixed-Race Babies: The New America in Recent Asian American Fiction”[J]. MELUS: Pedgogy, Praxis, Politics, and Multiethnic Literatures, 2005(2): 243.
[3]Jerng, Mark C. Claiming Others: Transracial Adoption and National Belonging[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211.
[4]Anshaw, Carol. “The 21st-Century Family”[J]. The Women’s Review of Books, 2004 (2): 8.
[5]Gardiner, Michael. The Dialogics of Critique: M. M. Bakhtin and the Theory of Ideology[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25.
[6]程正民. 巴赫金的文化诗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8, 64.
[7]Jen, Gish. The Love Wife[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4.
[8]M. M.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第五卷:诗学与访谈[M]. 白春仁,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9, 222, 255, 276, 344, 347.
[9]王建刚. 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50.
[10]Lanser, Susan S. The Narrative Act: 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81: 133.
[11]Genette, Gerard. Narrative Discourse[M].tr. By Jane E. Lewi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228, 232.
[12]施洛米丝·雷蒙—凯南. 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M]. 赖干坚,译.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165-166.
[13]Friedman, Natalie J., “Adultery and the Immigrant Narrative”[J]. Multi-Ethnic Literature of the U.S., 2009 (3): 74.
[14]M. H. 艾布拉姆斯. 文学术语词典(第7版)[M]. 吴松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29.
[15]Matsukawa, Yuko & Gish Jen. “Interview: Gish Jen”[J]. MELUS: Asian Perspectives, 1993(4): 114.
责任编校:林奕锋
Multiple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The Love Wife
LIU K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aug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Abstract:The Love Wife Iis a novel with innovative narrative skills. With its multiple narrative strategies such as dialogic narrative, embedded narrative and carnivalesque narrative, the novel exhibits a world of text with uncertain meaning as well as the subtle and complex relationship among various minority groups in the American society. The dialogic narrative responds to such postmodern aesthetics as the rejection of sameness and the denial of absolute truth, while the open ending resulting from the “unfinished” embedded narrative and carnivalesque narrative suggest Gish Jen’s critique of western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subversion of eastern imaginary community.
Key words:Gish Jen;TheLoveWife;I narrative strateg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