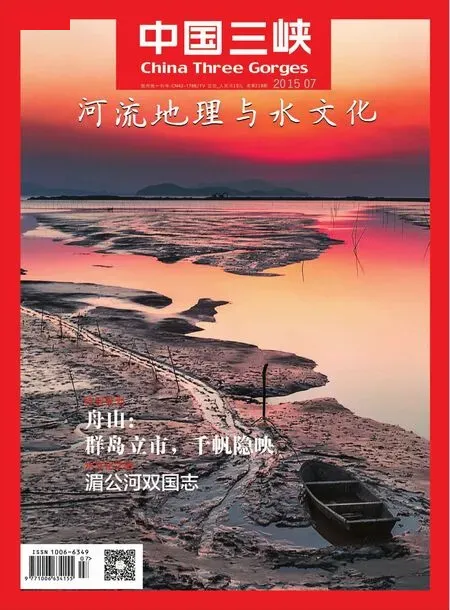斧凿声里的朱家尖
2015-12-16朱红萍编辑吴冠宇
文/朱红萍 编辑/吴冠宇
斧凿声里的朱家尖
文/朱红萍编辑/吴冠宇
古老的东京城,早已沉入远古的记忆深海,它回光返照的景象,也成为海面上偶尔露出峥嵘的“移城”奇观。然而,时间的潮流却将它的美丽情韵注入了这块宝地;人性的激情随着一波一波的时代涌浪,苏醒和复活了文明的潜质。
朱家尖,是舟山群岛1390个岛屿里的第五大岛,74万平方公里岛域独拥3万亩海岛平原,是一块未经刻意修饰的海岛湿地,纵横着日渐萎缩的河流,散落着随性放置的绿地,其间有鸥鹭翩飞、栖息。这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海岛,安然地,如一枝青荷娉婷,伫立于波澜蔚然的东海洋面,惠风紫涛的莲花洋畔,与海天佛国普陀山一衣带水,慈悲交响。
朱家尖,古称“福兴岛”、“马秦山”、“佛渡岸”等,明嘉靖后始称“朱家尖”,据说因为最早住民姓朱而得,还留下了“至今何处问朱家,只剩山间水一涯”的诗句。这次出行,真的是突然兴起,想在朱家尖还未被斧凿锤击成国际旅游岛前,在它独具海岛特色的自然风光外,去寻访那些被时光掩埋或遗留着的人文残片。这样一念而起,拉上忙碌的水风先生驾车,直扑“残片”而去。尽管是土生土长的岛上人,也貌似上演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满眼的绿,并未掩没“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层峦叠嶂。寥落的几声鸟鸣,更显青山寂静。
大青山,披着嫩绿墨绿的色彩,夹着丛丛粉红深红的杜鹃,正在暖风中起伏。晌午的太阳出奇地好,带着春未远离夏未至的温暖,都能听到富有质地的阳光照射下来的“叮咚”声了。山腰处,穿过一条槟柃树和杜鹃花簇拥的“南雁崖”小径,闯破两道洁净的蜘蛛网,到达一处观景台。面对眼前的海山,不仅有“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感怀,更有豁然俯瞰最为完整的五大沙滩——十里黄金海岸线的壮美。
此刻,我和水风是唯一的闯入者,把整座青山独揽。满眼的绿,并未掩没“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层峦叠嶂。寥落的几声鸟鸣,更显青山寂静。风挟着阳光拂来,带着清凉的温暖。我怀想起未遭开发的古时大青山了,据说那时曾有人隐居山上,他会选择山的何处落脚?又为何选择此山隐居呢?
他是指宋朝名臣黄龟年。《延佑四明志》记述秦桧第二次任宰相之后,黄龟年遭到弹劾,“龟年寓湖州,桧摭其过,押使回福州,后居昌国之马秦山,多为记文,与兄岳年同隐焉。山有石,面平五丈,与僧马耆、处士张光赋诗于此”。据考,黄龟年在马秦山可能隐居了近十年时光!
有一篇《解读〈题马秦山图〉兼谈宋元之朱家尖》(作者胡永久)的文章提及黄龟年隐居地“高台似掌广堪坐,千峰相抱宽可宫”的诗句,并根据“今朱家尖大青山景区有一方巨岩,状若平台,可容数十人坐卧,应是诗中所说的‘高台’了”一句推测出:当年黄龟年应隐居在朱家尖大青山。而文章同时又提到“绍兴初,黄龟年到普陀山,作《宝陀山观音赞》,有‘朝发东秦岸,须臾达莲宫’之句。‘莲宫’是指观音莲座所在地普陀山,而‘东秦岸’很可能指的是马秦山的东岸。”这令我对黄龟年隐居地持疑。
大青山在朱家尖的西南角,决非“东秦岸”,从大青山出发也不可能“朝发东秦岸,须臾达莲宫”。此刻,我站在大青山上,遥望如今朱家尖东北方向,那座如莲蓬舒展的“大平岗山”,它的所在地沿袭着“莲”的称谓,叫香莲村,附近地名至今留着浓浓的“佛”意:关爷殿、朝阳洞、修竹庵、金竹庵、佛手庵……大平岗山的入口处曾有一座庵,庵门口有一荷花池,铺着长长的红石板,大平岗上有朱家尖最大最平的大石头,还有一口井,井在石缝中,井水长年不枯竭,只是找不到当初的“下马墩”、“歇轿岩”。从大平岗脚下的某个码头去隔海相望的普陀山,倒是“须臾达莲宫”。
我来大青山是寻访宋时名臣的隐居遗迹,却不知为何将视线遥望到了另一山头……如若当初,你也将此山隐居成了“终南山”、“桃花源”,估计就不会再有我当下的“身在青山,心系平岗”了。时光流逝,总能无声无息地将一切淹没,唯有你曾来过的记载,成为一段随风而去的历史记忆。
“岗峰斜峙双华表,溪水周流一港环”,道出了筲箕湾“山环水绕,脉大气大,砂水为用,藏风聚气,气局两全”的吉地之势。

朱家尖岛凉帽潭晒盐场景。 摄影/蒲斌军
筲箕湾,就在大青山西麓,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形似农家用的筲箕,因此得名。这里有200多座石墙屋民居,错落有致地簇拥着,抹着老旧的浅灰色时光,坐落在群山绿林的怀抱之中,和村前静美壮阔的海湾组合成一幅绝美的山水,带给人一种凹陷的视觉冲击。走在这些石屋的小巷小弄间,发现坐在屋檐下的,或晒在阳光里的,大都是些带着褶皱的脸,似要睡着般静默着。整个村子也在山风中,细微地安静着……
只有当回望这个被称为“普陀第一古渔村”历经的旧时光,你才会在时空深处,听到它曾经的喧嚣和繁华。“岗峰斜峙双华表,溪水周流一港环”,道出了筲箕湾“山环水绕,脉大气大,砂水为用,藏风聚气,气局两全”的吉地之势。村落的先民择此处落脚,是有根源的。

朱家尖七星寺。 供图/朱红萍
村口那条被岛屿拦起的海道,就是被称为“海丝驿站”的乌沙水道,自东向西绵延不尽,自古到今奔流不绝,它哺育了村落最早的文明,从秦汉至明清,始终是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这条古老的乌沙水道,曾迎送过多少风雨中的身影,走进历史深处:徐福率三千男女东渡,鉴真东渡日本弘法,真如法亲王来大唐求法,著名的海上贸易家、航海家张保皋、朱克熙等来往于中日之间……筲箕湾成了南来北往者休整续行的据点,离家或返乡的驿站。这个乌沙水道更被寄予一种浓浓的乡愁,乌沙港畔留下他们驻足远眺的背影。
宋元时期,随着大批商船、渔船在乌沙门往来,筲箕湾成为自然天成的渔需品补给基地,官府在此设立“砂岸(似现代渔港)”,专门管理船舶和税收等。如今看来那么小的一个渔村,曾是那样“辉煌”……类似像筲箕湾这样的千年“砂岸”遗址,在当地极为罕见。在筲箕湾嘴头处,还有一处樟树庙古迹,里面供奉有观音、财神、土地公及身披霞帔、头戴凤冠的“天后娘娘”等。据传,约清咸丰年间,村民在筲箕湾沙头拾得一尊木雕妈祖神像,并移至嘴头设坛奉祀,后来乌沙门水道两旁建起了多座妈祖宫庙。至今,樟树庙成为唯一遗存,而妈祖信仰已成为一种心灵契约穿越时空。
两株两抱大的柏树在寺院门口枝繁叶茂着,进出山门有平石板铺成的道地,大殿内供奉的菩萨好像并不多,两旁的厢房倒是有好多间,整个寺院掩隐在树林中。
七星寺,掩隐在朱家尖寺岙村四柱山的绿荫里,它傍山依水,在一弯绝佳的山水里,背靠的四柱山峰峦叠嶂,逶迤起伏,山势陡峻,状如“北斗”,就知寺名由来了。两百多年来,当地人口口相传着“先有七星寺,后有寺岙村”的说法,这是对一座庙宇经久的敬重和感恩。
当我们沿着沙滩边缘的环岛公路,驶经碧波微漾的小田湾水库,专程拜访它时,一时吃惊于它的变化。眼前仿清的七星寺建筑已在中轴线上耸立起天王殿、大雄宝殿,两旁三层楼的厢房正在扩建,将原本犹如民房般老旧矮小的建筑撇在了两旁树丛中。据记载,七星寺于清康熙年间,由普陀山白华庵僧兴建。据普陀山《白华庵筑塘碑》记载,清嘉庆年间,七星寺有“祖置田产三百余亩”。清末至民国初期,白华庵在朱家尖有耕田地800余亩,寺院有山门、大雄宝殿、厢房等殿屋20余间。建国后,香火渐淡,僧众离散……直至1992年有居士顾信岳等人重建七星寺大雄宝殿三间,并从水库左侧挪移至右侧。这期间,七星寺也历经世道变迁。
这让我回想起父亲记忆中的七星寺,那时他才十一二岁,应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两株两抱大的柏树在寺院门口枝繁叶茂着,进出山门有平石板铺成的道地,大殿内供奉的菩萨好像并不多,两旁的厢房倒是有好多间,整个寺院掩隐在树林中。寺院后面是一片大大的竹林,很清静,竹林里放养着山鸡。七星寺住持与当时普陀山白华庵黄袍子方丈是师兄弟,俩人都是清瘦模样。方丈瘦小些,住持瘦高些。他们与我爷爷是朋友,每年都要往来。我的父亲叫住持为师公,每到笋长出来的季节,他都要一捧捧地拿来送到我家。
这么一恍惚,竟有了隔世的感觉。现在的住持常宏法师于2010年在上任住持惟定法师过世后接任。约定了见面,看着他掸着身上的灰,从大殿右侧的在建楼中走出来。随着他的指点,看到古朴而高大的大雄宝殿内,透着原始本色的一抱多的山樟木柱顶着大梁,其间唯有木榫衔接,不见一枚钉子。殿里供奉着药师七佛,对应着七星寺名。大殿后面是一尊浙东地区最高的木雕喷金阿弥陀佛,背靠四柱青山,站立于天地之间,尽显庄严、雍容、祥和与安然。面对他的微笑,心灵渐入一种至纯至柔至静至美的境地。药师佛主管当下人世,阿弥陀佛主管往生世界。生与死只隔一道门槛,只在一步之遥。这样的供奉与构架,在庙宇中都是极少见的吧。
东沙洋面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又该去哪里寻觅“塌东京,涨崇明”的传说呢?
东沙滩,在岛的东南边,当我们赶到时,太阳已经偏西。沙滩上游人依旧成群,紧临东沙滩的五星级大酒店“绿城•威斯汀”草坪上,还有围坐在一起玩牌的人。在这类似海滨浴场的氛围里,东沙洋面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又该去哪里寻觅“塌东京,涨崇明”的传说呢?
据《国家海岛生态公园朱家尖》一书记载:村前的东沙,春日多雾天,人行滩上,时常只闻涛声而不见浪潮,东沙就显得很是飘渺神秘;晴朗天气的清晨,站在东沙滩上观日出,碧海丹阳,壮丽无比,“东沙涌日”为十里金沙中的一大景观,历来吸引着千万游人。据民间传说,朱家尖岛东边不远处,相传为古“东京”城池所在地,至今,在东沙滩前仍能挖到石柱、城砖、泥煤等古代遗物。东沙村民也曾看到在海的远处浮现出亭台楼阁,还有身着盔甲的古代骑士,在城楼下跃马横戟和大队兵马游动的奇异景象。
说到这一奇观,村民谓之“移城”,也就是海市蜃楼的民间说法。东沙村民胡文雅曾印证说,她小时候亲见“移城”奇观,后来还常在村子的地下8米处挖出大树根、碗、盆、小酒瓶等,挖出来的黑土(泥煤)晒干了能当燃料烧饭。结合这些文物推测,远古时这里很可能就是“塌东京,涨崇明”传说中后来塌陷下去的城池的组成部分。在当地老人口中,还留下过将来要“失崇明,还东京”的古话。
古老的东京城,早已沉入远古的记忆深海,它回光返照的景象,也成为海面上偶尔露出峥嵘的“移城”奇观。然而,时间的潮流,却将它的美丽情韵注入了这块宝地;人性的激情,随着一波一波的时代涌浪,苏醒和复活了文明的潜质。于是,我们看到,今天的东沙不再落寞如单调的涛声,而是已经生长出了一个崛起中的“新东京”雏形。
濒海临风的“绿城•威斯汀”,酒店后面崭新的样板新农村“东荷嘉园”,和绿意盎然的山坡上一幢幢别墅,不正在应验着“还东京”的预言吗?当朱家尖建成为国际旅游岛,岂非就如曾经繁华的东京重返世间?
流年似潮。有多少曾经的岁月都已流失在时空深处,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口口相传中,演变成传说或传奇。远古的东京只留给人们一个苍凉美丽的剪影,但东京当年的繁华,已置换成美好生活的憧憬,多少年来一直存活在东沙人的记忆深处,未曾随眼前的东沙浪潮退去。
这时,听到一声略带惊呼的轻喊:快看,天上,那朵七彩祥云是咋回事?顺着水风手指的方向,确实,朱家尖岛上空,一朵令人欣喜的七色云彩正挂在前方。这一块如丝绸般的七彩祥云,似一朵投映在天幕上的佛光,仰头遥望时,内心竟生出一种无名的愉悦和美好!
回头看到西边山顶上的太阳,带着温和又桀骜不驯的光芒,斜照着整个朱家尖岛。试想,千万年前,它照见的这个海岛一定不是当下模样,那时,这里也许还是一片汪洋。就在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的时空间,一个个绿岛渐渐浮现,一个个先民渐渐到来,历史才有了陈述的可能,人文才有了遗留的缘起。今天,我们行走的只是岛的一侧,而在另一侧还有更古旧的讲述。

左上、左下:朱家尖月岙夕照。摄影/杨海峰

右上:朱家尖滩涂赶海人。摄影/杨海峰

右下:朱家尖东沙晨景。摄影/杨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