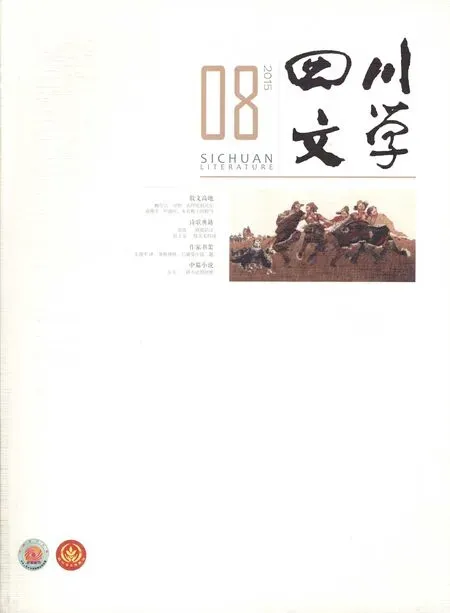关于乡村的七段札记
2015-12-16○唐棣
○ 唐 棣
一、姥姥与蛇
上磨坊磨麦子看见两条大蛇在碾上盘群,敢二话不说搬石头砸下去,足以说明姥姥之前是不怕蛇的。
这事发生在秋后,家里的粮食少了,姥姥便决定走一趟磨坊。临出门,让姥爷扛出了一袋麦子,然后她独自推上独轮车去了村东。她回来,姥爷没发现不对劲,上前扛下打好一袋的面,往屋里走去。而姥姥转身便走。还完了邻居的独轮车,再回到家,一家吃完晚饭天便黑了下来。
转天,差不多也这时间,姥爷从生产队赶马车归来,问闺女,你娘哪去了?我母亲当时年纪尚小,手指远处,说了半天,话在嘴上一断一续,“西、西边、西。”姥爷出门追向西边。那有一条大路,姥爷就是在那条路上最后追上姥姥,等她不挣扎了,再把发过疯的姥姥扶回家的。
第二天,作为生产队骨干的姥爷请了假,姥姥做着针线,发出埋怨:“这损失多少公分啊。你老盯着我看嘛!”
姥姥的眼神开始是平静的,后来就开始不对劲了。从手上的针线活转移到墙角,然后柜底、墙缝等等。姥爷上前问,你咋?姥姥的身体这时也在姥爷手里变得像一块铁锭子一样。按说,姥爷是老车把式,平时摆弄骡马。这次使出浑身力气,还是让姥姥冲出阻拦,破门而出了。
这消息很快传遍村子。在那个年代的乡村,癔病一般离奇古怪,更无药可救。姥爷找了几个风水先生,前后一说,他们一般给不出啥说法,只是忙着掐手指,等我姥爷走了,才跟旁边的人小声嘀咕:“命里都写着呢……”有的人把这些话透给了姥爷。姥爷还问,没有说别的?那人不说话了。他知道,算命先生的话时常说一半;他也知道,朋友在这件事上的话,也不太好说。
姥爷每次把姥姥从西边路上扶回来都累得连呼带喘。等姥姥的眼神不再飞转,姥爷才会轻声地问:“是不是看见啥了?”姥姥有气无力地说,前天去磨坊看见一对蛇。
姥爷总结出姥姥发病的特征:一是在日头平西时,一个沿大路往西,见水便停。姥爷心里就怕姥姥万一顶着邪气投了水。那些天,头沾枕头就睡的姥爷睡不着了,就想问题出在了哪里。有哥几个提醒说,向西跑,西面有啥?还有,知道姥姥得了这样怪病的乡邻也来探问她在西边到底看到了啥?“西”在中国传统中与冥界有关,所谓“西方大道”、“驾鹤西游”等。姥爷不敢想这些让人后脊发凉的东西。
这事让一个平时没什么人知道的农妇出了孬名。姥爷安慰她,她哭着,不听。一天,正是快黄昏时,姥爷从外面急匆匆赶回家,进屋看见姥姥的面前摆着一段绳子。
“赶紧把我捆上。”姥姥把身体凑上去,“省得我出去丢人!”
头几次,姥爷不舍得把绳子勒太紧,姥姥曲折起身子,一团一拱,差点钻出了绳套,吓得姥爷赶紧上来按住她,搞得两人一晚上累得爬不起身(第二天姥爷还要去出工)。后来,姥爷下了狠心,拿出了绑牲口旳绳法。
将近一个月每天日头平西时,姥姥都会被绳子捆着。我母亲都看在眼里。她说,捆也不老实,急了还伸舌头,颠屁股,整个人由炕头颠到炕尾,嘴上不闲着:“累死你,累死你!”
熬到天黑,姥姥整个人便会瘫软在炕上,活像蜕了一层皮。看这样子,姥爷咬牙舍得捆是对的。按姥姥恢复正常后的话说,便是“那不是我,那是一条蛇。”
这段生活发生在我母亲七八岁时。至于后来,姥姥为啥忽然不疯跑了和开始怎么便疯跑起来一样,没人解释得清。发生过这事,姥姥是不是也怕了蛇,还是没人知道。
二、母亲与蛇
母亲听到有人说蛇都会浑身发抖。她小时候家里贫困,活计也多,上了一年级便辍学了,姥姥让她喂猪放羊,小小的母亲很早便担起了一大家子的责任。有时,家事多杂,干完了,羊们等得急了。咩咩叫得人心烦。姥姥一心烦便骂人。母亲赶紧趁别人吃午饭时赶羊出门。
日头最烈,地面烧着脚丫。羊们不劳指挥,自己闻着草味撒开了步子。母亲一路小跑追到一片坟地边的草地。晴天白日,羊们在吃,母亲也不觉得害怕。正午时分的坟地上一丝风都没有,似乎更热。倚一棵树,看了一会儿,她觉得头晕。
等再睁开眼,几只羊已跑到远处的坟头上。母亲喊它们,它几个偏不听,拿出了一股犟劲,越喊越往坟地深处走。母亲只能趟草追了进去。他们还展开了拉锯战,为首的山羊是平时母亲最不喜欢的那只。“果然是你作怪,”母亲心想着,“回头,非拾掇你!”
快抓住山羊时,只感到脚背一阵凉,像一条河水做的绳子一样从草间拽了过去。母亲也没在意,打了个激灵,眼下制服那头山羊才是重要的。没想到,一来二去,天色有些晚了。山羊被擒后的态度是良好的,低头认罪一路没抬头,直到进了羊圈还在反思。姥姥问,你上镇上放羊去了?母亲没搭话,赶紧关好篱笆门,进屋洗菜,准备做饭。做着做着,母亲一头栽在了地上。
她一睡便一星期,每天只喝一点水。姥姥回想闺女昨天放羊回来的样子,便猜到了。紧忙下炕去。姥爷问:“去哪?”姥姥说:“折桃树枝去。我记得,好像三婶子家有棵桃树的。”
三婶子家的桃树差不多枯死了,还好只剩了一根枝。她跟姥姥说:“拿上,我再告诉你一套法。”从她家出来,转天正午时,姥姥的叫魂声便开始在那片坟地边的草地上飘荡了。她一只手拿着桃树枝,一手拖着一碗水,叫着母亲的名,围着草地走七圈,然后给母亲把那碗水喝下。
第一天,母亲没任何反应。二天,姥姥顶着日头又去。姥爷不信这些,不过自打姥姥得过那次癔病后,也不特别阻拦。他想,过几天闺女不醒,便上医院。巧的是在第三天头上,母亲睁开了眼。
“醒了,你快别去叫了。”
姥爷说着,姥姥瞪了他一眼,转过头,眼睛又透过窗口,看看日头,等位置到了天的正当中,姥姥啥活计都会放下。我们村里的很多人都回忆说:“那年,气温最高,老太太晒得跟土一个色,愣是又把闺女的魂叫了一星期。”老话说,(魂)在身上黏得死死的了,姥姥才罢手。
这些事据母亲说,记不大清了。我把一些人的讲述读给她听完,只问她,是不是打从醒来,便再也听不得,更见不得蛇了?她不晓得该说什么。
三、我与蛇
作为我们那儿出名的捕蛇少年,我觉得被咬是迟早的事。别人不这么觉得,尤其当母亲得知我被蛇咬了以后,从两里地以外的厂子一路哭回来,一把抱住我时,我都没搞清她怎么这么爱哭。当时,我好像在上小学三四年级,这条比我胳膊粗的蛇是我费了很大劲才从一座坟前的洞里拽出来的。我不曾想到它敢跟我动嘴。咬了我,我一点事没有。一路走回家,没多久,一放学回家的小伙伴们便带着他们的家长来了。
母亲回到家时,我家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我早被他们问烦了,没有疼痛的感觉,也不觉得豆粒大的伤口镶着一圈紫色的边儿有啥大不了的。
母亲风风火火地带我去了乡卫生院。一进门便跟医生喊:“我儿子被毒蛇咬了。”搞得那个时间本来安静的医院热闹起来。看到医生给我处理伤口时的表情,和听他们说话,我才发觉毒和伤口引出的一系列词中,也包括死——像那些葬礼中躺在棺材里的人似的。
我被吓愣了。一整个过程,我都没有哭,直到意识到这个,突然我嚎啕大哭。医生和周围的人吓一跳,赶紧跑过来给我打针,母亲开始用我父亲去世时特有的哭声喊着:“救救我儿子吧。”
我们那的医生从未接触过这种事。面对乡里第一例蛇咬病例,卫生院院长都出动了。我记得那个老头说:“不知道毒多厉害,先观察一下,我们把伤口给你处理好。”一个小护士给我用酒精擦拭伤口时,看那圈紫色的镶边特别认真,然后回头跟我母亲说:“大姐,咱们这边很少毒蛇。”
我记得很清楚,自己在乡卫生院急诊室的长椅上干坐一个下午。母亲和医生不断走到我面前,问我哪不好受么?我很困,眼睛有点睁不开,便指着脑袋说:“这疼。”所有人都很困惑地看着我,这让我觉得不应该这里疼似的。
我醒过来已是第二天一早,熟悉的环境让我变得轻松很多,我躺在家里。母亲在我身边干坐一夜,她看我睁眼,又问我:“哪不好受?”
我没有说话是因为搞不清该说哪里不好受。庆幸我没有死于蛇毒,那次经验告诉我,也让我至今不怀疑,比死更可怕的事是等着死。
四、姥爷与驴
在七十年代,驴是马州人眼中的奢侈物;在七十年代的马州,能够接触到驴的人很少,能交易一头驴的人就更屈指可数了。在七十年代的马州,那些关于驴的交易都发生在石榴河畔的牲口市上。我们村一个上年纪的老人曾手戳着一片建筑废料回忆出了这个市集的准确位置。在他的浓重方言里,集市似乎仍平静地杵在菜市和小商品市的外围,或靠树林,或搭河岸的地方。对比我们对乡村集市早些年的繁华盛景,它偏安一隅,又意义别样。
一九七二年夏天,马州集市靠河的这个牲口市上出现了两个之前完全不认识的男人,他们结伴而行,窃窃私语,时而严肃,时而开怀。一个身穿的确良上衣,一个嘴是歪的。歪嘴汉子后来止步了一会儿,紧接着又跟上的确良上衣的老头,他一边用那张歪嘴不停说话,一边扭头看向驴叫声传来的地方。老头神情始终保持严肃。最后,他们在一面土墙前站住了,午后的阳光在他们俩的影子上照出一层毛边儿。驴叫声停止了。不远处一个树上拴着一头驴正呲着牙,朝他俩呼出热气。从那满口的新牙、捋顺的皮毛就可以判断出这头驴之于当时牲口市的性价比无疑是最高的。它的年少和强壮显而易见。它的主人,也就是这时土墙前的歪嘴汉子显然洞悉着一切。自从开市后,他身边总是人来人往。歪嘴汉子的手一直缩在袖桶,眉头在探问的人走后,又放开,而在又一个人把手伸进袖桶里时,迅速紧缩——这一幕被我认为是马州牲口市上最为动人的一幕。这一幕的参与者之一就是我的姥爷。那身黑确良上衣在我母亲的印象里一直穿到他去世。在那之前的每一个夏天,这件上衣都会在村里田间出没。我姥爷当时在生产队里赶大车。那次,他受队长重托拿着队里的积蓄去买驴。不是说,手离了袖管,把驴牵走,这事就完了。在那个时候,有的事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的横生枝节。姥爷买回驴后,每月两次赶饭口到牲口市上,专门请歪嘴汉子到家里来吃酒。土墙前的一遇让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一次相见恨晚啊。一九七二年的这个夏天,姥爷回到生产队时已是夕阳西下。村子距离集市一两里路,我姥爷又是上午出发,让人想不通一个寡言的人一下午都在说什么。平时,问姥爷事,一般都是“哦”。征求意见,不同意一般都是“扯”。同意就“哦”一声。由驴的事情引出了两家人的走动。逢年过节,走村、过街多了个熟悉的门可进。生产队长和我姥姥也觉得不可思议。
记得我母亲说,她跟歪嘴汉子,叫叔。叔进到村里,见人常说:“来看看驴。”姥爷则一脸严肃地感叹:“怎么能说看看驴呢?”在场大笑的社员都知道驴是这个朴素的友谊故事的起点。我母亲还说,歪嘴汉子和姥爷拜把子成兄弟的那天特别冷。不料,晚上大雪封门,一堵三天,他们在火炕上又聊了三天。歪嘴汉子后来一走,姥爷再也没有跟家里人、村里人说过一句整话。直到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号,此人死于大地震中,两家断了往来。
五、袖筒与秘密
在我姥爷买驴的七十年代,交易不仅是易物,也是打交情。一个“打”字里藏着多少力量,在两颗心之间,具体到我姥爷的故事就是,两个袖筒,两只手,十个手指之间了。
现在,我们马州有的地方也把“还价”称为“打价”。据我所知,这个词大部分时候用于口头。而“打指”是一种在我们马州牲口市上的特殊现象。他们把“价”藏在袖筒,掐在手指上,捏七,卡八、钩子九,都是当时的叫法。我经常在想,一说讨价还价只剩俗气,可变成两人袖筒里的秘密陡然就高级起来。由此及彼,再想一想他们杵在一面朝西的土墙前,旁边时而有人路过,或提几只鸡,或牵一头羊,行色匆匆,日上树头,林间鸟飞鸟回,没人注意到他们滑稽的样子。就像手牵手。
乡村集市上的人变得面目模糊,叫卖声变得相近的血腥。很多时候,我在熟悉的地摊前走过,人物已变,从声嘶力竭的叫卖声中,听到的是“跳楼价,大出血”、“清仓甩卖”听完,摸摸自己的心,只剩惊悚。
我的记忆里怀念的是“这有一匹好缎子,要不您过过眼?”“这书我看了,还行,可以拿一本。”一方面说买卖,一方面说事。后来,买卖就成了事,事里就有爱憎、有心情,越聊越温暖。
以至于后来,一到集市,即使不买什么,我也总是去看看那人,听听他说话,感觉是去见一个朋友。我在乡村集市上结识了很多这样的老人。早几年,夏天赶集,因为人多,到了集市,有点中暑发热一阵空白,想不起要买啥。于是,穿过人群,在他们的地摊前一坐,说着说着,很多事逐渐清晰了,才道个别,再去买菜买物。现在,我打听到的总是他们去世的消息,或者有的也只是在家养老,没了他们的乡村集市面临着荒腔走板,至少于我心中,那些地方回到了惊人的陌生中。
六、大事与小事
超市在马州新兴那几年,我曾遇上一个年龄稍长的妇人,身穿名牌,一副城里人打扮在超市和一个服务员争吵。小姑娘话语尖刻,捍卫价格,妇人誓要打折的样子,看起来有些像泼妇。可是她有错吗?在某种环境下的惯性,促使她忘记这里的空气,是空调吹出冷风;这里的地面是明亮的瓷砖;还有这里的人穿戴一致,言行经过培训,看上去都一样保持着不真实的笑容。
这种尴尬在于我们在应该遗忘的时候,忽然地想起。我周围有不少这样的人,包括我自己,有时拿起一件东西也想问能不能便宜?有时,知道不能便宜,仍禁不住试问。“不能便宜”从售货员嘴里说出,传回耳朵,最初还曾是一种难受。后来,我假装认同这些事。至少在一些地方,假装的人多了,就不再分得清伤害。
一些城里的朋友不能理解我的言论,更不屑于乡村集市。他们看到我买回来的书又相当渴望。为什么不去?我觉得,可能是装得太久了。他们大部分是乡村出身。后来,高楼、商厦、超市楔入他们的生活。其中几个人跟我去过几次乡村集市,却在乡村的朴实面前,显得十分尴尬。
我在回来的车上跟他们说,打价不重要,醉翁之意在乎的是别的。对方好像不懂,我也作罢,干脆不提下次再来。在有些地方数字真不重要。如我的经验里打价买书是数字增减,卖书人非要送我一套书的事又是什么?这样的事情总有发生。还有,姥爷买驴收获了一个能和他说上话的拜把兄弟;姥姥买布不仅买一块布,还学了一件褂子的新做法;我姑奶更厉害,以逛集为主,却经常在集市上扮演包公的角色,处理买卖双方的纠纷……按我城里朋友的话说,这是奇闻异事,叫人难以置信。
七、驴与书
值得一提的还有几天前,我们在朋友的书店闲聊,刚好聊到这些如今看起来难以置信的事情。大伙都怂恿我做一个纪录。忽然,听一个顾客在柜台前问,能便宜不?当我听到售货员面对“打价”淡淡的回答,特意留意了一下他脸上的表情,和我想象中一样,是有点怅然若失的。不过,他依旧抱着那几本书不肯放手,又摸索了一会儿,才交钱离去。
这与一九七二年夏天马州牲口市旁土墙前的一幕,几乎代表了两个时代。各自动人,我看到他一边走着,一边摸索着那几本书,他是爱书的,他是舍得的,就像我姥爷牵着驴,一边走着,一边摸索着他的鬃毛,彼时看着他们的应该是歪嘴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