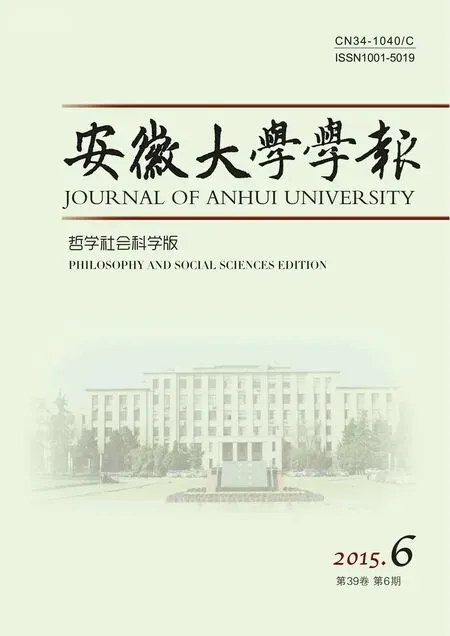被启蒙的“伊甸园”
——论施莱尔马赫对伊甸园传说的解读
2015-12-16朱云飞
朱云飞
被启蒙的“伊甸园”
——论施莱尔马赫对伊甸园传说的解读
朱云飞
施莱尔马赫作为启蒙时代德国重要的思想家和古典语文学家,将《圣经》作为诗歌艺术的作品,在其经典著作《论宗教》中,以重述的笔法对《创世记》的伊甸园传说进行了重新解读,揭示了启蒙的人性论,从而为西方现代文化提供了经典的支持。
古典;创世记;重述;人性;启蒙
西方现代文化并非凭空而起,而是在继承和突破古典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其历史发展过程蕴含着特定的内在脉络和关键枢纽。《圣经》作为西方古典文化渊源之一,被重新诠释,获得了新的含义,正是塑造西方现代文化极为重要的关节点。而作为《圣经》开篇,《创世记》的地位举足轻重,其中的“伊甸园”传说独具魅力,近现代对它的解读层出不穷。施莱尔马赫作为启蒙时代德国重要的思想家和古典语文学家,通过其经典著作《论宗教》对《创世记》进行了解经,以启蒙式的解读重述了伊甸园传说,为西方现代文化提供了经典的支持。
一、重述的意图与笔法
施莱尔马赫对《创世记》“伊甸园”传说的解读方式别具一格,既非传统的注经方式,也不是哲学的分析方式,更非一般的文献引用方式,而是“重述”伊甸园传说:将《圣经》关于伊甸园传说的记载进行整编改写,以融入《论宗教》整部作品中。这种解经做法看似简单,实际上隐含着施莱尔马赫的匠心。
施莱尔马赫的重述,原文很简要:
很久很久以前,第一个人仅仅同自身和自然在一起(mit sich und der Natur),不过神祇(die Gottheit)高高在上地主宰着他,神以不同的方式同他打招呼,但他不理解(verstand)这些,也就不能应答神祇的招呼;他的伊甸园是美丽的,天体从美丽的天空给他倾泻万丈光芒,却激发不出他对世界的感觉(der Sinn für die Welt),他自身也不能从他心灵的内在之处(aus dem Innern seiner Seele)发展出来;但他的情感(sein Gemüth)为对世界的渴望所动,于是便想共同推动对动物的创造,看能否从什么东西中培育出一个来。由于神祇了解到,他的世界一无所有,这么长时间他都是孤身一人,就给他创造了一个女伙伴(die Gehülfin),这时才在他的内心激起富有生命和精神的声音,只有这时他才第一次张开眼睛看世界(nun erst ging seinen Augen die Welt auf)。在他的肉之肉中,在他的腿之腿中 (Indem Fleischevonseinem Fleische und Bein von seinem Beine),他发现了人性(die Menschheit),在人性中他发现了世界(die Welt)。从这一瞬间开始,他变得有能力倾听上帝的声音和应答上帝
的招呼;从这时起他罪恶的逾越律法行为,也不会再阻断他与永恒存在者(dem ewigen Wesen)的来往。我们所有的历史都是在这个神圣的传说中讲述的。①施莱尔马赫:《论宗教》,邓安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1页。该段译文部分有错误,笔者根据德语原文作了改译。德语原文可参见F.Schleiermacher,Über die Religion:Rede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1799),Hrsg.von Günter Meckenstock,Berlin&New York:Walter de Gruyter,2001,SS.95-96.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重述伊甸园传说之前,施莱尔马赫庄严地宣布:
让我给你们来揭示一个秘密,这是在诗歌艺术和宗教的最古老的原始文献中隐藏的秘密。②施莱尔马赫:《论宗教》,第51页;Schleiermacher,Über die Religion:Rede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S.95.
这表明施莱尔马赫重述的意图是在揭示秘密。问题在于:这是什么秘密?通过这段文字所处的文本位置和文脉(即处于《论宗教》第二讲“论宗教的本质”关于人性与宗教的论述之中),可以知道施莱尔马赫所说的秘密是人性的秘密。这段文字内容本身也表明其围绕的核心就是人性的产生、发展及其引发的后果。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施莱尔马赫之前,西方关于人性的著述早已是长篇累牍,仅休谟的《人性论》就有六百页之多,更何况康德一生致力研究的四个问题③可参见《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9页。无一不与人性相关。但是,施莱尔马赫所说的人性秘密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在诗歌艺术和宗教的最古老的原始文献中隐藏的秘密,直接地说,就是施莱尔马赫眼中《创世记》伊甸园传说隐藏的人性秘密,而不是启蒙哲学家宣扬的人性论,也不是基督教关于人性的传统教义。
接下来的问题是:伊甸园传说流传千古,对人性论基本上已有定论,施莱尔马赫又如何通过解读伊甸园传说,揭示其中的人性秘密?这关涉施莱尔马赫的解读方式。他首先重新界定《圣经》文本的性质,认为《圣经》作为最古老的原始文献,不仅是“宗教的”,同时也是“诗歌艺术的”。这一点看似轻描淡写、无关紧要,实际上是要消除笼罩在《圣经》上的光环,剥夺传统赋予它的特殊性,这在《论宗教》的后文中有明确的呼应。因此,《圣经》作为一本“诗歌艺术”著作,没有路德所言“唯独圣经”的神圣性,当然应该像解释别的古典著作一样解释圣经。后来,施莱尔马赫在解释《圣经》其他篇章时仍然以这种观念为指导④卡岑巴赫:《施莱尔马赫》,任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5页。。这种指导观念为其解读伊甸园传说拓展了广阔的空间。正是在此空间下,施莱尔马赫运用了“重述”的方式。他抛开亦步亦趋的转述,淡化其中的宗教特性,采用经过剪裁后的简述:既有对原文的省略,也有补充,更有精心的改写。施莱尔马赫的重述实质上乃是一种解经,包含了他的深刻意图,也融入了启蒙的精神。
二、人的“自然状态”
《创世记》第1章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故事之后,紧接着以整整两章的篇幅记载了伊甸园传说。这个传说在西方几乎家喻户晓。施莱尔马赫将它重述为一篇近乎格林童话的寓言故事,直接以“很久很久以前”开篇,引出人的“自然状态”。进入启蒙时代以后,西方社会兴起一股潮流:为挣脱基督教传统对人性和社会的限定,众多思想家、文学家纷纷构想新的人性和理想社会,这中间既有理性所设计的契约社会,也有梦想的阿卡迪亚式的田园生活。尽管思路各异,但这些构想几乎都有一个共同倾向:为实现最终的社会理想和人性的完美,都在寻找人的“自然状态”。探索自然状态并不是为了展现历史的事实,而是要考察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最初人的外在自然处境,另一个是人自身的内在自然本性。
通过回到“很久很久以前”,施莱尔马赫引领人重返自然状态。他对人的自然状态的揭示,紧紧围绕一条线索:人与自然。施莱尔马赫先以白描的手法,指出:“第一个人仅仅是同自身和自然在一起”,“他的伊甸园是美丽的,天体从美丽的天空给他倾泻万丈光芒”。这些诗意般的描述无一不在表明:人与自然和谐一体,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之间没有分离,更没有对立。这就是施莱尔马赫对最初人的外在自然处境奠定的基调。值得注意的是《创世记》第1章叙述了神创造世界的故事,而后在讲述伊甸园传说时再次提到“创造天地的来历”①《圣经·创世记》(和合本)第2章第4节。下引该书以标出章节形式随文夹注。,施莱尔马赫却将此一笔抹去,没有描述任何《创世记》中神创造世界和人类的情节。这一点与启蒙时代的思想潮流密不可分。自近代以来,启蒙思想家不再将神置于优先的地位,而是把自然置于优先的地位②Michael Allen Gillespie,The Theological Origins of Modernit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p.262.,并且开始从自然的角度解释世界③汉普生:《启蒙运动》,李丰斌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第19页。亦可参见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上,刘北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7页。。为避免同这种启蒙的立场直接冲突,省略这些内容而又保留“神祇”,乃是施莱尔马赫“有意为之”。虽然神创世的内容被隐去,但是《创世记》所记载的创世后“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被施莱尔马赫所吸收,被重述为:“他的伊甸园是美丽的”——两者的精神一脉相传。同样是基于对圣经的解读,霍布斯看到的是自然状态的恐惧,施莱尔马赫再现的是伊甸园的美丽。在这一点上他与卢梭对自然状态的构想可谓遥相呼应:弥合与自然之间的裂痕,应对的正是启蒙时代一个大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现代人,甚至使得德国浪漫派惊呼:“鉴于自然与人类如此频繁如此尖锐地相互矛盾,哲学大概无法避免覆灭的命运”④施勒格尔:《〈雅典娜神殿〉断片集》,《浪漫派的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尽管伊甸园如此美丽,但施莱尔马赫并未沉醉其间,视其为圆满,毕竟美丽不等于完满。最初人的外在自然处境与人的内在本性虽然分属自然状态的两个方面,实际上两面一体。因而,伊甸园中的缺陷对应的就是人的内在自然本性的“不能”:“也就不能应答神祇的招呼”,“他自身也不能从心灵的内在之处发展出来”。
人之所以“也就不能应答神祇的招呼”,施莱尔马赫已将原因摆明:“但他不理解这些”。何为“不理解”?就是不能运用理性并且缺乏理性。那么,不能运用理性并且缺乏理性不正暗示人需要启蒙吗?因为“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来。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⑤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页。那么,什么是人的“受监护状态”呢?原来是“神祇高高在上地主宰着他”。有了启蒙,才会走出受监护状态去使用理智,才会有理解。就此而言,施莱尔马赫的立场是呼唤理性,欢迎现代的启蒙精神,他不是一个泥古不化之人。
伊甸园的美丽激发不出人对世界的感觉,其原因也被施莱尔马赫列出:“他自身也不能从心灵的内在之处发展出来”。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何以人自身不能发展出来?其缘由已被“很久很久以前,第一个人仅仅是同自身和自然在一起”所设定。在这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状态中,人不能将自身与自然分开,其自身根本分辨不出外在的世界,又何来对世界的感觉?伊甸园纵然再美丽,终究也是枉然。席勒的洞见,也许会将施莱尔马赫简洁的叙述剖析得更加清楚:“只要人处在他最初的物质状态,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感性世界,只是感觉感性世界,他就仍然与感性世界是完全一体的,而且因为他自己只不过是世界,所以世界对他来说还不存在。”⑥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3页。在这种近乎物质状态中,物我不分,必然没有“他自身”。
如果说施莱尔马赫通过两种“不能”,表明人在自然状态中缺乏理性、缺乏自我意识,没有对外在世界的感觉,那么这种状态正如他后来在《圣诞节谈话》中所言:“在原始的大自然中,尚未有本体和现象、永恒与时间的对立,但那种生命和喜乐不属于我们”⑦F.Schleiermacher,Christmas Eve,trans.by W.Hastie,Edinburgh:T.&T.Clark,1890,p.65.。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难道人的自然状态是空无一物?施莱尔马赫笔锋一转,引出“但他的情感(sein Gemüth)为对世界的渴望所动”。可以推想,施莱尔马
赫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还有“情感”!在这种“情感”之中,人“于是便想共同推动对动物的创造,看能否从什么东西中培育出一个来”。这个细节根本不是《创世记》原文所载,而是施莱尔马赫所增加的。关键是他增加的是什么性质的细节?这个细节乃是:人拥有了“为对世界的渴望所动”的“情感”。西方近代以来,为矫正启蒙对理性的过度张扬,提倡情感的思潮源源不断地涌现:莎夫茨伯里(Shaftesbury)和卢梭对情感的呼唤是施莱尔马赫的先声,德国浪漫派的多愁善感和少年维特的烦恼此时还环绕在施莱尔马赫的周围,弥尔顿在其对伊甸园传说进行启蒙式演绎的史诗《失乐园》中,赋予了人各种人间情感。必须要说明的是,正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这种为施莱尔马赫一生所重的“情感(Gefühl)”的萌芽①“情感”不仅在此处出现,在施莱尔马赫后来的解释圣诞节含义的柏拉图式对话作品《圣诞节谈话》中再次出现,而且其晚年巨作《基督教信仰学说》更是对它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正是以“情感”为核心,施莱尔马赫开创了西方现代神学的典范。。此处所说的“情感(Gemüth)”是“为对世界的渴望所动”,根本不是普通的心理感受或者情绪。后来,施莱尔马赫将此处的“情感”进一步界定为对世界的绝对依赖感②可参见F.Schleiermacher,The Christian Faith(1830/31),trans.by H.R.Mackintosh and J.S.Stewart,Edinburgh:T.&T.Clark,1986,pp.12-18.,旨在重建人与世界不可阻断的关联。总而言之,施莱尔马赫在人的自然状态中,清除了理性和对世界的感觉,唯留有珍贵的“情感”。
这里出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人的自然状态是否就是人性的本原?大多数考察思路将两者合二为一,简而言之,人的诞生意味着人同时具有了人性。于是,在此基础上展现人性的内涵就成为思想家、文学家尽显神通之处。与席勒的做法相似③席勒将人的发展分为三个状态:物质状态、审美状态和伦理状态。在物质状态中,自然始创了人,但人性还没有产生。可参见《审美教育书简》第二十四、二十五和二十六封信。,施莱尔马赫将两者切割开,即人的自然状态不等于人性的本原,或者说在自然状态中,人性没有产生,人尚未具有人性。那么,就此而言,自然状态乃是一个“原点”,只是为人性的产生提供基础而已。
三、人性的产生
揭示人性的秘密,是施莱尔马赫重述伊甸园传说的目的所在,也是整个寓言故事的中心环节。在自然状态中人的情感萌动了,但是人依然没有获得人性,因此说明人性的产生便是施莱尔马赫揭示秘密的第一个步骤。
所谓自然状态中的“第一个人”,实际上也是唯一的一个人,施莱尔马赫为其安排了“一个女伙伴(Gehülfin)”:“由于神祇了解到,他的世界一无所有,这么长时间他都是孤身一人,就给他创造了一个女伙伴。”施莱尔马赫叙述的情节紧扣《创世记》的记载,基本上是对原文的转述:“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2章18节)只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原文中的“配偶”是指合适的帮手④可参见Adele Berlin,Marc Zvi Bretteler eds.,The Jewish Study Bible(Tanakh transl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6,亦可参见《摩西五经》,冯象译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6页。,施莱尔马赫将其转换成“女伙伴”,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女伙伴”与“第一人”在精神上亲密的配合关系;另一层是两者在地位上的平等关系。两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在此需要予以特别注意,不仅是因为“女伙伴”的称呼,还由于施莱尔马赫在后文的叙述中有意省略的一个情节,就是《创世记》中人类偷食禁果后,上帝对女人的惩罚:“你丈夫必管辖你”(3章16节)。所谓“管辖”,就意味着“丈夫要做你的主人”⑤《摩西五经》,第8页。,即失去平等地位,主奴关系随之到来。施莱尔马赫意图一直保持两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同时又在这平等之中展现两性的不同及其不可或缺的配合关系。他的立场不仅符合启蒙思想对平等观念的倡导,还隐约地回荡着柏拉图掀起的浪潮声。为缔造理想国,柏拉图曾掀起三股浪潮,第一股浪潮就是“不同的本性均匀地分布在这两类生物中,女人按其本性能参与所有的事业”⑥柏拉图:《理想国》,王杨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那
么,对人性的产生而言,人性涵盖女性,不仅女性完全能够作为平等者参与其中,而且女性的参与必不可少。由此可以认识到,人性应当包括不同的男、女两性,缺一不可,两性合二为一才会有真正的人性。当然,这些观念在施莱尔马赫的叙述中暂时还只是含苞的蓓蕾,待到《圣诞节谈话》就迎风绽放了。
在后文中,施莱尔马赫又称“女伙伴”为“他的肉之肉”“他的腿之腿”。很显然,这个称呼是对《创世记》的沿袭。《创世记》记载了“第一个人”(亚当)的配偶是用他的身上取下的肋骨造成的,因此称其为“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2章23节)。这个称呼也表明第一个人与其配偶之间的肉身关系。对这个细节施莱尔马赫略而不提,却保留其中的称呼。如此处理使得这个名称本来所蕴含的肉身关系被两者之间亲密的配合与平等关系所代替,或者说施莱尔马赫将原本的肉身关系精神化了。
“女伙伴”出现以后,人就脱离了自然状态:“这时才在他的内心激起富有生命和精神的声音,只有这时他才第一次张开眼睛看世界”。原本美丽的伊甸园“却激发不出他对世界的感觉”,“他自身也不能从他心灵的内在之处发展出来”,那种没有理性、没有自我、人如同物质的自然状态现在被彻底改变。这种改变的前提就是“女伙伴”,改变的结果有两个:首先就是人具有了关于“他自身”的自我意识,有了自我意识才会有人的内心,否则“激起富有生命和精神的声音”根本就无从谈起。其次,从物我混沌的状态中走出来,看到自身之外的世界。这种改变的结果就是“在他的肉之肉中,在他的腿之腿中,他发现了人性,在人性中他发现了世界”,恰好与人的自然状态正相对应。发现人性就是人性的产生。
从人的自然状态到人性的产生,唯一的决定因素是“女伙伴”的出现,“女伙伴”成为施莱尔马赫重述的一个核心元素。因此,问题在于为什么“女伙伴”能够促动人性从“原点”到产生?原因在于“女伙伴”打破了“第一个人”所处的自然状态,通过成为“他的肉之肉”“他的腿之腿”,在两者间建立起独特的精神关系。虽然这种独特的精神关系在“女伙伴”的称呼中已经显露出来,但是其实质依然未得到清楚的说明。直到此处,施莱尔马赫才以“爱”之名予以彻底揭示:“他只是在爱中并通过爱才找到人性”①施莱尔马赫:《论宗教》,第51页;Schleiermacher,Über die Religion:Reden an die Gebildeten unter ihren Verächtern,S.96.。只有这样,自然状态的“第一个人”才会从近乎物质的人转变成具有人性的人,具有人性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人与人性才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具有这种精神品质的“爱”,不仅产生人性,而且指向整个世界。因此,它完全不同于凡俗之爱,毕竟凡俗之爱指向具体的人,是在人性的基础上才得以萌发。
施莱尔马赫回溯到人性的“原点”来寻找人性,不同于启蒙思想家以自然状态直接界定人性,也没有承袭文学家透过现实生活描摹人性的手法,而是通过伊甸园故事架起一座桥梁,一端吸纳启蒙的精神,另一端又回应古希腊的呼声。这种做法虽然仍然是在《圣经》传统的框架之中,但实际上引入了新的内容,为现代人性品质的奠定提供了基础。
四、人性的罪恶与希望
对人而言,发现人性并不仅仅意味着进步,而是喜忧交集,施莱尔马赫就如是观:
从这一瞬间开始,他变得有能力倾听上帝的声音和应答上帝的招呼;从这时起他罪恶的逾越律法行为,也不会再阻断他与永恒存在者的来往。
《创世记》关于“伊甸园”传说的记载中,第一次提到上帝对人的招呼,是上帝对亚当颁布诫命:
园中各树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2章16、17节)
此时人没有应答。而人第一次倾听到上帝的声音并应答上帝的招呼,是在夏娃让亚当吃了“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实之后,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即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3章9、10节)按照《圣
经》传统的解释,人之所以倾听到上帝的声音并开始应答上帝的招呼,原因在于人吃了“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因为“分别善恶的树”就是善恶智慧之树,这种善恶智慧不仅是理智的知识,而且包含道德上的善与恶和生活中的幸福与痛苦①可参见Adele Berlin,Marc Zvi Bretteler eds.,The Jewish Study Bible(Tanakh translation),p.16.,所以偷吃了这种树的果子以后,“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3章7节)。而这种偷食“分别善恶的树”果子的行为,违背了上帝第一次对人发出的招呼(诫命),是“他罪恶的逾越律法行为”,这也就是所谓的“原罪”。“原罪”产生后,才出现人对上帝的应答。这都是《圣经》的明文记载。
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圣经》所刻画的人性“原罪”痕迹,在施莱尔马赫的重述中消失殆尽。人倾听到上帝的声音,应答上帝的招呼,不是由于“原罪”,而是因为“女伙伴”出现而产生了爱,在爱中人找到了人性,发现了世界。这种倾听、应答洗去“原罪”的污点,反而是“他变得有能力”的表现。按照这种祛除“原罪”的思路,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的树”果子的行为自然就会呈现出另外一幅面貌。早在施莱尔马赫之前,英国诗人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就已经描写了亚当对夏娃的世俗之爱,夏娃出于报答摘取果子给亚当吃,而亚当毫无顾虑地吃了,不是因为被夏娃欺骗,而是由于被女性的魅力所征服②弥尔顿:《失乐园》第九卷,朱维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331页。。弥尔顿通过引进人的精神来试图暗中解开“原罪”对人性的捆绑,而施莱尔马赫则用精神性的“爱”遮盖“原罪”。“原罪”之论源于《圣经》,为奥古斯丁所弘扬,但是启蒙时代涌起的历史潮流不断冲击、否定“原罪”,施莱尔马赫即处其中。
虽然在重述中“原罪”几乎不见踪影,但施莱尔马赫并非没有看到人性的罪恶和堕落,而是知道发生了“他罪恶的逾越律法行为”。那么,人性的罪恶因何而来?《创世记》的说明并不含糊:这是“原罪”的结果。但是,施莱尔马赫的答案并不清晰,需要根据他提供的线索思考。人在自然状态之中,没有“他自身”,如同物质,当然不会有罪恶可言。罪恶作为人性的一种状况,必然是在人具有人性之后才会发生,然而“他只是在爱中并通过爱才找到人性”,那么这种产生人性的“爱”必然尚不健全、完满。简而言之,“爱”不完满,就会有人性的罪恶。
人性存在罪恶,但施莱尔马赫并不绝望,相反,他充满希望:“从这时起他罪恶的逾越律法行为,也不会再阻断他与永恒存在者的来往”。他看到了人性的罪恶,却没有陷入卢梭忧心如焚的状态,也没有重蹈帕斯卡孤寂无依的心境。施莱尔马赫的希望在于:人性的罪恶不再阻断与永恒存在者的来往。这种希望不是来源于空想,而是如施莱尔马赫后来所言:它是伊甸园故事必然包含的意义③F.Schleiermacher,On Religion:Speeches to Its Cultured Despisers(from the third German edition[1821]),trans.by John O-man,London:Kegan Paul,Trench,Trübner&CO.,Ltd.,1893,p.112.。这种希望的根据在于,既然“爱”不仅产生人性,而且指向世界,那么爱与世界必然不可分离。在重述的伊甸园故事中,施莱尔马赫没有强调上帝作为世界的创造者的身份,而是突出“神祇高高在上地主宰着他”的永恒存在者身份。这个永恒存在者是在世界之中的永恒存在者,不是超脱在世界之外。因而,指向世界的“爱”与永恒存在者的关联不会被阻断,人性虽然产生过罪恶,终究与永恒存在者相通。这就是施莱尔马赫谱写的人性的希望,也是他为现代人提供的完善人性的方向。
施莱尔马赫重述的伊甸园传说,展现了人性从自然状态到产生、从产生到堕落、从堕落到希望的三个发展阶段。因而,他认为“我们的所有历史都是在这个神圣的传说中讲述的”。经过文学化重述,他将《创世记》的伊甸园转变成“被启蒙的伊甸园”,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从中揭示了人性的秘密。这隐含着施莱尔马赫的良苦用心:通过对古典作品的“寓意解经”,为经过启蒙洗礼后人性的完善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指引方向。
责任编校:余 沉
B971.1
A
1001-5019(2015)06-0016-06
朱云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学博士后,讲师(北京 100872)。
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6.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