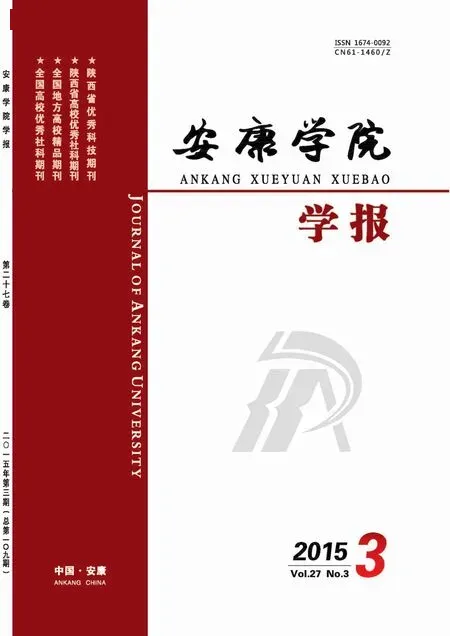战国时期楚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吾”“我”比较研究
2015-12-13尹喜艳
尹喜艳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7)
上古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系统较为复杂,有“我”“余(予)”“朕”“卬”“吾”“台”,战国时期第一人称代词有“我”“余(予)”“朕”“吾”,其中“吾”与“我”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两个第一人称代词。“吾”与“我”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甚感兴趣的问题,近年学者多从时间或专书角度来研究二者的关系。战国时期楚方言地域特征突出,《楚辞》和楚地出土的战国楚简是研究战国时期楚方言的丰富材料,它们为从方言角度研究“吾”“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一、问题的提出
“吾”与“我”的关系问题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目前对二者的历时比较研究有了一些新的进展,但尚无从地域性差异角度研究二者关系的相关成果。战国时期楚地方言特征明显,《楚辞》更是研究楚方言的重要材料,从地域差异角度研究战国时期第一人称代词“吾”“我”的关系,能够更好地提示上古第一人称代词系统的地域特色。
(一)前人关于“吾”“我”关系的探讨
近代学者马建忠第一个注意到“吾”“我”在格位用法上有量的差异,胡适在1917年的《吾我篇》中认为:一是“吾”“我”有格位分别,“吾”用于主格,“我”用于宾格。二是“吾”“我”同可以用于领格,但有数的分别,“吾”用于领格,单数为常,复数为变;“我”用于领格,复数为常,单数为变[1]。高本汉则认为:“吾”是用于主格跟领格的代词,“我”是用于宾格的代词[2]。对于格位说,王力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吾”字用于主格和领格,“我”字用于主格和宾格[3]。随着研究的纵向深入,对于上古时期的“吾”“我”的比较也在不断深化:有的学者以时间为切入点,如胡伟对战国至西汉时期“吾”与“我”的对比研究[4],有学者从专书角度出发,如夏先培对《左传》中“吾”与“我”的对比研究[5],等等。
(二)从地域角度研究“吾”“我”关系的可能性
战国时期楚方言特色鲜明,黄盛璋指出,从殷周到秦的统一,历时很久,地区也相当广大,语言是发展的,不可能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他认为《楚辞》是上古汉语人称代词地域性上的代表[6]。张玉金在研究西周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时间性和地域性问题时,提出了“宗周方言”的概念,他认为这种语言在地域上存在差异的现象可以看作是语言类型地理推移的表现[7]。可见,上古时期的人称代词的方言差异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学者们也已注意到《楚辞》所反映的人称代词的地域性,这种地域性正是楚方言地域性的体现。
(三)考察战国时期楚方言第一人称代词的材料
《楚辞》是战国时期楚方言的典型传世文献,所收作品之作者从战国时期直至东汉时期,年代前后跨度达500余年,其中战国时期的屈原与宋玉的作品能准确反映战国时期楚方言的语言面貌,《楚辞》中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宋玉的作品有《九辩》[8]。此外,丰富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是战国时期楚方言的真实反映,主要包括:长台关楚简、望山楚简、九店楚简、包山楚简、曾侯乙墓简、郭店楚简(仅限明确为楚方言背景的《老子》和《太一生水》)、曹家岗楚简、葛陵楚简、五里牌楚简、仰天湖楚简、杨家湾楚简、夕阳坡楚简①长台关楚简,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撰《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望山楚简,见湖北文物考古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合编《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九店楚简,见湖北文物考古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合编《九店楚简》,中华书局,2000年;包山楚简,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曾侯乙墓简,见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郭店楚简,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曹家岗楚简、葛陵楚简、五里牌楚简、仰天湖楚简、杨家湾楚简、夕阳坡楚简,见陈伟等著《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
有了以上丰富的材料,本文拟在对《楚辞》以及楚地出土战国简册作穷尽性统计与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对比研究战国时期楚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吾”和“我”,以期能在“吾”“我”关系问题上获得一些新的认识,这对于我们认识上古人称代词系统的发展演变以及地域差异,乃至探讨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有意义的。
二、战国时期楚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吾”与“我”之差异
在战国时期的楚方言中,“吾”使用频率较高,“我”使用频率较低;“吾”最重要的句法功能是作主语,“我”最重要的句法功能是作宾语;在语义功能上,“吾”是无对指的自称,“我”是有对指的自称。
(一)“吾”与“我”在使用频率上的差异
战国时期的楚方言中第一人称代词有“余(予)”“吾”“我”“朕”,“余”跟“予”两个字的写法不同,但是同一个词。根据笔者的统计,战国时期楚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共使用211次,“我”作为上古时期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第一人称代词在战国时期的楚方言中却处于弱势状态,使用20次,占总数的9.5%;而“吾”在战国时期楚方言中却要活跃得多,使用74次,占总数的35.1%。楚方言中“我”的这种弱势状态的存在,跟“余(予)”的强势存在紧密联系。这一时期楚方言中,“余”是最重要的第一人称代词,共用110次,占总数的52%。第一人称代词系统是一个数量相对固定的集合,其中某个人称代词的大量使用,势必影响到其他代词的使用频率,呈现出此长彼消的状态。“余”成为楚方言最重要的第一人称代词的同时,也造成了“我”的地位的弱化[9]。
(二)“吾”与“我”在句法功能上的差异
1.“我”最重要的句法功能是作宾语,“吾”最重要的句法功能是作主语
战国时期楚方言中“我”最重要的句法功能是作宾语(18%);“我”作主语和定语的比例都较低,分别为9%、4%,不足十分之一。再来看看“吾”的情况,这一时期楚方言中“吾”最重要的句法功能是作主语,比例高达61%(见表1)。

表1 战国时期楚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句法功能分布
2.“吾”较“我”在宾语功能上存在不足
如表1所示,“我”作宾语占第一人称代词作宾语总数的18%,“吾”作宾语占第一人称代词作宾语总数的14%。虽然比例上差别不大,但作宾语是“我”最强的句法功能;而作宾语却是“吾”最弱的句法功能,二者的宾语功能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我”作宾语的情况有两种:作介词宾语和动词宾语。其中作动词的宾语时,可以作动词后宾语,也可以在否定句中作动词的前置宾语。
“吾”作宾语的情况是:只作动词谓语的宾语(包括动词后宾语和动词的前置宾语)但不能作介词宾语。
(三)“吾”与“我”在语义上的差异
元代赵悳在《四书笺义》里就提出:就己而言则曰“吾”,因人而言则曰“我”。也就是说,“我”是对着别人说自己,是相对他称而存在的自称,句子前后会出现相对应的人或事物;“吾”是说自己本人的情况,不涉及他人(另一方)的情况。战国时期楚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吾”与“我”基本是符合这一规律的,“我”基本上是因人而言,是有对指物的自称,如例(1)以及例(6)-(80);“吾”基本上是无对指的自称,如例(9)-(11)。但以上规律也存在少量例外的情况,“我”可以用于无对指物存在,如例(12);“吾”可以有对指物的存在,如例(13)。
(《楚辞·九章·抽思》)(“吾心”与“人之心”相对应)
三、战国时期楚方言第一人称代词“吾”与“我”的共同之处
作为战国时期非常重要的两个第一人称代词,楚方言中的“吾”与“我”在相互的差异之外,在称数功能以及谦敬功能方面也存在一些共同之处。
(一)“吾”“我”在称数功能上都只表单数
上古时期第一人称代词“我”经历了从仅表复数到无称数功能限制的变化,“吾”经历了从仅表单数到无称数功能限制的变化。二者在战国时期的共同语中都已经演变成为无称数功能限制的人称代词,既可以用来表单数,也可以用来表复数。
那么战国时期楚方言的情况如何呢?据我们的统计,在战国时期楚方言中的“我”共20次,全部表单数,如例(14)(15)。探究其原因,“我”仅表单数,因为“我”在战国时期的楚方言中使用并不多,并不活跃,所以也就少了很多用于表示复数的语境,这也造成了楚方言中“我”在称数方面与当时共同语存在这一差别。战国时期楚方言中“吾”共出现74次,也全部表单数,如例(16)(17)。不同于共同语无称数限制的情况,“吾”在战国时期的楚方言中仅表单数,笔者认为可能与“吾”对楚方言影响的滞后性有关。张玉金曾指出:西周早期文献中出了第一人称代词“卬”,这个词是宗周方言词,“卬”是后世“吾”的源头,“吾”是“卬”的变体,“吾”最开始的身份是宗周方言词[7]。我们认为,从西周开始,随着周族人成为天下的统治者,宗周方言,尤其是作为第一人称代词的基本词汇对共同语以及其他地域方言的影响必然是非常大的,那么楚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宗周方言的影响。“吾”逐渐地从宗周方言走向共同语,并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共同语中最高频的第一人称代词,楚方言因受到宗周方言的影响,也逐步接纳“吾”作为楚方言的第一人称代词。总体来看,共同语中的“吾”的发展是一个数量上由少到多(西周末年出现,到战国时期成为最高频第一人称代词),称数功能上由仅表单数到兼表单复数的逐步发展的过程;楚方言中的“吾”使用数量占整个第一人称代词系统的比例高达35.1%,可见在使用频率上,楚方言中的“吾”已完成了一个由少到多的演变过程。是否可以推测,楚方言中的“吾”尚未完成由仅表单数向兼表单复数的转变呢?这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去论证。
(二)“吾”“我”都不具有谦敬功能
关于“吾”和“我”的谦敬功能,根据我们的研究,“我”共使用20次,屈原、山鬼、圣人、天帝都可以用“我”自指,可见战国时期楚方言中的“我”并没有表谦敬的功能。“吾”使用的74次,湘君(湘水之神)、主巫、宋玉、屈原等都可以“吾”自称,可见“吾”也是不具有谦敬功能的第一人称代词[9]。
四、结语
战国时期楚方言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吾”和“我”,二者有一定的共性,如二者在称数和谦敬功能方面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一致的。除共性之外,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在使用频率上,“吾”是比“我”活跃得多的第一人称代词;在句法功能上,“我”最重要的句法功能是作宾语,“吾”最重要的句法功能是作主语,“吾”较“我”在宾语功能上存在不足;在语义方面,“吾”更多地是说自己,“我”则常常与相对应的人或事物共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