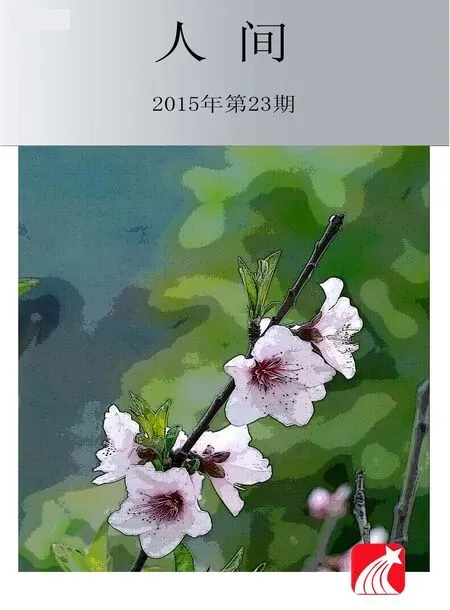浅析韦伯宗教社会学思想
2015-12-11马鑫博
摘要: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家、宗教学家,马克思·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一经提出就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韦伯所处的历史时期正是资本主义兴起,并极大发展的时代,他以独特的视角,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之上,分析了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在现代条件下,宗教是如何与经济相结合,并最终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长足进步。韦伯的思想虽然至今仍备受争议,但其研究方法、思想内涵对学界的影响仍不容小视。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8-0071-02
马克思·韦伯作为西方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其宗教社会学的思想可谓是其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其著作《经济与社会》中详细阐述了宗教何以从原始状态发展成为现代条件下的形态,指出了宗教伦理对于人们社会行为的影响,尤其是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一、宗教的起源
对于何以称之为“宗教”,韦伯本人并没有做出任何界定,他认为“我们甚至并不关心宗教的本质,因为我们的任务是研究一种特殊社会行动类型的条件和效果”。 [1]对于韦伯来说,他的研究的重点并不是深刻剖析宗教的内涵,而是将宗教这一存在物放在其所在的历史环境中,研究其所形成的条件以及反作用于社会所出现的效果,这正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的特点所在。
宗教最初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我们现在称之为“巫术”的行为,站在现代立场上我们可以轻易对其进行辨别和判定,但这并不是评价的标准。韦伯认为“由宗教或巫术因素激发的最基本的表现方式,都是以现世为取向的” [2],虽然在现代看来大多是荒谬的,但在当时却是基于经验所得出的,正因为如此,巫术或宗教不能脱离人们的日常生活活动。韦伯认为,原始宗教中只存在巫术的因素,而巫术之所以可信,是因为实行巫术的巫师具有某种非凡的力量,韦伯称之为“超凡魅力”,而只有拥有这种魅力的人或物才能成为具有灵性的存在。
韦伯认为,原始宗教中只存在巫术,人们只是单纯的相信这样一种驱使鬼怪神灵的行为,认为能从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事物,因而,从这一点来看,人们对于巫术的信奉也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行为。在巫术向宗教转变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将“超凡魅力”抽象出了一种观念,即“精灵”的信仰,“某种存在物隐藏在具有超凡魅力的自然物、人造物、动物或人物‘背后’并支配着他(它)们的活动” [3]。这样一来,巫师所具有的“超凡魅力”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所谓非凡的力量不过是精灵的赐予。人物所能感官到的一切存在物和现象都是精灵的致意,由此,巫术失去了过去绝对的优势地位,精灵信仰的出现逐步演变成为了对神明的信仰,巫术原本是强制驱使超人格的力量为人们服务,而神明信仰的出现使得巫师的强制驱使有了被拒绝的可能,加之生产生活的不断发展,经验的累积使得其作用不断增强,“巫术从一种直接的用力,转变成了一种象征性活动”。 [4]
至此,神明的出现以及对巫术的取代形成了宗教的雏形,人们通过祈祷礼拜等行为一方面表达对神明的崇敬之情,一方面希望从神明那里获得利益。这样的历史转变是必然的,“只要一个组织不是建立在单个统治者的个人权力基础上,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联合体,它就会需要一个自己的神”。 [5]
二、宗教的发展
韦伯认为,宗教的核心问题是使人们通过信仰让灵魂获得拯救,因此,宗教在韦伯那里更像是一种“救赎论”。救赎的思想贯穿了世界各大宗教的思想核心,但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国家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形式。
首先,对于下层民众,尤其是“贱民民族”,在这里特指犹太人,期望宗教救赎的感情十分强烈。韦伯认为自巴比伦囚虏和耶路撒冷神殿被毁之后,犹太民族在形式上和事实上都成为了所谓的贱民民族,
“‘贱民民族’指的是一种世代相传但没有自治性政治组织的特殊社会群体,其突出特征是内部有种种对共餐和异族通婚的禁律,这在最初乃是基于巫术的、禁忌的以及仪式的训诫。贱民民族还有另外两个特征,一是丧失了政治与社会特权,而是在经济活动中表现出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特殊性。” [6]
这样的身份使得犹太人对宗教救赎的渴望异常强烈,表现出了对现实的强烈的仇恨。而同样作为下层民众的印度教亦是如此,种姓制度的严苛直至现代在印度社会仍可见一斑,低等种姓始终希望通过救赎使得来世能够高级种姓。因此,对下层民众来说,宗教救赎是使心灵获得解脱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其次,作为贵族官僚,对宗教的救赎表现得就没有前者那样的热衷。这一阶层很清楚的了解自身的优越与下层人民的艰难,他们不需要通过救赎来实现心灵的解脱,因为现实环境不足以使他们忧虑物质生活而转而寻求精神解脱。对于宗教的态度这类人表现得十分模糊,宗教对于他们的唯一用途就是为自身优越地位辩护,试图从宗教的命定论中来证明自己所处环境的合理性。
第三,理智主义的知识分子和僧侣集团对宗教救赎所表现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教义是有适当的取舍的,在这里韦伯举中国的儒教为例,认为儒教在中国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通过教理来教化人们为社会服务。这一阶层的宗教更像是一种统治社会的工具。而僧侣集团对宗教是十分虔诚和敬重的,他们是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人,这些人认为只有经由他们的手人们才能获得救赎,宗教组织内部等级清晰严格,与儒教相比,这类组织更加倾向出世的精神。
第四,对于非特权阶层,这里特指城市手工艺人等,对宗教的态度则与前三者都不尽相同,也是韦伯重点论述和赞扬的一种宗教救赎论。在这类人群中,基督教由于其特殊的宗教起源因素而具有十分深厚的民众基础。人们为了获得救赎而积极工作,不但通过朴素可行的行动使个人达到了恩宠救赎的状态,客观上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高度的赞扬。
三、宗教与经济
宗教伦理何以对社会尤其是经济产生影响一直韦伯宗教社会学的重心所在,其思想在《经济与社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都有所阐述。在这类宗教伦理的形成过程中,路德宗和加尔文宗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路德认为修道院里的生活与神的本意背道而驰,是逃避责任的表现。积极投入到世俗的劳动中是一种邻人爱的外在表现,这样就将职业履行与个人的道德实践相关联,路德强调履行世俗义务是获得神的垂爱的唯一的道路,是上帝应许的唯一的生存方式,这样就在宗教层面上为积极劳动奠定了基础,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宗教对于世俗劳动的鄙夷态度的禁锢。
加尔文宗在路德宗的基础之上发展了其职业观念。加尔文宗主张上帝预选说,认为“在人类中蒙神选定得生命的人,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按照他永远与不变的目的,和自己意志的隐秘计划和美意选出的。” [7]这就否定了善功与善行在蒙神恩宠这件事上的意义。而且加尔文宗认为“人由于堕落在有罪的状态中,已经完全丧失一切关乎得救的属灵善事之意志力”,不给人通过善功得救留下任何可能。神是绝对自由的,选民是上帝预选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成为选民也不可能;人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异于教会-圣礼的方式确证自己属于上帝的选民。在这个关键点上,加尔文宗给出了两种方法:其一,每个人都有义务相信自己是选民,并且将任何怀疑都视为魔鬼的诱惑而加以拒斥,因为缺乏自信就是信仰不足、亦即恩宠作用不够的结果。第二,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作为获得那种自我确认的最佳手段。因为被神拣选的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在现实里遵行神的戒律,各尽其本分来增耀神的荣光。“由于‘邻人爱’是唯神的荣耀是事,而非服务被造物,所以最首要的是表现在履行那通过自然法所交付的职业任务。” [8]
在“上帝预选”说之前,人可以犯错误,只要忏悔,更正就可以洗刷罪恶,教徒也不必重视超过他们义务之外的善行。而此说之后,人的命运就没有变化的可能了,部分人永生,有些人注定死。信徒会产生巨大的焦虑,必须时刻努力履行世俗义务,通过“邻人爱”的方式荣耀神来寻求确证。这就要求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是个僧侣终其一生,而且要终其一生坚持过这种理性的禁欲生活。这样的要求也恰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培养了人才,为资本形成创造了条件。
四、评价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思想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学界的轩然大波,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后,唯物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其中除了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之外,当然也包括宗教这一类文化现象,而韦伯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宗教是促进资本主义经济长足发展和进步的精神动力,亦或是唯一源泉。
韦伯虽然提出了新颖的解释经济发展的思路,但其思想仍有不足之处。其突出表现在对东方宗教的认识不足,韦伯虽然对世界各大宗教做了详尽的分析,但究其根本是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的立场之上,难免出现理解不足或刻板印象,这使得韦伯关于东方宗教的剖析出现了偏差。韦伯将东方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发展起来归结为东方宗教或是文化上的不足,借此将西方的新教推到了极高的地位,这是有失偏颇的。对此,我们仍应该认识到,应当承认文化对于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但无论是何种社会历史现象,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因素作用,单凭一个宗教、一种文化是难以全面的阐述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