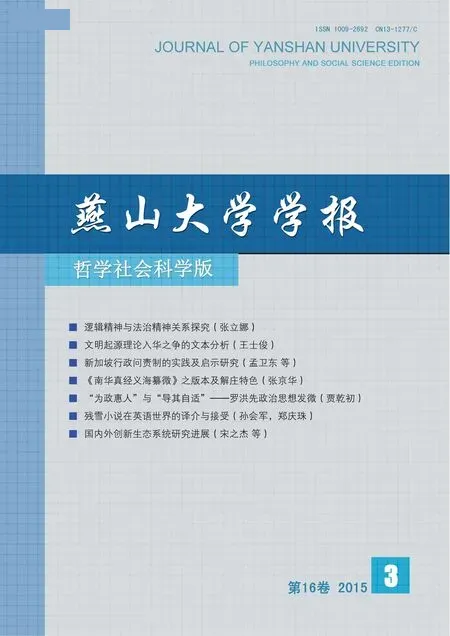“普遍之物”的现象学澄清:洛克和胡塞尔
2015-12-10朱光亚
[摘 要] “普遍之物”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千年。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对世界本原的寻找在一般和个别之间游荡,即是在寻找“普遍之物”,柏拉图的理念论达到了这种寻找的高峰。但是今天,理念论真的已经是一种没有必要再讨论的粗浅实在论吗?经过了唯名论和唯实论斗争的洗礼之后,洛克和胡塞尔最终找到了“普遍之物”吗?似乎尚无定论。
[文献标识码]A
[文章DIO]10.15883/j.13⁃1277/c.20150301005
[收稿日期] 2015⁃03⁃15
[作者简介] 朱光亚(1982—),男,河南许昌人,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基础部讲师。
胡塞尔在谈到“普遍之物”的时候曾经说过:“一部关于一般对象的新论述以及其他一些情况表明,至今为止,洛克关于一般观念之学说的错误所得到的阐明是多么微乎其微。” [1]140,A134/B135①这鲜明地表明了胡塞尔对洛克关于一般对象学说的批评态度。尽管洛克“除了承认个体对象之外,也承认一般对象”,和胡塞尔有类似之处,但胡塞尔绝没有仅仅停留在洛克的意义上,他对一般对象的研究集中反映在《逻辑研究》尤其是第二卷第一部分的第二研究中。
一、纯粹逻辑学意义上种类观念统一的批判对象
早在《逻辑研究》第一卷,胡塞尔在反驳心理主义时就提出存在一个特有的真理领域,这个领域是纯粹逻辑学的领域 [2],“论证纯粹逻辑学的可能性以及确定它的可能范围”是“纯粹逻辑学应当承担的基本任务” [3]。这些任务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确定纯粹含义的范畴、纯粹对象的范畴以及它们之间有规律的复合;第二个层次是对建立在这些范畴中的规律和理论的寻找;第三个层次是建立有关可能的理论形式的理论。《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研究《表述与含义》就是对第一层次——确定范畴——的深化” [4];而第二研究《种类的观念统一与现代抽象理论》则讨论了贯穿西方哲学始终的主线之一——共相和殊相的关系。这一关系源自于古希腊哲学对世界本原的寻找,经过古罗马哲学一般和个别的讨论、基督教哲学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近代认识论哲学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批判、康德哲学对二者的调和,直到胡塞尔才被视为真正得到了解决。胡塞尔对此问题的探讨归属于纯粹逻辑学任务的第二个层次。经过胡塞尔的一系列批判,心理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被弃若敝履,洛克的抽象理论似乎被完全高高挂起,而贝克莱、休谟等人的“现代唯名论”似乎成为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但是,胡塞尔对共相和殊相问题的解决是最终解决吗?今天,心理主义的回潮、存在主义的鼎盛、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告诉我们,共相和殊相问题似乎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胡塞尔的批判从实在论开始,按照胡塞尔,在关于一般对象学说的发展中,有两种错误的实在论解释。第一种“在于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对普遍之物做实在设定(Hyostasierung) ②,在于设想处于思维之外的一个实在的种类存在……这种实在论的典型代表是柏拉图的理念论”。 [1]128⁃129,A121⁃122/B122⁃123胡塞尔认为,还有一种实在论,它“以心理学的方式对普遍之物做实在设定,设想处于思维之中的一个实在的种类存在” [1]128,A121/B122,这是一种心理主义的实在论,这种实在论的代表是洛克。但是,“人们为了避免洛克抽象观念的荒谬性,必须完全否认一般对象是特殊的思维统一,并且完全否认一般表象是特殊的思维行为。由于人们误解了一般直观与一般含义之间的区别,因而他们会将后一种‘概念表象’连同其特殊的表象意向加以拒绝,并且将个体的、仅在心理学上特殊的个别表象视为‘概念表象’之基础” [1]128⁃129,A121⁃122/B122,这样,就会有第三个错误的解释,这个解释是唯名论的解释,“这种唯名论相信,它可以以各种形式在对象和行为方面将一般之物解释成个别之物。”[1]129,A122/B122
这样,在共相和殊相关系问题上,胡塞尔的批判实际上分为三个层次:一、对传统实在论的批评,主要针对柏拉图及其拥趸;二、对心理主义实在论的批评,主要针对洛克;三、对唯名论的批评,主要针对严重受洛克影响的贝克莱和休谟。在《逻辑研究》中,他认为,柏拉图化的传统实在论早就已经不值一驳,可以置而不论;而洛克是贝克莱和休谟的基础,因此,在对“普遍之物”的批判讨论中,对洛克的批判就成为关键。
二、洛克关于“普遍之物”的心理主义实在论思路及胡塞尔的批评
从唯名论和唯实论斗争到经验论和唯理论对立的一般渊源关系上来讲,唯理论继承了唯实论,而经验论继承了唯名论,胡塞尔将经验主义的洛克看作实在论,那是因为洛克的心理主义与柏拉图的实在论具有共通之处。一般而言,在近代哲学中,经验论与心理主义相伴而行,作为心理主义者的洛克和柏拉图一样,对一般之物进行了实在设定,但在柏拉图那里,这个实在是理念,而在洛克这里,这个实在是观念。然而,洛克的实在已经超越了感性一般,观念已经不像理念那样是并列于感性事实的实在,或者是比感性事实更为真实的实在,观念实在只存在于意识之中。洛克的实在论也不否认感性具体的实在性,感性具体是作为个别的实在,是在意识之外的;而观念是作为一般的实在,是在意识之中的。胡塞尔分析洛克的思路说:“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普遍之物”这样一类东西,实在地实存着的只有个体事物,它们根据其种、属方面的相同性和相似性而依次排列。” [1]132⁃133,A125/B126但他又分析洛克的观念说:“如果我们维持在直接被给予之物、被体验之物的领域内……维持在‘观念’的领域内,那么事物现象就是在如下意义上的‘简单观念’的复合:同一种简单观念、同一类现象特征通常会以个别的或群体的方式一再地回归到这些复合中。”[1]132⁃133,A125/B126
根据洛克的一般观念,当我们指称一个事物的时候,这些事物都为人的意识所显现,由此,其本身成为意识。我们对思维对象的指称已经先天受我们意识的指导,我们的意识规定着思维对象的确定性。并且,当我们在指称事物的时候,我们不仅用专有名称来称呼它们,而且用共有名称来称呼它们,但无论是专有名称还是共有名称,事实上我们所指称的都是意识。意识是存在着的事实,无论以何种形式存在,全部哲学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人的意识原理问题。根据此原理,当我们用一个普遍名称来指称许多事物的时候,这个事实已经表明了,必然有一个普遍意义、一个普遍观念与这个普遍名称相符合,在这里,普遍意义、普遍观念起着普遍名称与对象的联系中介作用,它具有一个对所有对象来说都具有的共同特征,即,普遍名称的同义性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有效:对象只是借助于这个特征,而不是借助于另一个特征而得到指称。因此在普遍含义中进行的普遍思维具有一个前提:“我们具有抽象的能力,即具有那种从作为特征复合被给予我们的现象事物中划分出局部观念、个别特征观念,并且将它们与作为其一般含义的语词相联结的能力。” [1]133,A126/B126⁃127这种划分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通过这样一个事实而得到保证:“每一个普遍名称都具有其本已的含义,即负载着一个仅仅与它相联结的特征观念;与此相同,我们可以随意抽取出某些特征并使它们成为新的一般名称的特殊含义。” [1]133,A126/B127
但是,胡塞尔认为,“‘抽象观念’或‘一般观念’的形成、精神的这种‘虚构’和‘造作’的形成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们呈现出来时并不像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容易。” [1]133,A126/B127比如说洛克的三角形,它既不能是直角的,也不能是锐角的,还不能是斜角的,三角形没有任何形状,我们如何去抽取出一个一般观念或者一般特征呢?也正因为如此,胡塞尔认为洛克的“观念”存在问题:观念被洛克定义为内感知的每一个客体,它同时在“表象”这一狭窄的含义下被理解;并且,“洛克将表象与被表象之物、显现与显现物、行为与被意指的对象混为一谈” [5]56;与此相关,将那些属于这个对象的特征与那些构成表象行为之感性内核的内在内容相混淆;更为重要的是,在洛克那里,在直观表象意义上的表象和在含义表象意义上的表象之间根本不存在区别,含义意向等同于含义充实。胡塞尔认为,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错误,使洛克达到了这样一种认识:每个普遍名称具有自己的普遍含义是不言自明的。并且这种自明性让洛克主张:每个普遍名称中都包含着一个普遍观念,“而这个普遍观念对这个普遍名称来说无非只是对特征的一个直观性的特别表象。” [6]22洛克提出这一主张的必然原因在于,“由于语词含义是根据这个特征的显现才充实自身的,因此他将语词含义和这种显现本身混为一谈;这样,被区分的含义,无论它是含义意指还是含义充实,就变成了对特征的被分离的直观。由于洛克同时也没有将特征的显现和显现的特征区分开来,正如他也没有区分作为因素的特征和作为种类属性的特征一样,所以他提出的‘普遍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对‘普遍之物’的心理学实在设定” [1]138,A132/B132,“普遍之物”对于洛克而言仅仅是一种实项的意识材料。
由此可见,洛克关于“普遍之物”的实在论思路实际上是与他的心理主义立场分不开的,而这一点恰恰是胡塞尔从《算术哲学》到《逻辑研究》进行转变的大背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一卷中猛烈批判了心理主义的整个体系,这种批判是为了阐发其现象学理论自身,在《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研究中,胡塞尔对洛克以及整个“现代唯名论” ③体系的批判想搞清楚的关键一点在于:作为共相,“普遍之物”是否存在?
然而,胡塞尔的批评却搞乱了整个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的论辩体系——我们实不知这种搞乱是否是一件幸事,但我们确知其根源在于康德对唯名论和唯实论的调和。在康德以前,唯名论认为,存在的事物都是个别的,心灵之外没有一般的对象,共相不过是名词而已。它分为极端唯名论和温和唯名论,极端唯名论者认为共相不过是名词和声音,而温和唯名论认为共相不仅仅是空洞的名称和记号,而是有意义、有内容的概念,因此被称为概念论,这种概念论认为,共相要么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要么和个别事物完全同一,存在于人类理智之中。与唯名论针锋相对,唯实论则认为,共相不仅是心灵的一般概念,而且是这些概念的外部实在。它也分为极端实在论和温和实在论,极端实在论者继承柏拉图,认为这些概念对应于一个更高的外部实在,而温和实在论者主张共相是一种实体形式(隐蔽的质),它既存在于个别事物之内,又存在于人的理性之中,是个别事物的一般本质。 [7]胡塞尔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在《逻辑研究》第二研究中“把‘概念论’划归到‘实在论’的范畴下,即‘心理学化的实在论’,把‘唯名论’仅仅指极端唯名论”。 [8]
三、胡塞尔的“普遍之物”:意指性表述与含义相统一
这样一来,“概念实在论所导致的结果在于,人们不仅否认了种类的实在性,而且也否认了种类的对象性”。 [1]115,A110/B110作为概念实在论的洛克不否认共相的对象性,但作为受洛克影响的唯名论者贝克莱和休谟却要承担因一般对象的丧失而导致的苛责 ④。在洛克那里,共相被创造出来作为人类把握知识的工具,他说:“总相和共相不属于事物的实在存在,而只是理解所做的一些发明和产物。而且它之所以造它亦只是为自己的用途,只是它们作为一些标记用——不论字眼或观念。” [9]胡塞尔也总结洛克的思路说:“现在我们指称这些事物,并且不仅用特有名称来指称它们,而且主要是用共有名称来指称它们。但事实在于,我们可以用同一个一般名称来同义地指称许多事物,而这个事实表明,必然有一个一般意义、一个‘一般观念’与这个一般名称相符合。” [1]132,A125/B126
就“普遍之物”的对象性这一点而言,胡塞尔和洛克显然具有共识,但胡塞尔的种类对象与洛克有明显不同。洛克只承认个别之物的实存,将“普遍之物”局限于意识之中;而胡塞尔则认为个体之物与种类之物都是存在的,在他看来,无论具体之物还是抽象之物,无论实在之物还是非实在之物,他们都作为对象而存在,因而都是一个含义统一。在对种类和个别进行区分的时候他说:“我们意指种类的行为与我们意指个体之物的行为是根本不同的;无论我们在后一种行为中所意指的是整个具体之物,还是一个在这个具体之物上的个体部分或个体标记。” [1]113,A108⁃109/B08在这种意指中,对象的现象连同那些通过这些内容而被体现出来的属性对我们构造其自身,它既是一个个体的意指行为的表象基础,也是一个种类化的立义与意指行为的表象基础;这就是说,当这个事物,或者说,当这个事物的标记显现时,我们所意指的并不是这个对象性的标记,不是这个此时此地,而是它的内容、它的观念;我们所意指的不是这所房屋上的红的因素,而是这个红。在此过程中,作为普遍对象的种类就通过这种立义方式的特征而得以成立,与此密切相关的种属也如此产生,那种在种类与个别之间存在着的原始关系得以显露,那种通过比较来统观杂多个别的可能性得以形成。在此情况中,个体因素都是一个个不同的因素,但在每一个情况中实现的都是同一个种类。
在此基础上,胡塞尔“回溯到那些指称着种类的名称的含义(意义、所指)上去,回溯到那些要求对种类有效陈述的含义上去” [5]61,对一般和个别作了更进一步的区分:种类的个别性、个体的个别性、种类的普遍性、个体的普遍性。他说:“在个体个别性和种类个别性之间进行区分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经验事物是个体的个别性,数学中的数和流型、纯粹逻辑学中的表象和判断(概念和定律)是种类的个别性。” [1]115,A110⁃110并且,“与个体的和种类的个别性之间区别相符合的是同样本质性的个体的与种类的一般性(普遍性)之间的区别。” [1]115⁃116,A111⁃111这四种类别对应于判断中的四种情况:个体单个的判断,如:苏格拉底是一个人;种类单个的判断,如:2是一个偶数;个体普遍的判断,如:凡人都会死;种类普遍的判断,如:所有纯粹逻辑学的定律都是先天的。因此,胡塞尔明确地判断说:“一个种类在认识中真实地成为对象,并且,与种类有关的对同类逻辑形式的判断是可能的,就像与个体对象有关的判断也是可能的一样。”[1]116,A111⁃111
普遍对象在胡塞尔那里以一种与个体行为有本质差异的行为方式被意识到,它在对那些指称着种类的名称的含义(意义、所指)上和那些要求对种类有效陈述的含义上可以明晰地获得。一个种类在认识中能够真正成为对象,而且与种类有关的对同类逻辑形式的判断是可能的,就像与个体对象有关的判断也是可能的一样。甚至,逻辑表象、统一含义都是一些观念对象,无论它们本身所表象的是“普遍之物”还是个体之物。“在胡塞尔看来,个体的东西与种类的东西(一般之物),实际上都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含义,它们都是观念对象。所谓一个‘观念对象’,就是一个‘含义统一’。” [5]57并且,就含义本身而言,它是明显统一的,语词存在偏差实际上不是含义的偏差而是意指的偏差,含义本身并没有变化。胡塞尔将含义本身(Bedeutungselbst)与作为行为的意指(Bedeu⁃tenalsAkt)区分开来,在对存有偏差的意指行为与观念统一的含义进行了细致分析之后指出,“人们对个体对象和种类对象作出各自不同的陈述和意指时,这个陈述或意指本身可能不会完全相同,但不论主观的陈述或意指如何变化,它们所关涉的含义本身却始终是同一的和稳定的。” [5]61
四、胡塞尔对洛克的超越与局限
这样我们看到,在对“普遍之物”的回答上,胡塞尔至少在两个方面比洛克推进了一步:第一个方面是,一般对象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存在的,或者说是真实的?第二个方面是,一般对象相对于个别对象具有何种特殊地位和权利?
对于第一个问题,胡塞尔认为,从含义统一或观念统一的角度来看,决定一个对象是否真实存在的关键在于:对这个对象的意指性表述是否与这个对象本身的含义统一相符合,而与这个对象是个别还是一般无关。一般之物的存在,不是因为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它是与感性现实相并列的客观实在,也不是像心理主义实在论者所说的那样,是在意识中的存在,而是由于它们都是被陈述或被意指的对象(意向相关项)。按照胡塞尔,即便是个体之物,如果没有进入现象学分析,不是作为意识分析的对象或意向对象,它也因为是外在的自然存在而必须悬置,从而中止做出存在与不存在的判断。
对于第二个问题,胡塞尔认为,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类似于一种种类与直观对象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种类与在直观对象上显现出来的种类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洛克抽象意义上的关系,洛克的抽象忽略掉个体事物的特殊成分而保留个体事物之间相似的成分,但胡塞尔认为这种个体之间的相似关系是不存在的,红布一点都不红,白雪一点也不白,我们并不能抽象出稍微红一点的红布和粉红色的红布之间的相似成分红,我们直观一块红布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具体的、个体的红布,我们可以意指它,但我们也可以意指在这块红布上显现出来的红的种类本身。在个体的红布中,我们直观到的是这个对象性的特征;而在种类的红本身中,我们直观到的不是对象性特征,而是红的“内容”,即红的“观念” [5]58。“红的对象和在它身上被突出的红的因素是显现出来的,而我们所意指的却毋宁说是这同一个红,并且是以一种新的意识方式在意指这个红,这种新的意识方式使种类取代个体而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1]112,A107/B107
如此一来,按照胡塞尔,个体永远不能成为我们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当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说存在不可言说的时候,我相信他的意思源自于胡塞尔对个体的批判。只要我们一开口言说,我们说出来的东西即成为包含我们所意指个别对象的一般。例如,当我们说“苏格拉底”这个概念时,凡是学哲学的人都知道他是古希腊的一位伟大哲学家,那是因为我们思维的惯性让“苏格拉底”这样一个概念和“人”这样一个概念联系在了一起。但就“苏格拉底”这个表述本身而言,他却是古希腊那个伟大哲学家作为个体意义上的一般,个别和一般永远都在关系中,离开了关系我们永远无法言说何谓个别?何谓一般?假如我们设想“苏格拉底”这个名称代表了以下不同的含义:一位古希腊的圣人苏格拉底;一只我养的宠物小猫起名叫苏格拉底;还有我的邻居,他的名字也叫苏格拉底。那么在这样的一对对关系组合中,“苏格拉底”这个名称又成了一般。
然而,特瓦尔多夫斯基却说:“通过一般表象而被表象的东西是一个对这个一般表象来说尤为特殊的对象。” [10]尽管胡塞尔在一般对象对象性的基础上确立了其存在性,但并不代表一般对象就具有了超越个体对象的特殊地位和权利,所以很难说胡塞尔的研究使种类超越了个体。事实上他回避了个体和一般何者更真实的争论,或者说,在胡塞尔那里,一般和个别何者更真实不重要了。我们对一件事物既可以直观到个体,也可以直观到包含了个体的类;在个体中,我们直观的是个体的对象性特征,在种类中,我们直观的是种类的“内容”和“观念”。因此,作为红的个体和红的种类的一般都是存在的,个体对象和一般对象也可以说都是真实的(并存的)。
最终我们看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所关注的既非直观的具体个体,也非这个客体的一个“抽象的部分内容”,而是在种类统一意义上的观念。如果说,这个观念也是在逻辑意义上所进行的抽象的话,这种抽象不同于洛克形成简单观念的简单抽象,而是在先验逻辑学和现象学认识论上被标识的抽象。这种抽象不是对一个部分内容的单纯突出,而是那种在直观基础上直接把握种类统一的特殊意识。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的《逻辑研究》的内容,均源自于倪良康教授以荷兰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出版的埃德蒙特·胡塞尔《逻辑研究》两卷本的考证版译出的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年12月第1版。凡引文均在正文中标明出处,除了在注解中给出卷数、册数和中译本页码以外,还分别标明A版(第1版)和B版(第2版)的页码,这些页码在中译本中作为边码出现。以下不再注明。
②Hyostasierung源自于拉丁词汇,其希腊文为hypostasis,意为基础、实体、实在,其动词意义为“将……视为实在的或者实存的,将……实体化”。倪梁康先生将其译为“实在设定”。
③指胡塞尔写作《逻辑研究》时代以贝克莱和洛克为代表的唯名论,它实际上相当于传统唯名论和唯实论斗争意义上的极端唯名论。
④在这里指人们对以贝克莱和休谟为代表的怀疑论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