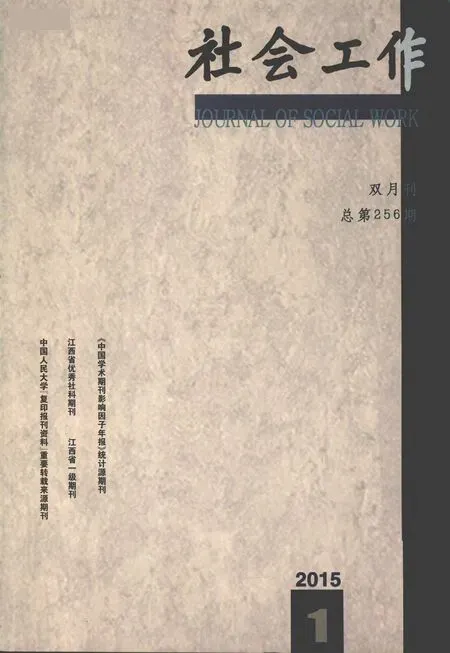可持续生计:一个城市减贫的新范式
2015-12-09胡彬彬
胡彬彬
胡彬彬,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贵阳 550025)。
可持续生计:一个城市减贫的新范式
胡彬彬
胡彬彬,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贵阳 550025)。
城市贫困群体区别于农村贫困人群,具有致贫根源上的结构性、经济上的更脆弱、环境上的高风险、社会中的被排斥、心理上的边缘化等特征。起源于上个世纪末的“可持续生计”概念虽然最初立足于解决农村背景下的生计问题,但是在国外已经开始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城市生计分析,也为我国的城市减贫工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将可持续生计分析应用于我国城市减贫工作中,需要对其资产要素、作用路径以及具体内容进行“本土化”的修正,构建适应于我国国情的城市贫困群体生计框架。
可持续生计 城市贫困 范式
国内外的反贫困理论研讨和政策实践曾经都将贫困主要视为一种农村现象,但随着经济社会体制转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市贫困者的行列正在不断扩大。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社会学家对于“城市贫困会随着现代化的‘起飞’而自然而然地消失”的推定,并未成为现实。据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3年年末,我国共有2061.3万人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在城市整体经济形势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不可忽视还存在着一个数量如此庞大的生活困难群体。城市贫困群体对于工作、住房以及城市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一切都亟待政策研究者们寻找城市减贫的新出路。
一、城市贫困群体的特殊性
城市贫困具有贫困问题的诸多共性,但也因其主体的个体特征、社会环境、生计方式的不同而区别于农村贫困。构建应用于城市背景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必须对城市贫困群体的特性有清晰把握。
(一)根源上的结构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具有鲜明的城乡分割特征,城镇职工的福利高度依附于单位,拥有固定职业的居民对单位福利制度抱有强烈的期待。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大批国有企业职工难逃下岗或失业的命运,失业人员大量出现。同时,新经济组织不断发展壮大,职业人口流动加快,进城务工人员队伍不断增加,这些都为城市中结构性贫困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正如学者们指出的,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最根本的变化就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行政因素逐渐减少,市场因素逐渐增加;先赋因素的作用逐渐下降,后致因素的作用正在上升(孙立平,1994:51)。社会结构的分化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和新的利益群体、职业群体的大量出现。我国已经从一个经济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不平等程度较大的国家(李强,2005:246)。这部分贫困者区别于以往城市中的“三无人员”,被研究者称为“新贫困群体”。城市新贫困人口既具有生活状态差、收入水平低等传统贫困的特征,又有缺乏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机会,在城市生活中处于边缘化、家庭负担重、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固定资产、居住高度集中封闭、主要分布在一些困难行业和企业等特点(刘璐琳,2012:53)。这些因体制性原因导致的城市贫困具有再生性和被动性,表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二)经济上的更脆弱
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著作《贫困与饥荒》中已经对不同生产方式的个体所拥有的权利关系做出了经典阐述:“收益分成佃农所得到的报酬是可以直接食用的粮食,不需要通过变化莫测的市场。相反,接受货币工资的工人则不得不依赖于其货币工资的交换权利……当饥荒发生时,佃农往往比工人更具有相对优势……类似的,其他服务业人员或出卖手工业制品的人——像工资劳动者那样——往往比种植粮食的农民更容易遭受饥荒”(阿马蒂亚·森,2001:11)。在资本市场发展高度完善的今天,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所拥有的交换权利差异则更为典型。城市贫民或许要花更多的钱来购买商品和服务,并且在面临市场状况变动、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工资实际购买能力下降的状况时就显得更为脆弱,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近乎完全货币化的经济之中。
(三)环境上的高风险
与经济上的脆弱性相伴随的,是城市贫困群体在生活环境方面的高风险性。虽然我国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贫民窟”,但在很多城市都存在弱势群体密集居住的“棚户区”、“贫困社区”、“城中村”等区域。这些居住环境具有一些共性:高度拥挤;环境脏乱;配套设施不足,用水用电用火安全无保障;公共卫生设施差甚至没有;工业污染威胁;暴力、犯罪多发;等等。这一切都让城市贫困群体处于严重的环境健康风险中。曾有西方学者预言,“不断增长的贫困状况、自然环境退化的状况、避难场所的不足以及对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下降,所有这些情况综合起来,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城市民众的健康状况要比周围农村地区人口的健康状况恶化得快”(Pryer,J.&Crook,N.,1988:5)。
(四)社会中的被排斥
中国的乡土社会结构是一个以己为中心,亲属关系、朋友关系为经纬的层层展开的“差序格局”,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制度、礼治秩序在现代化浪潮下经受着巨大的冲击。农村社会的人情礼俗纽带受到的冲击较小因而保存较为完好,而城市居民的生活则早已被工业化的钢筋水泥进行了彻底的洗礼。大部分城市贫困群体不仅不能享受到远亲近邻等社会网络资本的支援和照顾,反而会遭遇种种排斥。集体冷漠使得中上阶层对城市贫困人群的境况熟视无睹,有识之士欲施以援手却又遭遇信任危机,或者还背负着消极的道德评判烙印挥之不去。许多贫困人群居住在高度不平等的城市之中,以致不平等以及与此相伴的支撑着社会排斥的种种关系,已经成为城市贫困和城市社会政策的一个关键性维度(Beall,2002:41)。城市贫困居民或许会比农村贫困人群更能够接近各种设施和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居民必定能够支付得起这些设施和服务。比如,贫困的女性会被诊所拒绝诊治,或者,那些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儿童可能会被学校拒之门外(Beall,1995:427)。
(五)心理上的边缘化
目前的城市贫困人群有很大一部分由“新贫困”阶层组成,他们由过去端“铁饭碗”的令人羡慕的生活演变为靠领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在心理上无疑是承受了巨大的落差。而城市低保制度所采用的家计调查、张榜公示等程序也在无形中刺痛贫困群体的神经。另外,来自经济生活的焦虑、相对剥夺感以及对命运的自我掌控感不足,都会对贫困群体产生社会心理上的负效应:一方面会导致他们对改革成果的评价趋于消极,另一方面会阻碍他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积极性。因此,无论是在经济方面的工作意愿,还是政治民主参与,或者对新技能新知识的学习欲望,都表现出一种“疏离”的状态。他们知识贫乏,无远见卓识,只关心个人事务,相信“宿命论”而自暴自弃(毛增锋,2008:162)。甘愿接受“下等公民”的标签,自我认同身份的“边缘化”,形成一种封闭和自我维系的心理体系。
二、可持续生计:一个分析框架
可持续生计的发展思路可以追溯到1988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该会议提出了“可持续性生计”这一具有整合性的概念,其含义是指“具备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须的充足的食品与现金储备量以及流动量”(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2006:135)。在联合国发展委员会的政策文本中,“可持续”概念也通常在人类生计对环境的影响角度被提出。其后,该概念被学者们不断扩展,能力概念、政治资本等贡献因素都被加入原始框架中。“生计系统是由一套复杂多样的经济、社会和物质策略构建的,这些策略通过个体借以谋生的行为、财产和权利得以实行。人们进行选择,利用机会和资源,同时又不妨碍他人目前或将来的谋生机会——稳定的生计即由此获得”(纳列什·辛格、乔纳森·吉尔曼,2000:124)。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指出“稳定的生计可以使有关政策协调地发展、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地使用资源”。2002年,在认识到迅速城市化带来的城市人口迅猛增加,居住在城市中的极度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的趋势下,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提出了首个城市发展战略,“满足城市贫困的要求”,这是对1997年英国政府发展白皮书中一系列减贫及发展目标的回应。它对如何让贫困人口更好地理解生计,以及让政府更有效率地帮助人们建立自己的资产,获得服务和生活的机会作出了规划。

图1 原始可持续生计维持框架
如上图所示,可持续生计框架是一个动态系统,在整个相互作用的系统中包括了脆弱性背景、生计维持资产、转型结构和过程、生计策略、产出等多个变量。可持续生计分析区别于传统的贫困分析,它并不聚焦于贫穷问题本身,而是认为穷人的相对贫困和经济状况应该从人本身来理解。从可持续生计框架来看,贫穷是多维度的,而且每个家庭的贫困状况会随着时间变化而变化,因此传统的收入贫困线或者消费测量的手段并不能充分代表贫困。相反,需要对人们所采取的生计行动的范围和策略进行整体的、参与性的评价,尤其重要的是穷人在执行他们的生计策略和克服不可控的外在条件带给他们的脆弱性时对于资产的可及性。因此,可持续生计框架强调的是对于穷人“财富”的建设而不是关注他们的“贫困”症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持续框架完全排斥传统上以收入、支出作为衡量贫困的标准,而是设想民众同时会追求更加多元化的目标。既包括收入的增加,也包括健康水平的改善,还包括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自身脆弱性的减少并能有效规避风险。实现这一系列目标就需要诉诸于一系列资本性资产,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财政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以及原始框架中所缺乏的政治资本。
因此,可持续生计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将贫困人口置于分析的中心,遵循整体性原则,强调微观与宏观因素之间的联系。将经济增长与社会投资目标相结合,运用多机构、跨部门协作的方式来共同促进发展,国家、公民社会、私人部门和国际机构都被包括在分析框架中,是一个由一系列彼此相互作用的变量所构成的动态模型(宋宝安、贾玉娇,2009:207)。由于可持续生计系统具备强大的诊治功能,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分析和解决贫困问题的依据,这一思路开始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政策制定与发展计划过程中,往往被研究人员及政策制定者作为诊治贫困问题的技术工具。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这种分析方法都只在农村背景下得到广泛应用。关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是否也适用于城市背景并能提供一个有效的城市减贫策略,国外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尽管存在一些质疑之声,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应用于城市贫困分析(Carole Rakodi&Tony Lloyd-Jones,2001:16)。
三、我国城市贫困群体可持续生计模型的构建
充分衡量我国传统文化、国情的特殊性,以及城市贫困之于农村贫困的特性,可从以下方面对
原始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本土化”修正。

图2 我国城市贫困群体可持续生计维持框架
(一)资产要素的增补
原始可持续生计框架是在20世纪末提出,而且是基于对农村问题的关注,因此忽略了生计主体政治资本的重要性。然而,将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当前对城市贫困的分析时,政治参与则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变量。政治资本可以被界定为因政治身份、政治权利、政治参与行动而产生的影响力。这一因素在城市个体、家庭或群体的生计策略获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证调查数据显示,政治资本对城市居民收入、行业收入、地区收入都有显著影响,而且与收入不平等直接相关(杨灿明、孙群力,2011:35)。这意味着政治资本不光对资产总量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还会通过对其他资产因素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到整个生计框架。因此,将政治资本融入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
(二)作用路径的调整
可持续生计框架由五个部分组成,其核心内容为生计资产,另外还有脆弱性背景、转型结构和过程、生计维持策略以及生计维持系统的产出。其中,脆弱性背景不仅会直接作用于生计主体的资产建设和积累,而且会影响到生计维持策略的可及性,同时会影响生计系统的产出效率。转型结构和过程的作用路径与之基本类似,会同时影响到生计资产、策略选择以及生计输出。生计维持策略与生计资产之间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生计策略对生计资产的积累会带来直接的积极效应或消极效应;另一方面,资产的拥有量会增加或减少策略的可及性,比如财政资本的充足可以让生计主体选择储蓄或者投资等各种方式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生计危机。生计资产与系统产出之间也是相互作用关系:资产的充足会带来更多的收入、更好的福利、食品的安全,而资产的匮乏无疑将导致难以维生的收入及匮乏的福祉;而系统产出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各种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三)具体内容的本土化
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脆弱性背景包括:重大事件的打击,比如疾病、自然灾害;长期趋势性问题的影响,比如人口统计学上的趋势、自然资源储备量的趋势;季节性周期波动的作用,比如季节
性的商品价格上涨、就业机会变化(Carney.D,1998:3-23);另外,还会受到更多的环境恶化带来的威胁。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人口的52.6%集中在城市,集中在城市中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创造了整个国民经济总量的90%。同时,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从2010年起已经位列世界第一,其中大部分来自城市;201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空气质量最差的前100个城市中有21个来自中国(郑思齐等,2013:72)。城市中的人口、工业、交通的高度集中,都带来了城市贫民的“高风险”。近几年中国城市中继发的因大型工业项目选址建设、垃圾焚烧、高压线及输变电站建设、非法排污、具有噪音和辐射影响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群体性事件就充分说明中国城市环境问题的严峻局面。与城市其他阶层成员相比,因自身资产的匮乏,贫困群体欠缺对疾病预防与免疫、卫生安全的重视和能力,各种传染性疾病、寄生虫疾病以及化学污染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将严重威胁到城市贫民的健康,增强其脆弱性。
在转型结构与过程方面,我国城市贫民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的结构主体应该既包括公共机构,如行政机关、立法部门;也包括社会组织,如各种非政府机构;还应该包括私人部门。这三者在可持续生计维持系统中应是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公共机构负责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通常将公平原则置于效率原则之先,而且因其巨大的国家强制力和可支配力在减贫行动中位于中流砥柱的地位;各种社会组织则应充分发挥其资源整合、行动倡议功能,为生计主体担当起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而私人部门则应充分发挥其效率优势,在为贫困群体的生计维持策略中提供多样化服务,我国越来越多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外包都是其发挥作用的最好平台。在转型过程中,与生计相关的法律、政策、制度、文化在各个层面发挥作用,从个体层面直到国际舞台。经济与劳动力市场政策、生计支持项目、社区发展计划、社会庇护服务、医疗与环境卫生项目、城市空间规划等等,在城市背景下都是关键性支持要素。
生计策略是指人们为达到生计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做出的决策,以及各种选择的结合。生计研究蕴含一个潜在假定:人们的目标旨在寻求安全的生计。生计主体拥有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他们自我决定应该如何使用和支配这些资产,比如通过节省、储蓄,或者为完成特定的义务和责任而进行处置,或者发展共同的支持网络。而这个决策的过程既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资产情况,也取决于他们发现并利用生计机会的能力。决策的目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节省、储蓄或者多样化自己所拥有的资产组合来应付各种压力、打击,提高从危机中复原的能力;(2)维系或者强化能力与资产;(3)为下一代提供可持续的生计机会(Chambers.R,1989:1-7)。个体和家庭根据他们自身所处的环境及变动的背景要素来调整资产组合。在我国目前的城市贫困群体中,很大一部分群体的生计策略较为单一,他们或者仅仅依靠非正式就业的货币工资,或者从事不稳定的自雇职业,或者彻底地依靠国家救济,这就为其生计的可持续性带来较高风险。任何一种生计方式都可能在外界环境的冲击下迅速跌入不能满足最低生活需求的范围。因此,通过各方面的社会支持以及资产建设行动,提高贫困群体的生计决策能力和可选择范围,是我国城市减贫的当务之急。
生计维持系统的产出是生计策略的成就或结果。更多的经济收入、更高的幸福感、脆弱性的减少、食品安全性的提高以及自然资源利用方面的可持续等等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我国的城市背景中也别无二致。在我国城市减贫的长、中、短期发展目标中,关爱基金组织(CARE)在应对脆弱性、提高生计主体发展能力方面的“供给(provisioning)——保护(protection)——促进(promotion)”思路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参考。“供给”是指为维护贫困群体的基本营养水平和生命而提供的直接援助,一般在紧急事件的发生后实施,是一种针对“症状”的短期行为;“保护”旨在预防安
全性的降低,通过防止生产性资产的损耗或者对贫困群体的(从重大事件中的)恢复过程提供援助,关注的是导致贫困的直接原因;“促进”则聚焦于潜在的、根本性的导致不安全和脆弱性的原因,旨在建立个体或家庭的资产性基础,增加其对于生计策略的选择范围,并在一个长期的过程中改善他们的弹力,从而获得更完善、更稳定的生计产出成果(Drinkwater.M&Rusinow.T,1999:132)。
自20世纪末提出以来,可持续框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热烈的争论。其本身的整体性视角决定了其必然是一个持续的动态变化过程,并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具有不同表现。本文结合中国的国情尝试性地修正原始框架,并构建了中国城市贫困群体的可持续框架模型。但正如原始可持续框架的制定者们所指出的,任何图表或模型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对复杂现实的过度简单化问题,我们应当仅仅将其作为一个观察世界的导引或者棱镜。中国的城市贫困群体可持续生计框架也需要在实践中得到不断验证与完善。
[1]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2006,《发展型社会政策》,罗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阿马蒂亚·森,2001,《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3]刘璐琳,2012,《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城市新贫困问题治理研究》,《宏观经济管理》第12期。
[4]李强,2005,《从社会学角度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科学战线》第6期。
[5]毛增锋,2008,《城市贫困人口心理分析及对策研究》,《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第4期。
[6]纳列什·辛格、乔纳森·吉尔曼,2000,《让生计可持续》,《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4期。
[7]宋宝安、贾玉娇,2009,《社会管理策略的转型:从现代化到可持续生计》,《社会科学战线》第10期。
[8]孙立平,1994,《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9]杨灿明、孙群力,2011,《政治资本与居民收入分配——来自中国城市问卷调查的证据》,《财政监督》第33期。
[10]郑思齐、万广华、孙伟增、罗党论,2013,《公众诉求与城市环境治理》,《管理世界》第6期。
[11]Beall,2002,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exclusion in cities:framing the debate with lessons from Africa and Asia,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14(1).
[12]Beall,1995,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networks among the urban poor in Pakistan,Habitat International,19(4).
[13]Carney.D,1998,Implementing the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pproach,in Carney.D(ed)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What Contribution Can We Make?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London.
[14]Carole Rakodi,Tony Lloyd-Jones,2001,Urban Livelihoods:A People-centred Approach to Reducing Poverty. 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15]Chambers.R,1989,Vulnerability,coping and policy,IDS Bulletin,vol 20(2).
[16]Drinkwater.M and Rusinow.T,1999,Application of CARE’s livelihoods approach,paper presented to the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Natural Resource Advise Conference.
[17]Pryer.J and Crook.N,1988,Cities of hunger:Urban Malnutrition in Developing Counties.Oxford:Oxfam.
编辑/陈建平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族群认同与民族地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问题研究”(项目号:12CSH092);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贵州省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项目号:09ZX09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理论和制度构建研究”(项目号: 10JZD0033)。
C913
A
1672-4828(2015)01-0046-07
10.3969/j.issn.1672-4828.2015.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