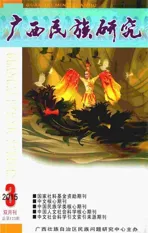城郊新村民族文化重构及价值:以南宁市郊留肖壮族新村为例*
2015-12-09秦红增王淇楸毛筱倩
秦红增 王淇楸 毛筱倩
一、研究缘起与概述
2006年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指出,中国自2010年起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实现人口、空间结构的两次转变,建设城乡平衡社会。其中第一次转变是从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转变是城市人口变为郊区人口,实现城乡平衡。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20%,人口在三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取消户籍限制,建立信用社会。[1]由此可看出城市郊区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该报告还指出,未来中国社会需要完成两次社会转型:一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二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城市社会向城乡动态平衡社会转型。众所周知,中国传统上以农立国,上下几千年所延绵的文化文明深深地植根于小农经济土壤里。因此,人口进城也意味着文化进城,“文化重构”是社会转型中面临的必然问题。
就近些年来的实践看,中国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可粗略概括为两条路径:一是“内生型”,即乡村社会主要依靠自身的产业发展来实现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如东部沿海或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兴办乡镇企业、经济开发区等实现的城市化,原来的乡村变为相对独立的城镇或卫星城,譬如东莞市就是由若干相对独立的城镇构成。离区域中心城市较远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借助农业产业化、外出务工,以及旅游、休闲、观光等第三产业实现的乡村都市化。在这些地方农民的身份、居住地虽然没有改变,但实际上生计方式、消费观念,甚至组织方式 (如成为公司的农户、员工等)已被纳入城市范畴。二是“外推型”,即乡村社会由于城市扩张而被“城市化”,典型的如“城中村村民”“城郊农民”等。这部分人群往往是无地或失地农民,是通过“新村”营建如城中村改造、“村改居”等造城运动,而不是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向城市社会的转型。其身份虽已变为城市社区居民,居住场所、生计方式、消费观念也渐渐向城市靠拢,但乡土社会固有的地缘性不但没有被触动或弱化,反而因为其要面对强大的城市扩张力量,迫于寻求新的谋生手段而得到强化,其农民的、家族的、民族的等身份更容易得到高度认同。[2]
在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尽管都面临“文化重构”问题,但不同的转型路径,重构方式也有所差异,各个地方实际情况千差万别,也难以借助几个模式来概观。不过就现有的社会实践及学术界的研究而言,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别:一是民族或乡土文化的自我更新,即立足于乡村自身的人际网络、土地、生态等,开办各式各样的农家乐、渔家乐、牧家乐、山家乐等,搞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民族旅游,以有效地把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都市生活观念结合起来,满足城里人或外地人闲暇消费需要。如笔者曾研究过的桂中武台新村的例子,乡村民众充分利用自身交通优越、生态良好、奇石丰富等优势,发展了以民族文化、奇石文化为特色的农家乐。[3]类似的例子可说是多不胜举。[4]二是“留住乡村文化”,这类大多为乡村城市化较为成熟的区域。相较于城镇的繁荣,原有的乡土文化凋敝零落,这有违于城市化的初衷,于是兴起了“文化留村”等保护乡土文化浪潮。譬如浙江省近些年来推行的“农村文化大礼堂”建设等。[3,5,6]三是城市或城郊“新村”文化重构,迫于城市失地或少地农民的生计,以往这类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农民的城市适应问题,在新的生存境况下,农民如何重构民族或乡土文化却涉及很少。但是这类村落由于被纳入到了城市发展的体系以内,文化赖以生存的空间历经了巨大变迁,文化重构形势更为严峻。
从目前中国内地城镇化实际情况看,“城中村”被视为顽疾,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对于市郊而言,这样的理念显然是不对的。从目前境况来看,中国快速地、贪大求全的“造城”运动已显现出不少弊端,而如何发挥“城郊”的优势则成为新型城镇化必然考虑的基本问题,因此我们更应当在这一区域进行“文化重构”,并形成有别于城市与乡村的“城郊文化空间”。可喜的是,近一两年来,随着保护乡村文化的呼声日渐高涨,一些学者也把眼光放到城镇化与文化保护方面来。如张士闪就提出要“以城镇化为契机重构乡土文化”,并提出了消除对乡土文化的偏见、培养农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让农民自我发展等措施。[7]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已经行动起来,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本文研究对象南宁市郊留肖壮族新村就是例证。
留肖壮族新村原名留肖坡地,人口340余人,是以壮族为主的民族聚居区。“新村”建设工程于2006年3月启动,目前建成的90户房屋中,已有89户入住。近年来,该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山地鸡养殖、鱼塘养殖、花卉苗木种植等特色种养业,走出了一条有产业特色、经营规模化的城郊型新村发展路子,并成为国家民委、财政部首批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首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南宁市统筹城乡改革发展试点。笔者曾于2008年前后陪同韩国人类学家全京秀去参观过一次,当时正在营建当中。2014年6月、11月,在当地干部的带领下,又分别两次前往该村进行田野调查,本文即是在两次调查中所收集的资料上论述而成。
二、留肖壮族新村民族文化重构的空间解析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同的研究者,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普里查德在其著作《努尔人》将空间分为物理 (朴素和实在,原本的)的、生态 (人口密度及分布状况,当地人建构的)的和结构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表达价值观,研究者建构的)的三重空间,更谈到在努尔人社会中,时间与空间的关系联络紧密,即由于人的因素,在哪个时段、哪个场所举行何种活动是约定俗成的,从而形成“文化空间”的概念。[8]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文化空间就是文化事项与活动分布于特定空间与时间交叠形成的场域,而这种场域依据文化的脉络而定。
伴随着城市的急剧扩张,郊区被无限制地纳入到了城市发展体系,大量土地被征用,传统城郊村落要么陡然间楼房林立,变为人口密度大、拥挤不堪的“城中村”,要么异地搬迁,另立具有商贸、租赁、住宿等功能的“新村”。无论是哪类形态,农民传统的生计方式都已不复存在。他们主要依靠地租、楼租等租金生活,所寻找的新职业多为散工、零工,技术含量低,稳定性差,收入少。如留肖新村,尽管当地政府已下了很大力气,但在新的特色种养产业链中,当地农民仍处在最低端,由于在市郊,出租的土地、房屋,有时连租金都收不回,因此村民的居住环境虽有了较大改善,但相较高额的生活成本,目前的生活质量并不尽如人意。如此一来,建立在土地及农耕之上的社会秩序被彻底打破,原有的、承载民族文化的空间已不复存在。
从逻辑意义来看,只要有人的存在,新的文化空间便是存在的,只不过与传统的不同罢了。当然,由于是新村建设,又是城郊,相较原始部落,其社会构成更为复杂,虽然很难按普里查德三个空间逻辑来描述,但是仍属于村落“空间”,我们可以依循其中的建构逻辑与过程来剖析其中的空间文化构成。
(一)政府与社区精英主导下的留肖“新村”营造
从留肖新村营造缘起来看,政府与社区精英的合力是关键。旧村原在山坡上,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南宁市城区的不断扩张,当地村民就萌生了异地迁村重建的想法。当时市政府刚好酝酿启动旧村改造工程,于是留肖村就成为南宁市较早实行“旧村”改造的村子,也成为着力打造的城郊壮族“新村”。
案例1:留肖新村的规划与建设
在访谈过程中,留肖新村王队长说:旧村距离新村只有3公里的距离,但是环境就差很多了。以前在旧村的时候,山高,我们从山顶上可以看见整个城市。村道很陡,大概有1米多宽,只能通行自行车、摩托车和手扶拖拉机。1980年的时候,开始分田到户,平均每人3亩土地,村里种了十几年的稻谷。在1986至1990年间,村民收入偏低,后来就种植辣椒、西瓜、甘蔗。因为农田收入偏低,一部分农田就变更为水产养鱼,但山路狭窄,所以收益不太好,生活上也很不方便。我20多岁的时候,就从村里走出来,后边其他人也陆续出来。1998年村里几位有威望的老人为了以后的发展,便商议村庄的重建事宜,后来所有村民也都同意了,我也帮着策划申请。新村建设是请专家规划设计,并且询问村民意见,村民全体同意后,才开始修建。我们村是壮族村,所以专家论证后,依据民族特色设计了图纸,村庄完全按照图纸的设计装修。此外,住宅也符合现代建房的标准,是按照防8级地震的标准建造。
(二)留肖新村壮族文化元素与标识
在传统乡村社会里面,村落文化体现在各类“物理”的空间当中,譬如戏台、庙宇、祠堂、学校等,典型的如侗寨里的鼓楼、风雨桥。如果没有了这些“空间”,村落文化便无从依附。经过持久的文化积淀,这些空间也就成为村落的“文化标识”,内化为村落“文化空间”。留肖旧村旧址就在离新村约3公里的山坡上,人们可以从高大茂盛的古树、破败的老屋、残存的晒场依稀辨出往日的景致,但与标准的村落文化空间相比,则少了许多。不过,在新村营造过程中,由于定位是“壮族”新村,壮族文化也就准确地体现在新村的文化“结构”里,新建的民居、办公场所、围墙,无一例外地将铜鼓等用作装饰,借以强调其壮民族内涵。换言之,新村里各类“物理”空间,已与壮族文化元素有机结合,以塑造出村落的文化标识。
案例2:留肖坡新村对壮族文化的融入
建成后的留肖坡新村有了文化活动综合楼、文化广场、灯光球场、文艺舞台、民族文化展示中心等配套设施,整合并且融入了许多壮族文化元素。居民住宅外墙上的装饰图案,多为铜鼓、绣球、壮锦、收获的果实以及壮族日常生活的生产工具等。特别是村民小组办公楼墙上,巨大的铜鼓和绣球图案在村庄之外的路上都可望见。在新建的“民族文化长廊”围墙上,有的写着标语,宣传广西精神、雷锋精神、民俗留肖等;有的画着民族体育项目,例如抛绣球、板鞋舞、打陀螺、抢花炮等,都配有壮文;还有的是对传统文化中的典故的介绍。这不仅是对村民进行宣传,还给外来者提供一个了解留肖坡的窗口。
(三)留肖新村“干栏式”居民楼
在留肖新村的设计、建造中,充分考虑了壮族民众的居住结构、民间信仰等生活惯习,统一把居民住宅建成“干栏式”的4层楼房。一楼可以用柴火做饭,大厅设置神坛,2、3、4楼可以用来居住,顶楼可以散步、养一些鸡鸭,这使得壮族在长久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生活习惯得到了留存,也使得壮族“干栏式”的建筑文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得到了继承与重构。
案例3:留肖坡村新村“干栏式”居民楼
留肖新村90栋家屋统一为4层“干栏式”居民楼,大门朝东南方向,一楼入内为大厅,正中是神坛,房间分别为主人房和厕所以及厨房,有些住户还和以前在旧村一样用柴火。2、3、4楼大都有两间房间,可为客房 (套间样式),也可用作仓库等,每层都有1-2间厕所。村里有些人将新屋的几层租出去,或者是单间出租,甚至整栋楼都出租,不过也有不愿意出租的。顶楼为悠闲场所,村民可以在楼顶散步,也可以养一些鸡鸭。两栋互相依靠的楼房顶层的看似“小阁楼”的装饰,实际上还可以用来区分两栋楼楼顶的使用权。
(四)留肖新村壮族文化展演
村落“文化空间”是硬件,如果没有相应的民族文化展现,仅是一些固定的文化符号外,新村文化重构可说是失败的。在留肖新村,当地人除了在空间上重构壮族文化外,还花了很大力气营造壮民族文化的活动氛围。如“每月一节”“节日文化展演”“民族工艺传承”等。
壮民族有着“每月一节”的节日习俗,大致为:春节的蚂拐节、陇峒节,二月的祭社节,三月的花王节、歌圩节、清明节、龙母节、布罗陀诞辰节、开耕节,四月的牛魂节 (敬牛节)、拜秧节,五月的药市节、农具节、五月五,六月的盘古诞辰节、莫一大王节、尝新节,七月的祭祖节,八月的请月神节、跳岭头节,九月的庆丰节,十月的赶降节,十一月的壮年和十二月的冬至。[9]从山上移居下来以后,留肖新村的“每月一节”节日保留了传统壮族节日习俗的框架和部分内容,还吸收了村外其他民族 (尤其是汉族)的节日传统,构建了新的“每月一节”节日习俗。
案例4:村王书记谈新村“每月一节”
正月初七开年,这是一年最大的日子,既是客人最多的一天,又是过得最隆重的节日。具体时间从初三到初七,新村在初七过节。到了初七这天,全村的家家户户都会摆酒宴请亲朋好友。二月初二为“春社”,是土地公的生日,当天要做糍粑吃,那是用鱼塘边一种叫白头翁 (音译)的草进行加工的绿色糍粑。另外还要吃土鸡蛋。这一天,全村人都要聚在一起吃一餐饭。三月三主要的活动就是拜山 (扫墓)和做糯米饭。四月初八拾垃圾,节日气氛较淡,但每家每户在这天也会杀鸡、鸭吃。这一天有“四月八,拾垃圾”的说法,因为四月份下大雨,河上游冲来垃圾,就要捡起来。五月初五端午节,比较隆重,家家包凉粽。六月初六的牛魂节气氛比较淡。因为牛为人耕田犁地比较辛苦,特地让牛休息一天。七月十三到十五为中元节,也称“七月半”。这个节日非常隆重,每家都要吃鸭肉,出嫁的女儿女婿都要回来,一起用餐。八月十五和汉族人一样过中秋节,吃月饼。九月二十九与三月三基本相同,都是拜山 (扫墓)和做糯米饭。但是村里人现在比较少人在这一天扫墓。十月留肖坡没什么节日,但是对面的路西村有吃糯米饭的习俗。十一月过冬至,各家各户吃鸡肉鸭肉。十二月二十三“灶王节”,过小年,送灶王,打扫干净房子迎新年。
由于是地方政府重点打造的民族文化新村,因而在国庆节、春节等重要节日中,留肖新村会在村头民族文化舞台上举行歌舞联欢活动,参与者不仅有本村村民,也有来外面的表演者和观看者。表演节目类型丰富多样,有民族舞表演,也有广场舞、健身操、电子琴演奏等现代流行元素,以及知识问答竞赛、唱红歌等环节。活动所呈现出以壮族文化为主的、传统与现代的多元文化表演体系。
此外,留肖新村还专门建有“文化活动综合楼”,一栋独立的3层“干栏式”楼房。2008年初次参观时,当地陪同干部介绍说文化室除村委会办公用外,准备建壮族文化展示中心。2014年调查时,虽然还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一些相关民族文化活动先期已经开展。比如用“竹笼机”制作壮锦,穿针引线做绣球等。陪同我们调查的兴宁区民族局马局长就说:为留住传统技艺,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特色产业,2013年兴宁区民族局在留肖壮族新村开设为期半年的织锦、绣球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培训班,未来这里将成为兴宁区民族手工艺品制作培训、展示基地。通过开办培训班,引进壮锦产业,不仅能丰富南宁壮族特色村寨的内容,促进少数民族特色工艺、文化的传承,而且能够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掌握一门特色工艺技能,促进增收,走出一条特色产业道路。当地村民们也讲,土地留转后,家里的地没有了,但学习制作壮锦让我掌握了一门技术,以后生活没有了后顾之忧。学习传统手工艺,既传承老祖宗留下的财富,也增加了一份技能,学成后我可以把自己手工制作的产品卖给游客,增加家庭收入。[10]当然,其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来验证,但至少已在城郊先行了一步。
三、城郊“新村”民族文化重构价值
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11]笔者也曾阐释了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的是文化多样、而不是文化单一的乡村和谐;需要的是合理地将现代与传统、都市与田野、全球与地方等有机相合,从而塑造出独特、多样且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型乡土文化,而不是单纯地“城市化”,让城市吞并农村。[12]因此从社会整体转型看,城郊新村民族文化重构,其价值在于防止在该类区域单向度“城市化”的发生,让郊区成为有力连接城市与乡村、现代都市文明与乡土文化、民族文化的“中间地带”,以实现新型城镇化中“以人为本,文化传承”的核心内涵。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容乐观。近年来,伴随着各地的造城运动,各类“开发区”“高新区”等的建立成为城市向农村拓展、乡村社会向城市转型的重要标志,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忽略了区域内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这不仅导致诸多文化传统与资源的流失,也造成许多城市新城区千城一面、没有“文化”特色的城市化伤痛。因此,作为联络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的城郊文化重构必须加以重视。
当然,这种现象正在不断地改观。正如留肖壮族新村,在地方政府、精英人物、当地民众的协同努力下,民族传统文化正在一点一滴地融入新的社区之中,这也进一步表明,城镇化与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并不矛盾,“新型”城镇化之新正在于文化的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也只有这样的城市才能特色,才有活力。所以,唯有不断推进郊区民族文化的重构,城镇化推进的过程才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深化过程,才不会产生“城市文化吞噬民族文化”的悲剧,才能够确保城郊作为城乡的交接地带所应发挥的文化传承、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功用。
[1]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6[R].北京,2006-02-08.
[2]秦红增,郭云涛.“南宁市城中村改造及村民市民化等问题”研究报告(内部资料)[R].南宁,2014.
[3]秦红增,杨恬.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实践[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4]秦红增,郭帅旗,杨恬.农民的“文化自觉”与广西乡村生态旅游文化产业提升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4(2).
[5]鲁可荣,曹施龙,金菁.文字留村与村落重振:乡村学校嬗变与村落发展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6]熊春文,折曦.乡村学校的演进及其社会文化价值探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7]张士闪.以城镇化为契机重构乡土文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2-06.
[8][英]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的描述[M].褚建芳,闫书昌,赵旭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9]覃彩銮.壮族节日文化的重构与创新[J].广西民族研究,2012(4).
[10]尹海明.兴宁区:留肖壮族新村彰显勃勃生机[N].南宁日报,2013-12-24.
[11]中国政府门户网站.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EB/OL].(2014-03-16)[2015-02-23].http://www.gov.cn/zhengce/2014-03/16/content_2640075.htm.
[12]秦红增.乡土变迁与重塑:文化农民与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设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