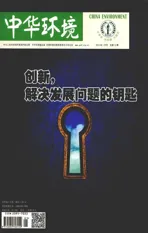难以告别长江源区
——记绿色江河会长杨欣和他的团队
2015-12-08陈金陵
陈金陵
难以告别长江源区
——记绿色江河会长杨欣和他的团队
陈金陵
这是一场特殊的颁奖典礼。没有显赫的颁奖嘉宾。主持人报出名字后,四川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简称“绿色江河”)会长杨欣,走到刻有自己组织名字的奖杯前,轻轻取下,环抱胸前,音乐起,灯光闪。时空定位在2014年11月28日,上海,福特汽车环保奖颁奖典礼。杨欣和他的团队凭“长江源生态拯救行动”项目,获得本届福特汽车环保奖“自然环境保护——先锋奖”一等奖,从自己近三十年寄情的青藏高原长江源区那里领取属于他和他的团队的奖杯。杨欣还是近三十年不变的“造型”,长发,满髯。

绿色江河组织的“让我飞得更高”斑头雁守护行动,在班德湖边,设置观测站。图为:绿色江河负责人杨欣。CFP/供图
上篇
评委会给杨欣团队的评语是:长江源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水源地。“绿色江河”以科学数据为基础,通过当地政府、牧民、社会组织多方合作的模式,探索解决本地生活垃圾污染、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有效途径,为长江源的生态保护贡献了力量。
独特的高原垃圾收运体系
现代文明带来的陋习之一是随处可见的生活垃圾,这种陋习也进入了原本纯净的青藏高原长江源区。自驾车畅游高原一路欢歌一路甩下垃圾,散落在青青草原那么扎眼。当地牧区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悄然变化,不知什么时候起,孩子们不再喝自家产的牛奶而捧起了包装漂亮的“伊利”“蒙牛”;不吃奶奶做的牛肉而大嚼精美小包装的牛肉干。废弃的饮料瓶、包装袋随手扔在帐篷外面,风起,塑料空瓶嘭嘭作响,废包装袋飘落远方草地上。
任何人无权干涉他人选择文明先进的现代生活,无人能阻止生活垃圾出现在青藏高原。牧民缺乏垃圾收集处理的观念,政府没有足够资金收运方圆几万平方公里散落高原上的垃圾。
杨欣带着“绿色江河”的志愿者们走进这片被誉为高原净地的长江源区。他们用了八年时间调查这些生活垃圾的种类、来源、去向,采集到大量一手数据,帮助牧民和当地政府制定出一套适合当地的不可降解垃圾的收运体系。
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青藏高原长江源区的垃圾收集运输处理方式必须具有地域特色。杨欣带着志愿者们走访散居的牧民,告诉他们这些不可降解的垃圾会破坏已经十分脆弱的草场,牛羊误食了会死亡,随便焚烧产生的毒气会导致生病。浅显的道理打动牧民,大家开始自觉收集垃圾,赶集时用自家牦牛、摩托车把垃圾带到小镇上的“长江源水环境保护站”,交给那里的志愿者。10个空饮料瓶可以换一瓶饮料,10个废方便面袋换一袋方便面,甚至10节废电池能换4节新电池。消息传开,散落高原的生活垃圾慢慢集中到保护站的院子里。
“绿色江河”志愿者们把收集来的垃圾初步分类、消毒、整理、打包,但垃圾总不能积在保护站院子里,得运出草原集中处理。
“长江源水环境保护站”是杨欣带着志愿者在青藏高原建立的第二座自然保护站,位于长江源区沱沱河边公路与江河交汇处,自驾游的游客以及青藏公路运输线上过往车辆常常会在这里歇歇脚,拍照留念。
杨欣他们说服自驾游客回程时捎走一两袋整理好的垃圾,运到数百公里外的格尔木绿色江河专设的高原垃圾收集站。“绿色江河”网站上定期公布带走垃圾朋友们的名字和车辆,让更多人知道这些保护长江源区免遭垃圾污染热心人的公益行为。
自驾车只能带走少量垃圾,杨欣他们又盯上青藏公路回程的大卡车。他们发现出高原的车辆80%是空驶,如果请这些司机顺路捎走垃圾,费用仅仅是正常运价的五分之一。他们计算过,这样变单向运输为回程带运垃圾,全年仅需20万元运费,便可运走长江源区1万平方公里范围内各种不可降解的生活垃圾。
绿色江河设在格尔木的高原垃圾收集站有专人负责处理垃圾,空饮料瓶等卖出的钱成了工作人员的生活补贴,不能卖钱的送到城市垃圾处理点集中处置。
“分散收集、长途运输、集中处置”是杨欣和“绿色江河”创建的长江源区垃圾收运处置模式,当地政府部门也来找杨欣,取经、探讨、复制,解决了长期无法解决的长江源区散落上万平方公里的生活垃圾集中、分类、长途运输、无害化处理的大问题。
“自己找上门”的项目
用杨欣的话说,斑头雁保护项目是偶然“自己找上门”的。斑头雁不是国家级野生保护动物,以前并没有进入杨欣的视野。有位大娘找到杨欣,担心地说她们那里的斑头雁产下的蛋很多被人捡去吃了,蛋没了,雁少了,会不会慢慢没有了呢。杨欣组织人去调查发现,当地人捡斑头雁蛋吃的现象非常严重,甚至驻军、公安、政府工作人员也去捡蛋买蛋,斑头雁数量明显减少。
保护长江源区生物多样性本来就是“绿色江河”职责之一,但斑头雁不属国家级保护鸟类,从哪里入手呢?调查中发现,斑头雁是世界上飞的最高的鸟,可以在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20%的高空飞翔,可直冲9000米高空8小时长途飞行,从印度越过喜马拉雅山直到青藏高原。
“让我飞得更高”成为宣传保护斑头雁的切入点。杨欣利用与媒体相熟的优势,请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国环境报》等主流媒体的记者大力宣传保护“飞得最高”的鸟。
保护生物多样性必须有政府参与,杨欣找到政府相关部门,详细介绍了“绿色江河”调查以及发动群众保护斑头雁的情况,请政府部门加入保护这一物种行列。政府有关部门终于正式发文明确保护斑头雁,当地驻军、公安、政府工作人员带头响应,和志愿者一起宣传劝阻人们捡拾斑头雁蛋。
“自己跑来”的项目做了三年,据绿色江河建立的3个定点观察哨统计,2012年观察到1117只雁,三年后已经超过2500余只,数量翻了一倍。
保护斑头雁仅仅是一个“自己闯进来”的不大的项目,但它的出现及成功实施,在杨欣以及志愿者长江源区生物多样性系列行动中,有着既普通又特殊的意义。这样一个个“自己跑进来”的项目构成了近三十年方圆数万平方公里长江源区保护生态环境的时空,构成杨欣及志愿者们一个个扎实的脚印。
“围魏救赵”保护烟瘴挂峡谷
一位常年致力于青藏高原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的民间人士告诉杨欣,长江源区通天河“烟瘴挂峡谷”正在筹划建一座水电站。这可是长江上游最后一处未被人为毁坏的自然峡谷了。水电站一旦建成,通天河发生梗阻,直接影响到长江上游来水,也会对长江源区生态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

杨欣给志愿者戴上红袖标。CFP/供图
“烟瘴挂峡谷”深深扎进杨欣的心。他太了解长江源区,太了解通天河,太了解这个叫“烟瘴挂”的大峡谷在当地生态环境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要关注,要上去,要为“烟瘴峡大峡谷”身躯的完整无缺做些什么。
大西南地区水电开发在当地经济发展、社会影响以致在中国民间环保人心目中,都有着特殊地位。十年前有怒江、金沙江,现在轮到“烟瘴挂大峡谷”,长江上游又要再一次被横腰截断吗?通天河上最后一片完整的生态环境要被践踏吗?
结论在杨欣心中不言而喻,但要有恰当的办法,有大量科学数据做依撑,有足以令决策者动容并重新思考的定论式理由。
杨欣想到一个“围魏救赵”的办法,他选了一个极恰当的切入点,做通天河生物多样性调查。
绿色江河请来国内相关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挑选大量志愿者,组成相当规模的考察团队,以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名义,进入“烟瘴挂大峡谷”,他要“铁证”!
“烟瘴挂”是长江上游通天河第一个大峡谷,位于海拔4500米的青海曲麻莱县曲麻河乡措池村。通天河在这里被冬布里山阻挡,河水在群峰之间左右冲撞,形成这条约10多公里长的通道。峡谷两侧山峰高耸云端,峡谷中河流蜿蜒曲折,喀斯特地貌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成就了长江源区最神奇最壮美的峡谷,更是长江干流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最多的地方,雪豹、白唇鹿、野牦牛、藏羚羊、藏野驴、岩羊、棕熊分布期间,尤以棕熊多著称。
这是长江源区最后一个纯自然的大峡谷,考察将使这里的生态价值最大限度地完整体现,将完成相关调查报告,在科学数据、文字、图片、影像的基础上,借助多方力量,为当地牧民寻求一条可持续发展途径,使“烟瘴挂大峡谷”得以永续保护。
杨欣带领团队与当地其他民间组织合作,于今年5月正式启动“烟瘴挂寻踪——长江第一峡谷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由动植物专家、人类学者、志愿者组成几个科考队,计划用二三年时间对人迹罕见的“烟瘴挂大峡谷”进行全方位考察。其中野生动物调查在传统调查方式的基础上,首次大规模使用社会各界捐助的多台高清红外自动跟踪监视器、39台红外线摄像机等先进仪器设备,及时捕捉雪豹、白唇鹿等大型野生动物的行踪。
“烟瘴挂大峡谷”项目开展半年多取得初步成果,采集到大量数据显示,大峡谷地区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6种,是全球雪豹密度最高的地区;这里是青藏高原草地最好的区域之一,食草动物多,链条完整,承载种类繁多,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誉为上天赐予的“飞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各调查队专家学者、志愿者们带来一个有一个惊喜,同时也发现生态环境问题有逐步上升的趋势。调查团队用科学的调查成果引起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的更大关注,有助于对烟瘴挂水电项目的重新论证。
下篇
2014年福特汽车环保奖的颁奖舞台上,没有名人高官颁奖,杨欣从青藏高原可可西里从长江源区冰川雪原那里接下这座沉甸甸的奖杯。
“绿色江河”会长杨欣和他的团队此次获得福特汽车环保奖“自然环境保护-——先锋奖”一等奖 的项目为“长江源生态拯救行动”,这是一项对长江源区生态环境的整体关注项目,从源区的垃圾收运处置到区域性生物多样性调查保护,着力于长江源区生态环境的全面认知与保护,已然取得骄人的成绩。这些项目都在高寒偏远的青藏高原长江源区,生存条件极为艰难。杨欣和他带领的团队以及全国各地招募的志愿者深入源区做调查做项目,依托的生存基地便是“长江源水环境保护站”,杨欣他们自豪地称作“第二站”,以别于十几年前在可可西里地区建立的第一站“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给冰川立碑关注气候变化
杨欣觉得,既然已经有那么多人参与保护藏羚羊,我们就去选择新的关注点,去关心那些还没有被人们重视的其他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吧。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青藏高原长江源区的冰川。上世纪80年代杨欣做其他项目时就多次进入长江源区冰川地带,他发现那些曾经数千年亘古不变的冰川,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剧,已经悄然变化。
“冰川是气候变化的标本和标志,冰川学家认为最近几十年来的冰川总体趋势是退缩,但它每年到底退却多少却众说纷纭,我于是萌生了找一条冰川每年立碑以测定其退缩速度,以此来提醒公众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念头。”杨欣这番话为他们在长江正源沱沱河源头的姜根迪如冰川设立观测点做了诠释。
从2005年开始杨欣团队组成冰川考察队进入源区立碑,同时以GPS定位。5年间立了5个冰川标志碑,记录下5年冰川退缩的大量数据。他们还发现另一处岗加曲巴冰川退缩速度更是惊人,7年间居然退缩了1240米,每年接近200米!
考察测量立碑中,杨欣和伙伴们多次遭遇险境。最险的一次被暴风雪围困,食物渐渐少了,外面风雪暴虐,又冻又饿。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冲出暴风雪回到安全地带,谁也不敢想能不能等到安全返回后方保护站的那一天。整整六天六夜。好不容易等到天气稍好些就急忙往回赶,越沼泽穿戈壁,多少次陷车迷路,直到深夜11点多赶回后方营地。后来得知那场暴风雪吞噬了一支15人的石油勘探队。冰川科考成了“绿色江河”最艰苦最危险的一个项目。
几年冰川观测考察下来,他们以大量数据科学论证形成正式报告,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相应政策及行动措施提供依据。
离不开熟悉的高原
杨欣今年50出头,要和80、90后志愿者们拼体能,爬雪山杨欣打头探路,扛器材小伙子们赛不过他,深入冰川腹地危险之地,永远是杨欣开头车。考察队宿营时,他把帐篷里最好的地方让给年纪大的专家,照顾志愿者安排铺位,最后实在没平整的地方了,他就在帐篷凸凹不平的旮旯悄悄躺下。高原苦寒地带,食物就是生命。团队人多食物有时供不上,他笑眯眯看着别人先吃,总说自己跑野外惯了,吃的少,有一口就够。让食物、抢吃苦、睡地铺、挑重担、开头车、走险路,这些所谓的平常事在高寒的长江源区,艰难程度不知放大多少倍。杨欣说,这对自己来说很正常。
这样的艰辛不是一两个项目,更不是一两年,一不留神,杨欣在长江源区坚守了近三十年。
认识杨欣多年,有些疑问总想当面和他聊聊。中国数不清的民间环保人,像杨欣这样坚守一个地区,尤其又是高原艰苦之地近三十年的屈指可数。难道没有想过撤下高原,做些其他项目,换一种能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享受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
问话还没出口,杨欣说起一件事。一次他独自开车从一个高原观测点到另一个点,要在荒原上开八小时的车。几小时过去,荒野空无一人,车前是无垠的荒原,身边不时有野生动物跑过来好奇探望,空气中混杂着泥土青草野生动物的气味。熟悉的高原,熟悉的空气。杨欣不禁哼起歌来。杨欣问我,你说这是辛苦还是幸福?
每每从长江源区返回成都市,或者直接从高原下来赶赴上海、北京开会,生存环境的巨大反差,在杨欣心里掀不起更多涟漪。
杨欣微笑着说,生活的甜酸苦辣好比7个音符,人生缺了哪一点都不完满。项目一个个跑来,你能说这个做那个不做?你能说这个艰苦那个条件不具备,等等再说?斑头雁保护这样“自己跑来”的项目不断出现,“绿色江河”会一个个做下去。
我突然觉得自己原先设计的采访问题很可笑,对杨欣和他身边的志愿者来说,不能用简单的时空概念读懂他们的言行。三十年算什么,数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长江源区算什么。衡量杨欣和他的团队的标准,唯有一个个项目,一个个落在长江源区的清晰、踏实的脚印。
我问,你的第三个站有目标了吗?
想了十几年了,杨欣说。我想在成都郊区建一座“绿色黄埔军校”,为着孩子们。
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