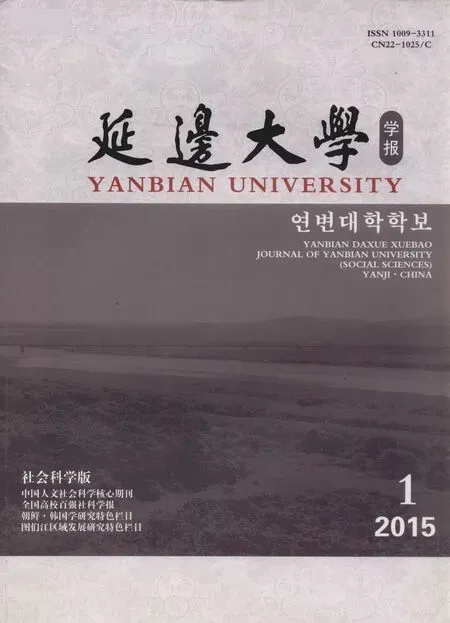四面楚歌中的回忆——论张爱玲《小团圆》的叙事模式
2015-12-08王晓习孙淑芹
王晓习,孙淑芹
(1.延边大学 科技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0;2.延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吉林 延吉 133002)
张爱玲的《小团圆》创作于上个世纪70年代,小说中描写了主人公盛九莉和邵之雍之间的情感纠葛。这部张爱玲最后的长篇小说,在张爱玲逝世多年后,于2009年4月在中国大陆出版,出版后又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由于小说的人物与故事情节大多来自于张爱玲本人的生活体验,“张爱玲自己说过;‘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1]因此《小团圆》具有浓重的自传色彩,出版后也受到各界的“热议”,而张爱玲本人也曾经表示:“《小团圆》要销毁”。[1]由于张爱玲的朋友,也是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宋淇明白张爱玲根本舍不得“销毁《小团圆》”,最终得以出版。
张爱玲身为中国20世纪文坛上一位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斯菲尔德、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2]张爱玲早以她不同寻常的姿态在当时的文坛“独树一帜”,读者尤其爱她智慧华丽的文字,一针见血的比喻,以及甚至连自己也从未放过的“嘲弄”。
然而,张爱玲在《小团圆》中的叙事技巧不同于以往的作品,似乎有意运用更加娴熟的叙事技巧,将读者和作品之间隔离,产生阅读障碍。同时,在叙事语言上也不同于以往的华丽词藻,在语言的选择上更加沉稳、老练,似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却有着非比寻常的魅力。使得读者在张爱玲“四面楚歌中的回忆”里沉迷,不得不接受从回忆里爆发出来的撕裂的痛感。
《小团圆》是张爱玲后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的小说。本文从模糊、断裂的叙事模式,多重身份的叙事者及“张氏”的细节语言角度出发,研究张爱玲《小团圆》的叙事模式,或许对于张爱玲晚期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变可以有所启示;同时,也是对于张爱玲《小团圆》作品叙事魅力的另一种解读。
一、模糊、断裂的叙事方法
众所周知,时间对于小说艺术的展现至关重要,那么作家对于小说叙事时间的把握必然会影响到作品的表现力,也反映出作家对作品掌握的娴熟度。张爱玲对于故事的时间和节奏的掌握无人能及,她通过概述的运用和叙事时间的忽略,以达到模糊时间的目的,同时将叙事时间置于特定的空间,使作品具有跨越时空的魅力。
张爱玲小说的时间具有模糊性,在叙事时间的处理上和传统的处理情节线索的方式截然不同。虽然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对于时间和空间也常常采取模糊、断裂、跳跃的叙事方法,但张爱玲以往的小说对于故事时空的铺垫还是集中在一两个中心人物的身上,读者也较容易把握小说的脉络,比如《倾城之恋》、《茉莉香片》、《十八春》等。
她的很多作品对于时间或时空的处理同样都具有模糊、断裂的特点,可是在《小团圆》中却开辟了另一番天地,和以往的小说大不相同。可以说,《小团圆》的时空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小说出场的人物也众多,出场时也毫无铺垫和交待,甚至消失得也无影无踪,人物和事件转换频繁,情节纠结复杂,给读者的阅读造成很大障碍。
回忆的方法多少会为故事带来时间的模糊。我们在故事的开头看到“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因为完全是等待”。[1]这是女主人公盛九莉登场的铺垫,我们知道是九莉快30岁生日那天,看见床上的月光开始做梦,梦见考试。由此可见,《小团圆》的叙事时间前置应该是张爱玲精心设计的。她深知这部作品与自身经历的紧密关系,但同时作为一个严肃的作家,不得不采取专业的手法将创作与生活拉开距离。因此,叙事时间又清楚地告诉读者《小团圆》从本质上是一部文学作品,并不完全等同于自传。在作品中通过文字所传递出的信息,和文本之外的其他因素不存在任何关系。
九莉梦见考试后,文章自然跳入九莉在香港大考前的情景,这显然是九莉30岁生日之前发生的事情,但具体时间被取消了。这种对于叙事时间连续性的忽略在《小团圆》中也是一个重要表现。“她家里在香港住过,知道是亚热带气候,但还是寄了个睡袋来……”,交待事情发生的地点是香港。虽然“香港”一词在第一、二章也只不过出现三、四次,但战时的情景通过九莉的内心体验得以传达,如参加战时工作的比比,她的声音在九莉听来是“单薄悲哀,像大考那天早上背书的时候一样”,“战场如考场”。在这里,作家常常将考试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因为考试对于学生来说正如“战争”。而战争正在进行,即使未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大概也可以感受考试对于学生意味着的那种折磨与煎熬。张爱玲一直惯用个体的感受来进行侧面描写,甚至有时运用连侧面也算不上的描写进行“浸染”,在这里我们可见一斑。又如,九莉在跑马地墓园对过看到的对联“此日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亦相同”等等,说的都是港战爆发前夕的氛围。正由于《小团圆》没有时间性,所以作品也产生了亲切感。时间的不确定性,也给她的创作带来了高度概括的可能性。战争可能过去,但战争留给人的伤痛和记忆还会延续。人物如走马灯似地上场,比比、三姑、亨利嬷嬷、蕊秋、安竹斯先生等数十个人物,除了比比和蕊秋外的其他人几乎是登场即离场,和主人公九莉的关系也似乎没那么重要,也就使第一、二章的叙事结构显得杂乱而突兀。
断裂的叙事时间也是《小团圆》的叙事模式之一。第三章开头“自从日本人进了租界……九莉回上海那天”将故事一下子转到了上海,在叙事的同时夹杂着对童年和少年往事的回忆。这种时空跳跃,在回忆的同时,回忆到处可见,如第三章三姑问九莉:喜欢纯姐姐还是蕴姐姐?九莉由此想到蕊秋和三姑刚回来的时候,竺大太太的问题:喜欢二婶还是三姑。接着极其自然地出现了父亲乃德抱着年幼的九莉,从口袋里拿出金镑和银洋,带有嘲弄地提出要洋钱还是要金镑的问题,显然这是带有伤痛的回忆。张爱玲在九莉的世界里随意地“切换镜头”,这种非线性、散点的叙事符合回忆者九莉的心理特征。从主人公九莉的此种断开、跳跃的回忆,我们同时可以真切地感受和体会到九莉与亲人之间,特别是与父母的关系疏离。小说各章节的叙事时间和空间相互交错,如一团乱麻缠绕在一起,想理也理不清,加之又难以找出明线、暗线,读者也只能跟着九莉不自觉地共同回忆,被迫进入到主人公的感情世界,和主人公共同“喜怒哀乐”、感同身受。正是这样断裂的叙事方法使小说的叙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小团圆》不仅在情节叙述上经常进行跳跃,小说中的人物在叙述上也常常不照顾读者的阅读感受,人物的出现和消失常无交待,如前几章出现的“剑妮”、“纯姐姐”、“简炜”、“绪哥哥”等。但人物的出现和消失也还是有迹可循的,就是全部跟随九莉的心理活动,有时追忆,有时回到现实,让读者来不及理清头绪就要接受新人物出现,还没来得及消化就消失在追忆或现实中。如果说小说的次要人物属于此类情况,那么主要人物同样也是在断裂的叙事时间里时隐时现的。比如,姑姑在第一章便出现,并在九莉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姑姑的形象是由各个散点组成的,通过九莉回上海和姑姑住在一起展开叙述,并将九莉和主人公之雍的感情生活与姑姑的生活交织在一起,最后我们可以得知姑姑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九莉母亲,而九莉对于姑姑的感情也是既近又远的矛盾心理。除此之外,其他人物如母亲蕊秋、九林、之雍等也都采用了断裂的叙事模式。
《小团圆》的内容复杂,人物众多,情节交错。其模糊、断裂的叙事方法使读者不得不紧紧追随主人公,并揣摩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主人公共同回忆,共同跳跃。因此,时间和空间的交错与任意转换也是小说整体上显得松散和混乱的原因。正因为主人公个体的心理活动在行文中的重要性,《小团圆》在情节结构上就明显具有自传体小说的特性,许多“张迷”也正因如此,对于《小团圆》的最后出版也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但是,《小团圆》的叙述经常以回忆其人生道路为线索,小说的结构如人生碎片的拼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经常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但这也恰是张爱玲小说的魅力所在。
二、多重身份的叙事者
小说叙事的重要技巧之一是叙事角度,叙事者与小说世界保持各自不同的间距,可以适应不同的题材和情感表达的需要。“传统意义上的‘视角’一词至少有两个常用的所指,一为结构上的,即叙述时所采用的视角(或感知的角度),一为文体上的,即叙事者通过文字表达或流露出来的立场观点、语气口吻,它间接地作用于事件。”[3]张爱玲的小说经常采取第三人称叙事,全知全能的上帝叙事可以深入人物的内心,又可以游离于人物故事,就人和事做出评价,在人物的情感之外冷静地进行人生总结和领悟。
张爱玲在小说《茉莉香片》中,描写男主人公聂传庆和活泼可爱的同学言丹朱之间的感情关系,其中就运用了第三人称叙事,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他的自私,他的无礼,他的不近人情,她都原宥了他,因为他爱她。连这样一个怪僻的人也爱着她——那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丹朱是一个善女人,但是她终究是一个女人。[4]
这段话出现在小说的高潮之后,即传庆认为丹朱的父亲(他们共同的教授)也应该是他的,她霸占了他的父亲,剥夺了他的幸福;他要报复,虽然是完全不合理的报复。虽然不能报复,他所需要的爱也不是丹朱所能了解的爱。丹朱的半哄半同情的态度,使得他说出一段丹朱听不懂的话,但是丹朱愿意帮助他,相反使得他火气更大。他很快沿着小径走下山去,她想追上他。传庆疯狂地虐待丹朱,将他生命的空虚全部暴露了出来。他的性格中带有阴郁、别扭和些许的女性化,他的生活是不幸福的,同时他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却存在妒忌和鄙视的矛盾心理。张爱玲在她的文字里常常以这种方式表现她对于历史文化的认识和对于善恶的直觉。
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小团圆》的叙事角度却有些特别,表面上看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叙事,但读下去很快发现叙事者和九莉难以分开。同时,因为自传体小说的特性,叙事者和张爱玲本人又经常合二为一地出现在读者的眼前。这种重合必须通过叙事来实现。一方面,张爱玲的回忆和当下的身份之间的沟通需要一个叙事者来帮助;另一方面,叙事者与九莉在叙事的过程中经常分离,张爱玲往往在不经意间借助叙事者的身份,用对话或心理分析的方式来自我总结评价或表达情感。例如,《小团圆》中九莉约比比一起回上海时的问话,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即通过借助叙事者的身份巧妙地进入主人公的内心,再以主人公心语的方式进行对人或事件的评价,叙事者又可以时时从主人公的内心游离出来。所以,读者有时难以区分是主人公的内心感受,还是作者或叙事者的评价。
再如,蕊秋去修道院看望九莉,亨利嬷嬷问母亲蕊秋的住处,蕊秋回答浅水湾饭店后,有一段九莉的心理描写。从九莉在旁边的奇宭,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是从叙事者的视角出发,但“她倒会装穷……”,我们也可以认为是九莉的一种羞愧的心理描述。在描写九莉执意还给母亲蕊秋钱,蕊秋在沉默中只低头坐着拭泪时,张爱玲加入了大段的心理描写后,又以叙事者的身份旁观九莉,写道:
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从前的事凝成了化石,把她们冻结在里面。九莉可以觉得那灰白色大石头的筋脉,……作为一个身世凄凉的风流罪人,这种悲哀也还不坏……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张爱玲、叙事者、九莉三者之间的游走、分离,在自我书写体验的同时,从体验者的身份抽离出来,反观“那时、那景、那人”,变身旁观者进行评价和解剖,近乎残忍的分析也将读者带入“痛苦之浴”,以完成“四面楚歌中”的回忆。
因此,从张爱玲在《小团圆》的视角出发,小说中自我书写的色彩极其浓厚。九莉作为贯穿始终的主人公,并以第三人称出现,但九莉毫无疑问地就是“我”,她存在于小说的各个角落里,很多叙事的视角实际上都是从九莉的“眼睛”看过去的。这等同于《小团圆》的视角是一个人物视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限制视角”。这样,张爱玲在小说中的九莉又成为第一人称,因为这样更加契合自传小说作者的自我书写和表达。于是,张爱玲是作者,同时也是叙事者,加之是小说中事件实际的经历者,但是为了使小说不得不存在虚构度,还要和其中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小说本身是回忆、是回顾,也是张爱玲通过小说对于自己的重新审视。所以,张爱玲在创作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意象是非常复杂的,让读者难以把握和理解,总是将读者隔离在外。至于张爱玲本人,通过文字来观照回忆,观照自身的精神和情感世界,自然将自己难以解释的心境带入作品之中,造成叙事者的多重身份和繁杂的问题。
“张爱玲、叙事者、九莉”三者的重叠及分离,导致小说产生了一些看似矛盾的问题,如小说叙事受到九莉的视角限制,使得小说的叙事视野狭窄,题材不宽泛。其实张爱玲本人也十分清楚这点,“《小团圆》因为情节上的需要,无法改头换面……”,[1]但这并不影响作品的整体效果,作者在题材创作上下功夫,必须要进行叙事视角的转变,这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
三、“张氏”的细节语言
张爱玲的小说向来重视细节,甚至认为细节胜过思想与主题。《小团圆》几乎是完整地再现了作者全部人生的体验,用“张氏”特有的细节语言来表达其人生态度。张爱玲的人生经历,赋予其华丽的笔锋和与众不同的文风。在表达上常常一针见血,甚至连自己也毫不吝啬。
张爱玲早期的小说一向以华丽浓艳的词句著称,作品中也常常出现色彩浓重的词语描写自然、房屋、人物装束等等,作品呈现出色彩斑斓的效果。张爱玲注重色彩的倾向在《小团圆》里似乎变得有些清新淡雅。脱去了华丽的外衣,我们看到:“地势高,对海一只探海灯忽然照过来,正对准了门外的乳黄小亭子,两队瓶式细柱子……”。[1]在句子中,虽然有“乳黄”的亭子、“粉笔灰”的阔条纹,但是没有了以往的看似雕琢的华丽,而更加单眼,别有另外一番魅力和风味。
张爱玲对于细节语言表达的技巧,在《小团圆》里也可见一斑,如“时间变得悠长,无穷无尽,是个金色的沙漠,浩浩荡荡一无所有……永生大概只能是这样……”,[1]在句中把对于时间的悠长体验和在沙漠中的行走联系起来,可以立刻感受到悠长时间带给人们的焦灼感。再如,灯火管制的城市没什么夜景,黑暗的洋台上就是头上一片天,这样一贯优美的句子在《小团圆》中并不多见,大多以更直接、平实的语言面对残酷的现实,洗尽铅华后对比反衬美丽的个体在绝望的生命中的无奈与脆弱,似一曲“四面楚歌”的绝唱,伤痛的滋味慢慢地浸漫身躯,从小说的细节语言表达中流露出来。
在《小团圆》中,细节体验随处可见。例如,在回忆中写道,母亲蕊秋在九莉9岁时单独带女儿上街,等着过马路,九莉见来了个空隙,觉得有牵着她手的必要,一咬牙,抓住她的手,抓得太紧了点,没想到她的手像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本是平常母女同过马路,在张爱玲的笔下准确地写出了母女之间的隔阂,因为身体接触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反应。要不要牵手的心理活动及外部表现被张爱玲用细节如白描般刻画出来,而本应是温暖而有力的母亲的手,女儿的感觉却是“细竹管”,甚至对于母亲的称呼也仅仅用“她”来代替,似乎有意将母亲放在一个与己无关的位置上。九莉对一位母亲应当为女儿所应当承担的一切也丝毫不在意。
不仅如此,九莉得了800港元的奖学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值钱的钱”而送给蕊秋,被蕊秋轻易地打牌输掉,九莉是一回过味来,就像是有件什么事结束了,感觉是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女儿对母亲行为的黯自失望、伤心跃然纸上。因此,九莉的经验使她意识到:金钱是她和母亲之间亲情关系的延伸。这也就不难理解,直到后来,九莉还想着还钱给蕊秋,年老的蕊秋意识到女儿还钱给自己,只低头坐着拭泪,而九莉竭力搜寻过后,还是没有任何感觉。得知蕊秋过世后,想到的也是“她们母女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永远是在理行李……她母亲传授给她的唯一一项本领就是理箱子……”。文中的细节描写将九莉与母亲过去的种种,对于亲情的绝望,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
除了母亲以外,与另一个重要人物之雍的过往,我们也可以通过“张氏”的细节语言来了解。“杂志上写了篇批评,说我好”,邵之雍就淡淡的出现了,九莉眼里则“永远看见他的半侧面,背着亮坐在斜对面的沙发椅上,瘦削的面颊,眼窝里略有些憔悴的阴影,弓形的嘴唇,边上有个棱”。如果不是从心底里爱慕这样一个男人,大概没有哪一个女人会这样观察一个男人,会用这般言语和耐心来刻画一个男人。所以,九莉收集之雍的烟蒂,不在乎他的汉奸头号,甚至对他的不忠也视而不见,这样的迷恋也使九莉最终脱胎换骨,最后也只能说,我已经不再喜欢你了。事实上,她只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维护自尊心。与其他人物的过往,读者都可通过“张氏”细节语言的表现感受得淋漓尽致。
综上所述,从某种角度上讲,有人认为张爱玲的《小团圆》叙事杂乱而冗长;加之具有多重身份的叙事者的出现,使得故事的视角有所限制;而语言上又不如之前作品中出现的一些耳熟能详的名言名句。实际上,张爱玲在《小团圆》中的叙事比之以前作品更加考究,更加注重了叙事的巧妙性。而在叙事者的问题上,我们也可以深入地感受到,张爱玲本人将那些真实的内心体验和经历通过艺术加工,使其再现于作品中。因此,读者会时时将张爱玲、叙事者、主人公九莉视为一人,这也是在张爱玲早期其他小说创作中比较少见的,特别是涉及到张爱玲个人的情感世界。在语言上,张爱玲则回归更加直白的语言直指对于人生的体谅,执着于生命的真实,揭示人性中的弱点与欲望。读者乘坐上张爱玲精心打造的时光机器,随着她的语言共同进入我们灵魂的最深处后,才发现张爱玲的淡然和对生命的悲悯,也再一次发现张爱玲的不同之处。
[1]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
[2]夏至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4页。
[3]申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
[4]《张爱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