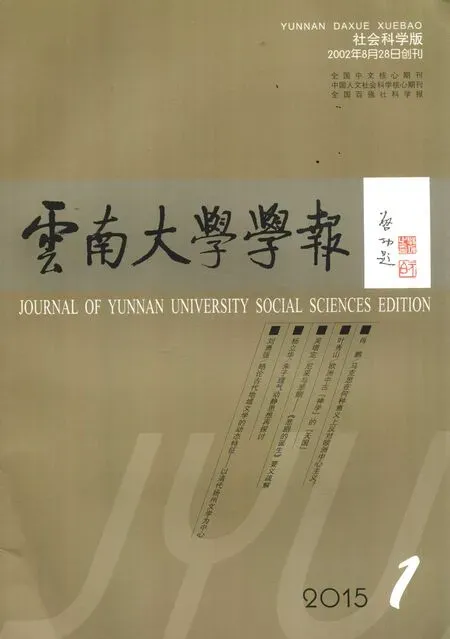欧洲中古“神学”的“天国”
2015-12-08叶秀山
叶秀山
[清华大学,北京 100081]
欧洲中古“神学”的“天国”
叶秀山
[清华大学,北京100081]
关键词:基督教;信仰;自由;科学
收稿日期:2014-08-03
作者简介:叶秀山,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清华大学哲学系双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503
文献标识码:码:A
文章编号:号:1671-7511(2015)01-0011-12
摘要: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古代希腊哲学施加了诸多影响,作为东方宗教的基督教也很快被“西化”,成为“西方-欧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支柱,在这个“西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欧洲哲学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使这个宗教更具有“理论”的“深度”,渐渐地成为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力量。这一宗教的“教化人心”的力量在于把“信-信仰”放在“知识”之上,而由“哲学”之助,它的“信仰”不是“迷信”,而是“理性”的,有“理论-理路”根据的,故而有“凝聚”为一种“力量”的可能性。
欧洲古代希腊哲学留下一个“纷争”的局面,在古代的种种条件下,要在“二律背反”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形而上学”的“统一”的“哲学王国”,亚里士多德未能完成这个“大业”,他的“哲学”显得那样“庞大”但较少“纯粹性”,所以后世对这个古代的“百科全书”也有“折衷”之议。
于是,当亚里士多德“统一”不起来的时候,人们又“回到”了柏拉图,遂有“新柏拉图主义”的出现,而这个学派对于后来成为“一统”的“基督教”“神学”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影响当然是不可忽视的。
“哲学”原本是要在古代原始宗教“迷信”的“纷争”中“收拾山河”的。古代希腊哲学将人们的思想集中到“事物自身”上来,“排除”那些“超越自身”的“武断-迷信”之“判断”而建立“合理”的“理性王国”,通过“理性”,人们得到了对“事物”“正确”的“判断”,“认识”到“事物”的“前因后果”,“时间”成为“可以理解”的,而不再是“神秘”的;人们不可以到鸟的内脏中去“预测”人们的“命运”,而“人们”的“命运”“掌握”在“人”“自己”手里。“人”用自己的“理性”“掌握”“异己”的“事物”的“自己”,在“认知”的意义上,“异己”也是“自己”,“异己”是“自己”(设定)的“对象”。
古代希腊的先哲要在“异己”的世界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对象-客体”的世界,也是“合理”的世界;不过,我们看到,这个“合理”的“世界”仍是一个“纷争”的“战场”,“(第一)哲学”的“一”“产生”了“多”,“产生”了怀疑论、斯多亚派、伊壁鸠鲁派,等等,“哲学王国”成了一个“战场”,“众多”的“自我”不仅“各霸一方”,而其“战祸连绵”,并不“各就各位”,“理性-自我-自由”成为“僭越者-侵犯者”;“哲学”作为特殊的“科学”-特殊的“知识”,由“建构”走向“解构”,而“哲学”这种独特的“二律背反”使任何“建构”都不可避免地要“被”“解构”,“一时”的“和谐”敌不过“永久”的“纷争”。
人们的“思想-意识”“需要-缺乏”“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思想-意识”“没有-缺少”“自己”的“家园”,“思想-意识”“不存在”。
基督教的产生有许多的社会历史条件,当从各个角度仔细研讨,在这个论题中,我们想说它顺应了人们的“思想宁静”的要求,而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它将“哲学”“压制住”,其理由也在于“哲学”只会“引起”“纷争”,而尽管基督教神学要“利用”“哲学”的“理论”来“维护”自己的“存在”,但“哲学”只是处在“婢女”的地位,“哲学”为“宗教”所“用”。“哲学”是“宗教”的“工具”。“基督教”“用”“哲学”之“一”与“多”“关系”之理路为“宗教”的“一”“服务”。
在“基督教”“归一”的主导下,“哲学”只能以其“一元论”才能为它更好地“服务”。希腊“哲学”的“自己-绝对”-“理念”由新柏拉图学派发展起来的理论,对于基督教“神学”也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柏拉图被感性事物的“经验概念”所“困惑”时,基督教神学强调的是“理念”的“绝对”之“一”的意义。同时,反过来说,基督教神学也是从它自己的角度把“哲学”从“多元-混乱-纷争”中“拯救”出来,“神”“拯救”“世界”,也“拯救”“哲学”,“令”“哲学”“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纷争”的境地,“哲学”的“自己”已经“分裂”,无能-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自己”的“家园”,“哲学”“分崩离析”而又“相互攻击”,“哲学”无以为“家”。
当欧洲“哲学”“无家可归”时,基督教给了“哲学”一个“家”,但这个“家”不是“哲学”“自己”的“家”,“哲学”“住在”一个“异己”的“家”里,只能是一个“仆人”的“地位”,从理论上做一些“服务”工作。“哲学”“寄养”在基督教神学的“家”里。
在这个“神圣家族”里,“神”为一家之“主”,而且是“唯一”的“主”。基督教为“一神教”,唯有“一神教”才有可能“敉平”这个“家族”中的一切“纷争”和“祸乱”。
基督教之“一神(教)”向“水深火热”中的“世人”显示,也向“争论”得“不可开交-难分难解-难分上下”的“哲学”显示:凡求“宁静”、“平和”者,“入我门来”。
然而这扇“门”却是一个“时间隧道”,“门里门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神”的“世界”是“另一个”“世界”,对于“世俗世界”来说,是一个“异己”的“世界”。“神”“住在”“彼岸”,“天国-神城”与“人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必须“异化”“自己”,“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才能“进入”“神城”。“人”为“领取”通向“神城”的“通行证-护照”,必有一番“程序-手续”,这些“程序手续”的目的在于将“人”的“自己”“转化”为“异己”。“人”为求得“和平-宁静”,不能“近取诸身”,必须“致远”才得“宁静”,不但“静”则“远”,而且“远”则“静”。
然则,“世间”之“纷争”此起彼伏,“神城”又在“彼”不在“此”,于是便有“教会组织”“垂示”一个“人间天堂”,成为“远离”“尘世”的“世外桃源”,基督教“许诺”:一旦“弥赛亚-救世主”降到“人间”,“普天之下”“莫非桃源”,则“开万世之太平”,这样,“彼-此”之“区别”也被“敉平”,“异己”又“复归”“自己”,而“自己”为“同”,“自己”就是“非己”,“神学”“化解”了“哲学”。“九九归一”,“众人”也是“一人”,“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克己复礼”,“人-己”为“一”,“无分彼此”,“同(礼)”“恢复-复(覆)盖”一切“差异-区别”。
于是我们看到,古代希腊的“哲学”固然受到“东方”思想的种种影响,而真正在西方-欧洲世界“推行-扩大”这种影响的,早期基督教神学可以当仁不让。
当然,基督教很快就被“西化”,成为“西方-欧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支柱,在这个“西化”的“过程”中,传统的欧洲哲学起到了“催化”的作用,使这个宗教更具有“理论”的“深度”,渐渐地成为一股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力量。
这个宗教的“教化人心”的力量在于把“信-信仰”放在“知识”之上,而由“哲学”之助,它的“信仰”不是“迷信”,而是“理性”的,有“理论-理路”根据的,故而有“凝聚”为一种“力量”的可能性。
一、“为知而信”
“为知而信”,也就是说,“信”在“知”前,“信”而后“知”。
“哲学”因为“追求”“真知识”(亚里士多德),引起许多“纷争”,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中,虽说可以“设定”一个“终极目标”,但“知识”要以“无穷”的“探索”来“接近”这个“绝对”,这个“绝对”似乎是“可望不可及”的。于是乎“知也无涯”,“纷争”“难免”;“智者”“沦为”“蛊惑者”,甚至“欺骗着”,“挑起争端者”,“唯恐天下不乱者”。
“天下分久必合”,“人心思一”,基督教神学教人“信”字当头,“知”“在”其中。“信”为“不疑”,“信”“规定”“知”,“不疑”才能“真知”,“不信-疑”出来的“知”,只是“一知半解”,没有“力量”“克服”“疑”,“知也无涯”,则“疑也无涯”。于是,人生-甚至人类-人族无非是一群“疑疑惑惑”的“懵懂者”。
于是,基督教“开启”“人族”心中的“信念”,唯有比“知识”更为“强大”的“信念”才有“力量”“克服”人心中的“疑惑”。
我们看到,在这个意义上,欧洲文化,在“知识就是力量”(培根)之前的格言乃是“信仰就是力量”,“知识”永处于“疑惑”之中,何来“力量”可言?
“信”的“力量”来于“权威”,“哲学”则“不信-怀疑”任何“权威”。古代希腊哲学将“真理”和“意见”严格区分开来,“权威”的“言”只属于“意见”,只有经过“证明-论证”,才是“合理”的“真理”;“意见”为“多”,“真理”为“一”,只是古希腊哲学的实际状况,很难“证实”这个“理论”,它们“纷争”不断。
基督教神学“颠倒”了这个关系,“知识”只“停留”在“意见”上,“知识”为“多”,而“权威”则只能是“一”,“多”和“权威”本身的意思相左,唯有“唯一”才是“权威”,这个“权威”则是“超越”“众人-多”的“唯一”之“神”。“信”就是“信”这个“唯一”之“神”。因为他“高高在上”,“超越”一切“众生”,“超越”“万物”,故而中文在“信”的后面加上一个“仰”字,“仰”为“下面依赖上面”的意思,应是相当“传神”。
这样,欧洲文化传统中,就有了“信仰”与“科学(知识)”的对立。
基督教设定的“权威”是它的《圣经》,唯《圣经》所“言”,不“可以、允许”“质疑”;凡“质疑”《圣经》-“圣言”者,必受到“惩罚”。盖“质疑”《圣经》即“挑战”“权威”,当这个“权威”为“唯一”时,这种“挑战”就是“犯罪”,因而必受“惩罚”,“罚”与“罪”“相随”,才能化“纷争”为“和谐”,将“多”转化为“一”,维持着基督教《圣经》之“唯一性”。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哲学与科学)”皆因“质疑”而受到“惩罚”,发挥“权威”“迫使”它们“放弃”“质疑”,“回归”到《圣经》的“道理”上来,而《圣经》的“道理”在于“信仰”:“信而后知”。
二、唯“圣言”可“信”
“圣言”之所以“绝对”“可信”,是因为它是“立法”之“言”,世间“万物”皆“按”“言”而“存在”,这与古希腊的哲学传统观念是不同的。古希腊的“始基”只是从“万物”中“寻求”一个“原始之物”,以此来理解万物之“元祖”;至柏拉图的“理念”,理解为万物之“原型”,类似一些“设计图形”,“神”“设计”出这些“图形-图式”以此“创造-制造”“万物”,力求让实际的“事物”“接近”他的“图形”,这个(或者“这些”)“神”有点像世间万物的“总工程师-总设计师”,“神”是万物的“设计者”、“制造者”,至亚里士多德遂有“形式”与“质料”之分,探讨的是“世间万物”的“构造”的“原理”。
基督教《圣经》教导就很不一样。《圣经》教导人们,“神”“说”“(有)光(存在)”,“光”果然就“有”了,“存在”了,“神”“说”有“水”,于是“水”也就“有”了,“存在”了,以此类推,“神”“说”“有”“什么”,就“有”了“什么”,“神”“说”“什么”“存在”,“什么”果然就“存在”了;“神”从“没有-无”中“产生”出“万物”,“神”的“创世”是一个“奇迹”。
如果古按希腊以来传统哲学的观念来理解这个“圣言”,未尝不可以将它当作“概念”讲。万物本是“混沌”,唯有“概念-语词”将其转化成“可以理解”之“事物”,在这个意义上,“神”为“万物”“命名”,“名正”而“言顺”,“顺”者“有序”,“言”将这个“序”“开显”出来,“世界”“有序”而“可知”,成为“宇宙”。“混沌”“开显”为“宇宙”,“质料”而有“形式”,是为一个“奇迹”。于是,《圣经》的“圣言”是“逻各斯”。
“逻各斯”是“名正言顺”。在这个意义上,不仅“道成肉身”,而且“肉身成道”,“天下纷争”,“归于”“和谐”;因为有了“(圣)言”,“世界”才有了“理”,因而“逻各斯”是“言”,也是“理”。
“言”使“万物”“存在”,“(语)言”是“存在”的“家”,“存在”“居住”于“语言”中,在《圣经》的意义上,也就是“神”“令”“万物”“存在”,亦即,“神”“令”“奇迹”“发生”,“神”“创造世界”,也就是“神”“令”“奇迹”“发生”;“神”“使(用)”“奇迹”“令”“万物”“存在”。
于是,“神”为“创造者”,天下万物为“被(创)造者”。
三、“人”作为“神”的“独特被造者”
“神”“创造”“万物”,也“创造”“人”,但“人”是“神”的“独特被造者”,“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模样-模式”“创造”出来的,“人”是“神”的“宠儿”,“人”“接近”“神”,这就意味着,“人”是最“有可能”打破“唯一”的“信条”成为对“神”的“权威”的“挑战者”,凡是“接近者”,也就会是“挑战者”;越是“接近”,就越容易“挑战”。
“人”之所以有可能-有能力“挑战”“神”的“权威”,其实也是“神”“赋予”“人”的一种“权利”,“神”“给予”“人”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自由”,“自由”是“神”“赋予”“人”的“天赋人权”。
“自由”就是“自己”。万物混同,本无“自己”,“圣言”使万物有了“自己”,有了“自己”的“存在”;“神”更“赋予”“人”以“意识-思想”,“人”遂有能力“意识”到“自己”,“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也就是“意识”到“他者”的“存在”,“意识”到“万物”的“区别”,而不是“混沌”的“同一”。
“人”“在”“世界”中,意味着“人”“有”一个“世界”。“动物”也“在”“世界”中,“万物”都“在”“世界”中,但只有“人”有权力说“万物”之“存在”,因为“万物混同”,“万物”“没有”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令-使”“万物”“存在”,“人”也跟“神”一样,“有权”“说-判断”这个“世界”。
既然“自由”的“意识-觉悟-觉醒”“令-使”“万物”不是“混同”,而是有了“区别”,有了“各自”的“自己”,则“人”也“有权”“自由”地“判断”“自己”的“世界”。
对于“神”来说,“自由”的“纠结”在于:既然给了“人”以“自由”,就有可能“丧失”“神”“自己”的“权威”,这是一个“神学”的“二律背反”。“自由”“建构”“权威”,又“解构”“权威”。“神”将“自由”“赋予”了“人”,“自己”只“剩余”了“权威”,则“权威”必以“惩罚”来“维护”,即“消灭”已经“给出去”的“自由”,来“维护”“权威”。
“神”“创造”了“人”,也就是“制造”了“麻烦”,在“万物混同”的“伊甸园”里安放了个“定时炸弹”。
从“消极”的意义来说,“偷吃禁果”并非是“积极”的“自由行为”,而是受到了“美食”的“诱惑”之“(被动)行为”,谈不上“自由”;然而,一切“自由行为”都可以通过“感性”的“途径”来表现,“自由”不等于“克己”,而“正己-证己”——“证明”和“证实”“自己”的“自由”才是“现实”的“自由”,因而“偷吃禁果”才可以被看作一个“自由”的“行为”,而并非一种“贪欲”;于是“神”的“震怒”,不是因为“人”“过于贪欲”,而是在于“违反禁令”,“挑战权威”。“神”警觉地意识到,如此胆大妄为下去,“人”就会跟“神”“平等”了。“人”“挑战”了“神”的“唯一性”。于是,“神”必须把“最近者”——自己身边的“叛逆者”加以“惩罚”。
四、“自由”的“诱惑”
“偷吃禁果”是“人”的“原罪”。“人”并非“吃”“果子”而获“罪”,“偷-盗”才是“原罪”。“吃喝”乃是“人”的“自然”禀性,而“偷盗”则是“挑战”一个由“权威”“颁布”的“禁令”,“原罪”并不在于“顺从”“人”的“自然禀性”,而是“挑战”“权威禁令”,并“维护”自己的“自然禀性”;不是“克己复礼”,而是“无礼复己”。“自由-自己”“挑战”一切之“礼”,“自由-自己”“胆大妄为”。
在这个意义上,“神”“视”“自由”为“万恶之源”,而并非“人”的“自然禀性”。“万恶淫为首”,“自然禀性”之所以会“泛滥(淫)”,乃“植根”于“自由”,“自由”为“无度”,打破“界限”。古希腊人告诫世人“自知-无过”,阿那克萨哥拉的“无界”观念,受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事物”的“自己”,正是“事物”的“度”。
基督教的“神”把“自由”给了“人”,也就把“无度-无定”给了“人”,“无度-无界-无限”不是“人”的“自然禀性”,不是“贪欲”。“人”之所以“欲壑难填”,乃是“自由”的“怂恿”,“我要”而无视一切之“度”。“自由”不是“自然”的事,而是“理性”的事,“自由”乃是“理性”的“僭妄”。“理性-自由”“努力尝试”“挑战”一切之“度”,无论“自然”给出的,“人”给出的,还是“神”给出的。
“理性”的“僭妄”也是“理性”的“诱惑”。
《圣经-圣言》告诉我们,“人”之所以“犯禁”乃是“蛇”的“诱惑”,因受“诱惑”而“堕落”成为“偷盗者-挑战者”。“人”在“神”的“禁令”与“蛇”的“诱惑”之间做出了一种“选择”,“选择”是“自愿”的,“人”居然不“听命”于“神”,而“听命”于“蛇”,此种“选择”“加重”了“神”的“愤怒”,也“加重”了“神”的“惩罚”。实际上,“神”对“蛇”的“惩罚”无非是永远匍匐于地,永世不得“翻身”,原本也是“蛇”的“本性”,而对“人”的“惩罚”则是“人”必须付出“艰苦劳作”来“维持”“人族”之“存在”。
“人”从“悠闲”走向“劳作”,“人”从“思想”的“智慧”走向“劳作”的“技能”,“人”必须永久地“学习”“技能”和“知识”。“知识”和“技能”是“自由”的“成果”,这个“成果”以“放弃”“悠闲”为“代价”。
“人”“自愿”地“放弃”“伊甸园”的“悠闲”而“甘愿”以“劳作”来“维护”自己的“存在”,“人”不惜“流汗-流血”来维护“自己”的“自由”,“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子子孙孙”永久地为“维护”“自由”而“斗争”。
于是“人”意识到,“神”“赋予”“人”的“自由”,并不是“逍遥自在”的“自由”,而是“沉重”的“自由”,“自由”是一种“担当”,“人”要“承担”“养活”“自己”和“他人——家人以及鳏寡孤独”的“重担”。在“自己”面前的“他人”“有权”向你“要求”“一切”,因为“他人”“一无所有”。“自己”“拥有”的“自由”,使“他人”“属于”“你”,“他人”“为你”,“你”也“必须-应该”“为他人”,“你”的“自由”使“你”“意识”到,“你”“为己”,也就是“为他”,“他人-他者”使“你”的“自由”成为“现实”的,而不仅仅是“思想”的,“他人”“有助”于“你”的“自由”的“实现”,“保障”了“你”的“自由”的“现实性”,“他人”“施恩”于“你”,“他人”将“自己”的“一切”“用”来“维护-促使”“你”的“自由”;“他人”“牺牲”了“自己”的“自由”,“奉献”给“你”,以便“你”的“自由”得以“实现”,“他者”“一切”皆“属于”“你”。“自由者”“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者”“一无所有”,则“有权”向“你”“要回”“一切”。
“人”作为“自由者”“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万物”都与“你”“息息相关”,“任务”当然“繁重”,“责任”自然“重大”,于是乎“自由者”并不“逍遥”,而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自由者”“受”“神”的“重托”,“自由者”“受命于天”。
“神”因“人”的“自由”“挑战”而“震怒”,使“人”的“自由”“脱离”“自由天放”的“原始状态”,进入一个“文明道德”的时期,“自由”与“责任”永远“相随”的时期。
“神”因“震怒”而“遗弃”了“自由”,“令”“自由”“一切自理”,“人”不可以以“神”“赐”“自由”而将“责任”“推脱”给“神”。“神”“遗弃-不要”了“自由”,也就“遗弃-不要-不负”了“责任”。“人”作为“自由者”“承担”着“世间”的“全部”“责任”。
于是,“自由”的“诱惑”,也就成为“责任”的“诱惑”。“自由者”作为“负责人”,自有一种“威严”,“责任”越大,“威严”也越大。“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天下”的“负责人”,“威严”不可谓不大了。
“负责人”的“欲望”,也就是“权力”的“欲望”,“权威”的“欲望”。“权力欲”不是“自然”的“欲求”,而是一种“理性”的“欲望”,是一种“自由”的“意志”,因而是“不可”“满足”的“无限”的“欲望”。
“人”作为“自由者”,不仅要“他人”“理解”,而且要“令”“他人”“崇拜”,“自由者-责任人”行使着“信而后知”的“模式”,“令”“他人”“信仰”。
“人”“挑战”“神”的“权威”,要“树立-建立-建构”“自己”的“权威”。
五、“圣言”与“人言”
“圣言”“启蒙”世人,使芸芸众生“得知”“人”“有”一个“世界”,“人”“有”“日月山川”、“小桥流水”。“人”“听信”“圣言”而“有知”。“神”为“世界”“立言”,“立言”即是“立法”;“法”自有“权威”,“神”因“圣言”而“树立”“威严”。
在“神”的“(被)创造物”中,只有“人”才会“说话”,“神”按自己的“形象-模型”“创造”了“人”。
“言为心声”,有了“言”,则有了“内-外”的“分别”,有了“心-物”的“区别”,有了“主-客”之分。“人”因有“内”而成为“主体”,也因“言”而“有”一个“客体”。于是,按照“神”“创世”的“模式”,“人”的“客体”,也是“人”之“主体”的“创造物”。
“名正”而“言顺”,“言顺”而“有序”。“言必有据”,这个“据”乃是“证据”,也是“根据”。“动物”或可有“表情”,只有“人”“有能力”“说理”,“语言”的“本质”“根据”于“理性”。“人”有“语言”是“人”有“理性”的“证据”和“证明”。
在这个意义上,“人”“立言”也就是为“万物”“立法”,也就是“理性”为“天地”“立法”。“人”因“言”而有了“立法权”。“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内-心声”“替”“天地”“立法”,“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王国”。在“天下-地上”“建立”“人的王国”是“人”的“理性”的“神圣使命”,因为“人”“言”之权,原本是“神”“赋予”的,是“神受人权”,“人”乃是在“天下-地上”“替神立言”,“替神行道”,“理应”得到“神”之“嘉许”;但是“人言”不是“神言-圣言”,“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自己的“权力”,“人言”既然是“理性”的,也就是“自由”的。
于是,古代希腊的“理性”“自身”的“二律背反”,就转化为“圣言”和“人言”的“二言背反”,“言”即是“律”,是“自由律”与“自然律”的“背反”,也是“自由”与“命运”的“背反”。
“圣言”并非根据“自由律”,而是根据“必然律”。“神”并非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创造”“世界”;如果“神”按照“自由律”来“创世”,则将对于世间一切“负有责任”,因而对于世间的一切“恶”“负有责任”,也就是说,世间的“恶”其“原因”也在于“神”,而“神”不可能是“恶”的“原因”。“神”固然也“惩恶扬善”,但“神”之“罚”不是古希腊式的“平衡”,“惩罚”不是“终极目的”,“拯救”才是真正的“神”之“意愿”,“惩罚”“属于”“救赎”,“拯救”出于“神”对自己的“创造物”之“爱”,“神”“爱”“世人”,凡“忏悔-赎罪”者,一律皆可“回到”“神”的身边。“坦白”一定“从宽”,乃是“神”的“千金一诺”,“神”的“许诺”从来不可能“收回”,“神”之“圣言”乃是“必然”的“命运”,“过去-现在-未来”皆在“必然”的“大箍”之中。
在“必然律”中不存在“恶”的问题,“恶”只是“命定”的“过程”中的“现象”。在“神”的眼里,“为恶之人”犹如“迷途的羔羊”,早晚“归队”,“回到”“牧人”的身边,对于“迷途”的、“归队”的,“牧人”一概充满了“爱”。
“神”“拯救”“世人”并非“神”的“责任”,“神”因“爱”“人”而“救”“世人”。
一切“责任”皆在“人”,在这个“天下-地上”,“人”是“责任者”,因为“人”是“自由者”,“人”“自由”地“发号施令”,“人言”遵守“自由律”,因而“人言”尽管“模仿”“圣言”,“申言”“服从”“神”的“权威”,但“骨子里”却是按照“自由”的“原则”“发言”,“借用”“圣言”的“权威”来“建立”“自己”的“权威”。
按照“宗教神学”的理路,是“人”“借口”“自由”“行使”种种“恶行”,“自由”为“万恶之源”。“人言”与“圣言”的“二律背反”,也就是“善-恶”两种“不同原则”的“言”,乃是“相互”“对抗”之“言”,尽管它们在“语言”形式上是“共通”的,但在“精神-原则”上是“对立”的。
可能最初的“言”都有“令-命令”的意思在内,尽管在语句的形式上未必全采用“命令式”语句。“圣言”“有光”,内含着“令其有光”;“人言”“吃禁果”,也是“让我们吃果子去”,作为“语言-概念”“基础”的“命名”就是以一个“令-让”的意思,一个“这是什么”的“判断”,不仅是“描述”,也包含着“令其”为“什么”的意思在内。“圣言”为“发号施令”,“人言”也是“发号施令”,是从“两个司令部”发出的“号令”,“人”这个“自由”的“司令部”因“言”而“建立”了自己的“权威”,而因其“自由”就有“对抗”“另一个”“权威”的可能性,而又因其“自由”,“人言”为“维护”自己的“权威”,就会将这种“可能性”发展成为“现实性”,从而使“自由”在“另一个”“权威”的眼里是一种“犯上作乱”,“为非作歹”为其“本性”。
六、“善”-“恶”两个“原则”的“二律背反”
在这个意义上,“圣言”与“人言”的“二言背反”,也就是“善”与“恶”的“二律背反”,这是“神学”的断定。
基督教“神学”不愿意把世间的“恶”归因于“神”,于是“人”的“自由”就“背上了”“恶”的“罪名”,因为“人”是“自由者”,也就是“恶”的“责任人”,“人”“改变了”“世界”,“承担着”“恶”“名”;一切的“科学发明”都曾受到过“神”在“地上”的“代表”——“教会”的“谴责”和“惩罚”,“教会”的“宽容”是“相对”的、“暂时”的,“谴责”是“绝对”的、“永久”的。“神”的“律条”要“行使”在“人世间-大地上”,必定与“人”的“律条”发生“不可克服”的“矛盾”,“人”按照“理性”的“自由律”“行为”,终究是要使“人”成为“僭越者”。“僭越”是“自由”的“本性”。“人”“愿意”“肩负”“责任”的“重负”,“不断地”“僭越”,“不断地”“超越”。
在这个意义上,“圣言”是“宗教性”的,而“人言”是“科学性”的。“圣言”突出一个“信”字,“人言”则突出一个“知”字。“宗教”“信而后知”,“科学”则“知而后信”。只有在这两个“原则”“划疆而治”,“各不相干”时,才因“避免接触”而不发生“二律背反”。这是欧洲人晚近才知道的道理。
“神管神的事”,“人管人的事”是一个理想的“境界”,但“裂土分疆”又常常是“纷争-战争”的“根源”,“神”为避免“纷争”,力求“一统天下”,“神”“要”“管”“人”的“事”,其结果,仍然是“二言背反”的“纷争”,因而,“二律背反”是一个普遍现象,也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在“神”看来,“人”作为自己的“子民”,在得到“自由”,有了“人言”权之后所做的第一件称得上“自由”的“事”居然是“反抗”“神”的“禁令”,可谓“大逆不道”、“忘恩负义”;而在“人”看来,如果永远“安于现状-忠实服从”,“自由”则是一个“虚设”的“空位”,“自由”不在“人”的“言行”中“显现”出来,则同样“违背”“神受自由权”的“初衷”,“人”不能让“神”陷于“虚伪”,则“人”“勇敢”地承担起“自由”的一切“责任”,宁可陷“自己”“为恶”之“险境”,也要“勇敢”地、“愉快地”、“心甘情愿”地“行使”自己的“自由权”,而“承担”“自由”的一切“后果”,将一切“荣耀”归于“神”,而将一切“苦果”自己“吞吃”了。
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神”的“替罪羊”。
“人”能为“自己”寻求的“出路”和“理由”,只是努力将“为非作歹-犯上作乱”的“自由”转变成就其本质而言,乃是“绝对”“善”的。
“人”为自己的“自由”“辩护”:“自由”的“根据”在“理性”,并不“受制于”“自然”,“偷吃禁果”并非为“自然情欲”所驱使,而是“理性”的“尝试”,是“我要知道”,由“无知”而“知”,“自由-理性”有“权”“怀疑”一切“现成”的“事物”,为“知识”“敢于”“挑战”一切包括“权威禁令”在内的“权威”,“自由”“动摇”一切“既成事实”,通过“知识”而“建立”“自己”的“事实”。
于是,“圣言”固然是“至理名言”,而“人言”也是“合理”的。“人”“自由地”“按照理性”来“构建”“自己”的“人的王国”。
“自由”当然承认自己一定会“犯错误”,而恰恰是“人”的“自由理性”承认“恶”是“不可避免”的,在“人世间”要想“避免”“恶”是一个“空想”;但“自由理性”也可以承认,“恶”不是“绝对”的,“恶”是要“被克服”的“消极”的“负能量”,但“恶”是“自由”在“开创”“自己”时,会“不断”出现的,“人”与“恶”“斗争”具有“持久性”;而“神学”的观念,则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天国”,一个“全善”的“王国”。
“人”没有“能力”“在地上”“建立”一个单一的“全善王国”,“人”持久地与“恶”“抗争”,只有“神”才有“除恶务尽”的“大能”;于是,“神”“派遣”他的“特使”做“人”的“救世主-弥赛亚”。“人”“期盼”这个“特使”的来临,但至今“人”尚在为“自由-理性-善”而“斗争”,“人”仍处于“二律背反”之中,在作出“自由”的“选择”中,“付出”“沉重”的“代价”,“肩负着”“自由”的“责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之“死”意味着把“自由”“交还给”“神”,“交出”了“自由”,也就“交出”了“责任”,“摆脱了”“二律背反”,“回归”“单一”的“纯善”的“存在方式”。
七、欧洲的“世外桃源”
中国的“世外桃源”在“人间”,无非是“避乱隐居”,在那个“小天地”里,照样“生生不息”,也有“变化-运动”;只是因为“小国寡民”,“矛盾”经常“协商解决”,这样,“桃花源”只是一个“在”“时空”中的“王道乐土”;基督教神学“克服”“纷争-矛盾”之道,要“彻底”得多,它的“伊甸园”“在”“天上”,“超越”“时空”,是一个“永恒”的“天福乐园”。于是,“地上”的“桃花源”只是“时间”中“长短”的问题,而“天上”的“伊甸园”却是“超时空”的“永恒”。
古代人民无论中外,无不“向往”从“纷繁”的“世界”“解脱”出来,从“因果律”的“必然大箍”中“解放”出来,“有”一个“自由自在”的“天然”的“乐土”,在那里“既无风雨又无晴”(苏东坡),“永享”“天福”。
只是欧洲的基督教神学提出了一个“超越时空”的“永恒”问题,将古代希腊哲学中比较“含糊”的“时间长短”的问题推进到“绝对”的层面,改变了“神”只是比“人”“活得更长-更强有力”这类的“经验”“尺度”,而建立了一个“绝对”的“尺度”:“神”真正成为“不死者”、“永生者”、“永恒者”。
“永恒”问题从“经验尺度”中走了出来,“超越”了这个“尺度”,成为“绝对”的“尺度”,“尺度”而又“绝对”,则为“无度”,“永恒”完全从“经验时空”中“超拔”出来。“经验世界”“需要”“度”,而那个“超时空”的“绝对世界-天堂”,则不需要“度”,“无度”为“无需度”。
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神学改变了古代希腊德尔菲格言的方向:不是“勿过”,而是“超越”;不是“知己(此岸)”而是“信他(彼岸)”,将“科学”“颠覆”为“信仰”,从而也“颠覆”了“自由”的古代“自然天放”的意义,“自由”“摆脱”了“自然”,也成为“超越”的“意志”,“自由”一旦“进入”“自然-经验世界”,则“辛辛苦苦”并“战战兢兢”地在一个“异己”的“世界-自然界”中“开辟”“自己”的“道路”。“天上”的“自由”是那样“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地上”的“自由”则没有那样的“有趣-好玩”。
在某种意义上,“自由”是“万能”的“神”手中“惩罚”“人”的一个“武器”,也是一个“计谋”。“人”满以为得到了“自由”就立即可以“自在”,不曾想到,“自由”不能“马上”“自在”,“自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看得见”“自在”的“可能性”,而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历史发展”的“无限的长河”,“自由”是一个“无限”的“绵延”。在“自由”的“压力”下,遂使许多“人”宁愿“利用”“自由”的“选择权”,“选择”“放弃”“自由”,“回归”“自然”,将“自由”“归还”给“神”,“人”“回归”“自然”,于是乎“优哉游哉”,“逍遥遨游”,或者甚至“无知无识”,“归于”“涅槃”,已经是东方道家和佛家的一种“选择”。
“自由”只有在“地上”才会“遇到”难以对付的“对手”——“自然”,产生“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律背反”。因为“自由”原本“在”“天上”,如今“被罚下地来”,原本是“超越时空”的,如今“被罚”到“时空”中去,要求“两全其美”,就怕“难矣哉”。
欧洲的哲学向“自由”“提供了”“理路”而“挽救”了“自由”,“自由”不必“放弃”“自己”,“交还”给“神”,而从“现实”思路上,为自己找到“根据”:“自由”为“自己”“创造”“时间”。
“自由”“搁置”“现存”的“时空”,通过“自由者”的“行为”,“创造”“自己”的“时空”,所以,就“自由者”(这个视角,这个观测器)“看来”,“时间”是“自由”的“绵延”,“历史”“铭刻”着这种“绵延”的“轨迹”,“历史”不仅仅是“事件”的“因果链”。这是“历史发展”的“二律背反”,“自由”与“因果”遵循着“两种不同”的“原则”。从“因果关系”来看,一切皆为“自然”,“人”“听命”于“自然规律”的“摆布”,无非是“随波逐流”;但就“自由”的眼光来看,则“人”作为“责任者”,对一切“貌似”“自然”“无可选择”的“事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每一个“事件”,“人”都是“肇事者”,是“始作俑者”,因此“历史学”不仅“断”“因果”,而且“评”“功过”。“史家”的“笔”,乃是“春秋”之“笔”,“历史”让“乱臣贼子”“惧”,不仅“口诛笔伐”,“令”其“无遗族”,而且“载入史册”,“警惕后世”,亦即“令”其“无后”,于是,“史家”之“笔”,也是“刀笔”。
然而,“自由”既然与“自然”“相遇”,这种“二律背反”就“不可避免”,“现实”的“历史”是一部“纷争”的“历史”,不仅“因果”的“关系”有种种“不同”的“证据”,就连“史家”“评判”的“功罪”,也有种种“对立”;“史家”固力求“公正”,但毕竟不是“神”的“末日审判”,“翻案”文章,屡见不鲜,“后人”的“评说”,也难得“同一”,即使寄希望于“人民”,无奈“人民”也会“众说纷纭”,“因时而异”,不是完全“固定”的。
于是,“自由”“开创”的“时间”,是“异”,而不是“同”,“权威(包括现实政治的)”只能求“一时”之“同”,不能“永久”地“泯灭”“异”。
然而,一个“绝对”的“权威”——“神”则在“道理”上有“可能”“消弭”一切之“异”,“建立”一个“完全”的“同”。在“天国”的“大同世界”,不允许“异”的“存在”;这个“大同”世界,“避免-克服”了“二律背反”,只有“神”的“一条”“律令”,“听从”“神”,则“同享太平”,“神”为“万世开太平”。
为此,“神”“收回”了已经给予“人”的“自由”,“消灭”了“自由”,也就“消灭”了“异”。为“收回-剥夺”“人”的“自由”,“神”“令”“人”为“有死者”。“有死者”而又“自由”,是为“有限的自由者”,而“自由”本意为“无限-不受限制”,这样,“人”“自身”又成为一个“矛盾体”,“人”“自相矛盾”,“人”的“生活”,“人”的“意识”,“人”的“智慧”意味着对“死”的“抗争”,“克服”“自己”的“二律背反”,即,“人”既是“自由”的,又是“自然”的,“人”依靠“理性”的“智慧”“保持”“自己”的“自由”,使“死东西”也成为“活东西”的“轨迹”,“自然”成为“自由”的一种“存在”方式,使“死东西”成为“活东西”的“记录”,“自由”“激活”“自然”。
“人”不必把“自由”“交还”给“神”,“人”努力使“自由”在“时间”“中”“永生”。
“人”一旦“意识-觉悟”到“人间”“自由”的“永生”,也同时“意识-觉悟”到那个“超越时空”的“永恒”乃是一个“僵死”的世界,“自由”被“贬抑”为“自然”,“神”“收回”了“自由”,如同“宝物”一样“藏诸深山”,“束诸高阁”,只是“以备不时之需”。
于是,这个“神”的“伊甸园”虽然“自然天放”,甚至“其乐融融”,但犹如“一潭死水”,“水波不兴”,园中一切“生物”,也如“行尸走肉”,“了无生趣”,其“处境”远不如“桃花源”。
“神”的“伊甸园”“冻结”“时间”,“终止”“变化”,也就是“万物”的“终结”。“神”是“异”的“终结者”,使“万物”“绝对”“保持”“自身同一”。“瓜果梨桃”固然不会“腐烂”,但“种子”也不会“发芽”,“种子”就是“种子”,“存在”就是“存在”。就哲学的眼光来看,那个“伊甸园”以最坏的方式“图解”了巴门尼德的“存在”和柏拉图的“理念”。由“终止”“自由”得来的“伊甸园”因“避免”了“二律背反”而取得“永久和平”,似乎是“万物”在“神”的“唯一条律”“安排-控制”下,“各安其位”;然则,如果真有“神”“在”,当不会“满意”于这样一种“永恒”的“局面”,就“神学”的眼光来看,这种“死寂”的“世界”,只能“炫耀”“神”的“权威”,而无法“增添”“神”的“荣耀”,“伊甸园”将成为“神”的“玩物”,而不是“神”“光环”。
“自由”“在”“时间”中的“创造”给“人”带来“功业”,也给“神”带来“光彩”:“自己”的“被造者”同样也会“创造”。“人”的“自由”的“创造”如何“显示”“神”的“荣耀”,这个课题,给“神学家”留下了“工作”的余地。一旦“神学家”“完成”这个“课题”而被“神”以“优良”成绩“通过”,则“人”-“神”都不再“需要”那个“铁板一块”的“伊甸园”的“存在”,这样,“终结”的就不是“自由”,不是“时间”,而是“伊甸园”。
八、“人世间”的“纷争”、“和谐”与“同一”
“人世间”与“天上”的“伊甸园”完全不同,那是一个“征战之地”,因“自由”“进入”“自然”,是两个“不同来源”的“规律”的“相遇”,“两个”“原则”的“激荡”,“纷争-冲突”“不可避免”。“自由”通过“人”的“意志”和“行动”“自己”“创造”着“自己”的“时空”,“自由”“改天换地”。
当然,“人”不是“神”,“人”在“创造”“自己”的“世界”时,须得“审时度势”,不仅“自由地”,而且也要“聪明地”(尼采)做自己的工作。“人”固然努力“摆脱”“现存”的“时空条件”,“创造”“自己”的“新时空”、“新世界”;但“人”“必须”“在”“既存”“时空条件”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世界”;而对于“神”来说,那个“伊甸园”恰是一个“既存”的“世界”,“人”“被罚”“进入”一个“新世界”,要用“血汗”“开发”出来;而“开发”出来的“成果”却又“归于”“神”,是“神”的“奇迹”,是“神”“证明”“自己”“存在”的“证据”。“人”“被罚”“有死”而使“自己”一切的“劳作”皆归于“无”,“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人”的“自由”也因“死”而归于“灭寂”。
于是,“人”既然“带着”“自由”“被贬”“下凡”,第一要务则为“争取”“自由”“存在”的“权力”,而不使“自由”成为“空谈”,亦即“自由”不仅是“思想”的,而且也是“现实”的;但“现实-既存”的“时空”是“铜墙铁壁”,是“自然”的“必然”,于是“冲突”变得“不可避免”。“自由”“藐视”一切“既成”的“铜墙铁壁”,“确信”“自己”有“摧枯拉朽”之力,有能力在“废墟”上“建立”“自己”的“时空”,“时空”是“属”“自由”的,而不是“属”“自然”的,“自由”为“自然”“立法”,而不是相反。“自由”不像“孙悟空”有“大闹天宫”的本领,而只能“大闹地宫”;“自由”的“证据”在“地上”,而不在“天上”。
于是,“自由”“需要”“科学”,“自由”要“通过”“科学”来“实现”“自己”。“自由”通过“科学”使“自己”“自然”,也使“自然”“自由”。于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来自“自由”,是“自由”“创造”了“科学”,“自由”为“科学”的“创造者”,而“被造者”“出”,“创造者”“隐”,“雕塑(象)”“完成”,“雕塑家”就“隐”去,除非刻上了自己的名字。一切科学艺术之“作品”之所以多有“署名”,初不在“维护”“知识产权”,而是“彰显”“自由”。
“自由”“创造”了“科学”,同样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对立面”。“科学”的“原则”不是“自由”的“原则”,“自由”由“确信”“自己”开始,而“科学”以“不信”“自己”开始。“自由”以“确信”“求知”,“科学”则以“不信”“求知”;反过来说,“自由”“不信”任何“他者”“有可能”“限制”“自己”,而“科学”则“确信”“有一个”“他者-客体”“正在”“给”“自己”以“限制”。“自由”“高傲”地宣称“自己”为“无限”,“科学”则“谨慎而自谦”地“承认”“自己”为“有限”的。“科学”的“可能”的“对象”,“在”“经验世界”。
“科学”在“经验世界”“建立”“秩序”。“科学”在这个“世界”也“发号施令”,“令”“万物”“各安其位-各行其道”,在这个意义上,“秩序世界”也就是“和谐世界”;只是这个按“科学”“原则”“建构”起来的“和谐世界”并不是“永恒”的,“科学”的“和谐”并不“终结”“万物”的“变化发展”,“变异”留下了“纷争”的“可能性”,而已经“进入”“经验世界”的“自由”,虽然“被”“隐蔽”起来,但却“暗潮涌动”,“搅动”这个既存的“和谐世界”,不使“陷入”“死水一潭”的境地,“自由”给这个世界“注入”“活力”。
“科学”“治理”这个“经验世界”,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自由”却“引导”着这个“世界”的“方向”,“自由”“维护”着“科学”在“时间绵延”中“无限”发展的“权力”,但“科学”“面对”的是“有限”的“时空”“世界”,“承受”着这个“时空”的“制约”;“自由”“引导”着“科学”“超越”“当下直接”的“时空”而“协助”“自由”“开辟”“另一个”“新”的“时空”,于是“科学”同样具有了“自由”的“权力”。“科学”不仅是“维持”“现实”的“和谐”的“手段”,而且是“改造”“当下现实”的“强有力”的“武器”。“科学”是“自由”的“武器”,“科学”为“自由”“工作”,“科学”“协助”“自由”“开辟”“理性”“自己”的“(新)时空”。
“科学”的“旨趣”是在“现实世界”“建立”一个“和谐”的“王国”,“确信”“自己”“建立”起来的“和谐”是“合理”的;但“科学”的“精神”又自“怀疑”“开始”,“科学”“总是”“打破”“自己”“已”“建立”起来的“和谐体系”,“重新”“取得”“更高级”、“更深入”的“发展”,在“科学领域”“学无止境”。
“科学”由“疑”而后“立”“信”,似乎“疑”是“绝对”的,而在“怀疑”“暂停”时这个“信”是“相对”的,“与时俱进”的,“信”“在”“时间”中。
“自由”则似乎有一种“相反”的“过程”:“自由”的“理性”似乎是确立一个“无可怀疑”的“信”,“信”“自由”“自己”的“现实性”,由此“怀疑”“一切”“现存”的“持续-和谐”,“推动-引导”“科学”“打破”“已建立”的“和谐”,“重新”“建立”“和谐”。
在这个意义上,“和谐”是“经验”层面的,而“自由”的“同一性”,则是“哲学”层面上的“意识”;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即“理性”有了以“自由”为“同一”“核心”的“哲学意识”,“理性”才有“化解”“宗教”的“可能性”。
就“知识论”来说,“有理智”的“人”有了“人、手、足、刀、尺”的“知识”并不能与“宗教”“抗衡”,“人”或许有资格“候补”一个“神”的“天使”的“差事”,发挥一些“管理”的“才能”;“人”只有具备“自由”的“意识”,亦即“有了”“善恶”的“知识”,才“触怒”了“神”而“被赶出”“和谐”的“伊甸园”,因为这种“认”“自由”为“绝对”之“善”的“知识-意识”,将“破坏”包括“伊甸园”在内的“自然和谐”,使“人”这个“被造者”成为“创造者”。
所谓有了“善恶”的“知识”,也就是说,有了“善恶”的“评判”“权”,而“人”在没有“自由意识”之前,这个“权杖”一直都在“神”的手中。
“在”“人世间”,“人”“自己”来“评判”“善恶”,尽管“神学-宗教”会说,尔等所作一切比起“绝对神圣”来说,都是“恶”的,“恶”是“善”的“阙失”,“人”的“自由”的“抗衡”,则意味着“善恶”“人”自“评判”,如果“人间”之“事”只是“不同程度”的“恶”,则任其为“恶的轮回”,“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科学”“尊重”一切“人”的“评判”,但并不“僵化”一切“评判”,唯“理性”是从,唯“自由”为“绝对”。
于是,在欧洲文化传统中,“哲学”是一门很“特别”的“科学-知识”。“(经验)科学”以“感觉世界”为“对象”,而作为“超越科学”的“哲学”则以“理性自由”为“对象”,以“绝对”为“对象”,以“(同)一”为“对象”,亦即以“理性”“自身”为“对象”。于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希腊德尔菲神庙的两句格言,都有了“交代”:“勿过”是对“经验科学”说的,“知己”则是对“哲学”说的。
“勿过”为“谨慎”的态度,而“知己”则为“确信”的态度。“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确信”“自己”之“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经验科学”“面对”的是一个“可能”的“世界”,而“超验哲学”则反倒面对的是“必然”的“世界”。“经验科学”“在”“外在”“时空”“内”中“工作”,“哲学”则“在”“自己(内在)”的“时空”中“工作”。哲学作为一门“不同于”“经验科学”的“特殊学科”,后来欧洲哲学家经过“超时空”的“本体-思想体”的“理解”,到“在”“时间”中“同时-瞬间”“工作”(克尔凯郭尔)以及“时间性”“运思”(海德格尔)的发展,理论阐述固然并不相同,对于基督教神学的态度各异,但在这个“尘世间”坚持对“自由”的“确信”态度则“一”。
“人”的“理性”“在”“人世间”有自己的一套“原则”,无需求助于“神”,“理性-自由”自己就是“立法者”,而又以“科学”来“管理”,犹如“神”“身边”的“天使”,“管令”“世间万物”“井井有条”,“欢乐和谐”,“在”“异”“中”求“同”;“和谐”者乃因“异”而“求”“和”,故曰“和而不同”。“科学”“求”“不同-异”中之“关系”,以探索“万物”“运行”之“规律”,使“万物”“和谐相处”,“和谐发展”,如古人仰望之“星空”,“群星灿烂”而“各有其位”、“各有其道”,“科学”“探索”“种种”“不同”的“位(置)”和“道(理)”。
然而,“科学”“面对”“大千世界”,只能“与时俱进”,“不断修正”“自己”,“和谐”总是“相对”的,而“纷争”倒是“永在”的,“科学”永远是“未完成”,是“杂多”而不是“同一”。“暂时”的“和谐”不意味着“同一”。“同一”为“出于”“一”而又“归于”“一”。
于是,“理性”“在”“人世间”不仅“要”“建立”“科学王国”,而且“要”“建立”“哲学王国”。“哲学”“出于”“一”,而又“归于”“一”。
“神学家”常批评“哲学”“制造”“纷争”,当然“事出有因”,古代“哲学”以“科学”的形态问世,“科学”原本从“怀疑”开始,才有“经验知识”在不断“争论”和“积累”中的“发展”,“哲学”作为“科学”的一种形态,当然也在“疑”字上下功夫,甚至是“于不疑处生疑”。“理性”之“自由”更是一种对一切“既成观念”的“否定者”和“挑战者”。“自由”是一种“消解”的“力量”。
不过,“自由”除了“否定”的“消极”意义外,尚有“积极”的“建构”意义。“自由”“怀疑一切”,但不“怀疑”“自己”,“自由”“确信”“自己”的“现实性”,因为“自由”的“现实性”“来源”于“自由”“自身”,“自由”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同出一源”,皆“出于”“理性”自身。“万法归一”,“同出心源”。
于是,“哲学”是一种“特殊”的“科学”,“哲学”以“自由”“自身”为“对象”,“客体”也是“主体”,“哲学”遵循着“认识你自己”的古训,为“自由”的“科学”,在“主体客体”为“一”的意义上,是“同一”的“科学”,“纯粹”的“科学”,亦即“纯粹自洽”的“科学”。
在这个意义上,出乎“神学家”意料之外的,我们说,唯有“哲学”才有“避免”“纷争”的“可能性”。“哲学”的工作,包括了“论证”“终止纷争(同一)何以可能”。
欧洲哲学的传统,由于“披上了”一件“科学”的“外衣”,也会像“经验科学”那样“纷争蜂起”,“学派林立”,又由于“暗含着(无论有意或无意)”“终止纷争(同一)的可能性”这个问题,“哲学”的“诸学派”又各自摆出一副“唯我独尊”、“唯一真理”的架势,遂使“哲学学派”之间的“争论”,也都成了“二(众)律背反”,不能像“(经验)科学”那样,有较为明显的“进步”,“哲学”在“历史时间”中的“发展”,会令“哲学山头”越来越多,各种“主义-论”“层出不穷”,每一个“哲学学派”都有可能成为“铜墙铁壁”,成为一个“没有窗户”的“单子”(莱布尼兹),“单子-学派”“内部”力求“自洽”,“单子”之间则“一片混战”。
于是乎,“哲学”“退居”“内线”,“修整内部”,“苦心经营”起“自己”“内在”的“一片乐土”,使之“天衣无缝”,“自洽融通”,而又“与世无争”;并不是说,“哲学”“放弃”“世界”,欧洲的“哲学”传统中固然也有像斯多亚派那样的“逃离”“现实世界”的,但在尝试了各种“逃离”方式之后,发现可以像基督教那样以一种“超越”的方式,从“自由”的“创造”再“回归”“自由”的“基地”,“哲学”的“工作”就可以在“认知-认识-意识”这条道路上寻找出自己的立足点。
“哲学”仍是一种“科学知识”的形态,但是一个“特殊”的“科学知识形态”,它不再以“(经验)科学”为“外衣-形式”,而是将“(经验)科学”“吸收-融化”为自己的“内容”,成为“哲学”的“内在”的“世界”,成为“自由理性”“开创”“自己”的“世界”的“经历”,也就是在“经验”的“世界”中“意识到-认知到”“自由”“发展”的“历程”,在“种种”“可能性”中“认出-识别出”“自由”“实现”“自己”的“必然性”。
在“必然-绝对”的意义上,“哲学”果然有“化解”“宗教”的“可能性”:一切“纷争”在“哲学”的“同一”中被“化解”为一个“必然”的“过程”,“哲学”由“始基”“出发”,又“回到”“始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经过”“多”,又“必然”地“回到”“一”。
■责任编辑/卢云昆
“Paradise” of theology i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YE Xiu-shan
Although Christian theology as an eastern religion in the Middle Ages had much influence o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y, it was quickly Westernized and became the important base of the central values for the Western-European culture. In this process of westernization, the traditional European philosophy functioned as a catalyst for strengthening this religious theory which gradually became a strong ideological force. The moralizing power of Christianity consists in putting belief upon knowledge; with the help of philosophy, its belief is not a kind of superstition but a kind of rationality based on reason and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