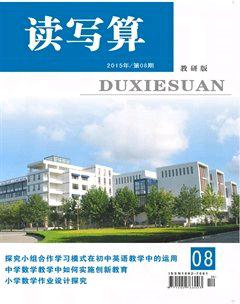赖声川戏剧中嬉皮理想价值观与佛法思想的融合
2015-12-07胡明华
文‖胡明华
赖声川戏剧中嬉皮理想价值观与佛法思想的融合
文‖胡明华
嬉皮理想价值观与佛法思想构成了赖声川戏剧创作的核心思想价值观。在嬉皮理想价值观的影响下,赖声川在剧作中坚持对于西方科技与物质文明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对于内在精神信仰的追寻与建构、对于自由和叛逆的艺术创作追求等。而佛法以其系统和深刻的生命智慧以及关注现实人生的修行实践弥补了嬉皮理想价值观的不足之处。两者在赖声川的戏剧作品中得到了融洽地统一。
赖声川;嬉皮理想价值观;佛法思想
嬉皮与佛法,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字眼却在戏剧家赖声川的身上及其戏剧创作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影响下的赖声川,嬉皮文化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嬉皮文化的精神虽然以自由叛逆为主,其价值观也体现出多元甚至矛盾性的特点。从嬉皮文化多元的价值观中,赖声川所吸收和坚持的是其对于西方主流文明的反思与批判精神,包括自由、平等和爱的追求、物质主义和消费文明的批判、自由叛逆的艺术个性表达以及对于内在精神信仰的追寻等内容,这些积极理想的价值观一方面帮助赖声川走上了佛法修行的道路,另一方面又让他在戏剧创作的道路上以自由叛逆的精神不断地寻求新的创意与突破。
在赖声川的戏剧作品中,首先是通过嬉皮意象或符号的设置来表达对于那个逝去时代的缅怀与追忆,并传达嬉皮轻物质主义、反对战争与暴力、追求自由与爱的价值观;其次通过嬉皮理想价值观与佛法的融合揭示佛法才是一条更为宽广的通向自由与理想的精神道路。对于佛法,赖声川有自己独到的体悟:“真正去理解它之后,你就会发现它根本不是宗教,是对于生活的态度,对于生命的追寻,它是一条道路。道路的终点就是对宇宙和生命真正的理解。”[1]24最终,由于赖声川在利他主义的思想层面把嬉皮理想价值观与佛法统一融合在一起,使其在戏剧创作中展示了超越民族和国界的宇宙视野与生命关怀意识。
一、赖声川与嬉皮时代的文化价值观
赖声川在谈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曾说过:“我等于是六十年代长大的。六十年代对我来讲还很近。它是某一种文明的开花,有人说是最后一次开花。”[2]165这种文明的开花即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后来席卷西方的反正统文化运动——嬉皮文化运动。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自二战以来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传统信仰的失落,那时的年轻人出于迷惘和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产生了强烈的碰撞,并最终形成了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一种完全自发而纯粹精神性的运动:嬉皮运动。伴随着这个运动,嬉皮士们产生了。他们大多留着长发,穿着奇装异服,与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针锋相对。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复杂多面,甚至包含着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既有积极的一面,如重感情、轻物质,反对战争和暴力,呼唤自由、平等和爱,尊重和保护自然等主张;也有消极逃避的一面,例如通过幻觉革命、吸毒、性自由来逃避现实的生活方式。赖声川虽然承认自己是个嬉皮,但他是有选择地接受嬉皮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完全摒弃其消极堕落的生活方式和手段。正如研究者所言:“嬉皮士运动发展到后期,便背离初衷,向两派发展。一派
是真正的理想主义,一派是纯粹的享乐主义。”[3]32而且,需要明确一点的就是,在赖声川思想中所体现的嬉皮价值观与美国社会1960年代流行的嬉皮价值观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和差异的,因为赖声川结合自身的成长环境和佛法修行,对嬉皮价值观进行了有选择性地接受和转化。一方面,在台湾戒严环境下倍感束缚和压抑的成长经历,使他与崇尚自由和叛逆的嬉皮精神产生了心灵上的契合,大学时代玩音乐的经历,还有后来在戏剧创作中自由叛逆的艺术追求都可以看到其嬉皮精神的影子。另一方面,赖声川本人内敛温和的个性,以及自身在佛法修行中所接受的慈悲利他的思想使其摒弃了嬉皮运动中具有放纵、破坏性和暴力性的一面。
总的来说,赖声川从嬉皮时代的文化价值观中所吸收的思想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嬉皮文化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主流文明价值观的反叛,不仅在赖声川的戏剧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于西方以工业和物质文明为代表的主流价值观的批判,而且他本人在东方文明的佛法修行中积极寻求并建构人生价值观的选择和坚持都是对于嬉皮反叛精神的最好证明。在美国这一反叛的群体以中产阶级子女为主。对于他们来说,“美国主流社会所强调的个人竞争和物质享受思想已严重毒化了社会空气,人们不仅因相互之间激烈竞争而使得人际关系冷漠,而且还因疯狂追逐物质利益而导致心灵世界空虚”[4]96。加之,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学家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1911—1972)对于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对人的异化现象的分析等社会思潮,也推动了美国青年采取多种方式反叛中产阶级所代表的主流价值观,他们或者加入政治组织寻求社会进步和公义,或者通过打造嬉皮士文化的方式来“表达对爱、自由、和平的渴望”,以“重建一个充满爱的世界”[4]96,还有许多嬉皮士放弃了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选择到东方文明的国家或地区寻求精神的家园。赖声川就是阅读了嬉皮时代Gary Synder等人的诗歌后开始对东方的宗教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第二,嬉皮文化的核心为自由叛逆的精神。这种自由叛逆的精神主要体现在赖声川的戏剧创作理念和实践中。他接受凤凰卫视《大剧院•零距离》采访时说:“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很叛逆,我很叛逆我才会做《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才会做《暗恋桃花源》,这些戏它还是需要一种叛逆的性格,而且这个叛逆的性格不一定是对社会的叛逆,或政治体系的叛逆,它可能是对艺术的叛逆,就是说你传统或你主流该怎么做,我就不怎么做,所以很多人现在把我变成主流,我都觉得蛮好笑的。”[5]
首先,赖声川所选择的集体即兴创作方式本身就是1960年代欧美戏剧界反叛精神的产物。在1960年代嬉皮反叛文化的影响下,集体剧场、公社剧团纷纷出现,大力发展了这个原由法国戏剧家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最早提出的集体即兴创作理念。例如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的“国际剧场研究中心”(ICTR)、法国阿莉安•努虚金(Ariane Mnouchkine)的“阳光剧团”(Théâtre du Soleil)、约瑟夫•柴金(Joseph Chaikin)的“开放剧场”(The Open Theatre)和理查•谢克纳(Richard Schechner)的“表演群”(The Performance Group)等都先后采用了集体即兴的创作方式。由于集体即兴的创作方式赋予每一位成员以同等重要的地位,使导演从霸权式的独裁者转化为创作团体中的倾听者与协调者。导演往往不设定自己的喜好与立场,而是扮演引导着和刺激者的角色,让演员在无压力状态下释放最大的创作能量。因此这种方式充分体现了1960年代嬉皮运动所追求的自由平等以及对传统剧本创作方式的反叛精神。其次,在对于传统艺术的态度上,赖声川持有一种颠覆和叛逆的创造精神。无论是《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对相声这一传统艺术的现代剧场处理,《暗恋桃花源》中使用意大利艺术喜剧的手法解构经典文本《桃花源记》,还是《西游记》中对唐三藏西天取经故事的重新编排与改写等等,都可以看到赖声川在承继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反叛与创新的艺术追求。再次,赖声川勇于实验不同类型的剧场形式与风格。三十分钟的实验短剧《菩萨三十七种修行之李尔王》《新加坡即兴》《先生,开个门!》,八小时的环形剧场史诗剧《如梦之梦》,环境剧场形式的《落脚声——古厝中的贝克特》《梦游》等不同剧场类型的作品都证明了赖声川求新求变的艺术创作精神,但是这种自由与叛逆的戏剧创作精神因为与佛法利他主义思想的融合,使其并未走向极端的反叛,而是在包容观众的基础上实现了先锋实验与大众艺术的融合。相比于颠覆传统、反抗权威、舍弃语言、反对文学性戏剧的西方前卫剧场,赖声川仍注重在剧场中讲故事,认为故事是最容易与观众发生沟通,并实现剧场创意的核心所在,因此他又是一个传统的偏故事导向的戏剧家。归根结底,这是由利他主义的价值观与对社会人生的关怀态度所决定的,因此赖声川的戏剧会从先锋走向大众文化主流,也是其必然的一种发展趋势。
第三,在嬉皮文化中还包含着利他主义价值观的成分,尽管它并不是嬉皮精神的核心内容,也不在较为显性的层面为人注意,但是赖声川根据自己对嬉皮文化的接触体验发现了这点,并在佛法的影响下有意地突出和强化了嬉皮价值观中的利他主义思想,并且主动地在利他主义的层面,把嬉皮的理想追求与佛法思想融为一体。
赖声川曾提及过西方60年代流行文化对他的影响:“台湾的六十年代,我们非常受西洋文化的影响。然后,西洋正在发生一个文化大革命,当下文化的价值观就在‘我’‘我要’‘我爱’,而我们在六十年代所接触的流行文化是相反的。‘我要怎么改变这个世界’‘我要怎样为人类服务’‘怎样让这个世界更好’,不是无聊的个人小事情,而是整个世界的大事情,讲穿了,我们那个
时代是一个理想的时代。”[6]正如约翰•列侬在歌曲《想象》中所唱的:“想象一下吧,如果这世上没有贵贱之分,人们哪里有贪婪的必要,甚至连饥饿也会远离我们,人们将亲如手足,情同一家。”还有披头士歌曲《黄色潜水艇》中的歌词:“所有的朋友欢聚一堂,左邻右舍就在我身旁”“我们生活无忧无虑,人们彼此相亲相爱”。类似的歌曲还有约翰•列侬《给和平一个机会》、鲍勃•迪伦《战争的主人》等等,它们谈的不是“小我”的问题,而是世界和平以及对人类之间平等友爱关系的呼唤。后来赖声川在美国柏克莱大学求学期间,曾是嬉皮运动大本营的柏克莱以其独特的自由包容的文化氛围,让赖声川直接跟这种精神连接在一起,更加体会到了一种宏大的视野与关怀,因为在那里,“所有人都不是来自那里。所有人都是为了更大的东西在思考”[2]167。赖声川不仅感触于自己去对地方了,并直言:“你要走自己的路,而你的路是去帮助别人的,而不是帮助自己的,我觉得这就是柏克莱精神。”[7]
而1960年代的嬉皮精神与东方的佛教思想本身就存在着密切互动的关系,因为“就嬉皮士的宗教信仰和灵魂拯救而言,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对东方宗教的崇拜和对东方神秘主义的迷恋”[4]174。20世纪60年代,许多嬉皮士前往印度、巴基斯坦等东方国家寻求精神超越和灵魂拯救。赖声川也是在大学期间读了嬉皮时代美国诗人所推崇的中国寒山等人的诗歌,接触到东方的佛禅思想。
赖声川1975年有缘接触藏传佛法、成为密宗弟子后,无论是好友马修•李卡德的亲身所为还是佛法中“自他交换”的修行法门都让他更进一步坚定并拓展了嬉皮利他主义的价值观。法国人马修•李卡德是一个从60年代的嬉皮转化为佛教徒的典型例证。马修原来是巴黎巴斯特学院分子生物学博士。年轻时才华横溢、兴趣广泛,但当他26岁时,觉得拥有各种艺术或科学才华并不能让他满足,反而是像甘地那样能关怀、启发、改变别人的人才是他仰慕的。他在1967年第一次前往印度之后,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2年,他抛弃了西方优裕的世俗生活条件,常年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区,追随藏传佛法上师学习和修行。在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对于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的反叛,在东方宗教中寻求心灵关怀的精神正是20世纪60年代嬉皮们的典型写照。赖声川说:“马修在我生命中是重要的灵感来源。他的生活非常忙碌,……从事慈善募款及建设工程(他每年固定在四川、青海藏族区建造新的医疗诊所、学校、修筑桥梁,并亲自指导工作),还要出新书、开摄影展(他也是著名的摄影家),参加宣传活动、发表会,还要参与科学实验等。仔细想一想,这么多事情,没有一件是为他自己,我也从来没有看过他烦躁或不安。或许,这就是他快乐真正的秘诀。”[8]马修在现实生活中所实践的利他主义让赖声川深受感动,而它也体现了在利他主义价值观层面,嬉皮理想与佛法思想的完美融合,因为,利他主义也是佛法慈悲精神的核心。马修的佛法上师顶果钦哲王说过:“当我们能够关心他人,一如关心自己,能够忽略自己,一如忽略他人,我们将觉醒。”[9]49此即菩提心开始生起的方式,也是菩萨秘密的诀窍。这种利他的精神直接影响了赖声川的艺术创作理念。
嬉皮理想与佛法思想在利他主义价值观层面的统一使赖声川在戏剧创作中追求的不是个体自我的表达,而是为了实现对于他人和社会的关怀,这种创作动机即利他主义思想的表现。赖声川说:“动机里有两种,一个是利他,一个叫做利己,这两种动机之间,我们需要摆正,每一个创作者都在这中间寻找自己的定位。……它来自内心,它很抽象,但是却是形成所有具体的东西最重要的因素。”[10]因此,以赖声川的作品为例,从关怀弱势群体的《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过客》、《摘星、》《红色的天空》,再到关怀个体生命的《如梦之梦》、《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水中之书》等,正是那种对于他人和群体的关怀和利他主义精神使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历史经验的层面,具有了宏阔的宇宙视野和人文关怀。
二、赖声川戏剧中的嬉皮意象与理想价值观
赖声川在戏剧作品中一方面通过嬉皮意象和符号的设置表达对于那个理想时代的缅怀与追忆;另一方面在创作主题上肯定并传达了嬉皮某些积极和理想的价值观念,例如对于现代物质文明价值观的反思与批判;对战争和暴力的否定、对自由、幸福与爱的理想追求等等。
首先,在赖声川的戏剧中经常可以看到种种嬉皮意象和符号的设置,通过这些嬉皮意象和符号,既表达了对于那个时代嬉皮追寻自由与理想之精神的缅怀与追忆,又传达了嬉皮追求自由、爱与和平的价值观。例如《变奏巴哈》中“有一位戴太阳眼镜、穿花衬衫的男士从右下舞台上,像是画家一样,独自一人把空气当成画布,在上面描绘着什么似的”[11]29。《西游记》中有一位现代工人打扮的涂鸦者多次出现,他在古老的城墙、现代建筑物的墙上、现代台北公司内玻璃隔间的玻璃上展开涂鸦的喷射工作。无论花衬衫,还是涂鸦,都是20世纪60年代嬉皮时代的印记与符号。《十三角关系》中那个手拿喷漆罐喜欢在地铁车厢上涂鸦,喜欢听重金属摇滚乐的安琪是当时嬉皮士的典型形象写照。《如影随行》中那个穿着花衬衫、梳着黑人发型的BOSS也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典型嬉皮士的造型。BOSS工作的“堕落天使机车行”的名字其实是来自于“地狱天使”,赖声川说:“我把剧中的机车行名字取作堕落天使,美国人一看就知道,这与地狱天使有关,骑重型机车哈雷的团队被称为地狱天使。”[12]20世纪60年代,正是一群骑着大功率摩托车四处流浪、追求自由的美国嬉皮士创造了这个名词。《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的女主人公叶樱出场的造型为“她是一位中年妇女,打扮有些嬉皮”[13]130。《新加坡即兴》中的男人和女人最后都变成了嬉皮士的形象。男人从开场时穿西装变成了一个身上披着一块布的流浪汉;女人也从一个穿着旅行衣服、戴着太阳眼镜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头上和身上披着一块大布的吉
普赛流浪女。当时的吉普赛人因其自由不羁和被置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生活方式成为了60年代嬉皮生活的样板。甚至《如梦之梦》中的五号病人与江红在法国客人眼中也是秉持理想主义的嬉皮形象,“他们家好像很有钱,不用靠卖这些东西。听说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离开自己的家庭,然后那个男的,他反战……那女的为爱放弃一切,跟男的流浪天涯,环游世界”[14]172。
在以上多个嬉皮意象中,其中最典型的还是短剧《新加坡即兴》中那个未出场的男人形象。该剧围绕着一个神秘的房间展开,在这个房间里,留有原先房间主人的物品,包括葡萄酒杯、眼镜、派克六十一钢笔、书、项链等等,从这些物品可以看出,主人应是一个注重精神生活追求的人。而根据后来的交待,这个男人最终抛弃了这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选择了一条从西方文明中心到东方佛法圣地的旅途路线去流浪,即柏林→赫尔辛基→萨拉耶维→耶路撒冷→喀什米尔→加德满都。这条路线从地名来看,除了柏林之外,都不是现代世界主流文明所在地,其中的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萨拉耶维即萨拉热窝,被誉为欧洲的耶路撒冷;巴基斯坦的耶路撒冷称为“圣城”;处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喀什米尔是一个多种宗教信仰聚集地;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出生地。这些城市多烙上了战争与宗教的印记,以文化和宗教的包容性而著称。这条路线正是20世纪60年代嬉皮们所热衷的旅行路线。赖声川的好友马修•李卡德在谈到20世纪60年代时,曾说过:“那是嬉皮的时代,嬉皮们喜欢以搭便车或乘坐一部破雪铁龙国民车的方式穿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15]20因此,与马修•李卡德相联系可以看出,《新加坡即兴》中这个虽然从未出场的男人形象其实是对于一个不满于现代主流文明、注重内在心灵世界探索、追求自由和信仰的60年代嬉皮士的典型写照。
其次,赖声川在戏剧主题上也倾向于传达嬉皮的理想价值观,包括轻物质主义、反战以及对于爱与自由的向往和追求等等。具体作品分析如下:
(一)嬉皮轻物质主义的理念体现在:赖声川的戏剧中有很多有钱却并不快乐的人物形象设置以及对物质和消费主义的批判。在嬉皮文化价值观中,重感情、轻物质,希望人类之间相互关心、相互照顾是其重要的内容。赖声川说过:“嬉皮就是不接受社会现有的价值观念,不以物质价值观为生活唯一标准的生活方式。”[16]38嬉皮们追求自由、幸福和爱,但他们认为这些并不是依靠物质(金钱)就能实现的,“我觉得有史以来,并没有人证明过说金钱可以让人快乐,甚至于我觉得可以看到无数的例子是金钱让人不快乐,金钱是让人,你积累的越多,他让你更紧张,更焦虑。”[17]例如《我和我和他和他》中的主人公沈墨和简如镜,虽然一个身为神州集团总裁,一个为知名企业二代代表人物,但他们最自由最幸福的时光却是在他们一无所有、平等相恋的那段时期。《十三角关系》中身为社会成功人士的三位主人公——蔡立委、花姐和叶小姐,他们都在追求利己的幸福和爱,而真正的幸福与爱也离他们渐行渐远。《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中的富商钱大哥,虽然很有钱,能买到豪华的物质享受,却因为抛弃了病重的妻子活在内疚之中,金钱对于他而言,并不能买到内心真正的快乐。《如影随行》中的大桥生意做得很成功,却因为忙于赚钱而缺失了对于家人的爱,导致了自身和家人的痛苦。《快乐不用学》中的大企业第二代宪在身处于家族企业利益的争夺战中,迷失了自我,找不到真正的快乐等等。通过这些有钱却不快乐的人物形象,赖声川表达了重感情、轻物质主义的嬉皮价值观,即幸福、快乐与金钱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而是与我们对他人的爱有关。“那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真正的感觉到更充实在这个世界上,那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怎么去定义它呢?它可能有很多的名字吧,但是也许其中的名字就叫爱,怎么去学会去爱别人。它是真正愿意来奉献自己的一种力量,它是真正愿意去服务的一种力量,它是一种无私的力量,这个东西能够找到的话,其实人生什么都不怕。”[17]在《快乐不用学》剧中,赖声川就直接让何时这个角色说出了自己关于快乐的观点:“快乐是一个抉择,我们此生要选择利他还是利己?最直截了当的证明就是懂得利他的人是快乐的,只懂得利己的人是不快乐的,所以利他带来快乐,利己带来的是不快乐!”[18]23
在《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乱民全讲》《这一夜,WOMEN说相声》等剧中还可以看到赖声川对于消费文明的批判。例如,《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中的人物劳正当感慨:“其实所有的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没有人可以教我们怎么活。唯一能教我们活的就是媒体,而你如果相信媒体所教我们的,它唯一的讯息就是‘尽量而且赶快去消费吧,买买买!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这已经成为我们生活最高指导原则了,再也没有任何指示给我们这个心灵空虚的时代了!”[19]98《乱民全讲》“深度旅游”片段中旅行团的成员不论是挤到奢侈品店里抢购名牌皮包,还是享受顶级的精油按摩和美食,其实质都是通过疯狂的消费来填补自身空虚的心理需求;《这一夜,WOMEN说相声》段子四则通过一个婚姻破裂的女子讲述了现代女性在充斥着美容、减肥和购物等消费元素的商品社会中寻找自我的艰难旅程等。
(二)对战争、暴力的反思与批判也散见在赖声川的多部剧作中,例如《变奏巴哈》中通过一个写信者记录了原子弹毁灭人类的悲剧:“在二十世纪中期,我们发明了一种强而有力的炸弹,作为我们战争的武器。在日本的一个小城市,这个炸弹使得房屋全毁,当时的温度是摄氏两万度,把柏油和金属烧成液体。逃难的居民被火烧成皮肉破烂焦黑,五官模糊,不成人形……”[11]87还如《乱民全讲》中G对于战争的反思。与其他游客在旅行中通过物质消费、沉醉于感官的物质享受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同,G更愿意体验内在心灵世界的超越与升华,他站在战争的废墟面前“看着墙壁上的弹孔,好像感受到当年的士兵哀嚎和祷告的声音,不知不觉的,我一个大男人泪流满面哭的像个小孩一样”[20]153。还有《如梦之梦》中
五号病人对于柬埔寨地雷炸死儿童的控诉:“一直到现在,柬埔寨每天还有小孩子莫名其妙被一些不知名的地雷炸的缺一只手,少一条腿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二十五年了!是谁放的地雷?他认识那个小孩吗?哪里来的那么大的仇恨,要去炸死一个你不认识的人?”[14]174再有《西游记》中核废墟的末世景象,显然也是对战争怪兽威胁的一种隐忧和批判。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赖声川对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反战争和暴力思想的表达。
(三)对爱与自由的呼唤和理想愿景的建构。例如《十三角关系》中的安琪自称是天使,她被派到人间是为了传达自由与爱的讯息;《如影随行》中的露露和真真也都是代表真与爱的天使,她们却在人间因为爱的缺失而丢失了翅膀,无法返回天堂,因此爱才是生命获得自由的重要力量;《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中外星人之所以绑架叶樱的丈夫,是为了下载那个把一家人连结在一起的“爱”以拯救遥远星球上濒临灭绝的生命。还有对于理想愿景的建构。例如《暗恋桃花源》中从桃花源回来的老陶对那样一个理想的所在有具体的描述,“那个地方实在太好了,那地方的每一个人,看起来都是好平静、好祥和……每个人都不再为自己,而是为别人着想,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很美好”[21]69,因此利他的爱才是桃花源的本质所在。《十三角关系》中安琪所描绘的天堂景象,“其实,大家以为天堂是很遥远很遥远的,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喔,天堂不见得是很远的地方。其实,天堂是随时可以看到的”[13]76,对于安琪来说,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中叶樱从巴纳斐尔寄来的照片中也呈现了一个看起来很快乐的地方。通过以上种种对理想愿景的向往和描述,赖声川所要表达的是对于利他之爱的呼唤与肯定。
三、嬉皮理想价值观与佛法思想的融合
赖声川在戏剧中除通过嬉皮意象和符号的设置传达并肯定嬉皮的理想价值观以外,还更多地把嬉皮理想价值观主动地融入佛法内涵之中,来强调和突出佛法的智慧与包容。
嬉皮理想价值观既让赖声川坚持对于当前社会物质文明的批判与反思,另一方面又坚定了他对于心灵修行的追求与信仰;而佛法对于生命无常与虚幻的认知,对于痛苦与快乐之因的探究,又使赖声川找到了更为明确的收获自由与快乐的智慧和方法。因此嬉皮理想价值观与佛法思想在赖声川的身上得到了自然地融合,如前所述,融合的焦点即是利他主义的观念。嬉皮运动在西方昙花一现,原因在于它只有理想价值观,缺乏一定的哲学和思想支撑。而这个缺陷在佛法这里得到了弥补,所以赖声川从对嬉皮理想价值观的守望逐渐转向对佛法思想的侧重,他表示:“看来看去,对我来说,就只有佛法一直可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问题的检视,可以让人不断深入。走得越深,就有更深的智慧等待着我们。”[22]
以《西游记》为例,其中既包含了嬉皮对西方主流文明的反叛与否定精神,还有对于佛法的肯定与追寻。舞台上贯穿始终的现代工人打扮的涂鸦者形象就是明显的嬉皮符号指代,而古老的佛像与《心经》的出现又在昭示着佛法的内涵。剧中三个西游故事既平行发展又相互穿插映照,一是神话层面的孙悟空西渡求长生不老之术;二是近代史层面的清末留学生唐三藏向西方求取真知以富国强民,三是当代层面的台湾青年阿奘留学美国谋求幸福生活。赖声川通过现当代的中国与西方接触、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揭示了西方工业文明和物质文明过度发展是具有毁灭性的,它并不能够解决人类生命中的终极问题,也不能够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和自由。第一幕开始,舞台上就呈现了自古至今人类所必然面对的终极问题——死亡。现代病人阿奘在手术台上接受心脏手术,但是手术以失败告终;古代的美猴王孙悟空亦为将来身亡之事而忧虑。第四幕,在西方的伪中式餐馆内,当唐三藏对西方的一切先进成果都照单全买,阿奘为了留在美国享受一切最新、最进步的科技、学问、思想,花钱买通律师办身份的过程中,舞台上通过一个外国家庭成员生老病死的种种变化展现了生命的无常真相,而这样的生命图景通过一个外国人的家庭来呈现,所表达的是现代西方即使拥有再先进的科技和文化,面对生命的种种无常也缺乏应对的智慧和方法。剧末身老体衰的唐三藏与穿着病人袍子的阿奘,以及舞台上的废墟包括爆炸的核能厂、手臂、机器、书、汽车的遗憾等,它们既宣告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已陷入困境之中,同时又表明中国要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注定是悲剧性的结局。剧中阿奘的心脏病、外国人乙突发的心脏病寓意着心灵问题在西方发达的科技与物质文明中是无法得到有效治愈的,而出现在剧中的佛法经典《心经》或许才是对症之药。剧末,唐三藏在西方绕了一圈之后还是要带着《心经》,解救孙悟空去求取佛经,他的经历证明了或许通向东方佛法的道路才是现代人类从中获得心灵解脱与自由的最终选择。
《新加坡即兴》也是一部把嬉皮理想主义价值观融入佛法思想的作品。该剧原来是赖声川2002年为了纪念已故好友——新加坡戏剧家郭宝昆而制作的一部实验短剧,剧中那个理想主义者——神秘男子的形象就带有郭宝昆本人的影子。赖声川通过这个神秘男子的形象既表达了对于嬉皮士自由与理想情怀的追思,同时又通过佛法的智慧与包容指出,自由与理想的道路其实不在远方,而存在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改变中。
剧中那个神秘的男子像嬉皮一样选择了以流浪的方式来追寻自由和理想,而他在日记中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所有的路的终点就在这里。”[23]这句话是理解该剧主题的关键。剧中除了这个并未出场的神秘男子之外,还有其他两个人物,一个是前来入住房间,寻找多年前存放的手提箱的男子,一个是为了保存自己与神秘男子的过往记忆而封存了房间内的一切,为了追随神秘男子流浪的脚步而离开这里的女人。因为女人带走了手提箱去流浪,导致那位在房间里
疯狂寻找手提箱未果的男子也不得不追随女人去流浪以找回手提箱。最终,当他们如同神秘男子一样经过了漫长的旅途流浪归来之后,无论是他们所执著的房间物品还是手提箱对其而言都已经失去了重要的意义。女人发现房间里的物品并没有如同自己预期的保持原样,天花板被钻了个洞,风扇上的布也没有了,地上有一堆象征着佛法无常意味的沙子,这一切起初都让她紧张、惊讶,但最终还是认命、坐下、慢慢地摇头,接受变化的发生;男人回到这个房间里,看到桌子上放着自己梦寐以求的手提箱,过去,打开,却发现里面是空的,“男人无奈的把手提箱放在地上。他坐在沙发上,戴起桌上的眼睛,安静的看着海”。通过男人和女人前后的变化,可以看出经过旅途的流浪,他们最终收获了应对人生种种无常的智慧与态度,剧末,女人起身,把桌上的蜡烛点起来,象征着智慧之灯在他们的内心被点亮,这既是他们所流浪过的路的终点,也是嬉皮士追寻理想与自由之旅的终点,因为他们所追寻的一切都能在佛法的智慧中得到求解。
《快乐不用学》一剧中既有对金钱必然能给生命带来快乐的否定,也有佛法对于生命快乐的认识和智慧。剧中的三个男人——宪在、无名师、何时的外公都曾富有过,但是富有的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快乐,反而是焦虑与痛苦,身边的人也都离他们而去。何时遇见了一个小女孩,宪在遇见了自己的回音,他们对待小女孩和回音的态度决定了他们能否得到快乐。“生命中碰到每一个人你都不知道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可能有很深的关系,你都不知道。你应该尽量对他好才对。”[18]50剧中把小女孩设置为何时的母亲,把回音设置为宪在的前世——音乐家巴哈,都是具有佛法含义的,佛法认为:“如果你想的不只是今生,而是无数的前世,你就会了解到,所有众生都曾是我们的母亲,都曾像今生的母亲一般照顾你。”[9]49“当我们能够关心他人,一如关心自己,能够忽略自己,一如忽略他人,我们将觉醒。”[9]52何时和小女孩在彼此的关爱中收获了真正的快乐与幸福,宪在也在与回音巴哈的友好相处中找到了真实的自我。因此他们的故事既有嬉皮反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流露也包含着佛法对于快乐的智慧启示。
另外,赖声川剧中的一些人物形象身上也体现了嬉皮与佛法思想的融合,例如《如影随行》中的BOSS从外表上看是一个身着奇装异服、行为怪异的嬉皮形象,但他同时也兼具了佛法上师的角色,正是他帮助处于中阴身的大乔认识到自身的处境,鼓励他勇敢地走向下一个生命的轮回;《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中的叶樱外表是嬉皮装扮,但是却持有平等慈悲的宇宙生命观等。
总之,正因为赖声川在嬉皮价值观方面“相信人的理想可以改变世界”[24],在佛法方面相信“要改变社会,还得靠每个人自己内心的改变”[25],嬉皮的理想主义与佛法的心灵修行在赖声川戏剧作品中得到了自然地融合,而后者又以其深刻的思想给他更多的智慧火花。2000年之后的作品,如《如梦之梦》《在那遥远的星球,一粒沙》《如影随行》《快乐不用学》等剧中所蕴含的佛法理念越来越明显和集中,这既是赖声川对于嬉皮理想主义价值观的一种坚持和发展,也是他多年佛法修行的成果。
[1]高宇倩.赖声川访谈:向外看的人在做梦 向内看的人可以觉醒[J].生活,2013.(2)
[2]汪俊彦.戏剧历史、表演台湾——1984-2000赖声川戏剧之戏剧场域与台湾[D].台湾大学戏剧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
[3]夏学花.嬉皮士——美国主流社会的叛逆一代[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4]王恩铭.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嬉皮士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赖声川.台湾剧场拓荒者的戏梦人生[EB/OL].凤凰网专稿. http://phtv.ifeng.com/program/ dajuyuan/detail_2011_09/19/9293527_3.shtml.
[6]赖声川,柴静.做时代的结绳者与观察者[EB/OL].新浪视频. http://video.sina.com.cn/p/ent/s/ m/2012-05-01/212661737559.html.
[7]赖声川.走别人不走的路[EB/OL].中央电视台《开讲啦》栏目.2013-7-13. http://tv.cntv.cn/video/C38875/ a6a9c0bc0d4a4ffdaa20bd95fce4028f.
[8]赖声川.快乐学•序言[M]//马修•李卡德.赖声川.丁乃竺,译.台北:天下杂志出版社,2007.
[9]顶果钦哲法王.觉醒的勇气[M].赖声川,译.高雄:雪谦文化出版社,2005.
[10]天蓝.赖声川:以智慧打开创意[N].新京报,2006-10-25.
[11]赖声川.赖声川:剧场2[M].台北:元尊文化出版,1999.
[12]张霞.赖声川:《如影随行》解读人生[J].21世纪经济报道,2008-04-07(44).
[13]赖声川.赖声川剧作:魔幻都市[M].台北:群声出版有限公司,2005.
[14]赖声川.如梦之梦[M].台北:远流出版社,2001.
[15]尚•方斯华•何维尔,马修•李卡德.僧侣与哲学家[M].赖声川译.台北:究竟出版,2012.
[16]黄小米.嬉皮赖声川[J].财智生活,2010(3).
[17]赖声川.拆掉所有分别心 待人接物莫分贵贱[EB/OL].凤凰视频文字实录.2013-6-3. http://phtv.ifeng.com/yuanchuang/ detail_2013_05/31/25949648_0.shtml.
[18]赖声川.快乐不用学[Z].“表演工作坊”提供剧本材料.
[19]赖声川.赖声川剧作:世纪之音[M].台北:群声出版有限公司,2005.
[20]赖声川.赖声川剧作:拼贴[M].台北:群声出版有限公司,2005.
[21]赖声川.赖声川剧场第一辑[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22]陶庆梅,侯淑仪.刹那中——赖声川的剧场艺术[M].台北时报文化出版,2003.
[23]赖声川.新加坡即兴[Z].“表演工作坊”提供剧本材料.
[24]李玉玲,于国华.相对论——赖声川丁乃竺:低声密语三十年[N].联合报,2005-04-05.
[25]邓莉蓉.台湾著名戏剧导演赖声川:不要再勉勉强强[EB/OL].联合早报. 2008-05-04.http://www.zaobao.com/ special/face2face/story20080504-28447.
J80
A
本文为2014年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项目(2014347)。
胡明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