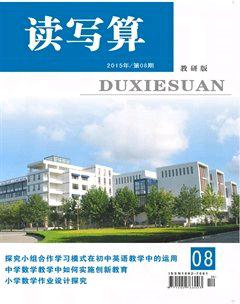赛博空间中的拟真风景
——以网络游戏“刺客信条”为个案的分析
2015-12-07钟碧莉
文‖钟碧莉
赛博空间中的拟真风景
——以网络游戏“刺客信条”为个案的分析
文‖钟碧莉
随着数码拟真技术的发展,人们已经可以在赛博空间(cyber space)模拟人的城市生活,而近年来大热的电子游戏“刺客信条”则以其高度逼真地“还原”古代城市(包括佛罗伦萨、大马士革等)而深受玩家追捧,很多玩家甚至认为自己通过在虚拟世界中的游戏,穿越了时刻,亲身游历赛博空间所营造的城市。然而,根据鲍德里亚的建筑美学论调,“拟真”乃是通过代码的自我复制,过度繁殖而扼杀了本真和真实生活。的确,“刺客信条”中的虚拟城市建筑本质上的确是代码通过对时代有名的建筑的“碎片化”拼凑而成的,它的高度仿真剥夺了真正建筑所应有的错觉和美感。玩家的体验并不是城市的体验,而是代码的体验;越是逼真,就越是无法实现的美学谎言。
赛博空间;拟真;鲍德里亚;城市风景;建筑美学
“刺客信条”是由著名的育碧蒙特利尔工作室(Ubisoft Montreal)开发的一款3D动作类游戏,玩家以一名叫Miles的刺客后裔的身份开展游戏,游戏中的Miles通过虚拟机Animus回到12世纪的中东,目的是为了寻找失落的伊甸园碎片。这款游戏以逼真的城市风景而著称:迄今为止“刺客信条”分别推出了以古佛罗伦萨、大马士革、波士顿、巴黎和纽约等城市为场景5个版本的游戏,里面的拟真风景令无论是玩家还是观看者都叹为观止,制作团队还开放了一个庞大的,包含对游戏中所出现的建筑物、风景详细资料的数据库,并宣称和真实场景的相似度达到80%以上。“刺客信条”作为一款电子游戏,它首先开发了一个丰富的赛博空间,里面有各色虚拟的人物,活动在拟真的风景之中——因此玩家会发现自己穿梭在佛罗伦萨的街道,或跳跃在纽约摩天大厦的顶部,或迅速越过巴黎圣母院的玫瑰花窗……这里面的拟真风景(包括著名的建筑物、居民的房屋、城市的运河和堡垒)给玩家营造了一种“身临其境”“以假乱真”的真实感,很多人甚至津津乐道自己已经“游历”过这些城市——在游戏之中。这就不得不引起对于一个问题的思考:这个赛博空间中给观者所呈现的城市及其建筑,是否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着城市的美学?这些给玩家们“身临其境”的虚拟城市,和我们真正在城市居住者,或者旅游者有何不同,我们真的能够在游戏中体验“游历”甚至“居住”某个城市吗?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亦即是,赛博空间所提供给我们的拟真体验和我们真实的传统生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丰富,亦或是掠夺?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要弄清什么是“拟真”。
一、拟真技术进入感官场域
关于“拟真”,似乎没有能比鲍德里亚的著作《象征交换与死亡》给出更为详尽的答案了。鲍德里亚将“拟像”(simulation)分为三个阶段:文艺复兴的仿造、大工业时代的复制,以及数码时代的拟真。拟真作为最后的阶段,不在是“一种指涉性的存在,或一个实体。它是由没有原本或现实的真实模型的创造物:一种超真实。”(1)它比错觉更具真实性,但本质却只是一个由条形码生产出来的乌托邦。(2)条形码作为拟真时代最为重要的系统元素,催生了一种“无本体”(non-original)的生产。文艺复兴的仿造必须基于原作,而且临摹品和原作之间的距离也是必须的;只有保持距离,临摹品才能借助原作的光环以实现自己人文修辞。大工业时代的复制,按照本雅明对于“机械时代”的论述,虽然掠夺了原作的光韵(aura),但这种复制是有源头——原作品的,例如一张照片的复制必须从一份胶卷开始,虽然它可以被拷贝无数份,但这并不损害胶卷作为首个源头的存在事实。但到了拟真时代,本体(原作品)的地位被完全消融,所有的产品都是从条形码的1和0中被“创造”出来,这是一种流向;另一种流向则是真实世界的物品被强制性“编码”(coded),从而嵌入条形码构成的庞大结构之中。
统一的1和0如同驱魔一般驱除了所有“异己之物”,在现代社会这个中心丧失、失序、混乱的游乐场中,这种强制性统一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无比的安全感。无论是有生命之物,亦或是无生命之物,都可以被编码,纳入,类型学在此达到了自己的极致又复而完全吞噬自己——再也没有任何类型了,有的只是面目完全一致的代码;个性被面目模糊的统一取代,技术全面入侵生物学和我们的感官体验。最为明显的是“人”不再是生物学,或者法律上的主体,他/她被简化为一堆由条形码表达的信息,存在一个称谓“人口”的数据库中。现实中,很多退休老人死后,其退休金仍被长期冒领;或者某个失踪人口的身份证为他人所冒用的戏剧性场景屡见不鲜。这是因为,人已经不是在真实空间中鲜活的、呼吸着的、生活着的人,而是一组信息,国家机构根据这组信息决定对待每一个人:死亡/生存,残疾/健康,男/女……代码成为了一种病毒,所有人都被污染。
同样,“刺客信条”中的风景也是如此,玩家所看见的一栋栋著名建筑,或者游走的每一道纽约的黑巷,不过是由条形码胁持的真实世界的碎片产生出来的虚拟幻象,它并没有错觉闪烁的美感,因为它有着更大的野心:取代现实。讽刺一般,玩家们宣称的“如临其境”比照片的观看者更为失真,至少照片的观看者凝视着的是风景的复制品,但赛博空间的游戏者们感官舌头所舔到的不过是赤裸裸的“媒介”(medium),媒介作为代码系统的手足操控着一切,定义着所有的意义(3),人和世界的接触由此被悬置, 被架空;但人们却毫不担心,因为拥有了代码所给他们带来的“真实感”,他们似乎并不在乎本真的失去。
观察图1中的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和维琪奥桥,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拟真风景塞壬般的迷人之处:建筑物不仅是外部轮廓和特征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而且所有的细节都得到了极致的对待:每一个窗户、窗户的位置、装饰性雕花在游戏中都得以呈现。
假如说错觉是以一种隐蔽性的在场诱惑观者的话,那么拟真就是其完全的对立面:它通过细节来解构真实,通过代码的收编将所有分解出来的细节进行拼凑、重组,使模型本身成为了具有最终意义的符号。那么为何玩家会如此相信其中的虚拟感觉呢?那是因为游戏本身,或者游戏制作团队本身所拥有的话语权力:通过一个类似造物主的形象,游戏制作团队创造、命名了一切,他们的话语具有形而上的威力,而身在通过他们的话语所产生的空间之中,玩家别无选择:我说这里是佛罗伦萨,就是佛罗伦萨。这种媒介的“霸权”并不是拟真时代的独特产物,早在本雅明笔下的“机械时代”,媒介对人的操控早现倪端:镜头引导和制片人的剪切。观众在屏幕上(无论是电影或是电视)所看到的,无一不是镜头所“让”观众看到的(made them see),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失去了选择权,只能被动地接受镜头的引导;另一方面,演员和观众的互动联系被切断,如同观众面对屏幕,演员们只能面对闪着红光的圆形镜头,他们无法控制自己在作品中的呈现,一切都取决于制
片人的剪辑。他们原本自然的表演行为被剪切得支离破碎,又被重新组合起来,仿佛诉说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感到陌生的诧异语言。连叙事的顺序也可以被打乱,不同于戏剧必须按照剧本从头到尾开始表演,电影或者电视的叙事完全按照现实的经济或者演员的档期进行。故事的结尾可以一早就拍好,跑龙套的演员贯穿整部戏的零散镜头可以在一天内就全部完成拍摄,并离开剧组,但观众却认为这位不知名的演员由始至终一直“在场”。同样,在“刺客信条”这个赛博空间中,玩家实质上并非操控者(虽然他们手握着鼠标);相反,他们不过是被逼对于这个拟真游戏所做出反应的一个机体(organic),一个零部件——虚拟最终的完成需要他们的同谋。
更为讽刺的是,游戏中所呈现的虚拟风景和原场景的相似程度其实并没有玩家认为的那么重要,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种拟真性的体验,而这种体验的成立(上文已经说过)最为关键的是某个形而上的话语。真实的城市所给人带来的感受是源发性的,它从每一栋建筑、每一条街道、湖边的翠柳、林间小路的鸟鸣、公交车站的颜色、店铺的排列所生发出来,仿佛普罗提诺所说的光的“流溢”——本真的光韵从自身流淌出来,对置于其场域的人进行熏陶;但拟真的城市却是一种既定的冷冰冰的话语,它首先告诉(或者宣布):这里是巴黎;或你现在身在12世纪的大马士革……这个话语有着决定性的催眠作用,一旦玩家听到这个命令式的话语,他们就如同机械人一样听从了话语的内容。当他们带着既定性的目光去看待某处风景时,它们的真实与否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结论早就定好了,问题被问出来,但不需要回答,或者说,问题已经全面吞噬了答案。而且,3D游戏本来就是一个矛盾:3D意味着三维立体,但它却只能呈现在一个平面——屏幕之上,玩家所
体验的立体感,不过是代码在一个封闭空间中无限自我繁殖的效果。拟真的话语以单一的逻辑性(1和0)削平了本真固有的深度和精神,游戏里面的风景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他们进行取景,然后复制,将复制品转为条形码,下指令让程序运行,三维的建筑被高度还原在二维的屏幕之中,游戏开始了。
二、拟真风景的错位和拼凑
世界已经毁掉了自身。它解构了它所有的一切,剩下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人们所能做的只是玩弄这些碎片。玩弄碎片,这就是后现代。
——鲍德里亚
去中心化、非连续性、消融、解构、延异、拼凑……这些都是后现代屡见不鲜的标签,其中,20世纪60年代所兴起的解构主义,剪切出了后现代最鲜明的离散特色,然而,即便是解构主义的“去中心化”,它也是以“中心”为基地的——假如中心从未在场,解构也就没有了对象,那岂不是唐吉可德般对着风车胡乱地舞剑?解构主义的“否定式”也是有对象的否定;然而到了数码时代,代码才实现了真正的否定,因为本真——中心完全被吞噬:“符号的光韵和意义本身被最终消解:一切都变成了收编和解码。”(4)它甚至不再气势汹汹地提什么“中心”、“边缘”,因为再也没有这样的差异和界限,一切都是代码的等价物,如同一切商品都可以换算为纸币的等价物一样。拟真是通过彻底粉碎一切来达到目的的,它粉碎的东西包括黑格尔的逻辑、康德的道德、索绪尔的能指所指、马克思的资本,自然还有人本身的定义。一直的文学传统,人都是由对立的二元——身体、灵魂组成的,我这里所指的灵魂,并非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灵魂或者理念,而是人作为人,就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可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的人的本质,或者精神面貌。然而,代码推倒了一切的对立和差异,抹杀了能指——所指间的距离。所有的历史逻辑都被连根拔起,所有的等级界限都被抹平——当代码收编了一切,将它们都变成数字以后,它就可以肆意地调用库中的存货,肆意地进行复制——这就带来了鲍德里亚所说的“过剩”:只要我需要,都可以为我所用。
在这类操控的体系中,最后所产生的结果就是错位和拼凑,定义失去了意义。现代艺术这种拼凑和错位最为明显:如朋克文化的海报、衣饰,就是这样一种拼凑文化;拼凑的不仅仅是外形,还是性别。朋克女孩往往喜欢穿着雄性气味强烈的皮衣、柳丁;而男性却涂着口红,画着浓妆,似乎非常享受这种阴阳兼有的气质。异装癖和性倒错不仅是单纯的生理或者心理上的示威,还是一种惧怕被定义,惧怕被固定而发生的逃逸现象。但逃逸的欲望却最终破灭:为了逃逸,主体选择了碎片的游戏,以破碎的拼凑来拒绝外界的定义,最终却落入了代码的圈套——变得毫无差异。这同样发生在实验音乐领域,德国前卫电子乐队kraftwerk就以模拟机器人,毫无感情的音乐输出而著名,他们的专辑《computer love》中不断重复、冷酷的节奏仿佛就是一个音符化的机器人,当然还有更早的约翰·凯奇(John Cage)的“偶发音乐”(4分33秒)和勋伯格“十二音技法”,但这些由偶发的,单纯的不断自我复制的音符组成的音乐,在扫荡了观众的听觉和好奇之后,似乎再也没有剩下什么。但他们的音乐风格却注定是容易复制的、低门槛的,似乎任何一个称为实验音乐家的人坐在一部钢琴,或者一台电脑前,随意用手指敲击出来的,都可以称为一种“无序音乐”,他们试图逃逸被定义的结局,最后都成为了一模一样作品的牺牲品。阿多诺曾经批判过以爵士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pop music),因为所有的流行音乐不过是片段的不断重复、循环,用复制式的、变化甚少的唱段来填满大众的耳朵;但反观今天,爵士乐似乎已经比现代电台和MTV的音乐好得多了,起码其中的“即兴”段是带着艺术家创作精神的。假如阿多诺听到如今的实验电子音乐不断的“loop”重复,他必然不会将这个称为“实验”(experimental),而是死板、拷贝和恶性繁殖。这也和尼采在《敌基督》里面说的不谋而合:除了耶稣,后面的都是伪基督徒,福音书也不属于基督,基督教的意义在耶稣赴死的瞬间已经完成了;同样,实验音乐的意义也在它被第一位作者创造出来的时候完成了,后来的都是伪作,是装模作样的表演,是害怕世俗意义上“庸俗”落到自己头上所表现出来的造作。
回到“刺客信条”游戏的本身,从它的游戏剧情设定,到游戏中的场景,统统都带着拼凑和时代错位的痕迹。主角Miles是通过高端的科技仪器——虚拟机Animus(5)回到了古代,置身于中世纪的场景之中。现代和中世纪、高科技和古风相互交错,尤其是主角的衣服,虽然身披盔甲、手拿宝剑,但无论是纹饰和腰封都显得太现代了,所以当他处在古佛罗伦萨,或者大马士革的城市风景中时,就显得尤其突兀。时代错位在蒸汽朋克为主题的电影、动漫中尤为突出(图2)。
这些作品往往设定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但其中的场景却充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机械和交通工具:巨大的螺旋桨、复杂的齿轮体系、活塞、有着现代机械元素的热气球;而且故事的情节往往是魔幻和科学、原始和先进共存。宫崎骏的作品《哈尔的移动城堡》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点:哈尔是位魔法师,他可以随意变形,但他的城堡却是一堆机械零件凑成的住所,而且还有机械腿可以行走,使得拼凑成为可能。正是由资本支撑着的编码系统:历史上一切的元素都被纳入了代码结构当中,然后被任意植入虚拟世界。但时代错位造成的突兀感,却似乎丝毫没有影响观者或者玩家的拟真体验,这就表明了虚拟的结果——最终指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虚拟,亦即是媒介的本身,是媒介认识到自己“作为”媒介的意识(awareness)。
三、拟真风景的预定性和诱惑的丧失
鲍德里亚在建筑美学论述中,提到了拟真时代建筑中错觉和诱惑的丧失,他对“过剩”的代码有着相当的反对态度,认为虚拟是真实的大敌:
将现实置于视角中是一种哲学的直
觉,因为没有任何“否定主义”的味道。置于虚拟,在对现实的技术性清除举动中,它才是真正的否定主义。(6)
虚拟,意味着对人类、建筑、城市风景、甚至感官体验的克隆;虚拟需要代码的收编和自我繁殖,由此造成了“过剩”,这种趋势来势汹汹,乃是因为:
在无尽的复制中,代码系统终结了本真的神话,以及它在运行过程中获得神秘性的指涉价值。通过终结本真的神话,它也终结了内在的矛盾对立(再也没有一个真实或者真实的指涉物来对抗它了)。(7)
既然本真失去了意义,那么,在城市美学的角度而言,亦即是建筑失去了意义,再也没有什么“建筑”了。现代城市中的“过剩”表现为人造空间,人造文化的过剩。实物的消费完全堕落为符号的消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城市中出现的所谓打着“欧洲风情小镇”或者“禅意居所”等广告的楼盘。这些商业楼盘,一方面用拟真(非临摹)的手段搬来了欧洲或者中国各种元素:前者多是尖顶屋子,庭院式别墅、门廊;后者则是在公共区域平铺上大片的水域,抹去一般的绿化树木,取而代之的则是几块孤零零的石头,并对业主宣称这是来自日本“枯山水”(图3)的造园方式,连各式的石头都纷纷被取上了“洗净尘土”、“冥想”等富有禅意的名称。在这个虚拟的乌托邦中,繁忙的城市人是否能体验到所谓的东方禅意呢?这类型建筑,在鲍德里亚看来,就是为了吸引“凝视”,为了戏剧性炫耀的建筑,而非真正的“无意识的本源性”而造的建筑。
“为了让人刻意凝视”,“并非为了人自身的建筑”,没有比这些更能来形容“刺客信条”中的虚拟城市建筑了,它们的存在,完完全全就是为了玩家视觉上的欢愉,而这种欢愉和原建筑关系甚少:玩家进入赛博空间,看到了周围的建筑,感觉到自己身处某个“异域”,仅此而已。即使不是佛罗伦萨,不是巴黎,不是波士顿,场景置换成沙漠、外太空、深海,对于玩家本身都是毫无影响的;他们一旦疯狂地在赛博空间中进行游戏,所有的建筑和风光,不过就是一幅幅二维背景罢了;所谓的城市体验不过是自欺欺人。
赛博空间中虽然对城市建筑有着高度的还原,而且玩家还能进入建筑内部,观看建筑的细节,但它和真正的城市建筑有着根本性区别的原因在于顺序,具体而言,是叙述的顺序。任何建筑/风景,其意义并不是一开始就拟定的,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并没有一个什么形而上的话语先制定了某处建筑,或者某处风景“应该”给人带来的体验,而是人通过接触了建筑,走进由其构成的空间而有的感受:文艺复兴诗人彼得拉克身处罗马废墟,看到了时间的流逝,人和词语在其中不断死亡;但帝国的光辉却永远存在。或者像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说的那样:工具的存在,是由于人对它的“上手”,而不是早已有一个“工具”的概念存在;同样,也不是先有一个“建筑”的概念存在等待着人去填充,相反,是由于人的聚集,居住,文化活动使得围绕他们,遮蔽他们的场景成为了我们称之为“建筑”的东西。
拟真话语的本末倒置,它的结局预
设实际上是消解了结局:
结局不再是在最后,也再也没有什么结局,或者定局。结局在伊始就被订好,收编在代码之中。(8)
结局一旦被预先定下,也就再无悬念,没有悬念就是失去了诱惑,仿佛是侦探小说一开始就告诉读者,谁是凶手。诱惑,就如同女人裙子的长度,不能过长,但过短了就是过度透明的展示,低俗的卖弄风情,和诱惑相差甚远。中国古代的画轴中,往往用一架屏风,女性显露的一处衣角,就完成了诱惑;而如今的建筑满是高墙,广告女郎铺天盖地,真的大为逊色。诱惑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叙述方式:它必须同时将对象置于真实/幻觉两种话语当中,而完成它同时在场/缺席的游戏:
诱惑不是简单的呈现,也不是纯粹的缺席,而是一种隐蔽的在场。它的唯一的策略就是同时出现/缺席,从而生成一种忽隐忽现的闪烁……在这里,缺席诱惑出现……(9)
“刺客信条”给观者呈现的建筑是一种仿真度极高的风景,但正是由于过度的相似,反而没有了诱惑;而且,由于预先定下的结局(例如已经设定了场所的位置:意大利、法国、美国),剩余的只有玩家的好奇心了,但这种好奇心并不代表美学体验;正如游戏中美轮美奂的场景不能体现真正的建筑之美一样。
鲍德里亚的建筑美学和城市美学显然是一种带有复古情怀的精英主义,在如今人口膨胀,城市迅速发展,人类生存空间越发狭窄的现实,他所提倡的诗性建筑其实并不容易实现,甚至不容易为城市真正居住的人们所理解。他和阿多诺一道,对于技术所带来的膨胀甚为警惕;但我们不能忘记本雅明在其中的乐观:技术同时将艺术带到了民众之间,打破了贵族对于艺术的垄断。赛博空间中所呈现的建筑或整个庞大的城市,本质上是代码,但无可否认的是,它也给观者带来了愉悦的感官体验,使得大众对于古代城市构造有了更多的认识,这种虚拟体验只有技术才能带给我们——我们没有时空机,是技术填补了时间流逝的遗憾。
注释:
(1)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The Body, In Theory: Histories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trans. By Sheila Faria Glas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P1.
(2)万书元在《鲍德里亚:建筑美学关键词》一文中是这样阐述“拟真”的:“虚拟现实却完全是另一种东西,它是建立在数字技术基础上的仿真。它一方面比错觉显得更真实更细腻,一方面更虚假更具有欺骗性。在建筑中,虚拟现实往往意味着虚假的美学许诺。一个屏幕里的美轮美奂的虚拟建筑,往往就是一个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参见《现代哲学》2013年第2期第37页)“刺客空间”中华美的欧洲古风建筑,难道不就是一个对玩家的空洞的美学许诺吗?玩家在其中似乎掌控游戏,掌控世界,身怀绝技,但不过是个乌托邦一样虚无的“愿望”。
(3)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和死亡》一书中写道:It is in fact the medium, the very code of editing, cutting, questioning, enticement and demand by the medium that rules the process of signification.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 By Iain Hamilton Gran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ike Gane, Sage Publication, 1993,P60.
(4)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he whole aura of the sign and signification itself is determinatedly resolved: everything is resolved into inscription and decoding”,P58.中文为笔者拙译。
(5)令人感到讽刺的是Animus的词源来自于拉丁语的“灵魂”,但“灵魂”却变成了一台高科技的机器,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技术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刺穿”(penetrate)。
(6)转引自万书元《鲍德里亚:建筑美学关键词》,原出处是鲍德里亚:《冷记忆5》,张新木、姜海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7)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In its infinite reproduction, the system puts an end to the myth of its origin and to all the referential values it has itself secreted in the course of its process. By putting an end to the myth of its origin, it puts an end to its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there is no longer a real or a referential to which to oppose them),P60.
(8)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Finality is no longer at the end, there is no more finality, nor any determinacy. Finality is there in advance, inscribed in the code”,P58.
(9)转引自万书元《鲍德里亚:建筑美学关键词》,原出处是Seduction.Trans. Singer, Brain. Montreal:New World Perspectives & Ctheory Books, 2001,P85.
[1]Jean 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The Body, In Theory: Histories of Cultural Materialism[M]. trans,Sheila Faria Glaser.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2]Jean Baudrillard.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M].trans,Iain Hamilton Grant. London:Sage Publication, 1993.
[3]Jean Baudrillard.Seduction[M]. trans,Singer Brain. Montreal:New World Perspectives & Ctheory Books, 2001.
[4]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and Other Writings on Media[M]. Boston: Belknap Press, 2008.
[5]Theodor W.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M. Bernstein[M]. New York:Routledge, 2001.
[6]万书元.鲍德里亚:建筑美学关键词[J].现代哲学,2013(2).
[7]万书元.时尚与建筑——兼论鲍德里亚的时尚理论[J].艺术百家,2012(6).
[8]万书元.新媒体艺术论[J].艺术百家, 2009(1).
[9]胡健.“玩弄碎片,这就是后现代”——略论后现代状况的审美特征[J].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10]吴娟.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城市文化观[J].改革与开放,2014(6).
[11]张劲松.拟真时代:鲍德里亚媒介理论的后现代视角[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J01
B
钟碧莉,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