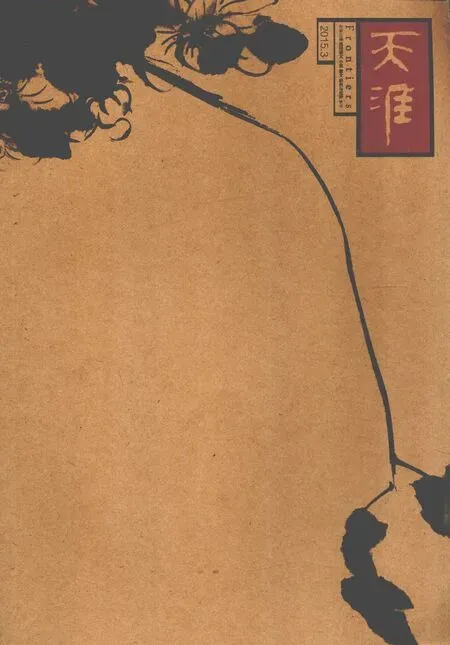写作的女人危险
2015-12-06那海
那海
写作的女人危险
那海
文字是探险的工具
不可避免,女性写作,总会自然地带有一些女性特征,如女性特有的感觉、身体、空间、意识等,凭借天生细腻的观察力,将周围生活的微小线索累积起来。女性写作的生存与发展,既取决于对女性审美视角的深度开掘,也取决于对女性单一性别的不断超越。但是,写作的女人也往往被过度叙述,同时,也被审美价值赋予各种更为苛责的要求。
就写作的女人而言,长相普通的世界推理小说三大宗师之一的阿加莎·克里斯蒂被人们称为“阿婆”,乔治·艾略特被称为“姑妈”已经是很客气的表述了。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当玛格丽特·杜拉斯年老,“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个男人走了过来,他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容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情人》)此时,人们早就原谅了她中年后因嗜酒而扭曲残损的脸。如果可以,人们很愿意停留在《情人》中那个湄公河的轮渡上,静静地打量着那个十五岁半的女孩:“茶褐色真丝裙衫、戴着一顶男式呢帽、梳着两条印第安人的长辫子,伫立在泥泞的河水的闪光之中,在渡船的甲板上孤零零一个人,臂肘支在船舷上……”
容貌对写作的女人而言,并非绝对重要。《简·爱》中的简身材矮小,相貌平平,分明就是夏洛蒂·勃朗特。而才华与美貌的结合,自古难全。写作的女子中,非得有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令人痴迷的美貌,才引得法国总理拉法兰根据她作品的题目《一种微笑》,在她的悼词中称:
“弗朗索瓦兹·萨冈是一种微笑,忧郁的微笑,像谜一样的微笑,一种排遣的微笑,但也是快乐的微笑。”
如果这样的“微笑”放在《写在身体上》的当代作家珍妮特·温特森身上,确实是一个尴尬的话题。但这一点也不妨碍珍妮特·温特森成为当代最好也是最有争议性的作家之一。她时常一袭黑衣黑裤,镶金的鞋尖略显朋克气味,神情冷峻。“我不是一个喜欢写作的同性恋,而是一个恰巧喜欢女人的作家。”温特森十六岁就爱上一个女孩,并为之离家出走。她在颇具自传色彩的小说《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中记下一件童年往事:
“有一次,我去买黑豌豆,快要回家
时,有个老太婆突然抓住我的手。我还以为她要咬我呢。她看了看我的掌纹,笑了几声。‘你永远不会结婚,’她说,‘你不会,而且你将漂泊一生。’”
至少到现在,这个预言还在生效。
确实,对于写作的女人,人们总是期待她的文字越是沉静,她本人越是摇曳生姿,旖旎美妙,让人无法抗拒。或者,深邃的思想,抑或温婉典雅、真情率性的文字的背后,浮现的都是类似萨福或者年轻时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的面容,非同寻常的爱恨情仇,不同常人的生活方式,甚至流浪漂泊,也应该是如何的完美。
因为年代久远,人们对古希腊的女诗人萨福可谓知之甚少。但是,人们理所当然认为,萨福有着慑人之美。最为靠谱的证据就是萨福自己的诗句:“周围的群星黯淡无光/而她的光华,铺满了咸的海洋和开着繁花的田野。”而且,既然留存世间的萨福的诗歌,大多以人的爱和欲望为主题,诗风优雅精致,性感香艳,那么,相传她五十五岁时为了一位英俊的青年男子殉情,跳海自杀,似乎也是人们为这位“抒情女诗人”设置的最好的归宿。
应该说,诗性的灵魂总会在人类心灵的深处绽放它自性的色彩,总有那么一种异样的美,在苍茫大地,散发出阵阵玫瑰的芬芳。当写作的女人记录自己满怀的深情、纵情的岁月、悲情的抉择之时,在我们心甘情愿的想象中,她的文字的魅惑,早已通过我们的感知,取代了她所有表象的东西,在文学史上留下一抹温柔绚丽的光亮。
事实上,大多才情四溢的女作家,长相普通平常,阿加莎·克里斯蒂、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多丽丝·莱辛、夏洛蒂·勃朗特、勃朗宁夫人……这样的名单后面还跟着很多。如果说,女性的文学写作实质上是突破沉默的言说和对个体自我的确认,意味着向男权中心地位的挑战,那么,她们通过写作来试图了解自己的做法,不单单是为了寻找个性,也是拒绝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自我毁灭的一部分。这些觉悟的女子,她们的文字无可避免地成了探险的工具。而她们,无论是拥有天生的美貌,还是长相庸常,如果她们的才情足以征服读者,都无不例外地散发着致命诱惑。这种气息与生俱来,且与自己的作品一起发酵、沉郁,让人无法抵挡。
杨比玛格丽特·杜拉斯年轻近四十岁。当时,杜拉斯已经六十六岁了,杨二十七岁,是一个刚从哲学系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住在冈城。他称自己被杜拉斯的作品深深吸引:“初次相遇就是《塔吉尼亚的小马群》。第一次读,第一次喜欢。后来,我抛开了一切,抛开了所有别的书,只读她的作品。我是一个真正的读者,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每一本书。”之后,他抛开一切,来到她的生活中。这是她一生最后的情人。
生于1889年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在她五十六岁那年,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以塞亚·伯林仍为之倾倒。他比她小二十岁,他第一次见到她,两人一夜倾谈,伯林早晨回到住处,辗转反侧,翻来覆去只有这句话:“我爱上了,我爱上了。”阿赫玛托娃则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可听见/我怎样把活着的你呼唤。/我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关上你虚掩的门板。”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第二任丈夫伦纳德与其说是欣赏她的美丽,不如说是被她的文字深深吸引,从而仰慕她的超凡智慧。他曾给伍尔夫写了一封情书,堪称情书中的经典之作:“我自私,嫉妒,残酷,好色,爱说谎而且或许更为糟糕。因此,我曾告诫自己永远不要结婚。这主要是因为,我想,我觉得和一个不如我的女人在一起……正因为你不是那种女性,就把这种危险无限地减少了。”
但是,伍尔夫的心理疾病落下的性恐惧和性冷淡,使伦纳德极为困扰。他们结婚第二年,伍尔夫因旧病复发,精神分裂,吞服安眠药企图自杀。伦纳德从此认命,他眼里,伍尔夫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智慧的童贞女”,他被她的智慧所吸引,迷恋她表述的文字。这桩基本无性的婚姻,继续了二十九年,他自此追求精神之爱——“她是个天才”,他给她足够的敬仰与照顾,就够了。
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终其一生都不曾见过里尔克。这是段因文字而吸引,因文字而生情的爱情。1926年春天,三十四岁的茨维塔耶娃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推荐和介绍,与诗人里尔克取得通信联系,距离里尔克身患白血病辞世,仅剩七个月时间。他们以热情的文字,无羁的情感与纯净的热望,妙不可言的诗性与爱情串起诗歌及精神生活的文本。里尔克被茨维塔耶娃的文字深深吸引,他致信茨维塔耶娃:
“我所有的话语都骤然向你涌去,每个词都不愿落在后面。”……
“哦,我如果能像你阅读我那样地阅读你,该多好啊!”
而茨维塔耶娃的炽热与大胆,袒露的激情,更是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火一般的恋情,也只停留在纸片上的亲吻和拥抱。茨维塔耶娃在致里尔克的信中说:“我不活在自己的唇上,吻了我的人将失去我。”并且她说明自己追求的是“无手之抚,无唇之吻”,只是,“请你别生气,今夜,我想和你睡在一起。”不过,“就是单纯地睡觉,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正如茨维塔耶娃所说的,这段爱情只活在言语中。当她的文字深深吸引里尔克的同时,她也被里尔克的文字所吸引。这是一种相同的气息,让她无力自拔。
在得知里尔克死讯后,茨维塔耶娃仍满怀深情地,写下最后一封情书:
“亲爱的,爱我吧,比所有人更强烈地,与所有人更不同地爱我吧。别生我的气,你应当习惯我,习惯这样的女人。”
写作的女人与向死而生
1836年,夏洛蒂·勃朗特二十岁,她壮着胆子把自己的几首短诗寄给当时的桂冠诗人骚塞请他指教。然而,得到的却是这位大诗人的一顿训斥。骚塞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对她说:“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
这是封有名的回信。事实上,只要打开生于1661年的温澈西夫人的诗集,就会看出这是一个普遍的答案,我们也能看到温澈西夫人对写作的女人地位的忿忿不平:
唉,一个尝试写作的女人,
被人认为是这么狂妄的东西,
以致再没有美德能赎回这个过错。
他们说我们错认了性别和为人之道;
礼貌、时髦、跳舞、衣着、游玩,
才是我们应学的才艺;
写作、看书、思想、发问,
会遮蔽我们的美貌,糜费我们的时间,
而且阻挡我们青春时代的获得,
至于卑贱的家务管理,
有人认为是我们最高的艺术和用途。
在传统美学和男性文化的双重权力中心支配下,无论如何有才华,身为女性,就必须要奉献和牺牲。连大文豪巴尔扎克都认为:
“女人的命运和她唯一的荣耀是赢得男人的心……她是一份动产,确切地说,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写作的女人的艰难可想而知。女性必须照顾家庭、孩子,且举一生之力支持男性,适当时候还要为男性鼓掌,似乎只有这样,才是女性活着的所有价值。而且,一旦她开始写作,就注定既要背负沉重的历史与社会责任,同时也必须承担着她的家庭责任。“如果说女人是世俗的、平庸的,基本上是功利主义的,那是因为她被迫把自己的生存奉献给做饭和洗尿布,她无法取得一种崇高感!”——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此也早有论述。
很少有女人能在完满的婚姻生活中将欲望化为叙事,并呈现其思想的深度与力度。弗吉尼亚·伍尔夫是个例外。用她日记中的一段文字:“要是我嫁给利顿,我肯定写不出任何书。不久前晚餐时我作如是思想,他限制和约束人的方式怪异。伦纳德可能更严厉,但他善于激励人,与他在一起,存在着各种可能性。利顿是温和消沉的,就像一片秋天的湿树叶,孤零零的已过壮年。”世上有几个伦纳德,能给弗吉尼亚·伍尔夫们以“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大多情况下,婚姻中的女人,如西方思想家舍勒所说,婚姻不可避免地会妨碍她们的精神“从周遭结构的铁钳中挣脱出来,成为投向世界大全本身的自由目光”。
阿娜伊斯·宁必须在两桩婚姻中寻找自己文字与激情的出口;西蒙·波伏娃与存在主义鼻祖萨特终身相依,却未走向婚姻,两人签订协议,其中约法三章:云游四海,多配偶制,一切透明。这份契约当时为期两年,遵守则合,违约则离,却履行了一辈子。与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的苏珊·桑塔格,十七岁时,遇到了二十八岁的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十天后,两人闪电结婚。二十六岁,她离婚,携带了“七十美元、两只皮箱、七岁儿子”来到纽约,再也没有步入婚姻。我们不能不说,完美的婚姻与写作的女人始终是矛盾的存在体。稳定的婚姻生活往往会削弱女性思想与表达的欲望,钝化女性的复杂感受。完满的婚姻也是女人安身立命的温床,但其中稳妥的生活方式以及伦理标准,则让女人失去了对思想内核的探寻。
然而,这些写作的女子,一方面,文学和艺术更让她们接近精神的内核;而另一面,琐碎的日常生活与忙碌地操持家务,让她们无法找到自己创作的欲望与生活中多种矛盾的平衡。于是,终其一生,她们向往婚姻生活带来的世俗的圆满,但她们往往没有了婚姻。
这些文学艺术领域的杰出女性,都因自己的超凡才能而付出巨大代价,此后,她们也大多面临共同的生存困境:精神折磨、贫困、对抗常规、受教育权被剥夺、为世人指责或唾弃、早逝、疾病、吸毒、酗酒或被送入疯人院。
1995年9月,孤独终老的七十五岁的张爱玲被人在洛杉矶西木区的公寓里发现已经离世,时值中秋,死时身边竟无一人。她身穿一件磨破衣领的赫红色旗袍蜷在地板上,这是她最后的姿势。比起勃朗特三姐妹,张爱玲总算长寿。勃朗特三姐妹中,最长寿的夏洛蒂三十九岁去世,这年她刚刚出嫁,生病去世时还怀有身孕;单身的艾米莉仅活到三十岁,小妹安妮去世时也仅二十九岁。
萧红以一部《呼兰河传》立世,可惜她三十一岁因病去世,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命。有着“明治紫式部”之称的女作家口一叶,留下令人萦怀难忘的文学芳香,死时年仅二十四岁。世称与莎士比亚齐名的简·奥斯汀去世时才四十一岁。《心是孤独的猎手》的作者卡森·麦卡勒斯则五十岁去世,她十五岁时患风湿热,勤勉的写作加速毁掉了她的
健康,之后,她经历了三次中风,二十九岁时瘫痪,一生备受病痛折磨和家庭暴力的困扰。
艾米莉·勃朗特倘能活到更长时间,她或许会给世人更多的惊喜。我无法否定我读《呼啸山庄》的震撼,当她以寥寥几笔点明一张脸后面的精神世界,并将她自己繁盛强大的生命关注以及对人性的思索灌注到作品之中,这是一种发自女性内在的创作的力量,让人充满敬意。可惜她只活了短短的三十岁,没有结婚,没有子嗣,除了工作以维持父亲这个穷困的家庭,还要承担全家繁重的家务劳动,洗衣服、烧菜、烤面包,晚上的一点余暇写作的时间,是对一天枯燥乏味的辛劳工作的一种解脱。试想,如果她有如同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经济独立,生活上不受干扰,会不会更有利于她创作,去写她想写的东西,抑或,她会长寿些?但是,如果她拥有这样的生活,她还能写出《呼啸山庄》吗?
在简·奥斯汀时代生活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体面的婚姻,差不多就是没有社会话语权的女性,藉以掌控人生的唯一出路。当简·奥斯汀把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琐碎的家事,小心翼翼地不让别人知道她在写小说,我们可想而知她内心的悲苦。“她躲在屋里写小说时,只要有人一推门,她就把稿子迅速藏起来”,“为了不让人发现,她使用很小的纸片,因为小纸片容易收藏,或者可以临时用一张吸墨纸盖住”。她的另一个哥哥亨利则在回忆录里写道:“要是她还在世,不管会给她带来多大的名声,她也不会把自己的名字署在作品上。”正因为这样,她发表第一部作品《理智与情感》时,扉页上仅署名为“一位女士”。这个女人,她一生都和姐姐卡珊德拉共用一间卧室,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尽管她写作,但是,她往往没有自己。
1941年3月28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五十九岁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自己衣服的口袋里装满了石头,投水自尽。
在此之前,她已有两次自杀的经验。她不爱旅行,不爱社交,也不热衷于恋爱,“参加宴会能把裙子穿反,烤面包能把戒指丢进去一起烤了”。穷其一生,她都在与自己的幻觉斗争,写作加剧了她疯癫和幻听等精神分裂的症状。当精神分裂的疯狂来袭,死亡无疑成了一种解脱。
茨维塔耶娃写死亡的诗并非如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在歌颂死亡,沉迷于死亡之美。她的死亡诗带有一种历史感,是对自己未来的一种信念。她坚定地相信,百年过后,她虽死犹生。“经历了整整的一百年啊,/我才最终迎来了你!”(《致一百年以后的你》)
1941年8月,茨维塔耶娃经历了一生最不堪承受的精神和物质双重的危机。她期望在即将开设的作协食堂谋求一份洗碗工的工作,但是,这一申请遭到了作协领导的拒绝。8月31日,绝望中的她自缢身亡。或许,只能用她自己的这一行诗作解释: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
1963年情人节的前夕,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平静地为孩子们做好早餐,在自己两个幼儿的小床里放上面包和牛奶,然后,封住了自己的门,开了煤气自杀。在她已经过艰难的四次自杀后,这次自杀终于成功。如她所说,“死亡,是一种艺术,我令它更加精彩”。
为何这些才情四溢的女子会迷恋死亡,就如同迷恋写作?当她们向死而生,写作串起了生存与死亡的纽带。正如西尔维娅·普拉斯所说,“写作是一种宗教行为”。选择了写作,也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信仰。这当中,必须忍受被排斥和抛弃的命运,忍受孤独、骄傲的心的不被理解,以及忍受纷至沓来的妒忌与质疑。当她们无法释放内心的情绪,写
作往往会加剧毁灭,而这种直抵内心的毁灭,却也成就了她们中的许多人在文学史上的璀璨地位。
艰辛而百感交集的旅程
大凡写作的女人,总是将写作的起点建立在对传统经典文本的解构与重建上,关注女性的内心与生存状态。这些女子,无法屈从生活,只有毁灭。而另一些女子,她们无法湮没在尘埃之中,于是就扎根大地,在艰辛中顽强绽放。安娜·阿赫玛托娃就是后者。
阿赫玛托娃经历了三段失败的婚姻,她的一生与许多人有过亲密关系,她非贤妻,也非慈母。1910年,阿赫玛托娃与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相识六年后结婚,对方曾为了娶她而四次自杀未遂。婚后彼此都发现,两个诗人的结合却是荒谬的。1918年12月,离婚后的阿赫玛托娃嫁给考古学教授希列伊科,很快发现,这是一个“悲惨的误会”,希列伊科需要的是一个妻子,而不是诗人。阿赫玛托娃与第三任丈夫艺术史家普宁,是一段长达十三年的“不忠”之恋。两人结婚时,普宁并未离婚。阿赫玛托娃则与他签订了一份婚约:“我同意尼·尼·普宁与别的女人生孩子。”这是一段畸形的感情,普宁风流成性,阿赫玛托娃的激情更为奔放,不时会有或精神或肉体的红杏出墙。直到1938年,她还未离开普宁,这样的生活碾碎了她的精神。这时候的阿赫玛托娃像个普通而认命的女人:“这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传说。有谁能拒绝自己的生活呢?”
事实上,早在1921年,阿赫玛托娃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因“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被处决,1924年,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被禁,她就步入艰辛的人生之路。此后,她经历了贫困、监狱和战争的磨难。她唯一的儿子因不承认父亲的罪行三次被捕入狱,一生中有二十多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作为一个母亲,阿赫玛托娃把她的这段不平常的血泪史记载成长诗《安魂曲》。这是一首由十四节小诗组成的抒情长诗,在未曾平反的岁月悼念那些在1930年代肃反扩大化中冤屈而死的所有无辜者。苦难让她把目光投向了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共同灾难,诗作中强烈的人文精神,也让阿赫玛托娃登上诗歌创作的巅峰。
我们发现,阿赫玛托娃的一生,旖旎的诗情始终追逐着她苦难的生活,同时也让她打开了被诗评家称为“一颗与其说是极其柔软,倒不如说是刚强的,与其说是爱流泪,倒不如说是残酷的抒情的心灵”。她早年以撷取生活的戏剧性细节表现恋爱中人物的心理活动而见长,在走过了偃蹇多舛的生活道路之后,诗风变得开阔而苍凉。无论是斯大林授意苏联作家协会称其“不完全是修女,不完全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与修女”,还是她的第三任丈夫普宁称其“如此完美和纯洁的天使竟会与如此肮脏和罪恶的肉体合为一体”,当她选择书写,她就多了一份争议,也多了严肃内心无法清算的与世界沟通以及表达的力量:
上帝!你看哪,我已倦于复活,
甚至也倦于死亡、倦于生活。
拿走一切吧,但要留下这朵红玫瑰,
让我再一次感受到它的鲜艳。
——(阿赫玛托娃《最后的玫瑰》)
多少年了,这朵静静的涅瓦河边绽放的红玫瑰,依然光彩夺目。或许是最苦难的生活,最无望的爱情,造就了有着“俄罗斯诗歌月亮”之称的阿赫玛托娃,而女性自身的坚韧与期待,在她的作品中熠熠生辉。无可否认,上苍赋予阿赫玛托娃非凡的诗情之时,又命她必须支付沉痛代价。而她情感路径的放浪、肆意、率性,命运的多难,始终与其高贵、
柔情、苍凉的诗风,并驾齐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誉为“文学洛神”的萧红,一生坎坷。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而“最大的痛苦和不幸,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在上海,她还搬过七八次家。在情感上,她一生都在不断找寻和被遗弃。她爱过萧军,最后被萧军所弃。与端木蕻良生活在一起,病逝时,却是一人孤苦伶仃。但是,在苦难的生活中,萧红以柔弱多病之躯,创作了一批风格独特的文学作品。极端苦难,总带着极端体验,随之而来的,就是缪斯女神的青睐。
写作的女人,她们作品中的语言或苍翠欲滴,或华美饱满,抑或清冷孤寂,简洁从容,她们的生活却通常支离破碎。她们内心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对不可能实现的至善与自由的向往,而她们自己,终其一生,也都在这种向往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中挣扎。
这些女子,当她们写作,注定拥有的是——艰辛而百感交集的旅程。
那海,作家,现居浙江台州市。主要著作有散文集《有限的完美》《写作的女人危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