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河的诗
2015-1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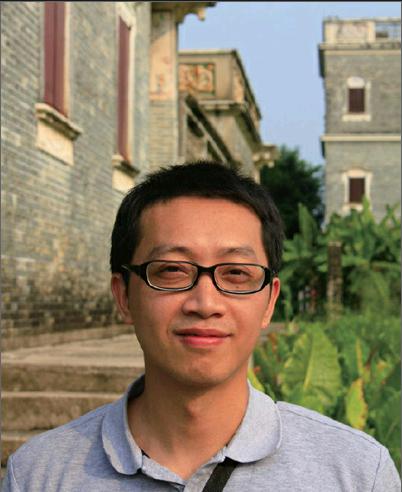
扫墓路上
夜雨后的早晨,
我们合家去扫墓。
走过欢腾的小河,
来到那个山脚的树林。
春天到处充满了富余,
仿佛一切都是美好的,
连纪念也像一曲老歌,
适合火车里的游子归乡时听。
乌云低沉,雨后的
水珠在橘子树叶颤动,
湿漉漉的青草味迷茫而兴奋,
正像我们此刻的心情。
春天来了,
我们在纪念死亡,
我们来到亡者的坟头
像来到了一块复苏的田野。
春夜的雨声
今天我为春天失眠,
因为黑夜的雨声里有一种让人失眠的想象。
这想象里有雨中的野花和菜地,
还有发光的长满苔藓的大树。
我应该在这样雨天待在家里,
和人说话,看院子里的水缸盛满雨水;
也应该像个哑巴走进山中,
牵一头水牛独自度过余生。
也许任何一种生活终究都是孤独,
但也可能每一种孤独都是幻梦。
缠绵的雨滴今夜无法落完,
我知道我的失眠其实是贫瘠的痛苦。
鄂尔多斯
从雾霾到晴天,
中间隔了一场雪,
从晴天到雾霾,
一场雪已经融尽。
我第一次到鄂尔多斯是在冬季,
我第一次到遥远的北方是在春天。
草场枯黄,
机场的士载我在它的波浪上起伏,
原野无穷,
寂寥的天空有一只想象的鹰在飞翔。
后来我终于看到平原上的城市,
它安静得像远方的废墟。
我在它的酒店里住了一周,
坐在它的餐厅时看见了下雪。
餐厅里的客人只有零星几个,
女服务员穿着暗红的衣服在那儿窃窃私语。
也许这儿应该点一根烟,
玻璃墙外的松柏眼看落了一身雪。
第二天,雪就化了,
酒店门前的汽车变得更脏。
阳光白得耀眼,
天空蓝得好像背后还有一层蓝。
所以我从酒店坐车去了郊外,
想看看像鄂尔多斯一样明亮的北方。
我在城市边缘游荡,
低矮的楼房、宽阔的道路,
这一切都如此寂寞新鲜,
而我也变成一个遥远的我。
我观望着遥远的我和遥远的城,
像我曾经出生在这个地方。
谒汤显祖墓
他的墓地挨着一座湖,
那湖水已经发臭
但看起来还很漂亮。
湖心有岛而他的墓旁是座亭子,
亭子里放了块黑色的“三生石”,
亭子名叫牡丹亭。
我一个人来到这儿,
后来又来了一对老夫妻,
挽着手,走进“因情感梦”的围墙,
然后是对年轻的恋人。
这墓园只葬了他一个,
在这儿徘徊的也只有我一人,
但这里有的一定不是死亡,
说不定他的骨骸也不在这里。
围墙下是个水塘,
落满枯叶,长满野草,像块沼泽。
这儿实在不算优美的景点,
也没有什么古迹可以凭吊,
但它的安静如此吸引人,
就像所有的墓地一样。
我在这儿坐下,站着,或者独行,
就像在寻找一种青苔,
陌生人从他的坟前穿过
就像戏文里飘过的几片云。
这相似的静谧,
让我仿佛和他有着隐秘的联系。
暴雨将至
一一为同名电影而作
葡萄园里有一位美人,
他其实失去了性别。
他在葡萄园里采摘番茄,
就像他在沙漠里迎接雨季。
他的教堂就建在沙漠里,
那沙漠连接着一片翻卷的大海。
二十多年他都生活和平,
他的美也是一种宁静。
信仰给他带来了沉默的愉悦,
少年时他就决定不再说出一句言辞。
但是,夜晚,在他那个收音机都没有的房间,
他遇到了另一个命运迥异的美人,
她睡在窗户下的月光里,
像一只棉花做的狗被雨浇湿。
他感觉她是一个梦,
又察觉到她非梦的部分。
他于是起床看到了她悲哀的眼睛,
接着看见她少年般的嘴唇和隐蔽的肉欲。
但他们都没有说话,他给她两个番茄,
想带她穿过雨季越过大海。
两个美人于是在月光下决定流浪,
要从马其顿逃往遥远的伦敦。
他还不知道这就是爱,
肉体和灵魂混杂的爱,宽广又狭窄。
但她却相信这是爱,刺激仇恨的爱,
所以她死在仇恨的枪声里。
她到死也没有越过那片大海,
而他拥有了那只共同逃亡的旅行箱。
他抱在箱子上低声哭泣,
就像两块墓碑紧挨在一起。
下雨的春天有一种孤独的幻想
下雨的春天有一种孤独的幻想,
你在雨中工作,在雨中看表,
在雨中的山坡上放羊,
鼻息呼应着雨丝的节奏,
就像你胸腔的森林里有一条钟摆,
和世界上所有的钟摆一起摆动。
下雨的春天有一种孤独的幻想,
躺在床上好像一只轻盈的蝴蝶,
潮湿的被褥和房间也许应该变成旷野,
窗外应该盛开杏花并有一座泥泞的村寨,
一个被雨雾打湿的女孩。
下雨的春天有一种孤独的幻想,
草垛升起蒸汽,雨天穿过牛眼,
洗衣的妇人在河边打伞,
看不见的人在墓地抽烟,
无路的地方有一座桥相连,
骑马的人在桥上呜咽。
大芬油画村
它在你的记忆里,
就像你生活在离它很远的地方,
其实又离得很近。
十多年前你就听说了它,
十年后你搬到了这里,
你买了幅画挂在客厅。
蓝色地球上的一小片树叶,
颜料做的施特劳斯父子,
生活在梵高耳朵里的星空下。
没事你就来这里逛一逛,
金色的油画多得像一堆堆垃圾,
吸引穷人那样吸引你。
挑一挑吧,也许
里边真有一个痛苦中的梵高
和趾高气扬的达芬奇。
画铺里的女人拍手迎客,
但从未用梵高取悦你,有一种
匆忙像照相机代替了我们的记忆。
有人用想象画了阳光下的村舍,
还有人一口气画了三个主席,
你站在过道上看他们作画。
穿堂风吹着你的头发,
你看着他的画布开始变蓝,接着变绿。
你认出那是一片海,
海的边缘是一片树林,树梢舞动,
波浪上的阳光像闪烁的镜片,
你忽然发现画它的人其实已经消失。
你发现在一分钟之间,
达芬奇曾骑着电动车出现在你面前,
而梵高面对着一块油菜花地。
他的蒙娜丽莎和他的麦田,
竟然属于同一个城中村,或者
同一个嘈杂的菜市场。
你绕过巷子里的画架,
过道里简陋的露天厨房,仿佛
感到梵高在世界尽头的心情。
回归
——为同名电影而作
深夜她梦见死去的母亲,
她穿着夏天的凉衫,推开门,
微笑着熟悉地向她走来,
来到她的床前,和衣躺在她的身旁。
她知道她死了,又觉得她还活着,
她感到她的鼻息,于是翻过身
像只鸽子一样依偎在她的肩膀上,
仿佛预感到她有话和她说,
说她没有死,或者她死后的生活,
墓园的美丽喧嚣与安静。
她于是又抱住她,像抱着
真爱的情侣,那爱的梦幻
让她像堆棉花一样温暖而轻柔,
像月亮一样孤悬太空。
荒凉坟墓里的孩子
因为自杀叫中毒死亡,
所以水泥房子等同于坟墓。
因为两头猪代表了富裕的生活,
所以冷漠也不是我们的责任。
四个孩子曾经生活在我们的村庄,
最后死于同一个荒凉的墓穴。
他们加起来活了三十几年,
全部的人生都在孤独中度过。
这冷漠冷得让我们害怕,
所以我们撒谎给自己一个安慰。
这谎言就像风中之烛,
这孤独大过了太空。
夜色降落,夏天到了,
连死亡的抽搐也不能带来一丝温暖。
你是谁
你是谁?
你哗啦一声擦燃了一根火柴,
你的脏手捧着火焰和你的眼睛,
它们闪烁着,又明亮又脆弱。
在夜的村庄里,
灯和电视机说着话,
狗和鸡在窃窃私语,
而你的孤独像一条狭长的隧道。
你像孤儿一样被忘记了,
只有一场灾难才能把你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