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结与死结——论洪峰的长篇小说《梭哈》
2015-12-03徐勇
徐 勇
对于近几年的文坛来说,“复出”似乎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先是有马原隐逸后的“王者归来”,尔后又有洪峰“潜隐十五年”后的新作推出。而杂志也似乎乐于以这种“复出”效应招徕读者,在这方面做足了文章。毕竟,“复出”一词,总是让人遐想联翩,充满期待。这对纯文学读者日渐萎缩的今天,当然可以算得上是一剂强心剂。这种期待,于洪峰而言,更是意味深长。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今年年初发生在云南的 “洪峰被打”事件,这一事件使得人们突然想起还有那么一位叫洪峰的作家存在,这于健忘的大众,不啻是一场“宣告”。而洪峰似乎也不甘寂寞,在人们还未从这一事件中及时抽回“目光”的时候,以带病之躯,趁热打铁向读者捧出了长篇新作《梭哈》(《人民文学》,2012年第8期)。
十五年的潜隐,对于一个作家,并不算短。这一时间的两端,当时还是青年的洪峰,走到今天也已年近老年。但是时间的长度与作家的进度/进步并不成正比,《梭哈》虽然是在期待中登场,读后却多少有点遗憾。这一遗憾不是因为作者文笔不好,事实上,相较此前,作家的文字更见老到了。遗憾也不是因为情节编得不好,相反,情节的编织恰恰一直是洪峰的强项;但强项往往也是弱项,至少在这篇据说“贴地飞行”的小说中是如此。
一、视角和死角
有研究者注意到洪峰喜欢写性,“洪峰小说的故事纽结主要是性爱”,“性爱或者说爱,在洪峰小说中大致被表现为三种形态,一种是较少道德约束的自然形态,第二种是用手段掩饰目的的文化形态,还有一种是作为人的性爱的参照而存在的,即赤裸裸的动物形态。”(毕光明:《洪峰小说性爱描写的意义》,《文教科学》,1994年第1期)作家自己也曾坦言,“每一种写作方法对我都是一种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掌握叙事的一种手段”,“在我眼里看来,最形而上的东西肯定是以最形而下的方式得到显现的”《生死约会·谈话录》)可见,性或者性爱,即是作者表达形而上的方式之一种。以此观之,《苦界》(1993年)虽是在跨国谍战,但其实是颂扬普世的爱情。这一爱情不同于纯粹的精神之爱,而是与肉欲不可分割的性爱。爱可以使人堕落,也能让人飞升。爱使人温暖,使人在冷冰冰的世界不再感到寂寞。《梭哈》中也同样充斥着性和对性爱的描写,甚至性或者性爱一度成为人物之间多重关系的核心;从这点来看,洪峰虽然沉寂十五年,但他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方式并没有大的改变。以前的洪峰,小说中对性和性爱的描写,往往以“奇”制胜,在《梭哈》中则是视角向下,开始表现芸芸众生市井百姓性事上的世相百态。
虽如此,洪峰还是一如既往地赋予性爱以过高的地位。且不说性爱在这些芸芸众生生活中的位置之重,其意义也被明显放大。这在王老皮和大脑袋的身上得到极为象征的表现。王老皮甫一出生,即长满鱼鳞式的皮肤,这令他的生活暗淡无光,尊严和自信从此与他无缘,更不用说女人的爱抚了。但自从盲人雅芝的出现,他的生活从此改观。在这里,有一个黑暗/光明和内/外的对立、缠绕和翻转。王老皮生活在阳光普照的世界,他的内心却是一片“黑暗”——暗淡无光;雅芝虽然看不见任何东西,但这一“黑暗”只是在表面,内心却很亮堂。众所周知,光明和黑暗是不可能同时出现的,它们之间只能作为对立状态呈现出来。王老皮的例子表明,“光明”的世界,人的内心并不一定光明:“光明”的世界中,人其实是处于一种内外分裂的状态。显然,王老皮是一个“有病”的人,这不仅仅表现在皮肤上,也表现在内心状态上;而医治他这一疾病的,恰恰是雅芝和雅芝给予他的性爱。是雅芝的性爱,使得王老皮回到了正常的光明世界中来:他的皮肤神奇地变好,内心也不再“暗淡无光”。而事实上,王老皮还是原来的王老皮,有病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视他“有病”的外部世界。这里,其实是以性爱的纯洁对应现实世界的不纯:性爱显然被赋予了批判现实世界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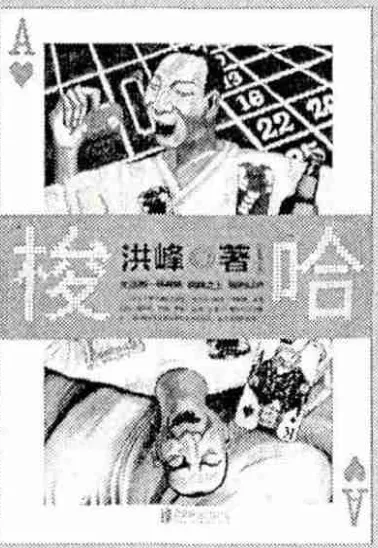
《梭哈》
同样,这一性爱在大脑袋和玉凤之间也被过于放大。大脑袋与王老皮既同也不同,不同表现在性爱拯救了王老皮,却没有拯救大脑袋;同则表现在,性爱都被赋予了极重要的地位。性爱使得王老皮的皮肤变为正常,也差点使得大脑袋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而且对于两人而言,这都是一种“性”的“变态”:在王老皮那里,只有盲人才愿意和他做爱,而在大脑袋那里,则是性虐待。大脑袋向来猥琐,老婆和他人私通,也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只是在绝望——即玉凤坚决要离婚的时候,他才表现出男人的愤怒和野蛮:他强奸并暴打了他老婆。这一野性,让玉凤突然发现,大脑袋其实很爷们,她不想离婚了。大脑袋却错误理解了这点,而事实上,他也只是在极端愤怒的时候才显得像个男人,平时任是怎样都总是服服帖帖。结果可想而知,大脑袋并没有挽回婚姻。显然,在这里,性能力是同性虐待以及真正的男人联系在一起的。而实际上性虐待终究是非常态,想以非常态的方式拯救大脑袋显然注定要失败。小说以大脑袋的例子表明,性爱虽然极为重要,甚至具有救赎的力量,但这一救赎,是通过“变态”成就,其“常态”最终也变得渺渺难及了。小说虽然在写性爱的拯救力量,最终却以不可能颠覆了这一预设。这一悖论在文玲和亚亚的身上也得到明显体现。性爱拯救了文玲,最终也毁灭了文玲。同样,亚亚想以性爱报复男人,最终死于性爱的游戏之中。看来,性爱一旦被赋予过高的地位,最终毁灭的只是它自己。世界的不洁并不能凭借和寄希望于性的微力。
虽然,性爱可以成为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方式,而且洪峰对性和性爱的描写也确实表达了他对世界的独特的认识,但若几十年来认识世界的视角都没有发生改变,这一视角毋宁说也是死角。洪峰的世界以 “性”观“天”——世界,这世界便只呈现出“性”。这一世界无论如何都并不真实,也并不“贴地”。而事实上,只有那些虽然看重性,但不惟“性”的人那里,如刘吉和白芷、桂柳、大肚皮等,性才没有成为毁灭的力量,性一旦达到满足,便不再重要。性在他们那里,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换言之,性于他们只是生理上的满足,显然不能承受超过它本身的重负,否则便只能适得其反。
二、贴地与高蹈
小说虽如介绍“贴地飞行”云云,但其实仍很“高蹈”。“贴地飞行”当然是一个比喻,“贴地”即是指对日常/庸常生活的关注和描写。而说洪峰“贴地飞行”,是因为在此之前,洪峰一直就很“高蹈”,不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都是如此。洪峰总喜欢制造“事件”,总喜欢赋予“事件”以某种意义,这次“被打事件”是否也正暗合了这点,我们不得而知。
在先锋作家中,洪峰算得上是一个象征性极强的人物。早年写作“先锋小说”的时候,其对形式的玩弄,无所不用其极,在在让读者不知所措;而一旦进入九十年代,先锋没落之后,转型又比谁都快。《苦界》就是最好的例子,这部小说中几乎看不出任何先锋的影子在,相反,小说题材内容及形式上的向下趋俗(不是贴地),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使其并没有在文学迅速边缘化的时代被人遗憾,反而是大获成功,取得了非常可观的市场效应。可以说,洪峰及其写作实践,在在表征了文学同市场间的奇怪关系:要么是极端忽视市场,要么是迅速拥抱市场,中间很少过渡。而这某种程度上,恰好就是中国文学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转型的鲜明表征。
综观洪峰的小说创作,不外乎两端之间,一是对形式的经营,另一是对情节的编织。两端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相通之处,更很难有中和的可能。其九十年代以后的创作,多从情节的编织入手,偏重于“奇”“怪”和悬疑等风格特征,很少有写实的倾向。以此观之,《梭哈》无疑是作者的新变,因为小说中满是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庸碌之辈的烦恼,很少在“奇”上用功。小说有趋向写实之意。
所谓写实,并不仅限于日常生活的描写和叙述,还表现为一种叙述的逻辑和世界观。应该说,先锋写作并不乏对日常的关注,但日常在先锋作家眼中其实是破碎的,无法还原和补缀的;日常生活之间既不连贯也无逻辑可言,这一零碎的日常表明了先锋作家对意义追寻的拒绝和抗拒。先锋作家以破碎的日常显示他们自己的非本质主义世界观。相反,写实则不同。写实不仅要注重细节的真实,日常的琐碎,还要会讲首尾连贯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视角的向下,以一种平视的角度观照并理解芸芸众生,而不再追求生活世相背后的本质或宏大命题。换言之,写实就是关注生活本身,而非其他。
这样来看洪峰的《梭哈》,显然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小说中的“近景”人物,如卡卡、宫作家、刘吉、亚亚、桂柳、白芷、大脑袋、大肚皮、王老皮、文玲、三哥等。小说对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确实写得琐碎平实,很见功力,特别是他们之间的对话,更是体贴入微;但对那些“远景”人物,如玉凤、王文理、刘吉的老师、网友等,对这些人物,小说的叙述者则始终处于半明半暗之中,他们的行为怪异,不可理解,到最后也得不到解释。尤其是王文理,表面看来谦和质朴极有风度,但谁能晓得他竟是一个性变态和杀人狂。对于这种极端性格的形成及其转变,实在让人困惑。
显然,说小说是“贴地飞行”,只能用在前一类“近景”人物身上。而从后一类“远景”人物身上,仍可见出作家早年先锋小说风格的影子,即对离奇情节的编织、及其呈现出的原因的缺失和对世界的不可理解。这样一来,小说就形成一极大的张力,即一边是扑面而来的庸常,琐碎,但也真切,让人感到亲切;一边则是飘渺不可及的异常,对这一异常世界,若隐若现,我们只能窥见其大要,并不能还原其因果和起承转合。这种张力,某种程度上正表明作家世界观人生观的变化。以前的小说中,虽然充满奇情和夸张,但世界仍是可以而且能够把握和理解的,不管这一世界是眼前,还是几千里之外的异国他邦。但现在却不同的。《梭哈》中的世界充满了未定,就像“梭哈”这一赌博形式一样。围绕我们日常生活的,往往是一些“近景”人物,对于这一世界,我们多半熟悉、理解并能从中找到自我认同的途径。而对于那些我们的日常世界所不及的“远景”世界(包括虚拟世界),我们虽然偶有所闻,但其实渺不可及难以理解,其中到处暗合着陷阱,稍不小心,便会身陷其中,万劫不复。这一矛盾和复杂正表明作者面对急剧变化的世界的恐惧和无力。小说充满了宿命色彩。

洪峰
三、结语:落地的麦子不死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洪峰的 《梭哈》不管是从视角还是写法上,总不脱此前创作的影响。其虽表现出写实的倾向,但并不彻底。总的说来,这只能看成是一部带有转型意义的作品,如果作者还想继续创作的话。就像马原创作《牛鬼蛇神》,虽然潜隐二十年,仍只能看成是过渡之作。
而若比较洪峰此前的小说创作,这一过渡意义更见明显。仅举《梭哈》同《革命革命啦》(2004)之间的联系,即可说明这点。这两部小说都以沈阳街道上的小老板(或小店主)作为原型人物。而且也都涉及到互联网和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冲击。在《革命革命啦》中,作者探讨了互联网带来的“革命”及其限度,这一探讨在《梭哈》中有所延续。作者不仅看得这其中的无限可能,也为其中隐藏的陷阱和危险深感忧虑,这一忧虑在最近的《梭哈》中更见明显。
从小说中不难看出,随着年龄的渐老,洪峰开始倾向于回归传统和趋向写实 (有趣的是,马原的复出同样如此);但岁月荏苒,昨是今非。今天的现实早已不是八九十年代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回归其实并不可能。这一现实内涵的变化,最为鲜明地体现在互联网带来的种种新变上。随着互联网这一虚拟空间的介入,现实不再那么容易理解和可预测,现实充满了种种可能,其中杂糅了希望、诱惑,困惑乃至陷阱,对于这样一个世界,现实主义式的“反映”如何才能成为可能?
显然,在现实主义看来,现实是可以理解和把握的。现实虽然五花八门五光十色,但在这纷乱的表象之下总能找到并发现本质的、内在的和规律的东西在,人们籍着这种努力,总能理解世界并安置自身。但在互联网时代,面对这样的现实世界,人们包括作家在内,并不总能做到这点。从这个角度看,洪峰《梭哈》的张力,正是现实的新变带来的,而其所为“梭哈”,并不仅仅意指赌博,更是一种隐喻,一种在互联网时代个人对自身命运之不能把握和无能为力的虚弱感,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世界的不可捉摸。
或许,小说的意义就在于这种进退失据上。仅就小说本身而论,洪峰确实善于编织情节,写实的功力却有待加强。而且,从作者90年代以来一贯的小说风格来看,这部小说更像是好莱坞式的写法,小说中综合了情爱、凶杀、悬疑、先锋等多种元素,充分吸收了好莱坞悬疑片的种种技巧。如此种种,都一再表明,洪峰虽然有“贴地飞行”的倾向,其实并不彻底。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小说中的矛盾和犹豫不决,是否可以看成时代的变化带给作家的困惑和对困惑的表现?只不过,在这时,作家并不见得比我们普通百姓高明多少,作家不再是全知全能型洞若观火的上帝或者旁观者,他只是同我们一样平凡琐碎甚至平庸迟滞的芸芸众生。果真如此,我们又怎能去苛求作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