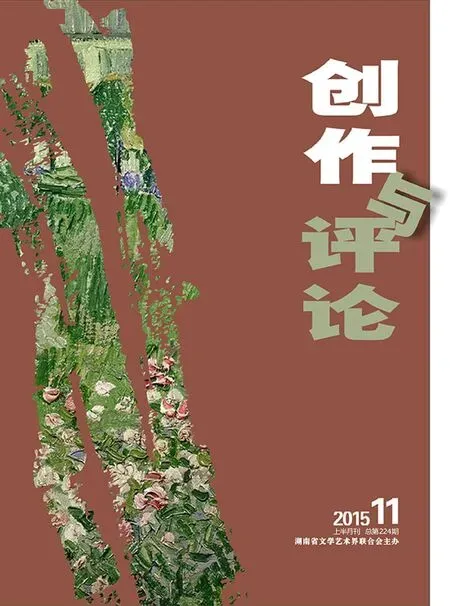罪与罚
2015-11-22
回到工棚,钟强把自己狠狠褪剥了一回,仍觉着浑身上下脏兮兮的,像是刚刚从阴沟里打捞上来,气味从毛孔渗入了骨头缝。老于和三和却是发泄后的满足,两个人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一搭一句地回味着刚才的事。说到那个女人的叫,对面床上的三和竟腾地弹起来,手臂一张一张地比划着,将屁股下单薄的床板摇得咯吱响,整个宿舍跟着动荡起来。经了这番折腾,钟强就觉着肠胃里翻腾起来,想出去吐一回,终于还是忍住了。
“装死?”老于的声音在黑暗里升起来,“一回来就蔫巴了,屁都不放一个?”
宿舍鸽笼似的,却塞了两架上下铺的床。钟强跟老于睡一架,他在上,老于在下。另一架归三和跟一个河南人,前天,那人回老家给儿子办婚事去了,就剩了他们三个。
“我恶心!”话没出口,又被他咽回去了。
三和嘎嘎一笑。“这家伙是被窝里放屁,独享!”
钟强想回骂一句,到底没吭声,由着他们说笑。
晚上喝过酒后,他跟着他们去了离工棚不远的一个城中村的院子。本来他不想去,可是老于早把话放在前面了,谁不去谁他妈是孙子!老于是大工,得罪不起,更何况他肚子里的酒花也顶得厉害,就跟着出来了。三个人被分头安排到了不同的房间。里面散发着一种含混的气息,除了一张简单的铁架床和一个床头柜,再没别的摆设。没多久,轻手轻脚进来一个女人,好像冲他说了句什么,便坐到床上脱衣服。不知为什么,他竟没一点反应,女人帮他,可他还是木木的,无动于衷。他不明白自己这是怎么了,他其实很想,离家都几个月了,夜里一躺下,脑海里就会跳出个喷香的肉身,像是媳妇四花,又不像,身体的情势因此会变得紧张起来,一触即发。女人催他快一点。他低下头,显得很不好意思。隔壁有了动静,女人指着墙让他听,他勉强觉得行了,可上去没多久便垮塌了下来。女人笑笑,问他要了钱,走了。
老于和三和终于闭上了嘴巴。
他想睡却睡不着,总觉得那种脏腻感更强烈了,像是有虫子在身上蠕动。他迟疑了一下,还是跳下床,拎起一只水桶朝外面走去。黑暗中,他听得他们身子动了动,目光棍子似地戳向他的腰背。门口不远处有口井,一截水管从井口探上来,他拧开阀门,待水桶被注满,用力一举,哗地浇向自己。他身上只有一条短裤,水从头顶一直漫到下体,给了他一种说不出的快意。但没一会儿,又被那种脏腻感紧紧地攫住了,他真想从身上撕起一层皮来,或者将它们从毛孔里抠出来。他没一点办法,又往身上哗地浇了桶水,又浇了一桶。这时,从那边移过来一个人影。
“大半夜的,你小子不好好睡觉,跑出来干啥?”是看工地的老头。
钟强支吾了一句,掉转身往工棚里走。
“神经病。”他听得老头在他背后骂了一句。
钟强一进门,灯蓦地开了,他感到四道目光刺到了他还在淌水的短裤上。“你狗的犯啥神经呢,折腾了那么久,火还没下去?”老于出了声。
“管得着吗?”钟强嘟哝了一句。
“你小子造反啦?”老于腾地跳下床,“好心好意领你去舒服一回,你倒好,一回来就哭丧个脸,死了爹还是娘啦?”
“是,好心当了驴肝肺,你到底给谁脸色看?”三和帮腔。
“给我自个。”钟强说。
“给你自个?到底啥意思?”
“没啥意思。”
“你狗的痒痒啦,想他妈的挨揍?”老于眼瞪得牛蛋似的。
“你打!”钟强抬起头,盯着老于。
“当爷不敢揍你?”老于真的举起了拳头。
“算啦算啦,”三和也跳下床,将老于推到了一边,“少跟这死狗扶不上墙的东西一般见识。”
“一起出来混,有福同享,这死狗倒好,哭丧个脸给咱看,这不是成心不让人睡觉吗?”老于越骂越上火,“四花咋找了你这么条死狗?我要是四花,早一脚蹬了你。”
“好,说得好!”钟强一扬脸,“蹬了好,我他妈的脏。”
“我算明白了。”老于冷冷一笑,“你狗的跟我尥蹶子,是怕四花不要你了,对吧?你肯定在心里骂我领你出去耍女人了吧?骂我把你带坏了,对吧?妈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远天远地的,你家四花能知道吗?你就是把那个女人搞死,四花也不知道,懂吗?”
“没有不透风的墙。”钟强感到眼里有了泪,慢慢蹲在了地上,“她迟早会知道的。”
“瞧这点出息,”老于又一笑,“这么多年我走南闯北,睡过的女人比你见过的都多,可我老婆知道吗?啥都不知道。”
“你能睡女人,我不能!”钟强说,“我跟你不一样。”
“你狗的说啥?你咋跟我不一样了?”
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只蚊子,像电影里的美军战斗机,在宿舍的领空上四处冲撞。可能也觉得老于太张扬了,蚊子骂了句“龟孙子”,翅膀一扇,开足马力,“轰”地朝他那张大板脸撞去。老于本来盯着钟强,不提防有飞行物撞过来,肯定在心里觉得这厮比面前这个自称跟他不一样的家伙还要可恨,视线和两只手立刻高射炮似地举起来——美军战斗机可能也觉出了危险,照着他那张脸又撞了一下,便没了踪影。老于哪里肯放过它,全身每个毛孔都睁大了,蓦地,他发现目标降在了门板上,慢慢移过去,一只手“啪”地扇下去,再张开时,掌心里便是一摊粘稠的暗红的血。
钟强看了一眼,觉得胃又一阵翻腾。
老于将手掌在床杆上擦拭了一下,又把目光转向他。“说,你狗的咋就跟我不一样了?你是三头六臂,还是能头迎下走路?”
“我就是跟你不一样!”钟强霍地弹起来,“我比你懂得啥叫脏!”
老于两只眼睁成了电灯泡,唾沫星四溅,“嫌脏你早他妈的干啥去了,没人绑着你去吧?啊?”
“不怪你们,是我管不住自个。”钟强说。
“装吧,你狗的就装逼吧!”老于哼了一声。
“想不到这狗的真会装。”三和摇着头对老于说,“我敢跟他打赌,明早一起,这狗的比谁都能吃,比谁都能干活。老于你信不?”
“那就等着看吧!”钟强心里对自己说。
老于和三和相互看了看,忽然大笑起来。
几缕阳光从窗口刺进来,就落在钟强右侧这面墙上。
一宿没合眼,他觉得脑袋和身体都生了锈,成了一具僵尸。那两个人出门时,似乎喊了他一声,他木然地看着他们走了。整整一夜,他承受着他们的呼噜声,老于,声音像工地上的挖掘机切入了坚硬的地层,一个劲地嘶吼,吼上一阵子忽然会沉下去,似乎是发动机出了故障,没多久,又亢奋起来,要将一切碾碎似的。三和,声音细细弱弱的,像是水管拧细了,有一下没一下地淌着。他被他们聒噪着,无法入睡,当然就是能睡着,他也不会给自己这个机会了。他不能跟头猪似的,吃过了就睡。他得好好想想,想明白一些什么。
整个夜晚,他感到有个人一直站在自己面前,那是四花审视的目光,她木桩似地戳在他们的呼噜声中,像窗外的月光挥之不去。有一会儿他好像睡着了,觉得四花就躺在身边,不由把手伸过去,然而,好像刚触到一点细腻的肌肤,就被轰一下推到一边去了。醒过来后,他发现自己真躺在两架床之间的空地上,那两个人却没一点觉察,依然是呼噜声山响。
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这么赖在床上了,要么坐起来,没事人似地出去吃饭干活,要么就得给自己一个惩罚。但他无法做到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他没老于的能耐,既这样,那就该选择惩罚。可是他想不出来,怎么才能惩罚自己呢。但是,他觉得自己必须起床了,先起来再说吧。他跳下地,也懒得擦把脸,就那么木木地出了门。整个世界一如既往地运转着,不远处的楼上已经有了忙碌的身影,黄色的安全帽反射着阳光。
——没有人关注他,更没有人想到他遇上了事。
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只蚂蚁,被这个世界彻底忽略了。
他在工棚前的空地上走了很久,又返了回来——他实在找不到惩罚自己的办法。他只能把自己关起来继续想了。他没上自己的床,怕躺下后会舒服地睡去。河南人走时将铺盖卷起来了,大半个床板光秃秃的,他半个屁股坐了上去。他蓦地想到了牢房,那里的床可能就这样,没有行李,只有硬硬的床板。蓦地,他感到衣袋里的手机颤了一颤,摸出来一看,是四花的短信。手机还是来工地时,四花给他买的,国产货,直板,大屏,花了一千来块钱。当时还不是很落伍,能使用流量上网,看八卦,聊天,但他不喜欢玩,也就是隔些天,用它给四花报个平安。三和因此嘲笑他,说他彻头彻尾一个土鳖,甚球也不懂,白白浪费了每月那点流量。
“你没事吧?夜里我的眼皮一直突突跳。”四花在短信里说,“真怕你出啥问题,这两天干活切记小心。”
看过后,钟强一下愣住了。
没多久,手机微微一颤,又是一条短信。“你一定要好好的。”
钟强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哗地决堤而出。
他忽然明白了,这就是自己要找的惩罚。他做了对不住四花的事,她却在关心他,这不是惩罚又是什么?但是该怎么回复呢?就说自己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让她放心好了?可这样的回答未免太简单,连他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那怎么办?他忽然觉得该把事情说出来,否则,就没法驱走压迫在心头的肮脏感。说出来,可能就会轻松一点。
“可真要把一切都告诉她吗?”钟强心里问自己,“说出后,她会原谅你吗?会吗?”
他感到自己遇上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真要说出来,她会怎么想他?又怎么看他?他不知道。
这时候,他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其实并不了解自己的女人。把她娶过门后,他就抛下她不管了。他每天要考虑的是,怎么挣钱糊口,怎么养家。这几年村子里几乎空人了,地,他不想再种,种了也挣不了几个钱。他只能出来打工。他在超市当过搬运工,当过酒店的保安,但没有一个工作留得住他,最终选择了去建筑工地当小工,这营生苦累一些,赚钱还行。他几乎很少去陪她,也就她坐月子时守了一个月,以后给她的时间就零敲碎打了。
然而,四花的短信又来了。
“看到我给你的话了吗?”
那头的四花肯定挺心焦,要不然,她也不会这么接二连三地给他发短信。她很少这样急,大多数时候就那么沉默着,一年也打不来几个电话,有时连他也暗暗佩服她那股韧劲。他忽然觉得该说了,豁出去也得说了。不然,他心里就不得安宁,那种脏腻感也不会离开他。他开始给她写短信,写了几个字删了,又写了几个字又删了——这事他怎么说得出口呢。
“真他妈的浑啊。”他在心里唾了自己一口。
正煎熬着,三和一推门进来了。
“你狗的真不去?”三和拿眼瞪他,“老于正日骂你呢。”
钟强看了他一眼,木木地摇了摇头。
“到底哪根筋拧住了?还在想昨晚那点事?”
钟强没吭声。
“老于不是说了吗,你不说四花就不知道。走吧,跟我去工地。”
“你咋就知道她一定不知道了?”钟强冷冷地看着他,“这种事有感应,她肯定会知道的。”
三和说:“你不去,老于会给头儿打电话的,不怕开除?”
“让他们看着办吧。”钟强头也没抬。
三和一下给噎住了,看了他一眼,出了门。走时摞下一句话:“真是个一根筋!”
等三和走了,钟强想,不能再拖了,就跟四花都说了吧。迟疑着,他拨通了她的手机。
“你咋回电话呀?”那头的四花有点吃惊,“回个短信就行了,大老远的,不觉着打长途费钱?”
“这,这个。”钟强有些结巴。
“你不会真遇上啥事了吧?”
“我,四花。”
“有啥你直说,说呀。”
钟强迟疑了一下。“那我就说了啊。”
“说吧,听着呢。”
“这个,”钟强还是觉得说不出口,又临时变了卦,“其实也没啥。”
“你真要急死你媳妇吗?”电话那头的四花真急了,“我知道你在那边也没个说处,说出来我也帮你想个辙儿。”
“真的没啥。”
“你不说,那我去工地找你啦,反正待在家里心也不安。”
“大老远你跑来干什么?那得多少盘缠路费。”钟强担心她真的跑来。
“那你就说吧。”
钟强叹了口气,硬着头皮开始讲昨晚的事。
他说得很艰难,磕磕绊绊,丢三落四的,但来龙去脉还是摆到了那头。他还说了自己的困惑,他被那种肮脏感抓得死死的,一夜未眠,连活儿都不想干了。他没心思干别的任何事情。他能感觉出那头的沉默,偶尔“嗯”一声,意思是她在听。他害怕她突然挂了电话,或者破口大骂起来,然而她却什么都没说,一直在默默默默地听。这反而让他心里更忐忑了。
“我做下了肮脏事,”钟强嚅嚅地,“你想骂就骂吧,咋骂都行。”
那头没吭声。
“说话呀你。”他急了。
她还是不吭声,他有些后悔说出来了。他蠢得不如个驴!
半天,她终于出了声。“都做下了,再骂还有用吗?其实我早该想到会有这事的,出去那么久了,你咋能憋得住?”
“我,我真他妈不是东西!”
“说这些没用了。”她重重叹了口气,“对了,你没去工地?”
“没。”
“去吧,丢了饭碗,你咋养活我和孩子?”
“你,真没往心里去?”
她没吭声。
“我真没脸皮,这样的事,换谁不往心里去呢?再好的女人也受不了呀。”他啰哩啰嗦地说。
“好了,别说了,这次不跟你计较了。”
“真的?”
“还有假的吗?上工去吧。”
钟强还想说什么,那头却挂断了。他愣愣地握着手机,感觉像在梦里一样,事情这就算完了?会有这么简单?他真有点不相信。可听四花那口气,好像真的不跟他计较了。可能,她觉着他在工地,怕他心里不痛快,又会惹出别的事来?多好的媳妇!他心里越发内疚了。
钟强到底还是去了工地。
这楼有六十层,据说是这个城市的最高建筑,骨架春天就起来了,眼下留了一部分人做里外的细活儿。这几天,老于带着他和三和打外墙水泥面,他的活儿自然是和水泥了,他把水泥和沙子拌好,铲进料斗,再提到老于和三和身边。三和现在都成大工了,这家伙会来事,把个老于侍候得舒舒服服的,自然就被另眼相看,跟着打墙面了。
钟强到了楼下,他本可以跟老于打个招呼,让他们把脚手架降下,坐着升到工作面的。但他不好意思麻烦他们,在楼前停了一会儿,他便进去从楼梯上爬,等他呼哧呼哧爬上来后,早满身臭汗了。他站到工作点的楼层里,听得外面窗前,三和正跟老于唠叨他。
“真没想到他那么怕老婆,你开导了半天,他还是听不进去。天下哪有这样的窝囊废?”
“他原本就是个扶不上墙的东西。”
钟强咳了一声,从窗口腾地跳进了脚手架,把那二位吓了一跳。
“不是不想来?”老于半天泛上话来。
钟强没吭声。
三和看了他一眼,又把脸转向老于。“你还信他的话?他是那种说了算的人吗?丢了饭碗,他咋养活四花?一家人喝西北风去呀。我早料定他会来的,瞧瞧,我没说错吧?他这种人,就他妈的会装逼!”
“你说啥?”钟强把脸转向他。
“说啥?”三和冷冷一笑,“说你就会装!”
“你再说一句,”钟强心里的火腾地升了起来。
“说你咋啦?”三和又重复了一句。
钟强攥紧了拳头,他真想照着三和那张脸砸下去,可最终还是将心头的怒火压住了。每次回了家,四花总是说,在外面嘴秃点,少跟人斗气。他觉得四花说得没错,出来是挣钱的,不是跟别人斗气的,有些事就得忍耐。他看了三和一眼,不再搭理他,低下头去和水泥。三和见他服了软,哼了一声,拿起泥铲子去当大工了。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钟强心里骂了一句。
一个人要供两个大工,钟强不敢歇一下,弯着腰吭哧吭哧地死受。老于有时会停下来靠着脚手架抽根烟,三和也能偷会儿懒,钟强却不能停,他一停老于就会斜着眼看他。抹完这一层的外墙面,老于又把脚手架降下了一层。钟强紧着手做活,不去看别处,更不敢看下面的虚空处了,这是高层作业的常识,看久了,人就会胆怯,头晕目眩。这还是在楼的半腿处,若是靠近了楼顶,往下看一眼会心跳半天。
“妈的渴死了。”三和本来想喝口水,矿泉水瓶却空了,他把它扔到脚下,踩了一脚。“有瓶啤酒解解渴就好了。”
“美得你!”老于哼了一声。
“不美还不想呢。”三和说。
“美事多着呢,你小子还想啥?”老于笑了笑。
“想得多着呢。”三和谄媚地看着老于,“晚上下了工,咱再好好喝一顿,喝过了再去耍一回。”
“那你问他去不去?他去,我就去。”
钟强感到老于扫了他一眼。
“他肯定去。”三和说。
“你又不是他,咋知道他肯定去?人家不是说了吗,他跟我们不一样。”
钟强感到老于又扫了他一眼。
“有啥不一样?他那是装逼!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装逼货!”
钟强心里的火又腾地升起来。
“你咋知道他装?他不是差点就不来了嘛。瞧瞧他那眼睛,熬得都是血丝,肯定一夜没睡。不能再拉他了,他比我们干净。”老于说着,又把脸扭过来。“哎,钟强,我说得对吗?”
钟强停下手里的活儿,没出声。
“说话呀,哑了?”老于又紧着声问。
“老于你少跟他啰嗦。”三和眼一瞪一瞪地说,“我算看透他了,就会装,你好心给他块肥肉,他吃也吃了,香也香了,完了抹抹嘴对我们说,不好吃,脏,恶心。你说他还有点良心吗?”
钟强再也憋不住了。“我就是觉得脏,恶心!”
“装逼货!”三和说。
“骂谁?”
“当然骂你,装逼货!”
钟强觉得心里起了风暴,一把攥住了三和的工服领子。
“你,你想干啥?”三和脸一下灰了。
钟强吼也似地说:“老子想把你扔下去!”
下面好不虚空!
二十几层高,扔下去,铁打的也会摔个稀巴烂。高空作业,尽管身体外侧有护网兜着,可是以他的力气,挡得住吗?人要是决心去做某件事,谁又拦得住?大前年,他们有个兄弟,村里留守的妻子让人拐跑了,他觉得生活一下黑到底了,从脚手架上跳了下去,摔了个脑瓤四溅。这还不说,又让楼脚下的钢管戳破了肚子,肠肠肚肚地流了一地。
“钟强你可不敢乱来啊,”老于也慌了,“快松开他!”
钟强并不收手,还往护网边搡了三和一下。“说,老子装了吗?”
“我,我没说!”三和嘴唇一颤,“你是爷,是大英雄!”
钟强冷冷一笑,这才松开了他。
“咋开这样的玩笑呢,”三和身子仍抖抖索索地,“吓死我了。”
“谁跟你开玩笑了?”钟强手又动了动。
三和闭上了嘴巴。
钟强不再去理他,低下头做自己的活儿。
“钟强,你,不如下去歇歇吧。”老于忽然出了声。
“我不累。”钟强说。
“可是,”老于小心地看着他,“我觉着你有点不正常,还是下去歇歇好。”
钟强停下来,回过脸看向老于。“你啥意思?”
“也没啥意思,我想放你几天假。”老于陪着笑脸说,同时往三和那边移了移身子。“等你歇好了,再来上工也不迟。”
“放我假?”钟强一下愣住了,“为啥?”
“这还不明白吗?”三和几乎是从老于腋窝里探出头来,“老于他是为你好,说到底他是你媳妇娘家人,心疼你,是不是?等你歇上几天,觉着正常了,再上工也不迟。”
“我不正常?我咋不正常了?”
钟强看看老于,又看看三和,看得他们都快把头扎进裤裆里去了。
“明白了,你们是嫌我不顺眼,想撵我走,对吧?”钟强冷冷一笑,“不让干就不干,老子也不想侍候你们了。”
“你?!”老于想说什么,又把话咽回去了。
钟强又看了那两个人一眼,爬上窗户,往楼里钻。站到里面后,他发现那两个人正大睁着眼看他。
“看啥看?”钟强吼也似地说,“你们才不正常呢,整个两头猪!”
说完,他穿过房间,往楼梯那边走去。
或许是里面的活儿做完了,钟强进去时听不到一点人声。楼梯的扶手也装上了,还没有来得及上油漆,锈迹斑斑的,看着有点脏。下了一层,又下了一层,他忽然停下来,想进去看看。他知道,今天下去了,明天或许他就上不来了。老于的意思很明白,他不想让自己待在这里了。他认为他不正常。看来,他得离开工地离开这个城市了。从去年冬天起,这栋楼就开始预售,据说每平方米的价钱是一万五,这对他来说自然是个天价,想都不敢想。这样的楼房,他就是再活五百岁,怕也买不起一个角。
钟强进了右侧的户室,一进来这个房间显得很宽大,他想将来这里肯定是做会客厅用的,他在各个房间转了一圈,最后又回了那个大房间,站在了中心位置。他环视着整个房间,脑子里冒出了一个问题,假如将来他也能有这么一套房子,该怎么装修呢?他费力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在这方面他真是可怜得没一点经验。是的,他在村子里连处新院子都没有,又怎么想得起楼房的装修呢。可有一点他知道,得给儿子留一个房间,让他安安静静学习,然后给他和四花留一个大卧室,客厅呢,当然要买一个大沙发,可以让一家三口都坐得下。别的,他就再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原来他什么都不懂啊。
透过还没装玻璃的窗口,他看到外面的天那么蓝,那么洁净,没有一丝半点杂质。
他迟疑了一下,忍不住朝阳台那边走去。
房子大,阳台也就显得宽大,他停下来,深深吸了口气,像是要将那一片蓝也吸进肺腑里来。
这时,一只鸟儿忽然从他背后的某个房间飞出来,几乎是擦着了他的头顶,他一愣,抬头看去时,它早扑棱着翅膀飞出了窗口。它刚才藏在哪里,他怎么没有看见呢?或者,它是刚刚飞进来的?他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在哪里见过呢?蓦地记起来了,小时候,在村子的河边,他见到过它的影子,嘴巴粗短,羽毛灰绿,眨眼间就飞到了高处。对,应该是这种鸟。他记得,它从某个隐蔽的地方飞起时,喉咙里会发出好听的声音,脆生生的,像笛子在吹奏。它的嗓子,声音,纯得像蓝天。对,是这样的,那一刻,他为自己脑子里蹦出这个比喻变得兴奋起来。他立在窗前回忆着那只鸟。它一边唱一边向高空顶去,像箭,箭也似地射到幽深的蓝里,一会儿就没了影儿。然而过不了多久,它又蓦地出现了,一个小黑点慢慢放大,它是在俯冲,在直刺下来,带了一种急迫的心情。刺下时,它依然会发出好听的声音,清脆,婉转,洁净,对,蓝天一样的洁净。他曾问大人,那只鸟怎么唱得那么好听呢。人家告诉他,它是在为自个的媳妇唱歌,跳舞,耍杂技,它这么做,就为了让它媳妇高兴啊。他说,那它媳妇又在哪里,看得见吗?人家指着河边的灌木丛说,看到了吗,就在那里,它们在那里有个窝,有个家,它媳妇就在那里看着它,等着它。
想着那些事,他蓦地记起了四花,他的媳妇。她不也在家等着他吗?他盯着那只鸟飞去的方向,还是想不起它的名字,然而对他来说,不记得起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最要紧的事是飞起来,对,飞起来。四花,他亲爱的媳妇,就在这蓝色天宇下的某个地方等着他啊。他继续朝着那只鸟飞去的方向看去,似乎又看到了它的影子,也听到了它的声音。他学着它的样子张了张翅膀,不,是抬了抬两只胳膊。
飞吧,就这样飞吧。
他说了句什么,也许是唱了句什么,然后,他看见自己飞了出去,像那只云雀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