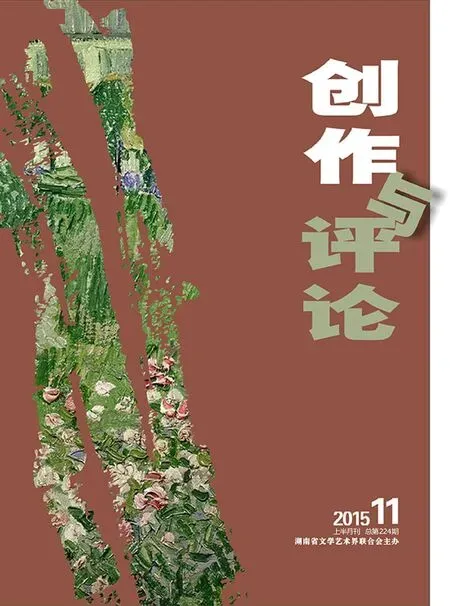池上一跃,翩然翎落
——评池上小说《这半生》
2015-11-22赵柏田
○赵柏田
池上一跃,翩然翎落
——评池上小说《这半生》
○赵柏田
夏日某天,接池上电话,问能不能为她的新小说置一小评。我于写序作评的事,向来能躲则躲,但池上那一日的怯声细语,却让我推托不得,再加上读她的《在长乐镇》大有好感,就应承了下来。
整个夏天都在外奔忙,待得想起池上这部躺在电脑里的小说,已过立秋了。而这女子,竟也不来电催促一声,就好像对自己的这个新小说有着十足的把握似的。后来我想,小说之外,于这女子,我是喜欢她的静气的。
静则虚,虚则体道入微,从从容容去织小说之网。
网,是池上小说给我的最初意象。这大抵是因为,她总要给小说里的人物设置一个困境,而这,也未必不是她内心镜像的一个投影。一个现代都市里的时尚女子,爱嗔爱笑,领着一份安稳的教职,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忽一日,发兴做起了小说,这要么是因为梦的牵引,要么是,她结结实实地遭逢了生活的迷思。而池上,尽管在我眼里青春年少,时作疯玩,却也是过了被梦蛊惑的年龄了。由是之故,她写小说,是不甘,是不羁,是挣脱内心诸困境的努力一跃。
——《这半生》,正是池上向着小说的金苹果之枝的凌空一跃。
“云惠年轻时受过一次伤”,故事开场时,主人公还是一个女大学生,在一家KTV做兼职。这个过去完成时态的句式,把云惠“这半生”在情爱世界里的痴痴缠缠、转头成空,都归结到了年轻时的一次感情受挫上。经历过一次爱与别离,女人的情感世界便不完整。随着故事推进,我们会看到,这道伤,一直延续到了她与沈兆南的婚后生活。无疑,他们的性生活是不和谐的。因为有前一段欢爱,她的身体似乎是天生排斥这个男人的——“好像是被打了抗体”。她的负罪感只有无穷无尽做家务活才能抵消。终于她怀孕了——这是故事向着好方向转变的兆头么——她也做好准备,要真心实意接受这个男人了,却因为母亲罗琳女士禁止他们在孕期过性生活的告诫,又带给了她莫大的羞耻感。
故事至此,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这段婚姻走向终结。池上设置他们的婚姻解体时,安排了让沈兆南在嫖娼时被抓,尔后又玩起了失踪。云惠去探望被拘的丈夫,丈夫说:“今天我们把话挑明了,我是找小姐,可找小姐怎么了?实话同你讲,我随便找个小姐都比你来得真诚。”嫖娼者反倒成了一个愤怒的控诉者,这角色的颠倒,说来逆转得快,却也丝丝入情。
离了婚的女子,还是要过活的呀。她的世界虽不再完整,但还都是要一一去打理。与父母、与儿子阿宝,都是费心费神,还要去跟一个个陌生男子、二婚男去相亲,高的,瘦的,各种职业的,就像她妈说的,“一个女人家,要吃、要穿,要生活,多少辛苦。你嫁了人就不一样了,有了依靠”。兜兜转转一大圈,终究是十二姻缘空色相。终于,她身边出现了一个叫林国光的靠谱男,大学教师,丧偶。干净,也重情,还陪着她为亡父守灵。眼看着她就要有个好归宿了,却让一个“真相”把靠谱男给吓退了:这女子,儿子都上幼儿园了,她的乳房竟然还是他的!
小说至此已经行进到约三分之二,这个一路走来中规中距的故事,至此突然被一股情感的暗流所裹挟(裹挟这个词太被动,说主宰,可能更合适),走向了另一个方向,一个情感畸变的方向。常识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危险的向度。这让我们为池上捏着一把汗,她如同在玩攀岩游戏,一脚踩空,就可能跌落小说的悬崖。
她终究踩稳了。她把脚踩在“乳房”这个意象上,缓慢地移动着。至此,小说获得了一个明晰的方向,那就是母与子关系的书写:对立,冲突,貌似的和解与最终到来的爆发。她的身影算不上多么轻逸,却也平安落地了。
乳房是爱的容器,母爱的器官,也是性爱的表征。当云惠第一次让儿子阿宝吮吸她的乳头时,这个缺爱的女子,是把儿子当作她全部的情感和未来寄托的。“他的嘴用力地裹着她的奶头,她能感觉到她的血液、骨髓乃至灵魂伴着她的乳汁流至了他的。”他的什么?自然是生命。尔后,她与林国光的感情升温,阿宝“我不要”的拒绝态度,是有让她不安的,到了她当着林国光的面,一掌把儿子打哭,由爱生恨的种子已然种下。此后的小说叙事速度明显加快,这快,有一场长跑奔向终点的欣然,却也难免笔墨潦草起来。
阿宝上高中了,云惠也老了,母子间的对立愈加尖锐。看上去一向懂事的阿宝拒绝参加高考,云惠无可奈何;阿宝去酒吧做歌手,云惠也无可奈何。儿子带了各式各样的女人回家,喝酒,做爱,叫床,她也都小心忍受着。及至后来,看着这个女人像个小偷似的,进到儿子满是酒味、烟味和精液味的房间,把脸整个儿裹进了他的被窝里,呼吸着儿子不再单纯的体味,我们会发现,这个女子,已经被内心的高墙困住了,她是被失去儿子的恐惧攫住了,被变异的爱攫住了。小说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个晚上是,她来到儿子床边,把自己柔软的乳房抵住他,但儿子耻辱的惊叫,让她觉得“整个世界都暗了”。这一切,加速着故事奔向终点:一个女孩爱上了阿宝,而且那女孩各方面都很不错,当她意识到儿子将被这个女孩永远带离她的生活时,她突然当着女方家长的面发作了,细数儿子的种种劣迹,惊走了那对母女……她的胸中涌动着快意,因为她一向高高捧着的男人——她的儿子——原来是如此弱小。
多少伤害,以爱之名义而行。这爱的悖反里,作者已经无力对云惠作道德上的甑别和指责,她沉浸在了悲哀与同情里,只有让卢舍那大佛的慈目,看着始终。卢舍那,梵语的意思是光明普照,以此观照处处暗角的人性与人生,同情里也尽是反讽意味。
在这种女性主义的叙事态度里,爱情背后,那个寻找或被等待的男子,是女人现世的依靠,也是一生的宗教。所以,罗琳一声声地交待女儿,一个人过,要吃要穿,多少的苦,“嫁了人就不一样了”。所以即便到了婚礼一刻,她们还是觉得这是一场赌注大到没边的赌博,以至一念及此,就浑身发颤,几乎是一种生理性的惧怕。
而比之于女人们投身情爱场的思前想后、舍身忘我,男性世界几乎是扁平的,男人们也大多是自私的情欲动物。杜江对她始乱终弃;沈兆南嫖娼被抓,不知所踪;林国光也是连个招呼都没有就消失了。她的父亲,丝厂工人蒋大峰,惟一有点温暖感的男子,也抵不过情欲的诱引与人通奸,离了婚,最后一个人在出租房里孤独死去。
从《在长乐镇》里的唐小糖,到《桃花渡》里的阮依琴,再到《这半生》里的蒋云惠,池上在自觉建构着她的女性情爱世界。那浮世里的女儿心,说穿了也不过是遇一人以终老,安稳度世。然,最难不过遇合事,于是有了那一点点痴心,一点点怨念,再加上性爱照亮时的义无反顾和激情成烬后的形只影单。这一切,都没有逃过池上明亮的眼睛。
我揣想,池上写着这个叫云惠的女人的大半生故事时,脑海中是闪现过张爱玲、苏青这些书写情爱世界的前辈的身影的。苏青写《结婚十年》,尽是柴米油盐,笔端都是酱扑气,张爱玲写《半生缘》《沉香屑》,好歹有一个大时代作苍凉底色。她们的好处,都是展现了日常生活的密实针脚。而池上与这些前辈的迥异之处,乃在于她的眼光穿透生之表层,注视到了情感与人性的幽暗与曲折处,暗角虽小,亦是道场,经营得法,照样风生云起。
——这像是在说池上写作的将来气象了。她不机伶百变、弯弯绕绕,也不离地三尺、形上形下。从一开始读池上,我就觉得她不是那么凌厉,也不是那么“我执”。她的视野是开阔的,眼风是温和的。俗世的情怀,她有,拉开了距离的审视,她也有。
池上的小说篇幅,都有些长。她的短篇,不是那种灵光闪闪的“金短篇”,中篇呢,也是骨骼舒展,暗藏起长篇的命运感。就像门罗总喜欢写长一点的故事,这种文体,也是带着池上个人印迹的。她就这样絮絮叨叨、实实诚诚地给你讲故事,她就安于这样的身份——讲故事的人。按照本雅明的说法,有资格这么做的,都是经历过远方历险的。池上每讲述一个故事,焉知不是一次心灵的远行和归来?
我想,作为小说家的池上,是知道自己的这些颖异之处的。但她似乎又不满意于自己看世界的那副眼光,惟觉过于清浅,纯真,生怕让人看轻了去,总是想作些改变。其实池上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既然写作了,那还是让心顽固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