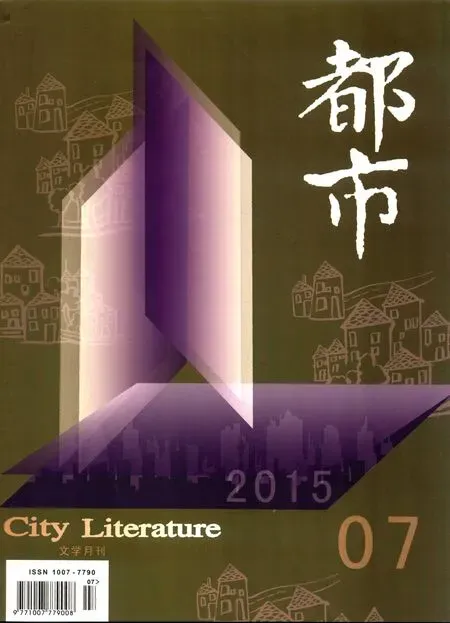故乡三记
2015-11-22韩振远
韩振远
故乡三记
韩振远
空宅院
曾经目睹游离在外的游子回到老家的情景,他们对故乡那份恒久不变的感情,对养育过自己老宅的痴情迷恋,让我感动。我理解他们的感情,自己却做不到,自父母故去,越来越不愿意回到我的老宅了。
我家的老宅足以让人自豪,不算太大,却有前后两进四合院,庭院深深,苔痕苍然,有这座院子在,说家里不富裕没人信。据我所知,我家祖辈从没有大富大贵过,充其量只能算个小康人家,建这样一座宅院,不知要积累多少年。我懂事时,这座宅院已有近百年历史。我家世代单传,到了我这一代,有兄弟六个,老宅渐渐盛不下这么多人,好在兄弟们都先后走出去,在外面成家立业。老宅也正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解体,在父亲的主持下,宅院被分成七份,我们兄弟各一份,另一份父母留下来养老。没几年,先是大哥分出去单过,拆了两间过厅。我结婚后,又拆掉大部分房子,仅留下一座南房,在原址建起北房和西房。老宅不在了,魂魄却寄托在了新建的房子上,兄弟们回来,踏进的是新建的房子,脑里萦绕的还是那个老宅。就连晚上睡觉,梦里出现的都是老宅的样子。
虽然经过改建,院子变了样,但我依然把它当老宅看。有几年,我在刻意美化老宅,在院里砌了花墙,栽上了葡萄、石榴和杏树,种上各种花草,春天来临,阳光照在院里,各色花儿开放,捧茶一盏,赏花品茗,会有一种其乐融融的感觉。清晨,鸟鸣树梢,晨露欲滴,院里清幽雅静,让人心神俱安。父亲退休后,与母亲一起回到老宅,我又拆了南房,建起新屋供父母居住。父亲更喜欢种花,将原来的东房基底很快经营成一块花圃,常邀二三老友,清茗一壶,薄酒数盏,几位白头老翁围几而坐,一边石榴火红,一边月季灿烂,小院里便有了仙境一样的感觉。
老宅的温馨到底没有留住父母,几年后,二老相继仙逝。老宅内除了美好的回忆,再没有可令我牵挂的。我搬离了老宅,先在县城里租屋而居,接着买下了现在的小院。在四合院里住了几十年,我的意识里潜伏着对小院的热爱,始终接受不了鸽子巢一样的单元楼。不料女儿假期回来,看见我还以为不错的小院,说:这叫什么院子啊!在女儿的心里,分明在用老宅与我现在的小院比较。
老宅从此大门紧锁。这三十间,老宅里的人一年年减少,先是我与四弟考上大学,离老宅而去。接着二哥将二嫂和侄儿侄女接到省城,后来,父亲又将母亲和两个弟弟接到山东,本来
想让我毕业后留守老宅,现在我也走了,老宅空空如也,竟连一个人也没有。
县城离村里不过20公里路,一开始搬到县城,过一段时间还要回去看看。也许是因为工作忙,也许是因为不方便,一年过后,回去的次数渐渐少了。等到有一天,与妻子走进老宅,我们都被老宅里的情景惊呆了。花圃东边的墙在一场暴雨后轰然坍塌,断垣残壁,一片狼藉。花圃内,杂草疯长,快齐腰高,其中虫鼠奔窜,连院里的砖缝里也长出了杂草。门、窗、墙壁都留下雨痕,走进屋里,尘土盈室,几无落脚处。我与妻子呆呆地站着,心里都生出一种荒芜凄凉的感觉。想当年,这里是多么幸福温馨的一个家,才一年多没住人,竟变成这样。
把这种感觉对朋友说了,对方哈哈笑,说:现在哪个村都有许多像你家这样的老宅,这叫空壳村。
我当然知道空壳村,也知道这是城镇化浪潮必然会出现的结果。但是从没有想过与自己有什么联系。经这么一说,顿时明白自己也是城镇化浪潮的一滴水珠。
老宅在村巷中间,我与妻子再回去,感觉空落落的,好像失去了什么。巷里看不见一个人,没有倚墙而坐,寒暄问候的老人,也没有嬉戏追逐的儿童,连鸡鸣犬吠声都没有,天空湛蓝,阳光灿烂,只在地上留下我们晃动的身影。这条我曾经走过无数遍的村巷落寞寂寥,几乎家家门户紧锁,只剩下巷头的小庙挺着一副呆板的面孔,替村人照看家园。
我从巷东头往巷西头数去,大狗媳妇去城里当保姆、庚红两口子在城里工作、七叔两口去北京给女儿照看孩子、与我家相邻的定有去西安打工,据说是炼地沟油的……算了算,原来20多户人家的村巷,竟只剩下三四个院落还有人住,而且多是老人,整条巷里,找不见一个年轻人,更找不见一个上学的孩子。走到巷头,碰上刚从地里回来的堂弟,说起村里的现状,堂弟说:你不知道,现在巷里连打扑克也凑不起一摊人。
又想起几位亲戚的空宅院,他们和我的情况略有不同,大表哥是个成功的企业家,腰缠万贯,几年前将老宅拆除,重建的房子气派豪华,却一夜也没住过。表哥明知房子再好也会闲置,所以这么做,只是一种心灵安慰。我曾和他开玩笑:大概只有等你百年后,才会在这里睡两三天。表弟也将老宅拆了重建,目的只有一个——发落老人。果然,三姨故去后,这座新建的院落派上了用场,除此,谁也没在里面住过一天。几位作家朋友有些例外,用他们并不丰厚的稿酬,在家乡建起房子,只是效仿陶渊明“复得返自然”,在家乡平静祥和的气氛中写作,据我所知,房子建成后,他们没有一个在其中居住过,更谈不上在里面写作。
后来每到一个村子,都会留意这种现象,发现,一个村子里最气派的院子和最破败的院子,往往都是空宅。气派的,是在外发达了,要在家乡光宗耀宗,并非真要居住;破败的,则和我一样,不打算再回到老宅,要把乡村的根彻底拔掉,任其在风吹雨蚀中败落。
我回老宅的次数越来越少,仅仅只有20公里路,一年也就在节日回去两三次,有时候即使有事路过,也是过家门而不入。难道对老宅没有一点感情?后来终于想明白,没有炊烟味的家不是个家,没有人的院落更不是个家。老宅,只是个留下记忆的院落,再也不可能给人以温馨。这可能是我不愿意回到老宅的原因。
孤独的轩轩
岳父家四世同堂,轩轩是我的晚辈,中间隔一代人。我住城里,他住乡村,一年也就见那么两三次吧。即使偶然一见,他也不会主动和我说一句话,多是他玩他的,对我的问候不闻不顾,若我亲切过度,他会闪着一双惶恐大眼不知所措。随后,迈着小腿一溜烟地逃离。
轩轩极可爱,红扑扑的小脸,明眸皓齿,才九个月时,就能满地跑,像个会挪动的玩偶一般招人喜欢,却不爱说话,认生。别的生人与他无关,偏偏我这个生人是他的长辈,又喜欢他摇摇晃晃的样子,一见面,不是要抱抱,就是举起来在半空中晃,结果,每次轩轩都不高兴,在我手里挣扎扭动,眼看就要号啕大哭时,我不得不将
他放下来。双脚一着地,轩轩又一溜烟逃,躲到一边独自玩。轩轩没什么玩具,随便逮住一样东西,只要他喜欢,都能玩得聚精会神,比如他太爷爷的药瓶子,他爷爷的钥匙链,而且不耐烦大人指点,仿佛从小就要做自己的主。
每次见到轩轩,都觉得他长大了一些,话少了一些,好像从生下来那天起就在默默玩。对我的话,他感兴趣的很少,后来,我知道轩轩对什么话最有兴趣,每次见了都问相同的话。问:妈妈呢?轩轩黑豆一样的眼里立刻会放出光,说:上班去了。又问:爸爸呢?轩轩又答:上班去了。再问其他话,轩轩仿佛听不见,只顾玩他的。轩轩人小,嗓门与同龄的孩子一样稚嫩,说出的话却不属于这个时代,都是从他爷爷奶奶那里学来的,比如他说的上班,其实是外出打工。他爸爸妈妈没结婚时在外面打工,结婚后有了他还在外面打工,一个在青岛,一个在离家乡不远的一座小城,只有逢年过节才回来看一下。轩轩从出了满月能离开妈妈开始,就由奶奶带,一直带到现在,轩轩都四岁了。
轩轩的爷爷长我几岁,是我的大舅哥,此人脾气极倔,偏偏老婆也脾气火暴,一辈子打打闹闹、寻死觅活从没消停过。到大舅哥52岁那年,一番昏天暗地的打闹,两败俱伤,从此势同水火,竟开始分居。家里人本来就少,连同轩轩一共也就三口之家,却两张灶台,各做各的饭,连生活用具也分得清清楚楚,只有轩轩是共同的。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两个人做饭,不管自己喜不喜欢吃,全看轩轩口味。吃饭时,两张饭桌分别摆在两间屋里,那边喊:轩轩,爷爷蒸了红薯。那边喊:轩轩,奶奶煮了红枣。轩轩摇摇晃晃两面跑,有时把奶奶的饭端到爷爷这边,有时又把爷爷的饭端到奶奶那边。这么过了有几个月吧。一次两边都做好饭,轩轩不想两边跑了,噘起小嘴拉着爷爷的手,非要让爷爷也坐到那边一起吃,不去,就哇哇哭。大舅哥尴尬地站在院里发呆,屋里,他奶奶早就泪水涟涟。等坐在一起,他奶奶含着泪说:要不是轩轩,这辈子不理你。话是这么说,其实除了轩轩是共同话题,夫妻之间还是没话,后来,大舅哥也出去打工,轩轩就成了他奶奶一个人的了。
轩轩的活动范围很小,基本上就在大舅哥的院里。另外可以去的地方是他太爷爷家,也就是我岳父住的院子。岳父母都是80多岁的老人,反应迟钝,有时,轩轩都在屋里玩了好一会,才看见一个小小的人儿默默坐在一旁。岳父曾在外地当过几十年工厂厂长,是个有文化的人,看见轩轩来,就想和曾孙子说说话,教唐诗宋词之类,轩轩总没有兴趣,来这里,只因为再没地方去,所以每次都这样,无声无息地来,无声无息地玩,玩够了,又无声无息地回去。
去年,轩轩上幼儿园了。我回乡下,看见他在纸上涂抹,神态极认真。近前看,画得是两个歪歪扭扭的人儿,我指着画上的人问:这是谁?轩轩说:妈妈!不用再问,另一个肯定是爸爸。
大舅哥先在西安打工,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居住的这个小城,在一个建筑工地当小工,干了三四个月后,突然来到我家,一副心身俱疲的样子,说儿子儿媳闹意见,看来要离婚。我马上想到了轩轩,问:那轩轩怎么办?大舅哥叹一气说:谁知道?听媳妇的意思,好像不愿意要轩轩,人家还年轻,想在那边利利索索再找个好人家。
大舅哥说完,喃喃自语,说:轩轩有一年多没见过他妈了,媳妇要真嫁那么远,轩轩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他妈。
远去的耕牛
走进乡村田野,看见拴在墙角下反刍,或者田野里躬耕的牛,会油然生出一种亲切感,如若正当暮色四合,农人赶牛缓缓归来,这种感觉会更强烈。不光要站住仔细看,还会拍照,与主人交谈。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感受到熟悉的田园风情,仿佛回到从前。在我的记忆中,耕牛是田园风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是因为现代乡村,耕牛实在是少见了,看见一头牛,会像看见珍稀动物一样。即使在我们这片有五千年农耕史、土地平坦肥沃的地方,看见一头耕牛也不容易。
牛是一种体型庞大的食草动物,力大而且善良温驯,新石器时代被人类驯化,从此成为人类从事农耕活动的最好帮手,陪伴人类走过了
漫长的农耕文明。说起牛往往会联想男耕女织的农家生活,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中国人甚至把牛与妻子儿女连在一起,成为理想生活的标志。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牛还具有象征意义,代表着吃苦耐劳,坚韧有力,吃下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几年牛又和强劲、有气势联系起来。比如牛气,说谁牛B可不是骂人,话语中一定充满赞叹。牛的另一个特点是沉静,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还会发现,若出现牧牛、牧童之类的场景,往往会带着几分神秘,让人想到隐逸生活,接下来必有异人出现。《三国演义》中,刘备在襄阳险遭谋害,乘的卢马跃过檀溪,等心情平静下来,看见的首先是一个骑在牛背上的牧童。“{刘备}迤逦望南漳策马而行,日将西沉,正行之间,见一牧童跨于牛背上,口吹短笛而来。”这情景,让人在领略美丽田园风光之际,又感觉到几分神秘。接下来,果然就出现了异人水镜先生。罗贯中的这种描写,可能与老子有关。老子是道家始祖,当年西出函谷关,坐骑就是一头青牛。
对于以耕作为业的乡民而言,牛则是实实在在的,“大田耕尽却耕山,黄牛从此何时闲?”杨万里的这首诗,说的是春天到来农事开始繁忙,却能看出牛在农耕活动中的作用。至今还记得,村里谁家买回一头大健牛是件很荣耀的事,不光自己自豪,别人也会羡慕。二十多年前,从我们这里的乡村经过,还能看到“穷巷牛羊归”的景象,如今,羊偶尔还能看到,牛没有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里的牛一天天稀少,田野里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隆隆作响,机械让农活变得轻松起来,牛成了累赘的同时,乡村一天天浮躁,田园风情一点点消失。
几年前,我去黄河岸边的一个村子看朋友,再次看到了他家门前拴的那头老牛。每次来他家,这头牛都悠闲地卧在门前,嘴里像含着口香糖一样,不停地嚼动。这牛是他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养的。朋友说如今做农活早就用不上牛,父亲养牛,纯粹是一种精神寄托,和城里人养宠物基本没什么区别。朋友的父亲是个精神矍铄的老人,脸色黝黑,皱纹纵横,见我看他的牛,老人的话里带着几分忧伤,说这牛是牛里的老党员。见我不明白他的话,解释说:这是生产队时期的牛,实行责任制时还是个牛犊,八十块钱买的。这牛一死,全中国可能都找到不集体化时代的牛了,你说,不是老党员是啥?听了老人的话,我哈哈笑。老汉又补充说:不光是集体化时代的最后一头牛,恐怕是方圆几十里内的最后一头耕牛。
再早几年,朋友曾多次动员父亲把这头牛卖了,老人也同意,因为现在耕作完全用不上牛。可是,每次买主来,老汉都要先问人家把牛买回去做啥,结果无一例外,全是宰杀后卖牛肉。老汉也无一例外地拒绝,他不忍心让他的牛变成盘中餐,以后,照例精心饲养,白天要为牛割草,半夜要起来添料。只是再没有买主上门买牛,这牛太老了,不光干不了活,杀了吃肉也没人会要,只能等着一点点老去。
我离开时,老汉仍在门前,梳理着老牛光滑的皮毛,一副怜爱不已的样子。
朋友很理解父亲的感情,对我说:前十多年,曾看见父亲一边赶牛耕作,一边和牛说话,那语气,那神情,好像比他这当儿子的还亲近些。现在,这牛老了,若是人,该有八九十岁,一旦死去,且不说父亲有多悲伤,以后,村里的孩子可能知道牛肉、牛奶,却再看不到活生生的牛了。
其实,乡村的年轻人并不在意牛的消失,在他们的世界里,耕牛消失是自然而然的事,就连我对耕牛的感情,也仅局限于田园风光,对于牛在中国漫长农耕史上的作用并不特别留恋。
走出朋友家,从乡村小路上再度领略田园风光,田野里,风光依然旖旎,几位农人还在劳作,庄稼还是那么翠绿,却给人感受却分明和以前不同,心想,以后,在繁重的劳作中,陪伴在他们身边的也许只有突突作响的机器,再也没有可以吆喝交流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