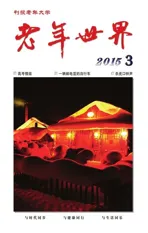父亲的味道
2015-11-20毛君秋
毛君秋
进入耄耋之年的父亲,在把他的几个儿女安顿成家后,终于清闲下来了。开车去看他,回程时总是要叮嘱一番。刚刚到家,他的电话就打来了。放下电话,我总能想起他慈祥的面容和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腥膻味。
父亲13岁当缝纫学徒,后来成为附近村子最有名的裁缝。父亲最拿手的是做“皮货”,那是一般裁缝不会接的活儿。那时的“皮货”都是原生态的,以羊皮为主,所以闻起来有一股浓浓的腥膻味。做皮衣很麻烦,也很讲究。父亲做皮衣最看重三道关键环节:量、裁、缝。他给顾客量尺寸,前后左右的一些重要部位都会细细地量了又量。他做皮衣不用剪刀剪,因为羊皮比较厚实,还容易把皮上的绒毛剪掉,他用一种专用皮刀裁,也不能用缝纫机,缝纫机的针根本穿不过,只能手工一针一线地缝。
每逢过年,我家便是最忙的。村里大人牵着小孩或扶着老人像赶集似的,往我家里走。前脚还未搭进门就喊:毛师傅,没得办法,帮忙给我家老爷子和小孩子做两件衣服。看着案板上堆成小山一样高的料,父亲皱了皱眉头,憨厚地笑了笑,收下了。
“皮货”主儿都是要过年穿的。吃过晚饭,父亲把煤油灯玻璃罩子擦得通明,把皮刀磨得锋利无比。母亲在屋角生起一盆炭火,全家人便开始忙碌起来。父亲戴着老花镜伏在案板上,一会儿用划粉和竹尺在皮面上比划,一会儿用刀子把羊皮划得嚯嚯响。姐姐坐在缝纫机前缝衣服,母亲拿起针线给衣服绞边,我和弟弟就着案板的一角做作业。屋子里只听见哒哒哒的缝纫机声和嗤嗤嗤的皮刀划破羊皮的声音。羊皮散发出来的那一股特有的腥膻味儿与炭火燃起的味儿搅在一起,时时会有一股温暖洋溢在心里。
有时半夜过了,我睡一觉醒来,发现父亲还在弓着腰身,眼睛凑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缝皮衣。头上稀疏的发丝在亮光里清晰可辨,微弱的炭火在角落里一闪一闪,羊皮的腥膻味儿在屋子里萦绕。
一年冬天,我在市师范学校读书,父亲去看我。把他带到寝室,他身上那股不一样的味儿,感觉特别难闻,斜眼瞟见一个室友还偷偷捏了鼻子。送走父亲时,我说:你以后少来。从此,父亲再也没来过。
后来成家了才慢慢体味到,父亲凭缝纫手艺维持着全家的生计,还供我们兄弟几个读书,是多么不易。父亲一生做了多少件皮衣,却没有一件是自己的。可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那是一种幸福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