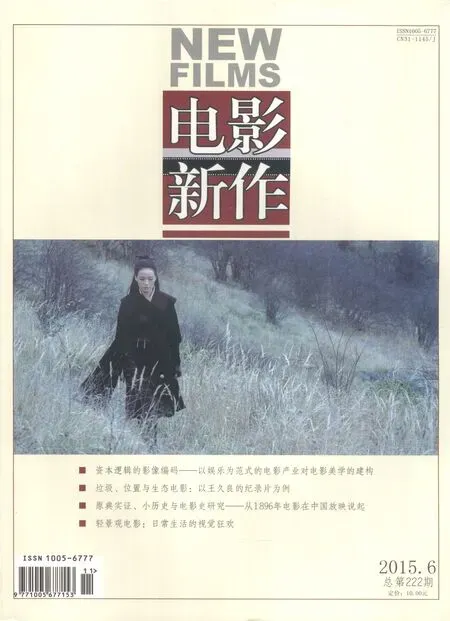资本逻辑的影像编码——以娱乐为范式的电影产业对电影美学的建构
2015-11-20段运冬
段运冬
资本逻辑的影像编码——以娱乐为范式的电影产业对电影美学的建构
段运冬
近20年以来,电影美学建构的窘困不断明显。越来越强势的电影产业需要新的理论演说,而电影美学(包括电影理论)似乎与电影产业的发展呈反向发展。在开阔视野之下,吸纳新近相关成果,在文化产业之资本逻辑下,思考以娱乐为核心范式的美学建构,从而在新的社会语境下构想影像美学建设的可能性,突破过往以先锋艺术形态为支点的电影美学形态。
资本逻辑影像编码娱乐电影产业电影美学
一
电影美学与电影产业的非均衡发展一直是产业界与学术界的矛盾问题。一方面,电影产业在急速发展(最少对于近10年来的中国电影产业来说),电影生态中诸种构成元素的新风貌在不断涌现。另一方面,电影理论自身无法更新自己的知识观念,久而久之,把自己逼到了异常尴尬的位置。为此,当代批评家本雅明·布赫洛①,毫不含蓄地指出:
对于批评功能的废除,仿佛是在以电影批评与影视业的关系为蓝本。在该领域,大部分批评家长期以来不过是工业机构豢养的傀儡,即使偶尔会有一个孤独的声音来反对这种花钱买来的众口一词的喝彩,对一致而强大的被远程操控的赞同表示异见,这一行为也只会被大众当成是病态的,或者干脆就置之不理②。
布赫洛教授是站在艺术批评的角度,对电影批评的现状做了批评与讽刺。这对于谋命于电影学术的“知识生产者”来说,即使有种种的不爽和无奈,纵使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个学术努力,都也无法对这种现象进行反驳。因此,电影的产业发展与美学建构的撕裂,不仅让西方学者痛心疾首,也是我国电影学术界的共同难题。
在我国的语境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产业角度对此问题进行真正的回应,最早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电影娱乐性带来的对电影产业的呼唤对计划体制的突围,新世纪以来,产业作为电影发展方向被确立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之后,电影学术的焦点进一步迈向对电影产业经济的关注。有意思的是,在产业化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对电影资本增值的过度关注,又导致了影像文化属性的缺失,尤其是在影像的“国家性”与“文化价值”方面,较为突出。这样,“主流电影”“国家形象”“文化价值”的讨论成为学术界对产业实践的矫正。当然,随着电影产业中众多偶发性热点的出现,接着又出现了“低成本”“微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走出去”等等,诸如此类,话题繁多。总的来看,中国电影产业与电影学术的研究是在呼应着传统文化大国复兴语境下,现代国家的文化身份的建立,这种建立包括了产业机制③、艺术的自身建设,以及电影学术自身的反思。
电影产业与电影理论发展之间的尴尬,不单单是我国电影学术的窘困。欧美学术界里(或英语文献)亦为如此,都在纷纷努力,致力于文化产业的美学之间的归纳与总结,试图弥合两者之间不平等的比势关系,更新或者升级电影学术对产业界实践的阐释能力或者阐释体系。电影产业对美学的建构,最初发轫于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霍克海默、阿多诺),他们的研究被称为批判性的媒介研究。即便是带着敌意的有色镜,在他们的著述中,除了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之外,真正涉及并讨论电影的,寥寥无几,只字片语。
依据产业实践进行理论构建的,体现于好莱坞的研究,出现了把美学与电影工业整合在一起的努力,诸如作者论、电影类型、主流影像的观看机制,等等。但是,从产业实践带来的这些电影美学的构建,都是50年前的学术成果。此后,即便出现了一波一波的“重建电影研究”,出现过基于产业反思的努力,有效的建构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或者有效的建构性仍然不够理想。
有意思的是,产业研究的突围最早来自于跨学科的社会学与人类学。据电影学者孙绍谊的考察,英语世界里,最早从产业考察电影的是社会学家里奥·罗斯顿(Leo C. Rosten),他于1941年出版了《好莱坞:电影殖民地和电影人》(Hollywood: The Movie Colony, the Movie Maker,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紧接着,人类学家霍顿斯·波德梅克(Hortens Powdermaker)于1951年出版了《好莱坞梦工厂:人类学家眼中的电影制作人》(Hollywood, The Dream Factory: An Anthropologist Looks at the Movie Makers,Boston: Little Brown)。随后,霍拉斯·纽康姆(Horace Newcomb)和罗伯特·埃利(Robert Alley)的《制片人之媒介:与美国电视创作者对谈》(The Producer’s Meidium:Convertations with Creators of American TV,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的《黄金时段节目考察》(Inside Primetim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83)、道格拉斯·戈梅里(Douglas Gomery)的《分享的愉悦:美国电影放映史》(Shared Pleasures: A History of Movie Present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2.)、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信息时代的好莱坞:银幕时代的超越》(Hollywood in the Information Age: Beyond the Silver Scree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4)④等等。当然,从笔者的学术经验来看,在美国学术界里,还有一人,该文未曾提及,这就是来自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提诺·巴里奥(Tino Balio),他属于美国较早进入电影产业以及产业史研究的学者,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他不仅很早开始电影产业的研究,而且还参加由美国国家人文基金组织撰写的美国电影通史工作,负责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电影史《作为现代产业企业的好莱坞,1930——1939》一卷的撰写。应该说,他在美国电影产业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纯粹从电影产业的角度出发,对于我国的电影学术界,还要提到的是上世纪50年代解放初,作为“反面(敌对)知识”出版的两部关于好莱坞电影产业的研究的专著。这基本上奠定了中文世界里,电影产业研究的学术视野。
新世纪以来,电影产业的研究得到极大的改观。来自于美国西海岸的电影学学者,利用毗邻好莱坞的优势,继承了电影的产业研究。其中以加州大学教授(UCLA)约翰·卡德威尔(John T. Caldwell)和加州大学河畔分校教授托比·米勒(Toby Miller)的为代表。约翰·卡德威尔出版了《制作文化:影视产业的反省意识与批判实践》(Production Culture: Industrial Reflexivity and Critical Practice in Film and Televisi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后来还参与主编《生产研究:媒介产业的文化研究》(Production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 of Media Industries,Routledge, 2009),2013年还在美国电影与媒介协会的刊物《电影杂志》(Cinema Journal)刊发《超越产业:好莱坞外包研究》(Para-Industry: Researching Hollywood’s Blackwater, Cinema Journal, 52: 3)一文⑤,成为“生产研究”的带头人,从而奠定了自己在电影产业研究上的领军地位⑥。托比·米勒是一位高产的学者,撰写、主编30多部著述,发表了上100篇文章,其学术思考遍及电影理论、电影产业、媒介产业、文化政策、电视研究、文化研究,甚至公民文化素养,相关的成果诸如《全球好莱坞1、2》(Global Hollywood 1、2, British Film Institute, 2001、2004)、《当代好莱坞读本》(The Contemporary Hollywood Reader,Routledge,2009)等等⑦,均为该领域的重要著述。另一批值得提及的学者来自经济学领域,包括营销、产业经济学的专家,也推动着电影产业的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约书亚·艾利夏伯格(Jehoshua Eliashberg)就是这样的代表,他对媒介以及娱乐产业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刊发了《电影产业:实践、当前学术,以及新研究方向的批判性问题》(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Critical Issues in Practice, Current Research and New Research Directions,Marketing Science, Vol. 25, No. 6, Nov.-Dec. 2006)、《从故事线到票房》(From Storyline to Box Office: A New Approach for Green-Lighting Movie Scripts,Management Science, Vol. 53, No. 6, June 2007),等等。
对电影产业学术史的简要回顾,我们发现,电影产业与电影美学的关系,一直是电影产业研究中弱势领域。究其原因,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产业实践与美学构建之间无法搭建有效的沟通桥梁,经济的实践话语无法及时与审美的诗性话语相结合,从而使产业研究主动地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拱手让给了社会学或者是人类学。另一方面,实践诉求与美学追求不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实践诉求总是瞄准资本的盈利与增值,而美学追求则更多关注故事文本自身与审美体验的共振。而对于产业实践来说,审美共振只是实践诉求的一种手段而已。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电影产业实践与美学分析所形成的相互孤绝互不相干之态势,美学活跃的地方最后只被锁定在实践结束后的文本领域⑧。
二
既然产业与美学的隔绝状态已经是产业信息与美学信息相互交流的壁垒,那么如何打通产业与美学的隔绝状态呢?显然,我们得在它们之间寻找一个中介,这个中介一边联通着产业实践,一边挑起了审美机制。这种努力,在最近的学术成果中得以体现,陈国贲(Chan Kwok-bun)在《视觉考古学》杂志撰写了《娱乐:快乐还是斗争?》(Entertainment: Enjoyment or Struggle?,Visual Anthropology,182005:97-102),把建构的目标锁定在“娱乐”一词上。Vassilis Dalakas 、Jeff Langenderfer 的文章《消费者电视欣赏的满意:娱乐产业洞察》(Consumer Satisfaction with Television Viewing: Insight for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Services Marketing Quarterly,Vol. 29[1]2007)同样把产业语境下的连接中介放在了“娱乐”一词之上,只不过多出了“消费者”。彼特(Peter Vorderer)、克里斯托弗·克里姆特(Christoph Klimmt)、尤特·利特菲尔德(Ute Ritterfeld)撰写了《愉悦:媒介娱乐的内心》(Enjoyment: At the Heart of Media Entertainment,Communication Theory,14:4[November,2004]),提出了另外一词:“愉悦”。甚至,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克里斯托弗·克里姆特(Christoph Klimmt)等人将之运用于游戏的分析上,提出“媒介愉悦”之说⑨。更为有意思的是,身体美学的主要代表人分析美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也加入了这次讨论,他在《英国美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上发表了《娱乐:为美学的一次提问》(Entertainment:A Question for Aesthetics,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Vol. 43[3], 289-307)一文,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显然,“愉悦”,或者与之意义近似的“娱乐”“快乐”成了当下产业环境下建构电影美学的。舒斯特曼指出,“近期一个愈加重要的美学争论,涉及艺术地位与流行艺术的文化价值。正是因为流行艺术才是今天多元社会里被大多数人所消受的艺术,对于文化民主来说,其地位非常关键”。但是,这些有价值的问题都被“左派”知识分子(巴赫金、葛兰西)处理成为防御的对象,甚至连一些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诸如西奥多·阿多诺、汉娜·阿伦特、皮埃尔·布尔迪厄等人,也把自己的敌意送给了流行艺术。更有甚者,自柏拉图⑩开始,来自哲学与美学的观念,就把与流行艺术相一致的审美快感,特别是娱乐,当成高雅艺术的对立面,甚至是美学的敌人。但时至今日,流行艺术铺天盖地,审美功效越来越强大,如果跳出“左派”与保守知识分子划定的防御性保护圈的话,它的确能够“获得真正的美学价值(aesthetic merit),提供与之相配的社会回报”。显然,在突破柏拉图式的错误归纳方式之后,如何在新的知识理念下去讨论“娱乐”“愉悦”,以及展开对它们的研究,这成为一个新的话题。
为此,舒斯特曼另辟蹊径,在回顾了西方美学思想史对跳出传统美学或者哲学的观念,从“社会向善论”(meliorism)的角度出发,重新反思与推演了娱乐的美学意义。他指出,“快乐(pleasure),如同真理一样,有助于构建我们的神圣感觉,都能建立或者强化我们最深的价值观”。“对于这种存在着的消极感觉,现代经验论,仅仅是以对客体体验的个人精神世界去理解快乐(体验更为普遍)。这样的设想,快乐好似微不足道。但是快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消极感觉,正如亚里士多德认识到的那样,它更多的是所有事物的品质,通过把活动做得更有滋有味更富有价值,提升活动本身所涵盖的兴趣,从而去‘完成’或促成这些活动”。为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审美快乐和娱乐微不足道化,因为它们以许多有意义的方式在生命的维系、意义,以及丰富性方面发挥着贡献”。
超越传统哲学观念,重新对人类生命中娱乐(审美快乐)的意义与价值进行承认,这不仅暗示了西方学术语境电影美学的转变,而在我国的香港也有回应。香港浸会大学(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社会学的陈国贲教授在文章《娱乐:快乐还是斗争?》中指出,“娱乐首要地是什么呢?来自台湾焦点公司(Focus Group)的成员告诉……电影很少关注于意识形态、真理、现实问题;更多关注的是盈利的兴趣以及物质利益,它们拍摄出来去开拓消费者的欲望与幻想,这些才是原初的天然的商业主义、物质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就这样纯粹而简单”。由此可知,被传统哲学所鄙视的“娱乐”(包括与之伴随的审美快乐),已经从被鄙视的“丑小鸭”状态走出来,进入了美学研究中的“白天鹅”阶段。
其实,对于电影美学来说,即便“娱乐”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成为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式,那么我们又如何去思考这个美学范式或者哲学问题?虽然快乐是产业与美学的联系中介,但是美学需要的是哲学思维,而产业则受控于资本,亦即如何在美学的哲学思维中,或者娱乐的哲学化中,将之与资本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也是制约电影美学建构的难点所在。为此,我们需要简要地回顾电影美学的建构历史。
和娱乐在哲学知识传统的境遇相似,我觉得传统的电影美学,其构建问题也存在两种态度。一种是精英的艺术知识分子态度,这个传统起源于法国。早在1906年,乔治·梅里爱发表了《电影摄影术之思》(Cinematographic Views);接着,意大利人里西奥托·卡努杜于1911年发表了《第六艺术的诞生》15,自此直到经典电影理论的集大成者安德烈·巴赞、电影黑格尔之称的让·米特里,几乎均是精英知识分子。有的是艺术的激进者,比如卡努杜本人就是未来主义诗人,而巴赞本身就是现象学的忠实信徒。这样的情况,在苏俄亦毫无例外,库里肖夫、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等等,在共守着电影作为教育与宣传社会主义民众之精英理想的同时,他们背后都有着20世纪早期各种前卫艺术流派,诸如未来主义、构成主义之理念作为支撑。显然,这个传统是排斥娱乐的,排斥产业的,他们最为心仪的不是商业的盈利,而是现代派的各种艺术理念的实验,获得“纯粹的艺术精神”。电影美学充斥着理论构建者所具有的从事这种艺术的理想、激情、冲动。
从电影媒介的角度,发现电影产业中,经过产业建构了的电影文本之美,是对好莱坞电影的言说。尽管巴赞曾经分析过美国的西部片,但仅仅是直觉,而察觉到的也只是古代神话叙事体系在西部片的体现,深入的美学关注并不是他的全部。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时期,又是一个法国人注意到了电影中的快乐,并将之联动着电影的产业的现象进行阐释。这个人就是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他在20世纪50年代连续出版了两本电影著述《电影,想象的人》《明星》,其中提到的“电影,作为飞行器”(the cinema, the airplane)“明星与占星术”等观点,与经典的法国电影理论差异巨大,表面看似天马行空,却慢慢地把研究对象从先锋性艺术转到了通俗的由产业操控的艺术样式上,得出不一样的观点,逐渐趋近电影的产业逻辑。
此后,电影类型理论、作者论,开始触及了电影产业与电影美学的构建问题,并从不同角度,诸如文本风格、导演,甚至过渡到了明星(包括与之相伴名流、绯闻研究)、电影节等,对电影产业里的各种产业机制进行研究。当然,也有的理论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世俗神话、白日梦幻等观点。
有意思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来自哈佛大学的哲学家兼电影理论家斯坦利·卡维尔,也注意到了好莱坞电影中的一些商业现象。他在《看得见的世界:电影本体》一书中,对美国的商业电影,发出了比较精彩的评说,提出自己的观点:
电影的本体论条件表明,电影本质上就是色情的(当然并不是色情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成百万个电影镜头结束的时候,是在衣服背后的拉链刚刚拉到底,或者是一个女人恰好在她的袍子落地的一刹那间走进淋浴室的门背后,或者是一件衣服掉在一动不动的摄影机面前——这些并不是突然的诱惑或者色情的旁白,而是满足一个无法避免的需求,尽管只是部分地满足。全世界的海斯办公室都无法禁止这种做法,而只能强制影片在这个时刻中断。
随后,斯坦利·卡维尔还注意到电影如何把军人与女性缝合进了观看系统,认为这是电影媒介特有的逻辑之一。他这样论述到:
如果电影边线群体性的典型参与方式确实是通过男性的友谊(而不像小说和戏剧那样通过家庭);如果女人确实示范群体的(因为他们干扰友谊);如果外来的女人(即性感)和电影上的妻子(缺乏性感)除了例外不能复制,而这又会进一步干扰群体,那么我们最好是不要过于匆忙地来为电影规定道德规范吧。
其实,所列举的只是斯坦利·卡维尔的部分论述,但是基于电影媒介,将受产业(资本主控)的文本编码活动,上升为电影本体论问题,这是他的最大贡献。但是,通读斯坦利·卡维尔的著述,从产业与娱乐的角度建构美学,仍然还只处于探索之中。
时至今日,不论前辈所做努力如何,娱乐、审美快感、电影产业、资本逻辑、大众文化,已经将电影产业对电影美学的建构问题,再次推到学术界面前。如何依据产业与美学显现出的新的共生关系,提升电影理论的研究室成为电影理论的当务之急。
三
如前所述,电影理论的当务之急是对电影产业建构电影美学的回应。我们将之转换成另一句话进行回应,就是探寻电影文本里的资本表征、产业的资本逻辑,如何以故事的形式缝合与调动观众的情感。这样,工业化的福特主义,如何体现甚至转换为文本意义的参数式编码,以及众多被资本编码之后的美学呈现方式、美学范式的形态。这也许是产业建构美学的核心诉求。为此,我们以德国艺术史学家汉斯贝尔廷的一句话作为开始:
随着教育人们对文化应尽的义务失去耐心,希望把文化变成为一种娱乐,而娱乐的目的不是开导人,而是令人惊喜,娱乐应该激起一种轰动事件,在这个轰动事件中,我们参与了我们某种不在理解的活动……艺术不再严格地、令人难以接近地代表文化和它自己的历史,而是参与各种纪念仪式,或者根据观众的文化水平参与各种娱乐性的歌舞杂耍演出,在这些演出中,文化被请求重新登台演出。
来自艺术史学科的汉斯·贝尔廷指出了两个关键点:文化变成了娱乐、艺术变成了杂耍演出。其实,不论是文化变成了娱乐,还是娱乐本身就是艺术机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这在电影媒介起源时就是被确认了的事实。对于这个被确认的事实,斯坦利·卡维尔是这样表述的:
电影是用什么方式满足这个神话呢?我们的回答是:自动地……它的意思是:不用我做任何事就能满足,靠希望就能满足。一句话:魔术般的……因为电影起源于魔术;是从世界下面来的。
客观地说,斯坦利·卡维尔把电影媒介的特性与神话、与魔术相联系,是颇有启发意义的,甚至认为媒介性(或者媒介的美学性是起源于下面的),对于重新思考电影美学,在方向上是颇具有启发意义的。但是,不论是“魔术”,还是“从下面来的”,其实都是在一个产业环境下,媒介的特定逻辑与人类的原始情感的切合。这个切合点就是:娱乐。
可以说,娱乐话语整体进入文化层面还与现代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民众生存质量逐渐改善有关,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休闲成为生活一部分,“随着享受闲暇的人越来越多……娱乐也开始逐步采用大规模生产技术……最令人瞩目和疯狂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大规模闲暇活动,所有这些活动中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们使人惊奇、兴奋并得到放松,但是它们既不能使人的理性和感情得到深化,也不会允许自发的情绪得到创造性地发泄”。随着休闲的出现,娱乐成为当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也许尼尔·波兹曼针对的是电视,但对电影来说,同样面临如此问题,娱乐元素被扩容,而与娱乐相反的东西被消解。甚至,有更为激进的观点出现,还发展到了“娱乐至死”的程度,出现了“反交流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在美学中,这种理论被称为‘达达主义’;在哲学中,它被称为‘虚无主义’;在精神病学中,它被称为‘精神分裂症’。如果用舞台术语来说,它可以被称为‘杂耍’”。
在人类自身情感的表述中,社会现实要具有娱乐功能,需经过仪式化处理。英国学者戴维·英格利斯曾言,电影院也如同一个场所,这些场所被划分出来,区别于日常平凡和世俗事务,在其中日常生活世界被关闭在外,因此在里面的人们会感觉他们正在体验的事情有些“特别”并不那么普通25。社会现实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戏剧冲突,永远只是“生活故事”,要上升为“电影故事”,需找到一条二元对立的主线,让观众在故事的正反跌宕中体味情感,最终发生价值的正负转换。为此,娱乐就得跨越“社会现实”与“影像机制”之间的鸿沟,削平它们之间的张力。电影的主要功能是缝合观众与现实逻辑的间离效果,强迫观众认同影像的幻觉机制,现实必须打破自身的逻辑结构,进入神圣化、仪式化、狂欢化、催眠化的阶段,通过乌托邦式的梦幻机制替代现实的缺省。这一点,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是按摩”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发现,日常生活结构与新的传播媒介确实类似。‘日常性’是必然的基础,即使否定这一点的影片也必然与它为起点”,然而“日常生活确实是盲目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存在通常丧失了确定意义,或者说,远离了确定意义”,作为“一种趋向程式化的陈陈相因的存在”,难道“电影的天赋、巨大的贡献和被征服的新大陆就是这一切平平淡淡的习俗、司空见惯的功能和单调的过程?”
当然,电影的娱乐是置放在产业化的环境下完成的。作为现代化生产体制,新的工业化生产流程或者程序化管理流程中,新的工作环境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审美观,即“工业中的人际关系的新意识形态”,“总体设想就是要达到这一效果:为使工人快乐、有效率并乐于工作。”这种体悟打破了传统手工艺带来的工作经验,亦即“乔治·米德(George Mead)将这种美学上的体验表述为一种试图‘捕捉住寓于一项任务的产出品的完美性当中的乐趣,并把这种快感传递到工作的对象和工具之中,传递到为了成功地实现这个目标而必须做的各种活动之中’的力量”,为此,现代电影产业迫使“在所有涉及人格市场的工作中,人的品格和个体素质变成了生产手段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个人便使其个人的内在特点工具化和外在化了。在一些白领工作中,人格市场的兴起已使自我和社会的异化达到非常极端的程度。”显然,工作已经被现代工业化语境下观众机械化的情感体悟遮掩,工作只是谋生的需要,工作之外的快乐远比工作更重要。我想,这就是娱乐社会性存在的原因。
此外,工业社会还催生了一种新事物——休闲,亦即闲暇时间的富裕。“闲暇只是在过去的50年才成了得以普遍享受的东西……随着享受闲暇的人越来越多……娱乐也开始逐步采用大规模生产技术……美国社会最令人瞩目和疯狂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大规模闲暇活动,所有这些活动中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们使人惊奇、兴奋并得到放松,但是它们既不能使人的理性和感情得到深化,也不会允许自发的情绪得到创造性地发泄。”随着工作理念的改变、富裕时间的出现,娱乐成为当下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工作内涵的改变和闲暇时间的出现,带来了消费文化的盛行,“文化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它关心的是如何花钱、如何享乐……注重游玩、娱乐、炫耀和快乐”。就像博德里亚指出的那样,消费成为一种“神奇的思想”,它是“一种决定日常生活的奇迹心态,是一种原始人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意义是建立在对思想具有无比威力的信仰之上的:这里所信仰的,是标志的无比威力。富裕、‘富有’其实质是幸福的符号积累”。显然,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是一种符号幻象,现实的真实意义永远让位于符号的虚拟意义,感官快乐主义是其首要原则,他们隐匿于电影、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中,极力追求身体的修饰和性的愉悦,“娱乐至死”成为他们内在的快乐动力和口号,亦即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所说的那样,“消费文化使用的是影像、记号和符号商品,它们体现了梦想、欲望与离奇幻想;它们暗示着,在自恋式地让自我而不是他人满足时,表现的是那份罗曼蒂克式的纯真和情感实现”。
在“工业意识形态”的统领下,审美情感被艺术生产流程和大众传媒置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而处于这个流程化上的审美客体,实质只是一种僵硬与冷漠的美学肌理。总的说来,审美意识是随着文化和道德观建立起来的一套话语体系,是一种十分重视阶级趣味与荣誉感的美学话语形态,并把这种话语形态渗透到中产阶级美学“地形图”的方方面面。在艺术观上,它以是否适合现代社会的荣誉和声望来判识;在评价体系上,它并不关注艺术所附带的人文内涵与历史深度,而是过分炫耀文本的形式,注重情感的泛滥,造成文字载体向视觉载体的滑移;在接受语境上,它崇尚资本以及资本所带来的各种品牌意识;在艺术的伦理学立场上,宏大的历史意识和人文意识开始式微,以至于被扬弃,个人责任和历史深度被感觉和快乐左右。
对于现代社会语境下的娱乐情形,在电影中,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通过资本逻辑进行情感编码。显然,资本的影像编码,就必须处理三个方面的维度:影像生产的工业化流程、资本主控的文本编码、观众的被调控了的情绪。由此,上升到三个层面岁娱乐进行支撑:工业化的系数设置、文本图式化表现(影像的图谱设置、情感的雷同化叙事)、观众的审美快乐。
就此三方面来说,只有文本图示化表现,可以与之前的类型理论叠合,但是其他两个方面,还有待深入讨论。为此,如何从美学或者诗性的角度,密切联系电影媒介的独特逻辑,将现有电影产业实践的问题式的感知(诸如资本的、盈利的,产业的盈利性实践),在以票房为核心指标的产业逻辑的制约下,上升到学理性(美学的学理,电影美学的学理)分析,对主控观众情感的文本,进行新的解码应是投入更多的目光。
当然,在现有电影美学的建构实践中,这仅仅是单纯的第一层,其实它还受到美学以外的其他因素主控,诸如影像本身的伦理规范、国家逻辑、文化逻辑的制约。所以,如何在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进行影像情感场域的讨论与建构,其难度和纯度,都需要新的侧面和角度。
四
第四部分作为结语。我想引述两个人的论述,再次强化娱乐作为电影美学范式的重要性,但是许多人并未真正给予它们足够的重视,并将之美学化和理论化。其实这个问题,早在70年前,第二代艺术史学的代表性人物——欧文·潘诺夫斯基,就这样指出:
打开(电影)进化的正当道路的办法,不是在背离本身具有的可能性的限度内加以发展。电影生产在民间艺术水平上的原型(成功或报应、感情、激动、色情和粗俗的幽默)可以开花结果,成为真正的历史、悲剧和浪漫故事、犯罪和冒险,以及喜剧,只要电影创作者能认识到这些东西是可以转换的。转化的办法不是人为地注入文学价值,而是利用新媒介独有的和特殊的可能性。
在潘诺夫斯基的眼里,电影作为一种媒介,或许只有把电影作为一种媒介来看待,正如艺术媒介的任何一次演化而言,才能在人类的情感长河中,才能重新思考,为什么人类对某些情感的表述只会交给某一类特定的媒介,这样的说法可能太过于主观,或者说为什么在长期的实践中会发明发现某一特定的媒介,逐渐找到它与人类某一类情感的高度融合性呢?这对于我们重新思考,产业对电影美学的建构提出了新的思路,回到媒介历史的原点。
对于媒介历史的原点,其实斯坦利·卡维尔已经发出了他自己的疑问:
人们记得,电影的历史在多大程度是电影界个别知名女人的历史。个别的男人,即使最伟大的男人,如果同她们相比的话,除少数例外,都只是匆匆的过客和道具而已。知名的导演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通过电影而反复研究同一个女人……如果男明星因为某种原因而同女主角配不上,那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挽救这部影片。
显然,电影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说,是观众,是观众在观看。但同时,也是导演是产业在迎合观众,并最终主导观众。显然,在观众与产业这种互渗过程中,必定产生了影像的共振美学。只不过,这种切合被产业界在资本实践过程中,摸索到了。
当然,就现有的学术努力来说,这种摸索并没有被完全充分地呈现出来。但无论如何,对电影美学的建构而言,这种摸索却是一种方向性的决定性的。所以,如何打破精英分子(准确地说,应该是从古典哲学到现代主义视野下知识分子的传统路术)的知识态度,联系产业,对资本逻辑的影像编码进行新的解码与构建,应该是电影美学再次创新的一种可能性。
【注释】
①本雅明·布赫洛(Benjamin H. D.Buchloh),1941年生,哈佛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教授,当代著名的德裔美国艺术批评家。
②BENJAMIN H. D.BUCHLOH. Neo-Avantgarde and Culture Industry[M].Cambridge, 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 2000:Xxxii.
③产业机制包括以政策为核心的管理体制的转换、以制片为核心的企业扶持、以银幕数量增长的院线建设,以及如何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下区域与区域之间电影产业优势的资源配置问题,等等。
④参见:孙绍谊. 电影产业研究:理论与方法[J]. 文艺研究,2013(9):91-99.
⑤英语原文Blackwater,为美国的黑水公司。该公司在伊拉克战争时期,因接受军方委托的合同服务于美国军方,使自己处于舆论的中心。中文翻译经过和作者讨论,文中“黑水公司”是外包的隐喻,在中文语境下无法传递其意义,因而原文作者和笔者均认为直译为“外包”。
⑥有意思的是,这种研究还影响到了美国东海岸。2011年12月中旬,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安能堡传媒学院(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专门召开了一次产业研究的研讨会。受邀发言的就有约翰·卡德威尔。随后,他还以访问教授的身份为宾大博士生开设与电影(媒介)产业研究相关的研讨课。此期间,笔者刚好在宾大安能堡传媒学院访学,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也参与了约翰·卡德威尔主持的讨论课。
⑦其他著述可以参见其网站:http://www.tobymiller. org/,访问日期,2015年4月7日。
⑧对这个领域的占领,主要有电影批评来完成。电影批评的现实性鲜活性,使得它缺乏美学范式建构的自觉性追求。
⑨CHRISTOPH KLIMMT1, CHRISTIAN ROTH, IVAR VERMEULEN, PETER VORDERER, FRANZISKA SUSANNE ROTH. Forecasting the Experience of Future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Interactive Storytelling'' and Media Enjoyment [J]. Games and Culture,7(3) 187-208.
⑩柏拉图的反对,是因为快乐与娱乐直接模仿了真实世界,从而缺乏对真理与智慧的认识,最终快乐成为堕落性的快乐。
段运冬,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国主流艺术的国际化研究》(项目批文号:教技函[2013]47号)、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青年项目《中国主流电影问题史研究》(项目编号:10CC080)、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新媒体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项目编号:SWU100908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