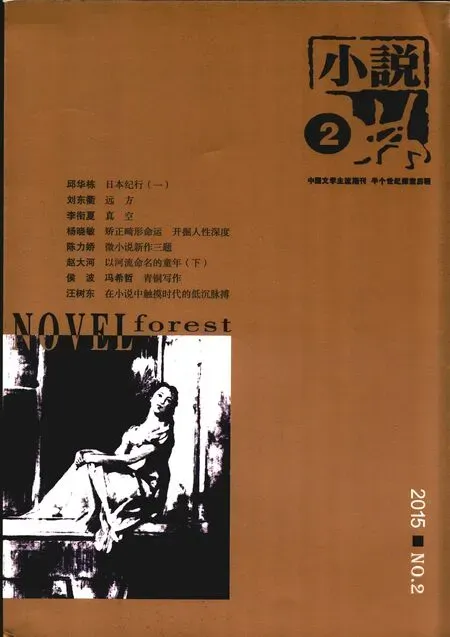日本纪行(一)
2015-11-18邱华栋
◎邱华栋
日本纪行(一)
◎邱华栋
东洋·扶桑
飞机上的电视屏幕上,随时在显示着飞机行进的方向和具体所在的位置,一条红线在快速地向日本延伸。我们的飞机是从首都机场起飞,直接向东飞行的。全日航空公司的飞机宽敞舒适,空姐的微笑十分含蓄迷人。似乎没过多久,我看见,我们已经飞临渤海上空,在大海上空向东飞。透过飞机舷窗,可以隐约看见苍茫的大海在下面无边地铺展。
我知道,存在着两个东洋——对于中国人来讲,东洋人就是日本人的代称,因为日本就在我们东边的海洋上。可是对于日本人来讲,东洋,好像指的却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地区,甚至还包括日本、东南亚诸国、印度、西亚等等,这些广大的地方都是东洋地区,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扶桑是一种木槿属的灌木植物,可是,从很早的中国古文献中,像《山海经》《南史》中,就已经用扶桑来称呼日本了。扶桑的方向,就是今天日本所在的方位。
扶桑这种植物四季花开不断,五色婀娜,非常美丽,是不是我国古人因此用来象征和形容大海上日本的美丽与神秘?
从日本列岛的地图上看,确实,大海包围着它,除了面对来自大海的威胁,来自海上的影响,日本没有别的选择。日本从地理位置上讲,就必须要向任何来自大海上的力量开放。
对于这个我从来还没有来过的东方邻邦,日本的形象一直很神秘,很含蓄,很安静,当然,也很暴烈。菊花与刀——一个美国学者对日本文化模式的符号化解读。我不知道,我会看见一个什么样的日本?
成田机场
飞机才飞行了两个多小时,就在东京成田机场降落了。飞机下降的时刻,我看见了东京附近的海湾在发亮,机场十分清晰地出现在了我的视野里。
这个时候,我想起来过去看过的日本电影导演小川绅介于1967年开始拍摄的纪录影片《三里冢》,这部纪录片讲述的就是东京郊区三里冢的村民,为了反对在这里修建机场,和政府对抗的艰苦历程。
小川绅介拍摄这部影片,前后花了十一年,基本上就落户在这个地区,和那些居民一起共命运。最后,他剪辑出来的成片《三里冢》,一共有十六个小时,共拍摄剪辑了七部成片。通过对三里冢的居民多年和政府进行抗争的纪录与展示,使这部影片成为了日本民众争取自己权益的一部史诗。
当然,最后机场还是修建成了。在这部影片中,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幅画面,相当震撼人心:当黑压压的军警向成田村走过来的时候,他们愕然发现,在他们前面,每一棵树上,都绑着一个女人,而每一棵树上都有一个孩子。军警不得不要干的,就是砍掉所有的树,而绑在树上的女人和树上的孩子,就是他们的障碍。
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他的摄影组的同仁多次被警察打伤。这个影片系列中的《三里冢:第二道防线的人们》成为了世界纪录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德国电影史专家乌尔利希说,“它的现实性,达到了迄今为止一般纪录片所无法达到的高度,具有古典武士戏剧的水平。”
这个影片后来还在1971年的莱比锡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史登堡奖。而我,就是在这样的联想中,伴随着巨大的喷气式飞机的轰鸣,平稳地降落在了成田机场。
成田机场似乎有些老旧了,但是机场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似乎很高,听不到太多的喧哗,没有嘈杂的声音,只有机场各种橱窗中的广告牌,那些颜色明亮的影像在闪烁。
等到办理完出关手续,我们看见日本外务省的翻译平田敦子小姐,已经迎候过来。
东京电视塔
一辆奔驰商务车载着我们几个人,向东京市区而去。在并不宽敞的高速公路上,车速很快。路边不断地闪现一些日本大企业的广告标志,松下、丰田、佳能、富士……这些广告符号不断地在疲倦的大脑里刺激着我。外面似乎刚刚下过了雨,空气潮湿,天空多少有些阴郁,看不见太阳,绿色的植物非常有生机。我们的车经过了东京迪斯尼乐园,经过了临海副都心的高架桥和跨海大桥,进入了市区。日本似乎是一个很含蓄和安静的国家,从街景看上去并不喧闹,似乎没有什么声音。
在市区里,有时候有些堵车,但是看不到多少警察,他们的智能化交通管理系统看来相当成熟,一般一辆车可以连续走好几个绿灯,这在堵车已经成为一大痼疾的北京可以说是很不容易发生的。
一个小时以后,我们抵达了要下榻的东京王子大酒店。
王子大酒店是一家很安静的酒店,并不高大,四周被绿树掩映,非常典雅。这个季节正是樱花开放的季节,树上的点点樱花在酒店四周都有分布。
我通过房间的后窗,看见了东京电视塔,它就屹立在酒店的后面,竟然这么近,离我只有几十米远。过去我曾经收到过我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一个日本大学教授邮寄给我的明信片,上面就是这个东京电视塔。
这座塔高三百三十三米,是东京最高的建筑。它于1958年建成,是完全模仿法国巴黎的艾菲尔铁塔修建的,但是,这个时候,日本人的钢铁冶金技术已经很发达了,所用的钢材就要比巴黎的艾菲尔铁塔轻很多。现在,东京的很多电视台,都要靠这个电视塔来发射信号。这座电视塔在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展望台,在二百五十米的地方,还有一个小展望台,这两个瞭望台,可以在天晴时,看见东京不同层次的风景和市貌。
在塔下面有一个蜡像馆和一个水族馆。每年不同的季节,打在塔身上的灯光颜色是不一样的。春夏天,打在塔上的灯光是白色的,这样可以使塔身特别明亮,冬天则打上黄色的光束,这样就有了冬日的暖意。
塔身旁边还有一个宽敞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的边上,种植了很多大树,其中的樱花树已经开放了,远远看去,点点樱花在夜灯的照耀下,比白天还要亮丽一些。
荞麦面
我们收拾停当以后,就坐车去市区吃饭。我们很快就抵达了一家看上去很不起眼的面馆,房间里面的装饰都是日式木料,特别整洁清新,没有中国餐馆惯常的那种俗艳装饰和人声鼎沸的喧闹。
各种漆器和木制的餐具非常考究细致,精雕细刻。形状十分复杂漂亮,多边形、三角形、四方形、树叶形和贝壳形,颜色不同,形状不一,特别刺激人的食欲。
面是荞麦面,颜色半绿半棕,用筷子吃,鱼是生鱼片,可能是金枪鱼的鱼肉,用芥末相伴,入口香鲜。酒是啤酒,像泉水样的清爽型。
茶,不是中国式的茶叶,而是已经碾成了特别细碎的粉末的绿茶,味道略微有些苦甜,我一共添了五次。
清淡的味道,味蕾上面的舞蹈——我知道,这就是日本人的美味。
外面又开始了小雨的淅沥,在这样的雨水滋润中,我感觉东京各处的樱花,正在悄悄地开放着,带着水珠在伸展着娇嫩的花瓣。
德川家庙:增上寺
早晨阳光很好,我和祝勇很早起来,去酒店的附近地区溜达。没有想到走了几十米,穿过了几棵怒放的八重樱,我们看见了一座寺庙。这就是增上寺。增上寺是净土宗在关东地区主要的寺院。
十六世纪中,日本长期割据,控制日本中部地区的尾张国的大名织田信长控制了六十六个小国的三十个,可以说基本控制了日本政权,开始了日本的统一历程。织田信长死后,他部下大将丰臣秀吉继续统一日本的事业,完成了日本的初步统一。这个丰臣秀吉,有着军事强人的雄才大略,后来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据说他还想进一步侵占中国,甚至是印度。不过,在明朝军队的援助下,朝鲜屡次打败了日军。1598年丰臣秀吉死于疾病,大权落在了织田信长的另外一个大将德川家康的手里。在江户地区,德川家康是日本幕府时期有名的大名。
1603年,拥有关东重镇江户——过去东京旧称呼的控制权的德川家康,取得了争夷大将军的称号,在江户建立了幕府,从此,德川家族的德川幕府,实际统治日本两百多年,一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才结束。因为德川家康和寺庙当时的住持结为了师檀关系,就把这个寺院建立为自己的家庙。
德川幕府是日本历史上十分重要的统治时期,一开始,幕府为了加快统一的步伐,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上,采取了各种削弱各地大名的政策。而且,德川幕府开始还提倡和朝鲜与中国的贸易往来。1633年,决定驱除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为主的欧洲人,主要是觉得天主教和基督教对自身的文化有威胁,从此渐渐地闭关锁国了,一直到1853年美国海军将军佩里进入东京湾,才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德川家族的家庙——现在是增上寺了,进了院子,气氛很幽静,两侧的歌碑显示了历史的久远。潮湿的空气打湿了正在开放的几棵樱花树,花瓣纷纷落地,没有任何声音,我不禁感到了一丝禅意。每年,从一月到十二月,月月都有法会在这里举行。
家庙的主建筑很像我们一般寺庙的大殿,门板紧闭,里面好像有值日的僧侣在活动。旁边还有一座小的配室。围绕着增上寺边上,是很多石头雕刻的、模样完全相同的石头小人,大约高三十厘米,形成了很长的队列,这些石头小人的头上还戴着红色的毛线编织帽,在小石人前面,有的有供品,有的插着红色或者彩色的小风车,在风中唰唰地转动,声音忧郁而哀愁。后来才知道,这些小石人是那些引产或者流产、死婴的家庭在这里供奉和捐助的,为的是向上天告慰消失的那个小小的生命。
增上寺的大殿后面,是一片公共墓地,黑色的墓碑林立。旁边还有一个很小的墓园,据说安放着德川幕府家族的灵骨。
我看到,通往墓地道路旁边的几棵樱花树,开得特别丰盛灿烂,在小风吹拂下,落英阵阵,繁花似锦,却又美丽凄清。我和祝勇完全被墓地边上的樱花凋谢所震撼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日本人为什么喜欢开花短暂的樱花——它就是璀璨放射生命光华的象征,生命,不在久远的平庸,而在刹那的闪耀。
这是我们在日本看到的第一片美丽的樱花,在这样一个撒满了阳光的早晨。
上野公园
酒店的早餐是日式自助餐,酱汤、豆腐和各色小点心都很可口。
最早知道上野公园,还是在鲁迅先生的文章里,说到“上野的樱花又开了”等等,这使我确实对上野公园的樱花非常向往。每年的春天,上野公园就成为了东京人主要观赏樱花的地方,据说这里种植有一千多棵樱花树。
我们上午十点钟的样子,到达了上野公园,发现那里已经有很多游人了。这个季节正是一些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很多穿着漂亮的和服的女孩子,脸上带着特别动人安甜的笑容,和穿着庄重的父母亲一起穿越上野公园,向附近的东京大学、东京艺术大学、农业大学和医科大学等而去,成为了我们眼睛中别样的风景。
上野公园的樱花果然漂亮,在公园里,几条路径的两边,都是已经怒放的樱花树,宛若粉色的云霞,那樱花开放的阵势,确实可以说是云蒸霞蔚了。我想起我的母校武汉大学的樱花大道来。当年日军攻克武汉之后,曾经把武汉大学的古老校舍当作战地医院,为了安慰那些想家的伤病员,于是在老校舍下面的一条大道两边,种植了樱花树,成为了武汉有名的樱花大道,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每年三月份,樱花大道游人如织,花团锦簇。所以,当我看到上野的樱花,不禁眼前时光重叠,母校的樱花和眼前的樱花,在记忆里和当下同时开放,我有些迷离了。
在眼前的樱花大道上漫步,我看见道路两边有一些画了方格的地方,放了不少黄色的布袋,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旁边还有人坐在那里。平田敦子小姐告诉我,那是人们晚上放垃圾用的,而那一个个坐在小马扎上的人,是为了其他同伴晚上来品赏樱花,早早地来占座位的。到了晚上,就是在这棵棵樱花树下,三五成群的东京人,他们是朋友或者同事,家人或者亲友,一边赏花一边喝酒作乐的。一些东京人显然是把生活艺术化了。
我们细细地品赏了樱花,然后步行去公园里面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主馆是东京博物馆,不很大,它的地位应该类似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几个侧馆,一个是建于明治末年的表庆馆,是为了纪念当时的皇太子成婚的,现在里面陈设了很多西方国家送给日本皇室的礼物和珍宝。右首是东洋馆,陈设了东方各国,包括中国、印度、西亚、东南亚、埃及等各个国家的文物与艺术品遗存。
此外,还有一个平成馆,一般进行特别展览和日本考古遗存展,另外一个很小的展览馆是法隆寺宝物馆,这个展馆是奈良的法隆寺在1878年献给日本皇室的珍贵文物,大约有三百多件,主要是一些佛像、漆器、木器、金器和书法、织染等。
在博物馆本馆的二十四个展厅里,我仔细地观看日本出土的历史文物,多少有些失望。说实话,这个国立博物馆,和国内的一些省份的博物馆,比如陕西博物馆、河南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相比,都要逊色些,更别说和北京的国家博物馆相比了。
这也难怪,因为日本民族的形成原因,主要是五千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的新石器时代,从中国的东北和沿海地区居民移民到了日本列岛,主要是通古斯族,和来自蒙古系的人种与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系的人种,多次混合繁衍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就是今天日本的主体民族。
大多数日本史学家考察日本的历史,都要从公元前660年的神武天皇开国来算起,其实,神武天皇时代完全是神话传说,并不可靠,所以,日本民族的起源,在日本早期神话式的历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上有历史记载的,是从公元507年的维体天皇算起的。但是,即使是这个结论也是不完全可靠的。而六世纪末期,推古天皇登位时间,才是日本民族比较可以考证的历史纪年,这是日本历史学家普遍赞成的。
由此看来,可以说日本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中国相比确实不算长。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里面流连了两个小时,看到了从先绳文时代开始,经过了弥生时代(大约相当于我们的秦朝)、飞鸟时代(我国隋唐时期)、奈良时代、平安朝,到了镰仓幕府时代(我国南宋时期)、室町时代(我国明朝),一直到后来的江户幕府时代、明治时代、大正、昭和和平成时代。
从上野公园出来,我们驱车来到了一家酒店里面的一个西餐厅,吃了一顿意大利式样的面条,非常可口。我发现日本的西餐厅非常多,而且口味也比北京的更加地道一些。看来东京一些日式的餐厅,也在逐渐地西餐化了。
哲学堂
我们先去中野区立哲学堂公园,这是一个隐藏在东京市区里面的一个幽静的去处。一路上,可以看到很多两层楼的日本民居,含蓄和幽静地隐身在寸土寸金的东京地面上。在公园旁边,是一座棒球练习场,一些日本少年正在那里练习棒球。
这个哲学堂,是已故日本哲学家井上门了博士,于明治37年4月所创立。在这个小巧的公园,曲径通幽,古树参天,大树林立,花木繁盛,溪流盘绕,一年四季都有花开。而且,不知名的小鸟和大鸟,在园林里唧唧喳喳,很是热闹。也有几棵樱花树,在淡然地开放,又是一种滋味和感觉。这个季节,东京处处是樱花,确实很有意思。
这个公园叫哲学堂,那它的建设,处处都和哲学搭上界了,什么哲学关、哲理门、常识门、一元墙、时空冈、百科丛、怀疑巷、三祖苑、唯物园、数理江、认识路、宇宙馆、唯心亭、经验坂等等,这样的妙处,大约有三十几个,个个都与哲学理念相联系。可以说是玄关处处,所到之处,不仅是园林胜景,也是可以引发你哲学玄思的处所。
我们在小公园里上上下下,穿竹林出花雨,直到柳暗花明,到了一片开阔的空地上,却看见一些幼儿园的孩子,正在由三个年轻的老师带领,进来在哲学园里面做游戏。由此可见明治时代日本发愤图强,以哲学和科学为强国之本,一直泽被到眼前的这些天真快活的孩子们身上了,让他们从小就有一个聪慧的头脑。这里可以说是一个有趣的去处,然而,让我也是引发了不少感想。
皇居
在哲学园里待了一个小时,我们离开那里,到达千代田区一家十分考究的西式日餐厅,会见了日本外务省文化交流部近藤部长。这家餐厅朴素无华,隐身在一幢高达二百米以上的玻璃幕墙大楼的后面,和这幢大楼的反差十分强烈。
近藤部长曾经担任日本驻法国大使,所以气质上有些像拉丁人。简短的会见,谈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细节和计划。饭是西餐化的日餐,食物精心,餐具别致,视觉效果很好,每一种东西上来,都是那样的精美绝伦,让我几乎不忍下嘴。
吃过饭之后,和近藤部长告别,我们离开餐厅,在东京警察厅门前下车,向皇居的樱田门走去。
这个东京警察厅,可是鼎鼎大名,很早的时候,我在日本电影《追捕》里面,就看到过它的模样。警察厅对面,是日本法务省那有些年头的大楼。
我们来到了皇居外面的樱田门。皇居,就是今天的日本天皇居住的地方。下雨了,雨是那种小雨,细密地打在皇居边上的护城河上,河面上,水面波纹阵阵,一些野鸭更加快活了。
皇居很大,从地图上看,是一片绿树掩映的神秘之所,它被巨大的石头围砌的宫墙所环绕,还有护城河的保护,宫墙边,大树参天,浓荫连片。皇居里面就住着现在的日本天皇。日本人一般很少见到天皇,天皇是日本人眼中的神,过去,即使是听到天皇的声音,也是会浑身战栗的。
这个时候我忽然想,现在的日本体制,虽然是一种君主立宪的体制,但是,其实也算是一种幕府体制的变形吧?天皇是一个象征和影子存在在这个体制里,真正管理国家、大权在握的,却是首相和那些首相背后的各种党派与政治势力。这些政治势力,和过去日本有影响的将军、大名其实没有多少本质区别吧?
在皇居外苑那开阔的地方,种植着很多姿态生动高矮一样的松树。东京的树多而且大,树种很多,我发现日本人似乎对一草一木都存着敬畏之心,小心地伺候,所以环境很好。我想,连东京这样巨大的现代城市都是如此,那日本那些偏远的地方,不容易被污染的地方,花草树木应当更为繁盛了。
皇居门外,开阔的广场上,都是那种走起来沙沙响的砂石。往东京火车站的方向看去,那里又是鳞次栉比的玻璃幕墙大厦群,是丸之内商务中心区。下雨了,我在皇宫的正门前流连了一阵子,想象了里面不远处日本天皇奢华居所的模样,看到了附近严密的电子监视系统,就离开了。
第二天,天色好些了,我们路过皇宫,专门在皇宫外边的一段护城河边上走了走——这里护城河两岸的樱花,开放得特别好,与上野公园的樱花相比,还要好些。因为有护城河的掩映,河两边的樱花有远有近,形成了视觉上的反差。近的就在我们的头顶,人们摩肩接踵地走在河边高高的堤岸上,那些怒放的樱花树下,脸上带着和樱花一样或灿烂或安详的表情。
远远地还可以望见,在护城河的河面上,还有人在泛舟,绿色的河水被细密的樱花所遮掩,那种感觉非常淡远,仿佛一幅水墨画。加上增上寺和上野公园的观赏,这是我第三次看到了不同的樱花。
邱华栋,1969年生于新疆。当代小说家、诗人、评论家。曾为《青年文学》杂志执行主编,现为《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夏天的禁忌》《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花儿花》《骑飞鱼的人》《单筒望远镜》《教授》,中短篇小说集《黑暗河流上的闪光》《把我捆住》,散文集《绝色喀纳斯》,书评集《和大师一起生活》,建筑评论集《城市漫步》,诗集《花朵与岩石》等七十多种。多部作品被译成法文、德文、日文、韩文、英文、越南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