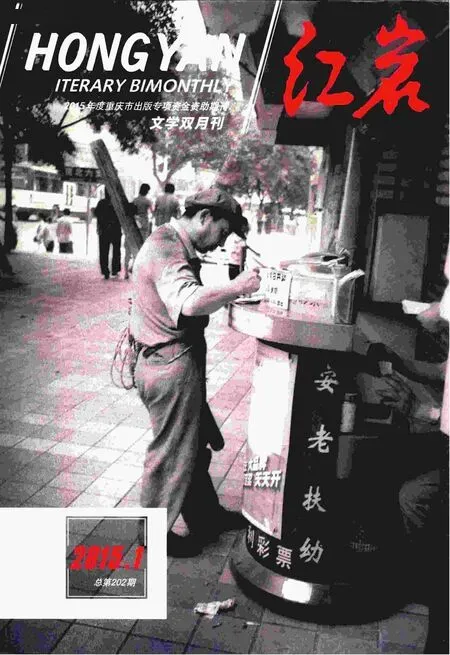余怒诗集
2015-11-17余怒
流星旋转—给吴橘
流星旋转仿佛天空有弹性
无人知道它们会落向哪里
言语之间一个空间推着一个
空间波浪远去剩下一分钟你
可以与咕咕叫的水鸟分享
哈什么是道家的孤独这就是
10月10日晚上她收紧了像一块
含玉的鹅卵石而那时我与寂静
已经一体了在冰上雕刻葡萄
那是肉体的欢喜飞动的鹳所
展现的解剖学长喙脖颈翅膀
脊背尾巴及其一系列形式感犹如
从飞机上抛下的亚麻衬衫飘动旋转
孤零零在白茫茫中
孤零零在白茫茫中
冲浪板在波涛里出没
我第一次领悟到时光
重现的样子哦原来是这样
孤零零在白茫茫中将你
带到世界之外我在相似的
磁场里站立读书睡觉
说话哭直到听到自己
的回音在四壁之间像
乒乓球反复穿越多棱镜
海面上平静如昔无边无际没
有任何做梦的人穿越我醒来
自然控制论
空货车在楼下马路上疾驰
探身窗外光线又深又宽
打开冰箱他在冷冻室里翻找
冷气产生白色的烟表明空气
是可以净化的但他就是
控制不了晚上穿山甲茫无头绪
在月光下读书可喊叫声无法翻译
因为恐惧所盖的这座大房子他在
周围种上石榴树山楂树银杏树
时不时喊很多人来做客
巴望快点结出石榴山楂银杏快点秋天
在我们失望之后坠落之前
夜晚总有点奇特
夜晚总有点奇特寂静如
避孕套而鸟鸣如勃起我在
林中四处溜达看看这棵树
看看那棵树考虑自己和世界
的关系感到夜空突然凹了进去
或者像是哪儿缺了一块少了
很多星星但仍然美妙在一棵
榉树身上我发现某某的几句
留言采取一封信的形式写给
一个人看上去是用小刀刻的
字迹随着树的长大变得模糊
某某你是谁呀这蛮有意思
嗯用爱情形容是用词不当
周围的蓊郁形成压力加之上面
的夜空让人不能自己于是我
大声说我也会改变自己的对着
一棵弯弯的柳树说而旁边是一
棵矮一点的开着白花的夹竹桃
语言训练
将晒了一天的衣服穿到身上
以期蒸发使自己high起来
在黑咕隆咚的房间里开始
语言训练啊呀唉咩咩汪汪
知道生物都有灵性很容易
进入无我之境获得安宁
那么你也就不必硬着头皮读诗
就像你不必了解粒子加速器
负氧离子质子和反质子
哪怕最后它们无端长成一株
夏威夷多骨朵水仙
今天不写诗了我下了决心
我将一件什么东西忘在了一个
什么地方可就是记不起来那是
一件什么呢哪儿呢深夜去月球
鱼之诗
水中游鱼岸上杨柳不顾一切
上了船雨中船悠悠驶进小河湾
我之所以使用这种抒情调子
是因为雨后我形成了与众
不同的世界观东边有清凉峰
西边有彩虹不同的表象但
有什么是真的呢雨越下越
大仍然空寂仍然不明不白
救生圈环绕我脚轻身子重
在我的眼中世界是倒过来的
那一天病房里很安静我走近
病床上一个睡着的姑娘我扒开
她的眼睑想让她看看我你还
记得我吗她曾经疯狂现在在熟睡
像一条睡在蒸汽机里的比目鱼
房间里的逻各斯
用彩纸装饰房间时我还在想
让我们之间变得单纯一些吧
不谈海怪不谈性日本海棠的粉红和紫红
外面下着雨我点上一支烟烟雾
缭绕我望着她的丰满臀部想到北极
冰天雪地我们没去过那里裹上毛毯
坐上雪橇雨雪霏霏别无二致是吗
关上窗户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抚摸电流贯注其中的她听电流
的奔突声嘶嘶雨中的天线她的
整体性奥妙和欲望由里向外溢出
刚做完爱的女人是反逻辑的她分成
几个部分走路大腿小腿足踝脚尖
滂沱大雨时
雨大起来空间比平常
膨胀三四倍树木摇晃
街道起伏空间有了具象感但里面
狭窄憋屈带给你一种反空间情绪
在雨中进行自我调整傻瓜都知道
变换形体先弄明白自己是谁
也膨胀三四倍呗是个好主意
谁说的雨天不能做爱发现自然
的灵性和肉体的排他性久而
久之它们从身上消失无影无踪乃胡说
雨中闪电照亮我们
从浴室里出来赤脚站在地板上
站立不稳分不清东南西北相互
视而不见有一种穿山越岭的感觉
力
在雨中骑车累了俯身
察看雨中植物的反应
车轮转动我在想诗该如何理解
它是玻璃花朵刚刚破碎但它
曾是花朵像你常常怀疑发出
那个声音的是我吗但不是吗
一个小伙子吊在单杠上旁边一个
老头在同他说话他就是
一个诗人他低吟他想成为你
自行车前后轮转动我整个人
不得不屈从那股扭动的力
回来时发现房子浸在水中那儿曾
有过一个我如今我们中只有我活着
我考虑以后以什么形式存在为好
蔚蓝色调
朋友们送来他们的新诗集
我草草扫过一眼将它们插入书架
在心里我骂自己为了保持古老
的否定法则只好说好吧世界
保持你唯心主义的蔚蓝
像昨天一样一个昏头昏脑的
孩子被逼着在网球场拉小提琴
发出稚嫩的不熟练的
音调砰砰它们在深夜回荡
被周遭数百台空调吸收这时你
会因写作而暂时忘掉他或打开
窗户对他呵斥在吃了冰块之后
那砰砰声听上去像是发自什么东西
的内部我说那是刚长大的小青蛙跳
出水面的声音还没有任何自我可言
异常空气
坐久了脑部缺氧像一只
颈部折断的老鸭子
窗外栀子花也开得僵硬
直挺挺的一点不像是花
所幸病房里的花是菊花
我不由感叹还是弯曲的东西惹人怜惜
我刚拔了一颗牙还想拔一颗
两个穿着飞行短裙的姑娘在
走廊的一头说话我在这一头
只听见嗡嗡声在次声波里她们
在谈论万有引力和尼斯湖怪
今天我嘴巴肿痛不想让人看到我尽管
她们很美丽还有输液室里的那些
女护士口罩上方的眼睛白大褂里
的身材曲线这一切像阿拉伯塔一样
与我无关心神不定伸懒腰跳起来手在
空中抓一抓空气又开始正常流动
虚空
早上不要读我的诗你
去看木架上的青葫芦
傍晚不要读我的诗你将青葫芦
摘下剖开取出它的籽
我的悲伤不够三个人享用可我的
诗值得你回味一小时转而
联想到你自己你可能正是那颗
青葫芦在空中发芽吧别做梦啦
在逝去的时间里一切似乎
都是针对我的而回过头来想
我应是什么或不应是什么
我希望死后一座白塔围绕
我的尸体而建且内部虚空然
后由你亲手拆除以还你自由
脱身方式
疲倦是早上的特征之一但早上
天气凉爽瘦女人穿着花裙子站立
鸵鸟般的孔雀
这一天他想跑出去自由支配
时间重复干一件事跳伞或冲浪
她躺在楼梯上双腿弓起随意赋形而
得以平衡她指着自己的耳朵
朝他眨眼他不明白其含义
上来呀轱辘带来愉快将身子
无故拉长为适应现状而转
不是只有天空和大海才适合你
你得停止在自己身上表演
去别人身上怎么样重复爬楼梯
爬上去滑下来快爬上去慢滑下来
极其微弱
不要急于弹琴先将那些
烦心事儿忘了我如是说
钢琴师是我的老朋友现在是
晚餐时间几个穿吊带裙的
单身女人围着一张餐桌她们小声嘀咕
一个红头发男孩和一个绿头发女孩
手牵手穿过我们朝吧台走去
他们点了两杯冰淇淋奶茶
相互干杯咬着塑料吸管笑
我让钢琴师先盯着那绿色看
再盯着那红色看然后重来先盯着
红色再盯着绿色各看五分钟
如此反复直到他们的杯子被吸干
琴声响起他闭上双眼他说已经极
其微弱极其微弱世界在哪儿终止
星际圆柱体
闲着没事就想想卡戎星
与安庆之间的距离
我生于1966像一列火车被
挤出火车站我常说星际列车
会带走我们这是自然选择
的结果这是个梦幻国家哈哈
整日坐着双手夹在双膝之间
尽想些真理情怀什么的我是个
诗人慢慢老了喜欢圆柱体
也就是很多圆叠在一起叠得老高老高
高度甚至以光年计借助光学原理
遥感技术超级计算机不是桌子上
你一叫它就稀里哗啦倒下的那种
心生象
从这儿大厦顶层俯瞰那些
道路汽车小贩行人那些
还没有找到宿主的光线像被人
按了快进键的视频闪烁雪花点
打开感觉器官旋即关上
你可要旋紧了那是个魔瓶
有人在远处屋顶上竖天线有几只鸽子
有人在玻璃幕墙上擦洗玻璃他
不时将耳朵贴在幕墙上通过察觉
他人来肯定自己的存在你是谁
华灯初上在楼顶上容易产生
脱离此身的想法我对着下面的喷泉广场
大声朗读自己的诗知我者谓之繁星
和天花乱坠不知我者谓之乱糟糟
被施了魔法
她对我耳语时我正在用刨子
刨丝瓜我白了她一眼不愿作答
唉厌倦这种感觉强烈
通过刨丝瓜发泄可她不知道
在了解语言的功能之后我们
才能说即使说也是词不达意
徒具形式藤蔓的形式
具体到一根丝瓜开花熟透
干巴巴的瓤子像偏执狂患者
的脑结构特写那不正是我吗
被施了魔法自生自灭故作衰老语
阴雨天
这几天阴雨床单衣服回潮
空气中弥漫着碳酸的气味
她要求我为这鬼天气写一首诗
看雨中撑着伞吵架的老夫妻看雨中
公交车里拥挤站立的无声的人们
他们也在看雨仿佛眼前别无一物
她趴在窗台上不让我碰她也不让
我跟她说话有可能目的单纯也有
可能想以特殊的姿势引发我的灵感
披散头发满脸雨珠地笑
我独自呆坐了一会儿感到无聊去睡觉
顺便朝窗外扔了个玻璃杯落到
楼下水泥地面上居然没有声音
那物理性—给黑光
假惺惺爱惜时光的游客
我要跟你谈一谈鸵鸟下的蛋
游历了名山大川你年轻好动
手脚有力有抽象的情感但一枚枚蛋
是具体的它们会孵出小鸵鸟
在沙漠里仙人掌聚集了大量雨水而
腹部一下子空了的鸵鸟又老又悲伤
像一只由1500块碎片拼成的布质鸟
很多年前我的物理老师说过
这个世界的物理性很可怕
他将我带入一间电磁实验室将
我关在里面听任生性安静的我
在漆黑的磁场里来回奔跑叫喊
扑啦啦
下班后他不想回家围着
植物园转圈什么植物可以
让新陈代谢慢下来
遇到朋友他说我在练习徘徊
上楼时他看见许多被涂成
粉红色的老鼠成群结队拥下台阶
粉红色代表喜悦部分来自
语言的专制部分来自条件反射
楼梯尽头站着女友笑盈盈
夜里他站在自家昏暗的阳台上
感觉到一群扑啦啦飞来的东西
不是鬼脸飞蛾不是多毛萤火虫不是
无头鸟或是任何带翅膀有生命的东西
不死鸟
装模作样听音乐听到巴赫
耳朵痒用棉签掏跑到屋外
看流浪艺人表演一个孩子
弯成一个圆环滚动一只狗
在上面保持平衡像滚绣球一个中年人
提着铜锣敲嘴里吆喝着快快
孩子悄无声滚到一个小媳妇裙下
朝她扮鬼脸她咯咯笑狗汪汪叫
现实主义令人心碎因为它的强大
食肉恐龙复活我想上前制止它们
你们回来吧这时前面驶来一辆运煤渣
的大货车撞向我我脑袋一热飞身迎去
难道我真的是不死鸟司机说你活得
不耐烦了我跑回屋里剥开一颗橘子
将整个橘子塞进嘴里回到巴赫里
始于星期一
星期一所有围绕骨头的肉都疼冲个澡
在书架前翻动霍克斯一边喝昨晚
他们剩下的半瓶可乐张嘴什么怪味
老鼠的尿臊咀嚼一颗跳跳糖现在他们
还像昨晚一样快乐吗那是服了药
分身于此处彼处告诉自己你要活在
现在停在出生的那一日我们就是佛确知
自己的力量且知晓往昔于是下楼去上班
跟四楼的骨科大夫打招呼因为他在
白大褂外面套着燕尾服狗日的跟五楼
的短发小孕妇打招呼因为她不知怎么就
怀孕了哈罗单亲妈妈非理性硅胶天使跟
二楼背着书包的小学生打招呼因为他
一直在偷偷打量我我脸上有唇印吗你
上的是怪兽大学吗跟虎着脸叼着烟
的小区保安打招呼别担心你不会被风
吹走的尽管他个子高挑站在售楼部的
台阶上耸肩凹胸有一种脱节感像可以撕下来
世界之轴
我敲行李箱发出沉闷
的声音说明里面是满的
我敲胸腔发出同样沉闷的声音那儿是空的
满屋子翻找一件淡蓝衬衫我曾穿过它
晚上我要是坐下来就会感到整个世界在打转在窗户外面
但也可能只是一个名称
围绕着另一个名称
菊花转动它纷纷花瓣
白色云
睡一觉起来看墙上挂着的
世界地图移动手指找班扎雷海岸
在波因塞特角与卡尔角之间我
没去过那儿心向往之更加疲惫继续喝酒
等待朋友们向我的屋顶空投食品他们会的
朝上望天空挂在天上湛蓝湛蓝纠正形而上下雪了
我有很多奇怪的爱好奇怪的朋友们语言
是不必要的因为幻听歪曲你所言同时
它也是无害的上帝和佛是两种货币相互可兑换
看在好天气的份上读诗吧拍打鱼缸使里面
的鱼感到轻微震动跃起又跌回水中怎么解脱我问你
窗外白云如我的恍惚
名叫克利的鸟
晚上11:30是睡觉时间仍然清醒
披着被子抱着猫坐在床上低头看
穿过绿绸缎的灯光打在我的胸脯上
我问自己今天心情如何挺好碧绿
今天猫也特别乖一遍遍舔我的手掌痒痒的
读诗厌倦了我从枕边拿起一本画册一座建筑的线条画
作者克利他的画总是朝一边倾斜像是马上要倒下来
有人说这是灵魂的几何学这是对过去的总结未免夸张
克利是一只鸟我在想我是否真的需要这只鸟今天晚上
可视之为思念
他们对着麦克风哼唱我也跟着
哼唱抱着一把转椅摇晃着这并不代表某种性取向
意念呼吸着空寂并且隐蔽
一个男人凑近另一个男人的耳边低语后者正往
嘴里塞着一个脆皮甜筒擦拭他的络腮胡子有些发白
奶油细腻如修辞而啤酒甜涩如某人
在歌声中自以为抓住了某人的幻象我们盲目自大到
称我们为主体称其他的一切为客体线形动物的本性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两只眼珠同时转动你看到了什么
空寂里排出的空气
平安夜
窗户狭小房间昏暗冬日书房里
一摞摞旧书籍散发出霉味我想
选择一个好天气烧了它们
朋友L来电话喊我去海边阳光灿烂我一口回绝尽管
跟一个海水般的胖子在一起你会四肢发热心情愉快
30岁我想建立一个童话国家想成为一个
纯粹的影子然后自由地脱离它现在我48岁
洗澡时我想象一个质量很小的女人像流星一样撞进来将
房间里的一切击得粉碎溅起满屋子活泼的水花
欢迎你来到这个昏暗星球我们一起冬眠
两个世界
深夜回家拖着疲惫之躯在
楼梯上站一会儿使自己平静下来
外面漆黑一团而屋内光线明亮两个世界正面
反面如果你一头闯进去你会大吃一惊谁戴着
牛头面具望着你眼泪汪汪孤独的唯我论
想起去年梦中猝死的某某一天他来串门在沙发上
一声不响不停地发短信猫在他腿上挣扎他没有感觉
我问他发给谁猜这个猜那个他笑而不语是否真有其人
一时半会得不到休息就像从游艇上突然降落到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