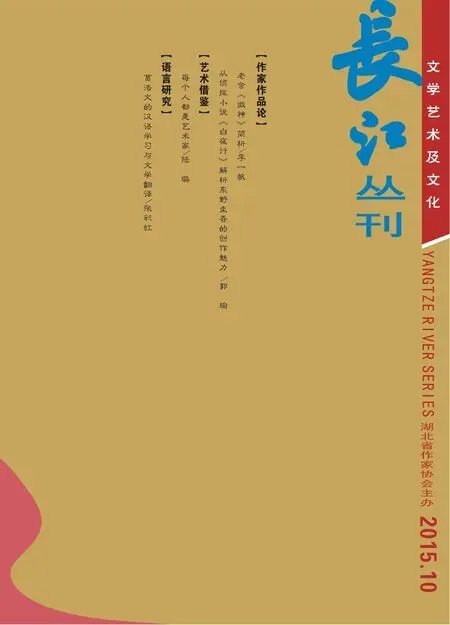葛浩文的汉语学习与文学翻译
2015-11-17张彩虹
张彩虹
一、前言
关于美籍汉学家葛浩文,中国学者最初是从他的几部文学专著知晓他的。葛浩文对中国新文学和以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的独特观点为他在中国文学界赢得了赞誉。上世界八十年代,他的专著陆续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之后传到大陆,其中一些评论曾开启了人们对东北作家群作品的重新认识和定位。而今人们对葛浩文的印象更多地是从翻译家这个身份形成。因为自从研究并翻译了萧红的系列作品,葛浩文就把研究重心从文学评论转移到中国文学翻译上来。他翻译作品数量之多,使之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史上第一人。但中国大陆翻译界对葛浩文的研究不过是近十几年的事情,尤其是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作为获奖作品译者的他无疑更迅速更广泛地得到人们的关注。
提到翻译家葛浩文,在学者界有很多标签贴在他身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夏志清)、“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生婆’”(John Updike)、“中国二十几位作家近五十部小说的译者”、“帮助中国作家获得英仕曼亚洲文学的第一功臣”。毫无疑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葛浩文是目前贡献最大的翻译家,没有之一。对他翻译思想的研究,大陆学者主要是通过葛浩文的一些文章和专访获悉,其中2002年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The Writing Life”[1]被引用频率最高,另外有关葛浩文的专访,如季进的“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2],舒晋瑜的“十问葛浩文(汉学家)”[3]是也关注率很高的两篇。通过这些文章和访谈,葛浩文阐释了自己在翻译和文学方面的基本立场和看法。在2014年11月的这次采访中,葛浩通过自己多年的翻译经验,从更深层次理解翻译和文学,其中也也透露出很多新内容和新观点。
Translation Review的一期刊登了学者Jonathan Stalling对葛浩文在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的访谈。在采访中,葛浩文凭借自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刻理解,阐释了中英文学翻译的基本问题:如何处理小说翻译中的复杂结构、异化与同化、汉语音体(the sound registers)转换、译者责任实现等问题。甚至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作家创作提出了自己的期许和建议,另对年轻译者也给予了建议,澄清了中国学者对他翻译的一些误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最初发表于网络的文章——“译者之声:对霍德华·葛浩文的采访”中,葛浩文还谈及了自己鲜为人知的求学经历,尤其提到了恩师许芥昱先生。本文重点选取采访中葛浩文关于自己早年学习汉语经历的叙述,和其对他之后文学翻译的影响,具体到对小说翻译过程中一些棘手问题的解决,以期对中国从事葛浩文研究和文学翻译研究的学者起到帮助作用。
二、汉语学习经历
(一)和台湾的不解之缘
据葛浩文讲述,他之所以最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都缘于年轻时在台湾的那段汉语学习经历。在这次Jonathan Stalling的访谈中,葛浩文提及大学毕业后去台湾之前的一段经历。他曾当了一个学期的小学教师,终因不喜欢这份工作而辞了职。越战开始,因父亲之前在造船厂工作,他便应征海军,却被派到台北。虽也曾想去越南参加轰轰烈烈的战斗,但发现自己心所向往的地方是台北,那个靠近战场的地方[4]。
初到台湾,葛浩文完全不懂语言。或许是命运使然,亦或许是当地文化、山水风景或某种莫名的原因,他被台湾这个地方深深吸引,两年后葛浩文突然开窍想学汉语。虽既非语言学家,也不是亚洲研究专家,但却产生了学习汉语的冲动,后竟发现自己很擅长学习语言。这个在台湾学习汉语的经历竟为他后来从事汉英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也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二)学习汉语
葛浩文最初以请家教上门的方式学习汉语。所请老师教法别具一格。用葛浩文的话讲,就是在情景中学习语言,用类似教小孩学说话的方式讲授,注重语言的实际运用,与现在学生学习语言的方法不大相同。或许这也不失为是一种好的学习方法,但葛浩文觉得不适合自己。于是跟家教学习约一年半,他从海军退役,开始了较为正规的语言训练。
当时台北师范大学的普通话培训中心(the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s Mandarin Training Center)接受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实行一种军事化而非学术性的管理方式(a non-scholastic way)。葛浩文在此学习汉语的时间至少在一年半左右。期间学过小学、初中教材,也学习过专业的报刊阅读。据葛浩文讲,这期间的学习并未使他达到能够使用汉语进行严肃写作的水平。后因父亲病危,不得不中断学业,返回美国。但他坦言在台湾学习汉语的那段时间成了他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三)与许芥昱及诗歌学习
1、鲜为人知的师生情
返美后的葛浩文由于缺乏从事研究经验,不知自己该做什么,后在长滩州立学院老师的建议 下去旧金山州立大学读硕深造,在那里遇到了“第一位真正的老师”许芥昱(Kai-yu Hsu)先生。葛浩文对许评价颇高,称其为一个了不起的人(a remarkable man)。实际上,许芥昱不仅在汉语学习方面引导葛浩文,而且直接影响了他博士阶段的深造,甚至包括他之后所从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事业。
在Jonathan Stalling的采访中,葛浩文详细回忆了他跟许芥昱相处的几件事情。以下是葛回忆自己第一次拜见许先生的情景:
He sat me down and he said:“What’s your background?”I said: “I can’t say; I’m embarrassed to say.” He said:“Forget background, what are your interests?”I said:“I’m not sure.” He said:“What do you do? What can you do?” I said: “I can speak Chinese.” And he said:“Let’s hear it.” And so I did. He said:“Can you read?” And I said:“A little.”“Can you write?” I said: “Not at all.” He said: “We’ll take you.”
So I went into his class and I stayed there, got a master’s degree — somehow they gave me a master’s degree after a year and a half.
从上可知,许芥昱为人非常谦和,行事利落,识才方面眼光独到。对于当时几乎一无所长的葛浩文,已在亚裔华人圈颇有影响的许芥昱竟毫不迟疑地将其收下,并在葛毕业后推荐给当时任教于印第安纳大学的柳无忌先生(Liu Wu-chi)。
其次,葛浩文还深情回忆了许芥昱赠送他书法作品的一件小事。博士毕业,葛浩文在旧金山母校谋得一职,工作第一天在走廊里见到许芥昱:
In the hallway he asked me:“Can you still intone that poem?”I said, yes, and I did the whole thing.“Not bad.” The next day on my desk was a piece of his calligraphy — he was a great calligrapher — with the fi rst fi ve characters of that poem.
葛浩文回忆自己当时看到这些字,已经忍不住泪水盈眶。且多年之后再次谈及此事,也是不禁满眼含泪,因为他说这是许先生给他“一辈子的礼物”(This is the gift of a lifetime)。
不幸的是,三、四年后的一天,一场暴风雨冲走了许芥昱先生所住的“天堂路”(Paradise Lane),人们最终没有发现他的尸体。几天后,在UCLA任教的葛浩文被召回,在许芥昱的追悼会上致词,背诵了那首唐诗以表道别。在采访中,他这样回忆:
So I — they called me back — and I spoke at his memorial. I said: “I just don’t know what words to say, he was my teacher, he was my mentor, he was my friend, he was my benefactor.”
葛浩文用“老师、精神益友、朋友、和恩人”来相容许芥昱,足见两人间深厚的师生情谊。而这些是葛浩文之前很少(或从未)对外提到过的。
2、诗歌学习
硕士期间,葛浩文通过学习逐渐理解汉语拼音并进一步加强对汉语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在欣赏中国诗歌方面他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许先生的熏陶和影响下,葛浩文对中国诗歌特有的音律产生了浓厚兴趣,这对他日后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处理文学作品中诗歌、戏剧等的翻译有不小帮助。
因许芥昱的缘故,葛浩文在研究生阶段所选课程均和中国古典文学相关。许先生在文学教育方面沿袭中国式传统教法:让学生通过吟诵、背诵来理解古典诗词;在学问研究方面却是西方式的:让学生以研讨会交流的形式进行学习。葛浩文在许先生的示范下吟诵五言、七言唐诗,之后博士阶段师从柳无忌研究元曲,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与元剧有关。元剧中很多唱词的音韵和诗歌极为相似,这些都归功于许芥昱教给他对唐诗、元宋早期散文等诗词韵律鉴赏的知识(Obviously Kai-yu had put that in my head.)。而据葛浩文讲,他日后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时之所以选择莫言作品最多,翻译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莫言作品中,声音成了表现主题的重要手段和内容。而葛浩文对于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声律特性则非常着迷。
三、汉语学习和文学翻译的一些问题处理
葛浩文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起了积极的意义。他的译文常给人一种简洁、整齐和音律美的感觉。在这次Jonathan Stalling的采访中,葛浩文以最近翻译的莫言《檀香刑》为例,畅谈了他在处理小说翻译中的大量戏剧唱词和其它语言叙述体方面的重要问题。
1、戏曲唱词的翻译
莫言创作小说时喜欢利用复杂的结构形式,《檀香刑》每章都以一段山东地方戏 — 茂腔(猫戏)独唱开始,且随着故事发展,戏曲吟唱往往和故事情节相互交织,声音效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檀香刑》几乎是莫言作品中戏词出现最多的一部。在小说“前言”,莫言说自己童年记忆中两种声音在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火车和猫戏。而火车声在作品中多已是一种象征意义,猫戏则多表达在声音层面。对于每章开始部分的唱词,葛浩文的基本译法是:第一稿先尽量捕捉戏词意思,然后参照作者“前言”部分的叙述加深理解。对于并非表达意思,仅为达到某种音律效果,配合特殊乐器演奏的戏曲唱词,葛浩文采用不同译法,重现或创造相同效果。译文中,葛浩文有时用正式语言(formal English translations),有时使用叙事散文(narrative prose),并以斜体表示。他坦言自己早期学习元剧的经历为翻译提供很大帮助。翻译猫戏中叙事性唱词(narratives)时,葛浩文说自己将自己当观众,却也像演员似的常常唱了起来,以此剥离“词壳”(vocables),“打捞”重要信息,获取听觉而非视觉上的重要声调和音韵(the sound and rhyme),最后将这些转换为英语中具有诗歌、戏剧、唱词性质的语言。与章首的戏词不同,章节中的戏词加入了很多其它因素,所以翻译时须在意义、韵律、形式和听觉等各方面寻求一种平衡(That is the balance of meaning versus metrics, versus form and aurality and all that.)[4]。葛坦言有时会因中英押韵的巨大差异不得不做出某种牺牲,但基本做到确保戏曲唱词中音律正确、韵脚保持,尽力做到让目标读者感觉译文听起来很棒[4]。
有关文学翻译中戏剧、诗歌等的内容和音律谁主谁次的问题,在采访中葛浩文以自己翻译小说《北京娃娃》的一个故事来说明。他回忆《北京娃娃》中有段“校规校纪”,都是些长短整齐、豆腐块样押韵的文字,葛浩文说为此曾费神很久,最后想到英语里类似结构的一首诗,各行字数相同,每行都押韵,就像小说里面的校规一样。所以他在翻译时借用了这首诗歌。因觉得原著并非正统严肃小说,不必逐句费心思量,所以如此处理,只需将作者意图传达即可,有时作品声音的传递、词语的跃动感(jumpiness)等对他来讲更为重要。
事实上,作为听众有机会欣赏到专业戏曲演员表演莫言《檀香刑》的采访者Jonathan Stalling也盛赞葛浩文的翻译,认为其巧妙地串合了小说中叙事者的念和主角的唱,时而哀 伤,时而狂怒,传达了原著戏曲的精髓,体现了译者的精打细磨和创新,完全达到了文学作品应有的效果。
2、语言叙述体(narrative register)的翻译
葛浩文在采访中讲到他在翻译每个伟大作家作品时尤其关心的另一问题 — 语言的叙事体。
首先他对叙事体进行了如此解释:“We speak at different levels. In terms of word choice and sentence structure,in terms of tonality, in all kinds of ways, we speak, all of us speak, at different levels.”实际上,叙事体泛指因出身、教育、经历、性格、场景等差异而形成的具有阶级差异的语言体。在《檀香刑》中,莫言塑造二十世纪初中国不同阶层使用不同叙事体的人物形象。这对中国二十世纪包括二十一世界受过教育的读者来说理解起来并无大碍,但葛浩文讲他在翻译时,考虑到美国出版商和美国读者,不能用维多利亚时代英语进行翻译,以免给读者造成两种错觉:小说人物是讲英语的中国人;和小说人物是讲着让人无法理解英语的中国人。因此只能小心措辞以再现小说人物性格。同时他坦言虽然费了很大功夫,甚至花费了比莫言创作更长的时间做翻译,但在人物语言叙述体方面并非都做到了一一体现差别,或许还需日后再做调整。如小说中有一个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国官员和他那个没受过教育的情妇的语言。他说两种语言不在同一个水平上,但也不能相差太远,使一个极其文雅一个极其粗俗。葛浩文承认误解和误译在所难免,令人敬佩的认真态度和谦虚作风可见一斑。
3、方言和特殊方言的翻译
众所周知,方言翻译是任何文学翻译当中比较棘手的问题。在这次Jonathan Stalling的采访中,葛浩文也谈及此问题,并给予较为详细的解答。
葛浩文讲,对于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出现的诸多方言,在英语为母语的目标读者缺少同类语言和相应“社会语言之镜子”(socioli nguistic mirrors)的情况下,为尽可能传递作家意图,译者有时不得不创作一种变异的语调形式(forms of differentiation of tone)。而对于某些特殊方言,如莫言作品中出现的体现性别差异的农村方言,葛浩文称一般还是会参考英语中的性别语言进行翻译,尽管常常感觉很难脱离汉语(尤其是仅有汉语才能达到某种效果时)去调整方法将其用英语翻译出来。[4]
对于常规正式方言如何进行翻译?首先涉及到方言的鉴别问题。葛浩文称他通常得利于自己很好的语言功底,如对闽南语的了解和较大汉语词汇的掌握。碰到不理解的语言,首先猜测会不会是方言,然后借助一些工具如字典和谷歌、百度等网络工具进行查询。有时会遇到特殊方言,比方言还方言(more idiolect than dialect),如某些地方对某些词语的特定重复使用,使其变为方言的一部分。也有小说中的特殊方言仅是作者的口头禅(tic)或对某些语言的特别使用而已。葛浩文提到贾平凹小说中到处可见的西安方言和陕西山区话,常让自己苦恼。那么如何处理这些呢?是否将这些方言翻译成一种听起来很酷的、说唱的、陌生的或其它语言呢?葛浩文认为在更广或全球化层面上讲,答案并不唯一,有时肯定,有时否定,有时两者兼而有之,主要取决于小说本身。译者倘若能找到恰当的俚语式、地方语式或稍古语类或不常用的词语表达同样的意思,当然会使用,如果实在不能找到,便不用了。因为毕竟源语读者看小说时并不在意这些方言,目标语读者也不在意,译者就没必要折磨自己。[4]
四、结语
作为学者,葛浩文虽是以学习古典汉语、中国古典文学为始,之后开始研究和翻译萧红及东北作家群,最终却从文学评论转移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的道路上,直到现今,可见他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愈来愈多的关注和关心[5]。他一生丰富的经历和学者身份转变造就了独特的汉学家身份。所以在从事中国文学对外翻译时,葛浩文更能以一种不同方式和目光审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问题。他对目标语读者的关注、译者主体性的认识、中国翻译文学命运的判断等,甚至对于中国作家如何才能在全球背景下进行创作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走近葛浩文,了解他的学者经历往往更能直接理解他的翻译目的和手段,也更能帮助中国文学接近世界读者。
[1]Goldblatt,Ho ward.The Writing Life[N].The Washington Post,Sunday.April 28,2002.
[2]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9(6).
[3]舒晋瑜.十问葛浩文(汉学家)[N].中华读书报.2005-08-31.
[4]Stalling J.The Voice of the Translator:An Interview with Howard Goldblatt[J].Translation Review,2014,88(1):1-12.
[5]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J].中国翻译,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