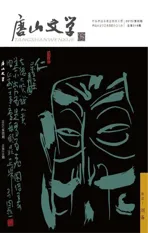精神还乡——评迟子建新作《群山之巅》
2015-11-17刘皓
刘皓
手头是迟子建的新作——与《额尔古纳河右岸》相隔十年问世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小说很显然是作家的一次精神返乡之旅。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长篇小说领域进行多种艺术尝试——内容上涉猎东北少数民族生活与东北城市生活、形式上每本长篇小说都变换叙事手段——之后,作家再次回到自己的艺术起点,即以一种诗性、晓畅的纯粹的语言,和一种紧凑、精致的小说结构,讲述一个情节不算难懂的东北故事,总体来说,作品的确呈现出几乎是“百炼成钢”般的美好的审美姿态。在这部新作中,作家摒弃了一切“花哨”的手段——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日记体叙述、动物第一人称叙述,等等,呈现给读者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之下的一个山区的故事。没有浓墨重彩的形式的遮盖,故事的本相便以洗尽铅华的方式自动展开在读者眼前。
一
小说主线极其简单。松山脚下龙盏镇屠户辛七杂的养子辛欣来回家后不久,即用斩马刀斩杀养母,后又偷光家用,并强奸了镇上人视之为神仙的侏儒女安雪儿,藏入深山。安雪儿之父,当地法警安平对辛欣来展开追踪,最终在松山深处将辛欣来归案。
尽管不具备我们在自“现代派”以来常见的所谓“花哨”的小说形式,《群山之巅》却并非在形式上毫无“机心”的作品。迟子建最初步入文坛时,正像当时大多数作家一样,是以中短篇小说写作而“出道”的。中短篇小说最讲求结构上的精致,如何在讲述一个故事时为读者布下“陷阱”,设下“饵料”,都需要作家精心营造,好的中短篇小说如园林如楼阁,处处有景,处处“惊喜”。获得过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的迟子建更是深谙此道。
小说并不是一开始就将血案展现在读者眼前,而是以这样的描述开头:“龙盏镇的牲畜见着屠夫辛七杂,知道那是它们的末日太阳,都怕,虽说他腰上别着的不是屠刀,而是心爱的烟斗。只要太阳好,无论冬夏,辛七杂抽烟斗是不用火柴的。他的两个裤兜,分别装着一面拳头般大的凸透镜,和一沓桦树皮。抽烟斗时他先摸出凸透镜,照向太阳,让阳光赶集似的簌簌聚拢过来,形成燃点,之后摸出一条薄如纸片的桦树皮,伸向凸透镜,引燃它,再点燃烟斗。”在这第一个出场的人物身上,有一定阅读史的读者可以辨析出的人物特征是:闲散,适意,更主要的是,人物已经浸淫于生存环境中较长时间,与之水乳交融、相处融洽。
这样的“淡化”的散文式写法,不是作者为拖延叙述时间而采取的手段,而是一以贯之。小说中每一人物出场时,均采用这一写法。先“点名道姓”,再指出其出身、职业、主要故事,不疾不徐,娓娓道来。如此写法,使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登上文坛、八十年代贡献出一批优秀短篇佳作的小说家汪曾祺。《故里三陈》、《职业》、《异秉》等作品多以此方法引读者“入彀”。早在2002年的访谈中,很少接受访谈的迟子建就曾畅叙自己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家的看法:“张爱玲的语言比较老旧,读起来却很有滋味;萧红语言俏皮幽默,少一些沧桑。当下很多小说的故事很好,但语言不好。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语言都比较不错,有一种古典优雅的风格。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家,是和这种精湛的语言密不可分的,说到底,文学毕竟是语言的艺术。……王安忆的语言魅力,耐琢磨。有些走红的作家的文学语言比较差,那么即使他的故事再新颖,我也不承认他是一个成功的作家。” 不难看出,作家对汪曾祺的作品是怀有强烈好感的。而形式上的散文化,就是迟子建与汪曾祺在创作上不约而同的选择 。散文化的写作,是迟子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步入文坛开始即十分偏好的艺术手法。“从小说文体的特点看,它不可能和话剧一样,人物一上场就是紧张连续的矛盾冲突,它可以更散淡、更随意一些。小说中的风景描写、心理描写等等看似边角废料,却在作品中起到很有成效的作用,能够使作品有特别的意味。考察屠格涅夫、川端康成的小说,如果去掉了散文化的东西,故事本身就失去了耐人寻味的韵致。也许我是女性作家的缘故,我的小说叙事节奏比较舒缓,形成了散文化的倾向。”
这里要捎带提及迟子建对汪曾祺式写法的发扬。“散文化”、“慢”、“淡”、“抒情诗化”等等,是汪曾祺这位于1980年代以特殊风格重出文坛的短篇小说家的标签。在这位小说家的笔下,苏北水乡风俗、人情以白描的方式跃然纸上,作家语言白而熟,不带一丝火气,人物也安于自己一番和谐融洽、颇有情趣的小日子,而这种创作特色,在今天这个语言伧俗化、网络化甚至“火星”化的写作时代至为难得。汪曾祺式的写作在21世纪的学术界之所以依然时常被作为创作典范处理,也与这种“难得”的精神密不可分。迟子建在这部小说中“反其道而用之”,反将这种散文化的处理用作对东北松山根深蒂固的恶的揭示,其间也许渗透更多的是作家对人类的悲悯情怀。而正是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了久已熟悉的迟子建。可以说,如果没有形式上的散文化,小说中密布的恶所带给读者的冲击未免尖锐,审美价值也就荡然无存了。
二
小说如伞骨状打开,龙盏镇各具面貌的人物如线上珍珠纷至沓来,让读者见识到了他们的恶。这其中有制度的恶:陈金谷从作龙山林场场长开始即动用职权,给诱骗来的妹夫唐汉成许以职位,不仅如此,他的一家,原来是盘根错节的地方一霸,其弟陈银谷是青山县副县长,小舅子和小姨子一个是松山地区财政局副局长,一个是计生委主任,其一儿一女,一个是松山地区公安局副局长,一个在林市环保局工作。如此令人错愕的裙带关系式腐败,恰恰见出迟子建的巴尔扎克式观察力:在我国边远或落后地区,这种裙带式腐败积久不变,树大根深,几乎形成地方的“世袭制”管理。而且,越是边远,越是落后,这种状况只怕越是严重。对“官员腐败”的表现不止于此,迟子建接着在“格罗江英雄曲”里格外点出了龙山深处的罪恶权肉交易——女大学生唐眉与女护士林大花主动作驻军部队团长和营长的情妇一事,林大花在本章主人公安大营的注视下与营长过了一夜,第二天即获得重金酬劳。
不仅有制度之恶,更有时代之恶。小说揭出一桩三十年前的罪恶,作为伞状展开的故事的“伞柄”的关节部分。这便是七十年代知青返城时刘爱娣与陈金谷的一段情史留下的“孽债”——原来辛欣来是陈金谷的私生子。令人唏嘘的是,这一往事的“挖掘”,起因竟是陈金谷双肾衰竭时亲子陈庆北不愿提供肾源——这又是个人之恶了。
小说中对个人之恶与群体之恶的表现,力度并不亚于对制度与时代之恶的表现。作家对人性的洞察力在这里作一总结。杀母、强奸、临终理容师偷情而使残疾丈夫在家中因煤气中毒憋死,等等,随着小说进程而一一聚散,难得的是迟子建并没有止于对恶的浅层摹写,而是将之变化为一个值得寻味的道德论题,如对“理容师偷情致残疾丈夫死亡”一事,对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内心的苦闷、对夫妻之情的极度渴望表现得一丝不苟,使得读者不敢下夺命签,不敢错勘贤愚。同样矛盾纠结的是小说中龙盏镇镇长唐汉成斗羊场上下黑手一事,唐汉成因保护山林自然资源考虑,不愿工程师开发本地的煤资源,于是对发现资源的单枪匹马的工程师痛下黑手,买通斗羊师李来庆指引斗羊攻其不备。如此种种的恶,其中包含的况味,是不容细辨的:推算故事主体发生的时间,由“三十年前”的知青孽债一事可以得出应是新世纪初,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小说中表现的农民个体与群体形象还与鲁迅、蹇先艾、王鲁彦时代的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极其相似。山之深、恶之深、恶之久,便更添触目惊心。
“冲动的善良人”,是小说一个细心的设置。除了上文中提到的镇长唐汉成,小说中的法警安平,也是这样的类型。在死刑改为注射行刑后,法警安平负责押送枪支上缴,途中饮酒后却提枪奔下火车追凶,最后发现不是辛欣来,因失职而被病退。小说借由这类人物的设置,更将解决难题的希望彻底掐灭:原来浸淫在山区的非理性文化之中太久,所有人都抽身难退,没人有能力实施自救。无论是被统一进伦理美的“人的价值”,还是在被统一进法制的公民的价值,悉数崩坏。换句话说,无论是作为康德所要求的道德律令的自律的道德,还是作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公民道德,在这“也就七八十万人口,却有一个法国那么大的面积,境内群山环绕,无人区多,好隐蔽”的东北松山地区,都成为根本无力实现的对象。 积聚三十年,根深蒂固、不能撼动的恶,便进一步在这种反复书写下呼之欲出。
三
也许是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余震”效应,迟子建在这部新作《群山之巅》中依然采用了人类学的视野对笔下人物进行观照。
为小说开头的人物辛七杂,其惊人创举就是绝育。绝育的原因是,他是日本人与逃兵的儿子。这一情节耐人寻味:辛七杂不久即接受抱养辛欣来,引发全篇的主线也随之而来。“种”的问题于是进入到读者视野。这种“一代不如一代”式的接力,不仅在汉人辛家是如此,在小说中唯一“善”的代表——鄂伦春族老英雄安玉顺的安家也是如此:安家第三代就是智障的侏儒安雪儿。当我们对比松山一霸、盘根错节的陈家时就不难发现,原来陈家代代健旺,陈庆北体检年年合格。处心积虑经营龙山关系的陈家香火旺盛,不过是随意落脚此处的辛家,和男随女愿前来落户的安家,却遭受重创,致使我们联想龙山为“可诅咒的群山”。同时,风葬习俗,绣娘最后的坐骑——白马,安雪儿的替罪者身份,等等,也不难使我们联想到《金枝》中一些饶有兴味的段落 。
叶舒宪在《文学人类学教程》中“重建文学人类学的本土文学观”部分中这样写道:“面对一个世纪以来西化的‘文学'和‘文学史'观念的误区,需要清理批判的三大症结是:A.文本中心主义 B.大汉族主义 C.中原中心主义”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人类学之风吹过之后,人类学视野一直以零星的方式出现在作品中,而不再形成创作风潮。《群山之巅》中的人类学视野的出现,不足以构成对小说主题的冲淡,却足够形成一层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潜流,与小说叙事的“散文化”一起,冲刷着作品的河床,使之形成道德主题明晰、人文色彩浓郁、神秘气息挥之不散的多重审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