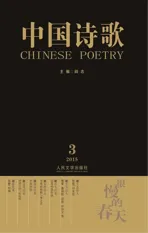栖居龟岛
——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及其诗集《龟岛》
2015-11-15白阳明
□白阳明
栖居龟岛——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及其诗集《龟岛》
□白阳明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1930-)是二十世纪美国当代诗坛著名生态诗人、生态思想家、翻译家、禅宗信徒、环保主义者,被称为“仍然没有垮掉的垮掉派诗人”。斯奈德出版过很多诗文集,他的诗歌大多体现保护自然环境与维持生态平衡的主题,因此他被称为“生态诗人”。斯奈德以其杰出的生态写作、关于人与环境的深邃思考引起美国文学界、思想界的广泛关注,更以不遗余力的环保呼吁和身体力行的环保实践赢得了人们的尊重。除了生态主题外,斯奈德的诗歌中融入了多种文化,它们相互交织形成了诗人独特的风格。斯奈德从第一部作品《砌石》(Riprap,1959)开始,就在尝试整合东、西方文化之精华。他跨越了东西方古老文明以探寻生态多元和文化多元的互动,挖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生态智慧,力求古代人类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汇贯通。斯奈德在诗歌创作中收录了不少非主流文化、边缘文化的声音,承认这些少数传统的主体性,让不同的声音参与对话,促进多元文化、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他努力从这些异质文化中找到新的文学创作源泉,并与美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跨文化现象,从而形成一种极富活力与创造性的文化思想。斯奈德一生与中国文学与文化相伴,给予中国文化极高的评价,所以,中国学者数十年来一直关注和研究斯奈德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研究成果。
1930年5月8日,加里·斯奈德出生于美国旧金山。诗人出生的时候,正是美国经济的大萧条时期,斯奈德一家的生活也因此变得非常的拮据。正是为了一家人能够顺利地度过那段难熬的时期,在斯奈德来到这个世界的十八个月之后,诗人全家都搬到了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地区,在那里斯奈德一家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生。正因为家人从事农业的关系,童年的斯奈德可以说是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他的身边还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就是这样的“山水田园”式的生活,让斯奈德与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1951年斯奈德毕业于里德学院,获得文学和人类学学位,后来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东方语言文学,并在此间参加垮掉派诗歌运动。此时他翻译的寒山诗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致使他东渡日本,出家为僧三年,醉心于研习禅宗。1969年回到美国后,斯奈德与他的日本妻子定居于加利福尼亚北部山区,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1985年他成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同时继续广泛地游历、阅读和讲学,并致力于环境保护。2003年他当选为美国诗人学院院士。
斯奈德出版的诗文集,主要有《砌石与寒山诗》(1959)、《神话与文本》(1960)、《僻野》(1968)、《观浪》(1970)、《龟岛》(1974)、《斧柄》(1983)、《留在外面的雨中,新诗1947-1985》(1985)、《没有自然:新诗选》(1993)、《无终的山水》(1997)、《加里·斯奈德读本》(1999)等,其中诗集《龟岛》获得了1975年度普利策诗歌奖,斯奈德本人1997年同时获得伯林根诗歌奖和约翰·黑自然书写奖,2008年获鲁斯·莉莉诗歌奖。
斯奈德是“垮掉派”目前少数仅存的硕果之一,也是这个流派中诗歌成就较大的诗人。但是,跟“垮掉派”其他诗人的张狂相比,他显得比较内敛,其作品的风格也有所不同。他是清晰的沉思大师,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翻译过寒山的诗,所以喜欢沉浸于自然。在大自然中,他既是劳动者也是思考者,因此他的诗“更加接近于事物的本色以对抗我们时代的失衡、紊乱及愚昧无知”。
1974年,斯奈德政治观点最鲜明、生态思想最丰富、影响力最大的一部诗集《龟岛》(Turtle Island)出版了,并在1975年获得了普利策奖。斯奈德认为这部诗集“第一次用文学展现了生物区域观的概念”。因为这部诗集的缘故,“龟岛”在七十年代迅速成为北美洲的代名词。在斯奈德的眼里,北美洲不是欧洲人发现的一块处女地,而是古老的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土地。斯奈德使用这个词,表达了他对古老文明的向往,对北美洲这片大陆生态环境的关注,对人类与野生世界共生存的一种理想。按照他的生态学,地球不是一块石头,而是一个生命体,由一个巨大的长寿无疆的乌龟支撑。“龟岛”的概念来自于土著印第安人的神话,是对北美洲的称呼。作为人类学研究者和森林看守人,斯奈德不仅是从书本上认识印第安文化,更是近距离与印第安人相处过。龟岛这个名字蕴藏着古老的智慧和重新栖居的新的动力,它向重新回归北美大陆的斯奈德敞开了一扇门,从中他看到了西方人结束漂泊生活,找到回归土地、重新栖居的道路。虽然广袤的龟岛卧在那里已经成百上千万年了,但斯奈德却第一次有了回家的感觉,所以,栖居龟岛也成为斯奈德创造新神话的第一步。
关于诗集《龟岛》,评论家们有一些争论。在《加里·斯奈德的龟岛:观察者和预言家的难以调和》一文里,查尔斯·阿尔提艾瑞对《龟岛》予以否定性的评价,认为《龟岛》没有斯奈德之前的作品让他满意。他从美学观点出发,发现《龟岛》中的斯奈德从早期观察者的角色转变成一个预言家的角色,而预言家的角色使得《龟岛》中的很多诗歌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共鸣”,这些诗在他看来并不成功,他建议斯奈德坚持做一个“观察者”,而不要企图预言美国的未来。但是,帕特里克·墨菲却认为,阿尔提艾瑞不满意这些诗的真正原因更可能在于,他听到有人对斯奈德诗中的生态预警表示赞同,他因此表示担心:“我们必须注意看清斯奈德在两类读者中难以抉择——一类是必须通过‘学习花朵’才能幸免于难的幸存者,另一类是可能阻止灾难发生的普通大众。”墨菲认为这个问题阿尔提艾瑞并没有阐述清楚,即为什么在同一部诗集中,一些诗不能得到第一类读者的认可,而另一些诗不能得到第二类读者的认可,这显然还需要更清晰的解释。伯特·阿尔蒙的论文《斯奈德近期诗歌中的佛教思想与能量》也在很多问题上回应了阿尔提艾瑞对《龟岛》的批评。这篇论文重点论述了佛教对斯奈德诗歌叙述方式的影响。阿尔蒙指出《龟岛》从斯奈德之前的诗歌中白描自然的倾向,转向叙述性的、甚至是解释说明式的诗体,较少像以前那样描写自然进程的流动,而这是因为“社会批判,以及要与美国西部达成协议的愿望优先于万物舞动之纹”,这也就从侧面回应了阿尔提艾瑞提出的斯奈德从观察者到预言家的转变问题。另外阿尔蒙还解释了斯奈德是怎样在不违背佛教基本戒律的情况下表达谴责和愤怒的。
《龟岛》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熊果树”收录有18首诗,第二部分“喜鹊之歌”共有31首诗,第三部分“写给孩子们”有9首诗,第四部分“大白话”收有5篇散文。熊果树是加州和俄勒冈山上都很常见的一种灌木丛,喜鹊不仅是山林里常见的鸟,也是一种喜庆的象征,斯奈德在反对环境污染的同时,更多地是赞美大自然,“熊果树”为诗集定性,“喜鹊之歌”为诗集定调。“写给孩子们”当然不是儿童诗,其中的诗歌和理念都是写给未来、属于未来的。至于“大白话”,诗人使用日常用语,他的诗歌都可以看成是大白话,但这个大白话有其自然的节奏和内在的韵律。在诗集的最后一篇《关于“对诗人而言”》的散文里,斯奈德阐述了他对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名句“能源是永久快乐”的理解,他认为“过于发达的当今世界面临能源危机,而石油和煤矿是古代植物锁进自己细胞的太阳能源,只有树木和花草能够使它们更新……还有另一种能源,接近于太阳能,但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是内在的力量,即“快乐”,活着和认知的快乐……同时生活在世界之内和世界之外的惟一途径是思维,即诗歌……给出的越多,能够给出的也越多,当石油和煤矿都竭尽时,这个内在的力量还存在……”
简约的语言,简练的意象,精准的描述,对原始生态的钟爱,对词语“声音”的注重,这些都是他诗歌的特点,受日本俳句的影响显而易见。但更为突出的特点是一种敏锐以及对生命的感悟,和一种原始而恬淡的、炫目而纯净的野性美。《龟岛》里印有几个汉字,比如在《光的作用》之下是“”,在《母亲大地:她的鲸鱼》后面是篮子里一颗“心”。也有以图代文,比如《鳄梨》下面是莲花上一尊佛像,这首诗起句是“达摩就像一枚鳄梨!”鳄梨又名牛油果,比《圣经》中的苹果渊源还要远,是生命之果。《龟岛》的语言除了纯朴之外,还给人一种梦幻的感觉,诗人在看,在听,在闻,在触摸,也在冥想。大自然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不信看看植物的结构、花纹,动物的步态、语言,生命的神奇太多,永远探索不完。斯奈德在语言结构上也有很多尝试和创新。他的诗,第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不完整的句子,即句子片段,这些片段式语句不仅带来跳跃的语感,也带来想象的空间。第二个特点是注重声音的巧妙运用,利用同音、谐音达到意象转换,转换之后让读者突然发现奇妙的内在联系。第三个特点是简单句子之间穿插歌咏般的复杂句型,复杂句型带来的是繁复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缤纷的思维与更加缤纷的野生世界自然结合的产物,比如《魅》这首诗,就有着非常复杂的语言结构,它表现的也是神话中复杂的自然界现象,但这种复杂句式并不繁琐,而是像一股山泉一样不断地转弯,绕着岩石流下来,一泻千里到你脚下。
《龟岛》从开篇到结尾是一个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过渡,也是从诗歌到散文的过渡,这个过渡不露痕迹,以最自然的形式表现内容。正如他所相信的,思维是自然物质的第六元素,所谓形而上也就是形而下,即威廉姆斯的“thingness”。附录中第五首诗的最后两行,可以看作是斯奈德的哲学理念、环保主义、诗学以及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学花朵/轻装上路”。
在诗人斯奈德创造的新神话中,强加给自然和大地的国家消失不见了,北美大陆被重新唤为龟岛。这颇似神话但又不是神话。生物区域主义的视角让斯奈德看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整片大陆由一个个区域、一个个地方构成,我们每个人都扎根于地方,全体人扎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龟岛;如果我们有重新栖居的勇气和决心,想要在龟岛上重生,那么就开放全部感官,敞开心灵,去了解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明确自己栖居者的定位,以一颗虔诚、谦卑的心去积累知识、亲身实践;最终我们将能听到来自土地的声音,而大地也感受得到我们的脉搏,我们与大地互相接纳了。这样,神话就得以从虚无缥缈的天空落脚于广阔厚实的土壤。在这之后,斯奈德关心的便是人类怎样在这片土壤上耕耘劳作,世世代代幸福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