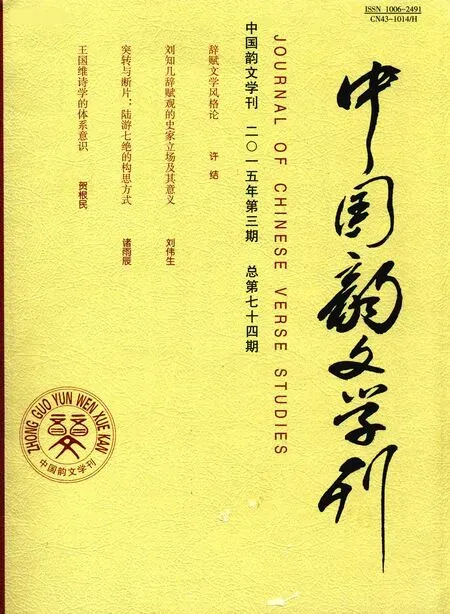鉴赏的眼光——评张宏生《读者之心》
2015-11-14王秋萍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2491(2015)03-0114-03
*作者简介:王秋萍(1986- ),女,江苏东台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和明清文献。
文学作品的鉴赏是一门见仁见智的学问。不同的读者因为学识积累、人生阅历、性情喜好等方面存在差异,对同一作品的阅读感受必然不同。西谚有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无怪乎西方读者理论的创始人姚斯·伊瑟尔索性将读者的地位推尊到极致,认为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方可实现。读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中,对读者的重要性的认识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已提出。《文心雕龙·知音》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知音善赏,然而知音难逢,刘勰的慨叹正说明了读者在赏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则认为“诗无达志”,并提出“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得之”(《薑斋诗话》),肯定了读者的解读可以是自由的。而清末的谭献更将王夫之关于诗之解读的观点延用到词的解读中,其《复堂词录序》云:“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至此,读者被赋予了开放的阐释空间,读者在作品流传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西方文学理论中有所谓“接受美学”之说,和谭献所论“读者之心”,本质上正是一致的。赏析,原本就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古典诗词鉴赏之风盛行一时,各种鉴赏辞典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鉴赏热是文化热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对古典文学的普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不少鉴赏文章来看,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千篇一律,仅仅满足于字词或句意的疏通,而缺少问题意识,因此也就未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开放的阐释空间。
2013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张宏生先生的《读者之心———词的解读》,似乎是对以往鉴赏热的一种延续,实则体现了非常独特的个人特点。该书以谭献所论“读者之心”为题,其对开放的赏析观念的推崇不言而喻。
不同于此前不少鉴赏文章“依注解书”式的品读,张著将问题意识融入词的解读之中,书中每一篇基本上都涉及文学研究中的某一个问题。这种贯穿全书的问题意识使得其赏析文字在做到浅显易懂的同时,又不失学理性。张著所涉猎的范围涵盖文学、历史、文化乃至科学等诸多方面,不可谓不广。作者每每能抓住适合的切入点,在不经意间将赏析引向所要讨论的问题,其间的衔接自然而不突兀。在探讨问题的深度上,作者也把握得恰到好处,意在将这些问题以简单介绍的形式呈现给读者,以启发读者深入思考。书中着重探讨的问题,如相反风格共存一体、诗词之别、词的寄托、词的翻案等等,无一不是学术前沿所关注者。最为典型的是词的比兴寄托,这是词学阐释学中的一个重大论题,也是张著中多次探讨的核心问题。比兴寄托之说由常州词派的开山祖师张惠言提出,是基于儒家经典阐释传统而建立起来的词学阐释理论。张著《喻意的专指及其能指》一篇从苏轼《卜算子》一词的解读切入,梳理了比兴寄托解词这一阐释思路的发展脉络,继而引出了关于常州词派阐释理论的相关探讨。从张惠言,到谭献,再到陈廷焯,他们的阐释观念如何在传承中又有新的拓展、如何互相补充以形成自足的阐释体系,对此书中都有明晰的揭示。然而理论归理论,以比兴寄托之法解词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存在不少困难,书中对此也有较多的讨论。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判断具体作品中是否含有比兴寄托之意。《作者所给与读者所得》一篇分析了晚宋黄孝迈《湘春夜月》一词是否含有比兴寄托之意;《秋蝉声态与亡国之痛》《至情追求与文化情怀》两篇分别剖析了王沂孙《齐天乐·蝉》、谭献《蝶恋花》两首词作中比兴寄托之意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历史真相与文本读法》一篇则以宋征舆《蝶恋花·秋闺》的被误读为例,分析了原本非比兴寄托之作如何被赋予了比兴寄托的内涵,提醒读者以比兴寄托之法解词需要警惕出现误读的可能性。该书在文本鉴赏的大框架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比兴寄托”问题进行探讨,寓论于叙,深入浅出,可以启发读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进行进一步思考。
就鉴赏方法而言,张著擅长通过比较来捕捉词人们的词心。该书的跋文对张著比较之法的运用有精当的归纳:“将一首作品与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相比、与同时代作家的作品相比、与前代或后代作家的作品相比;在相同主题或风格的作品之间比较,在不同主题或风格的作品之间比较;将境遇相同的作家作品作比较,不同境遇的作家作品作比较;既将女性作家的作品与其他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又将女性作家的作品与男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可见作者是有意识地运用比较的方法来鉴赏作品的。比较的眼光,往往能产生新奇的发现。譬如,异中见同。《飞入七宝楼台的野云》一篇将吴文英的《高阳台·落梅》一词与姜夔《暗香》《疏影》相对照。在文学史上,姜、吴并举,论者多言其清空、质实之别。然而书中通过比较见出姜、吴二人借咏梅而写别情的相同思路,并指出吴文英学姜夔而又有自己的创造。再如,同中见异。《易安情怀与湘蘋心事》一篇将明末清初的女词人徐灿与李清照相比较。徐、李二人均为著名的女词人,李经历了宋室南渡,徐经历了清兵入关,对国破家亡都有极深刻的感受。两人身世和时代相近,徐词对李词也的确多有继承。然而同中有异,徐灿因为丈夫陈之遴入清再仕,有亏品节,其作品中多了一层难言之隐,这种特殊的感受是李词中不可能有的,也正是徐词的独特之处。没有比较,对作家和作品的认识容易孤立和片面。比较的眼光,能够为文学作品的鉴赏发掘更多的话题,对作家、作品以及文学史的认识也就能更为丰富而立体化。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书中所呈现的诸多为作者所独有的奇思妙想正是“读者之心”最鲜明而贴切的诠释。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提到,书中的不少篇都是在教学中获得的灵感,“在讲课时喜欢由此及彼,不断跳跃,往往灵机触发,一些未曾预期的想法络绎出现”。《月亮想象与诗思神悟》一篇可以说是作者众多神来之作的代表。在这一篇中,文学与科学走向了融合,从屈原的《天问》到庄子的《逍遥游》,再到辛弃疾的《木兰花慢》以及魏源的《呼月吟》,作者以其飞动的联想能力发掘出了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科学质素,并参之以现代科学的探索成果,令人耳目一新。如果说屈原、庄子、辛弃疾、魏源等具备非同寻常的想象和“神悟”能力,那么作者对这些作者的想象和“神悟”能力的理解和发挥也值得大书一笔。灵感和想象可以说是赏析之学最为可贵的素养,是一种阅读的再创造,也是作者综合学养的体现,这一点,书中都有非常具体的呈现。
在文学史上,宋词堪与唐诗比肩,是一代之文学的杰出代表,其历史地位基本上已经明确,而清词的地位和价值则尚处在不断讨论中。对广大读者而言,清词比宋词要陌生得多。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张著并未因此而在宋词、清词之间有所轩轾,以迎合大众的趣味,相反书中对清词的有意推崇显而易见。张著意在突显清词题材之广、词境之阔,这从所选清词的篇目可明白看出。如顾贞观的两首《金缕曲》之以词代书、传达感人至深的友情(《友情之深与词境之阔》),胡成浚的《玲珑四犯·壬戌六月悯旱》之书写旱灾民瘼(《大旱书写与悲悯情怀》),江开的《渡江云》之反映鸦片战争(《拈大题目和出大意义》),孟传濬《沁园春·老将》之抒发老将壮怀(《老将情怀与边塞志意》),黄遵宪、潘飞声《双双燕》之表现国族忧患(《罗浮想象与醒觉意识》)。张著选录了这么多清词作品,既有一般清词选本中的名篇,也有甚少为人提及之作,似乎是在引导读者建立起对清词的多方面认识。至于清词在艺术上的独创之处,以往的词史往往非常推崇朱彝尊,可能是要对此给出具体例证,张著在清代词人中对朱彝尊的讨论独多。《金陵怀古的传承变化》一篇评价朱氏《卖花声》一词,较之前代诸多金陵怀古之作,虽气局稍逊,却以真切具体见长,由此肯定清代词人在宋词取得极高成就的影响之下另辟蹊径的努力。《物之表现与格之高低》一篇以《春风袅娜·游丝》一词为例,指出朱氏跳出了前人咏物而寄托的樊篱,专门从咏物的角度进行创造,符合文学审美的多样性要求。《虚写的境和实写的情》品评《桂殿秋》一词,对词中虚写之妙、以极淡之语写极深之情的手笔大加赞赏。《眷恋之情与难言之隐》一篇由朱彝尊与妻妹冯寿长之间无法明言的恋情点出朱氏特有的情感体验在《静志居琴趣》中表现为写艳情而呈现清新之风的特色。朱氏作为清代词坛的大家,他的词作在表现手法上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清词的独特性。书中对于清词的肯定与揄扬,诚然与作者三十年来在清词领域的潜心研究密不可分,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试图将清词及其研究前沿的学术成果推介给广大读者,以见出清词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有着良苦的用心。
当今学界,文本解读似越来越不受重视,而就词的解读而言,其受重视程度又比诗和文低很多。试将《文史知识》1981年创刊以来其诗文鉴赏栏目所刊登的鉴赏类文章作一统计,诗的鉴赏文章数目远远超出词,文的鉴赏文章数目也比词要多。张宏生先生作为词学研究的大家,在从事词学文献整理和词学专题研究之余,仍心系词的具体文本解读,或者正是对这一状况的有感而发。张晖在跋文中对该书的写作目的有所评述,认为作者此书不仅仅是要为古典诗词作品的鉴赏简单地招魂,更是作者想通过自己的赏析之作为鉴赏正名。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因此,我们也期待,随着该书的出版,学界能够对古典诗词的鉴赏有着更加多元化的思考,涌现出更多的能够体现时代感的鉴赏文章,以促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
责任编辑雷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