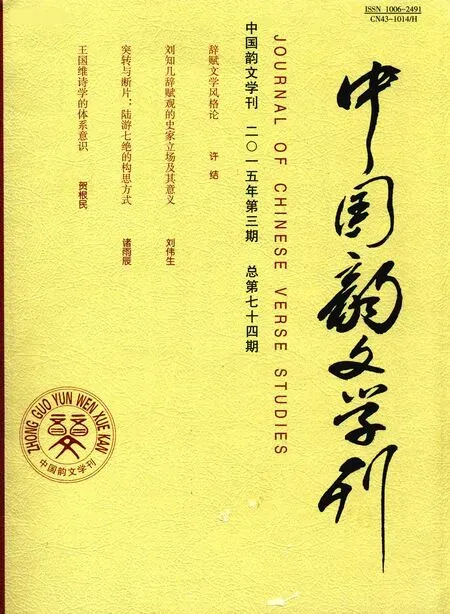高丽、朝鲜诗歌创作中的《春秋》“华夷观”
2015-11-14卢鸣东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2491(2015)03-0055-06
*基金项目:本文为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优配研究金资助项目成果,项目编号:“HKBU245913”。
*作者简介:卢鸣东(1969- ),男,广东东莞人,哲学博士,副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经学。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诗歌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揭示了诗歌的社会功能,千百年来,一直为文学创作所遵从,从而往往使得诗歌与时代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这一传统不仅在中国本土绵延不绝,即使对中国周边的国家,也同样影响深远。本文拟从古韩国诗歌创作中所体现的“华夷观”对此略作探讨。
历经三国、高丽至朝鲜时代,古韩国长期接受中华文化输出和影响,通过文化整合、累积和沉淀,由受容者渐次成为发扬礼义文教的传播者,并在文化身分上比拟中华,以之识别华夏周边的四方邻国。从高丽、朝鲜的文献资料中可见,两朝文人认为自箕子东渡以来,朝鲜半岛已在其文化身分上出现了转变,由原来的东夷属国,跃升成为华夏文化的旁支,消除了因种族差异和地域隔阂所造成的夷狄标识,由此也呈现出华夏文化地理版图的对外扩张。原载于《孟子·滕文公上》的“用夏变夷”是两朝文人阐释其文化身分之所以转变的思想理据,有关论说在他们的诗作中比比皆是,其中所体现的《春秋》“华夷观”,有助于揭示古礼传播与华夷分辨的问题关键,对探讨儒家礼仪文化在古韩国的发生与发展有着一定的价值。
一《春秋》“大一统”与华夏政权的正统
高丽、朝鲜两朝,韩国儒生注解《春秋》“大一统”经义,主要沿袭汉代《公羊》学说。朝鲜开国功臣权近(1352-1409)指出“一以奉天而立万世之法,一以尊王而示一统之大,二义并行,不相悖也。” [1](P4)认为“大一统”要义是“奉天立法”和“尊王一统”,与《公羊》学说无异。《春秋·隐公元年》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指(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代公羊学家何休曰:
文王,周始受命之王。……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王(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2](P28)
何休认为“王”是指周文王,他是华夏国君,其受命于天,不是继位于人,其法应天而行,以为天下施教,因此,华夏政权及其颁授法制的合法性皆得到天的确认,受到华夏臣民尊敬,以及四方夷狄推崇。朝鲜晚期,奇学敬(1741-1809)奉朝鲜纯祖之命注解《春秋》经义,指出“《春秋》第一大义即首揭‘王正月’也。……然则《春秋》之作,明一王之统,正万世之法。” [3](470)在《公羊》学说指导下,《春秋》“大一统”专指华夏汉族的正统,而周边四夷只是礼义教化的受容者,称臣于华夏政权。诚如权近的《醉后述怀》诗云:“三韩自古礼义邦,世修侯度尊中国。” [4]P59)
《春秋》“大一统”之义历经千载,在历史现实中难免受到冲击。北宋以来,中国北方已逐步被夷狄侵夺,靖康蒙难,南宋偏安江左,至辽、金衰微,蒙元崛起,赵宋败亡,华夏地区已尽落入胡元手中。汉族政权旁落,华夷秩序紊乱,历历在目;高丽、朝鲜两朝文人虽然未能改变中原政局的状况,但心存《春秋》“尊王攘夷”之义并没有因此磨灭。陈澕(高丽明宗至高宗年间),高丽朝人,号梅公,其于高丽高宗时担任使节,出访金国,回国后撰写了一首五言绝句,题为《奉使入金》,云:
西华已萧索,北寨尚昏蒙。
坐待文明旦,天东日欲红。 [5](P48)
《梅湖公小传》有陈澕于“高宗乙亥”,“以书状官如金还” [6](P35)的记载,从中得知他出使金国是在高丽高宗二年,即1215年。诗中“西华”指南宋,国势日值衰颓,故谓“萧索”;“北寨”谓金、蒙两国。陈澕出使金国同年,即金宣宗三年,蒙古成吉思汗攻陷金国首都燕京,此时呈现金国渐弱,蒙古益强的政治形势,造成中国北方昏暗不明的局面,而高丽置于两国对阵交锋之间,难断取舍,致令作者心存忧虑。诗末作者寄望中原及早重返昔日文明局势,扫荡腥膻,使礼义文教重申(新)传入朝鲜半岛。
朝鲜正祖八年(1784年),陈澕的《梅湖遗稿》经整理后刊行,其中收录了《奉使入金》诗。1783年11月,黄景源(1709-1787)为此书写《序》,兼评论此诗曰:
公能以高丽陪臣,知先宋之为中国,而蒙古之为夷狄,蔼然有《春秋》之义,岂不贤哉! [5](P25)黄景源赞赏陈澕是一位贤臣,因其仅以东藩属国的身分,尚能心存《春秋》华夷之辨。至于他出使金国的原因,吴载纯(1727-1792)在《跋》中解释曰:
盖公以书状官,奉使金源时诗,而其旨激昂悲咤,千载之下,犹令人击节而兴慨也。呜呼!当是时,中国陵夷,戎狄迭侵,而《春秋》“尊王”之义漠然不复闻矣。然窃尝怪以三韩礼义之国,犹且靡然服从于胡虏,终至结婚、媾通、朝宦,而不知耻,及读公诗,然后始知其时士大夫未尝无忍痛不得已之心,特畏约力,不能有为也。 [5](P120)
吴载纯指陈澕出使金国时,《春秋》“尊王”之义已荡然无存,他慨叹自中国汉代开始,朝鲜半岛的马韩、辰韩和弁韩便自居礼义之国,反观后起的高丽王朝慑服于夷狄,与辽、金两国修好,可谓不知耻辱。然而,他从《奉使入金》一诗理解,此实为当时政治形势所迫,高丽限于国力,不得已才作屈服,因此对此不应深责。值得留意的是,黄景源、吴载纯生活在朝鲜英祖和正祖期间,二人撰写《序》、《跋》之时 ①,清人入关已过百年,中原自蒙元之后再次失守于夷狄,华夷易主亦已成定局,然而,他们对华夏正统的一腔热诚,通过他们解读此诗中可表露无遗。
事实上,朝鲜文人对于汉族王朝正统地位被夷狄所取代的历史,显得痛心至极。朴兴生(1374-1446),号菊堂,朝鲜初年文人,1423年出任昌平县令,曾上呈《拟礼曹请女服华制笺》,倡议朝鲜中央应该执行妇女服饰从华制的政策,贯彻“用夏变夷”的精神。他还在诗文中揭示《春秋》“尊王”之义,其七言绝句《有感》云:
用夏变夷当戮力,叹今思古恐灾身。
自从秦汉经唐宋,劲节精忠问几人。 [6](P328)
诗人回顾中原政局剧变,汉族王朝饱受夷狄威胁,至宋室更被蒙元取代,因而有如此感叹。他归咎中原之士皆未能如岳飞般尽力抵御金人,精忠报国,慨叹对于夷狄的肆意挑衅,能负隅顽抗的中原之士毕竟不多,各人仅存自保的心态,致令华夏政权旁落夷狄。
虽然蒙元占领中原是不能改变的史实,但朝鲜文人坚守《春秋》“大一统”之义,并没有把蒙元视为正统。关于华夏政权的历史,明代曾先之节略十八种史书材料,撰写成《十八史略》,之后余进在此基础上加入元史,上承宋史的正统,称为《十九史略通考》。余进的《十九史略通考》东渐以后,备受朝鲜重视,诚如郑澔(1648-1736)曰:“而东俗亦深尊尚。” [7](P376)但对于余进不用“变例”记录元代历史,违背了《春秋》“大一统”之义,郑澔便深表不满。《史略补要·序》记载:
窃有所未晓于余氏所定《元史》一篇也。夷狄猾夏,据有中土,此实天地间一大变故也。作史者所当特用变例,以明《春秋》“大一统”之义,而今乃以胡元之统,混然接承于赵宋之统,何哉? [7](P377-380)蒙古一统华夏,据有中土,政权和土地归于一统,按形势理应承接赵宋正统,但郑澔认为“所谓‘正统’云者,乃历代帝王之统,非统合天下之统。” [7](377-380)正统与否不在于土地广狭,例如东周雒邑、蜀汉益周,南宋临安,所领土地不足与蒙元相比,但他们皆为汉族血嗣,华夏胄裔,具有“帝王之正统”。元代因以夷狄身份入主华夏,虽能“统合天下”,独霸中原,却不禀受“帝王之正统”,故他认为当用“变例”把其蒙元帝位定性为“闰位”,而把其帝统定为“绝统”,表示汉族正统自宋代以后中断,胡元不得继承。
二《春秋》“夷狄进至中国”与华夏文化身分的认同
《春秋》“大一统”学说在明代开国初年别具政治意义,自明太祖登基以后,祀孔庙、行释奠、祭宗庙和制礼乐等儒家礼仪活动相继展开,尽显其以恢复儒家礼义文化的政策,作为在“攘夷”以后重新建立汉族政权一统的表征。洪武元年(1368)二月,明太祖颁布诏令,规定汉人“不得服两截胡服,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 [8](P9)这政策反映明室革除胡俗的决心,强调华夷之间的分野。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再次颁下文教诏令,其旨是为了振兴华夏礼义之风:“于戏!用夏变夷,风俗之所由厚,哀穷赈乏,仁政之所当施。因时制宜,与民更化,期臻礼义之风,永底隆平之治。” [8](P9-10)明太祖承用“用夏变夷”这千古传诵的圭臬,作为重返汉族礼义传统的文教指导纲领;在中原境内而言,这是要革除蒙元以来遗留下来的胡人风尚,重新衔接汉族文教的正轨,而对于境外四夷来说,便是接受华夏文化的熏陶,启迪王化,提高本土礼义文教的水平。
元朝灭亡,高丽王朝为了修补朝中亲元势力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与蒙元残余势力划清界线,消除明太祖对高丽政治立场的疑虑,曾多次派遣大臣出访明朝京师,贯彻明室“用夏变夷”的国策。高丽晚年,郑梦周(1337-1392)曾多次以高丽使节身份访明。高丽恭愍王二十一年(1372)三月,“高丽国王王颛遣密直同知洪师范、郑梦周等奉表贺平夏,贡方物,且请遣子弟入太学。” [9](P486)此行目的之一是上表要求明室准许高丽子弟入读太学,接受华夏礼仪文化。之后,郑梦周于高丽辛禑王十年(1384)和十二年(1386),先后访明并上奏表笺至明太祖,“请便服及陪臣朝服、便服,仍乞蠲减岁贡。” [10](P609)表中并称高丽朝服遵从华服,落实“用夏变夷”制度。据此,明太祖劝告高丽君臣不得寄以空言,必须切实执行,其云:“及用夏变夷之制,在彼君臣力行如何耳。” [10](P609)这番评论反映朝鲜半岛虽然遵行明朝的文教策略,坦然有进至中国之心,惟明太祖依然抱持怀疑的态度,对此没有表示充分的肯定。
明太祖对于朝鲜半岛落实华夏礼仪文教的判断,与郑梦周等高丽、朝鲜文人的看法存在一定距离。郑梦周《冬夜读〈春秋〉》曰:
仲尼笔削义精微,雪夜青灯细玩时。
早抱吾身进中国,傍人不识谓居夷。 [10](P595)
诗人以夜读《春秋》为题,论述孔子赋予《春秋》之微言大义。诗中“早抱吾身进中国”句撷取《公羊》“夷狄进至中国”之义。《春秋·庄公二十三年》曰:“荆人来聘。”《公羊传》曰:“荆何以称人?始能聘也。”何休注曰:“《春秋》王鲁,因其始来聘,明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礼,受正朔者,当进之,故使称‘人’也。” [2](P302)楚地位处华夏南僻,以蛮夷身份犹能向鲁国行朝聘之礼,接受王化熏陶,因此,《春秋》进楚为“人”,以明褒进夷狄之义。
在地理版图上,古韩国位处东夷之地,远离中原,但从礼仪文教程度而言,高丽、朝鲜文人认为自箕子东来,设八教,教民礼乐,朝鲜半岛已脱离夷狄种族的身分,其礼义文教自可比拟中华,冠有“小中华”、“海外中华”、“礼义之邦”等美誉。成文浚(1559-1626)曰:“我东自箕子东封以来,用夏变夷,立我民极。逮于周末,余敎已泯,流风已微,而孔圣犹发欲居之叹,则我东之进于中国久矣。” [11](P214),郑梦周诗中之所以有“早抱”之义,正因为他相信早自箕子受周武王分封朝鲜以后,朝鲜半岛已遵行“用夏变夷”的制度,于文化程度上早已“脱夷”。《论语·子罕》曰:“子欲居九夷。”又“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12](P204)因此,诗人“居夷”之叹,不是指实际的地理位置而言,而是认为若然从礼义文教上衡量,朝鲜半岛早已不属于蛮夷之一,但“傍人”不辨,致视之为夷地。
朝鲜半岛的努力终明太祖在位年间(1368-1398)也没有被肯定,直至明惠帝四年(1402),即朝鲜太宗二年,明室始派鸿胪寺行人潘文奎出访,授以“九章之服”,以表扬朝鲜太宗能以四夷之国的身分,自进礼义。敕书曰:
敕朝鲜国王李讳,日者陪臣来朝,屡以冕服为请,事下有司,稽诸古制,以为四夷之国,“虽大曰子”,且朝鲜本郡王爵,宜赐以五章或七章服。朕惟《春秋》之义,远人能自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今朝鲜固远郡也,而能自进于礼义,不得待以子、男礼,且其地逖在海外,非恃中国之宠数,则无以令其臣民。兹特命赐以亲王九章之服,遣使者往谕朕意。呜呼!朕之于王,显宠表饰,无异吾骨肉,所以示亲爱也。王其笃慎忠孝,保乃宠命,世为东藩,以补华夏,称朕意焉。[13](P226)
明惠帝为了褒奖朝鲜进于中国,履行《春秋》大义,破格授予明代亲王等级的“九章”衮冕服制,虽然,夷狄最高爵位仅称为“子”。《礼记·曲礼下》曰:“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郑玄注曰:“入天子之国曰子,天子亦谓之子,虽有侯、伯之地,本爵亦无过子,是以同名曰子。” [14](P223)可见,夷狄进至爵位,最高不过于“子”。至于《春秋》“文备七等”,包括“州、国、氏、人、名、字、子”(庄公十年) [2](P266-269),据此进退夷狄,爵位也不过于“子”。因此,朝鲜以夷狄国,却获赐予明朝亲王服礼,阐明其身分已远高于夷狄之上,这在明室方面而言,已经是礼待备至。
三《春秋》“王鲁”与华夏文教的传播
文教水平,也务必贯彻“用夏变夷”的制度,于境内尽显华夏文化的风尚,华、夷两者相辅相成,以彰显风化天下的儒家达旨。
这种以华夏为中心的礼义教化秩序,其义在《公羊》学说的“《春秋》王鲁”中更见完备。何休注曰:“《春秋》王鲁,以鲁为天下化,首明亲来被王化”,《春秋》假鲁地为天下京师,作为王者教化的中心。《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何休注曰:“内其国者,假鲁以为京师也。” [2](P701)这说明王化从内而外,远及夷狄,而能够上朝王鲁的夷狄国,《春秋》皆褒进之。《春秋·僖公二十九年》曰:“介葛卢来。”《公羊传》曰:“介葛卢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何休注曰:
据诸侯来曰“朝”。不能升降揖让也。介者,国也;葛卢者,名也。进称名者,能慕中国,朝贤君,明当扶勉以礼义。 [2](P476-477)
“介”是东夷国名;“葛卢”是介国国君的名称。介因是夷狄国,故不能行升降揖让之礼,基于其能慕王化,到鲁行朝聘之礼,故《春秋》使其由“国”进升至“名”,称之“介葛卢”,以示褒进。据此,《公羊》“王鲁”学说予以“用夏变夷”的实践意义,以“夷狄进至中国”的具体途径,刻划出儒家礼义文化由华夏传播至四夷的线路。
明太祖立国以后,中、朝使节互访频繁,高丽、朝鲜两朝使节通过朝贡、进献、慰问和谢恩等名目,出访明朝,在为了巩固中、朝宗藩关系的同时,也秉持“以小事大”的慕华心态,撰写表笺,上请明室允许并下赐如服饰等礼仪制度,表明朝鲜半岛对华夏文教的向往,及释出全国上下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意向。例如洪武十九年(1386)12月,李崇仁(1347-1392)以高丽贺正使的身分出使明朝,上请服制,其于《请衣冠表》曰:“颙望宠锡之加,伏望扩兼容之量,推一视之仁,遂使夷裔之民,得为冠带之俗。” [15](P616)表中尽显高丽欲从华制之心迹。李崇仁有《送张学录使还京师》一诗,亦能反映此心态:
韩邦傍海近蓬瀛,矫首时时望帝京。
使介忽来传诏命,君臣齐出拜恩荣。
中原礼乐通夷俗,盛代文章属老成。
万古虞书精一训,君应持此佐升平。 [15](P563)
诗中的“矫首”比喻朝鲜半岛君臣对中原礼仪的殷切期待,他们从千里之外遥望中原国都,期盼明室使者早日传来诏命,赐下华夏礼乐文明。此外,诗人运用“中原礼乐通夷俗”一句,揭示礼义文教自中
华夏地区是儒家礼义文教的发源地,被视为文明教化的传播中心,相对中心边陲的偏远地区来说,彼此的分野在于文明程度的高低,而由此在华、夷地理位置上所呈现的文教优劣状态,决定了儒家礼义文化由内而外、由近至远的传播向度,使华夏地区成为礼义输出的起据点。在这文化地理标识的指导下,华、夷彼此之间在文化交流上并不对等:历代处于华夏地区的汉族政权,尽管有朝代兴替的变动,它们俱以传播礼义文教为己任,以此作为处理华夷外交问题的一贯政策,而四夷礼接华夏,致力提高礼义原所出,之后传播至四夷之地,这正切合《春秋》“王鲁”说所确立的王化轨道,藉此尊崇中原政权是礼义文教的唯一颁授者,并确认华夏地区是礼义文教的发源地。
以华夏地区作为礼义教化普及的开端,这也是明朝立国初年,中、朝双方士人所秉持的一种共识。高丽禑王十一年(1385)九月,明使臣周倬奉旨出使高丽,逗留期间得与成均馆大司成郑道传接待;他认为郑道传虽然“博于学问”,“议论弘达”,能“授领成均,为学者师”,但仍要来华亲身体验华夏文教。周倬曰:
吾尚期宗之上朝天庭,观风云际会之盛,识江山海宇之广,接衣冠文物之威仪,见城郭兵甲之富庶,睹制礼作乐之大典,则宗之之襟度学问识趣,超越乎今之器局。上可以歌扬皇风圣泽于无穷,下可以训国之俊秀,考古论今,忠君事亲,以尽用夏变夷之化。[16](P545)
郑道传(?-1398),字宗之,一生曾两次出访明朝。第一次在高丽禑王十年(1384)七月,其“为书状官,从圣节使郑梦周入朝京师,请承袭及谥” [16](P527),目的是请求明室承认禑王的王位及赐谥号给恭愍王;第二次在恭让王二年(1390)六月,“如京师贺圣节” [16](P529),此为明太祖祝寿。因周倬于1385年才出访高丽,此时郑道传已于早一年上访明朝,而此事周、郑二人于高丽论接期间应该得悉。此外,周倬此《序》职称郑道传为“成均司成”,此为郑氏于1387年由李成桂推荐,“召拜成均大司成” [16](P527-529),至第二次出访明朝前已迁为“政堂文学”,因此,周《序》当写成于郑道传任大司成至第二次出访期间。我们可以理解,周倬热切期望郑道传不一而足,应再亲身到华夏,接受礼义熏陶,尤其大司成主要职责是教授成均馆生员,此为培育高丽全国人才之所在地,故传道者当勤于访京,“慕王化”,“以尽用夏变夷之化”。
《春秋》“夷狄进至中国”的必然性决定于华、夷之间礼义文教程度的高低,若然这种文化秩序出现逆转,文化传播的向度便会出现偏离。朝鲜文人金诚一(1538-1593),号鹤峰,其《偶书》诗曰:
礼义何尝有夷夏,存能为夏去为夷。
莫将生死渝吾节,此道从来不可离。 [17](P48)
诗人认为夷、夏之分没有固定常态,他们的分野仅取决于礼义存否。因此,尽管是居于蛮夷之地,当地人们依然可循礼而行,不受居住环境限制。赵絅(1586-1669)曰:
昔延州来季子生长句吴蛮夷之国,所闻者击剑斗狠之事,……若季子者,天性与道合,虽不事礼乐,自是礼乐中人,而其曰:“习于礼。”则必是于礼有时习之功,岂待聘上国而后始行礼也,虽处蛮夷之时,亦能自拔于流俗,而用夏变夷也明矣。 [18](P520)
延州来季子是指春秋时期吴王寿梦的第四子季札,因封于延陵,故又称号延陵季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吴子使札来聘”一章,记载季札曾出使聘鲁,观周乐,从中分辨出周室政治兴衰。赵絅认为,季子虽然成长在吴国荆蛮之地,耳濡目染尽是蛮荒风土流俗,但其习礼有常,不必等待朝聘华夏诸国,也身怀儒家礼义教养。这样来说,华夷之民不必出访华夏,也不必等待王者化及,自身居于夷狄之地也能自变风俗,用夏变夷。
韩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至中国则中国之。” [19](P147)事实上,朝鲜文人认为朝鲜半岛早已进至中国并成为华夏的一分子,具备礼义文教的素养,因此,当清人入主中国后,个别文人便重新考虑中原政权在夷狄的统领下,华夏地区是否还存在师法意义?而礼义文教又是否还在华夏地区发生?姜再恒(1689-1756)溯源周代礼教形成的历史,对比朝鲜当前的文化形势,探索华、夷地理位置与其礼义文化的发展关系:
议者曰:“东西异宜,南北异治,越南蓟北,土俗迥别,况吾东方之地,隔海万里,风气与中国殊异,岂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乎?不如因其俗而为之制,保其国而安其民,策之上也。”是盖不然。夫子不云乎:“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昔者不窟窜于戎狄之间,公刘居豳,太王居岐,蠢然西夷之俗,而文王用夏变夷,成周家八百年郅隆之治。东方虽僻远,殷太师以范畴八政之治,垂教于后世,至于今名儒辈出,号为学者皆知宗孔氏,崇礼义,尊中国,攘夷狄,贵王贱伯之道,则其俗尙之美,可以侔拟于中华,而非四方诸夷之所及矣。……海外偏小之邦,善政美化,虽不能远及中华,而中华有王者作,必来取法,所谓王者师者,其不在兹乎。 [20](P361-363)
姜氏认为,周代发迹在华夏西面,虽处于西夷风俗,亦能开启八百年文教礼治的基业;朝鲜与中国相隔千里,兼位处九夷之地,然而俨如成周一般,无损其礼义文教的传承,并已在其土壤上孕育出不少名儒学者、宗孔载道之士,其礼义风尚自可比拟中华。可见,朝鲜文人面对清人掌管中原,汉族政权旁落的现实,遂从确认其华夏文化身份入手,变迁昔日以中原地区为文化本位的意识,并在礼义文教的转播上,提出从师法华夏到取法东方的文化地理转向。
四结语
在地理科学的测量上,由经纬度所组成的坐标系统,准确地标示出地理空间的所在位置,这种测量带有绝对的位置性,与由华夏礼义文教所形成的文化地理版图不一样。文化地理版图是以文化水平的程度高低,来决定文化轴心与周边文化地理位置的所在,彼此是带有相对性的,它们会因应各地水平的升降,随时变迁。在《春秋》华夷观下,古韩国一直以中原地区为文化轴心,而历代君臣皆以学习儒家礼义文化作为文教策略,他们贯彻实践“用夏变夷”的礼义制度,藉以提升境内华夏文教水平,达致“进至中国”,“脱夷变夏”的期盼。相对朝鲜文人而言,朝鲜半岛自箕子东来以后,已从接受、整合、改良而创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儒家礼义文化,而当清人入主中原,汉族政权再次失守于夷狄,朝鲜文人遂通过儒家文化地理版图的重新界定,以肩负起中国礼义在海外传承的使命。他们的这些思想,体现在各类文字之中,诗歌也是重要的载体之一。